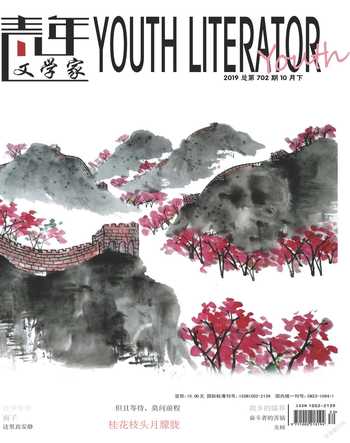从《文心雕龙》看“情”“采”的定义及其关系
摘 要:“情”与“采”作为《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具有诸多争议,刘勰对于“情”的认知更多的是强调其思想纯正,与志合二为一,是一种包含了真善美的类似于儒家理想的存在。“采”是一种美学风貌,包含了由“质”到“文”的整个范畴,是文章的外在形式,却又是自然的产物,“情”正而生“采”,“采”滥则掩“情”。
关键词:《文心雕龙》;情;采;范畴;关系
作者简介:丁雪,女,山东泰安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0-0-02
“情”与“采”作为《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具有诸多争议,传统的观点认为“情”即是情感,“采”就是文采的华丽。“情采论”类似于“文质论”,属于文学文本的内容形式层面。现今学者已经看到了此说的局限性,试图从多角度扩大其内涵,如周振甫先生就将“情”解释为情理,“采”还包括“精理秀气”。本篇论文将从整体出发,以《原道》等多篇作为辅助重新审视《情采》篇中“情”、“采”的范畴及其关系。
一、“情”、“采”范畴论
“情”在《文心雕龙》中多次出现,含义略有不同,如《诠赋》篇中说:“原夫登高之旨, 盖睹物兴情。”此处“情”指人自然流露之情,因外物所感发。《徵圣》篇:“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情采》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此处“情”周振甫先生解释作“情理”,褚春元先生理解为一种审美情感。我们可以将“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对比来看,“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为情造文”指的是作者“志思蓄愤”即有情志怀忧愤,不得不将情感宣泄出来而进行创作,“为文造情”则是“心非郁陶”,为了创作而虚构情感。通过对比可知“情”就等同于“志”“愤”“郁陶”,即作者郁积于胸的情志,它是在性情的基础上多加了“理”或“志”等理性成分,突出风雅之思,此“情”为圣人之情,追求儒家的礼乐理想、政治教化。“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仁、义、礼、智、信为五性,五性构成情文,此亦神理之数,先天形成。由此可见,刘勰对于“情”的认知已经主动剔除掉了无意义的恶的一面,而是强调其思想纯正,包含了真善美的一种类似于儒家理想的存在,将其称为神理之数,则是与《原道》篇贯通,试图从本源的角度为其理论找寻依据。总而言之,“情”无论是作为自然流露之情还是与“理”“志”合为一体的情,对于《文心雕龙》的解读都是较好理解的,我们将其总称为情感也并无不妥,但“采”的范畴则是与我们熟知的辞藻华丽具有一定距离。
采的本义是多色的丝织品,《文心雕龙》中“采”也是引申此义而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文采”,指文章追求对偶、声律、辞藻等外在的形式,多指文辞的华丽,《徵圣》篇:“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圣人的文章内容雅正,文采华丽,雅与实相对,丽即是华,辞之华者谓之为采。“采”可用“缛”来形容。如《情采》篇:“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序志》篇:“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缛即解释为文采丰富。邹奭善于修饰语言,像雕刻龙纹一样,以雕龙来比喻文章成体,则是着重突出了语言修饰的重要性。但是这其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古来文章都是重视语言的外在形式,讲求修饰,但皆是文采丰富吗?像经书这种散行白描文辞怎么能用“采”来形容呢?周振甫先生于是将采的范畴扩大,认为精理秀气也是采,经书虽没有丰富的文辞但却含着精微的道理,有着卓越的才气,这样貌似“采”便可以涵括所有文学形式了,但“精理秀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徵圣》篇末的赞言:“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精理为文”指文章含有精深的义理,与“采”无关,而“秀气成采”指圣人之文,正是由于秀气,故文成异采,“秀气”指圣人文章所自带的灵秀之气,范畴并不清晰,所以认为“精理秀气”就是文采也并不准确。
《熔裁》篇紧接着《情采》篇而来,如果说《情采》篇是“以阐明作家创作的真诚为文、以情驭辞为主旨”[1],提出了重“情”又重“采”的情采观,那么《熔裁》篇则是在创作方法上对于情采观的具体实践,所谓“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我们可以从具体的创作方法实践来倒推“采”的范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矫揉意为把木料弯成车轮,也就是说“采”是需要修饰剪裁的。“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议论精炼,语言简要,这是属于极简略的风格,思想自由奔放,词句铺张,是极繁杂的风格,简练与繁杂适合不同的文章不同的作者,也就是说“采”虽然指文辞的繁缛,但是刘勰也认为“采”也包含“极略之体”,文辞繁缛所以需要删减,而文章也需要善敷,则从反面说明了文辞的简练。无论繁复或简练都是“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采”只是一个“程度词”。
《通变》篇言:“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志合”也就是“通”,即“序志述时”,指这五个朝代的诗歌在内容思想上的皆是顺应时代表达情志之作,“文则”指“变”,即“质”“广”“文”“缛”“丽”。《考异》云:“《易》有‘天则’,见《乾卦》,《书》有‘王则’,见‘无逸’。则,法也,文则,文之法也。”“文则”也就是创作法则,但这里的“质”“广”“文”“缛”“丽”更多的属于在文辞上的区别。我们结合《情采》开篇第一句话“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可以推断,首先这五个时代的文章是圣贤书辞,而圣贤书辞都是具有文采,所以“质”“广”“文”“缛”“丽”中都能看到“采”影子。周振甫将这几个词翻译为“质朴”、“丰富”、“文采”、“辞采”、“华丽”,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个文辞上的渐进关系,从“质”到“文”皆是属于“采”的范畴,“丽”为“采”之极。无论是质朴还是华丽,都可以算作“采”,“采”即是文章的一种外在言辞形式,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風貌。《原道》篇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此处的“文”具有广泛含义,龙凤、虎豹、云霞为“形文”,林籁、泉石为“声文”,有心之器为“情文”。龙凤用纹理彩色来呈瑞,虎豹用花纹来构成丰姿,云霞构成华彩,草木开花,自然界的一切都有丰富的文彩,“傍及万品,动植皆文”中的“文”实际上依靠“采”来立论,或者“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可以换成“傍及万品,动植皆采”。“采”仅仅指一种外在的言辞形式吗?刘勰在接下来论述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言之文也,天地之心。”由此可见,“采”虽表外,但与文章的内在范畴本质相同,皆是自然之产物,所以文章以心为出发点,自然有“采”。
二、“情”“采”关系论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采”是一种美学风貌,包含了由“质”到“文”的整个范畴,是文章的外在形式,却又是自然的产物,而“情”则是类似儒家理想的存在,与志合一,表文章内在范畴,二者并无直接联系,属于文章的两个不同方面。但正如正文中提到的,刘勰用一个词“情文”将二者联系到了一起。“情文”实际上是“情”“文”“采”的融合。“情文,五性是也”“五情发而为辞章”,这里的“文”等同于“采”。“采”的构成方式有三种,五色、五音与五情,五情构成文采,意为情中含采,情感生发而成文章,故圣贤书辞皆具文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情”由仁、义、礼、智、信构成,依旧是一种儒家的理想。刘勰在后文接着指出:“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文质”即是“采”的两种不同程度,刘勰在此明确的说明了“采”附乎“情”,“采”是“情”的产物,只有情志清明雅正,才可以生发文采,驾驭文采。“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情”为“采”之本。“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翠纶桂饵”与“恶文太章”皆是“采”掩盖了“情”。“情”正而生“采”,“采”滥则掩“情”,刘勰一方面承认“采”的必要性和适度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情”本位的主体性,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情”是人最主要的体现,也是产生“采”的根本,归根到底,《情采》篇的主旨,也是刘勰的理想,则是情采自凝,彬彬君子矣。
注释:
[1]王少良.《文心雕龙》“情采”范畴释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1期.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中华书局.2016.6.
[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09.
[3]王少良.《文心雕龙》“情采”范畴释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6(01):86-92.
[4]童庆炳.《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J].江苏社会科学,1999(06):62-66.
[5]胡言会.郭梅.《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情”“采”關系新解[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
[6]刘丹.《文心雕龙》“情采”论之阐释[D].陕西师范大学,2005.010,26(02):5-8.
[7]左刚.“情采”范畴的确立及演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S2):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