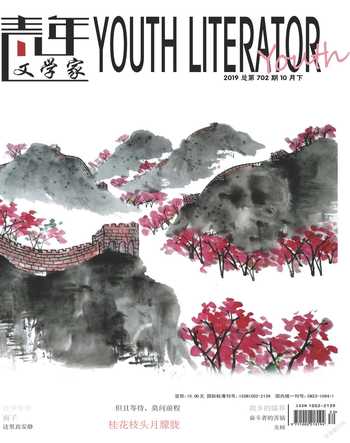美
唐晶
I
黄昏暗寂,伊莲娜坐着,笔直、毫无生气。一双瘦白的手搭在膝盖。她哭着,并未俯面;泪珠饱满,缓缓划过脸庞,深色的眼睛微弱着明暗。
今日她葬下了可爱的母亲,葬下了喧哗的悲伤,葬下她讨厌的蜂拥与现场。葬礼上,及之前,及之后,听着悼词,得节制不哭。她终于独处了,在自己纯洁的宁静里,一切都干净而又严整——悲伤的思绪从眼中涌出,泪滴默然。
伊莲娜之素服,庄重、纯黑,哀伤地裹着她——就像,提醒她正在哀悼日,这冷酷的衣裳无法不外现她黯淡的心。伊莲娜回想起温柔的母亲,——也知道,她生前之生,是和谐、明媚、严整,永远地逝去了。要做任何事之前,伊莲娜都得用冰冷的泪和无可躲的忧郁缅怀过去。
她母亲死时不老。她很美,如来自远古的女神。她举止缓慢、庄重。她的脸庞仿佛笼罩着悲伤的梦想,关于永远失去的或者令人难以理解也无法达成的愿望。其实很久前,就有死亡的预兆,是那阴暗的苍白。似乎厚重的疲惫倾覆下来,盖着宁息在这美丽的身体上。黑发间的根根白丝愈来明显,让伊莲娜奇怪地觉得母亲很快就要成为老妇人……
伊莲娜起身,走到窗前,缓缓推开厚重的帘幔,以看着暮色消失,她不爱暮色。但也从那边,从外面,灰沉昏暗的弱光折磨着她的眼睛,——伊莲娜坐回去,耐心等待夜的黑,也又泣下缓落冰凉的泪。
黑夜终于到来,房间送来了火盆,伊莲娜重走向窗。饱满的黑暗包裹街道。可乞、粗陋、庸俗都得以隐藏于暗夜的静谧,——这悲伤的黑暗中有着某种隆重。伊莲娜站着的窗户这边,已模糊难辨,窗另边的街,星点几盏路灯,和小小的、红砖的铁匠小屋。灯离小屋很远,显得小屋仿若黑色。
忽而铁匠铺敞开向大门成为慢慢滚过来巨大的红色火球,它周围的阴影更厚了——是铁匠铺掠出的焦铁块。伊莲娜灵魂中的快乐被点亮了,她默默地笑了起来——在简单无声的宁静里愉悦忽而闪过。
当黑暗中闪烁着红色花火,伊莲娜讶于自己这忽而的喜悦,原来她仍温柔而虔诚地在她的灵魂中嬉戏。它为什么会来,这喜悦从何而来,让笑照亮刚刚才哭泣的眼睛?美不令人愉悦令人兴奋么?不是每一个美丽的现象都快乐着么?
一瞬間美尽归于黯淡,归于那粗糙世界。它熄灭了,仿佛就是为了让美出现一下,用自己明亮而短暂的光彩使视线饱和……
伊莲娜走出没有灯光的屋子,屋里飘着茉莉和香荚兰的淡香,她打开三角钢琴;隆重简明的曲调从她指尖流出,她的双手轻轻在黑白键中移动。
II
伊莲娜爱一个人呆着,坐在自己房间漂亮的家什之间,它们大部分都是白色,空气中芬芳皑皑,一切都仿佛希冀美就是这样轻盈愉悦。这些淡香来源分别不同:伊莲娜衣服的玫瑰和鸢尾味、帷幔——白洋槐味、开放的风信子慵懒的甜美香气。房间书很多,——伊莲娜经常阅读,不过只读编订的合辑和严谨的著作。
和别人们呆在一起是对伊莲娜的折磨,——人们说谎、奉承、紧张,以夸张和并不欣然的方式表达感受。很多人荒谬而好笑:他们追逐时髦,莫名讲几个外语单词,拥有徒劳的欲望。伊莲娜曾在人群里忍耐,没能喜欢上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只有一个她爱的人,母亲,——因为她总是安静的、美丽的、真实的。伊莲娜真想其他人什么时候都能像这样,他们能明白生活里最重要的——就是美,而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明智体面……
灯亮了,——光芒稳稳当当倾洒下白色。弥漫着玫瑰和杏仁的清香。伊莲娜独自一人。
她用钥匙锁好门,在镜子前点燃一支蜡烛,慢慢,露出自己美丽的身体。
镜子前的她通体白皙而安宁,看着自己的倒影。灯光和蜡烛的光芒在她肌肤游玩,这让伊莲娜愉快。温柔地,似勉强张开的百合,柔软跟着皱巴巴的叶子,她站着。无罪的红玉漫覆在她贞洁的身体。空气里甜腻的苦杏仁味好像从她身体散发出,甜蜜的兴奋折磨着她,一点肮脏的想法都无法扰乱她天真的想象力。她幻想着温柔的、无罪的亲吻,宁静得好像午后的微风,愉悦得好像最幸福的梦境。
温柔地袒露着身体让伊莲娜感到快乐,——伊莲娜不自禁笑着,她安静的笑声在她沉着的、和平的庄严沉默中回荡。
伊莲娜躺在地毯上,轻柔呼吸。从这边,从下面角度看下体的部分很奇怪,她变得更开心了。她笑了起来,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在柔软的地毯上滚着圈。
III
连着好几天,每天晚上伊莲娜都在镜子前品赏着自己的美,——乐此不疲。她房间的一切都是白——在这白中,她的身体闪烁着猩红和暖黄的色调,好比最精致的贝母与珍珠。
伊莲娜抬起双手举过头,踮起脚尖,伸展、弯腰,放松双腿的肌肉。她满足于自己身体的柔韧。她快乐地看着自己,看着双腿紧实的肌肉在柔软的皮肤下弹回收紧。
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赤裸着身体,或站,或躺,她所有的姿态,以及所有的缓慢的动作,都是美丽的。她为自己的美丽而快乐。她赤裸着身体,度过漫长的时间,——她幻想着、欣赏着自己,好像阅读着大诗人美妙的词句……
在精致的银白双耳瓶中盛着芳香的白色液体:伊莲娜在双耳瓶中混合了香液和牛奶。她慢慢举起豌倒在自己高高隆起的胸部上。纯白、芬芳的液滴悄悄落在微微颤抖的粉红肌肤上。百合和苹果闻起来是香甜,这甜味滋滋将伊莲娜蕴在轻盈温柔的云间……
伊莲娜散开又黑又长的头发,散落鲜红的罂粟花在上面。再以镶满白色鲜花的腰带轻裹在她轻巧的腰间,抚摸着她的肌肤。这些芳香的花朵们在她袒露的身体上美丽无比。
之后,她卸下鲜花而又把头发挽做高高的结,裹上轻柔的衣服,用金色的扣子系上左肩。
这些薄薄的亚麻布衣服是她自己缝制的,并没有人见过。
伊莲娜躺在低而宽的床,甜蜜的梦在悄然闪烁——纯洁的爱抚、无辜的亲吻、在甜蜜的露水灌溉着的草地上肆无忌惮地圆舞,在晴朗的天空中,闪耀着欣然安祥的光芒。
她望着自己光滑的双腿——自大腿的曲线从短裙的褶皱下轻轻地跑出来,描画在均匀的暖白皮肤上,这黄的、猩红的色调使她悦目。那膝盖与脚腕突出的边缘、它们侧旁的小窝——伊莲娜凝视着每个细节,用手抚摸着——这给了她一种新的享受。
IV
这天晚上伊莲娜忘记在脱衣服之前锁好门,她赤裸着站在镜子前,高举起双手。
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小脑袋出现在窄小的缝里——是女仆玛卡琳娜。她是个漂亮的姑娘,脸上带着狡猾的表情。伊莲娜看到她出现在镜子里,真是太出乎意料了。她忘了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就一动不动地站着。玛卡琳娜便如她出现那般又默默溜走了。让你觉得她仿佛没有出现过,只花了下眼。
伊莲娜又恼又懊,虽然她几乎都来得及瞥一眼玛卡琳娜,但在她心里,已经看到了玛卡丽娜脸上挤过的不洁笑容。伊莲娜快步走到门口,用钥匙锁好,躺在那低矮柔软的床上,陷入悲伤、混乱的思绪……
她开始陷入折磨人的怀疑……玛卡琳娜是怎么想的?当然,她会去找别人,在那边,她会咬着耳朵,告诉厨师,丑陋地笑着。一阵羞耻可怕地袭向伊莲娜。她想起了厨师马兰尼——面颊红润的年轻妇人,高兴地、带着狡猾的笑声……
此时此刻玛卡琳娜在讲什么?伊莲娜似乎觉得听到轻语:
“我在门缝看到了,那姑娘站在镜子前,跟刚从娘胎出来一样光溜。”
“你说什么呢!”马兰尼喊道。
“上帝保佑她!”玛卡琳娜说,“完全裸体,还扭过来,扭过去,转转这边,那边……”
玛卡琳娜比划着,模仿着,两个人哈哈大笑。愤世嫉俗的、粗鲁话语毫不含糊地清晰可辨;从这些言语和女仆厨师的粗鲁笑声里,伊莲娜,她脸上满是羞愧和懊恼的通红。
她浑身都感到羞耻——它如火焰喷出,燃烧着身体的某种疾病。伊莲娜躺了很久,躺在一些奇怪又愚蠢的困惑中,——然后她慢慢穿上衣服,皱着眉头,仿佛在试图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仔细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
V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玛卡丽娜自控地表现着她仿佛从来什么都没有看到过甚至没有出现过,——这种假装激怒了伊莲娜。因为玛卡琳娜一直都知道,那天以及之前发生了什么,只是伊莲娜才明白,而这让她恶心。当着玛卡琳娜的面穿衣服脱衣服都很难受,接受她的服侍,听她念念碎语,这些话语在水流潺潺声里模糊,溅上伊莲娜的身体,已经震耳欲聋。
有一天,当玛卡琳娜像往常一样念叨时,伊莲娜开始听进去她讲的话,简直让她恼火。
早晨,伊莲娜步入浴室,玛卡琳娜扶着她的手肘,小心翼翼笑着说:
“像您这么可爱的人儿,谁不爱呢!除非他瞎了眼睛,才会注意不到您。看看您的双臂,看看您这双腿!
伊莲娜红了脸。
“拜托您,别说了。“她严厉地说。
玛卡琳娜诧异地看了一眼她,垂下了眼睛,——这只是表演给伊莲娜的吗?——她微微笑了。而这微笑让伊莲娜更加生气,——她紧紧控制着自己沉默不语……
就这样,没有了先前的喜悦,带着一些邪恶的想法与恐惧,伊莲娜继续每天暴露着美丽的身体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她比之前更频繁地这样做,不只晚上,在灯光中,也在白天,拉着的窗帘里。她不会忘记拉好帘幔,以免梁上君子偷听。可这羞耻感让她所有的动作都尴尬起来。
一切都不同于从前,伊莲娜觉得她的身体不再美丽。她寻找着这躯体的缺陷,——孜孜不倦地寻找。她想象出令人恶心的东西,——它们邪恶,会腐蚀、诽谤美丽,仿佛某种远古的蜘蛛网或黏液,令人恶心,无法摆脱。
伊莲娜常常觉得她赤裸的身体沉重地牵绊着别人和可怕的眼睛。虽然没有人看着她,但她觉得,整个房间在看着她,这让她感到羞耻和可怕。
无论是否白天,伊莲娜都觉得光线真无耻,它们锋利地从帘幔后穿过缝隙盯望着、大笑着。到了夜晚,角落里那些没有影子的阴影盯着她,无预兆地漂移,那些闪烁着的烛与灯,似乎是对伊莲娜无声的嘲笑。想到这种无声的嘲笑真令人可怕,伊莲娜徒然地说服着自己,那些只是普通、毫无生气、微不足道的阴影而已,——但它们的颤抖似乎暗示着自己非尘世、不平凡、对人嘲弄的生命。
有时候,会有一个人形出现在她闹钟。皮肤松弛、油腻,牙齿龋烂——脸上一副淫荡的恶心的小眼睛盯着她看。
有时在伊莲娜自己的面容中,她也仿佛在镜子里看到一些肮脏恶心的东西,无法理解它是什么。
她想了很久,觉得应该,是在她悲伤的灵魂的隐秘角落出现了什么不好的東西,她的身体里,赤裸白皙的身体里,颤抖和激动的热浪越来越强烈。
恐怖和厌恶感挥之不去。
伊莲娜意识到她无法忍受这些灵魂中的黑暗了。她想:“人,能在粗鲁和肮脏的想法中活着吗? 那些想法就算不是我想的、不源于我,但那么快就能意识到它们了,不是我想出来的吗?这一切不都是我的、都与我息息相关吗?”
VI
伊莲娜的会客厅里坐着列斯尼琴,一个小伙子,穿着时髦,有点呆板,但非常自恋且对此深信不疑。他今日的殷勤一样对伊莲娜没有任何用,一如既往,可惜了。然而之前她还用对待客人一贯的礼貌来对待他,来获得所谓的“愉快的社交“。今日她冷漠又沉默。
列斯尼琴感到沮丧,懊恼且紧张地摆弄着单片眼镜。他本来想把伊莲娜当作自己的新娘,而她的冷漠对他来说似乎很粗鲁。伊莲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厌倦他谈话中琐碎的鸡毛蒜皮。她本人的表述往往简洁而准确,任何人的过度表达对她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但几乎每个人讲话都这般——慌慌张张、毫无逻辑。
伊莲娜平静专注地看着列斯尼琴,好像看到了一丝与她苦涩思绪类似的共鸣,她意外地忽然问道:
“您爱人们吗?”
列斯尼琴随意咧开嘴笑了,带着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说:
“我自己就是人。”
“那你喜欢你自己吗?”伊莲娜接着问。他耸了耸肩,讽刺地咧嘴一笑,换上种假装的礼貌语气说道:
“人们没有讨好您吗?怎么,忽然这么问!”
显然,他觉得自己因为人们的事冒犯了,伊莲娜有可能就是不爱人。
“怎么会爱上人们呢?”伊莲娜问。
“为什么不会?”他惊讶地反问。
“他们自己都不爱自己,”伊莲娜冷冷说到,“不过也没什么。他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值得爱,不懂得什么是美。他们关于美的认知太肤浅,太庸俗,甚至觉得存在于世都是羞耻的事。他们不想活在世上。”
“但你就生活在这世上啊!”列斯尼琴说。
“那我还能去哪!”伊莲娜冷漠回应。
“人们去哪里更好?”列斯尼琴问。
“对啊他们去哪都这样,”伊莲娜答,唇边拂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列斯尼琴不懂了,这对话令他尴尬,对他似乎很不雅,很陌生。他急忙告了辞离开。
VII
夜幕降临。伊莲娜独自一人。
安静的空气里,她被天芥菜的香草味、樱桃的蜂蜜香气和玫瑰的甜美气息抚慰着。
“按照善良和美丽的理想去生活!生活在这些人群中,生活在这具身体里!”伊莲娜痛苦地想,“不可能啊!如何摆脱人性的粗鄙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人们的侵害!我们都生活在一起,好像一个灵魂到了众多面孔的人群里就萎靡不振。全世界都跟我同一体。但这现有的世界的样子,真让人害怕,——你一旦清醒意识到了,看清了,就发现它不应该是这样,这简直布满邪恶。应该谴责这样的世界,和他一起被执行死刑。
伊莲娜渴望的目光停留在一处闪光的物件上,那是个漂亮的玩具,躺在桌上。
“这就简单了!”她想着,“嗯,这就足够了。”
一把薄薄的镀金双刃匕首,它有时用来切割粘连的书页,手柄上装饰有精美的雕刻。伊莲娜久久把玩着它,这是最近才买的,不是因为需要,——而是被它手柄上不寻常的、纠结的线条图案所吸引。
“一个很棒的死亡工具,”她想著,微笑着。笑容安祥而幸福,思绪清晰而冷酷。
她站起身,匕首在她低垂、裸露的手中闪闪发光,在黄绿色连衣裙的褶皱中闪闪发光。她走进卧室,躺在枕头上,在床板上躺好,放下了匕首。然后,她换上一袭白裙,散发着慵懒的玫瑰花香,拿起匕首,躺在白色床单铺好的床上。白色鞋子挨在床脚,她一动不动地躺了几分钟,闭着眼睛,倾听自己安静的思绪。她脑中一片光明和安宁,那黑暗只折磨着她对尘世和今生的蔑视。
对,——仿佛有人专横地宣布她时刻到了。缓慢而有力地她插入胸部,——笔直正对着那颗跳动着的心,插入整个匕首到剑柄,——死得很平静。苍白的手张开,落在胸前,紧挨着匕首的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