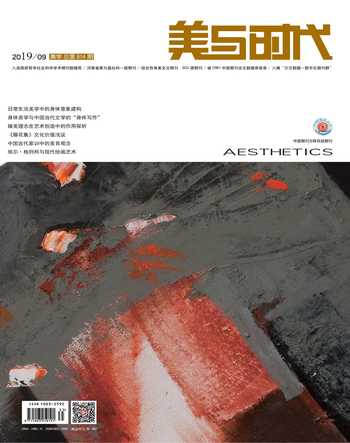穿越时空的诗之镣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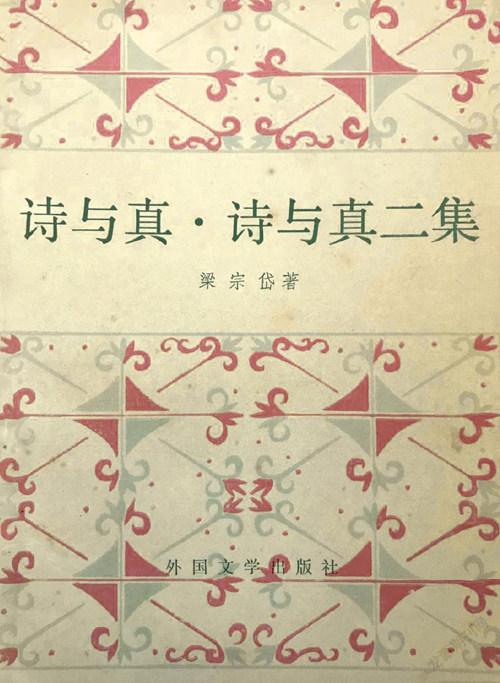
摘 要:梁宗岱通过中国古代诗词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对话,寻到“纯诗”这一创作理想,借以大胆面对现代诗、白话文的浅陋弊病。他的目的不仅在于改造新诗,还在努力解决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至新文化运动后的转变断层问题,为建设“中国诗”的本体出谋划策。他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音乐性、文学与思想、文学与生活乃至与抗战之间的紧密关系,呼唤创作的精思、新格律和新的语言工具。
关键词: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象征主义;纯诗;中国新诗
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界和批评界,梁宗岱(1903—1983)是一位深刻认识到象征主义对诗歌本体意义的理论家,是充分发挥中西比较文学精神的批评家,也是一位周游欧陆列国,与瓦雷里和罗曼·罗兰等西方文学家对话过的中国翻译家和诗人。《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撰写成书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学者将比较文学的方法从西方迻移不久,逐渐产生自觉意识的时期[1]。对于西方深沉博大的诗歌传统、精微凝练的自由诗,以及中国典雅蕴藉的古诗词,特别是脱胎于文言不久的白话和站在“纷崎路口”的新诗,梁宗岱是一位少有的拥有深厚扎实的中西学养和博古通今的宏阔眼界,并具备比较文学实践的意识和条件的文艺理论家。
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两部代表作中,梁宗岱用一种饱含激情与想象的诗性语调,为中国的新诗打造了一副“穿越时空的镣铐”——熔铸西方现代派、尤其是瓦雷里象征主义的运思与构造,并加入中国古典诗律和意境,镌刻上作者在现实中热烈生活的充溢生命。他正是在回忆与梵乐希的亲切交谈、在品味象征主义的滋味和色彩的过程中,思索着中国传统诗学,回忆着陶渊明、李白、姜夔,考虑着最实际、最切近,也是最浪漫的关于中国现代诗、白话和新文学的诸种问题。
有一些学者认为,《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两部作品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国新诗的建设与发展的问题”[2]110。这抓住了梁宗岱作品的重要脉络。但还可以进一步说,它们发展了一种东西方诗歌乃至哲学的对话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现代性如何迎接西方文化挑战,关于新时代的诗歌本体如何构造的问题,便都能得到有益启发。具体来说,梁宗岱认为中国新诗应借鉴象征主义,同时也是中国传统诗歌从哲理到意象的细密转换,紧贴中国文字和白话的音乐性,创造一种深厚丰富的语言工具。在社会中这种语言应该为了大众,改善他们的语言工具以提高其思想,而不是降低语言工具去迁就民众。
中西融通的梁宗岱对中国新诗事业有独有的热忱和见解,新诗和白话是现实目标,但他并未局限于中国当时的文艺环境内。1931年,远在柏林的梁宗岱收到徐志摩寄给他的《诗刊》创刊号后,写了一封回复长信——《论诗》,谈到诗的价值和方法问题:好诗既要有艺术手腕,又符合一种傳统价值“诗歌合为事而作”,最重要的是“一颗永久追寻的灵魂底丰富生命”[3]30,智慧透过文字挣扎在意境与表现中。而中国的部分新诗缺乏热烈的或丰富的生活作为背景,似乎只能体现出艺术的精巧。而诗的第二重价值,是立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本体:“生活和工具而外,还有二三千年光荣的诗底传统——那是我们底探海灯,也是我们底礁石——在那里眼光光守候着我们,(是的,我深信,而且肯定,中国底诗史之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3]34和光荣的诗史相比,白话诗必定有所不能及,但因为传统工具已经不能全盘接受了,梁宗岱便在《论诗》以及很多文章中阐述了改造新诗和白话的方法。然而,他强调说:“目前底问题,据我底私见,已不是新旧诗底问题,而是中国今日或明日底诗底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承继这几千年底光荣历史,怎样才能够无愧色去接受这无尽藏的宝库底问题。”[3]34换句话说,梁宗岱思考的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和中国传统旧诗的对立、孰优孰劣、线性转变的问题,更多的是接受西学冲击、建立现代白话之后的中国诗,是诗歌与语言的古今变化和现代性进程。对今天的学术语言、日常口语、方言和网络语等变迁迅速的语言来说,依然意义重大。他思考的是更为长远的问题,传统和现代在时间上是相对概念,在价值上也是平等的,都需要具体分析。
因此,梁宗岱并未像之前陈独秀那样带有急迫的现实指向,以“三大主义”贬古尊今,也不似王国维处于引入西学新视角的初期,使用叔本华哲学分析中国传统文艺。他对诗歌本体的思考是为了时代而超越时代的。在时代变化中,诗人如何承前启后,诗怎样才是它自身,这便是本文所说的诗的本体,包含诗的性质、创作方法和意涵规律。它既不只是缜密的理性思维,譬如康德的本体与现象;也不仅是中国哲学中的太虚、天道、虚灵、天理,或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象征主义”;而更多是一种诗的“最高的创作精神和原则”[4],结合理论与实践、外来与本土化所形成的诗的方法论。从梁翁畅游于德文、法语、文言、白话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他试图探寻的是人类诗歌的共同性,这基于情感、文化和语言的遥相呼应。因此,音乐性、诗律、官能契合的用韵……这些共同的“镣铐”有助于洗练共同的语言工具,使文艺这“天下底公器”尽其所用。
对于中国诗“无尽藏的宝库”如何滋养“今日”和“明日”,梁宗岱认为作诗的先决问题是“彻底认识中国文字和白话底音乐性”[3]41。音乐性在古今中外都造就了文与情、意与象的浑融无间。中国文字的停顿、韵、平仄和清浊与诗的形式关联紧密,从五言、七言诗到词,音律登峰造极,而句式的打破必须和作者的气质相通,是诗人的内在需要和诗歌音乐表达的契合。因此如有需要,新诗可以学习西洋诗的“跨句”。这种借鉴并非机械照搬,因为梁宗岱发现中国诗词的音乐性和富于节奏的法文诗距离很近,罗曼·罗兰也在与他的交谈中认为中法民族是相似的。因梁宗岱头脑之敏锐清晰而感到如同面对法国智识阶级般的亲切,可以说这种对于人的认可也缘于对两国文学极端精巧、丰富的形式的认可。认识中国诗歌的音乐性,汇入西方的韵律感,更易达到诉诸五官的契合与和谐。
基于音韵的相通,梁宗岱创造性地比较了中西诗人。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是南宋词人和音乐家,词作具有“幽韵冷香”“骚雅峭拔”[5]的独特风格。杨万里曾评价姜夔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绝为“有裁云缝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6]。但精工技法的白石词在中国传统诗学中也因缺乏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等为人诟病,所以姜夔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常常被忽视。而梁宗岱为姜白石找到了远在法国的同伴马拉美。他认为二人的诗学都趋难避易,注重格调和音乐,诗境空明澄澈,癖爱“清”“苦”“寒”“冷”等字眼,反映出诗人的人格。而对于李白和歌德而言,后者反映着希腊史诗似的“强烈的音韵和节奏与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底配合”[3]117,前者也有音韵铿锵的短促的诗句及其中蕴藏的深刻的感情或强烈的思想。这表明在音乐性上中西诗歌都注重“契合”——诗句同时诉诸五官,外物与人的界限开始泯灭,对宇宙的想象和同情贯通人的灵魂。“我们内在的真与外界底真调协了,混合了。我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3]82这些最上乘的诗,无论是如歌德所说“抒情诗应该是即兴诗”的质而自然的中国旧诗,比如李白、陶渊明,还是精工巧艺的谢灵运、姜白石,都唤起了波德莱尔所说的“歌唱心灵与官能底热狂”的两重感应,即“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澈悟”[3]83。
李白和歌德的第一层相似是艺术的手腕,第二层相似是宇宙意识。诗歌诠释诗人对自然宇宙的理解和情感,蕴含他对世界的认识方式。“狂飙突进”歌德的哲学底色恰恰是浪漫主义之前强大而乐观的理性,李白则立足于庄子的虚静和瑰丽梦幻的想象。这就涉及到梁宗岱对诗之本体的第二种期许:从诗的形式上升到人格和智慧。现代中国语言文字面临的挑战是传统的言文分离——白话失于散乱粗糙,而书面文字自周代开始就与政治、个人情志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由极端精细纯熟流于空洞晦黯。诗歌、文字语言与政治、文人思想情怀的关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而梁宗岱的贡献在于阐释了新时期语言文字与大众、与人之思想的关系。没有文字便没有思想,反之,有什么思想便有什么文字,而这样的文字能够培养这样的思维和头脑。
文化反映心灵的进展,“更进一步说,文艺底了解并不单是文字问题,工具与形式问题,而关系于思想和艺术底素养尤重”[3]64。即使某些伟大的作品拥有浅易和朴素的外表,但都不影响文艺欣赏诉诸理智的梳理和情感的潜化的特点。正因文艺与人有如此“默契”,对个人和民族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关键影响,所以不能不尽最大的努力来改善文艺所使用的语言。具体来说,梁宗岱认为一方面要使文学语言浅易化、现代化,恢复其新鲜和活力;另一方面须使现代语经过一番洗练和补充。这是“用什么话”的问题,也是生活和文艺中语言工具本身的发展要求。
注重中西方诗歌的音乐形式,诗与诗人、世界相通,即梁宗岱强调的“诗底绝对独立的世界”——“纯诗”。纯诗如同声无哀乐的音乐,摒弃客观叙写或主观意图,仅凭音韵和色彩的密切混合唤起感官和想象,使灵魂神游物表。散文中表达的情绪和观念,在诗中化炼到与音韵、色彩不能分辨的程度。马拉美曾用宗教来描述诗的神圣和神秘,而瓦雷里(梵乐希)正式提出“纯诗”概念:“我所说的纯,是物理学家所说的纯水的纯。我的意思是,问题在于了解是否能创造一部没有任何非诗歌杂质的纯粹的诗作。我一直这样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这样认为: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诗,永远是企图向着这一纯理想状态接近的努力。总之,所谓诗,实际上是用摆脱了词语的物质属性的纯诗片断而构成的。一句很美的诗便是诗的很纯的一种成分。”[7]304瓦雷里认为“纯诗”是一种追求完美诗歌的理想目标、极限或方向,而诗是接近这一目标的不完满过程——“它只能极为艰难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给散文的词语、形式和对象发命令。如果它的命令实现了,那就是‘纯诗’了。”[7]315诗的形式和逻辑不同于神学讨论中缥缈的直觉和广泛的灵感,而且相比较更为纯粹,不同于自然之声组成的音乐,诗人面临的材料是原始的、复杂的语言。
因此,在人为赋形方面,梁宗岱与瓦雷里对“纯诗”的意见相似,都主张诗应该成为独立的感觉艺术,有自身固有的存在理由,与其他的文体形式应保持距离。瓦雷里甚至认为,那种用再现的方式操纵观众心灵的艺术是一场谎言,只有不外借感情的形式或结构,内求于自身悲喜的作品,才是真“纯”的作品。梁宗岱的不同在于,对“纯诗”采取更切合事实的判定,并不认为“纯诗”是不可及的,他认为自己所推崇的李白、歌德、马拉美、姜夔都是创作纯诗的典范。而且他跳出“诗言志”的评价标准,关注纯粹的精神和形式领域,将“纯诗”理论中“音”“义”结合思想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格律艺术相结合。张洁宇认为,梁宗岱“意在建立一个现代汉语诗歌的‘纯诗’传统。因此,他的格律探索也正如一个枢纽,不仅连接了世界诗歌与汉语诗歌,同时也连接了现代诗学理念与古典诗学传统,其理论意义因此超出了格律探索本身”[8]。
那么纯诗的这种“不能接受的概念”和“欲望的理想范围”[7]311是否脱离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背叛了需要被大众接受的白话呢?是否适合新诗的建设呢?梁宗岱是从语言和文艺作品本身去思考这个问题的。首先,如前所述,他意识到文言分离的传统和白话的问题,在白话文运动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2]111。对于“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新诗运动,他批评道:“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3]175因此,他为使用和创造语言的作家指出了新的道路和努力的方向:“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3]96“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底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或者,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三头六臂,七手八脚,那么,就一齐去,随你底便!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3]33这都是建议作家既要选择并深入自己的生活,又要进行心灵建设。作家应创造能充分表现其个性、特殊的感觉、观察和内心生活的文字,用形式来使文艺作品永生。形式虽然是心灵和自由创作的镣铐,但也是重构松散的语言材料,是发见新音节和新格律的必经之路。
象征主义以冷静和理智进入纯美的艺术、融思想概念于秾丽的意象、外形和意义之中,互相浸濡,用忍耐和敏捷去锻造诗魂,给新诗创作以新的灵感。它要求以极端的努力自铸镣铐,遵从最谨严的古典形式,也有着更新的意义和更深的解释,将全副精神灌注在形式上面,“注意底妙工就在于擒住那单靠它底消耗而存在的事物的”[3]29。和歌德外倾的、从万象到自我的创作方式不同,和中国古典诗歌刹那的感性也不同,象征主义是“劳苦”而注重形式的诗歌。但它也并非是干枯生涩的堆砌,而是精力弥漫后的“返虚入浑”,是滥用极端完美而过度的精巧之后的觉悟。这是瓦雷里在梁宗岱法译《陶潜诗选》序中提出的“朴素”观念,另一种朴素则是原始的,来自贫乏[3]194。象征具有两个特性: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它带我们在和谐与韵律中达到形神两忘、万化冥合的无我境界。当对真理的追求不以理性和意志权威的方式出现,而是把心灵和想象倾注于物体,与外物契合,隔断人和自然宇宙的帷幕就被永远揭开了,而这就是梁宗岱对于诗歌本体的理想,“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3]5。
随着政局的变化,梁宗岱逐渐解释清楚语言和“纯诗”对政治和民族的独特作用。当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响起,中华民族进入危急存亡、浴血奋战之秋,“纯诗”的发展看上去必须让位于“国防诗歌”之时,梁宗岱依然坚持“纯诗”和象征主义的观点。正因为诗是心灵的产物,是极端超脱自由的,所以不管把诗当做精神王国的女神,还是达到服务抗战目的的婢女,都是正确的。“可是她有一个不可侵犯的条件:你得好好地做。”[3]63梁宗岱把“好好地做”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真诚亲切地感到它的存在和需要,即无论来自外在激发还是内心充溢的不可抑制的冲动;二是给予诗一个与内涵融洽无间的形式。这与梁宗岱讨论诗的音乐性时观点一致,因为这不只是某一时期、某个主义或某种诗的要求,而是诗歌成其为自身的固有的“镣铐”。可以这么说,诗和诗人都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长处,不能换了面目,失掉了阵地。对于大众、国家和民族,诗人的奉献只有诗,唯有以产出好诗、真诗为目的,才能达成一切的现实目的。梁宗岱还指出诗天生具有面向大众和针对个人的两种不同需要,詩人既不应一味走向追求个人“精深”和“纯粹”的“魔道”,蔑视面向大众的诗歌,也不能违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写作。而且,诗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服务国家,即凭借自己的观察与涵泳、幻想和精思,为苦难的祖国奉献辉煌的诗艺:“哥德在德法战争之役没有写战歌,他底诗到现在却为万国所宗仰,德国也引以为最大的光荣,最大的骄傲。”[9]66-67这便是纯诗的形式在诗人与读者之间,在凝定的文字和变动的历史之间,在不同民族和时代之间爆发出的巨大的“契合”的情感力量!
总之,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两部作品里,梁宗岱开掘、连接并擦亮了一条穿越古今中外的诗之“镣铐”,是中国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未来,诗歌的本体应该遵循的方法、原则。这条“镣铐”有两个分支:一支是态度上的,对于诗人来说,必须使自己深深扎根于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另一支则是方法上的,即借鉴象征主义探索并改造中国语言文字的音韵,形成对思想有益的白话。把这两支合成一股,就形成了对诗歌的最高理想——纯诗。梁宗岱的观点对今日的文学和语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文学武.梁宗岱与中国比较文学[J].文艺争鸣,2013(7):32-37.
[2]曾思艺.比较文学视野中诗的理论与批评——也谈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J].中国文学研究,2013(3):109-112.
[3]梁宗岱.诗与真[M].卫建民,校注.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文学武.梁宗岱与中国比较文学[M].文艺争鸣,2013(7): 32-37.
[5]陶尔夫,刘敬圻. 南宋词史(下)[M].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239-246.
[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下)[M]. 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2015:606.
[7]瓦雷里.论纯诗[M]//瓦雷里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8]张洁宇.论早期中国新诗的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09):1-9.
[9]梁宗岱.诗与真续编[M].刘志侠,校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66-67.
作者简介:高竞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