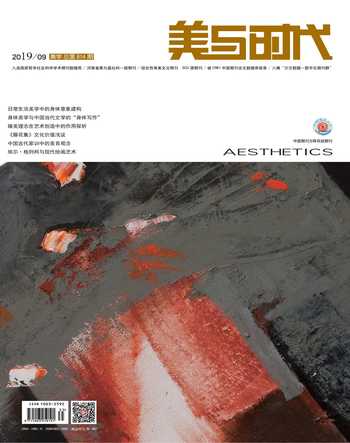世界文学的眼光与当代中国的精神现象
杨世海 朱永 李已尧
摘 要: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看,在张柠《三城记》中可以看到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列文的影子。《三城记》在叙事模式上虽然与《浮士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却没有采用传统小说的深度模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扇形结构。主人公顾明笛既没有成长为英雄,也没有被社会吞噬,但他在不断的追求中保持了自我。顾明笛作为一个典型人物,他的精神困惑和不断追求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城记》是以世界文学的眼光来写当代中国的精神现象。
关键词:《三城记》;世界文学;当代中国;精神现象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社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思想与时代》月刊及其学人群研究”(17GZYB39)阶段性成果。
一、《浮士德》结构的中国当代变体
朱永:读到《三城记》,我脑海里不仅出现一些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围城》等,还不断浮现出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例如《浮士德》《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等。《三城记》中的顾明笛这个人物,似乎有着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列文的影子,而且《三城记》在小说结构上很容易让人想到《浮士德》,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来谈一谈《三城记》和世界文学的关系。
杨世海:讲到《三城记》跟歌德《浮士德》的关系,我认为“浮士德”式的追求模式在《三城记》中是有的。但具体的阶段书写有差异,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我觉得就有很大的差别。浮士德处在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所谓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他所追求的是建功立业,实现个体人生价值。浮士德从书斋里面走出来,走向广阔的现实世俗生活,首先进入爱情阶段,之后走进政治生活,再走向艺术与美的生活,最后迈向事业阶段。浮士德的人生路径象征着欧洲人从中世纪宗教意识形态束缚中挣脱出来,走向广阔的世俗社会,并要建立世俗功业的过程,所以说他代表了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的欧洲精神,这是一种自强不息的世俗精神,这与现代性的展开是一致的,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现代性危机,还相当乐观,所以在诗剧结尾里,浮士德上了天堂。
《三城记》可能借用了浮士德的模式,即人不断地追求,人生不斷地切换阶段。但顾明笛的追求却不是要建立所谓的功业,不是要扬名立万,不是要实现某种价值,而只是为驱逐内心的不安、迷茫、焦躁,于是找另外的生活方式来替代、来冲淡。相当于讲,到了现代阶段,很多东西退潮了,人的那种安身立命的价值追求退却了,人的行动不再追求建功立业,只是为精神找出路,甚至都不是找出路,而只是排遣、填补。顾明笛要走出去,要去经历不同的人生,他要摆脱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不是追求什么人生价值,更不是要建功立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浮士德》或许是《三城记》的一个潜文本,《三城记》具有一定程度的神话书写模式特质,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又具有后现代特质。
朱永:我觉得《浮士德》的故事情节是类似阶梯式发展的,而《三城记》这部小说,我感觉是一种扇形的结构。
杨世海:对,所以,《三城记》是有《浮士德》的模式,但浮士德那种积极向上。一级一级往上的感觉是没有的,没有“浮士德精神”的内核。浮士德最后得救,灵魂上了天堂,但《三城记》没有救赎,也就是没有精神升华,仍然只是生活,也没有其它小说常有的那种痛彻或快乐的领悟。小说设置了开放式的结局,所以顾明笛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跟劳雨燕一起去河北开农场,不知道;他也讲要跟施越北到北京去,一边继续读书,完成博士学业,一边帮施越北的忙,也有这种可能。但究竟会怎样,不知道。这是很高明的结尾方式,很符合顾明笛的人物设定,这一结尾并非纯粹的技巧。总之,《三城记》的顾明笛是在寻找生活,是在寻找精神的突围,但方向是不明确的,那种所谓的救赎是没有的,那种领悟也没有,也即没有终极之思,以一种终极救赎模式来写现代人没有终极救赎之路,这是很高明的,更显示出现代人的尴尬处境。
朱永:假设这个小说结尾是顾明笛去了河北乡下,从事农业劳动,那么你觉得他就有救赎了吗?
杨世海:其实,传统的小说就喜欢这样的结构方式和结局安排,认同某一宗教或思想资源所倡导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并且让人物走向那里,《红楼梦》、雨果、托尔斯泰,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是这么玩的。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神学的救赎,还是世俗的领悟,都是有明确的指向性的。以前小说讲究确定性,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特别强调这个确定性,确定性代表着小说对人生是有教育意义,有引导作用的,其前提就是认为人生本来应该有方向和价值,没有是因为被遮蔽了,那么小说就是要把确定性的方向和价值通过叙事指出来。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列文后来找到了这个确定性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爱,要劳动,要与人民在一起。
这部小说并没有那种深度模式,不像传统的“成长”小说那样展现人物在苦难和磨炼中不断地成长,如《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典型的成长小说。《三城记》的主人公就好像你所说的那样没有上升,是一种扇面结构,他实际上是不自由的,总是不能自主,常常被动、偶然地进行选择。确实,顾明笛的选择好像就是被牵着走,这暗示现代人在自我选择和追寻中不断地自我迷失。现代人的自我越来越平面化,越来越不能自主,没有不断地自我更新和向上,只是生活场景的变换而已,是一种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一定是堕落。我觉得这是这部小说把握得非常好的地方,是亮点所在。因为我们在寻找和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地迷失,越寻找自我越不能自主,越追求个性越没有个性。现代生活看上去有很多选择,但选择其实并不能自主,最终越来越随波逐流,顺着他人走,以为这样不孤独。这是我们当下强烈的生命感受。毫无疑问,三十岁左右的八零后顾明笛就是如此。
朱永:我承认你说的这个确实符合一定的现实生活的情况。但是当我们在讨论一部作品的时候,作品这样平面化地设计人物发展,你认为有问题吗?
杨世海:我们对照另外一部知识分子小说《沧浪之水》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并不是小说的问题,《沧浪之水》的人物还在不断地退化呢!
朱永:对。《沧浪之水》的人物是不断地往下走的,不断地被社会吞噬,到最后完全被异化。那么这样说的话,人物的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像《浮士德》人物往上走的模式;一种是像《沧浪之水》人物往下走的模式。
杨世海:还有一种,就是你之前说的这部小说的“扇形”模式。
朱永:我并没有感觉顾明笛在书斋和在《时报》或者是在广州有了多大的进步或者是发展,但是也不会感觉到他堕落了。
杨世海:我感觉顾明笛这样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坏的状态,这是他的“不忘初心”。他是迷茫的,不断想走出迷茫,最后虽然仍然是迷茫的,但他并没有堕落。我觉得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这已经是当代英雄。顾明笛的精神状态是典型的“浑浑噩噩”现代八零后样态,在追寻,但追寻又不自主,这就很符合现代人状态,生活无论怎么切换场景,实质没有变化,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只是岁月流逝了,人不再年轻,我觉得自己这时就这样。
二、“局外人”的感觉与当代价值体系的破碎
杨世海:通读小说,我感觉顾明笛似乎缺乏生命的热度,虽然不断地生活,但整体感觉是冷冷的。我觉得小说很多地方都冷冷的,如他对张薇祎、万嫣、彭姝的态度,甚至对施越北、裴志武等人的悲欢离合也常有些心不在焉。顾明笛生活在世界之中,却游离于世界之外,甚至来讲,有点“局外人”的感觉,当然不完全是加缪《局外人》那种感觉。但小说有时候又会有小细节打破这种整体感觉,就如卷四中,顾明笛突然在过年的时候,跑到劳雨燕河北老家。这个情节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模式的再现:因为情感的冲动,就突然从一种状态跳跃到另一种状态,这形成浪漫的效果。我觉得这一情节是小说中最有温度的地方,仿佛顾明笛马上就要走出之前的浑浑噩噩状态,好像他就要找到方向了一般。但是,作者很快就把这样的确定性、方向性给打掉消解了。他们的浪漫行动有了结晶:劳雨燕怀孕了。然而他们经过商量后,最终决定把孩子打掉,而且打掉了之后,没有遗憾和惋惜。如果没有打掉的话,顾明笛和劳雨燕就有了联结到一起的纽带,这可能带来确定性,就可能把他们导向去开农场,但打掉了的话,就切断了这种确定性的可能。有意思的是,这会让人想到《浮士德》中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合生下欧福里翁的情節,欧福里翁最终是意外摔死的,而顾明笛和劳雨燕的孩子则是他们自己打掉的。如果说《浮士德》这一情节隐喻着现代精神和古典精神结合生下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因为太过激情而短命,那么《三城记》中的这一情节则暗喻着:在当下,无论是古典精神,还是浪漫精神,这些传统资源都难以跟现代结合,即便有结合的苗头我们现代人也会把它扼杀在萌芽之中,为的是不拖累自己和别人。传统与现代结合会带来什么,无从知道,不是因为它无法孕育,也不是胎死腹中,更不是因为它长不大会夭折,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它来到这世界。
我们透过了解小说情节架构方式的变化,可以体察到时代精神和小说书写模式的改变。像传统小说往往会往确定性推,借用一些偶然中有必然的因素来推动,如一些浪漫爱情邂逅,孕育生子等,最后让人物确定,觉悟起来。我们看那个列文就是这样,他跟吉蒂在一起,他们也有了孩子,他跟他人,跟土地关系就更密切,一步步把他推向觉悟,最终寻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顾明笛有一个浪漫主义的行动,可以说就是有了爱情,而且有了爱情结晶,但这些并没有推动他对社会、对人生有新的认识,从而得到新生,从而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们的孩子是被打掉了,这是很有隐喻性的。以前小说喜欢那种确定性,现代小说一般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融合了很多东西,有哈姆雷特的困惑,浮士德的模式,列文的迷惑,垮掉一代的情绪,局外人的疏离,等等。这些都是西方文学中颇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身上的问题我们也有,但我们也面临新的时代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物,尤其是十九世纪前的人物形象最后往往能找到一个精神的归宿或者是一个解决办法,就像哈姆雷特最后成为了英雄,浮士德最后上天了,列文获得了信仰接近了真理,等等。但现代人没有这个,寻寻觅觅而不得,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精神和生存状态,《三城记》正揭示了这种状态,而且用的传统的质朴现实主义笔法,这种现实主义目的不是要寻找背后的历史规律,也不仅仅是批判社会或人物,而是展示人的生存状态,其底色是存在主义式的,作家没有采用炫酷的现代主义笔法,而采用现实主义笔法,这是很独特的。
李已尧:杨老师刚才讲的“局外人”的感觉,能不能展开讲一下?
杨世海:“局外人”的感觉,是从人物塑造和小说的叙事来谈的。顾明笛跟张薇祎的关系,他跟母亲的关系都是淡淡的、冷冷的;包括他到了北京之后,万嫣对他那么的热情,他也是淡淡的冷冷的;他对彭姝也是淡淡的冷冷的;甚至他对施越北、裴志武的喜怒哀乐也并未表现有多大的热情。有时候就觉得他不解风情,或者是不尽人情,或者两种都有。所以他这个人通常就是冷冷的,除了刚才讲的突然跑去河北找劳雨燕之外。而小说在叙述这些的时候,显得极为克制和冷静,似乎追求一种“零度叙事”,这就加深了小说冷冷的感觉,从而使得顾明笛这一人物游离于人群之外,他读博时会精神失常并不奇怪。
朱永:这就感觉他对生活没有全身心投入。
杨世海:嗯,顾明笛内心是躁动不安的,极想深度介入生活,但是他跟环境始终有一种距离感。这个现象我就觉得是一种现代人的体验:想融入环境而不得,反而越发感觉陌生和疏离。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就喜欢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陌生和疏离。在传统世界里,我们有这样的设定:我们的世界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人生也是有价值的,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去确定哪个价值和意义更值得自己追求,以及怎么实现自己认同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儒家代表张载就是这样给人生定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只要去努力就行了。你努力的话,就可能成为圣人、半完人、完人等。西方的话,有上帝,也是顺着这个思路走:世界有价值,人生有意义;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总之,在传统看来,人与世界就是统一的关系,天地是大宇宙,人就是小宇宙,是统一关系。但现代就不是这样了,人与世界的价值和意义遭到了解构。在《三城记》里,顾明笛不思虑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他寻找的也不是这个东西。失去价值投射,人就难免有疏离感,自然也不会全身心地投入。综观整个小说,顾明笛虽然在不断地寻求生活,但缺乏深度介入,似乎总是在逃遁。
朱永:对!你说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所以人与环境的这种疏离,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实际上是整个世界价值体系的问题。
杨世海:对啊,关于人生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现代人是弄不清楚的,也似乎不想弄清楚,现代人对传统那些价值和意义并不信任。现代人的解放就是从传统中挣脱出来,这形成我们的思维结构模式:消解一切现成以及将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不信任一切。我们会信上帝吗?我们还觉得儒家价值观很靠谱吗?我们信任复兴的传统文化价值吗?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价值观真正进入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吗?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护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跟环境就会有疏离感,就会感觉很多东西是跟自己没关系。
讲得生活化一些,就像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父母的态度是冷冷的、淡淡的。他们也知道父母关心他们,但认为这样的关心没有多大意义,也就冷淡对待。小说里面顾明笛对母亲的态度就是这样,他感受得到父母的关心,也知道自己要关心父母,但又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也就疏远、冷淡。说到这里,我感觉小说有一点瑕疵,就是小说写到后面,顾明笛母亲这一形象就没怎么出现了。小说开头有交代,顾母是一位很强势,且爱干涉儿子生活的母亲,但顾明笛去北京后,顾母就好像消失了一般,这不符合人物性格。对此,我还认真翻了几遍小说,寻找与顾母相关的细节:在顾明笛考博的时候,提到顾母,说顾母打电话给他,打扰了他的复习;然后是考上博士之后,提到顾母很高兴;再就是精神出問题后,顾母来北京处理他的事情。像在“世界”这一卷中,压根没涉及到顾母。我觉得小说可以在叙述中,尤其是在“世界”这一卷中,不失时机地提几次顾母,可能更好,更符合顾母的性格特质。当然,或许作家是在有意强化顾明笛对母亲的冷淡,甚至在叙述上把她剪除,所以我就感觉到顾明笛对人特别冷淡,尤其对亲近、关心他的人,只要他觉得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意义就会很冷淡,他就像在这些人之外一样,家庭之外,男女关系之外,像局外人一样,当然不是加缪那样的“局外人”,那太极端了,顾明笛不是极端的人。
顾明笛与人相处是一种浅层的介入,始终与人保持距离,他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就是这样的,不论是和张薇祎、万嫣,还是跟彭姝、童诗珺,都有很大的疏离感。他知道别人对他有意思,他也想跟她们走近,但走不近,反而越来越疏远。顾明笛与人有疏离感,接人待物很被动,对劳雨燕才稍微有点主动。所以,我觉得小说中写他突然跑到劳雨燕老家去,确实是很意外,当然也很符合他这种人物设定。因为有一种人,通常是冷冷淡淡的,但偶尔也会做出特别疯狂的举动。只是到后面,顾明笛的主动性又被消解了,默许打掉孩子,说明他并没有根本变化。
朱永:其实就是一种卢卡奇所谓的总体性的破碎。什么是总体性的破碎呢?就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过去认为爱情不得了,爱情是很神秘的,又是神圣的。现在神秘感和神圣感都消失了。
杨世海:现代性就是祛魅神圣,只留世俗的东西,人化的东西。世俗的人化的东西就是很简单,就如吃喝拉撒一样,没有神秘感、神圣性。所以,现代人会把性行为看得跟吃饭一样,只是一种生理需求,不神秘也不神圣。既然不神秘也不神圣,也就没有多少禁忌,万事都可以。《三城记》中的人物主要是大都市的中产阶级,他们是这种态度,也有这样的困惑,他们某些方面像美国六七十年代“垮掉的一代”,把性看得轻松平常,只是还没有放纵而已。
三、行动哲学与时代隐喻
杨世海:《三城记》涉及的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一些人生活虽然富足,但对一眼望得到头的循规蹈矩生活越来越厌倦,无论是用思想,还是用行动都无法驱逐,这个可能是将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就这个我们可以联想到西方文学,“二战”之后美国有所谓的“垮掉的一代”,英国有“愤怒的青年”。他们反叛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生活。《三城记》的主要人物不就是“八零后”吗?“八零后”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中国垮掉的一代”。可以说,《三城记》以“浮士德”的模式书写了带有西方“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情绪的中国现代体验。顾明笛在上海的生活是比较滋润的,但是灵魂躁动不安,乌先生的心灵鸡汤式安魂也没用,他要出走,寻找另一种生活,于是他离开上海去到北京,后又到广州,但不是要建功立业,不是我们常说的要混出名堂,也不是要实现某种人生价值。从小说内容来看,顾明笛在北京、在广州没做出什么大事情,他也不追求要做什么大事情,有阻碍就放弃或转移目标了,当然他并不像“垮掉的一代”那样采取一种堕落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中国人越来越切实的体验,这非常有现代性,可以来讲,是中国的现代性。
李已尧:我有一种感觉,传统小说中主人公在自我实现的追求上来体现力量,例如《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博士、《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列文等人物形象,但是顾明笛明显不具有这样的力量感。这样的人物形象就好像是一种“多余人”形象的变体。
朱永:对,张薇祎让他多关注现实,不要老是回头。顾明笛老是写历史题材,这让我感觉一个作家老是写历史题材其实是挺无力的。
杨世海:张薇祎家里挂着《草地上的午餐》、家里有托尔斯泰全集,我觉得这样的设置是不是有一定的象征或者是暗示呢?还有就是张薇祎一直让顾明笛多关注现实,是不是代表着现代女性对男性的一个期望:走向现实,走向现代,不要老是回顾传统的那些东西,不要钻在里面走不出来。顾明笛经常和乌先生谈论传统的东西。这里我就疑问是不是作者在有意表露这样的观点:希望现代人多关注现实,而不是走向传统。现在传统文化、国学回潮,许多年轻人都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方向,盲目地附和所谓的文化自信。所以,我在想这里是不是作家的刻意书写,呼吁年轻人多去关注现实,介入生活,迈向现代,而非复归传统。《托尔斯泰全集》《草地上的午餐》不应是随意出现的,《草地上的午餐》是现代绘画,托尔斯泰也是面向现代,当然他们都对现代有反思,反思现代本身就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张薇祎是面向现代的。但是又有一种尴尬:顾明笛写作历史题材小说,博得文名,颇受欢迎,然而在介入现代生活则处处碰壁,人生最终变得不能自主,他与张薇祎也越走越远,最后连联系都断了。这里是不是隐喻呢?很多人都很想介入生活,改变现实,但一旦触碰到那神秘力量也就无能为力,那神秘力量与政治权力紧密联系,无法撼动,与之相对只会粉身碎骨,人们也就只能回归到传统中去寻找一些依托,而且走向传统很安全,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现实利益和精神慰藉。
朱永:但是小说中的乌先生也是讲“行动哲学”的,乌先生有时候也是建议他去外面闯一闯。
杨世海:对,乌先生某些观念是蛮现代的。这是我的一种感觉:我们介入现实四处碰壁,无计可施的境遇,其实是与政治相关,在政治权势面前,人们发现问题却不能揭露,更谈不上解决,反而成为被解决的对象,这是顾明笛的困境。当然顾明笛并不去做死磕的英雄,他也没有这样的追求。最后,顾明笛在感情上走向了劳雨燕,并且产生回农村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又不能成行,成为泡影。作者写顾明笛这样的人生轨迹,有没有一定的普适性或说代表性呢?这些都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这部小说人物的人生轨迹有一定的政治隐喻在里面。我们常想起王夫之“上好申韩,下必佛老”的说法,上面要加强统治,讲求全面控制,下面的人就必然走向对佛老的关切和寄托,传统文化复兴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呈现的。顾明笛很想走出去,想介入现实,但发现现实问题不能揭露,没法解决,反而成为被解决的人,他被刘炜阳狠狠地收拾了几次,最终被开除。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出现了大问题,往前走不了,也不愿走,就又退回传统,把传统当作麻醉剂和遮羞布,这是一种危机。当然,我可能是过度解读了。
作者简介:杨世海,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朱永,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李已尧,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