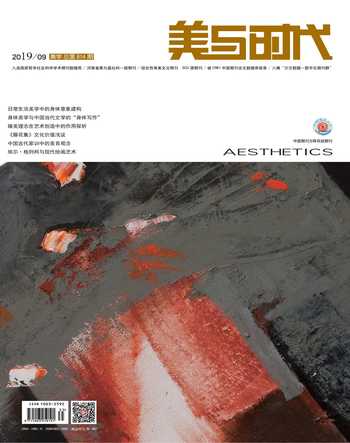《唐诗三百首》中的美育思想
摘 要:《唐诗三百首》是目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选集,书中所选大都是脍炙人口的唐诗名篇,题材和体裁都较为完备。目前,学界对此诗集的研究大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具体的分类研究比较少。从对《唐诗三百首》编者的背景、选编的方式、教育的反思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从而对其美育思想进行研究。
关键词:《唐诗三百首》;美学;美育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不但是唐朝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作为唐诗选集的《唐诗三百首》是否是最好的唐诗选集,在学界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无疑它肯定是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选集。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唐诗三百首》是属于蒙学读物,其中包含着很多中国古代的德育思想和美育思想。
一、从编者谈《唐诗三百首》的美育思想
《唐诗三百首》的编者,目前学界一致认为是蘅塘退士孙洙,对蘅塘退士身份认定的研究最早来自于朱自清在《〈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中所说:“有一种刻本题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孙洙’两字,也许是选者的姓名。”[1]后来的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他这一观点。
孙洙的一生,是典型的儒家学子的一生,其先祖为唐朝金吾卫,孙洙勤奋好学,先后考中举人、进士,成为知县,且热衷于文学创作。在为官之时,孙洙也是一个受百姓爱戴的好官,孙洙的成长之路深深打上了儒家的烙印。《唐诗三百首》的选编之所以充满了儒家的美育思想,这与孙洙的成长之路受到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他选编《唐诗三百首》的目的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2]。除此之外,他还想通过这本书来取代以往的诗歌蒙学著作《千家诗》,这与孙洙的学习经历应当是有关联的。作为儒家学子,《千家诗》是其求学路上不可避开的蒙学读物,而作为诗集《千家诗》的数量过于庞大(录诗1281首),并且囊括了唐宋两个朝代的作品,对于幼童来说过于繁杂。因此,也注定了《唐诗三百首》是充满儒家美育思想的一本唐诗选集。
除了孙洙之外,《唐诗三百首》还有另一个编者,她是孙洙的继室徐兰英。徐兰英善书工,《无锡县志》和《清朝书画家笔录》均有小传,曾得過御赐‘江南女士’的印章。徐兰英的参与,对于这本诗集有着重大的意义,意味着《唐诗三百首》的选编过程中有很多部分融入了女性视角,通过女性的角度来审视蒙学教育的需要,这在男权封建统治之下的社会中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对当时教育之中女性思维缺失的一种弥补。虽然在选编中女性诗人的作品很少(这也与当时大时代的背景有关),但相比之下女性视角的引入显得更为珍贵。例如大量的宫怨诗被选入《唐诗三百首》之中。根据统计,在313首诗中选入了13首宫怨诗,一方面是因为宫怨诗在唐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关作品的创作数量和艺术成就都达到了这一题材的高峰;另一方面,作为女性徐兰英对于宫怨这种痛苦有着更为深刻的感知,这是孙洙所不具备的,也是男性诗人集体欠缺的,更是它与其他诗集的差异性所在。除了女性视角外,徐兰英还是一位母亲,当整个社会由母系氏族发展到父系氏族之后,男性承担起了生产生活的重担,女性则在家庭教育之中付出更多,作为母亲的徐兰英就有了天然的优势,这也确保了诗集在编纂之初就与当时的家庭教育需求是紧密贴合的。
二、从选编谈《唐诗三百首》的美育观
我国最早的诗歌选集是《诗经》,它的选编者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孔子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和塑造理想的人格,这在孔子的美育观中即所谓的“成人”。孔子把“成人”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因此,我国历代都有选编文集、诗集的传统,这也是对于儒家美育思想的一种继承。唐诗作为历朝历代诗歌中的翘楚,蘅塘退士选择编纂一本唐诗选集也是对于儒家美育思想的发扬与继承,而选择面向蒙学更是儒士对于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唐诗三百首》中选编诗歌的总数为三百一十余首(不同的版本有数量上的细微差距),与《千家诗》相比仅仅为其数量的四分之一。这种数量的减少更有益于幼童的学习,真正考虑到了儿童有限的接受能力,这也符合蒙学的初衷,深刻地贯穿了儒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美育思想。此外“删诗”也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早在孔子编纂《诗经》的时候就设立了“思无邪”的美育标准。《论语》中说到道:“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按照此标准,孔子将几千首诗删到了三百零五首,蘅塘退士选择三百首这个数量,或许这也是孙洙作为儒生对于孔子选编“诗三百”的致敬。
除了数量的改变之外,在体裁的编排上蘅塘退士也有自己的选择。他先是以诗体作为分类的标准,再按照作者的年代为序排列下来,并且诗体的顺序也是按照诗歌的发展状况排列的:古诗、乐府在前,律诗、绝句在后,这样的编排方式保证了选编的整体性与条理性,体现出蘅塘退士对于形式美的一种追求。除了形式美之外,内容美也毫不逊色,《唐诗三百首》在题材的选择上囊括了山水田园、咏史怀古、登山临水、赠别怀远、边塞出征、思妇宫怨,而所选诗歌的风格或慷慨激昂、或哀怨悲歌、或飘逸豪放、或沉郁顿挫,实现了“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
当然,蘅塘退士最成功之处在于对于孔子“中和”“温柔敦厚”“雅正”等美育思想的继承,这一点最显著的体现是《唐诗三百首》在选编的时候没有将“李贺”的诗选入。李贺是唐代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齐名的诗人,被誉为“诗鬼”,但孙洙却没有选入一首李贺的诗,相比之下选了李白的二十九首诗、杜甫的三十九首、王维的二十九首诗,这个反常现象就是由于李贺的诗不符合儒家“雅正”与“温柔敦厚”的原则。李贺的诗风具有幽奇冷艳、虚荒诞幻、悲冷凄苦、怪诞想象、幽凄意象的风格,他在创作的时候也非常地大胆、偏激、特立独行。唐代诗人杜牧《李贺集序》云: “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5]7这与儒家的美育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此外,孙洙是清朝人,生活在康乾盛世,当时文字狱大盛,而李贺的诗风也可能会对编者带来牢狱之灾,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6]对于久经仕途的孙洙来说从政治上考量也不会冒此风险。除以上原因之外,李贺的诗不易诵读,不适合幼童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选编进去也达不到蒙学诗歌读本的目的,正如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云:“后人学贺者,但能得其诡幻,于佳句十不得一,奇句百不得一也。”[5]205
因此,无论是诗歌的数量、诗歌的形式与内容、诗歌的精神内涵的继承等都统统指向了儒家认为的诗歌所具有的“兴、观、群、怨”的作用,这也是儒家的美育思想的重要追求。
三、美育角度的教育反思
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唐诗三百首》之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且富有影响力的蒙学读物,有识字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戒律类的《小儿语》《弟子规》《朱子家训》《名贤集》和《论语》,声韵类的《千家诗》和《声律启蒙》,常识类的《蒙求》《龙文鞭影》和《幼学琼林》,这些作品对于幼儿教育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保障,但是也都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作品大都是通过让儿童反复地记忆、背诵、朗读来达到学习的目的,缺乏对于孩子创造力的挖掘。
马斯洛认为:“几乎所有的儿童,在受到鼓舞的時候,在没有规划和预先意图的情况下,都能创作一支歌、一首诗、一个舞蹈、一幅画、一种游戏或比赛。”[7]中国古代的蒙学读物对于儿童的记忆力训练很有好处,但创造性方面无形之中遭到了压制,儿童的感性受到了压抑,天真烂漫、亲近自然的一方面得不到展现,只会跟随着前人的脚步去进行创作,不敢逾越传统,很难有开创性的突破。僵化、保守、注重传统、山头主义、讲求正统的习惯从儿童时期的学习便开始逐渐受到影响,这与美育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这种学习方法无形之中将人当作了手段,将学习的目的早早指向了全民狂热的科举考试,以期通过学习追求仕途、追求功名利禄,产生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古代文学史上文道关系上的讨论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3.
[2]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M].章燮,注疏.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84:1.
[3]谭杰.论孔子的“中和”美育观[J].理论导报,2006(11):18-19.
[4]刘兆伟,译注.论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19.
[5]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孟轲.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0:225.
[7]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M].李文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24.
作者简介:李卓,长安大学文学与艺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