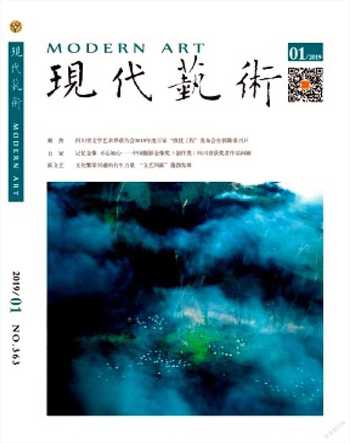道可道 非常道
李树峰
在全国摄影业界,人所共知的王达军先生,是著名的风光摄影家。从他的风光摄影作品来看,他所追求的,概括起来,是他所发现的极致之时的极致之地的极致之光,纯粹的自然之美。这个方面,代表作不少。如《喜马拉雅之光》《大地系列》等,业界人士耳熟能详。
然而,如果把王达军先生仅仅定位为风光摄影家,显然缩小了他的业绩,他用大量精力所投身的,是拍摄中国西部的人文地理。特別是1990年他与王建军、袁学军“西部五万里”的壮举,开拓了中国西部地理画卷的摄影行动,具有地理探索发现的特殊意义,从而使他们三人成为推动中国西部风光摄影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王达军面对自然拍摄出的作品,无疑具有地理摄影的学术内涵,其中很多作品又具有极致的自然之美。正因为如此,他面向自然的摄影之道具有了内在的矛盾性:当人们把他的作品单纯看作唯美的形式之时,人们也许忽略了他的内容之重;当人们把他的作品单纯看作地理地貌的纪录的时候,又似乎没有领悟让他激动的自然和心灵碰撞中的风与光。于是,他于矛盾中一次次经历人们对他的偏执阅读。而有一次达军告诉我,他非常赞同我所写的文章——把摄影作品的价值分成说明性与诗性。我那时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内心感受,以为只是他的一种理性认同。现在看来,说明性与诗性的矛盾,正是他摄影之道中的内在冲突,是他萦绕于心的一个艺术情结,也正是针对他摄影之道的恰当解释。
然而,我依然把王达军的摄影定位在风光与地理上,直到看了他所拍摄的《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中的西南石窟部分(先后出版共5卷),才知道他历时4年半(1993.3-1997.10)所拍摄的石窟雕塑在他一生摄影之中的重要位置和份量。他的拍摄有学者伴随指导,甚至有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的美学家王朝闻先生一同前往。这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探求和发掘,也是对摄影说明性提出很高要求的一次实际行动。从这几本石窟画册里,我看到了学术的光辉和敬业精神,也再次体悟了影像中说明性与诗性的关系。
西南石窟雕塑拍摄工程之外,王达军还与专家学者一起,做了另外两项工程——藏地寺庙和羌族服饰,为此他跑过200多座藏地寺庙和所有的羌族居住地区。两个项目的影像与文献都作为文化工程正式出版。
王达军以摄影方式寻道、问道,历时15年。从2003年拍摄三台县郪江古镇的城隍庙会,到遍访四川、重庆两地近百个道观,最后在青城山、鹤鸣山等二十余地的反复专心拍摄,由学术探索到摄影艺术表现,王达军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问道”与“问法”相互促进,最后形成了现在道法合一的“道·道”影像作品。
依笔者观察,摄影界拍佛者众,且流于光影和形式构成者多;拍道家者寡,以影像方式试图表达道教本身境界、内涵者更少。王达军敢于挑战这个难题,属于巴蜀之地犟人之为,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笔者虽然十分喜爱阅读老子和庄子的经典著作,对“道”有一定认知和体会,但对道教缺少研究,不敢放言纵论。单从王达军的影像方法来看,他的作品在努力表达一种“象外之象”和“道”的意蕴境界。这些作品也确实呈现出了这种境界,如摄于石角镇白云观、青城山上清宫、洛水镇川主庙等道观的作品,都达到了或清静或动态中“大道”专一精纯的境界,有强烈的吸引力,把读者带入这种境界中。他利用多次曝光把太极图与道祖形象融为一体,令人耳目一新;他把道家一百多种手诀拍摄下来并辑于一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觉表达系列;他运用室内外闪光灯使影调有更大的调控范围,形象动静结合,造成虚实相间的效果。
在影像编辑中,道人、道仪(道的仪式)、道存(民间存在状态)三个部分,从人和活动状态的关系中,思考道教的发展与变化历史,以艺臻道又回到了学术探索的大方向上。可以说,这是学术与艺术相互映现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