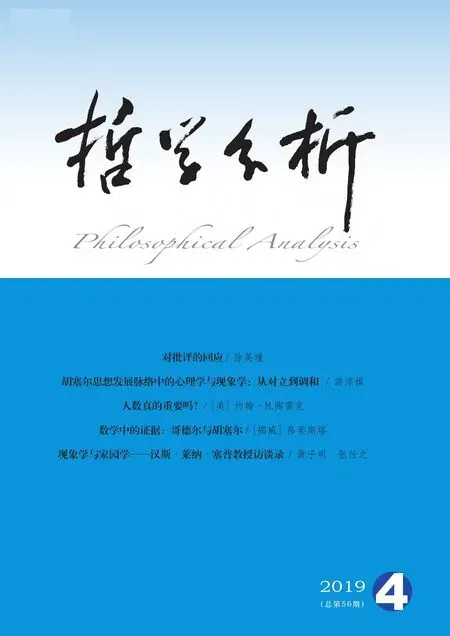数学中的证据:哥德尔与胡塞尔
[挪威]达格芬·弗莱斯塔/文
李晽 刘靖贤/译
一、哥德尔的胡塞尔研究
哥德尔于1959年开始研究胡塞尔。①WangHao, Reflections on Kurt Göde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7, p.12.他发现胡塞尔与他意气相投,很快就沉浸于胡塞尔的著作中。他拥有胡塞尔的所有主要著作,并且仔细阅读了这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勾画重点并在边页上作出评注。我们可以看到,哥德尔的评注大多数情况下都赞同并强调胡塞尔的要点。但他有时也具有批判性,特别是针对《逻辑研究》与《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的某些章节所做的评注。一般来说,哥德尔最赞赏《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笛卡尔沉思》以及胡塞尔1907年观念论转向后的其他著作。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大多数“分析”哲学家认为胡塞尔的早期著作比他后期的观念论著作更易接受。
早在哥德尔开始研究胡塞尔以前,他就在数学哲学方面表达过与胡塞尔类似的观点。他在胡塞尔那里所发现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并非完全不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是胡塞尔的整个哲学,这为哥德尔早期在数学哲学方面的观点提供了一个系统性框 架。
通过哥德尔的手稿以及他在胡塞尔著作上的评注,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究竟在哪些方面吸引了哥德尔以及哥德尔如何理解胡塞尔。在我看来,哥德尔对胡塞尔的理解是出色的,这使得哥德尔成为胡塞尔最好的解释者之一。
哥德尔在《什么是康托的连续统问题?》的修改版(1964年)中第一次提到他的胡塞尔研究。贝南塞拉夫和普特南想把这篇论文选入《数学哲学选读》中。然而,哥德尔坚持要修改这篇论文并进行增补,因为他的哲学观点自写完这篇论文后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反映了胡塞尔对他的影响。有许多段落表明了这种影响,我发现如下段落非常有益,因为它看起来是晦涩的,但如果在胡塞尔知觉理论的背景下阅读,就变得可理解。因此,这个段落有助于我们通过胡塞尔来理解哥德尔。哥德尔写道:“有些超出感官的东西实际上是被直接给予的,这一点(独立于数学)是从如下事实得出的,即使我们指称物理对象的观念也包含了在性质上不同于感官或纯粹感官组合的构成成分,例如对象的观念本身……显然,数学背后的这种‘被给予性’与我们经验观念中的抽象元素密切相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第二种所与(data)由于不能关联于某物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行动就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如康德所断言的。相反,它们也表征了客观实在的一个方面,但与感官不同,它们的出现是由于我们与实在之间的另一种关系。”①Kurt Gödel, “What is Cantor's Continuum Problem?”,in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Selected Readings, edited by Paul Benacerraf, Hilary Putna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4, pp.271—272.这个段落以简洁但晦涩的方式表达了胡塞尔的知觉理论,这也是胡塞尔与哥德尔数学哲学的基础。
二、胡塞尔:知觉与直观
传统知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把知觉看作一种接受。被知觉的对象以因果方式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通过神经系统以及大脑的过程,我们在心灵中拥有这个对象的某种表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感官’意味着有能力不带质料地接收事物的可感形式。这必须以如下方式来设想,一个蜡块获得图章戒指的印记但不带有铁或金的质料。”②Aristotle, De Anima, II, 12, 424a18.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转变了这一点。康德把知觉看作更为主动的过程,其中主体给知觉到的东西提供结构。胡塞尔追随康德的观点并且详细研究了这种主动结构。
鸭兔图有助于理解胡塞尔:当我们看鸭兔图时,我们可以看出一只鸭子或兔子。在这两种情况中,到达我们眼睛中的东西都是相同的,所以把知觉看作纯粹接受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种差异必须来自我们。我们对看到的东西进行结构化,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结构化。从外面到达我们的冲动不足以唯一地确定我们所经验的对象;还需要增加更多的东西。我们的意识是如此被结构化的,以至于这样的图像既可以被看作鸭子也可以被看作兔子。胡塞尔把意识的结构化活动称为意向活动(noesis)。每个行为都有一个意向活动。意向活动是经验的,有时间的事件。我们首先将这幅图看作鸭子,然后突然翻转将其看作兔子,接着又突然翻转回来将其看作鸭子,这三种行为是不同的、在数目上有差异的意向活动。然而,第一个和第三个意向活动是非常相似的。如果它们完全相似,那么它们例示相同的意向对象(noema)。意向对象是抽象结构,由意向活动例示。这里,关于类型(type)和标记(token)的区分是有帮助的:意向活动是标记,意向对象是类
型。
两个行为具有完全相似的意向活动,这是很少发生的。在鸭兔图中,如果首先将其看作鸭子,然后发现它也可以被看作兔子,后来又翻转回来再将其看作鸭子,那么第二次将其看作鸭子不同于第一次将其看作鸭子。如果将其看作兔子,那么我在其中学到,不应该过于确定地把这幅图看作鸭子。一旦存在两种意向活动之间的差别,那么相应的意向对象也是不同的。胡塞尔主要致力于研究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之间的关联 性。
我们的意识对经验到的东西进行结构化,如何结构化取决于我们先前的经验,即我们当前经验的整个背景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如果我们在鸭子的环境中长大,甚至从未听说过兔子,那么我们会更倾向于将这幅图看作鸭子而非兔子;兔子的观念很可能甚至没有出现在我们心中。
在胡塞尔看来,我们的所有经验从根本上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结构化;到达我们感官的东西不足以唯一地确定我们所经验的东西。只有在少数情况中,例如在鸭兔图中,我们才能在不同的结构化方式之间任意地进行反复推敲。
我们通常甚至没有意识到正在进行的结构化,对象直接被我们经验为一个有结构的对象。与布伦塔诺的另一个学生弗洛伊德一样,胡塞尔也非常感兴趣于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各式各样的意识活动。我们现在考察一下这些活 动。
首先,我们在知觉中是有预期的。在看鸭子和兔子时,我们的预期是不同的。例如,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预期在触摸时可以感受到羽毛。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预期可以感受到皮毛。如果我们获得了预期的经验,那么相应的意向对象的组成部分被看作充实了的。在所有知觉中总有某种充实:意向对象的某些组成部分对应于当下的“遇到眼睛”,这些部分被充实了,对于其他的感官也是类似的。我们也有关于未来和过去的“预期”。如果我看到面前的一棵大树,转身片刻后,我预期它在我转身回来时仍然在那里。同样地,在这种情况中,我也预期这棵树在我看到它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例如,它出现在一天前相同位置拍摄的照片 中。
这种预期和充实把知觉与其他意识样式区分开来,例如想象或记忆。如果我们单纯地想象事物,那么我们的意向对象可以是任何东西,一头大象站在我面前或一辆火车头停在我面前。然而,知觉包含感官经验;意向对象必须与感觉器官所接触的经验相匹配。这就排除了我在单纯想象时所拥有的许多意向对象。在目前的情况中,我不能拥有关于一头大象的知觉的意向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知觉的意向对象只能被还原为你们坐在我面前的场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任何情况中,我可以拥有许多不同的知觉意向对象,它们都与当下感觉器官所接触的经验是相容 的。
这一点在鸭兔图中是显然的;我们可以在鸭子的意向对象与兔子的意向对象之间任意地进行反复推敲。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中,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只有在意外发生时,即我所遭遇的“顽强不屈”的经验与我意向对象中的预期不相匹配,我才开始看到一个新的对象,它不同于我先前以为我看到的对象。用胡塞尔的术语说,我的意向对象“爆炸”了,我带着新的预期拥有一个新的意向对象,它非常不同于先前的意向对象。胡塞尔认为,这总是可能的。知觉总是包含超出当下“遇到眼睛”的预期,我们总有犯错的风险,无论我们自己感觉多么自信和确定,错误的知觉总是可能的。
三、无中介性
现在,是时候离开鸭兔图了,因为它的一个特征很容易让我们在理解知觉时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用这幅图来说明,任何看(seeing)都是看作(seeing as)。在看鸭兔图时,我们可以将其看作鸭子或兔子。然而,知觉并不总是图像。为了紧跟胡塞尔,我们应该换个例子,不是考虑图像,而是考虑真实动物的轮廓。在我们面对这样的轮廓时,我们可以将其看作鸭子或兔子。
在通常知觉中,什么是按照一种方式或另种一方式被看的东西?当然不是图像。哲学家经常诉诸感觉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感觉材料被认为是我们的感觉器官所把握的无结构的东西,然后被结构化为对象。
胡塞尔并没有引入这样的中介。没有任何被给予的东西是在我们的行为中被结构化的。限制我们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所观察的并被赋予结构的材料。限制我们的东西是在感官被作用时我们通常所具有的经验。胡塞尔把这些经验称为质料(hyle)。在神经系统被干扰时——例如发烧或麻醉,我们也具有质料。但是,我们通常在感觉器官被接触时才具有这些质料。为了产生知觉,我们的质料经验必须与意向活动和谐相 处。
在知觉行为中,质料发挥了限制作用。在想象行为中,我们的行为具有多种多样的意向对象(noema)及其相应的对象(object),独立于我们的感觉器官实际所发生的情况,但知觉行为是受限制的,它的意向对象与质料相容或和谐相处。这个相容性概念是错综复杂的:质料是经验,它们既不具有对象的性质也不具有意向对象的性质。质料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形状。它们具有时间的持续性,但这种持续性不对应于对象的持续性,对象的持续性比我们关于它经验的持续性更长久。质料也不能从一种行为被重新识别为另一种不同的行 为。
四、设定、存在与实在
和谐概念对于理解胡塞尔的知觉理论及其与实在概念的关联是重要的。我先前提到,我在当下情况中具有的意向对象不能对应于一头大象的知觉。然而,我们具有的意向对象可以对应于一头大象的想象。两种意向对象的差别在于一个要素,即设定(thetic)。知觉行为中的意向对象把存在(existence)归属于它的对象,它被经验为实在(reality)。想象行为中的意向对象没有把实在归属于它的对象,质料经验或其他限制条件也不必与意向活动的经验相匹配。
行为的设定特征在胡塞尔的观念论中是非常重要的。设定特征的研究让我们洞察到它对于世界及其对象的意义:“现象学的观念论不否认实在世界的实际存在……它的唯一任务和成就是澄清这种世界的意义,即在什么意义上我们都认为它是实际存在的并且实际有效的。世界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另一个问题是理解这种不可置疑性如何成为生活和科学的基础。”①Edmund Husserl, “Nachwort zu meinen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Husserliana V,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 pp.152—153.这些限制对于我们把世界经验为实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限制是什么?我们表明,对象接触我们的感觉器官就是一种限制。我们的世界观是,我所看到的事物必须相对于我的眼睛而处于特定位置。事物在我面前,这并不是充分的。如果我向着一棵大树转身,而一只兔子藏身其后,那么即使我应该碰巧知道有一只兔子在那里,我也没有与这只兔子相关的质料。因此,在我关于世界和自我的观念与我所遭遇的质料经验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 动。
五、再论预期
我们的预期通常与世界的普遍特征相关。例如,当我们看到下图:
我们将其看作立方体,或者三个平面所形成的角,或者9条线在各个点的相交,或者许多其他的布局。在首次预期与后续预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如果我们将其看作立方体,那么我们预期,如果我们转动它或围着它转,那么它将按照特定方式改变形状。我们可能不太熟悉几何学,不能非常准确地识别出我们的预期,但在关于事物空间移动的以往经验沉淀的基础上,我们很快发现立方体通常显现中的异常情 况。
我们的预期无需建立在关于特定立方体经验的基础上,任意立方体都是可以的。于是,立方体的形状是我们行为的对象,我们了解到这个形状如何在不同视角下显示出差别。胡塞尔把这个对象(立方体的形状)称为本质。这个特定立方体是一个物理对象,但它的形状是一个普遍对象,即一个本质。英语中以-ness或-ity结尾的单词通常都是本质的名 称。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活动都与本质有关,而不是与个体物理对象有关。考虑蒯因和戴维森所谓的语言学习中的“三角关系”:例如,一位母亲通过指着一只狗并说出“狗”来教她的孩子“狗”这个语词。如果这个孩子在这只狗下次出现时说出“狗”,那么他将得到奖赏。表面看来,这个例子包含三个物理对象:母亲、孩子和狗。然而,如果父亲走过来把孩子抱在膝盖上,在这只狗出现时父亲说出“费多”,那么这个孩子可能有些困惑,但他或许认为这两个语词都表示狗。一只新狗再次出现时,孩子说出“费多”,但没有得到奖赏。这只新狗不是费多,而是另一只狗。“狗”这个语词是通名,而“费多”这个语词是专名。为了学会这种差异,孩子必须能够对世界的内容进行个体化,必须掌握两个对子之间的差别:
两滴水是相似的,但由于是两滴,所以它们不是相同的。现在的我与小时候的我是不相似的,但两者是相同的个体。个体化与计数是一回事,它们紧密相关。把“水”这样的物质名词与“玻璃”这样的物质名词区分开来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水是不可分割的,但玻璃是可分割的。蒯因在《语词和对象》以及后来的著作中也谈到这一点,例如,他指出,个体化与我们的时空观是密切相关的。
六、可确定的X
我们现在进入到意向对象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确定的X(determinable X)。胡塞尔也称其为意向对象的对象极(object pole),意向对象的这个组成部分对应于指向一个对象的行为。我们不是经验一堆特征,而是经验一个对象的诸多特征。我们把世界结构化为对象,这些对象具有性质并处于相互关系中。可确定的X具有两个特征,它们都与个体化有 关。
首先,可确定的X构成了对象极,意向对象的其他组成部分围绕这个对象极汇集在一起:我们的经验是关于一个对象的经验,这个对象具有各种性质,这个对象比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更多,虽然它的性质变化了,但这个对象仍然是相同的对象。经过它所有性质的变化以及我们视角的变化,这个对象仍然被经验为相同的:“它提前指向知觉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接连不断地相互融合,构成了知觉的统一性,其中持续的事物总是在一系列新的预兆中表现出新的‘侧面’(或者旧的‘侧面’)。”①Edmund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iana III, 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91.
其次,可确定的X也给我们关于数目上不同的几个对象赋予意义,但是这些对象非常相似。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对象与我们先前遇到的对象非常相似,那么我们仍会提出以下问题“这是一个相同的对象还是不相同的对象?”相反,一个对象可以改变它的性质,看起来非常不同于它以前的样子,但仍然是相同的对象。可确定的X使我们区分了前面提到的两个对子:相同与不相同,相似与不相似。两个事物虽然相似但可能不相同。一个事物虽然变化了但仍然是相同 的。
因此,可确定的X说明了,错误的同一性究竟错在哪里。“不能进入到辨识意识的统一性中,就不能把一个人搞糊涂”——这是胡塞尔在1911年手稿中写下的。他在这份手稿中讨论了“孪生世界”问题,这个问题表明他早期关于指示代词的理论是不充分的。胡塞尔讨论的问题是:“如果两个天体上的两群人处于完全相似的环境,考虑‘相同’的对象,作出‘相同’的判断,这将会怎样?在这两种情况中,指示代词‘这一个’具有不同的意义吗?”②Edmund Husserl, Vorlesungen über Bedeutungslehre, Husserliana XXV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7,pp.211—213.胡塞尔对此给出一些有趣的评论,但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他关于可确定的X的观念使他理解了这个问题的意义,60年后普特南在“孪生地球”的思想实验中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 题。
七、本质洞见=本质直观
当我们观察一个对象时,例如一个三角形的交通标志牌。我们会把这个个体物理对象看作我们行为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指向这个个体物理对象,我们在特定的位置上已经看到这个标志牌很多年了,它也逐渐开始褪 色。
然而,我们行为的对象也可以是一个本质,例如这个对象的三角形。我们的行为可以指向三角形或等角三角形或等边三角形或这幅图所例示的其他本质。如果我们行为所指向的本质是三角形,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交通标志牌替换为一个修剪得很漂亮的圣诞树,我们的行为将会具有相同的对 象。
再看如下三幅图:
人们把其中哪两幅图看作相似的?许多人认为,瓷杯和玻璃杯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用于喝水。而少数人特别是学习拓扑学的人认为,瓷杯和甜甜圈是相似的,因为通过连续变换,它们形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瓷杯和甜甜圈都有“一个洞”,但玻璃杯没有。这两种答案都是正确的。在这三幅图所例示的本质中,瓷杯和玻璃杯例示了“喝水容器”这个实用特征,瓷杯和甜甜圈例示了“单一孔洞”这个理论特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频繁地关注于本质而非个体物理对象。我们与对象有很强的情感联系,我们感受到与一个人的亲近关系,或者,我们在睹物思人的意义上感受到与一个对象的亲近关系,例如,一枚订婚戒指、我的祖父制作的钟表或者前面提到的那只狗,主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象的个体性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我们通常是作为个体对象而与人类相关联,但即使人类也经常被看作一个种类的例示。即使有些关系在传统上被看作深刻的人性并且表达了深情,这些关系最终也是一个种类的成员,例如与某人在满足性欲方面的关系。
知觉行为的对象是个体物理对象,但胡塞尔把这样的知觉仅仅看作一般行为的特殊种类,这种一般行为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行为对象的洞见。胡塞尔把这些行为称为直观行为或直观。有两类直观:知觉和本质直观,前者的对象是物理对象,后者的对象是本
质。直观通过设定可以与其他种类的行为区别开来:我们把直观的东西看作实在的而非单纯想象的。直观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行为对象的洞见。当我们直观一个对象时,我们预期了这个对象的各种特征。我们的预期有时得到后续经验的确证,但有时这些预期没有得到充实,我们不得不修正我们看到对象的方式。如前所说,实在性与限制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知觉不同于想象,直观也不同于想象。
现在我们可以搞清楚前面引自哥德尔的晦涩段落,一言以蔽之,这个段落就是在回答数学基础方面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有非物质对象吗?“有些超出感官的东西实际上是被直接给予的,这一点(独立于数学)是从如下事实得出的,即使我们指称物理对象的观念也包含了在性质上不同于感官或纯粹感官组合的构成成分,例如对象的观念本身。”①Kurt Gödel, “What is Cantor's Continuum Problem?”,pp. 271—272.也就是说,知觉并非单纯地是物理对象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结果。知觉也是有结构的。我们知觉到物理对象,但是物理对象的观念包含了一个全面的结构,涉及算术、几何以及其他数学分支。例如,物理对象的观念包含了个体化的想法:诸多特征被汇集起来归属于相同的个体。个体之间虽然相似但仍然不相同,它们经历变化但仍然保持同一性。对象的结构化以及它们的性质和关系对于知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抽象要素都成为我们所知觉的东西;没有这些抽象要素,就没有知觉。它们是经验世界的特征,但它们不是知觉的对象而是本质直观的对象。我们预期了这些特征,但这并不使这些特征比物理对象更具有主观性,物理对象本身也是这些特征的一部 分。
其次,我们如何认识非物质对象?“显然,数学背后的这种‘被给予性’与我们经验观念中的抽象要素密切相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第二种所与(data)由于不能关联于某物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行动就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如康德所断言的。相反,它们也表征了客观实在的一个方面,但是与感官不同,它们的出现是由于我们与实在之间的另一种关系。”②Ibid.因此,我们经验到“我们经验观念中的抽象要素”,这不是因为它们是以因果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物理对象,而是因为它们是同样客观实在的要素。我们在关于世界的经验中进行预期,然后在关于世界的后续探索中放弃或修正这些预期。所以即使“我们经验观念中的抽象元素”也受到限制并需要修正。
如前所说,经验限制对于把某物看作实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给出信念并作出预期,对后续经验进行修正。把某物经验为实在的,这意味着我们觉察到它的存在和性质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数学不同于象棋,象棋受限于我们所制定的规则。但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规则,这是在象棋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如足球和其他体育运动中所发生的规则改变。反对者或许认为,数学中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例如,人们发展出新的几何理论。但是非欧几何最终运用于物理学。从数学角度看,任何几何理论都是对一个结构的探索。所有数学分支中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从纯粹形式角度看,有些结构被证明是非常有趣的。例如,在代数中被称为“群”的简单数学结构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类似地,数学中的其他想法也提出新的洞见并探索了非常有趣的结构。
哥德尔经常回到数学中的限制与数学对象的存在之间的关联:“数学家的活动很少表现出一个创造者所享有的自由。例如,虽然整数的公理是一个自由发明,但仍然必须承认的是,在设想出研究对象的初始公理后,数学家停止了他的创造力,他也不能任意创造定理的有效性。如果数学中有任何创造性,那么定理所做的恰恰是限制这种自由创造。然而,限制性显然独立于创造性。”①Kurt Gödel, “Some Basic Theorem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Kurt Gödel:Collected Works, Vol. III, edited by Feferman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14.
以下引自哥德尔的段落也支持了胡塞尔式的解读。首先,关于数学对象的客观存在:“数学直观对象的客观存在问题(顺便提一下,这个问题恰好是外部世界客观存在问题的翻版)。”②Kurt Gödel,, “What is Cantor's Continuum Problem?”, p.272.其次,关于知觉与数学直观:“虽然远离感觉经验,但我们就集合论的对象而言确实有某种类似知觉的东西,这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公理迫使我们承认其为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这种知觉(数学直观)比对感官知觉更缺少信心,后者引导我们构建物理学理论并期望与未来的感官知觉相一致。”③Ibid., 1964, p.271.
八、数学中的归纳法
如我们所看到的,胡塞尔与哥德尔给出了物理世界经验与数学中抽象世界经验之间的一些平行关系。我们也将看到,他们在方法上也有相似性。如下重要段落引自哥德尔的吉布斯讲座:“如果数学像物理学那样描述了客观世界,那么没有理由认为归纳法不应该像在物理学中一样运用在数学中。事实是,我们当今对待数学的态度仍像过去对待所有科学的态度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试图从定义(用本体论术语来说,从事物的本质)按照有说服力的证明来推出一切。如果这种方法想要垄断一切,那么它在数学中与在物理学中一样都是错误的。”④Kurt Gödel, “Some Basic Theorem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p.313.关于类与概念,哥德尔还写道:“对我来说,这些对象的假设似乎与物理对象的假设一样都是合法的,非常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存在的。在相同的意义上,它们对于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学系统来说是必要的,正如物理对象对于一个令人满意的感官知觉理论来说是必要的,在这两种情况中都不可能把人们关于这些实体所断定的命题解释为关于‘所与’的命题。”⑤Kurt Gödel, “Russell's Mathematical Logic”, in 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44, p.137.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段落写于哥德尔研究胡塞尔之前。这就证实了,哥德尔在研究胡塞尔之前已经具有了与胡塞尔类似的想法。据说,胡塞尔为这些想法所提供给的系统性框架给哥德尔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胡塞尔与哥德尔一样,他们都坚持认为,数学与物理学一样都通过假设展开:我们首先提出与边界条件似乎相匹配的假设,然后研究它们如何匹配,从它们之中得出结论,再检查这些结论是否匹配。
九、哥德尔论数学中的证据
哥德尔认为,我们对数学对象有某种类似于知觉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数学可以达到确定性。知觉和本质直观都不是不可错的证据来源。它们总是涉及关于对象各个方面的预期,这些预期尚未被探索,有可能最终是错误的。胡塞尔承认,即使在数学和逻辑中错误也总是可能的。哥德尔概述了四种方法,人们借此来获得关于数学领域的洞见。
第一,基本结论。正如我们通过可观察的预言来检验高度普遍的物理学理论,哥德尔认为,数学对象“在相同的意义上对于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学体系来说是必要的,正如物理对象对于一个令人满意的感官知觉理论来说也是必要的”①Kurt Gödel, “Russell's Mathematical Logic”, p.128.。哥德尔也指出,深奥的公理也具有基本结论。因此,在讨论各种无穷公理时,哥德尔认为,“可以证明的是,这些公理在超穷数领域之外也具有结论,这是这些公理的直接主题:在一致性的前提下,每个主题都可以增加可判定命题的数目,即使在丢番图方程中也是这样”②Kurt Gödel, “What is Cantor's Continuum Problem?”, p.264.。
第二,“成功”。哥德尔还指出另一个原因说明我们为什么把一个公理看作真的:“关于真理的概然判定按照另一种方式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通过‘成功’来归纳地学习。这里,成功意味着结论的丰富性,特别是可证实结论的丰富性,即在没有新公理的情况下可演证的结论,但是,在新公理的帮助下这一证明过程变得简单并且易于发现,也有可能把许多不同的证明缩减为单一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直观主义者所拒斥的实数公理系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实。”③Ibid., p.265.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推导出新定理,而是以优雅的方式从公理中推导出旧定理。这种简化经常是通过以新的方式看待旧的材料来实现的。
第三,澄清。有时我们发现,两个或多个非常不同的类都可以满足我们所设定的公理。于是,通过反思这些公理所要试图捕捉的概念,我们发现,其中一个类不匹配于这个概念。哥德尔认为,“可以猜想的是,连续统问题不能在现有公理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在新公理的帮助下可能得到解决,这些新公理表述了或蕴涵着集合的可定义性。”①Kurt Gödel, “What is Cantor's Continuum Problem?”, p. 266.
第四,系统性。在一份讨论胡塞尔现象学的手稿中,哥德尔提到第四种获得新公理的方法,也就是说,按照系统方式来安排公理,以此使我们发现新公理:“在数学公理的系统性安排中,虽然新公理不是按照形式逻辑的方式从已有公理中得出的,但新公理三番五次地变得显明。任何明确提出的是或不是的问题都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得到解决,这并没有被不完全性定理这个否定性结论所排除。越来越多的新公理在初始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变得显明,机器不能模拟这种显明性。”②Kurt Gödel,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in the Light of Philosophy,” in Kurt Gödel: Collected Works, Vol. III, editedby Feferman, et al.,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 385.
胡塞尔提出过证成的“反思均衡”方案③参见Dagfinn Føllesdal, “Husserl on evidence and justification,” in Edmund Husserl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Essays in Phenomenology,edited by Robert Sokolowski,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8, pp. 107—129.,系统化作为一种澄清概念的方法被胡塞尔赋予重要意义。这在他的证成观中是一个重要因素。
——论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时间观的继承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