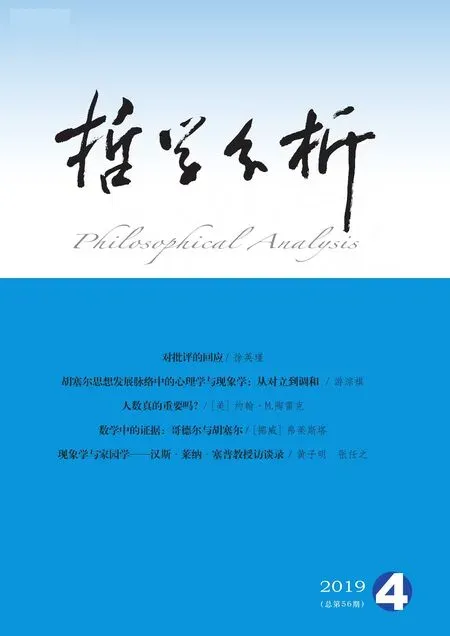规范性、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评徐英瑾的新著《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
徐 竹
导 论
在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中,主张自然主义立场的哲学进路,与偏重规范性立场的哲学进路之间形成持续的分野与争论,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常见的学术景观。前者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上立论,主张任何有意义的哲学思考都必须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追随科学的教导;后者则更多地继承了早期分析哲学所谓“意义澄清”的工作筹划,认为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领域,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在其中并不特别有助于哲学工作,这就是规范性议题的研究。类似的论证与争论遍布于当代哲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在心灵哲学、知识论、科学哲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中,一再地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反复呈现。
从学理逻辑上说,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传统影响的中国学者,在这场争论中是不应该缺席的。因为,从哲学上的自然主义到物理主义,再到唯物主义,存在着一条畅通无阻的学理路径。马克思本人在其经典著作中所做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论证了人类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和法律等规范性的存在本质上都不过是具体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产物。这既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同时也是对规范性议题作出的自然主义解释。然而,囿于学术传统的差异,真正能够从唯物论观点出发,在规范性与自然主义的争论中提出一家之言的理论努力尚不多 见。
徐英瑾教授的新著《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 (以下简称“《唯论》”)就是这一方向上的杰出成果。纵观全书,一方面徐英瑾充分利用了“从自然主义到物理主义再到唯物主义”这个畅通的学理路径,引入分析形而上学的思想资源来丰富唯物论观点;另一方面,他又用精致化了的唯物论观点反观规范性,对传统的规范性议题提出解释和思考,为这场争论中的自然主义立场提供了新的辩护。
如果笔者的上述理解是正确的,那么,评判《唯论》这项工作的价值,就要看它对规范性议题的解释是否深入和有效。全书写作计划非常宏大,笔者的考察将集中关注书中的两个要点。一是《唯论》在解释规范性方面的总体工作设想,即它对“唯物论需要怎样的规范性理论?”这个问题的回答;二是《唯论》对一个具体的规范性议题的处理,即是否存在不能以非规范性词项描述的“规范感”?①《唯论》书中实际讨论的是“道德的感受质”或“道德的主观感受”。但严格说来,道德只是众多规范性议题之一,而对它的感受质问题并非特殊的,而是在几乎所有规范性的方面,譬如遵从法律或交通规则等,都可以提出类似的疑问。因此,真正在规范性的理论层面提出的是有无特殊“规范感”的问题。对这两个方面的讨论将试图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一种唯物论的规范性理论,帮助我们较为具体地评判这一理论的内涵与意义。
一、规范性理论的唯物论进路
唯物论需要怎样的规范性理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好问题。而这种探究首先依赖如何界定唯物论。在《唯论》一开始,作者便提出了一个“本体论范畴树形图谱”(见图1),用以概括作出探究出发点的唯物论基本立场。具体说来,它将所有存在的事体(entities)分为三个框:甲框是只能做主项的具体存在物,包括事物、事件和“蕴相殊”(tropes)②通常多被译为“特普”,是指普遍的属性共相被当作具体殊相的概念。例如,红色一般来说是属性共相,但此花的红与彼花的红又是不同的“特普”,所以一般意义上的“红”只不过是众多红色特普的集合。(徐英瑾:《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唯论》中采用“蕴相殊”对译“tropes”,为保持一致,这里也采用此译法。,乙框是既可以做主项也可以做谓项的抽象物,包括集合、命题与事物的“分体论之和”①按照《唯论》的说法,分体论之和是“一个整体的某些部分所构成的和”,而这样的加和关系“并不是诸实体所构成的堆”(第35页)。这意味着分体论和要求有某种整体论的关系存在,组分内在地依赖于整体。(mereological sums),而丙框则是只能做谓项的共相,主要是指属性和关系的存在。
按照徐英瑾的看法,上述甲、乙、丙三框的分类,实际上厘定出了唯物论—反唯物论之争的概念空间。从唯物论的立场上说,甲框中的对象是最基本的,其他类型的存在物都必须或者被视作并不真实存在,或者被视作是甲框对象的逻辑衍生物。反唯物论者——特别是柏拉图主义者则必须视丙框为最基本的对象,而将甲、乙两框的对象看作是衍生出来的存在物。所以,在“唯物论—反唯物论”的争论中,乙框就是双方胶着论争的战场,它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基本盘,但又同时是任何一方都试图争取拉拢的“中间地带”。“一种完善的唯物论或柏拉图主义理论,也势必应当努力将这个中介地带中的本体论对象,化约为自身‘基本盘’的理论衍生物。”③同上书,第36页。但是,不管是唯物论还是反唯物论,都不能否认乙框的对象有其不可取消的相对独立性。例如,作为乙框对象的命题就有独立评价的维度。我们可以仅仅立足于命题的层面上讨论它的性质、命题间的推论关系,而不需要介入唯物论—反唯物论的争论。所以,完备的唯物论观点还要为乙框对象的相对独立性留出合理的空间。《唯论》的这个本体论范畴框架对规范性理论尤为重要。总的说来,规范性的存在也是乙框的对象,因而它们也必须是甲框的逻辑衍生物,但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可以仅仅在规范性的层面上讨论相关议题,而并不需要总是回溯到其唯物论的基础上去。这样的规范性理论才是唯物论所需要的。然而,从理论建构上走到这一步,还需要更多铺垫。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如何从描述跨越到规范。毋庸赘述,规范性问题的缘起就是“是”与“应该”的二分,所谓“休谟的铡刀”是也。如果这种二分可以从理论上被接受,那么意味着从“实际如何”的描述推不出“应该如何”的规范性判断;反过来,从“应该如何”的判断也无法揭示“事实究竟如何”。而《唯论》的上述本体论范畴都是分析形而上学的成果,其本质就是要回答“在世界中实际上存在着什么”的问题。①徐英瑾:《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第39页。那么,这样的范畴框架如何能够运用于对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呢?
徐英瑾的思路是,在回答“唯物论需要怎样的规范性理论”之前,先要思考它需要怎样的模态理论。这其实也是讨论规范性问题的常见路数。描述性判断不仅仅对规范性判断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它与因果必然性或自然定律的判断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鸿沟。如果我们仅仅描述了“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什么”,那么似乎既不能由此推出“应该怎样”,也不能推出“必然”或“可能”怎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规范性与因果性、必然性、自然律等一起都属于模态范畴。模态判断区别于纯粹描述性的判断,因为对模态判断的真假赋值,不仅需要考虑事实上的“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更需要支持反事实条件(counterfactuals)的考察。譬如,如果“人不应该说谎”为真,那么即便在谎言带来利益的情况下,人也没有理由说谎;如果“铀235超过临界质量必然发生链式反应”,那么这种必然性就体现在,假设月球是全由铀元素组成的,那么月球的质量也不能超过临界质量。不难想见,仅靠纯粹描述现实世界的判断无法决定上述反事实条件成立与否。
因此,对模态理论来说,最关键的是如何评价反事实条件的真值。徐英瑾认为,对唯物论立场来说,恰当的模态理论可以是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的“组合论”。按照这种观点,模态属性只不过是“在对世界的构成要素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之后所自动产生的衍生性性质”。例如,对“必然性”这一模态性质,组合论可以解释如下:“如果现实世界中存在着n个基本对象,那么这一点就是必然成真的:无论你如何排列这些对象,任何排列方式都不会导致少于n的基本对象数量。”②同上书,第58—59页。换言之,尽管模态性质并不直接由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所决定,但模态性质可变的界限却是由现实的描述决定的。一方面,这种模态理论的确是唯物论的,因为模态存在作为“乙框”对象的确是“甲框”对象的衍生物;另一方面,模态判断的相对独立性也得到了保证,因为在现实世界厘定的界限之内,每一个模态性质并不需要通过追溯其对应的描述性质而得以确定。基于这两点,唯物论的规范性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规范性的功能主义解释
当代哲学对“规范性”的讨论涉及诸多领域的话题。普通人一提到“规范”二字,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人不应该说谎”之类的道德规范。但哲学上的讨论要远远广义得多。例如,规范性概念在心灵哲学上是心理表征的诚实性(veridicality)要求,在知识论上是对知识与真信念的辩护(justification)与保证(warrant),在科学哲学上是对科学研究作方法论上的“合理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等等。《唯论》特别强调的是认知科学哲学的视角,“认知”几乎已经涵盖了包括道德判断在内的人类心智活动的一切方面,而《唯论》的工作就是致力于推进一种“认知科学化的规范性研究”①徐英瑾:《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第63页。。
基于这样的认识,徐英瑾在规范性理论方面主要借助了柏芝(Tyler Burge)在《客观性的起源》中的论述。柏芝所讨论的主要是心理表征的规范性。在他那里,规范性意义之所以存在,首先是由于存在着一种不同于生物学功能的“表征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而人们在表征功能方面做得好不好,完成到怎样的水准,决定了心理表征的规范性意义:
某些完成的水准也就是作为规范的标准。规范就是可能的行为表现的标准,那些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能充分完成某个功能或目标。对任何功能而言,这种意义上的规范乃是先天存在着的。
有的规范是自然规范。我所说的“自然规范”,并不是指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可还原的规范,而是指某种行为表现的水平,它足以完成某个功能或目标,构成了某种在解释上相关的类型,且无关乎任何个体究竟是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态度对待此功能或规范。②Tyler Burge, Origins of Objectiv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11.
所以,柏芝对规范性概念的刻画,一言以蔽之,就是作为“功能实现的完成度”的标准。这也是通常容易被想到的自然主义解释策略。的确,很多规范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们对实现某个目的或功能提出了标准和要求。例如,学习射箭时,你需要遵从教练提出的指导性规范,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帮助你完成“射中靶心”的目标。自然主义的解释从中提取出“功能—完成”的模式,作为规范性存在的一般依据,进而拓展到其他非人类、非意识层面的功能实例。例如,正在捕食的老虎追逐它的猎物,胃的正常蠕动实现胃酸对食物的分解和消化,这些都是有目标设定的功能过程,都有一个完成度标准的问题,因而也都存在柏芝意义上的“自然规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类行动的规范都需要还原为非人类、非意识层面的自然规范,因为只有在具体的功能过程之中才有规范性的存在,而不同的功能从内涵意义上说并不能相互替换。正如柏芝所强调的,表征功能并不是任何生物学功能,心理表征的规范性也未必一定有还原论意义的解释。但这至少表明,所谓规范性的存在其实并不神秘,并没有什么超越于自然主义—唯物论的意义。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解释的讨论中,有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就是“功能解释是不是基于定律和因果性的科学解释”。围绕这一话题,科学哲学家在“功能”与“自然定律”“因果解释”这几个概念之间展开了复杂的辨析与推论。这里并不试图深入呈现其中的复杂性,但回顾这些关联有助于我们理解柏芝思路的另一个面向:功能过程并不能脱离定律与因果必然性而存在。以前面的例子来说,如何完成射中靶心的功能?老虎如何能追捕到它的猎物?胃如何能正常地发挥消化食物功能?显然,要从科学上彻底解释这些功能完成的可能性,就必须诉诸一系列具有因果必然性的关联:譬如,射出箭的速度与风向、距离等环境因素的关系,老虎的加速度与周边环境的配合,支持胃正常蠕动的自主神经活动,等等。在这些必然性关联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得到诉诸定律与因果性的解释;与此相比,功能解释则更像是一种限定范围的理解。如果我们把解释的努力限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那么就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系统目标:射中靶心、捕食猎物、消化食物,于是就有功能解释。但如果我们的解释并不预设任何系统目标,那么就会看到,所有功能解释的有效性都需要定律和因果必然性的解释提供依据和支撑。
如果上述理解是对的,那么规范性的意义依赖某种具体与之对应的功能解释,而功能解释又进一步地依赖定律和因果必然性的存在,所以规范性的概念也最终奠基于定律与因果性的概念。这其实也是规范性的自然主义解释的大体归宿。前面提到,规范性与因果性都是模态概念,并在这个意义上都区别于纯粹的事实描述。然而,在自然主义—唯物论的解释中,这两种模态概念的地位是不对称的。从解释的优先性上说,规范性的存在最终需要由定律和因果性的意义来解释,反之则不成立。我们已经看到,根据阿姆斯特朗的组合论观点,任何因果必然性的模态性质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世界要素组合的衍生物,所以,由这种模态性质来解释的规范性意义最终也是现实世界要素组合的衍生性质的。需要注意的是,逻辑上的衍生并不必然意味着还原的可能性。因为,以“功能—完成”关系作为规范性与因果性之间的中介,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恰恰保证了规范性意义的相对独立性:尽管功能解释最终依赖定律与因果必然性的关系,但当我们限定解释系统的边界时,我们的确可以面向所预设的系统目标,仅从功能上解释现象,而不同的功能过程之间在内涵层面无法被替代或还原。《唯论》针对柏芝的观点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当他[柏芝]说什么“心理学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感觉系统的生物学功能的确与表征功能比较相近;心理学之所以有趣,又是因为前述两种功能并不同一”的时候,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无非就是下面这层意思……“乙框”中的规范性描述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这种描述在所指的外延方面与“甲框”中的事实描述所指涉的外延足够接近;而“乙框”中的规范性描述之所以有趣,乃是因为“甲框”与“乙框”各自的描述层次在内涵方面无法彼此替换。①徐英瑾:《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第65页。
回到《唯论》一开始给出的本体论范畴划分,唯物论解释的基本盘是“甲框”的具体对象,而规范性的存在则是“乙框”中可主可谓的抽象对象。我们还曾说,完备的唯物论观点一定要将乙框对象作为甲框对象的逻辑衍生物,同时又保证其相对独立性,即可以仅仅在抽象对象层面谈论规范性的存在及其相互关联。由上可见,将规范性刻画为“功能实现的完成度”的标准的确兼顾了这两个方面。因此,它就是唯物论所需要的那种规范性理论。
三、因果与规范:何为优先?
那么,这种规范性理论是否会有什么问题?以“功能—完成”的关系刻画规范性,是否会有所遗漏?实际上,20世纪的美国社会学曾经有过值得汲取的教训。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主流社会学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功能主义将社会类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任何制度规范都必须从它保持并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功能必要性上来解释。在帕森斯的理论框架中,“结构”与“行动”深陷于不平衡的关系,个体行动者的作用越来越被边缘化,完全沦为实现制度结构之宏观功能的工具。因此,帕森斯的批评者指出,在功能主义纲领下,行动者不过是一个“傀儡”,他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完成社会有机体运转所必需的功能角色。
帕森斯功能主义中的“结构”与“行动”的不平衡关系,与唯物论的规范性理论的一个要点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规范性与因果性在模态地位上的不对称性,或者说是在自然主义—唯物论框架中,因果性相对于规范性概念具有解释上的优先地位。如果我们把“规范性”理解为个人行动上的合理意义,而把社会宏观的结构和功能看作是因果机制的体现,那么模态地位上的不对称关系立刻就被转化为帕森斯那里的“结构”与“行动”的不平衡关系:结构可以用于解释行动,而行动却不是结构的解释项。
当代美国哲学家布兰顿(Robert Brandom)是在规范性问题上建树较多的学者。在他看来,由因果性解释规范性的不对称关系,甚至是由现实世界的要素决定模态衍生性质的“组合论”观点,都不仅仅应该被放弃,而恰恰是应该被颠倒过来:不是描述性质决定模态性质,而是使用模态概念的能力决定了作出描述性判断的能力;不是因果性在解释上优先于规范性,而是所有“真性模态”(alethic modality)①布兰顿区分了两种意义的模态概念。定律和因果性意义属于“真性模态”的概念,而规范性的存在属于“道义模态”(deontic modality)概念。的意义都取决于规范性的模态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康德—塞拉斯论旨”:
1.在普通经验词项的使用中,人们已经做了所有需要他们做的事情,以便引入并掌握模态词项的使用。
2.真性模态词项的特殊表达功能在于清晰阐释语义的和概念上的联系与承诺,这些联系与承诺原本已经隐含在普通经验词项的使用之中。②Robert Brandom, 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2.
布兰顿主要讨论的是语言哲学中的规范性话题,在他那里,规范性的存在主要就是概念间的语义关系与推论性联系。布兰顿自身又是实用主义在当代的主要辩护者,这决定了他不会像分析形而上学那样讨论本体论问题,但当布兰顿试图在不同类型的词项使用之间确立秩序时,他的确是在考察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优先性关系。例如,在“康德—塞拉斯论旨”的第1项,布兰顿实际上主张,模态性质在本体论上优先于经验中的描述性质。这表明布兰顿并不是唯物论者,他潜在地希望“乙框”对象作为“丙框”的而非“甲框”的逻辑衍生物,所以这对于唯物论的规范性理论并无特别的帮助。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2项,它主张定律和因果性的模态性质“表达”了规范性的语义关系,因而应该用规范性的性质来解释定律和因果必然性,而不是相反。所以,在布兰顿这里,是规范性而非因果性处于模态解释上的优先地位。这对唯物论的规范性理论来说倒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为了让一个解释深入和有效,解释项必须站到被解释项的“背后”,以便提供更深层的和有教益的(informative)的解释。如何澄清这个“背后”的隐喻?在笔者看来,布兰顿与《唯论》所诠释的柏芝分别代表了两种“站到背后”的路径。在柏芝那里,这意味着追溯功能实现的链条。规范性意义是这个链条的起点,它之所以存在,乃是为了以某个标准完成相应的功能目标,进而任何功能目标的完成都立足于某些普遍存在的定律与因果必然性。所以,因果性必须站在规范性的“背后”,因为若没有这种必然性,我们就无法确立规范性的意义。
而在布兰顿看来,这是要对使用各种概念从事语言游戏的能力作一种追溯前提的考察。在这种追溯中,定律和因果必然性不仅不是已经在“背后”的解释项,而恰恰应该是追溯的起点。因为对因果必然性的概念把握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我们之所以具备使用这类概念的能力,恰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开展有效的推理。例如,“铀235超过临界质量必然发生链式反应”,这是定律必然性,它意味着我们可以从“铀235超过了临界质量”必然推出“马上要发生链式反应”的结论。概言之,定律与因果必然性这样的模态判断,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功用,恰是表达了不同判断之间“必然推出”的语义关系,而这正是规范性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规范性反倒站到了因果性的“背后”,因为它才是发展更丰富的语言能力的前提:只要我们开始使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我们就已经是在一个规范性的意义空间中生存和思考。
这两种路径的分歧与对立,就与对“规范感”的讨论联系了起来。《唯论》中具体讨论的是主观的道德情感,它本来就是众多类型的“规范感”之一。主张“规范感”存在的人可能提出一个类似于心灵哲学“僵尸论证”的辩护:可以设想物理层面与人类相同,而缺乏对规范性存在的“现象体验”的哲学僵尸,而这样的僵尸无法真正成为规范性行为的主体,所以生物学无法说明道德情感这样的“规范感”。而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也基本套用了物理主义对“僵尸论证”的反驳,也就是否认哲学僵尸的可设想性:“我们很难相信:就两个在见到孺子入井后就立即去伸手救援的人而言,如若两者行为相同,在救人时所经历的神经活动也相同,其中的一‘人’(即所谓‘僵尸’)竟然会缺乏‘恻隐心’而另一者则有之。”①徐英瑾:《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 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第188页。
从柏芝所代表的路径上看,这一反驳是完全成立的。如果“规范感”只不过是对规范性存在的现象体验,而所有规范性关系在功能上都依赖某些定律与因果必然性的奠基,那么只要我们从认知科学中把握到这样的模态性质,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在规范感方面有所缺失。然而,如果从另一条路径上来理解,情况就稍有不同了。对布兰顿来说,规范感并不仅仅是像“恻隐心”这样的感受,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它可以是对概念间语义推理关系的现象性把握,某种对人类话语实践规则的模糊的体会。借助认知科学的概念对神经活动的描述和判断,既是人类话语实践的组成部分,也是对这种语义推理关系作清晰阐释的努力,而规范感作为被因果必然性表达的东西反倒具有模态地位上的优先性。所以,哲学僵尸的不可设想性恰好表明,只有以规范感——对神经科学概念的语义关系的隐性把握为前提,我们才能具备使用这些概念并作出定律与因果必然性判断的能力。
四、历史唯物论的规范性理论:一种新可能
那么,我们有可能采纳布兰顿那样的路径吗?不要忘记,《唯论》的目标是建构一种唯物论所需要的规范性理论,其中并未借助布兰顿的工作,可能主要也是考虑这其实是反唯物论的思路。不过笔者认为,似乎可以将“康德—塞拉斯论旨”的第1项与第2项分开来看,这样把布兰顿的解释路径从其反唯物论的立场中解脱出来,也并非不可能。因为我们所要建构的并不是一般唯物论的而是“历史唯物论”的规范性理论。
《唯论》其实已经花了很多篇幅讨论历史唯物论,但主要是从分析形而上学的视角为历史唯物论提供本体论的基础,却没有特别将这一思想资源引入对规范性理论的讨论中,殊为遗憾。笔者并非马克思哲学的专家,但就愚见所观,历史唯物论区别于一般自然主义—唯物论立场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为“个体—整体”“行动—结构”的张力关系提供了内涵特别丰富的阐释。一方面,历史唯物论像所有唯物论立场一样,强调个人受制于整体,行动限定于结构——用《唯论》的语言说,就是所有乙框的对象都只是甲框具体对象的逻辑衍生物。但另一方面,历史唯物论又肯定了这样的可能性:具有特定特征的个体——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够重塑结构与整体,因为这样的个体能够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即是将规范性的存在重塑为现实世界中可以描述的具体性质或对象。
不难看出,历史唯物论的后一个面向很容易与布兰顿的解释路径相联系,因为它们都可以承认,对规范性关系的把握的目的在于获得变革现实世界的能力。当马克思批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他更是实质性地接近了这个思路。但历史唯物论的解释毕竟不同于布兰顿的反唯物论立场,因为通过对规范性存在的把握实现的只是对世界的革命性重塑,而不会是从无到有的创生。用《唯论》的话来说,“乙框”中的任何规范性存在都不过是“甲框”要素排列组合的产物,其基本可能性不会超出本体论上多重组合的可能性。但“武器批判”的革命性恰恰在于,由于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的存在,某些重要的“组合可能性”已经被默认为不可能了,只有通过对乙框中规范性关系的把握,才能将这种被压抑的可能性重新召唤出来,而这就是对世界的革命性重塑和全人类解放的实现。
笔者不得不说,就一种历史唯物论的规范性理论而言,类似的话题还有必要继续延伸下去,但对《唯论》的评论却可以止步于此了。事实上,话题延伸的可能性已经揭示了《唯论》这项工作毋庸置疑的价值。如果说还能从方法论上作一点批评的话,我愿意提及这样的观察:自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论学说以来,很多人都说马克思本人用力甚多的是“上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但还需要“下半截子唯物主义”的补充,也就是本体论存在论的部分。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都是在尝试做类似的工作。《唯论》似乎也在同样的方向上提供补充,只不过它更多地借助分析形而上学的当代成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也有很多人并不赞同这种分“上半截子”与“下半截子”的解读方式,因为历史唯物论并不是唯物论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简单应用,而毋宁说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后的成熟形态——它本身就是新哲学的成熟本体论。这种解读也未必见得完全正确,《唯论》中也确实指出了其中的偏颇与疏漏之处①徐英瑾:《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第70—71页。,但就规范性问题的讨论来看,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