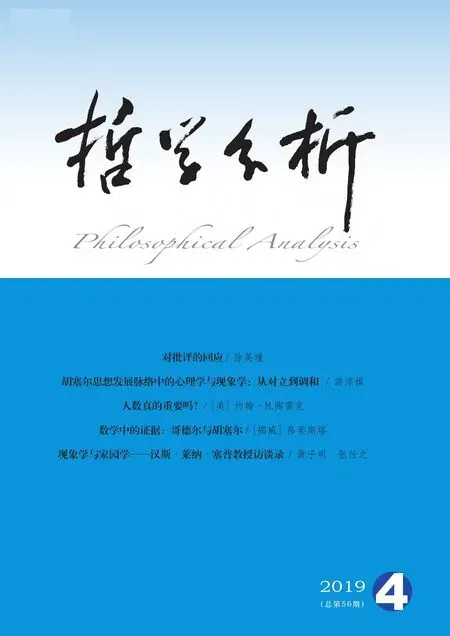反思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任 俊 孙宏赟
自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题为《什么的平等》的著名演讲中提出“能力”概念以来,能力进路(capability approach)在学术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社会科学领域,能力进路被广泛用于发展、贫困、公共服务等问题的研究。而在政治哲学领域,能力进路主要被用于构建正义理论。在发展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方面,当代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工作值得我们重视。①森和努斯鲍姆是捍卫能力进路的两位最重要的理论家。尽管森在正义问题上也有不少论述,但他主要是将能力作为评价社会正义和生活质量的关注焦点和信息基础,而没有提出明确的分配正义规则,其倡导的能力进路并不直接带有公共政策的含义。森拒斥所谓“先验制度主义”(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的主张,他认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不是制定完美的规则、实现绝对的正义,而是鉴别和消除明显的不正义。(参阅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相比而言,努斯鲍姆的理论旨趣更接近主流的正义理论,她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含正义规则的“最低限度的”正义理论,并希望以此对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发挥影响。在运用能力进路发展规范的正义理论方面,努斯鲍姆比森走得更远。森本人也承认,努斯鲍姆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对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的考察,将主要关注努斯鲍姆的版本。努斯鲍姆试图在挑战契约论这一经典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开启正义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她不仅提出要以能力作为衡量正义的尺度,而且捍卫以保障核心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正义原则。通过对能力进路正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本文试图指出:目前这一理论本身存在不少困难和疑点,还不足以成为我们研究正义的主要理论框 架。
一、单纯能力不足以评价个人福祉
能力进路的核心论点就是以能力作为信息焦点,评价个人福祉乃至社会正义。根据能力进路,判断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处于优势还是劣势,不是看他的主观偏好是否得到满足,也不是看他拥有多少资源,而是看他实际上能够做什么或成为什么。
不可否认,相比效用和资源,能力可以更恰当地反映人的生活质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一的能力概念对于刻画个人福祉而言是充分的。必须注意的是,一个人的福祉不仅和他具有的能力有关,而且和这些能力的安全性有关。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随时有可能丧失,无法长久稳定地保持,那么我们就倾向于对他的处境作出消极的判断。在衡量人们的生活境况时,我们必须将安全和风险因素纳入考虑。沃尔夫(Jonathan Wolff)和德夏利特(Avner De-Shalit)的合作研究指出:“能力进路没有抓住劣势(disadvantage)的一个重要而普遍的维度,即在很多时候,人们处于劣势是因为他们面临无法规避的风险,或者被迫承担在某种意义上比别人更大的风险。”①Jonathan Wolff and Avner De-Shalit, Dis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6.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努斯鲍姆本人接受了沃尔夫和德利夏特对能力进路的批评,认为后者对安全和风险问题的关注,推进了能力进路的研究,丰富了能力进路的理论机制。参见Martha C.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42—43。
首先,我们需要对这里的“风险”概念作一些澄清。将风险作为评估劣势的一个重要维度,并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就应该或能够免于风险。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来,没有风险的生活是平淡无味的。有时,风险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相反,它是一种兴旺人生的组成部分。承担风险的同时也意味着获得更多的人生可能性。开始一段恋情、开启一段职业生涯,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风险。但如果说这样的风险使得人们陷于不幸的境地,那就显得太荒唐了。事实上,这些风险恰恰构成了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经济领域),风险经常和巨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一些人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承担风险。因此,需要强调指出,作为衡量优势或劣势的维度的风险,是一种在非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承担的风险。在面临这种类型的风险时,人们不会体验到任何快感和乐趣。相反,当人们去承担这些不得不承担的风险时,他们感受到的将是实实在在的“负能量”。在这个意义上,面临风险就意味着承受不幸。
根据沃尔夫和德夏利特的解释,所谓被迫承担风险,是指由于没有合理的选项,风险无法被合理地规避。这里的“被迫”并不是说遭遇某种外在的强力。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仍然可以选择回避这个风险,但这样选择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风险或更确定的伤害。换句话说,对行动者而言,最合理的选项就是去直接面对这个风 险。
更紧要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面临风险构成了一种劣势?第一,面临风险意味着某种特定的能力或功能性活动不稳定,难以长久。比如,一个人尽管当下有舒适的居所,但面临随时被驱逐的威胁,他的这项基本能力就是缺乏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说他处在一个不利的境地。第二,面临风险的人通常感到极度紧张和焦虑,这显然会威胁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在一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福利制度还不完善的社会中,一个人即便在当下拥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他也会对未来感到忧心忡忡,生怕自己会失去现在拥有的这一切。显然,这种焦虑情绪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心理的不健康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其他功能性活动(如游戏、交往等)的发挥。第三,为了降低风险的概率或潜在的伤害所采取的措施,经常需要人们付出很高的成本。比如,一个人在治安很差的社区生活,在街道上单独行走随时面临被抢劫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维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他选择聘请保镖或减少外出。第一个选项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第二个选项则使他失去其他很多从事有价值活动的机会。第四,为了规避某种风险所采取的措施,本身可能也会使人置于不利的境地。例如,考虑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一个人担心未来的家庭收入将显著下降,于是决定在业余时间打工,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但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没有足够的休闲时间,而且陪伴家人的时间也会大大减少。无疑,这对他的福祉也是一种损害。第五,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陷入所谓的“意志瘫痪”,无法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人生计划,即便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如此。①参见 Jonathan Wolff and Avner De-Shalit, Disadvantage, pp. 68—69。不难想象,失去了对未来的精心筹划,人生也就失去了方向和活 力。
综上所述,风险——准确说是人们非自愿地面临的风险——是评估人们福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既然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风险社会”,那么,我们在审视人生时,就没有理由不将风险纳入关注的视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所谓的核心能力,还取决于这些能力本身的安全性。在一个能力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或丧失的条件下生活,同样是没有尊严的。因而,旨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其着眼点不能仅仅是人们当下所拥有的能力,还应该涉及能力的安全。也就是说,政府不仅应当努力去培育公民的能力,而且还应积极地创造条件,减少乃至消除能力面临的各种风险,保障公民的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稳定地保持下 去。
二、能力清单难以成为重叠共识的对象
努斯鲍姆把她的能力进路归入政治自由主义的范畴,反对将正义原则建立在任何整全性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或伦理学说之上。这既是基于稳定性的考虑,也是平等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努斯鲍姆写道:“能力清单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不完全的道德观念’提出的(这里借用约翰·罗尔斯的术语),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为了政治意图才提出的,而不诉诸那种按宗教和文化对人们进行划分的形而上学观念。”①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9.努斯鲍姆相信,她提供的能力清单能够成为重叠共识的焦点,得到社会上所有公民的支持,无论他们对于美好生活持有何种观念。能力清单就好比一个“模块”,可以和任何一种世俗或宗教的人生观对接。努斯鲍姆将此视为能力进路的一个重要优点,因为它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然而,问题是,努斯鲍姆版本的能力清单真的能够成为重叠共识的对象吗?是否在所有公民看来,那十项所谓的核心能力都是一个最低限度正义社会需要保障的?这里,我们要质疑的不是努斯鲍姆试图发展的政治自由主义这个理念本身,而是她的理论有没有实际吻合政治自由主义的理念。
在早期作品中,努斯鲍姆对其能力清单作了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辩护。②Martha C. Nussbaum, “Human Functioning and Social Justice: In Defense of Aristotelian Essentialism”,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2, 1992, pp.202—246.她认为,清单上列出的那些能力对于欣欣向荣的人类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显然,这里不可避免地蕴含了一种对何为美好生活的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能力清单就无法成为持有各种不同人生观的人们的重叠共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除非他也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抱有支持态度,否则很难全面认同努斯鲍姆的能力清单。运用这种整全性的伦理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和发展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设想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
近年来,努斯鲍姆对能力清单的辩护似乎淡化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转而诉诸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的概念。③尽管努斯鲍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有所淡化,但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仍是能力进路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从思想史上看,努斯鲍姆主要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了两个论点:选择和人的脆弱性。亚里士多德强调选择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的行动只有在出于自己的思想和选择时,才能被算作有德性的。一个人未经选择得到的满足,配不上人的尊严。努斯鲍姆强调公共政策的关注点是能力而非功能性活动,目的正是为人的选择留下空间。此外,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归根到底是一种动物,从出生到衰老具有很多脆弱性。鉴于这种脆弱性,人很难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体面地生活下去。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地对社会成员予以全方位、强有力的支持。努斯鲍姆接受了这个主张。她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和政策,积极地支持和强化民众的能力,而不只是不设置障碍。关于努斯鲍姆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继承,参见Martha C.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pp. 125—128;刘科:《对努斯鲍姆尊严观的反思》,载《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1期,第59—61页。努斯鲍姆论证说:“保护这十项基本权益,是有尊严的人生的本质要求。”①Martha C.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p.79.然而,关于什么是有尊严的人生或什么样的生活配得上人类尊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富有争议的问题。试图以这个问题作为起点列出一份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能力清单,可谓困难重重。更何况,努斯鲍姆追求的重叠共识是跨文化、跨宗教的共识,而不是像罗尔斯设想的,在一个分享民主政治文化传统的社会内部的共识。这就让人有理由怀疑,努斯鲍姆对于能力清单成为重叠共识的前景是不是过于乐观 了。
例如,努斯鲍姆将获得性满足和欢笑都视为实现有尊严生活所必需的核心能力。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会将性满足和欢笑与有尊严的人生联系起来。一个禁欲主义者会认为,任何形式的性满足都是罪恶的;在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家看来,笑只不过表现出人类的虚荣和自负。②Eric Nelson, “From Primary Goods to Capabilities: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Problem of Neutrality”, Political Theory, Vol.36, No. 1, 2008, p.99.当然,这些不是社会中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观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也不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紧迫的威胁,它们只是反映了某种特殊的价值观而已。如果将努斯鲍姆的能力清单作为制定宪法的依据,那么,对于那些持有特殊价值观的人们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有理由抱怨说,自己的价值观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而这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精神很不一致。
对于这个批评,努斯鲍姆的回应诉诸能力和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的区分。努斯鲍姆强调,针对成年的公民来说,恰当的政治目标是能力,而非功能性活动。政府的目标只是保障公民拥有相应的能力和机会,至于是否实现这些能力和机会,取决于公民个人的选择。“一个拥有正常机会获得性满足的人,总是可以选择过一种独身的生活。”③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87.根据能力进路,政府并没有把一种特定的生活形式强加在公民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努斯鲍姆认为,能力进路能够很好地容纳各种不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它表达了对多元价值观的尊重。
努斯鲍姆的回应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那些持有特殊价值观的人们对能力清单的质疑。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或政府在保障公民能力方面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按照某种“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的观念,公民拥有的主要是一种不受干涉的权利。换言之,只要国家放开其干预之手,公民的权利自然就得到了保障。这种观念在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传统中十分常见。而努斯鲍姆明确反对“消极权利”的观念,她指出:“一切权益都要求政府承担一种积极的任务,政府应当积极支持民众的能力,而不只是不设置障碍。没有行动的话,权利就仅仅是空头支票。”①Martha C.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p.65.
按照这个思路,要保障公民获得性满足的能力,政府仅仅不去干涉人们的私生活是不够的。政府还需要积极地采取行动、投入资源、创造条件,以确保每个公民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对于那些因自身生理问题而在性能力方面存在缺陷的人,政府应当出资向他们提供有效的治疗。政府对待他们的方式,应该和对待一般意义上的残障人士并无二致。政府的资金来源是民众缴纳的税收,而税收的一部分恰好来自那些禁欲主义者。毕竟,缴税对任何一个公民而言都是不可推卸的政治义务。但这里会出现一个直觉上令人难以接受的问题:一个将性生活视为罪恶的人,却不得不为他人获得性满足的机会提供经济支持。禁欲主义者虽然可以像努斯鲍姆所说的那样去自由选择过一种单身生活,但他仍然可以合理地抱怨:为什么要强制我掏腰包,去支持一项违反我的价值观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说我的价值观得到了尊重?
不仅是获得性满足的能力,能力清单上的其他一些能力——比如与其他物种保持良好联系的能力、欢笑的能力——也是有争议的。可以想象,不是所有人都会赞成将这些能力作为有尊严生活的构成要素。②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在发展他的全球正义理论时,也诉诸了尊严概念。在博格那里,尊严主要涉及三个维度: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肉体自我、精神生活。至于努斯鲍姆强调的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不在有尊严生活的关注范围之中。参见托马斯·博格:《阐明尊严:发展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正义观念》,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第20页。事实上,就连努斯鲍姆本人也承认:“看起来,清单上的某些能力要比另外一些更为确定。例如,如果身体完整的权利从清单中移除出去,就会让人感到吃惊。这在我们关于善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中是一个固定之点。”③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p. 77.然而不清楚的是,既然努斯鲍姆对某些能力不是那么确定,不是那么有把握,为什么她还要坚持把它们作为核心能力列于清单之中?既然能力进路被明确视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么多有争议的内容引入它的正义原则?笔者认为,为了成为重叠共识的对象,努斯鲍姆版本的能力清单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瘦身”,否则难以契合政治自由主义的理 念。
说到底,努斯鲍姆的能力清单反映的是她自己的一种人生理想,确切地说,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艺术倾向、拥有自我意识、自愿信仰宗教的西方女性”对于“何为有尊严生活”的独特理解。④Susan Moller Okin, “Poverty, Well-Being, and Gender: What Counts, Who's Heard?”,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31, No. 3, 2003, p. 296.然而,要真正贯彻政治自由主义的理念,努斯鲍姆应该诉诸的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人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完备的人生理想。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将努斯鲍姆和同样秉持政治自由主义理念的罗尔斯作一些对照。
罗尔斯在提出他的基本益品清单时,运用到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政治的人的观念。罗尔斯明确指出:“这里的关键是,作为人的公民观念,应当被视为一个政治观念,而不是一个从属于整全性学说的观念。正是这种政治的人的观念,通过它对公民道德能力和高级利益的解释,以及作为合理性(rationality)的善的框架、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人类成长和培育的条件,共同提供了规定公民需要和要求的必要背景。所有这些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份可行的基本益品的清单。”①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78.简言之,在罗尔斯那里,公民具有两种道德能力——正义感和善观念。一方面,公民能够理解和运用公共正义观,并依据这种公共正义观展开行动;另一方面,公民能够形成、修正并理性追求自己的善观念。进而,罗尔斯在开列基本益品清单时,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参与社会合作的公民,为了发展和运用这两种道德能力、追求自己特定的善观念,必须拥有哪些东西?基本益品是通用的,也就是说,无论公民具体的生活理想是什么,他们都会需要这些东西。基本益品清单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权利和自由;移居自由和在多样化机会背景下的职业选择自由;在基本结构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的各种责任职位中享有权力和特权;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②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181.不同于努斯鲍姆的能力清单,罗尔斯的基本益品清单没有植根于任何特殊的价值观或人生观。因此,在追求一种所谓“政治”的正义理论这方面,罗尔斯比努斯鲍姆走得更远。
三、能力进路的正义原则不具有公开性
任何一种规范的正义理论提出的正义原则,不仅要在道德上有吸引力,而且要在实践中可行。因此,公开性(publicity)是证成正义原则的条件之一。支配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应当具有公开性,也就是说,这种正义原则应该得到社会上所有公民的理解、认可和运用。对于正义原则实现与否的问题,每个公民——只要具有正常的理智能力——都应该能作出明晰的判断。此外,正义原则不仅是决策者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依据,而且还应扮演“公共理由”(public reason)的角色。正义原则的公开性要求,每个公民都能运用正义原则进行说理。当公民就具体的正义问题展开论辩时,所能诉诸的理由只能是共同接受的正义原则,而不是自己持有的某种特殊的伦理观念。正义原则为政治讨论、批评和辩护提供共同的基础。③Samuel Freeman, Justice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Essays on Rawls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91.每个公民都能基于正义原则作出有关正义或不正义的主张。正义原则的公开性意味着,正义原则对广大公民的心理条件和知识储备都不能提出苛刻的要求。在作出正义的判断和主张时,公民不需要涉及特别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如果需要结合太多的信息来进行正义的判断,这个正义原则就违反了公开性的要求。
公开性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基于稳定性的考虑。如果一种正义原则无法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接受,那么就只有依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相应制度的存在。而一旦骗局被揭穿,人们对制度的忠诚感就会迅速消失。其次,公开性是对人予以平等尊重的需要。正义原则所支配的社会基本结构深刻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前景和背景正义,因此,正义原则的内容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让所有人知道。如果认为正义原则只能让少数社会精英知道,而对普通民众秘而不宣,就是违反了平等尊重的要求,违背了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①一种被称为“政府大厦功利主义”的观点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这种观点,鉴于功利主义对人的心理条件要求很高,因而它只能让一小部分社会精英了解和采纳。至于广大民众,则不能让他们学习和接触功利主义。民众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社会制度背后的正义原则另有其他。“政府大厦功利主义”之所以饱受批评,就是因为这种精英主义理念违反了民主的公开性要求。参见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 (上),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8—59页。
现在的问题是,能力进路的正义原则是否符合公开性的要求。努斯鲍姆的正义原则,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在那十个核心领域,要确保每个公民拥有超出底线的能力。下面,我们从道德心理和知识储备两个方面来论证,这项能力进路的正义原则对普通公民提出了比较苛刻的要求,以至于它无法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充分的运用。
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是一种结果导向的观点。它认为,分配正义主要取决于结果,就是看公民的基本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至于如何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经由何种程序实现这种理想的结果,则不在能力进路的视野之中。对于那些核心能力严重欠缺的弱势群体,能力进路要求每个公民都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和帮助。能力理论家强调了援助的必要性,但似乎没有考虑援助带来的成本和责任如何在不同的公民之间作出区分。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能力进路还要求将社会合作产生的好处转移给那些根本没有参与社会合作的人,而这些人可能完全是因为懒惰消沉不愿融入社会合作。显然,要将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付诸实践,要求公民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倾向,对缺失核心能力的弱势群体抱有同情和仁慈之 心。
然而,能力进路对人们心理条件的要求可能过高了。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利他主义不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心理。即便有人能做到无私奉献,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即便一个社会大力弘扬利他主义的精神、营造奉献他人的氛围,也很难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这种品质。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能力进路的正义原则是否可以得到所有公民发自内心的认可。实际上,努斯鲍姆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她写道:“我的观点确实需要依赖于利他主义,因而需要花很长的篇幅去阐明,利他主义动机如何产生、为何产生,利他主义动机必须与之竞争的其他动机,以及我们如何以一种社会所允许的方式来培育有益的情感。”①Martha C.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p.96.
就算人们能够普遍认可能力进路的正义原则,如何对这项原则加以运用也很成问题。正义原则的公开性要求,广大公民能够基于正义原则对现实的正义问题作出判断、展开论辩。根据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实现了最低限度的正义,就是看这个社会的公民的核心能力是否得到了保障。如果有社会成员的核心能力没有达到底线要求,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严重的不正义。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如何对公民的能力进行测量和评 估?
由于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隐性的东西,无法被直接观察清楚,因此能力评估并非易事。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的能力评估方式。第一种是,首先评价人们功能性活动的水平,进而从中推论他是否拥有相关的能力。这种方式比较直接,问题也显而易见。能力和功能性活动之间不能画等号。我们不能认为,功能性活动的缺位就是能力的缺位。一个人没有参加投票,可能只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因为他缺乏政治参与的能 力。
第二种方式是,全面考察分析影响能力的一系列相关因素。②Ingrid Robeyns, “Justice as Fairness and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in Arguments for a Better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Amartya Sen, edited by Kaushik Basu and Ravi Kanb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409.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的特质、拥有的资源、自然条件、政治环境、社会风尚等。只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能力作出准确的评估。例如,要评估一个人是否具有充分的受教育的机会和能力,我们就要考察他的基本智力状况、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他是否拥有法律规定的受教育的权利、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对他接受教育构成障碍。这意味着,按照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我们要提出一个正义或不正义的判断,就必须了解大量有关个人及其所处环境的信息。问题在于,其中很多信息,超出了社会上普通公民的知识储备。而没有足够的信息资源,我们就没法运用“能力”的语言进行说理论证。看起来,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对公民的信息资源储备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而正是这一点制约了其正义原则成为公共理由、为公共论辩提供基础的潜力。能力难以直接被观察和评估的事实,严重限制了正义原则的公开性。③罗尔斯对阿玛蒂亚·森也有一个类似的批评,但他的焦点是人际比较的标准,而非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基本益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或优势就在于它的可行性。他指出:“一个公民的基本益品份额是公开可观察的,这使得理论所要求的公民间比较(所谓的人际比较)成为可能。”(参见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相比之下,运用能力概念来进行人际比较,需要涉及更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政治社会中难以获得的。
四、能力进路没有触及正义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阿玛蒂亚·森只是提出运用能力概念作为正义研究的一个视角或信息焦点,那么,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版本则试图发展一个规范的正义理论。努斯鲍姆这样来定位自己的理论:“就我的版本来说,能力进路是一个部分的社会正义理论,它没有声称要解决所有的分配问题,而只是规定了一个比较充裕的社会最低限度。使所有公民具备这十项能力,是社会正义的一个必要条件。正义当然可以提出更多的要求。例如,迄今为止发展出来的能力进路,没有阐明应当如何解决最低限度以上的不平等问题。很多社会正义的进路认为,一个充裕的底线对实现正义而言并不充分。一些进路要求严格的平等。约翰·罗尔斯坚持认为,只有当可以提高最不利者的生活水平时,不平等才能够得到证成。能力进路没有主张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但它也许在将来处理这些问题。”①Martha C.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p.40.
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是在批评罗尔斯契约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努斯鲍姆认为,契约论的一些核心要素和理论假定导致它难以解决那些不具有社会合作能力的人们的正义诉求问题。②实际上,罗尔斯的契约论并没有削弱非合作者的正义主体地位。契约论作为正义问题的研究进路,仍然可以容纳残疾人的正义诉求。参见任俊:《契约论并不排斥残疾人的正义权利——驳努斯鲍姆对罗尔斯的一个批评》,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22—28页。例如,罗尔斯假定,契约各方代表的公民必须是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这看起来意味着,在选择基本正义原则时,契约各方只会考虑能够充分参与社会合作的人们的利益,而那些有严重残疾、无法充分参与社会合作的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公平对待。相比之下,努斯鲍姆认为能力进路在处理非合作者的正义问题时更有优势。能力进路并不依赖所谓的“充分合作假定”,更不主张合作的目的就是互利。能力进路强调的是人作为人的尊严,以及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人配得上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要实现这种生活,仅仅靠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外界尤其是政府的积极介入和援助。在努斯鲍姆那里,一个人无论是合作者还是非合作者,无论在社会合作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有权利过上一种配得上人的尊严的生活。相应地,国家或政府有义务维护人的尊严,确保社会上每一个人拥有清单上列出的十项核心能力。只要每个人都拥有了这些核心能力,最低限度的社会正义就算是达到了。在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中,“合作”的观念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看来,努斯鲍姆在试图纠正契约论缺陷的同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由于抛弃了“充分合作假定”,转而诉诸“人的尊严”概念,能力进路能够很好地容纳非合作者的正义诉求,关注到那些弱势群体(比如严重残障人士、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受到歧视的家庭妇女等)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它对合作者之间的正义问题缺少应有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分配正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大多数正义理论家关注的问题。合作者之间的正义问题的重要性,来自相互性(reciprocity)的理念,即“所有参与合作并按照规则和秩序的要求履行职责的人,都应当以恰当的方式获益,而这种恰当性是由一种恰当的比较基准来衡量的”①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16.。根据相互性的要求,每一个合作者,无论其性别、阶层、种族和信仰是什么,只要对社会合作作出了贡献,都有权利获得公平的分配份额。如果一个合作者获得的利益少于公平的分配份额,那么他就有理由抱怨社会不公,抱怨自己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关于平等尊重的道德直觉,不仅支持对没有合作能力的残障人士予以特殊的照顾,也支持为社会合作投入努力、作出贡献的人们取得应有的回报。应该看到,这种相互性的正义(justice as reciprocity)要表达的是,参与社会合作是拥有正义诉求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②阿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在一篇著名论文中区分了作为相互性的正义和以主体为中心的正义。根据这一区分,努斯鲍姆的正义观更接近于以主体为中心的正义。在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正义时,努斯鲍姆要追问的是,在这个社会中,是否每个主体的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是否每个人的核心能力都得到了保障。参见Allen Buchanan, “Justice as Reciprocity versus Subject-Centered Justic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19, No. 3, 1990, pp.227—252。因此,它并没有否认那些非合作者的正义主体地位。解决合作者之间的正义问题,与满足非合作者的正义诉求完全可以兼容。
正如努斯鲍姆本人已经意识到的,对于我们思考合作者之间的正义问题,能力进路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提供启发和洞见。在分配正义问题上,我们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道德直觉,那就是分配结果应该“钝于禀赋”(endowment-insensitive)而“敏于志向”(ambition-sensitive)。③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 (上),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9页。具体说来就是,一个人所获得的分配份额,应该尽可能地反映他的选择和努力,而不是他的自然天赋和社会出身。后者只是纯粹的运气,而人的道德权利不应建立在运气的基础上。那么,能力进路在“钝于禀赋”和“敏于志向”这两方面究竟做得如何呢?
显然,能力进路在“钝于禀赋”这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在“敏于志向”这一项的得分就比较低。“能力进路宣称,从正义的视角来看,判断一种特定的政治情形是否充分,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去观察结果,看公民的基本权益是否以一种安全的方式得到了满足。”④Martha C.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p.95.这里,“公民的基本权益”仅仅基于人之为人的事实,它既不依赖于人的天赋和出身,也与人的选择和努力无关。这一点和我们的道德直觉是有冲突的。不同于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出身,选择和努力并非从道德角度看任意的因素。由于不审慎和不勤恳而在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不能说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 待。
设想,一个人虚荣心很强,贪图享受,迷恋奢侈生活,同时又缺乏审慎的消费观念,最终让自己陷于一贫如洗的糟糕境地,失去了任何可支配的财产。按照能力进路的观点,我们应当立即去补偿这个已经丧失基本经济能力的人;对他施以援手,就是在消除不正义或促进正义的实现。但在我们看来,这个人虽然很不幸,但他无法基于正义的考虑来要求社会对他予以援助。而如果动用强制手段逼迫其他社会成员给予经济援助的话,就会产生真正的不正义。他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抱怨说:凭什么强制要求我为别人的错误选择承担责任呢?当然,一个富有道德感的社会很有可能会帮助这个不幸的人重新恢复基本的经济能力,但这是出于人道、仁慈或同情,而不是正义。这些是不同类型的道德要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结果导向的观点,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没有为人的选择和努力留下空间,因而无法解决好合作者之间的分配正义问题。由于没有触及这个正义的核心问题,努斯鲍姆提供的与其说是一个分配正义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基本人权的理
论。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正义的尺度上看,单纯能力难以充分评价个人福祉;从正义原则的内容上看,过于厚重的能力清单难以成为重叠共识的对象;从正义原则的可行性上看,能力进路难以达到公开性的要求;从正义的论题上看,能力进路错失了相互性的正义维度。总之,在正义研究领域,尽管能力进路提供了新概念和新视角,但其本身还存在一定的修正和提升空间。至少就目前来说,能力进路还不足以作为我们研究正义问题的主要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