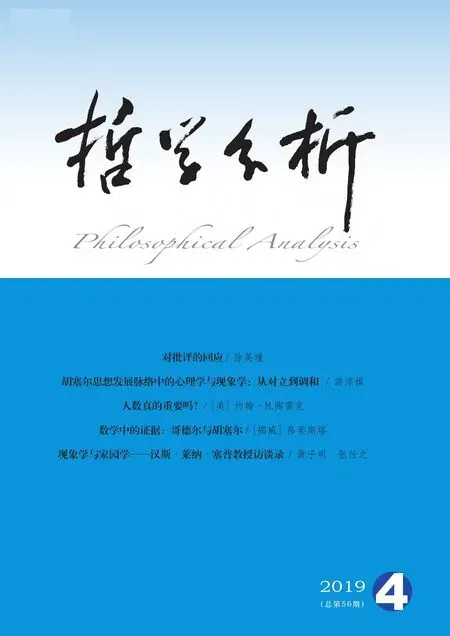评《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书中的“日本论”
——以丸山真男的思想为参照
宗 宁
一、《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书中的政治哲学与日本问题
翻开徐英瑾教授的新著《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的目录,读者不难发现,虽然本书从方法论上带有明显分析哲学印记,但其旨趣却是要填平唯物主义所关联的各领域之间的沟壑,从而为抽象的观念性问题寻找到一条具体的出路。这一充满雄心的工作以黑格尔式的层层推进的结构呈现出来:作者从“蕴相殊”(trope)论的形而上学,推进到由生物学和认知科学出发的元伦理学,最后归于对信息技术和社会现实的形而下讨论之中;这些相互勾连的话题铺成了一幅综合性的画卷,一方面,为“应然”的“规范”寻找得以锚定的根基,另一方面,也为辨析“实然”的“物质”范畴的哲学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本书从思辨的云端着陆到现实的地面之际,其最后两章的讨论集中围绕着有限时空中的社会、政治领域展开。通过对近现代日本三位哲学家(柄谷行人、和辻哲郎、田边元)的批判性分析,本书讨论了社会伦理产生和维系的空间性物质性条件(第十二章),评点了为日本战时“大东亚共荣圈”张目的田边元历史哲学的谬误(第十三章)。而在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参照之下,这些内容最终被整合进历史唯物主义对近现代资本社会的分析之中,使得书中以实证“信息交换空间”为侧重的理论获得了历史性(时间性)的批判维度。大致上,作者在这一部分的想法可以总结为以下三 点。
第一,信息交换的结构对人类组织形式、行为方式和伦理(包括宗教性的)规则之塑成、变迁具有奠基性作用;这一结构主要是空间性的而非时间性的。这一点构成了作者观点的描述性面相(descriptive aspect)。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空间性”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判断是非常决绝的,并没有引入“空间性的信息交换结构是历史的产物,被赋予了历史的本质又是空间性结构的嬗变本身”这种中庸的调和性的论
调。第二,信息交换的结构并不仅仅会生发出伦理规则的诸多表象,自身也带有更深层价值的维度;近现代以资本为主导的信息交换结构本身就是马克思所谓“异化”的直接原因。这构成了作者观点的批判性面相(critical aspect)。
第三,信息交换形式没有一成不变的元—结构;在后信息时代,全新的结构必将被演化出来,并功能性地重塑人类的伦理和行为。这是作者从社会现实在空间维度中的性质出发对时间维度中的对象(即历史)所下的判断。
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部分讨论的核心关切是:(1)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证精神应当如何在“空间性”概念的帮助下完成其在具体的社会科学中实体化的过程?(2)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批判理论应当如何在以观察和描述“人际通信网络之产生与维持”为主要任务的政治科学中寻找到批判的动力?作为对这些抽象问题进行思考的催化剂,日本思想以及日本本身都在作者的辨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思想既输送了理论的炮弹,也提供了反面的参照系;日本则作为分析的样本,被用来揭示书中理论的应用。那么,作为一本哲学著作,为何作者要讨论“日本”这一有限的时空对象,他的讨论具体又是如何展开的 呢?
在第十二章的最开始,作者花了些许笔墨介绍了柄谷行人从生产关系中物质流动和交换的规范性结构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后者基于“互酬制”概念提出的共产主义构想;接着,作者提出,这样的分析不仅可以应用在“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上,也可以应用到对局域的、乡土性的伦理的微观分析之中,后一部分的工作恰是柄谷所没有涉及的。作者因此批评道:“柄谷似乎对于‘联合主义—共产主义’的普遍主义叙事方式与东亚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亦缺乏系统的应对方案。”①徐英瑾:《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 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2页。
“为细致地刻画上述‘互酬活动’得以展开的风土条件”②同上书,第414页。,弥补柄谷理论没有涉及殊相所带来的缺憾,作者引入了和辻哲郎的“空间伦理学”。正如作者所介绍的那样,和辻认为,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而人的社会性是其空间性的衍生;“空间性”在和辻这里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范畴,它在这里特指“人化的自然条件”,也即区域性的“风土”。在马克思、柄谷提供的语境中,徐著颇有新意地将“空间性”和“物质性的信息交换条件”联系在了一起,继而将区域性的伦理规范解释为这些条件的“随附”特征。另外,在对其理念的具体解释中,作者强调了纵向和横向两种信息—物质交换渠道的相互对立、牵制的关系,为解释“中央—地方”“律法—宗法”“国家—族群”等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二元性的社会—政治形态搭建了一个框架。
随后,作者批判了田边元的“共荣圈逻辑”理论,并给出了自己的“日本论”。乍看之下,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引入这个话题是十分突兀的。不过,由于作者在书中已经向读者明示了其注重分析殊相的“唯名论”立场,也在解释和辻哲学时明确地将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同信息空间的“有限性”挂钩,我们不难领会作者引入本章讨论的哲学意图,即用对特殊的实存的分析来解构普遍的观念、用对事实的归纳来对抗独断的抽象、用地方史来自下而上地(bottom-up)重构世界史。本书关于日本的讨论正是为了呈现这种进路的具体操作方式。
在其关于“共荣圈”的理论中,田边元用黑格尔式的辩证语言系统阐述了“个体”“家庭”“共荣圈”等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国家对社会的法西斯集权控制,以及日本对东亚诸国的侵略进行辩护。站在否定的立场上,本书的作者揭示,田边的辩护得以建构的前提是如下观点:建立在家庭这种信息横向流动的社会关系是不稳定的,而国家这种纵向关系却是稳定的。作者接着指出,这种观点颠倒了事实,是田边立场先行的唯心史观所带来的后果。作为对田边理论的反驳,也作为本书所提出的“基于信息隐喻的自然主义叙事框架”应用到具体现实中的一个范例,作者正面陈述了他的日本论,其主要观点是:
(1) 日本的传统社会持有一个扁平且松散的横向信息传递结构,并以宗族—门阀—乡土为基本单位。作者将这种结构视为日本传统的根本特征,同时,也对这种横向结构带来的伦理系统持有积极的态度。①对于这一点,除了本书所给出的一些例子外,熟悉日本历史的读者不难找到其他印证,比如,在室町幕府时期最终取代了“班田制”实现土地私有“庄园制”就在最根本的生产关系上确立了这样一种扁平结构,而成功取代了“律令制”(试图模仿唐宋实现中央集权)的“守护领国制”(由守护大名管理领国)则是在政治上确立了类似的结构。
(2) 松散的横向结构是日本社会的根本空间特质,在中世和江户时期其形成并稳定,在不到百年的明治时代和昭和前期被强行扭曲,又在战后迅速复苏。这种强行扭曲恰恰以一种纵向的高压信息管制为核心特征。
有些可惜的是,由于篇幅和题材的限制,作者没有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全貌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而作为整个十三章重点的田边元“种的逻辑”这一“历史唯心论”的反面样本虽然有着精致的概念构造,却由于其偏激的意识形态和脆弱的底层预设,使得他成为了一个似乎比较容易反驳的对手。这自然会使得对日本史和日本思想感兴趣的读者(包括笔者在内)在读完这部分内容之后觉得意犹未尽。本书评——作为一个书评系列的一部分——的余下部分将试着从一个更广阔的“日本”语境出发,为本书的观点寻找一位难缠的日本论敌——丸山真男,一方面,为本书读者提供比较性的衍生评述,另一方面,也对徐著相关理论的韧性和适应性做出一番测试。
从主题来说,下文可以划分为“日本传统文化”和“日本近代政治”两大部分。在第二和第三部分,笔者将比较丸山真男的“古层论”和徐著中的“日本论”的异同(第二部分),并在本节所介绍的徐著的“信息—空间论”模型中尝试对丸山的一些洞见做出一些扩展(第三部分);在第四部分,通过回顾丸山对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批判,笔者将说明,在看似南辕北辙的观点背后,徐著和丸山的“日本近代论”之间也存在着丰富的互补性——这些互补性的存在正是徐著解释框架之有效性和应用潜力的侧面反映。
二、丸山真男的“古层论”与徐著日本传统论之异同
为什么本文选择丸山真男(1914—1996)的思想作为徐著日本论的试金石呢?首先,这是因为丸山对于日本传统文化和日本近代政治的批判在激烈性和深刻性上都超越了包括京都学派诸哲人在内的同时代日本学者,具有公认的理论价值。徐著所重视的当代学者柄谷行人,在讨论日本问题时,也常常不惜笔墨地同丸山展开隔空对话。②最为代表性的论述录于柄谷行人的《日本精神分析》 (讲谈社文库2007年版)。其次,由于丸山主要的讨论对象是政治史和思想史,也由于丸山自身对左派一直抱有同情态度(虽然我们很难将丸山直接归类为左派思想家),他的理论和徐书的内容和旨趣都有着一定的重合。这为我们讨论的展开提供了方便。
关于日本的传统,丸山提出了著名的“古层论”①在展开对于“古层论”的讨论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丸山对于“古层论”的详细论述,见于其《历史意识的古层》一文(歴史意識の「古層」)。此文从日本最早的神话文本《古事记》开始,对日本传统中一些重要的文化表象进行了细致的谱系学的考察。不过由于此文细节繁多、表述晦涩,并不适合本文讨论的语境,因此在本文中并没有作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本文所重点倚仗的文本是更具有纲领性质的《日本的思想》一书,在此书的第一章中,虽然丸山并没有直接讨论“古层”,但言简意赅地复述了古层论中最具批判性的内容,并同他对日本近代的“明治宪法”和“国体论”的批评联系了起来。第二,丸山的“古层论”,上承其“原型”论,下通其“执拗的低音”论,有着复杂的思辨语境,本文对古层论的简短介绍侧重的是:(1)丸山对于古层中诸多要素的“杂居性”的描述,以及(2)他对“日本性”本身内容虚无的论断,这并没有涵盖“古层论”的所有内涵。,其要旨大致是说,日本传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身的、统一的底层内容。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论断,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母国非日本的“旁观者”来说,日本作为一个特点鲜明的他者并不是什么难以定义的对象。比如在我国,从古至今,日本人的形象都通过贴标签的形式得到了一定的固化;在西方,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与刀》,多少也能代表一种对“日本性”的普遍理解。然而,在丸山这位日本学巨擘看来,“日本”却是内涵难辨,似乎在其丰富文化和风俗的表征背后,只有对外来文化半吞半咽的糅合,而没有任何能够能直接宣布其“发明权”的东西。以日本的哲学思想为例:空海、道元、亲鸾等日本佛教思想家都可以在中国古代诸多佛教流派中找到直接的亲缘联系,作为江户时期官学的朱子学和后来受到一定重视的阳明学自然也是舶来品;在近代,日本和中国一样经历了接受西方思潮的过程,而勃兴于大正时期的京都学派哲学(也是徐著的讨论对象)正是日本学者接受西学的产物,其主要人物在表达思想时也完全接受了西方哲学的术语体系。所以,当我们想要讨论“日本哲学”的时候,我们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讨论中国学、印度学、西洋学,而唯独不是日本学。又比如,被视为艺术瑰宝的日本佛像,其技艺许多都起源于随鉴真东渡的中国工匠的传授,以及后来日本匠人对鉴真在奈良时代带去的中国佛像的模仿。对于一个中日古代美术史的门外汉来说,将混在一起的两国佛像的精准分辨恐怕并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在一些更为重要的政治—宗教传统上,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作为日本大和政权立国基础的《日本书记》也是由古代汉语所写就的,而作为日本本土宗教的神道教,特别是神道教中以伊势神宫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其实也不过数百年的历史(而非许多人误认的1300多年),且和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密不可分。②《宗教史》,体系日本史厳書 18 (第二回配本),昭和44年第3版,第257页。
对这一现象有着深刻体察的丸山认为,日本文化善于吸纳外来文明却缺少原生力量的文化生长模式,使得它很难将自身和外来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他特别针对日本思想史领域中的这种状况写道:
如果将我们的思考和表达的形式分解为各种要素,并追溯它们的谱系,那么我们就会遇见佛教式的、儒教式的、萨满教式的、西欧式的东西——要言之,就是那些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其足迹的所有思想的断片。这里的问题是,所有的这些要素都杂然同居着,人们从来都没辨明它们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应占据的位置。不论是所谓“传统”思想①这里泛指的是与西方对立的东方传统。,还是明治以后的欧罗巴思想,在这一基本的存在方式下,我们都找不出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②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 (「日本の思想」),岩波新书(青版)2018年版,第9页。
丸山的讨论显示出的是一个日本知识分子在反思母国文化本质时所产生的深度焦虑,这种焦虑当然并不仅仅是由“难以定义”带来的学理性困扰,更代表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寻根时发现自己无所依凭时产生的迷茫和空虚。正如引文所示,丸山直截了当地承认,“日本思想”没有一个统一的坐标轴,“日本性”究其本质就是“杂居性”,而杂多的外来文化各安其所、互不侵犯的结果就是一个没有本真自我的“四不像”。那么,这种“杂然同居”的状况,又是由何种原因引起的呢?丸山的分析如 下:
(日本人)“把异质之物在思想上加以接合”这种行为常常作为一种合理化的逻辑而得以流通,这是由“什么即什么“”什么一如”③“〇〇即〇〇”和“〇〇一如”都特指佛教中关于同一性的逻辑关系的表述。“一如”这个词的意义在日语中得到了一定的拓展,泛指绝对同一的真实状态,产生了如“剑禅一如”这样的表达。这种佛教哲学的庸俗应用导致的。不过,对于像这样“无限拥抱”所有的哲学、宗教、学问——包括所有相互之间在原理上矛盾的东西——并让它们在精神性的经验中“和平共存”的思想的“宽容”传统而言,唯一异质的东西,毋宁说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原.理上要求否认这样的精神杂居性,并内在地强行促成世界经验在逻辑和价值上的秩序。④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第16页。
可以看到,在丸山看来,杂多不但是日本传统一个“自在”的客观特征,而且是以对“求同存异”“无限拥抱”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自为”规范。也就是说,日本传统之所以会陷入这种窘境,不仅仅在于日本文化被动地缺少一种辩论和淘汰机制,来为野蛮生长的草丛制定秩序,而更在于日本人主动地拥抱这种原始的杂芜状态,并将这种姿态内化为自身唯一的属性。所以,关于“日本性”,其实没有任何核心内涵可以被道说,只有这种既排除了中枢形成可能性也拒绝了整合秩序的力量介入的“宽容”姿态才可以被辨 识。
丸山的这些论述和徐著的日本论相比照,既有共鸣,但也有着不少分歧。一方面,丸山关于日本传统文化特质的判断,起码在三点上同徐著的论述不谋而 合。
第一,两者都将日本传统刻画为一个拥有复多的要素混合体,并且主张“杂然而居”状态乃是日本主动选择的结 果。
第二,两者都认为,日本传统中缺少一个有效的统摄全局的内核。若用徐著的话语体系来复述,这即是说,出于客观条件和主观选择,日本传统中没有演化出一个纵向的强力信息管制通道,其结构是横向的、扁平的、松散的。
第三,两者都认为,从观念上来说,“日本性”根本是无可道说的,而强行发明一个统一的“日本性”在文化和政治上都会招来恶果。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罗列出两者之间的一些主要区别。
第一,丸山关于日本传统文化的“无结构性”的论断是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表象本身的逻辑和关系切入的,而没有对它们所得以形成和维持的物质性(在徐著中主要指作为生产关系的信息交换网络)条件加以溯因性的追问。徐著则对这样一种工作进行了尝试。当然,这并不是徐著本身的专利,我们不难在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日本文化论和文学批评中自然找到类似的还原进路,比如,柄谷行人的日本文学观就是一例。①举例来说,在其早期文学批评的名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柄谷讨论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些特征——如“风景的发现”——同日本国内殖民史之间的关系。
第二,丸山对日本思想传统“坐标轴”的缺失的论断,本质上是对“不可能用线性叙事的手段为一本可能的《日本精神史》赋型”的哀叹。丸山这种追求讲出“一个完整故事”的内涵主义预设却是徐著所要否定的。后者倡导的是一种关于日本文化非线性结构主义的叙事方式。其核心主张是,虽然我们无法对日本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形式分享的共相加以定义,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其社会文化的种种表征所依赖的物质信息交换模式中辨认出有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规范结构,从而给出一个关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创生系统之运作机制”的功能性刻画。这种关于结构本质的刻画无法提供一个全局性的连贯脉络,却将依然是一册有效的说明 书。
第三,丸山对传统日本文化的态度是批判的,在回答“日本维新前传统为何如此容易地被新潮流所淹没”这一问题时,他将矛头直指日本传统的无根、脆弱和虚无。与这种焦虑的消极立场不同的是,徐著的“唯名论”的哲学观使得其对难以被共相所统摄的繁多殊相持有积极的态度。对于作者来说,各自为政的松散结构和杂乱无序的整体样态都不是精神“虚无”的表征,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社会性内涵的特定风土的副产品。
第四,丸山的讨论采用了以 “时间”为主线的解释图式。在这一视域下,日本文化的无根属性,便同佛教中的“无常性”概念,以及与“永恒”对峙“当下性”概念联系到了一起。①在《历史意识的“古层”》一文的“代总结”中,丸山如下叙述了他对于“历史性的认识”的看法:“历史性的认识,不管是在超越了时间的永恒者的观念中,还是在自然性时间的继起的知觉中,都无法产生出来。它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是通过永恒和时间的交汇才得以自觉化的。在日本的历史意识的“古层”中,占据了永恒者的位置的乃是处于谱系性连续中的无穷性,正是在这种无穷性中,日本型的“永远的现在”被构成出来……”(丸山真男:《忠诚和反逆——转型期日本的精神史的位相》,筑摩书房1992年版,第350页)在这段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引文中,丸山日本论中以“时间”为轴心的近似现象学的方法论一览无余。在日本,特定的文化表象踏着潮流而勃兴,又随着新的潮流而消散,仿佛不曾留下印记一般——这些现象正是时间性的“无根”的表现。除了在所谓的传统内部,这一现象也被丸山用来解释,为什么在明治维新后新的西学思潮可以迅速地取代看似积累了千百年的旧学。相反,徐著则主张,在时间中持存的“空间性”结构决定了日本传统和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且这种结构十分顽固,不仅贯穿古代、中世和近世,甚至跨越了近代的政治泥沼延续至今。
三、从“信息交换空间”论出发看日本对外来思想“偏差式”受容
对于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孰优孰劣这一问题,读者在进行细致的考察之前,不妨先采取谨慎的中立立场。不难想象的是,丸山理论的同情者或许会觉得徐著的讨论依然是站在旁观者立场上的脸谱化做法,又或者会觉得,徐著仅仅着眼于日本本体的以宗族为单位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而忽略了只有反思“东亚”这一更广阔的区域概念才能明见的复杂的内—外纠缠结构(这恰恰是丸山在考虑日本传统时所强调的)。对于这样的可能出现的质疑,本书的作者或者本书的思考方式的共鸣者要做出有效的应对,其实并不困难。在笔者看来,当我们超出书中本身的讨论,在丸山所提供的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反思“日本性到底是什么”这一困扰日本思想界的重大问题时,徐著的解释框架依然能够贡献有意义的思路。在这里,我将尝试对此做出一个扩展性分析。
虽然正如丸山所言,日本对本国之外文化的接受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普遍宽容的策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日本成长起来的非原发性文化就可以和其起源文化完全画上等号,这是因为这些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往往会生发出一些与原初和正统的文化系统之间的微妙偏差。丸山在其古层论中并没有指出的是,日本传统不仅对种种外来文化持有开放的态度,而且对这些有意无意产生的非正统偏差同样十分包容。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在中世对海外文明的接受史也是一部偏差史。①在其思想发展的后期,丸山对于这种“偏差”也有深刻的体认,他将之称为存在于日本文化底层中的“执拗低音”,并由这个概念出发发展了他的古层论。丸山并没有对“执拗低音”的出现做社会学式的溯因推理(像本文接下去要做的那样),而是坚持对文化样本进行比照性的结构分析。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日本佛教思想史和美术史的角度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所作《正法眼藏》的“佛性”篇中,道元奇怪地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中的后半句解释为“所有存在即佛性”(悉有即佛性),而不是“所有的存在都有佛性”。这显然不符合汉文原文的语法,也很难被认作经中本意;但这样明显的“偏差”却并没有受到正统派的攻讦,反而作为独特的机辩在日本得到接受,并成为日本古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想。第二个例子:江户时期的日本画大师伊藤若冲(1716—1800)的花鸟画,有一部分是对元代的文正(鹤鸣图)、明代的陈伯冲(松下双鹤图)等中国名家流入日本作品的临摹,但若冲的摹写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注入了自身的风格:当原画和若冲的临摹作品并列时,观者不难发现,他的画和中国的文人画比起来,少了一些幽玄淡泊的文人气息,多了一些江户时代所赋予的明艳鲜活的世俗生机。有意思的是,这些和原本“稍有偏差的摹写”本身,同若冲其他原创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绘画史上重要的结晶。
这样一种有偏差的学习和模仿在日本文化的各种领域广泛出现,不仅得到了普遍的接受,甚至也被接受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徐著的解释框架就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解释。我们可以说:从信息交流的空间条件来说,孤悬海外的先天地理条件,使得海外文明信息的输入出现偏差的概率提高,而当偏差和争议出现时,求证和修改的成本提升、效率大减;出于这种情况,更使得“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内容可以不受到由“正统派”所把持的纵向信息管理通道的影响,在日本本土生根发芽。同时,扁平多元的乡土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个对“非正统”的种种芜草相对宽容的环境,酝酿出新的可能性。②当然,纵向的管制并不总是缺席的。德川幕府对基督教的禁令以及将朱子学捧为官学的做法就是例子。最终,当这样一种偏差性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新内涵而得到日本本土的广泛认可时,它就逐渐内化为信息输送的独特形式而固定下来,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取向。
当然,这样一种将“误差”转化为积极能量的运作机制也有相当的副作用:在这种信息传播机制的土壤下嫁接出的树苗,虽然让人眼花缭乱,但又难免良莠不齐;由于在日本本土缺乏高效的信息交换网络,也缺乏纵向的正统派加以规制,由偏差产生的诸多新流派、领域之间的对话和交锋相应地也减少了,难以去伪存真。所以,丸山提出的“日本传统有着一种无节制的宽容”的说法,即使从本节给出的偏差性受容的解释来看,依然是有效的;笔者也已经说明,这一批评能够通过怎样的方式吸收进徐著的框架中。本节的讨论可以总结如下:
(1) 被徐著视为传统日本社会本质特性的日本岛内风土和政治的杂居性,也催生了一个副产品,即日本作为一个多元外来文明的容器——抑或熔炉——的杂居性。
(2) 这些杂居的外来文化同其起源文化之间,由于信息交换渠道的不畅难免产生偏差。
(3) 这些偏差在日本本土的扁平横向的信息空间结构中,又获得了在其他东亚文明中少见的宽容和承认。
(4) 我们可以将这些偏差视为日本传统文化底层的主体内容,而不用接受丸山对日本文化无古层的论断。
(5) 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如丸山所言,日本传统也有杂芜混乱、缺乏对低质量内容的过滤机制这一负面特点;这也是由日本的风土结构所造成的。
这些分析说明,徐著在“信息交换理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展开的关于日本传统特性的讨论具有进一步深挖的价值,也有着和丸山的思想史理论进一步对话的可能。
四、日本近代政治的“纵向补强”和“无人负责的体系”
正如笔者在第一节介绍的,与其对日本的乡土传统在价值上的认可态度相反,徐著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其自身传统政治改造是否定的。在提及这一改造的本质时,作者写道:
一种统一的“大日本帝国”观,则纯然是明治维新的产物,而非日本传统文化所孕育的果实。尔后开始的军国主义化进程,其实是以全面删减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横向交流结构”、补强其“纵向管制结构”为特色的。①徐英瑾:《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 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第468页。
根据徐著的判断,一个集权的法西斯的日本正是这一改造的结果;而需要为日本的侵略行径付出代价的,也是这种“纵向管制结构”。这个诊断和丸山真男的看法是不同的。
丸山对于这一方面的讨论,集中在他对“国体论”的批判上。国体论是一种政教合一的集权主义政治构想。①不过,这种政治构想也会暗藏在一些表面上看上去非政治的文本中。比如日本在1980年颁发的《教育敕语》,虽然是一份国民道德教育的文书,其内容却以“国体论”的重要观念为蓝本。这份文书包含了对儒家传统道德中的忠孝思想的鼓吹和对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治制度的正当性的确认。关于《敕语》和国体论的关系的简明介绍,可参照苅部直:《日本思想史的名著30》,ちくま新书2018年版,第194—198页。它从明治时期开始就成为了日本官方意识形态,并通过《明治宪法》成为了一种国家意志。根据最一般的描述,国体论的起源来自倒幕时期的革命者提出的“尊皇攘夷”思想②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我们刨根究底地探索“国体论”中忠君爱民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在德川幕府时期隶属于水户藩政治集团的会泽正志斋(1782—1863)所撰的《新论》一书,而众所周知,水户藩江户时期的思想界以崇尚儒学著称,其主要贡献是基于儒学的五伦提出了所谓的“大义名分论”。具体的讨论可参照尾藤正英的《日本的国家主义——“国体”思想的形成》一书(岩波书店2014年版)。,其核心内涵有三:第一,天皇至上,万民服从天皇;第二,在第一点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日本,从而取代过去以藩为基本单位的政治形态;第三,日本至上,即将日本所独有的“日本性”在价值判断上抬高到绝对的层面。不难看出,国体论的这些观念符合徐著对近代日本“补强纵向、削弱横向”的政治改造的描述。
丸山认为,国体论和其他被归属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一样,是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产物,在它内部,既有儒教的前现代的伦理内涵,又包含了西方近代立宪思想的内涵,甚至也有民主主义的要素。要命的是,这种兼容并包还采取了漫不经心的形式,它不仅缺少精巧的思辨来整合这些要素,甚至没有具体的内容来表述国体论的那些基本的原则应当如何在一个近代的体制中加以实现。所以他说:“由于日本的‘国体’本来便非彻底的内在性的东西,也非彻底的外面式的存在,所以它便如其所是地适应了(当时的)如此这般的‘世界史的’阶段。”③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p.37。
回归到现实层面,丸山指出,国体论作为一个政治纲领,并没有在日本得到真正的落实,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因为它的内在空空如也。基于这一点,丸山推论,在近代将日本引向政治灾难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一个实现了其最初构想的高压式的帝国体制,而是这种体制构建的失败。具体来说,这是指,当日本在进行徐著所说的纵向补强时,由于对这样一个目标应当如何实现缺少具体的解决方案,故而这一过程只是以一种粗陋和随缘的实用主义开展下去的(用丸山自己的话说最终这一过程变成了政治家“在办公桌前的自我运动”)。同时,过去的政治结构中的“去中心化”或者“无中心化”特征其实依然被整合进了这个新的体系中,并且成为实际上的主导。①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不少史实得到印证。在当时的日本政治界和思想界,对明治宪法所确立的体制,就起码有三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即大权政治、内阁政治和民本政治(参见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岩波书店1996年版);而这些主张又逐渐分化为一些更为一致的主张(甚至对于“内阁”的作用我们都可以罗列出“超然内阁”“举国一致内阁”“协力内阁”等种种不同的主张),进而被不同的派别(天皇亲政派、内阁派、议会派)所吸收,并为他们之间的斗争服务(参见坂野润治:《日本宪政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这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的极端暧昧性,显然并不正常。其结果是,在一个“万民一体”、仅余同质性的体制中,虽然每个人(除了天皇)都被赋予了同一且无限的责任,但这种极端的要求内涵的缺失和落地的失败,又让这种责任化约为无责任。由于没有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可以在真正意义上为这个隆隆开动的国家机器负责,所以松散的各自为政的政治团体就在一种暧昧的氛围中将这个国家推向恶的深渊。
那么,日本的传统是否应该对这样一种暧昧的政治结构负一定的责任呢?丸山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我们不难从上文的讨论中推断出来:正是由于熔炉式的日本传统只有对外来文化无批判的“无限拥抱”,而缺少真正的原生内涵,“国体论”这样的粗糙混合物才能大行其道。第二,在丸山看来,明治政府高层的政治状况,其实无非是日本传统中“以同组为纽带、共同祭祀和‘邻保互助的古风’所制成的部落共同体”之特性的一种投射;而整个明治时期的日本进行改造的本质,其实是将日本改造成为过去地方性的宗族共同体的一个扩大版而已。丸山分析道,这种构成日本社会基本细胞的风土共同体内部,通过人情这一纽带,形成了尽量避免冲突、保持内部一致的宗族传统;在这些共同体的风土中蕴含着的“集权主义”“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要素,很自然地在近代的日本官僚体系中得到了看似改造的继承,从而演化出了“无人负责的体系”。②参见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第49—57页。
在大方向上,徐著和丸山对于“日本传统和日本近代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首先,两者对于日本传统和近代政治之间的连续性持有对立的观点:丸山认为日本近代政治只是日本传统的一种延续,而徐著认为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通过破坏日本的传统社会结构而建立起来的。第二,两者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的社会政治条件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丸山认为,是对日本宗族社会运作模式的被动移植才造成了日本近代之恶,而徐著认为,造成日本近代走向错误道路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以纵向信息通路为主轴的集权体制。不过,在另一方面,两者的思考也不乏相通之处。比如,徐著和丸山都看到,日本传统的“杂居性”——作为一个空间性的特征——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即使经历了新意识形态的冲击和粗暴的政治改造,它也依然存活,并在明治后的日本(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比如,丸山和徐著一样,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传统宗族社会的“风土性”伦理,并将它作为解释日本历史走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引入了自己的讨论之中。
不仅如此,倘若细心梳理两者的论述,读者不难发现,其实即使是在表面上不一致的那些部分,这两种理论之间也存在着深层的互补性。
第一,徐著对日本传统的赞许,首先针对的是其诸多部落共同体之间的去中心化的分散分布模式。作者主张,日本的守护大名充当了民众和最高统治者之间的“中介性节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央对于底层劳动者的直接信息传输与物质榨取”。丸山对传统日本的批评,主要针对的则是这些共同体内部的虚伪暧昧的人情机制,而不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徐著在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在丸山的“日本传统助长了近代之恶”批评的射程之外的。不仅如此,对于本书的作者来说,丸山所给出的批评甚至可以被引入到书中关于战后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分析当中,从而对作者提到的日本现代公司的“年功制”和“终生雇佣制”的利害给出更为完整的评价。
第二,丸山的批评的要点,并不是日本传统的地方性风土本身自带着负面的价值属性,而毋宁是说,将这种宗族社会运作模式移植到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上是有问题的;而徐著在陈述日本的宗族共同体对战后日本的积极作用时,则明确表明,这种宗族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的成功,是由于它被因地制宜地应用到了处在社会中间层的市民社会的组织上。因此,虽然对于丸山理论的支持者来说,徐著没有看到日本传统和日本从明治到昭和前期政治的连续性,有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徐著对日本传统的积极意义的评价其实并没有和丸山的批评产生实质性的矛盾,倒是可以和丸山的理论结合,揭示一个“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道理。
第三,丸山关于“日本其实并没有在实质上完成‘万民一体,同功同罪’的集权体制的建设”的论断,来自他对日本近代官僚管理体制的反思,而徐著所说的日本近代社会的“纵向结构”,其确切的指称则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剥削性的“信息—物质交换”模式。前者关注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而后者谈论的则是这些制度背后更为深层的生产关系——这两者的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面进行。因此,徐著的观点也并没有和丸山的“无人负责的体系”论有实质的矛盾。可以想见,对马克思主义颇有微词的丸山应该很难认同后者的观点;不过,这并不妨碍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将丸山的洞见作为对徐著日本论的一个有益补充。
五、结论
如果笔者对徐著同丸山思想的互补性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徐著基于其“信息空间”论所给出的日本论,即使是在日本政治史这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中,也有相当程度的抗压性。不仅如此,丸山相关理论的许多洞见,其实也都可以在徐著的唯物主义解释模型中得到“落地”。比如——联系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当我们顺着丸山对“国体论”批评的思路,寻找这样一个糅合了东西古今的粗糙政治纲领的深层成因时,本文根据徐著的解释框架而给出的 “偏差式受容”论,或许就是一个可能的进路。因此,即使是那些对徐著的日本论略感违和的读者,相信也能在本书的具体分析中获得不少方法论上的启示。对于笔者来说,这正是阅读《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一书最后两章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