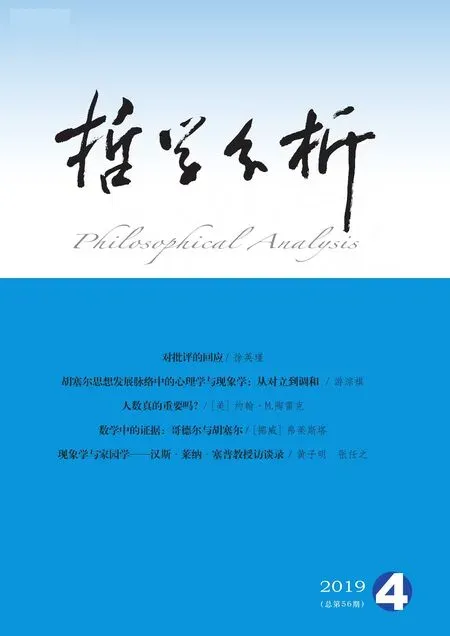“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新诠
——中古佛道论辩语境中的“老君身体”
白照杰
显庆二年(657)六月十二日,传说唐高宗亲临的一场佛道论辩会为接下来的讨论拉开了帷幕。道宣(596—667)是彼时极负盛名的护法高僧①有关道宣的生平和著述情况,参见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其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中对这场论辩进行了详细记述。论辩间,道士李荣(活跃于658—663)首先立“六洞”义(具体名目不详)②李荣为唐高宗、武后时期著名道士,曾住天元观、东明观等。《旧唐书·罗道琮传》称他是二教论争中道教方面的佼佼者。李荣于道教义学(尤其重玄学)颇有建树,注《西升经》《 道德经》《 庄子》等。李荣《庄子注》早已亡佚,另二书部分内容传世,前者可参见陈景元《西升经集注》( 载《道藏》,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后者可见蒙文通《辑校老子李荣注》(成都:四川省立图书馆1947年版)。有关李荣之道学成就,最值得参考的是藤原高男之系列研究(《道士李荣の道德经注について》,《香川大学教育部研究报告》1979年第47期,第1—30页;《西升经李荣注》,《香川大学一般教育研究》1983年第23期,第117—150页;《道士李荣の西升经注について》,《香川大学国文唐研究》1985年第10期,第6—16页;《李荣道德经注》( 一)、(二)、(三),《德岛文理大学论丛》1986年第3期,第97—132页,1987年第4期,第139—177页,1988年第5期,第103—139页;等等)。,其所谓“洞”者,指“于物通达无碍”。日后编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西明寺僧人慧立(615—?)难之:“若使于物通达无拥名洞,未委老君于物得洞以不?”李荣作肯定回答,云:“老君上圣,何得非洞?”慧立继续责 难:
若使老君于物通洞者,何故《道经》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无身,吾何患也?”据此则老君身尚碍,何能洞于万物!①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载《大正藏》,第52册,第4卷,T. 2104,第389a—b页。李荣顿时语塞,只得在高宗在场的情况下,求慧立“莫过相陵轹”“莫苦相非驳”。
慧立的设问,当然是指向今本《道德经》第十三章“何为贵大患若身?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②本文所引《道德经》内容,均出自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笑敢在书中对权威的或最早的五种版本的《道德经》进行对勘,十分便于使用。此处所引《道德经》文字,与河上公本和王弼本相同,帛书、竹简、傅奕本唯句间连接词不同(如“及吾”与“苟吾”之异),意涵并无二致。见《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第832—833页。李荣的语塞,直观地体现出“与道合一”的老君与《道德经》作者“老子(”人类)在身份上存在无法规避的矛盾,同时又隐含了更为复杂的多重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以下一系列提问:《道德经》中的“吾”是谁——作为大患的“身”是从属于“谁”的?在中古时期老君神化日盛的语境中,对《道德经》文本形成过程的理解,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时人对书中“吾”的理解?与此同时,佛教方面是如何在佛法的框架内理解《老子》中提出的“大患”一语?佛教内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变?而中古道教方面又是如何解决老君“身体窒碍”的张力及佛教方面的疑问?最后,这一“矛盾”被成功解决了吗?这一系列设问,将我们引入了纠缠复杂的荆棘丛中。截至目前,有关老子及《道德经》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然据笔者检索海内外相关成果所见,③有关老子和道德经的最重要现当代研究,可参考Alan K. L. Chan, “The Daode Jing and Its Tradition”, in,Daoism Handbook, edited by Livia Kohn, Boston and Leiden: Brill, 2004, pp. 25—29中所给出的参考书目;以及斯坦福大学的网络哲学词典所给出的参考书目,网络链接如下: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aozi/(2017年3月5日查询)。尚无专门探讨本文所关注之问题的先例,故在此希图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在繁复设问的荆棘林中开拓一条小径 。
一、“吾”的所指与中古时期对《道德经》成书过程的认知
在近代学术产生之初,学者们对《道德经》中的“吾”基本上都作“老子”自称来解读。然而20世纪以来,关于《道德经》是否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早已成为学界悬案。虽然仍有不少人认为,在缺少非常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应断言《道德经》就是多人跨时代的作品。但另外一批优秀的学者却不断地提出新证据,指出这部最著名的道教典籍实在不像是出自某一个人之手。①尹振环:《重识老子与〈老子〉——其人其书其术其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7—60页。虽然《道德经》的真实作者归属尚有疑问,但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却不构成障碍。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分析这部经典作为“文本”,在被实际“使用”的语境下,读者所感知的“吾”到底是谁。
从今人的一般阅读习惯出发,《道德经》显然是一部以“第一人称”进行撰述的作品,以此而论,其中的“吾”必然指向“作者”。然而,这一认识却脱离了《道德经》在历史中的实际“使用”语境。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Georg Müller)的观点对此问题的解答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出土《老子》中存在篇章排序错乱现象,这说明各篇章间不具有严格顺序,彼此相对独立。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老子》这样的文本‘通常’并不以书的形式存在,而是在口头记诵和记忆中存在”。由于《老子》的使用方式主要是读者“口诵”,而非“浏览”,因此其中的“吾”并不强调“作者身份”,“毋宁说它是一个潜在的读者——或者说是听众——要占据的空间的标识”②汉斯—格奥尔格·梅勒:《〈道德经〉的哲学》,刘增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梅勒的观点不免绝对,然其提出的《老子》中的“吾”未必一定指向老子或作者的观点却很有意义。如果“吾之有大患”中的“吾”并不指“老子”,而是指“阅读此书的读者”,那么显庆二年慧立与李荣之间的争论似乎便会成为一场“错解经典”的“历史误 会”!
实际上,仅就文本内容而言,《道德经》中的某些“吾”明显指向旨在说教的作者,如第四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③以上引文,以河上公本为根据,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第847页、第900页。然而,诸如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第七十四章“吾得执而杀之”中的“吾”④同上书,第884页、第904页。。则显然指向秉持国政的“圣人”,而非作者本人。除这两种情况外,《道德经》中更多的“吾”其实可以看作对所有接受其理论和思想的读者的“通指”,例如第二十章“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以及第四十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⑤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第841页、第874页。,均可指代读者自身,而不必专门归属于作者一人。如果再考虑到上述某些“吾”指向的“圣人”——实际就是这本经典的“预期读者”,显然《道德经》中的“吾”是否一定指向“老子”可被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具体到“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一句,其中的“吾”显然更适合作为阅读者的统指,毕竟“有身”是所有人类共有的特征,作者无法独占。
然而,与我们的认识不同,开篇引述的那场佛道争论中,佛道双方的代表共享了同一个认识,即“吾之有大患”中的“吾”就是“老君”本人!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不同时代对《道德经》的诠释存在差异的观点来为这一问题画上句号,要继续追问的是:这一差异是如何造成的?《道德经》中的“吾”在中古时期是如何被固定为专指老君一人的。从慧立使用“老君”而非“老子”一词,隐约可以嗅探到这一变化与中古道教的老子神化活动存在内在联系。一般经典因“撰著”成书,因此其中的“我”可以指向预期读者。然而,在宗教圣典中,常常出现神人说经,旁人记录成书的传说或现象。此类著作由于直接出自圣人之口,因此其中的“我”必然是指说经者本人。有关这一现象,最广为人知的例子莫过于佛教的“如是我闻”,佛陀口授内容中的所有“我”均指向佛陀自己。通过对相关材料的爬梳,我们发现,中古时期对《道德经》成书根源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恰恰经历“撰著”经典到“口传”圣典的转 变。
最早记载《道德经》成书的材料自然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41页。
显然,司马迁秉持《道德经》以“著书”而“立说”的观点,这一认知较符合经典成书的正常逻辑。司马迁的观点随着《史记》的广泛传播成为“正统”观点,约魏晋间成书的《列仙传》、皇甫谧(215—282)的《高士传》等大量后世材料②见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页;皇甫谧:《高士传》,收《四部备要》 (册46,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76页。《列仙传》旧传为刘向(约前77-前6)所著,对此早有疑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早期著录情况进行梳理,怀疑此书“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于向耶?”参见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第14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5—3756页。,均采“著”《道德经》之说。然而,约从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在“著书”说仍在流行的同时,道教文献中首先出现了老子“说”《道德经》的记载。如约成书于西晋、影响巨大的《西升经》称:“是以升就,道经历关。关令尹喜见气,斋待遇宾,为说《道德》,列以二篇。”③赵佶注:《西升经》,载《道藏》 (第11册,第1卷),第490b页。《西升经》为道安(312—385) 《二教论》所提及,故成书当在东晋或更早。更多讨论,可参见卢国龙:《〈西升经〉成书年代及基本思想》,《中国道教》1987年第2期,第45—49页。而这一认识历南北朝,到唐代达至极盛。如南北朝末到初唐成书的《传授经戒仪注诀》中记载:“至昭王二十四年,太岁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为关令尹先生说《五千文》。”④《传授经戒仪注诀》,载《道藏》 (第32册),第170a页。学界对这部经书的成书时代观点不统一,然唐高宗时王悬河(活跃于683)所编《三洞珠囊》中已获引述(见第9卷《老子为帝师品》),故成书当不晚于初唐。然《珠囊》所引《仪注诀》之说《道德经》时间与今本《仪注诀》不同,为“平王四十三年太岁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见《道藏》 (第25册,第9卷),第354c页]。盖老子出关、传经时间本来不详,道教方面在这一问题上时常作出调整,以期“合理化”之。有关《仪注诀》成书时间及其他介绍,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y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495—496。成书于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时期尹文操(约622—688)之手的《太上混元真录》①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77—578页。,进一步实化老子“说”经的故事,认为“老君乃于关令宅南望气台上说《道德经》”,将“说经”的地点作具体介绍,同时引用并改动了司马迁的原始记载,称:“故《史记》曰:老子为关令说五千余言,申道德之意是也。”②《太上混元真录》,载《道藏》 (第19册),第511a页。
随着道教老子“说经”观点的宣传广布,此认识随即在道教之外产生影响。隋唐之际的著名学者陆元朗(550—630)在《经典释文》中便说到老子“西出关,为关令尹喜说《道德》二篇”。③陆元朗:《经典释文》 (第2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6a页。佛教方面,如北周甄鸾(535—566) 《笑道论》,提到道教《文始传》中老子于“无极元年,乘青牛薄板车度关,为尹喜说五千文”的说法,认为相关故事均为杜撰,可发一笑;④甄鸾:《笑道论》,参见道宣:《广弘明集》,载《大正藏》 (册52,第9卷),第145c页。而到了唐初,著名护教僧法琳(527—640)在《辩正论》中虽仍鄙夷道教的很多认识,却不自觉地接受了老子“说经”的观点,称:“案刘向古旧二录云,佛经流于中夏一百五十年后,老子方说《五千文》。”⑤法琳:《辩正论》,参见道宣:《广弘明集》,载《大正藏》 (册52,第13卷),第181c页。随着唐代崇道日盛⑥有关初唐到盛唐,道教发展及政教关系问题的综合讨论,参见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0页。,源自道教内部的老子说经认识,经唐玄宗(712—756年在位)的《御注道德真经》及其在下令编纂的《一切道经妙门由起》中反复重申,几乎成为当时社会和官方的主流认识。⑦李隆基:《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载《道藏》 (第11册,第2卷),第724c页。玄宗于此也改动了《史记》的记载,称:“司马迁云:老子说五千余言。”其中,《一切道经妙门由起》所引《金玄羽章经》对老子“说”《道德经》的记述颇为奇特,称:“遇关令尹喜,即为著作《道德经》上下二篇于绿那之国。老子张口,于是隐文从口而出,以授于喜。”⑧《一切道经妙门由起》为玄宗下敕编纂,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引文见《道藏》 (第24册),第730c页。这一描述似乎是在弥合“著”和“说”之间的差异,但更是在为《道德经》附加中古道教天文成经的神圣外衣⑨有关中古道教的天文成经问题,参吕鹏志:《早期灵宝经的天书观》,收郭武主编:《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71—597页;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王承文:《灵宝“天文”的宗教神学渊源及其在中古道教经教体系中的重大意义》 ,收其《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40—789页;谢聪辉:《南宋中期以前传统道经出世的典型与特质》,收其《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与飞鸾》,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9—96页。,使之从一部诸子经典,彻底升华为代表绝对真理的“隐文”化现。⑩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老子“说”《道德经》观点越来越盛行的中古时期,“著”《道德经》的观念依然有一定影响力。如成书于萧梁或更早的《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便称老子“作《五千文》”。参见《道藏》(第18册),第236a页。唐代之后,两种成书认识一并流传至今,千年以来,似乎并无人注意到二者的本质差异。
当我们将本文开头那场佛道争论放到这样的语境中进行讨论时,慧立和李荣的争执便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二人的争论基础在于将“老君”毫无疑问地确定为“吾之有大患”中的“吾”,而这一观点其实是《道德经》为老君亲“说”的推演结果。这里,我们还需进一步指出《道德经》成书认知变迁背后的另一个问题——老君的神化。海内外学界有关老子神化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这使我们可以较为简略地勾勒出这里需要给出的相关信息。从索安(Anna Seidel)、孔丽维(Livia Kohn)、楠山春树、菊地章太、刘屹等至少数十位学者前仆后继的研究中①Anna Seidel, 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 dans le taoïsme des Han, Paris: PEFFEO 71, 1969; Livia Kohn, God of the Dao, Lord Lao in History and Myth, Ann Arbor: Center for the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楠山春树:《老子传说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9年版;菊地章太:《老子神化:道教の哲学》,东京:春秋社2002年版;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8页、第385—408页。,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发现汉唐时期是老子神化最为昌盛的时间段。东汉时期,老子从道家学者转变为与长生联系在一起的受时人祭祀崇拜的仙人,可以“道成身化,蝉蜕渡世”②边韶:《老子铭》,载《道家金石略》,陈垣编,陈智超、曾庆瑛校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学界普遍认为《老子圣母碑》也是东汉的作品,刘屹提出反对意见,但孙齐等人则对刘屹的观点进行批判。然此碑时代问题仍有一些疑问,此暂不引述。有关此碑时代问题的讨论,参见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5—335页;孙齐:《敦煌本〈老子变化经〉新探》,《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6—108页。,这一时期的墓葬中甚至也出现了“黄色、鸟喙”的老子形象。③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154页。稍晚成书的《老子想尔注》 《老子变化经》 《西升经》 《化胡经》 《老君变化无极经》 《太上妙始经》 《文始传》《三天内解经》 《太上老君虚无自然本起经》 《太上老君开天经》等道教经典④以上所举道经,均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书。学界近年对《老子变化经》的讨论最为热烈,综述参见孙齐:《敦煌本〈老子变化经〉新探》。,更是一步步将老子神化为等同于大道本身的存在,“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⑤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孙齐认为,在同一时代可能存在多种被神化的老君形象,老君神化并不存在绝对的线性历程(《敦煌本〈老子变化经〉新探》)。此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在相对较早的时间段里,老子身上的神化要素确实是随着时代的线性历程而更加复杂多元,直到多重要素并存的时代,人们才有可能在各要素之间进行选择和组合。。老子的神化,必然导致其著作的神化。众所周知,中古道教经典常常借鉴佛教因素⑥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 Stein, Vol.2, pp. 434—485. 刘屹在讨论灵宝经借鉴佛教因素时指出,“灵宝经的作者在制造灵宝经时,头脑中并没有后来佛教与道教之间那样壁垒森严的分隔。相反地,在他(们)看来,佛教理所当然的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因此,道教对佛教要素的借鉴或挪用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参见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而“说经”本来就是佛典最为典型的成书方式,道教对此体例的借鉴非常迅速。诸如《道藏》收录的产生于中古时期的《老子说五厨经》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 《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等大量“说”经,显然就是道教借鉴佛经体例的典型例证。以“说经”为体例的圣典,创造出“听—说”“凡—圣”之间的二元关系,将经书内容措置在神圣的、富有情节性的语境中。因此,较之“著书”“说经”显然更能表现出“神灵教化”的意味。在“说经”体例和老子神化成为中古潮流的背景下,《道德经》毫无困难地转变为一部由老子在终南山或函谷关,亲口传授的圣 典。
二、中古佛教方面对“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的解读
前文慧立将“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理解为(老君的)肉身窒碍,但中古佛教内部对这句出自《道德经》的话是否作其他有价值的解读或持其他态度,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此问题构成慧立观点的佛教内部语境。佛道关系问题是海内外学界近数十年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领域已取得大量成果,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探索。中古佛教领域如何认识出自《道德经》的“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即是尚未被提起重视的一个方面。就“态度”而论,中古佛教对这句出自道家典籍的“名言”不外乎正反合三个方面,以下分别论述。
(一) 中古佛教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的正面认识
现存中古佛教典籍中,最早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这句话进行讨论的是《牟子理惑论》。虽然学界对《理惑论》是否成书于汉末仍有怀疑,①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0页。但绝大多数学者都相信此书确实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佛教典籍。作为向中古早期中国人介绍佛教基本知识的小书,《理惑论》大量借鉴了《道德经》的语言和思想②有关于此,参见王启发:《〈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老子》,《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11—118页。,其中至少有两处直接涉及《老子》的“大患”问题。第一处出现在牟子尝试树立“魂神”不灭的论述中。牟子将身体比作“五谷之根叶”,将魂神比作“五谷之种实”,叶子(身体)会凋零,但种子(魂神)却不会消亡。继而提出“得道身灭耳”的观点,并将之比附于《道德经》的“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若吾无身,何患之有”③《牟子理惑论》,参见僧祐编著:《弘明集》,载《大正藏》 (第52册),第1卷,T. 2102,第3b页。。牟子的这段论述自然是中古佛教一系列“形—神”关系讨论的先河,其中所谓得道者“身灭”(神存)的认识与中国早期佛教对涅槃的认识相合,稍后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此类案例。牟子对《老子》“大患”一句的引用,显然是将重点放在“无身”而“无患”的层面上。换言之,牟子并没有将“大患”与任何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从相反的方向,将“得道”或“涅槃”的状态与“无患”的结果相对应。牟子对《老子》“大患”的第二次讨论在意旨上没有超出前一次的框架,当有人提问为何修道者仍会生病时,牟子回答称:“老子云: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壮,不壮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为大患。”④《牟子理惑论》,第6b页。同样,牟子在这里也是在表述得道(涅槃)后的状态——对“身体”的弃绝和超越。因此,在《牟子理惑论》中,出自《道德经》的“大患”一语指向佛教涅槃的理想,被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
将《道德经》“大患”一语与摒弃身体的涅槃状态相结合的理趣,在东晋僧肇(384—414)那里得到进一步论述。僧肇《涅槃无名论》称:
夫大患莫若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劳动莫先于有智,故绝智以沦虚。……所以至人灰身灭智,捐形绝虑;内无机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超然与群有永分,浑尔与太虚同体。……此无余涅槃也。①僧肇:《肇论校释》,张春波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8页。
僧肇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征引《道德经》中的“吾之有大患”,但引文中的“至人”和“绝圣弃智”等话语,无疑带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因此有理由推测引文首句“大患莫若于有身”就是指向《老子》的“大患”。②实际上,宋代僧人遵式(964—1032)在注解《肇论》“夫大患莫若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时,马上就点明了这一点,称: “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今借彼语。”参见遵式:《注肇论疏》,载《续藏经》 (第53册,第5卷),X. 870,第202a页。从这段材料可以发现,僧肇的观点与牟子相契合,同样是将“灭身”与“灭患”相对应,继而将身体的消亡视作涅槃的状态之一。较之牟子,僧肇进一步将肉身的泯灭与“智”的捐弃结合在一起,身心的双重超越最终成就无余涅槃。也就是说,在《涅槃无名论》中,单独对“大患”的超越尚不构成完满的涅槃状态,对凡俗心智的超越亦成为必须达至的任务。隋唐僧人颇崇《肇论》,僧肇的观点于是得到反复再现。如隋代三论大师吉藏(549—623)在论述涅槃义时,提到僧肇对涅槃的转译:“肇师翻为灭度,即开善用也。谓大患永灭,超度四流。……又翻涅槃作无为,言其虚无寂寞,妙绝于有故也,亦是肇师云所翻。”③吉藏:《三论略章》,载《续藏经》,(第54册,第1卷),X. 876,第838c页。澄观(738—839)和宗密(780—841)则在注解“二乘断灭,归于涅槃”一句时,分别借用了前述“肇师”的那一段话。④澄观:《华严法界玄镜》,载《大藏经》 (第45册,第1卷),T. 1883,第673b页;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载《续藏经》 (第9册,第7卷),X. 0245,第611c页。唐代僧人还通过其他方式将《老子》的“大患”与佛教的涅槃联系起来。如大觉(活跃于开元时期)在对僧伽衣着律仪的讨论中称:“故老子曰:夫大患莫若于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故圣人灭身以归无也。”⑤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载《续藏经》 (第42册,第12卷),X. 736,第974b页。“归无”,显然指抛弃肉身(灭身),回归涅槃状态。⑥实际上,后唐景霄在讨论相同律仪问题时亦引用了《老子》的这一段话,随即便明确地将之与“求无余依涅槃,化大梵之同于虚空”联系起来。参见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载《续藏经》 (第43册,第15卷),X. 737,第 393a页。从这句话中,还可以发现大觉将“老子”称为“圣人”,反映了当时部分僧人对“老子”及《道德经》中的高度赞赏。道世(约卒于683)在《法苑珠林》中征引了一个比丘与四禽兽的故事,也将《道德经》的“大患”与涅槃联系起来。故事中鸽、乌、蛇、鹿分别解说自己所认为最苦之事,而后比丘则点明这些动物“不究苦本。天下之苦,无过有身”,“志存泥洹,是故知身为大苦本”。紧接着,道世评论称:“故书云:大患莫若于身也。”①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 (第2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39—740页;道世在《诸经要集》第7卷中也使用了一段颇为类似的文字。道世的这个故事,将身体视作苦的根本,以泥洹(涅槃)来超越苦(身体)。道世用来作为最终评论的那句话,显然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道德经》文句相对应,“书云”二字或许有刻意隐匿道家文献出处的可能。
除将《老子》“大患”一语与涅槃联系外,中古僧人还常常将之与一般性的勘破“我执”相等同。如宗密引《老子》此语,解释“故知此身是一切过患根本,既执之为有,遂分自他,依此身心,起诸烦恼”②宗密著、子璿录:《金刚经纂要刊定记》,载《大正藏》 (第33册,第1卷),T. 1702,第173b页。。玄嶷(活跃于武周时期) 《甄正论》则将“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中的“有身”,解释为“自贵有己身,陵人傲物,贪声色财利以奉其身”③玄嶷:《甄正论》,载《大正藏》,(第 52 册,第 2 卷),T. 2112,第 566a页。;因此,《老子》所提倡的“无身”在这里必然就指向在根本上勘破“我”的虚妄,“自利”之心亦因无所附着而得到消弭。非常有趣的是,玄嶷实际旨趣在于表达“道之为教,诚亦多途”的观点。他对《老子》的推崇实际是想建构一个正宗的、清净的道教形象,以此来反照中古道教与老庄之学离题万里,贬低当时的道教。实际上,这一论辩方式在更早时候即为慧通所使用过。彼时慧通为驳斥道士顾欢(卒于齐永明年间)的《夷夏论》而借用《老子》“大患”一语,认为“老氏以身为大患,吾子以躯为长保,何其乖之多也”④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参见僧祐:《弘明集》,载《大正藏》 (第52册,第7卷),T. 2102,第46页。。对《老子》“大患”同样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也出现在道世《法苑珠林·感应缘》中,其中记载了左慈的传说故事。左慈因得罪曹操(155—220)而险些被害,化身为羊方才脱身。道世评论此事,称:“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俦,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也!”⑤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08页。在老子和《道德经》获得广大知识阶层认同的中古时代,强调老子之学与道教之术的差异,是佛教方面在二教争论中经常使用的手段⑥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第38页。,玄嶷和道世无疑延续了这一传统的争辩策略。正如儒家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一样,在中古僧人眼中“道家”或“道教”也存在气质上的绝对差异。
(二) 中古佛教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的负面认识
从现存佛教材料来看,对《老子》“大患”作出彻底负面诠释,并严厉批判的论述是非常罕见的。这类批判往往是出于护教原因的断章取义,流为荒唐的诋毁,缺少学理上的意义。
唐代僧人道宣所编的护教文集《广弘明集》中即录有两个案例。首先是释明为反对初唐傅奕(555—639)上书废佛的表文。唐高祖(618—626年在位)时期,由傅奕上书引起的沙汰佛道政策是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此政策虽因玄武门事变,高祖让位太宗而搁浅,却对唐代政教关系和宗教管制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①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第34页。面对咄咄逼人的傅奕,绵州振响寺沙门明 挺身上表,表文中称《老子》二篇对于治国治民均无价值,又称:
寻老子绝虑守真,亡怀厌俗,捐亲弗顾,弃主如遗,岂论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有何患乎?此令厌身弃世,弗可佐世也!②释明:《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参见道宣:《广弘明集》,载《大正藏》 (第52册,第12卷),T. 2103,第175b页。
明 的这段批判缺少学理意义,仅是意气之争。《老子》对“大患”的论说,在这里被曲解成对生命的厌恶,这显然是佛道论辩中的诋毁之词。第二个类似的案例是法琳(572—640)的文章。法琳是唐前期著名的护教僧人,因言辞过分,开罪太宗,最终获罪流放,死在贬谪途中。③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第37—39页。法琳在《辩正论》中称老庄之学是“灭身以惧大患,绝智以避长劳。议生灵于悬疣,齐泯性于王乐”④法琳:《辩正论》,收道宣:《广弘明集》,《大正藏》 (第53册,第13卷),T. 2103,第178b页。,将“灭身”的旨趣曲解为“惧”的心理。在法琳的这篇护教文字中,出现了将“吾之有大患”中的“吾”与“老子”直接对应的现 象:
李聃禀质有生有灭,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
开士曰:“老子云:‘吾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无恼,未免头白,与世不殊。若言长生,何因早死?”⑤同上书,第176a页。
显然,法琳认为“吾有大患”是老子的自指之词!结合唐代流行的老君出生即“白首”的传说可知,法琳在“老君”的“老”和对“身”的“患”之间建立起矛盾关系,希望“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对道教和老君传说进行批判。这不禁使我们回忆起开篇的那场二教争论。慧立的疑问实际可以归入这一类“反”调,而法琳此论也应当放在《道德经》由“写经”到“说经”的变迁脉络上进行解 读。
(三) 中古佛教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的有限认可和根本超越
除“正”“反”两种态度外,中古佛教对“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还存在一种“和”的态度。具体而言,部分中古佛教徒认为《老子》的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真理”相契合,却并不究竟,只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如唐代僧人智云对“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吗,吾有何患”一语的评价是“斯言近矣,而其有无之由,彼言未矣”①智云:《妙经文句私志记》,载《续藏经》 (第28册,第5卷),X. 0596,第257a页。,即认为“老氏”对身体窒碍的认识接近正确,但有关“有身”和“无身”的根本原因,则完全没能体会到。②宋代僧人智圆更直接地指出《老子》中这句话的“问题”,认为“彼徒知厌生,而无出苦之要”,与智云的说法在思想上可以衔接。参见智圆:《涅槃经疏三德指归》,载《续藏经》,(第37册,第11卷),X. 0662,第489页。然而,这一“有限认同,实际超越”的状态,不仅反映出中古时期佛教徒对道家思想的判释,有时甚至也潜藏着佛教内部义理之争的影子。这一点在禅宗的相关文献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南阳慧忠(675—775)对《老子》“大患”一语的讨论便非常具有代表性,其称:
二乘厌离生死,欣乐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乃趣乎冥谛。须陀洹人八万劫,余三果人六、四、二万,辟支佛一万劫,住于定中。外道亦八万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满犹能回心向大,外道还却轮回。③道原:《景德传灯录》,载《大正藏》 (第51册,第28卷),T. 2076,第438b—c页。
在禅宗看来,对肉身、生死的厌离态度,实际也是一种执着。因此虽然“外道”(道家)对“大患”的摒弃可以使其以较为玄妙的形式度过八万劫的时光,但这一境界终归不稳固,最终势必堕入轮回,比之二乘尤有不如。慧忠的这一观点,与前文谈到的将“无大患”比之“无余涅槃”而高度推崇的意见相左。实际上,学界常常认为禅宗的出现是中国佛教的一场“革命”,它对传统佛学的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以上引文中,慧忠所针对的不仅是作为外道的老氏之学,更是直接针对佛教内部的涅槃之说——以“彻底的无执”破除对涅槃的“执著”。慧忠的这一观点存在更早的直接渊源,曹溪慧能(638—713)的《金刚经解义》中即对以“生灭为烦恼大患”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是故凡夫有生则有灭,灭者不能不生。圣贤有生亦有灭,灭者归于真空。是故凡夫生灭,如身中影,出入相随,无有尽时。圣贤生灭,如空中雷,自发自止,不累于物。世人不知生灭之如此,而以生灭为烦恼大患,盖不自觉也。觉则见生灭如身上尘,当一振奋耳,何能缘我性哉!①慧能:《金刚经解义》,载《续藏经》 (第24册,第2卷),X. 0459,第532c页;又参见慧能:《金刚经口诀》,载《续藏经》 (第24册,第1卷),X. 0460,第534c页。
慧能认为,生死本身并无正面或负面的意义,丝毫不能影响自身的“佛性”。凡夫与圣贤的差异在于是否在“灭”后仍会退转入“生”的轮回,如果获得觉悟,那么就不会对生灭产生执着或疑惑。这一超脱生灭的认识,实际涵盖了前述慧忠对执着寂灭的批判。宋元禅宗有时还会将《老子》“大患”作为参禅话头或机锋之词②例如,有僧问金山瑞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审此身在什么处?”瑞新答:“旷大劫来无处所,若论生灭尽成非。”瑞新的回答实际与前述慧能的观点一致。参见《续灯录》,载《大正藏》 (第51册,第2卷),T. 2077,第478c页。,这亦能反应佛教方面对之态度的一种转变,但这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中古时段,此不赘 述。
以上对正反合三种情况的讨论,使我们获悉中古佛教对《老子》“大患”问题的认识。可以发现,佛教的相关认识存在多种向度,背后蕴藏着佛教中国化、二教争论、佛教内部义理变迁等多种元素。在这一相对完整的图景中,我们再来回顾开篇慧立的“机辩”质询,可以发现其将“老君”与“吾”对应起来的观点,虽然并非独一无二,却也是相对罕见的现象。其对“老君”的负面态度,以佛道争斗为背景,在中古二教交涉的脉络中占据一个较为特殊的位置。
三、中古道教理论超越“老君大患”的尝试
不论是否面对诸如慧立和法琳的责难,中古道教方面都要对老君的“身体”问题进行解释。是否窒碍于这具肉身,是关系到老君是否成为仙圣、与道合真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无法做到完美解释,那么老君的“神化”便存在明显而严重的缺 陷。
从东汉边韶《老子铭》和《老子想尔注》等中古早期材料的记述来看,被神化的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是“道成化身”③边韶:《老子铭》:《道家金石略》,陈垣编,陈智超、曾庆瑛校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④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12页。,“终乎无终,穷乎无穷,极乎无极”⑤葛洪:《老子道德经序》,参见宋太守张氏编:《道德真经集注》,载《道藏》 (第13册),“序”,第13a页。,从根本上超越凡人的生命形态,更遑论“肉身”“大患”的窒碍。然而我们发现,中古时期老子神性及传说的发展,显然是多种传统、多种人群共同创作的结果,其间虽然呈现出某种“递进式”的态势,但这一演化脉络却不具有绝对性。概言之,在同一时间会存在有关对老子的多种存在差别、甚至完全相左的神性认识;而已被高度神化的老子特征,也可能在更晚时候被拉回相对较低或潜藏矛盾的层面。因此,虽然在汉晋时期的某些人眼中,老子已经与道合一,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老君对肉身的超越仍不是不证自明的普遍认识。这一点在道教对《道德经》“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的关注中得到印证,而我们还将看到道教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明显含有针对佛教相应质疑的回应。
中古时期道教对“吾之有大患”一语的一些理解,显然非常接近《道德经》原本的意旨,即将“吾”理解为普指,而非专指“老君”。例如约出东晋时期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中太极真人介绍人的十种过患,认为“此十患在人之身也”,须当戒之,继而引《道德经》文字为证,称:“所以云:有大患者,为我有身。斯之谓矣,可不思与?可不思与?”①《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载《道藏》 (第6册),第160a页。这类“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方式,并不直接回应老君是否也有大患的问题,于是我们首先要将焦点转移到另一类专门将“吾”归属于老君(或以老君为代表的)的道教材料。据信成书于魏晋时期的《老子西升经》和成书于初唐之前的《太上混元真录》中,分别出现了以下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老君曰:……吾拘于身,知为大患。观古视今,谁存形完。吾尚白首,衰老熟年。②赵佶注:《老子西升经》,载《道藏》 (第11册,第1卷),第495b页。
老君乃于关令宅南望气台上,说《道德经》,其要曰:……吾拘于身,知为大患。观古视今,谁存形完?吾尚白首衰老,孰年?③《太上混元真录》,载《道藏》 (第19册),第512a—c页。
两则引文基本一致,二者的“孰年”当为“孰免”。两个材料均将“大患”相关内容纳入老子的宣讲之中,且以老子自身特征作为直观证据。显然,在中古道教的老子传说中,确然承认老子在某一层面上受到“大患”的窒碍。然而,即使在这些传说内部也可发现,老君的“大患”并不绝对。如在《太上混元真录》中,老君讲道结束后,拒绝尹喜随他远游,指出尹喜“道未成,岂能得远游耶”,需诵读《道德经》万遍,“深入自然”之后才可相随。①《太上混元真录》,载《道藏》 (第19册),第513c页。如果“深入自然”可以被认为是突破肉身大患的话,那么可以上天入地、四海八荒远游的老君自然已达到这种境界。因此,在这类神化传说的内部,实际隐含着老子皓首衰老的身体并不是其根本“窒碍”,而只是某种表象。实际上,宋徽宗对上引《西升经》一段的注解,便径以为老君是“示人以衰老之相”而已。②赵佶注:《老子西升经》,载《道藏》 (第11册,第1卷),第495b页。
《西升经》和《太上混元真录》等材料虽然认为老君在本质上并不会为肉身所局限,却并没有正面给出理论说明。但随着南北朝到唐代道教义学的快速发展,一些有识的道教徒随即从理论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约成书于刘宋时期的《三天内解经》认为:“道者,无也。一切之物皆从无生,有者则以无为本”,“忘身”则可“不以身为身”,“处有无之间,不有忧患也”;继而进一步解释 道:
故《老君经》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此之谓也,深哉毕矣!是知古始,还朴反真,复上古之始无,则与道合同。有形而无体,故真人能存能亡,承虚而行,日中无影,皆是无身。身与无合,故无有体影也。③《三天内解经》,载《道藏》 (第28册,第2卷),第416c页。
《三天内解经》的作者从相反的方向来解读“大患”问题,认为真人(当然包括老子)“无身”,因此也不会有“患”。真人在本质上与“道”或“无”合而为一,因此即使在有需要时化为“有形”,亦并不因此拥有不可随意改变的、束缚灵性的“体”。实际上,更早的《河上公注》解读“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时便称:“使吾无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④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页。因此,将“无身”和“无患”的状态比附当时的神仙形象,显然不是《三天内解经》的最早创造,但以“形”—“体”二分法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却又具有一些新意。而后,唐代张弧的《素履子》在论说“大患”一句时,也将重点放在仙道超凡的方面,认为其要旨在于“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于餐霞食气,塞兑转丸,履离尘之道也”⑤张弧:《素履子》,载《道藏》 (第21册,第1卷),第701c页。。
最晚成书于唐前期的《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经中,海空智藏借病集众,宣说法理,讲道“四大合故,假名为身”,“是我身者,即是大患。汝等应当厌离此身”,“内外无我,我以清净,此二等者,悉皆空空”。善种大王闻经后,指出海空智藏“得了法相”,“烦恼无主,身亦无我”,为说经故而化现病体,实际早已超越有无、我他的局限。①《太上一乘海空智臧经》,载《道藏》 (第1册,第9卷),第682b—684b页。《海空智藏经》体现出浓重的佛教空观意味,其以一切“无我、无我所”的观点来解释“无身”,指出“身”本身是假合或假象,对身相的执着实质是一种谬见。换言之,《海空智藏经》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尝试证明所有人都“无身”,并希望听众以此为念,厌离身体。因而,能享受“无身”的境界(与道合真)的得道者就成为完全贯彻“我空”真相之人。与《海空智藏经》成书时代接近的《洞玄灵宝太上真人问疾品》与前者相似,亦以神灵(天尊)托病的方式宣说身体为假合的道理,言道:“我身大病者,为有四大,无此者有何患哉?我实无四大,有何大患?……我有此苦,实非我苦,我死非死,我生亦非生,我老亦非老。苦哉有之,有之者非我身,无之者是我身。”②《灵宝洞玄太上真人问疾经》,载《道藏》,(第24册),第676a—b页。可见《问疾品》同样是秉持“无身”为真相,“有身”为谬见的观点来解读《道德经》“大患”的问题。这样的认识在唐中期尤其流行,唐玄宗对《道德经》的注疏即采用类似观点: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注:身相虚幻,本无真实。为患本者,以吾执有其身……③李隆基:《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载《道藏》 (第11册,第1卷),第720c页。
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执有身相,好荣恶辱,辨是与非……④李隆基:《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载《道藏》 (第11册,第2卷),第758b页。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离形去智,了身非身,同于大通,夫有何患?⑤李隆基:《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载《道藏》 (第11册,第1卷),第720c页。
疏:无身者,谓能体了身相虚幻,本非真实。即当坐忘遗照,隳体黜聪,同大通之无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荣辱之途泯,爱恶之心息,所谓帝之悬解,复何计于大患乎?⑥李隆基:《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载《道藏》 (第11册,第2卷),第758b页。
以上唐玄宗的注疏简洁明了,带有官方性质,可以算是唐代道教从“真空假有”角度出发对“吾之有大患”问题的总结。在玄宗的疏文中,还给出了通往世间真相的方法之一“坐忘”。成玄英对《道德经》“为吾有身”一句的注解是“执着我身,不能忘遗”⑦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载《道藏》 (第13册,第4卷),第387c页。,与玄宗的“坐忘遗照”彼此呼应。晚唐五代杜光庭在注解此句中“无身”一词时,亦言“非顿无此身也,但修道之士能忘其身尔”⑧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载《道藏》 (第14册,第13卷),第376b页。。非常有趣的是,在五代沈汾的《续仙传》里,闾丘方远(卒于902)的老师之一左元泽,在解说“吾有大患,在吾有身”时称:欲要返本,则当无为,无为当无心,不执有、无,“释氏以此为禅宗,颜子以此为坐忘”①沈约:《续仙传》,载《道藏》 (第5册,第3卷),第92c页。。看来,从盛唐开始,道教对“坐忘”的修炼实践就已经非常好地与道教义理(尤其是对“无身”的理解)的阐释结合在一起。②有关唐代“坐忘”实践的理论,当然以司马承祯的《坐忘论》为代表。有关《坐忘论》的探讨,参见朱越利:《〈坐忘论〉作者考》,载《道教考信集》,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48—61页。从此类解释出发,“老子”的“大患”问题显然很容易解决——是否超越大患,仅仅在于是否了知“无身”的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以“无我”的道理来解释“吾之有大患”,使“吾”成为一切“我”的代指(不是专指老君)。因此,在《河上公注》和《三天内解经》中充满神秘性的无身状态,与《海空经》 《问疾品》洞彻的心灵认知之间达成了某种一致。
隋或初唐的清溪道士孟安排在其《道教义枢》中提供了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解决“老子大患”的方式③孟安排的生平历来存在争议。从《道教义枢》的内容来看,其应该生活在南北朝后期到初唐的时间段内。参见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 (第1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即“法身”说。其法身说集中体现在《道教义枢·法身义》中,孟安排称:“法身者,至道淳精,至真妙体。表其四德,应彼十方。赴机于动寂之间,度物于分化之际。此其至也。”④孟安排:《道教义枢》,参见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 (第1卷),第291页。继而,他总结、升华了《本际经》 《本行经》《请问经》 《升玄经》等著名南北朝道教义学经典的观点,认为身者有三种,分别是道身、真身、报身,而报身又可分为应身、分身、化身三种(三者均为神力变化的结果)。道身者,即与道合一之身;真身者,乃清净无碍之身;报身者,则是为了酬答累世功德而获得的身体。此三身者,“本之三称,体一义殊。以其精智淳,常曰真身。净虚,通曰道[身]。气象酬德,是曰报身”⑤同上书,第292页。。接着,孟安排自然而然地将论述转移到仙人、真人是否有肉身大患问题,称:
圣人为此,故示无常,以高况下,夺其所计。故《西升经》云:吾尚白首衰老,孰免?此明世无常也。又云:……吾拘于身,知为大患。此示苦也。又[云]:天地之人物,谁独为常主?此明无我。又云:吾本弃俗,厌离世间,此示世不净。身亦是世间为患,……故说应身、无常、苦、无主、不净,便谓道果不足可欣,定是为常等四,为治此例,故说道果是常,是乐,是我,是净也。⑥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 (第1卷),第293—294页。
毫无疑问,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道教的三身义也带有浓烈的佛教色彩,从语词到内容都是对佛教相应内容的直接借鉴。然而,这一借鉴却可以很好地解决老君等圣人身体窒碍的问题。以上材料认为,圣人根本的道身和清净的真身均超脱肉体(physical)桎梏。表现为“肉身”而拥有各种烦恼过患的报身,实际是为了教化凡人而采用的方便法门,圣人虽然有此一身,却并不会真正窒碍于是。如果秉持此三身理论,那么开篇慧立对老子有大患的质询便很容易回答——老子的法身、真身无碍,作为大患的肉身是暂时的、不重要的、可以舍弃的存在,因此也无法令老君“不洞于物”。在《道教义枢》中,除以上三身义外,还给出了一个“众生本有法身”,“但为惑覆,故不见耳”的观点,与前文《海空智藏经》和《问疾品》的认识相合,此不赘 述。
综上所述,中古道教对“吾之有大患”一句作了多样诠释,尝试通过多种途径将老君从“大患”中解救出来,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如果说中古道教对“大患”问题的讨论更多地是对佛教的借鉴,那么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最晚从宋代开始出现的一些道教典籍,明显出现了针对前述唐代佛教批评的直接回应。如陈景元(1024—1094)注《道德经》此句时称“或以无身为灭坏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①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载《道藏》 (第13册,第2卷),第668b页。,便显然是佛教方面将老子“无身”批为纯粹的厌离所激起的反对。可见中国佛道交涉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借鉴”“抄袭”等词汇可以概括的复杂现象,其中隐含着频繁多样、循环往复的文化对话和变 迁。
四、结论
本文首先讨论了《道德经》中的“吾”,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专指“老子”的问题,其中老子神化和佛教影响下的经典成书认知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道德经》中第一人称“吾”的所指的转变,引发对此文本部分内容产生新的理解。“吾之有大患,为吾有身”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在佛教材料中,慧立对此问题的质询与李荣无法作答的尴尬,将这一转变所带来的认知错位放置在二教争论的放大镜下,突出了文本解读变迁所造成的诠释差异。
接着我们对佛道二教在“大患”和“老子身体”问题上的分别讨论也作了详细分析。整体上看,佛教方面对这句出自道教经典的话的认识还是相对积极的,虽然偶尔会出现激烈的反对和刻意的贬低,但佛教对“大患”一语的认可还是贯穿了整个中古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本文思考的慧立的质询在本质上主要是临场的“机辩”问答,未必拥有哲学或思想史意义的价 值。
本文对中古道教义学中解决老君“大患”问题的具体方式也作了详细介绍,从中可知,即使是在初唐时期,也已经存在多种解决老君“身体窒碍”的理论办法,显然中古道教对圣人(得道者)的身体特质提起了高度重视。由此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质疑《集古今佛道论衡》对显庆二年那场二教辩论情况的记载。如果初唐时期道教内部已经有很好的理论可以解决慧立的质询,那么作为当时道教界的代表、道学理论大师的李荣,不太可能哑口无言,更不可能在唐高宗在场的情况下当众讨饶。因此,这则佛教内部对二教争辩情况的记载,很可能有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
综上所述,我们对中古佛道二教在某个问题点上的讨论作了相对完整的讨论,希望以此方式勾勒出佛道在思想交涉方面的复杂语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文化交涉问题都需放在复杂的语境中进行综合考虑,对语境要素的分析越完整,就越能理解考察对象的真实价值。本文以此思路观察佛道关系,期待能够引发更多相关讨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