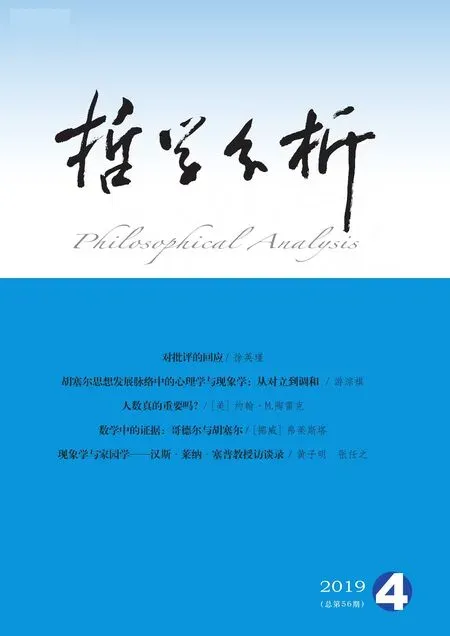现象学与家园学
——汉斯·莱纳·塞普教授访谈录
黄子明 张任之
汉斯·莱纳·塞普(Hans Rainer Sepp)教授任教于布拉格查理大学人文学院。1974年至1979年在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in München)学习哲学和德语语言文学。1982至1992年作为弗莱堡大学(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in Freiburg)胡塞尔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担任《胡塞尔全集》 (Husserliana)的合作编者。1991/1992年获取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4/2005年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人文学院和德累斯顿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获得大学教授资格。
塞普教授主持着一系列重要的现象学国际丛书的出版,如《现象学世界》 (Orbis Phaenomenologicus)、《现象学:文献与语境》 (Phänomenologie. Texte und Kontexte)和《回到源初:早期现象学研究》 (Ad Fontes. Studien zur frühen Phänomenologie),等等。此外,塞普于2004年至2014年担任弗莱堡欧根·芬克档案馆馆长,主持《欧根·芬克全集》的编辑工作。他还是布拉格查理大学中欧哲学研究所(Středoevropský Institut Filosofie,SIF)的负责人。
1988年塞普先生组织策划了“埃德蒙·胡塞尔与现象学运动”的展览,至1992年该展览先后在弗莱堡、慕尼黑、哈勒、维也纳、鲁汶、巴黎、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布拉格、普罗斯捷约夫、纽约、芝加哥和匹兹堡等地展出。2004年他在布拉格卡罗琳会堂组织了哲学艺术展“艺术与现象”(art & fenomen)。2000年他撰写了剧本《阴影国度——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生命与死亡的对话》,该剧在弗莱堡剧院上演,并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日语和中文等多种语言。塞普在圣彼得堡、图卢兹、东京、墨西哥城和香港等多地举行客座讲座。
塞普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现象学哲学的历史与问题,以及哲学、科学、宗教和艺术方面的一般知识理论。他目前致力于一门更新的身体性现象学纲领,这种现象学构成了跨学科和跨文化哲学理论的基础,它被称为“家园学”(Oikologie)。
他的重要专著有:《实践与理论——胡塞尔对生活的超越论现象学的重构》 (《现象学语境》系列第1卷,1997)、《图像——悬搁的现象学I》 (《现象学世界》系列第30卷,2012)、《论边界:跨文化哲学之导引》 (《黑皮书》系列第1卷,2014)、《想象之物的哲学》 (《现象学世界》系列第40卷,2017)、《家园学概论》 (2019年即将出 版)。
塞普获聘主讲2018年度“胡塞尔讲座”,该讲座每两年由德国现象学研究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DGPF)甄选。
问:塞普教授,您是《胡塞尔全集》的编者之一,是《欧根·芬克全集》的主编,也参与编辑《施泰因全集》,还主持编辑了几个重要的现象学国际系列丛书,如(《现象学世界》 《现象学:文献与语境》 《回到源初:早期现象学研究》等,同时也是布拉格查理大学中欧哲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能请您概述一下您过去在现象学方面所从事的研究及组织工作吗?
塞普:我在现象学领域的工作涉及现象学的整体工程,正如它在“现象学运动”中已经历史地实现出来并且还在继续展开的那样。对此我特别关心现象学立场的界限和边缘问题,也就是说,现象学的立场凭借什么同另一种或者所有其他立场划清界限。正是现象学表明了所有思想概念都是基于一种“原促创观念”(Urstiftungsidee),它引导理论的具体展开。虽然这些“原促创观念”对于最真实意义上的理论立场来说给予了尺度(maß-gebend)①形容词“maßgebend”字面意思是“给予尺度”,通常译为“决定性的”,“权威性的”,塞普教授在这里强调它从构词上显示出来的本来含义,故按其字面意思翻译。以下脚注皆为访谈者注。,但其自身在这个立场之内却大多保持着晦暗不明,正如胡塞尔在他后期的关于欧洲科学发展的《危机》中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保持着晦暗,因为它们处于一种理论的开端; 可以说是它们照亮了一种理论的研究领域,但它们本身并没有被它们自己产生的光所照亮。由于这些原促创处于理论的边缘,它们更多地涉及人类实存的运动(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②语出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契卡(Jan Patočka),参见 Jan Patočka,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Phä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I,Hrsg. Klaus Nellen, Jiří Němec,Ilja Srubar,Stuttgart:Klett-Cotta,1991。,这种运动相关于对其自身以及对其在世界中的位置的原促创,而没有涉及那种由此产生的理论的运动,这种运动已经将这种自我相关性融入由其构成的法典中。
虽然现象学已经揭示了这种原促创与继续促创(Fortstiftungen)的结构,但现象学本身在其众多的现象学立场上恰恰还服从于这一结构。因此,一门现象学的现象学(或现象学的哲学)就与这样一种任务有关,即在意义谱系中重构各自的实存的体验视角,在其中一种(现象学的)理论产生出来。因此问题是要在各种不同的现象学进路中找到一个统一的契机:即这样的事实,也就是现象学理论以及现象学在它的运动中的多样性展示出对人类实存运动隐含的反思,而这些是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这个目标从根本上指引着我所有的现象学兴趣——出版物、书籍系列的规划,以及座谈会等会议的组织。
问:在目前活跃着的现象学家中,您应该是对早期现象学运动最有研究了,能请您谈谈当前早期现象学研究的基本状况以及它的价值吗?
塞普:对早期现象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居于次要地位。相反,根据人们在(欧洲)哲学史上经常遭遇到的模式,认为只有“大人物”有话可说的这样一种看法占主导地位。因此人们将哲学思考的发生归结于少数人身上;而发生运动本身就这样没有落入视
野。然而正是以慕尼黑—哥廷根派为代表形式的早期现象学现在首次被理解为一场运动,一种知识社会学模型,这种模型实际上已经克服了在封闭自足的个人立场和学校教育(这基本上只是同一枚硬币的反面)二者之间进行的狭隘抉择。对于一场共同完成的运动当然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点,这个基点已经见诸形式的目的中,即在与诸体验境遇(Erlebnisdispositionen)及其相关内容有关的那种研究的基础上达到哲学的认识。尽管存在这种张力,人们在共同性中注意到,每个哲学思考者在存在论上锚定的哲学起点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如前所述,正是在早期现象学中不仅示范性地展示了现象学研究所发现的并在概念上带来的东西:将每一种理论锚定在人类实存的运动中; 并且在创造共同体的尝试中,人们意识到本己的概念(和为其奠基的、“促创”这概念的实存的经验)的边界,以及因此意识到与他人交流的必要 性。
因此非常欢迎今天年轻的研究者无成见地投入到对早期现象学的研究中,因为这表明了对他人以及他人成果的开放性。而且,由于理论静观(theoría)的运动总是具有社会意义,这种研究也会对一般社会概念,对理论之外的生活,即哲学和科学之外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也正是胡塞尔的目标:借助于革新后的理论,在一个开放的、无止境的过程中来改造社会实践(praxis)①这里的“theoría”和“praxis”用的是希腊语的拉丁文拼写形式。在希腊语中“theoría”相当于德语的“Zuschauen”,即“静观”,“praxis”对应于德语的“Tun”,即“行动”。塞普教授使用这种形式既可以强调“theoría”和“praxis”在词源上本来的相对立的含义,又可以凸显现象学赋予传统静观意味的“理论”新的运动的内涵。。
问:您目前所在的布拉格查理大学人文学院以高度国际化、综合性办学为宗旨。除了现象学专业领域之外,您的教学活动和研究兴趣还延伸至多项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比如您对东亚文化以及禅宗的研究。可以说,您的研究课题非常丰富。您认为这种将西方哲学与其他学科、其他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新型研究模式会成为与传统哲学研究方式平行的重要趋势吗?
塞普:我对其他学科和其他文化的兴趣都源于同一个基本观点:对世界的态度——无论是就其理论的或实践的本性而言——独特的(einzig-artigen)实存境遇相关联,它们都基于现象学上可揭示的经验。如果现象学的核心工作是澄清原促创过程,那么现象学就是一种能够将理论概念(哲学和科学的多样性)以及非理论和前理论的世界构成(文化的多样性)的实存条件课题化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现象学早期就与其他学科建立了桥梁,后来成为跨文化课题的一个重要场所。然而在跨文化性本身成为其研究对象之前,现象学事实上就已经是跨文化的了,比如当现象学在日本被接受时,西田几多郎就已将西方和东方的思想融合在了一 起。
总体上可以说,在19世纪现象学直接的前史之后,“交互的”(inter)或“在……之间”(zwischen)①拉丁语词“inter”相当于德语的“zwischen”,意为“在……之间”,与其他词合成后常见的译法有“交互……的”“跨……的”“……间的”。“inter”在文中多次出现,译者根据语境和参考通常的译名,在这几种译法之间选择调整。就通过现象学成为其特别重要的话题。因此,现象学通过将自身存在和非自身存在结合起来思考,告别了在相对主义(对真实的规定瓦解成不相关的元素)和普遍主义(一切的真实都从属于一个规定它们的优先性的东西)之间非此即彼地进行抉择:人类的实存是在自身中聚拢的,正如它同时又是对自身偏离的;它是停泊于自身之中的中心,并且同时也是边缘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自身中向外伸展的行为。主体性不再站在现实的对立面,而是交织于其中。行为者因此不再是自主的主体,而是处于关系中的主体。通过将这个中心解读为“相关性”(Korrelativität) (胡塞尔)或“共创性”(Konkreativität) (罗姆巴赫)②参见 Heinrich Rombach,Der Ursprüng. Philosophie der Konkreativität von Mensch und Natur,Freiburg: Rombach,1994。,中心转向它的边缘,转向他人的深度和自身的深度。因此,个体的或社会的位置不仅由其中心决定,而且首先是由其边界决定:这个位置只是“相对绝对的”(relativ absolut) (舍勒),因为它的边界表明对本己的肯定(向心的)并且超越它向外延伸(离心的)。同时作为中心和边界,这是“交互学科”和“交互文化”概念中“交互性的”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含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现象学仔细审查了“交互性”的难题,而且它的可能性条件本身自始至终就是这种“交互性”思想。因此,强调这一点也是一门现象学之现象学的任务。
问:您最近重点发展和从事的“家园学”③“Oikologie”(家园学)是一个新兴词汇,希腊语词“oĩkos”相当于德语的“Haus”,即“家”“居所”,与这个词同源的还有“Ökologie”(生态学)和“Ökonomie”(经济学)。Oikologie殊为难译,这里采用的“家园学”来自倪梁康教授的建议。塞普教授所发展出的“现象学的家园学”试图 “把经济学(Ökonomie)相关项与生态学(Ökologie)相关项关联在家园学(Oikologie)这一统一概念之下”,从而避免“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本身成问题的对立”。参见Hans Rainer Sepp,Grundfragen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Oikologie,2011。属于当前西方学术界的前沿领域,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中国读者对此还比较陌生。您能介绍一下这项研究吗?您最初的研究动因是什么?您说过,“家园学是哲学的哲学”,那么在现象学以及欧洲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家园学将会处于什么位置?
塞普:现象学基础上的哲学的家园学试图重新描绘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它反对两种广为流传的观点:一种认为个体的东西是社会的东西的衍生物,另一种将作为个人空间的家园(Oikos)与作为公共领域的城邦(Polis)截然区分开。与此相对的是对个体的两种模式的区分:一种模式是,个体实存作为个体的,其自身统觉实际上是特定社会文化的结果,另一种模式则是,个体的东西(das In-dividuelle)①拉丁语词“In-dividuelle”相当于德语的“Unteilbare”,字面意思是“不可分的”,塞普教授在这里强调个体作为不可分的存在。原则上先于社会的东西。在这里,个体或不可分者(In-dividuum)是被分离之物的典范——在列维纳斯的“分离”(séparation)的意义上。事实上,是“我”(并且没有人能代替我)在呼吸、吃饭、睡觉,等等。那么就要追问,是什么使得根本上分离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ät)社会化,答案就是:这种调解是通过“家园”(Haus)来实现的。可以说,家园是这样一种设置,通过它,身体性(因为个体的不可分的实存是一种身体性地被把握的实存)来试验其社会化能力。例如,对于本己身体,初步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从内部和外部形成,而对于家园,它们被再生产,并且通过语言和一般想象权能被“社会化”(家园是“第二身体”,就像身体已然是“第一家园”)。简而言之,家园是两种“内存在”(Insein)之间的中转站,第一种是被描述为纯粹身体性的内存在,另一种已经在一个世界背景下运作,也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比如海德格尔只认识到后者。然而问题在于,人们从后者出发再也无法获得前者。二者的交接处正是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中理解为“家园”的东西,而在城市建设文化中,它显然始于由石头筑成的、指向永恒的圣所(例如安那托利亚的哥贝克力石阵,英国的巨石阵)。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条件,人类作为“文化构成”的存在,也就是定居生活所担当的特别的角色(作为一种变形,无定居的游牧生活也包括在内),它们本身就存在问题,对此涉及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欧洲,哲学和科学的“原促创”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定居文化为前提,与此相关的,哲学上关于“原因”(Grund)和“论证”(Begründung)的话语,对(知识)拥有(Besitz)的追求,还有“理论”(Theorie)和“实践”(Praxis)的概念,以及作为“理论的实践”的理论(theoría)的发现(胡塞尔),等等,这些意味着什么。②“Stiftung”(促创)本义为“建立”,“Grund”(原因,根据)本义为“土地”,“基础”,“Begründung”(论证)本义为“建立”,“为……奠基”,“Besitz”(占有,占有物)词根来源动词“sitzen”(坐,占据)。列举这些词的本义及其在哲学文化上的引申义,在从语词的构成和使用上揭示了欧洲哲学和科学与一种定居文化的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园学也是一种哲学的哲学。它不是以某个“文化”的概念为前提的“文化理论”,而是要去澄清“文化之物”本身。
从这几点说明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家园学是现象学的一个必然成果。如果现象学表明了一种转向“交互性的”视野转变,那么家园学的问题就是,这一主题视野是如何在意义谱系上实现的,在关于“中心”“向心”和“离心”、“内部”和“外部”、“绝对”和“相对”等的意义偏移中,哪些条件直接构成了这个视野的基础。澄清这一点将是现象学的家园学哲学的任务。当然,这项澄清工作可以扩展到所有哲学运动,那将会有一种对哲学的家园学哲学,相应的还有对各种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家园学哲学。如果在现象学中产生出这样的洞察,即是那种在身体性中奠基的、自身定向和表现着的人类实存运动支撑着理论概念,那么让运动本身在场所构成(Ortbildung)的指导观点下成为课题就只是一个步骤了。家园学的动机就在于现象学之中,家园学是现象学固有的内在成果。
在所有这一切中,家园学的视角是基于立足点的变化:人们不再只是置身于某种“内部”(在某种社会、政治、哲学、科学、宗教的整体情况之中),而是通过悬搁从自己的家园中走出,可以自由地在它们的意义谱系中分析自己和他人的世界,从而展示出,“它们已经生成并且是如何生成的”。对此,问题不是采用一种自由浮动的“客观的”立足点,主要因为作为一种特定视角的客体化态度也是家园学澄清的主题。相反,这毋宁是通过重新构造(re-konstituiert)其发生进程来衡量一种时空整体情况的发生发展。
问:您曾经多次来访中国高校进行讲座及交流活动,也有大量作品在中国被翻译出版,中国当下的哲学及现象学研究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最后,您想对中国读者说点什
么?塞普:在华语世界中,特别是在广州中山大学,以及在北京、香港和台湾的短暂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地体会到,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是如何以高超的专业知识和巨大的干劲成功地建立起生气蓬勃的现象学研究和思考的中心,这些中心承担起了卓有意义的现象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并激励着年轻一代进行现象学的思考。未来的可预计的投入还不止于此。因为对于保持着蓬勃活力的现象学来说,有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传统进行编撰和分析性的维护,以及现象学专业研究的创造性发展。
此外,如果通过对现象学思考的充分理解的应用来增强对所有生活表现的典型核心内容及其边界的意识,那么在生活世界的、科学的和宗教的领域中社会组织会有很大的潜力。这种意识将成为文化内和文化间的均衡(Ausgleich)的先决条件,舍勒谈到过这种均衡,它包括将自身传达给他人,在自身中为他人提供一个场所,从而通过他人的目光加深对自身的体验。现象学在这里成为对一种态度的修养(Kultur),这种态度以基于实存的交流来应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分界。以这种方式实现的均衡并没有消解各个独立性,相反,它加强了它们,但是把它们的自我中心倾向还原为实体化。因此,这种均衡致力于一种稳定的不平衡①参见 Josef H. Reichholf,Stabile Ungleichgewichte. Die Ökologie der Zukunft,Frankfurt, 2008。,一种在不同世界通道之间的相互约束的协议。导入这种平衡似乎是提供给我们的思考和社会行动的唯一可能的东西,只有它可以确保人类在其个体性中生存下来。
我认为,这对于像中国文化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来说是一个适宜的导向,因为中国文化拥有一段如此丰富的、值得回顾的、关于均衡策略思考的本己历史,而今天现象学已在其中如此强劲地开启。因此,现象学思考的最内在的意义邂逅了中国世界观的本质特征,这样,在这个现象学作为家园学与中国文化的中心哲学内容相遇的地方,已经有了均衡的端倪,并且是关于对均衡的思考本身的。更清楚地阐明这些问题,将会是东西方现象学或家园学研究的一个强劲动力。
——专栏导语
- 哲学分析的其它文章
- 反思与展望“现象学的汉语经验”
——第三届“两岸三地现象学论坛”综述 -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暨“求道:在古今中西之间”学术研讨会综述
- 当代社会的伦理挑战及应对
——第19届《哲学分析》论坛述评 - 论自由意志并非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
- 反思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 人数真的重要吗?① 据John M. Taurek, “Should the Numbers Count?”,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6, No. 4, 1977, pp.293—316译出。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陶雷克仅发表过这一篇文章,《人数真的重要吗?》对当代英美伦理学的发展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