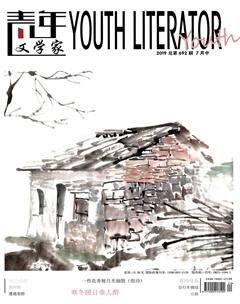“得其自”与“吾丧我”:追溯自我生命的历程
摘 要:《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是当前沈从文传记的最新作品。在内容上,作者对“自传事实”、“历史事实”与“传记事实”的展现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力图呈现传主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与文学个性,彰显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在形式上,该传记以时间为线索,呈现出简洁明了的写作风格。通过作者对传记材料的安排与呈现,给读者们逐渐呈现出一个鲜明的传主形象,也体现了作者的学者姿态。
关键词:传记;沈从文;前半生;得其自;吾丧我
作者简介:杨晨馨(1994-),女,江苏镇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如何运用相应的史料来再现传主的一生,或者说,通过传记的写作向读者传达什么样信息,一直是传记写作的核心问题。传记本身建构出以传主为中心的历史,向读者展现出传记家的某些眼光与观念。有的西方传记研究者强调发掘传记文学的文体潜能,规避数量庞大的史料证据,创造一种以传主为中心的“叙事”文风,在非虚构写作的立场上追求传记文学的修辞效果。①在2018年所出版的传记中,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成为他多年研究沈从文的一本总结性文稿,也是他沈从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与现阶段沈从文传记的最新作品。作为一名学者,该传记通过呈现传主沈从文的文学生涯彰显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尤其在传记材料的安排上,从“自传事实”、“历史事实”与“传记事实”三方面呈现了传主“得其自”与“吾丧我”文学创作上的生命历程,并体现出作者客观严谨的写作态度。
传记本身自成体系、有据可寻,这使得传记写作介于学术写作与虚构写作之间。学者赵白生注重传记材料的运用,将传记文学的重点要素归为“传记事实”、“自传事实”与“历史事实”,并指出该三要素联系紧密,呈现出“互文”关系,并构成以“传记事实”为核心的三维体系。其中,“传记事实”指的是“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作用的那些事实”;“自传事实”并非作者自述的事实,即“不纯粹是事实,也不纯粹是经验,而是经验化的事实”;“历史事实”的定义则比较复杂,作者引述前人“实证”、“主体”、“辩证”的三种观点,而作者自己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则是“不在史,而在传”。
《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一书的写作方法并不复杂,传记材料的排列与呈现的方式似乎也颇为简单,即通过写明各种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帮读者们画了一个以时间为横轴、以空间为纵轴的坐标系,摒弃了传记的多种文学手法,呈现出简洁明了、朴素无华的写作风格。随着传记“时间”的推移,传主沈从文的形象逐渐在读者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作者仿佛要通过一种画卷般的手法一寸一寸地打开传主的一生。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不仅呈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还使得读者不断有新的发现与体会。上文已经论述到,传主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世界是不断探寻生命本质的,其写作的过程也是他追溯生命的过程。这一过程被作者张新颖以“时间”的线索呈现出来,让读者追逐传主的生命历程、把握他的文学创作,增强了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在场感”。这种传记的写作方式似乎比较传统,对传记材料既不重新排列也不重新拼接,这毋宁说是作者的写作意图:追溯生命的历程比得出传主文学创作特征的结论更为重要②。
通过上两节的论述来看,作者呈现“传记事实”的方式的确借助于呈现传主文学创作生涯这一过程。在“自传事实”中,作者主要呈现了传主“弃武从文”的转折过程;在“历史事实”中,主要呈现了传主“弃文从史”的转折过程;在“传记事实”中,作者则将这两次放弃与转行统一在了传主“得其自”与“吾丧我”的生命历程中。《前半生》写的是沈从文第二次转行之前的生命历程,并且这个历程是在一定文学史背景下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作者是将传主放到了文学史中进行审视,并连带写了一些与沈从文文学创作相关的人与事。
从这个角度看,该传记与四年前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的确有不同之处:前者是将传主放在文学史背景下进行叙述,将传主的身份界定为一位作家;后者则将传主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叙述,并没有局限于文学史的背景,作者也没有非常清楚地对传主的身份进行界定,其身份也常随着人事的变动常有变动。因此,这两本书虽然呈现了沈从文的一生,但比较而言,《前半生》更将传主局限于一个身份,字里行间表达了作者张新颖的“学者”姿态,尤其在表达“沈从文的世界比人的世界大”这一观点的时候,更是以此概括了作者对传主前半生文学创作的观点。因此,在“传记事实”的呈现上,该传记对传主个性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学个性上。
在“传记事实”的择取与写法方面,与金介甫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由于该书印行多版,文中所用的为2018年7月的最新一版,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比较,也能显出该传记在呈现“传记事实”上的特点。一方面,张新颖的《前半生》多择取传主在文学生涯上的历史片段,而金介甫多择取传主所处的历史局势;前者注重传主的文学个性,并试图通过历史来突显传主个人的文学创作生涯,后者则突出了传主的历史观点对其文学创作发生的影响,有以文证史的倾向。另一方面,在“知人论世”的传统传记写作方法上,如果说金介甫写作传记的特色是将沈从文自身的历史及其所在的历史大背景与其文学作品互相阐释的话,那么,张新颖的传记写作则重点突出了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的开笔、成长、封笔的过程,其间穿插传主的恋爱故事、家庭成员在各时期各阶段的情况等支线,通过传主的文学生涯探索其人。
在后记中,作者写作的初衷得以窥探。因为作者想要“发掘对象的丰富性”,所以不想用自己的观念与眼光定义传主的形象,并通过材料的组织表现传主的一生,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思考空间。但实际上,通过前文的论述,作者不但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的观念与眼光,在择取“传记事实”表现传主个性的同时仍然有自己的侧重点,并从传主的“作家”身份出发,来呈现他的前半生。因此,在“传记事实”的呈现上,传主沈从文其人与其文之间的距离,是作者没有把握好的一点。作者对传主个性的界定虽然非常清晰,但仍有以偏概全之嫌。
作为一位读者,该传记在“自传事实”、“历史事实”与“传记事实”所构成的事实体系内快速地了解了传主沈从文在1902至1948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呈现出一定的“叙事”文风,,突显了传主的文学个性,在传记材料的发掘与排列中呈现一个传主的音容笑貌。由于平铺直叙的笔法与朴实无华的文风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非常顺利,其可读性不言而喻。作为一部传记文学,作者对传主文学生涯的呈现无意于通过新的理论、新的角度来重新展现与阐释传主的一生。作者张新颖所做的“创新”似乎也不是所谓的创新,而是通过对史料的重新展现与阐释发挥他们的价值。在传记材料的运用上,作者张新颖在“事实”的建构上,仍是非常客观严谨的。
注释:
①梁庆标:《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②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61页。
參考文献:
[1]梁庆标.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张新颖.沈从文九讲[M].中华书局,2015.
[4]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6]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8](美)金介甫.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