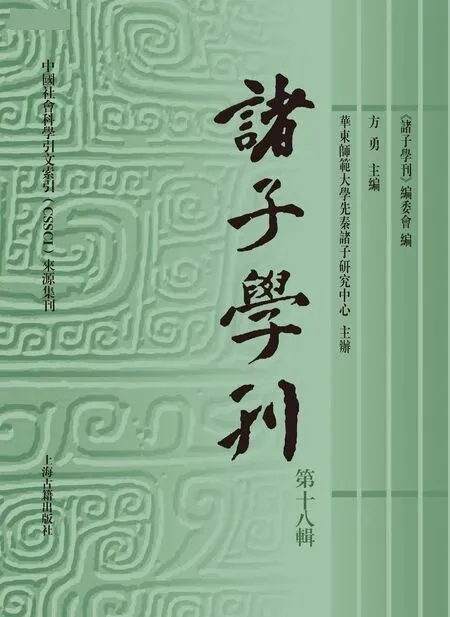芻議揚雄《太玄》對《周易》的模擬
于成寶
内容提要 論文探討了揚雄準《周易》作《太玄》的學術思想背景,認爲揚雄强烈的成名成聖思想、經學損益觀、易學占驗天道的獨特優勢及其天文學的造詣,是其敢於模擬《周易》作《太玄》的主要原因。而揚雄以《太玄》準擬《周易》的活動,模擬《周易》經傳是“本”,模擬卦氣易學是“用”;《太玄》以八十一首構建“玄”的宇宙圖式時,既模擬了孟喜的卦氣圖,又吸取了京房對孟喜卦氣圖的修正成果,即將六十四卦都納入實際值日之中,從而也解決了《玄》首與《易》卦的完全對應問題。《太玄》的出現有着重要的易學史意義,它以《易》而非《易》的形式終結卦氣易學,使易學重新回歸到《周易》經傳本身;高揚易學的道德指向,使道德重新成爲人們修身處事和價值評判的依據;弘揚易學的簡易之道,使易學率先從西漢繁瑣的經學中走了出來。
關鍵詞 揚雄 《太玄》 《周易》 易學史 意義
一、 揚雄準《周易》作《太玄》的學術思想背景考察
揚雄是西漢末期的大儒,堪稱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漢書·揚雄傳》總結揚雄一生的成就時曰: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1)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583頁。
在揚雄的諸多著作中,飽受非議的是《太玄》。其自《太玄》撰成那一天起,便受到時人的批評與譏刺。揚雄好友劉歆對他説:
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2)班固《漢書》卷八十七,第3585頁。
劉歆的話雖是善意的諷刺,但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在以經學爲利禄之進階的形勢下,揚雄苦心創作的《太玄》是不會有人研讀的。當時還有學者認爲揚雄作《太玄》是一種離經叛道的行爲:
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吴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3)同上。
清初王夫之評論《太玄》曰:
乃其尤倍者,則莫劇於《玄》焉。其所仰觀,《四分曆》粗率之天文也。其所俯察,王莽所置方、州、部、家之地理也。進退以爲鬼神,而不知神短而鬼長。寒暑以爲生死,而不知冬生而夏殺。方有定而定神於其方,體有限而限《易》以其體。則亦王莽學周公之故智,新美雄而雄美新,固其宜矣。(4)陳玉森、陳獻猷《周易外傳鏡詮》,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96~697頁。
王氏之論,對揚雄準《周易》而作《太玄》給予了貶斥,認爲《太玄》與易道相去甚遠,似可進一步討論;但他指出《太玄》的創作與當時曆法改進及王莽改制有關係,則是頗爲精闢的。
那麽,揚雄模擬《太玄》創作《太玄》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首先是揚雄思想中强烈的成名成聖意識。《漢書·揚雄傳》評價揚雄“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這是指出了他的“成名”意識。實際上,揚雄思想中更突出的是他的“成聖”意識,其最看重的《太玄》《法言》都是效法聖王、聖人而作。揚雄認爲,只有聖人之書才能經得起時間、空間的考驗,傳播久遠。《法言·問神》: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唯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5)汪榮寶《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59~160頁。
所以,當有人質疑揚雄: 聖人孔子都自謙“述而不作”,你怎麽敢“作”《太玄》呢?揚雄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的意圖就是擬經而“作”。《法言·問神》: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6)汪榮寶《法言義疏》,第164頁。
其次,揚雄個人的學術經歷使他形成了“經學損益觀”,即他没有把經學當成是一個僵化不變的體系,而是認爲經學所表達的“道”當隨着社會的變化而與時俱進。《漢書·揚雄傳》記載: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7)班固《漢書》卷八十七,第3514頁。
揚雄“不爲章句”而尚“博通”的學術風格,使他的學術不受西漢謹嚴的“師法”、“家法”的影響,從而對於經學發展有着更貼近歷史實際的理解。《法言·問神》:
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8)汪榮寶《法言義疏》,第144頁。
揚雄的“道非天然,應時而造”的觀點,在當時可以説是一個極具震撼力的口號。我們知道,西漢的董仲舒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口號: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9)班固《漢書》卷五十六,第2518~2519頁。
“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經學實質,就是要把學者的思想限定在六經的框架内而不准有任何的逾越。而揚雄則從經典的形成過程考察,發現原來五經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一個不斷的損益的過程。就《周易》來説,揚雄認爲伏羲開始造了八卦,這種易道在他的時代已經够用的了。到了文王的時候,僅憑八卦的道就不够了,於是文王將八卦增益爲六十四卦。到了孔子的時代,孔子又作《彖》《象》等,將《易》之道進一步發揚光大了。正因爲揚雄看到了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它獨特的道來與時世相應,故其認爲經學也應當是處在一個不斷發展而又不斷損益的過程中的。揚雄的經學損益觀無疑有着積極的進步意義,這也是揚雄爲什麽敢於“擬經”的勇氣與膽識之所在。
第三,揚雄在“擬經”中選擇模擬《周易》,不僅是因爲“經莫大於《易》”,更是因爲易學是西漢時期占驗天道最完備、最權威的工具。從西漢經學發展的情況來看,董仲舒通過闡發《春秋公羊傳》中的陰陽學説和《尚書·洪範》中的五行學説,構建了爲“大一統”政治服務的、以陰陽五行爲主幹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從而上升爲西漢官方新的天道觀。而《易學》則憑藉其獨有的符號體系使之成爲最富有變革性、最能吸納各種占術的經學。由漢初田何一家傳授,到王同、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家分立——這時已經出現了周王孫的《周易》古義學;再到漢宣帝時期孟喜的卦氣易學,汲取了當時天文學上的成果,以陰陽二氣消長學説爲理論基礎,將六十四卦巧妙地與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相配,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易卦解釋天地自然變化的圖式;再到漢元帝時期京房易學,他創立了八宫卦説,以陰陽二氣消長説系統地詮釋了八宫卦的内在機理與六十四卦首尾相蕩的原因,又創造了以卦爻納干支、五行、五星的模式以及建候、起算理論等,將當時在天文、曆法上所取得的最新成就一併納入易學的範圍中來,建立了一個以易卦預測宇宙運行、天地變化、人事吉凶的龐大圖式,從而實踐了《繫辭》“易與天地準”的思想,使易學成爲“推天道以明人事,察人事以預天道”的實用工具。所以,京氏易學不僅僅是漢代易學發展成就的典型代表,也是漢代經學發展成就的最高體現。而揚雄對於《易》的模擬,並不僅是對於《周易》經傳的模仿,更是對孟、京易學的模仿。
第四,揚雄模擬《周易》作《太玄》也與其愛好天文學有關。桓譚《新論》記載道:
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黄閎以渾天之説,閎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後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10)朱謙之《新輯本桓譚新論》,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8頁。
在揚雄創作《太玄》之前,揚雄已有在天文學上爲世人“立法”的宏圖大志。《新論》還記載了揚雄與桓譚辯論“渾天”與“蓋天”的事情:
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説天,以天爲如蓋轉,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曆數昏明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旦日出於卯,正東方;暮日入於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之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近,南道遠,彼晝夜漏刻之數,何從等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待報,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即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爲天左轉非也。(11)朱謙之《新輯本桓譚新論》,第29~30頁。
揚雄最初所持的宇宙學説是蓋天説,對蓋天説深有研究,並且已經圖畫形體,參以曆數,“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可見揚雄早已有爲後世立一個可循可法的“天道”的想法。後來在與桓譚就蓋天、渾天問題的辯論中,認識到了自己所持的蓋天説經不起實踐的檢驗,於是馬上將所作的蓋天説著作毁掉了。他還專門作了《難蓋天八事》批駁了蓋天之説,在他作《法言》時,還對渾天説讚譽有加: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12)汪榮寶《法言義疏》,第320頁。
揚雄正是建立在渾天説的理論上而開始創作《太玄》的,《漢書·揚雄傳》介紹揚雄作《太玄》時説:
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13)班固《漢書》卷八十七,第3575頁。
可見,揚雄以渾天説爲指導,“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在《太玄》構建起了“數度律曆”與“方州部家”相統一的宇宙時空圖式,“玄”既是“道”,還是“術”;既涵“易”,又包“曆”。“與《泰初曆》相應”,是因爲揚雄“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的太玄構建,與《泰初曆》將一日分爲八十一分有相通之處。“亦有顓頊之曆焉”,是因爲《顓頊曆》設定的一個回歸年的長度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而《太玄》八十一首中的七百二十九贊,每贊值半日,共三百六十四又二分之一日,再加上踦嬴二贊,以踦贊當四分之一日,以嬴贊當二分之一日,正合《顓頊曆》一年的長度。而《泰初曆》因采用的一日八十一分,一日與《太玄》二贊無法對應,所以《太玄》在曆法上,實際準的是《顓頊曆》,而顓頊曆是一種四分曆,這也是王夫之爲什麽貶斥《太玄》所本的是“四分曆粗率之天文也”。
可以説,揚雄冀望與聖人比肩的强烈願望、博通的學術風格、天文律曆學的喜好和西漢易學在占驗天道人事上的優勢,是促使他構建道與術相統一的哲學體系的深層原因。
二、 《太玄》對《周易》的模擬
《太玄》在創作上,既是對《周易》經傳的模擬,又是對孟喜、京房卦氣易學的模擬,這是毫無疑問的。而對二者模擬的意義是不同的: 模擬《周易》經傳是“本”,模擬孟、京易學是“用”。
先看《太玄》對《周易》經傳的模仿。從形式上看,《周易》有“易”,《太玄》有“玄”;《周易》有六十四卦,各卦皆有卦符,《太玄》有八十一首,各首皆有首符;《周易》一卦有六爻,各有爻辭,《太玄》一首有九贊,各有贊辭。就模擬《易傳》來看,《易傳》有七種十篇解釋《易經》,《太玄》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詮釋玄體。而且,二者之間存在着鮮明的對應關係: 《周易》有解釋爻辭的《小象傳》,《太玄》有解釋贊辭的《玄測》;《周易》有《文言》,《太玄》有《玄文》;《周易》有《繫辭》通論易理,《太玄》有《玄攡》《玄瑩》《玄掜》《玄圖》《玄告》闡釋玄道;《周易》有《説卦》記述八卦所象之事物,《太玄》有《玄數》講解數字所象之事物;《周易》有《序卦》闡釋六十四卦卦序之理,《太玄》有《玄衝》叙述八十一首相對之序。《周易》有《雜卦》不依卦序説明各卦的錯綜關係,《太玄》有《玄錯》亦不依卦序説明各首的錯綜關係。
從内容上看,《太玄》的首名與《周易》的卦名有着對應關係。《太玄》首名的構擬,或是采用同義詞代替的方式,如: 《周》首與《復》卦,《增》首與《益》卦,《争》首與《訟》卦,《減》首與《損》卦等。或是汲取了《彖傳》《象傳》等對《周易》卦名及其意義的詮釋成果,如: 《交》首模擬《泰》卦,首名取自《泰·彖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遇》首模擬《姤》卦,首名取自《姤·彖傳》:“姤,遇也,柔遇剛也。”《窮》首模擬《困》卦,首名取自《困·彖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親》首模擬《比》卦,首名取自《比·大象傳》:“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强》首模擬《乾》卦,首名取自《乾·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馴》首模擬《坤》卦,首名取自《坤·初六·小象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可見,《太玄》首名的擬定,是對《易傳》解《易》成果的一次繼承。此外,《太玄》贊辭在撰寫上與所模擬之卦亦多有相通之處。如《上》首模擬《升》卦,《上·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上·次六》“升於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上·次七》“升於顛臺,或拄之材”,《上·次八》“升於高危,或斧之梯”,多條贊辭皆言“升”。再如《衆》首模擬《師》卦,《衆·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温”,《衆·次七》“旌旗絓羅,干戈蛾蛾,師孕唁之,哭且”,兩次言及“師”。《太玄》在首名、贊辭的撰寫上對易卦的模擬,是我們弄清楚八十一首與六十四卦對應關係的主要依據。
與《周易》經傳相比,《太玄》唯獨没有模擬的是《周易》的卦辭和《大象傳》。揚雄没有模擬卦辭,是因爲《太玄》不是起源於占筮的實際活動,且按照《太玄》的占筮體系,卦辭在占筮中不發揮作用。《太玄》没有模擬《大象傳》,是因爲揚雄的《太玄》首形體系,不是象的體系,而純粹是數的表示,不具有《周易》六十四卦那樣强烈的卦象意義。可以説,揚雄通過對《周易》經傳的全方位類比,系統構建並闡釋了其以“玄”爲本體的天道觀和占筮體系。
再看《太玄》對孟、京易學的模擬。這主要體現在“玄”的宇宙圖式的構建上,即以八十一首準擬孟、京易學卦氣值日次序,仿照卦氣圖以構建了以“玄”爲本體的方、州、部、家與日、星、節、候相統一的宇宙圖式(14)鄭萬耕《太玄校釋》轉録自元人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外篇》中的《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及《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等,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88~404頁。,從而使《太玄》也成爲西漢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籠罩下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工具。
在揚雄模擬《周易》作《太玄》的問題上,有一個細節問題需要提出,就是《太玄》八十一首與《周易》六十四卦是否是一種完全對應的關係?我們之所以會産生這樣的疑問,是因爲在孟喜的卦氣圖中,作爲四正卦《坎》《離》《震》《兑》,不參與實際值日,而以其他六十卦值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即每卦值六日七分。《太玄》的八十一首次序,不是按照通行本《周易》排序,而是按照卦氣圖中次序排列的。鑒於此,學術界一種觀點認爲: 八十一首準擬的不是六十四卦,而是除了《坎》《離》《震》《兑》之外的六十卦。如鄭萬耕先生説:
范注以《應》首準《離》卦,似有只明其表之嫌。揚雄模仿《周易》作《太玄》,其首以孟喜、京房及《易緯稽覽圖》卦氣值日次序爲本,而孟、京和《易緯》以《坎》、《離》、《震》、《兑》爲四正卦,其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節氣,不再參與其餘六十卦分主六日七分(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之“用事”。范注不明於此,僅以《應》首贊辭有與《離》卦相交通處而附會,當不足取。(15)鄭萬耕《太玄校釋》,第124頁。
筆者認爲,這有商榷的必要,《太玄》八十一首應是準擬了《周易》六十四卦,而不是六十卦。一是從揚雄模擬《周易》作《太玄》的整個行爲來看,《太玄》對《周易》是一種完全類比,而不是部分類比。《周易》六十四卦是一個完整體系,脱離了任何一卦,《周易》無論在“象”、“數”還是“理”、“占”上,都是殘缺的,況且《坎》《離》《震》《兑》還都是《周易》中的經卦,不是雜卦。《太玄》八十一首如果不是對六十四卦的模擬,就等於認爲《坎》《離》《震》《兑》四卦在《周易》體系中是多餘的、無益於易理的,這本身説不通。
二是就《太玄》現存的注本來看,亦是認爲玄首與易卦是一種完全對應的關係。現存最早的注本范望《太玄注》,即認爲八十一首準擬的是六十四卦。范注中亦基本按照卦氣圖中的卦序來解讀《太玄》各首,而以第四十一《應》首準《離》卦,第六十二《疑》首準《震》卦,第六十四《沈》首準《兑》卦,第八十《勤》首準“坎”卦。范注在玄首與易卦的對應上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但范望是魏晉時由吴入晉的學者,他的《太玄解贊》吸收了三國時宋衷、陸績的注《玄》成果,其時上距揚雄創作《太玄》的時代未遠,而陸績又是孟喜、京房易學的研究大家,范望以八十一首對應六十四卦的意見亦值得我們重視。古代注釋《太玄》最有分量的當屬北宋司馬光的《太玄集注》,他將范望注本中玄首與易卦對應的訛誤作了徹底的修正,其以《太玄》第一首《中》、二十一首《釋》、四十一首《應》、六十一首《飾》,分别準易卦《中孚》《解》《咸》《賁》四卦之外,兼準《坎》《離》《震》《兑》四卦。對於《中》首,司馬光曰:“冬至氣應,陽氣始生,兼準《坎》。所以然者,《易》以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因爻象而定名,分《坎》《離》《震》《兑》直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每卦直六日七分。《玄》以一二三錯佈於方、州、部、家而成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於冬至,終於大雪,準《易》卦氣直日之敘而命其名。或以兩首準一卦者,猶閏月之正四時也。《坎》《離》《震》《兑》在卦氣之外,故因《中》《應》《釋》《飾》附分至之位而準之。揚子本以《顓頊》及《太初曆》作《太玄》,故日躔宿度氣應斗建不皆與今治曆者相應。”(16)司馬光《太玄集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頁。對於《釋》首,司馬光曰:“春分氣應,故兼準《震》。”(17)同上,第45頁。對於《應》首,司馬光曰:“夏至氣應,故兼準《離》。”(18)同上,第85頁。對於《飾》首,司馬光曰:“秋分氣應,故兼準《兑》。《兑》爲口舌,故《飾》多言。”(19)同上,第128頁。司馬光的觀點值得重視。
第三,從西漢卦氣易學的發展脈絡來看,孟喜易學僅是打開了卦氣易學的大門,其卦氣圖是一個初步的天氣、物候與人君政治的比附,而京房易學則通過引入干支、五行等手段,方使易卦體系成爲一個無所不包的宇宙體系。所以揚雄在《太玄數》中就“玄”的體系的擴展來看,所使用的手段與京房易學如出一轍。《太玄數》曰:
三八爲木,爲東方,爲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青,味酸,臭膻,形詘信,生火,勝土,時生,藏脾,侟志,性仁,情喜,事貌,用恭,撝肅,徵旱,帝太昊,神勾芒,星從其位……四九爲金,爲西方,爲秋,日庚辛,辰申酉,聲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勝木,時殺,藏肝,侟魄,性誼,情怒,事言,用從,撝乂,徵雨,帝少昊,神蓐收,星從其位……二七爲火,爲南方,爲夏,日丙丁,辰巳午,聲徵,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勝金,時養,藏肺,侟魂,性禮,情樂,事視,用明,撝哲,徵熱,帝炎帝,神祝融,星從其位……一六爲水,爲北方,爲冬,日壬癸,辰子亥,聲羽,色黒,味鹹,臭朽,形下,生木,勝火,時藏,藏腎,侟精,性智,情悲,事聽,用聰,撝謀,征寒,帝顓頊,神玄冥,星從其位……五五爲土,爲中央,爲四維,日戊巳,辰辰未戌丑,聲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殖,生金,勝水,時該,藏心,侟神,性信,情恐懼,事思,用睿,撝聖,徵風,帝黄帝,神后土,星從其位……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20)司馬光《太玄集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95~200頁。
揚雄的這种以數字納干支、五行的做法以及五行的“王相廢囚死”之説,當是受到了京房易學的直接影響。而對於孟喜卦气圖上,京房在繼承的基礎上亦作了修正,筆者認爲這个修正對於揚雄《太玄》的創作恰恰有着重要的影響。唐代僧人一行《卦議》曰:
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説《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唯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曆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爲四正之候,其説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静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21)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98~599頁。
可見,京房對於卦氣圖最大的改造,是將《坎》《離》《震》《兑》四正卦納入了實際的值日中去,具體的值日時點爲二至二分之首,時長爲八十分日之七十三——差八十分之七滿一日,故可視爲大約一日。如此,《坎》《離》《震》《兑》四正卦在卦氣圖中所體現的則是: 《坎》與《中孚》共值冬至起之初候,《震》與《解》共值春分起之初候,《離》與《咸》共值夏至起之初候,《兑》與《賁》共值秋分起之初候。京房易學的這種設計,將六十四卦都納入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的值日系統之中,這是對孟喜六十卦值日理論的一種完善;且《坎》《離》《震》《兑》四正卦只值所在方位的“二至二分”之日,不再統主二十四節氣,從卦氣圖的構建看更爲合理。揚雄在模擬孟、京卦氣易學以首準卦時,則不能不考慮傳統卦氣易學中以《坎》《離》《震》《兑》主“二至二分”的意義,以一首兼準二卦,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既解決八十一首與六十四卦的完整對應問題,又完美模擬了孟、京卦氣易學。
第四,從《太玄》的《中》《釋》《應》《飾》四首的贊辭來看,揚雄確實是在將其分别準擬《中孚》《解》《咸》《賁》四卦的同時,又作了兼準《坎》《離》《震》《兑》四卦的設計。兹詳細分析如下,先看《中》首:
中: 陽氣潛萌於黄宫,信無不在乎中。初一: 昆侖旁薄,幽。次二: 神戰於玄,其陳陰陽。次三: 龍出於中,首尾信,可以爲中庸。次四: 庳虚無因,大受性命,否。次五: 日正於天,利用其辰作主。次六: 月闕其摶,不如開明於西。次七: 酋酋,火魁頤,水包貞。次八: 黄不黄,覆秋常。上九: 顛靈氣形反。
“中”準“中孚”,這是顯而易見的,《中孚》卦義喻心中誠信,故“中”首曰“信無不在乎中”,《中·次三》又曰“首尾信,可以爲中庸”。在文辭的對應上,《中孚·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無咎”,《中·次六》曰:“月闕其摶,不如開明於西”,前者講月將滿月,後者講月圓而轉缺,對應的關係十分明顯。
爲什麽説《中》兼準《坎》呢?一是《坎》卦的卦義也是講“信”,《坎》卦辭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二是《坎》卦象外陰内陽,陽爲陰所包,孟喜卦氣圖曰“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黄宫”,《太玄圖》以“中”首位正北,二者相合。三是《太玄》以《中》準《坎》,除了與京房卦氣易學相應,更重要的在於其宇宙論的意義。一方面,揚雄在《中》首的文辭中表達其宇宙論,如《中·初一》“昆侖旁薄”,指“玄”體渾淪爲一,即《老子》“道生一”之意;《中·次二》“神戰於玄,其陳陰陽”,指宇宙陰陽二分,即《老子》“一生二”之意;《中·次三》“龍出於中,首尾信,可以爲中庸”,龍爲天地生物之最大最貴者,亦喻聖人,即《老子》“二生三”之意;《中·次四》“庳虚無因,大受性命”,指事物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稟受天命而生,即《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意,亦即《老子》“三生萬物”之意。可見《中》首的文辭,實是對“玄”體與用的摹寫。《中·次七》曰“火魁頤,水包貞”,大致意思是火養萬物,水包裹萬物,而“水包貞”一句更值得推究。因爲從《太玄》八十一首的依次展開來看,恰恰是從五行中的水行開始。“玄”所生第一首爲“中”,即“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之“天元”生“一”,“一”在五行的意義上屬水,而《坎》卦的基本卦象是水,在宇宙生成論的意義上與之相協,這也是“中孚”卦所不能代替的。如此,則水所包之“貞”?是否即是《乾》“元亨利貞”之“貞元”,或者説“天元”?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來看,這也是有可能的,戰國時期郭店竹簡有《太一生水》篇,認爲“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太一藏於水,行於時”(22)李零《郭店竹簡校讀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頁。。起於西漢哀平之際的緯書,又再現並具體化了這種思想:
《春秋文曜鉤》:“中宫大帝,其尊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23)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2頁。
《春秋元命苞》:“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24)同上,第631頁。
《春秋元命苞》:“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25)同上,第598頁。
如此可見,揚雄以之爲宇宙本根的“太玄”,也就是戰國中後期以來出現的宇宙最高範疇“太一”,其在實體上的表現則是秦漢以來人們的信仰對象——北極星。
再看《釋》首:
釋: 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税其枯,而解其甲。初一: 動而無名,酋。次二: 動於響景。次三: 風動雷興,從其高崇。次四: 動之丘陵,失澤朋。次五: 和釋之脂,四國之夷。次六: 震於庭,喪其和貞。次七: 震震不侮,濯漱其訽。次八: 震於利,顛仆死。上九: 今獄後穀,終説桎梏。
《釋》首“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税其枯,而解其甲”一句中已點出《周易》兩個卦名: 《震》卦和《解》卦。《釋》首準《解》卦,《周易·彖傳》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因爲《解》卦卦象爲坎下震上,所以本身含有《震》卦“震動”之意,會對判斷《釋》首是否準《震》卦形成困擾;但比較二者的文辭,就會發現《釋》首是對《震》卦的模擬。一是《釋》首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六、次七、次八等文辭要麽言“動”、要麽言“震”,可謂全首主要取《震》卦“震動”之義。二是《釋》首在文辭上模擬《震》卦卦辭非常明顯,如《震·六二》曰“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釋·次四》則曰“動之丘陵,失澤朋”,“丘陵”與“九陵”、“朋”與“貝”相通。《震·六五》曰“震往來厲,意無喪,有事”,《釋·次六》則曰“震於庭,喪其和貞”,一曰有喪,一曰無喪;再如《釋·次七》“震震不侮”,震震,形容雷聲來了人驚懼貌,顯然是模擬《震》卦卦辭“震來虩虩”之意。另外,《釋》首“震於”的句式,當是模擬《震·上六》“震不於其躬,於其鄰”一句。
再看《應》首:
應: 陽氣極於上,陰信萌乎下,上下相應。初一: 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次二: 上曆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次三: 一從一横,天網罠罠。次四: 援我罘罟,絓羅於野,至。次五: 龍翰於天,貞栗其鱗。次六: 熾承於天,冰萌於地。次七: 日强其衰,應蕃貞。次八: 極陽征陰,不移日而應。上九: 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
《應》首準《咸》卦,取《咸》少男少女上下感應之義。《應》首又準《離》卦。《離》卦的基本卦義爲附離、依附,《應·初一》曰“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意思是枝依附於幹,正取《離》卦依附之義。《離》卦的基本卦象是“日”,《應·上九》曰“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鄭萬耕説:“稷,與昃通。此句意謂: 日明之極,極則必昃,勢不可止,君子應時,與之消息,故曰應以大昃。《易象傳》:‘日昃之離,何可久也。’”(26)鄭萬耕《太玄校釋》,第126頁。而“元離”一詞,則出自《離·六二》“黄離,元吉”。由這兩處“離”字,可見《應》首準擬《離》卦甚明。《離》卦又象網罟,《繫辭》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而《應·次三》曰“一旋從一横,天網罠罠”,《應·次四》曰“援我罘罟,絓羅於野,至”,二者皆言“網罟”,當取義於《離》卦。此外,《説卦》曰“離爲《乾》卦”,以日附離(麗)於天之故,故於《應·次五》曰“龍翰於天”,《應·次六》曰“熾承於天”。
最後看《飾》首:
飾: 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初一: 言不言,不以言。次二: 無質飾,先文後失服。次三: 吐黄舌,拑黄聿,利見哲人。次四: 利舌哇哇,商兒之真。次五: 下言如水,實以天牝。次六: 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風。次七: 不丁言時,微於辭,見上疑。次八: 蛁鳴喁喁,血出其口。次九: 白舌於於,屈於根,君子否信。
《飾》首準《賁》卦,《周易·序卦》曰:“賁者,飾也。”《飾》首又準《兑》卦。按《説卦》“兑,説也”、“兑爲口”、“兑爲口舌”,可見“口、舌、言、説”是其基本卦義,《飾》首通篇講了各種情形的言説,正是因爲其模擬了《兑》卦。
總之,通過以上的分析,可見司馬光的觀點是正確的,揚雄在《中》《釋》《應》《飾》四首準擬易卦上,是分别兼準了《坎》《震》《離》《兑》四卦的,《太玄》在卦氣圖式的構建上,當是借鑒了京房將六十四卦全部納入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值日的圖式。這樣處理,也解決了八十一首與六十四卦的完全對應的問題。此外,還有一個需要辨析的問題,就是《永》首的準易卦問題,晉范望曰:“亦象《恒》卦,此合在《常》首之後,今且據舊本不易也。”(27)范望《太玄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今人多取此説。但就揚雄《太玄衝》的叙述來看:“《差》過也,而《常》穀。《童》寡有,而《度》無乏。《增》始昌,而《永》極長。”(28)司馬光《太玄集注》,第179頁。説明《常》《度》《永》三首的次序不亂,故“永”就字面意義上看雖近於“恒”,但《永》首準的卻是卦氣圖中的《同人》卦,若準《恒》卦,則導致整個以首配曆的錯亂。《太玄》八十一首與《周易》六十四卦的對應關係,見下表:

首序玄首易卦首序玄首易卦首序玄首易卦1中坎中孚2周復3礥4閑屯5少謙6戾睽7上8干升9臨10羨11差小過12童蒙13增益14鋭漸15達16交泰17耎18徯需19從隨20進晉21釋震解22格大壯23夷24樂豫25争訟26務27事蠱28更革29斷30毅夬31裝旅32衆師33密34親比35斂小畜36彊37睟乾38盛大有39居家人40法井41應離咸42迎咸43遇姤44灶鼎45大46廓豐47文涣48禮履49逃50唐遯51常恒52度節53永54昆同人55減損56唫否57守否58翕巽59聚萃60積大畜61飾兑賁62疑賁63視64沈觀65内歸妹66去無妄67晦68瞢明夷69窮困70割剥71止72堅艮73成既濟74致噬嗑75失76劇大過77馴坤78將未濟79難80勤蹇81養頤
三、 《太玄》的易學史意義
湯用彤在評論揚雄《太玄》時指出:“亦此所謂天道,雖頗排斥神仙圖讖之説,而仍不免本於天人感應之義,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察自然之理,符之於政事法度。其所遊心,未超象數。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29)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頁。湯氏之論甚爲精闢,受時代思潮的局限,揚雄在模擬《周易》經傳尤其是模擬孟、京卦氣易學創作《太玄》的學術實踐中,自然深受西漢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的影響。其所構建的,是一個涵蓋天、地、人的時空合一的宇宙圖式,在這個圖式中,自然變化與人事吉凶,通過一系列象數的手段而耦合在一起。這粗略看來,自然不脱孟、京易學的窠臼,但若進一步探究,就會發現揚雄《太玄》在易學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義。
(1) 以《易》而非《易》的形式終結卦氣易學,使易學重新回歸到《周易》經傳本身。《太玄》雖屬準“《易》”而作,但畢竟是抛開六十四卦爻象的體系另起爐灶,所以不屬於傳統易學的系統,與孟、京易學也是神合而貌離。而正是《太玄》這種“《易》而非《易》”的形式,使其在“以玄爲體、陰陽爲用”天道觀的表達上,天人合一的宇宙圖式的構建上,以及各種數術的融合上,較孟、京易學在六十四卦的框架内吸納各種數術以構建其天人感應的占驗工具,要合理得多,簡易得多,完美得多;從而也就杜絶了學者在《周易》六十四卦的框架内,進一步構建、補充或完善卦氣易學的可能,使易學研究又回歸到對《周易》經傳和傳統象數的意義發掘上。東漢時期官方學派的孟、京易學衰微,而作爲民間學派的費氏古文易學興盛起來,一些著名經學家陳元、鄭衆、馬融、荀爽都學習和傳授費氏學,易學遂在對《周易》經傳的詮釋中發展起來。這種學術的轉向,不能不歸功於《太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太玄》堪稱西漢卦氣易學的集大成之作,又意味着漢代卦氣易學的終結。
(2) 《太玄》高揚易學的道德指向,使道德重新成爲人們修身處事和價值評判的依據。《周易》雖起源於占筮活動,但從其成書之日起,即透露着强烈的道德意識和人文精神,形成於戰國時期的《易傳》,更是通過對《周易》卦德的闡述,使《周易》從迷信中解放出來,成爲人們立德、修身和處世的人生教科書。但就西漢官方易學的代表——孟、京易學來看,其重在構建“天人合一”的宇宙占驗圖式,使易學成爲“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工具,這就使“自然之變”及其“推究之術”成爲易學考察的重點,而《周易》與生俱來的道德思想,則被忽視了,不再成爲闡述的中心,故《京氏易傳》中滿篇皆是“陰陽”、“剛柔”、“動静”、“升降”、“進退”、“消息”、“飛伏”、“得失”、“往來”等,而不言“道德”。
《太玄》雖然在卦氣易學上模擬了孟、京易學,但其思想旨歸,卻在於“道德”二字——這當是揚雄創作《太玄》用力之所在,也是揚雄易學乃至其整個學術思想的根本。《玄掜》:“嘖以牙者童其角,揮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揚雄認爲,人與鳥獸的區别,在於人有道德,此是直接繼承了孟子的人性論思想;所以在《太玄》八十一首首辭和首測的撰寫上,賦予了强烈的道德評判意識。揚雄認爲,君子小人之辨,在於其是否以道德爲行事的標準,而君子要以德服人。如《强·次五》曰:“君子强梁以德,小人强梁以力”;《礥·次四》曰:“拔我不德,以力不克。測曰: 拔我不德,力不堪也”。道德是決定人生、事業成敗的根本因素,積德者昌盛,而失德者衰亡。如《徯·次二》曰“冥德徯天,昌。測曰: 冥德之徯,昌將日也”;《失·次二》曰“藐德靈微,失。測曰: 藐德之失,不知畏微也”,《劇·次三》曰“酒作失德,鬼睒其室。測曰: 酒作失德,不能將也”,《去·次七》曰“去其德貞,三死不令。測曰: 去其德貞,終死醜也”。對於統治者而言,要以德治國,有德則可長久;無德則不可長久。如《常·次三》曰“日常其得,三歲不食。測曰: 日常其德,君道也”,《更·上九》曰“不終其德,三歲見代。測曰: 不終之儀,不可久長也”。因爲人之所以爲人的根本在於人有道德,所以揚雄特别重視儒家“格物”、“自省”、“慎獨”、“慎微”等道德修養的工夫。如《格·次二》曰“格内惡,幽貞。測曰: 格内惡,幽貞妙也”,《差·初一》曰“微失自攻,端。測曰: 微失自攻,人未知也”,《周·次三》曰“出我入我,吉凶之魁。測曰: 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太玄》首辭和首測中還有很多以道德評判是非、吉凶、禍福、成敗的論述,就不一一闡述了。
(3) 《太玄》弘揚易學的簡易之道,使易學率先從西漢繁瑣的經學中走了出來。自武帝立五經博士以來,西漢官方經學逐漸形成恪守“師法”、“家法”的傳統,各經各家博士所作的經學章句被弟子奉爲圭臬,不能更改或違背,這就逐漸使學者走上了抱殘守缺又繁瑣冗雜的學術路途。班固《漢書·藝文志》在總結章句之學帶給儒學的危害時説: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30)班固《漢書》卷三十,第1723頁。
對於易學而言,漢初“訓詁舉大誼”爲特色的治學方法早已不復存在,《周易》自身特有的卦爻符號系統以及占驗功能使之成爲吸納一切數術的工具,西漢官方易學逐漸走上了繁瑣、龐雜和神秘主義的學術歧途。在《法言》中,揚雄針對當時日益繁瑣的章句經學,號召人們向着孔子的原始儒學回歸,號召學者走簡易經學之路。《法言·寡見》曰: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或曰:“學者之説可約邪?”曰:“可約解科。”(31)汪榮寶《法言義疏》,第222頁。
“可約解科”,可謂是揚雄改造官方繁瑣經學的主張和方法,而這又集中體現在其模擬《周易》創作《太玄》的學術實踐上。就揚雄之前的易學發展態勢來看,易學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是以焦延壽的《焦氏易林》爲代表,其依據《周易》的卦變理論,以每一卦各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四千零九十六卦,每一卦撰寫占辭,從而構建起了一個全新而龐大的占筮體系;一個是以京房《京氏易傳》爲代表,將各種數術生硬地納入易卦體系,試圖構建一個占驗天地人的系統體系,這兩種努力,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弊端卻使一貫有簡易之義的易學不但難於被學者理解和掌握,還因各種數術之間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而難於達到統一。這都説明了易學在繁瑣經學之路上走到了盡頭。而揚雄《太玄》通過對《周易》經傳的模擬,所用的手段是正是“訓詁舉大誼”,通過訓詁的手段以“首”名代“卦”名,詮釋了易卦的基本意義;通過撰寫首辭,賦予了易卦新的時代精神和哲學意義。揚雄《太玄》雖亦模擬了孟、京易學,但其以數爲本,以數爲先,以數明理,以數統象的學術思想和實踐,卻以一種雖機械卻簡單的方式構建了一個完美的宇宙圖式。揚雄萬物統一於數的創舉,雖别出心裁,深究起來,仍有着易學象數的淵源;而其更深刻的意義,在於向學術界宣告了漢易吸納易外數術構建宇宙論的破産,終結了後人繼續探究的可能,從而啓發人們向先秦易學回歸,走簡易易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