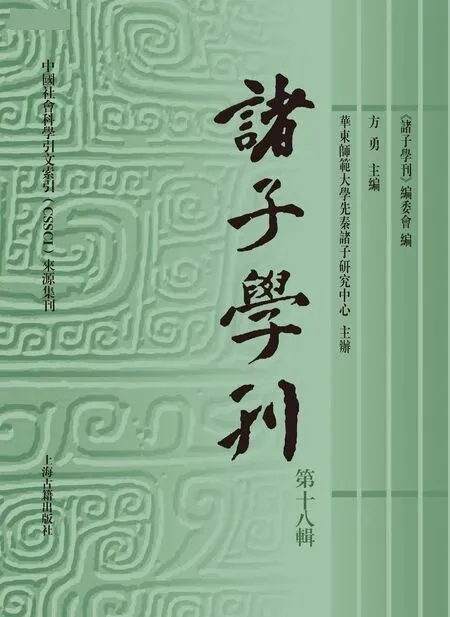“新子學”五年回顧
方 勇 張 耀
内容提要 到目前爲止,“新子學”的發展歷程可劃分爲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學界着重於探討一些基礎性的學理問題,包括“新子學”的定義、範疇、定位、意義及理論建構的操作方法等問題。在第二階段,學界則開始充實“新子學”的核心理論,並注重它與政治學、現代學術、當代文化等領域的交叉研究,同時又對之前的基礎性問題進一步探索。在第三階段,“新子學”其核心理論得到進一步充實,與其他領域的交叉研究更加深入,並力求更多地關懷現實生活,在中國大陸之外學界的影響也顯著增强。
關鍵詞 新子學 學理問題 理論建構 交叉研究 現實關懷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同樣,一代也應有一代之學術。21世紀是一個萬象更新的時代,那這個新時代又能留下什麽新的學術讓後人們研究呢?如果若干年後的人們在審視我們這個時代時卻找不到一種具有時代精神的學術來與之匹配,這將是多麽悲哀的一件事!
理論創造是一個時代任務!
可喜的是,在我們這個思想活躍的時代,各種理論層出不窮。在當代肥沃的思想原野上,已經形成了一片茂密的理論叢林。
於2012年10月提出的“新子學”,可以説是這片叢林中正在茁壯成長的一棵新生命。一晃五年快過去了,這一理論在學術界得到了廣泛討論,形成了相關文章200餘篇,促成了數次研討會議,它自身的發展的確如樹木一般經歷了從微小到參天的巨大變化。本文將回顧這一段探索歷程,以期爲該理論的深化提供更多的參考。
一、 概 述
依照研究者各時期所關注焦點的變遷,學界對“新子學”的研究歷程可分成四個階段進行梳理。
在詳細介紹各階段之前,筆者需要説明一個關於理論的比喻,以便更形象地描述“新子學”的發展歷程。筆者認爲,一種理論可以被比喻成一棵樹木: 關於它本身的概念、範疇、定位等基本界定要素相當於一棵樹木底部的根基。而它内含的核心思想及由此生發的一系列理念主張和以之構成的體系,則對應着一棵樹木中部的主幹。由上述主體思想向各維度擴展,與各領域問題交叉所産生的各種新思考與探索,則可視爲一棵樹木頂部的各段分枝。此外,一個理論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則可喻爲樹的葉子,它們都是生命力的標誌。當然,所謂“意義”都是從理論、抽象層面上來説的(即多由學者闡述而來),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實際、現實層面一個理論到底産生多大的“影響”(即在大衆中的接受廣度和深度),這種影響和接受則可借由樹木的花朵來譬喻,一個理論的傳播正如一棵樹的開花一般,既散播了花粉、延續生命,又展示了自身形象、深入人們的心中。如果一個理論的確産生了深遠影響,那現實中必然會有這一理論指導下的實踐,這種實踐則可喻爲樹木結出的果實,果實中孕育着新的思想種子,在適當的時機和條件下它又會萌芽出新的生命,這正如理論指導着實踐,實踐中的新問題又會産生新的理論。
“新子學”作爲一種新提出的理論,正如一棵新生的樹木,它的發展歷程也類似小樹的發育過程,在不同階段呈現的形態不同,重點發育的部位也不同。下面將依次介紹它産生和發展的四個階段,包括孕育期的階段和生長期的三個階段。
二、 種子階段: 孕育“新子學”的條件和背景
最初,“新子學”只是一顆思想的種子,它來自子學這棵千年古木上,是什麽讓它萌芽成長爲一個新生命?這是我們回顧“新子學”研究歷程首先要思考的問題。衆所周知,一顆種子的成活需要適宜的土壤和陽光,“新子學”的産生也可以從這兩方面解釋。
一方面,當前學術界的相關實踐爲孕育“新子學”提供了温牀。在當前的中國學界,國學正呈現强勢的復興勢頭,而作爲國學主幹之一的子學,在這個過程中則發揮着先鋒的作用。子學中的主幹是先秦諸子之學,它作爲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大源頭,在當代尤其被人所重視。不同於其他學術思想門類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命運,從晚清到現在的百年之間,諸子學一直呈現穩步上升態勢,這説明了它對當代世界的極强適應性與其發展的無限潛力(1)比如在晚清和諸子學一同復興的古學還有公羊學,可謂風靡一時,但它作爲政治儒學的核心在當代卻飽受争議。而側重於心性的新儒家人物,他們的思想的傳播在大陸有過中斷期,未能將其影響發揮到極致。這兩者的命運都可謂坎坷。另外,就算是代表現代中國發展方向的新文化運動,也因爲“批孔”的極端主張而受到當代人的懷疑,更遑論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等階段性的思潮,它們都隨社會浪潮而沉浮,更是有着芻狗的坎坷命運。相比之下,諸子學作爲思想學説的一種門類,其發展一直呈上升態勢,對各種社會浪潮都體現出適應性、貢獻着智慧力。。目前學術界研究諸子學的成果可謂日新月異,相比一百多年前的邊緣地位,現在的諸子學已成爲一門顯學。研究的深入促進了理念的革新,學者開始關注起如何將諸子學研究從西方學科分類體系中解放出來,樹立它自身的主體性,進而超越純學術範疇,復子學本原形態。爲實現這一目標,自然需要一套理論來作爲支撑與指導。但新理論的創造卻很困難,因爲它要求學界的共同努力、集體智慧,還要求研究成果的累積沉澱、整合重構,絶非一兩位學者的一兩篇論文就能完成。
近幾年啓動的“子藏”工程爲諸子學界創新理論提供了一個契機,該工程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整合各方力量進行運作,作爲超大型學術工程,它旨在對之前的子學文獻進行全面搜集整理,它的啓動在當代諸子學發展歷程上有重大意義,由之形成的系統化諸子學材料無疑能爲諸子學研究提供更堅實的文獻支援,它不僅是諸子學全面復興的標誌,更是諸子學再開新篇的基礎。筆者作爲該項目的負責人,不僅將其視爲學術工程,更看到了它的文化使命。它不單純是文獻的搜集工作,更意味着子學的復興與開新,所以筆者在運作該工程的同時,又積極開展相關項目,如創辦《諸子學刊》、主辦“諸子學”學術研討會、策劃“諸子研究叢書”等工作,這些努力結合着“子藏”工程使諸子學界學者得到凝聚,大家有了一個共同的平臺和目標,彼此之間的認同與共識也越來越多,諸子學界逐漸作爲一個整體力量出現在當代學術格局中。綜上,有了物的積累,又有了人的凝聚,如同土壤中養料和水分都積聚充足,“新子學”這顆思想的種子便有了生長的契機。
另一方面,當今時代的風氣爲孕育“新子學”營造了温室。中國文化在近現代經歷了坎坷的過程,而在當代則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期。尤其是在經濟取得進步的背景下,國人更加注重精神文化領域的發展。在學界中,學者們的思想也十分活躍,古今中外的思想輪番上陣,各種新理論層出不窮,紛紛争奪時代話語權。多元創新已成爲思想界的一大共識,各種有新意、有特點的理論都可以被提出、被推廣——總之,當代的中國迎來了一個理論的春天。同時,這又是一個充滿危機和挑戰的時代,各種前所未有的問題正在向我們襲來,衝擊着大衆心靈,也考驗着學者的智慧。這種多元而又有挑戰的時代,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誕生了諸子之學的春秋戰國時期,那麽諸子能給我們提供什麽智慧來應對這一時代,這種智慧又將如何轉化?我們能給出的答案自然是“創新子學”,這既適應了當代理論界多元趨勢,又應對了當代充滿挑戰的現實。總之,多元帶來的動力,挑戰帶來的壓力,都如同陽光一樣爲種子帶來了充足的熱量,保障了“新子學”順利萌芽。
在2012年4月舉辦的“先秦諸子暨《子藏》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提出了“全面復興諸子學”的口號,得到了專家的一致肯定和熱烈反響,引發了許多深化的討論。那麽,由上文可知,這一口號不是毫無來由的,它有上述時機和準備作鋪墊。並且,因下文可見,這一口號亦非爲暫時鼓氣而喊,它拉開了之後一出出大戲的帷幕,“新子學”將登上歷史的舞臺。
三、 第一階段: 萌芽破土、固本培基
基於上述契機,又結合之前衆人的相關探討,筆者在2012年10月22日的《光明日報》“國學版”上發表《“新子學”構想》一文,正式提出了“新子學”理念。這一理念提出後,得到了不少學者的回應,在2012和2013兩年中,學界陸續召開了三次以“新子學”爲主題的學術研討會: 2012年10月27日,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組織召開了“‘新子學’學術研討會”;2012年12月1日,上海大學新聞理論研究中心與銀川市《黄河文學》雜誌社聯合主辦“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傳承——現代文化學者視野中的‘新子學’研討會”;2013年4月12日至4月14日,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辦“‘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以及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學者共130多人參會。由於大量學者積極的參與,這兩年中形成的相關文章已達83篇之多(其中報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64篇(2)“‘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會議論文有少部分發表在2014年的期刊中,亦將其歸入2013年的文章,特此説明。,整理發表的會議發言2篇,會議綜述及報道17篇),之後,這些文章基本上都被收録進了《“新子學”論集(一輯)》一書中。
總體來看,因爲處於理論的初創階段,這一時期形成的文章在討論“新子學”時多着力於界定其概念、確定它在學術格局中所處之位置、釐清它與其他學問學説之間的關係,可見此時學界探討的焦點在於“新子學”的一些基礎性問題,基於這種共通性,筆者將這一時期定爲“新子學”理論構建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着重探討上述基本要素,正對應着一棵小樹在初生時總會着力延伸它的根基,以保證將來的迅速成長,故而在標題中筆者概括本階段的特點爲“萌芽破土、固本培基”。下面筆者將對本階段“新子學”理論建構的情況作詳細的介紹。
(一) 對“新子學”概念的多元化定義
《“新子學”構想》一文是“新子學”理論的開端,在本文中,筆者主要針對“新子學”的概念和範疇等基本問題進行了闡述。首先,筆者回顧“子學”發展的歷史,進而提出:“子學正再一次與當下社會現實强力交融,律動出全新的生命形態——‘新子學’!”(3)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進而,該文對“新子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界定:
所謂子學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應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具體内容上,則應嚴格區分諸子與方技,前者側重思想,後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録均不在子學之列。(4)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
關於“新子學”這一概念,《“新子學”構想》一文並未給出特别確切、細緻的界定,正如之後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雖然在《“新子學”構想》一文中,方勇教授已經對‘新子學’進行了闡釋,但並未對‘新子學’的概念進行嚴格的界定。……我們並不期望‘新子學’概念的界定毫無争議,相反,我們認爲更多的思想碰撞,不同的觀點交鋒更有利於‘新子學’的發展和完善,百家争鳴才是我們對現代和今後的中國文化環境的期待和踐行。”(5)高衛華、楊蘭、董浩燁《我國“新子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諸子學刊》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這種理解基本上代表了筆者的想法,“新子學”應該是在衆人討論中不斷完善的一套理論,所以在初期界定它的概念時不應設定太多的框框,而之後的事實也證明學者在“新子學”這一概念的定義上呈現出多元的取向,爲“新子學”理論的建構提供了多種可能,下文將簡述一些有代表性的説法。
1. 作爲學術新方法的“新子學”
一些學者立足於學術史的視野,從研究方法革新的層面來定義“新子學”。持此觀點的文章多先剖析“子學”作爲一種學術門類其自身的性質、特點和地位,然後由此深發,引出“新子學”的概念並闡釋之。其中,劉韶軍先生的文章論述了“子學”的發展歷程,並指出“所謂‘子學’就成了一個歷史的概念,在全新學科體系背景下,已是一個不復存在的學術概念了。……‘新子學’的‘新’在於‘舊子學’已在新的學科體系背景下無法存在。”進而該文給出了“新子學”的定義:“‘新子學’就是從新的學科體系背景下運用新的知識理念與方法研究‘舊子學’存留内容的學術。”(6)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在這一闡述中,“新子學”從屬性上是一種學術,它的研究對象仍是“舊子學”留存的内容,而它的“新”則體現在新知識理念與方法的應用上,“新子學”相比之前“子學”,可以説是“舊酒裝到新瓶中”,有繼承也有革新。劉先生這一觀點很有代表性,學界有不少研究者由這一思路定義“新子學”。如歐明俊先生認爲“‘新子學’有一對應概念,就是‘子學’或‘傳統子學’或‘古代子學’,筆者主張‘近代子學’、‘現代子學’、‘當代子學’皆可稱作‘新子學’,但各自有獨特内涵。我們今天討論的應指‘當代子學’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興起的以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新材料、新模式等研究傳統諸子百家學術的‘新子學’。”(7)歐明俊《“新子學”界説之我見》,《諸子學刊》第九輯。歐先生的文章對“新子學”之“新”作的闡釋更詳細,而其最終關懷仍是“研究傳統諸子百家學術”,由此可見歐、劉兩先生思路的一致性。而刁生虎、王喜英《“新子學”斷想——從意義和特質談起》一文則圍繞“新”展開了全文論述:“方教授提出的‘新子學’是相對於傳統子學而言的,自然其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其中的‘新’字!‘新子學’之‘新’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所處時代新;……二是研究對象新;……三是研究方法新。”(8)刁生虎、王喜英《“新子學”斷想——從意義和特質談起》,《諸子學刊》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該文著重從“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之“新”展開探討,可以説,刁先生定義“新子學”的視角也是與劉、歐兩先生相近的。另如張永祥先生認爲“新出土文獻、大型典籍整理、全新的學術理念和方法,這一切都需要我們用更爲系統的科學方法對傳統子學進行新的學術重建工作,子學研究重新崛起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一個‘新子學’的輪廓已經呼之欲出。”(9)張永祥《反者道之動——從子學走向“新子學”》,《諸子學刊》第九輯。此處的“新子學”亦是被定義爲學術史上的一個“學術重建工作”,所立足的也是學術史視野。
上述對“新子學”概念界定的思路體現着鮮明的純學術色彩,“研究”成了表述時必不可少的關鍵詞,由此“新子學”的屬性被固定在學術圈的範圍内。這種思路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因爲現當代的學術研究特别重視方法論的探討與革新,子學作爲傳統學術的四大部之一,在研究上一直缺少新的理論指導,“新子學”理念的提出正好給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理論觀照,故而衆多學者在“新子學”概念中填充學術史、方法論的元素,這種思路無疑能得到普遍的理解和支持。
2. 思想史、文化史視野下的“新子學”
但“新子學”概念的界定是多元的,學者們視角不同,所界定的“新子學”也不盡相同。當我們用思想史、文化史這層視角來審視時,會發現對“新子學”還會有更多樣的理解。
比如一些學者不希望將“新子學”界定爲明晰、固定的學術概念,而是將其視爲一種方向或思潮的籠統表達。景國勁先生提出:“‘新子學’,按照我的理解,它不是一個很嚴格的學術術語,它是一種狀態的描述,或者是一種方向性的倡導。要具體確立一個名詞解釋也許很難,它更需要的是我們去實踐,實踐之後,這個概念自然就豐滿起來了。”(10)計虹、白新茹《現代文化學者討論“新子學”紀要》,《諸子學刊》第九輯。王昀、謝清果兩先生則認爲:“‘新子學’與其説是一種概念,一種理論闡發,不如説是一種新視角,甚至於一種社會思潮之代表。‘新子學’代表了知識界面對傳統國學研究與當代學術環境所作出的思考,乃新時期國學研究與傳統文化傳播困境反思與轉型之産物。”(11)王昀、謝清果《還原、重構與超越——“新子學”視域下傳統文化傳播策略》,《諸子學刊》第九輯。景先生的文章指出了“新子學”概念的開放性與可塑性,並以具體的文化實踐作爲下定義的標準。而王、謝兩先生的文章則結合傳統文化傳播的問題,將“新子學”視爲知識界人士在特定領域的一股思潮。顯然他們的關注點不僅落足於純學術研究層面,而且牽涉了當代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元素。
基於思想史、文化史角度,這些學者定義“新子學”不再以“子學”爲基點,或者説他們理解的“子學”有了更超越的内涵,這些都讓他們所定義的“新子學”呈現出某種獨特、深刻的形態。
郝雨先生指出:“當然,‘新子學’概念的提出並不是相對於舊子學而言,不是先對舊子學做一個界定,然後對舊子學有一個新的超越而來的。實際上,‘新子學’的概念所針對的是‘新儒學’,因而我們需要對‘新子學’和‘新儒學’的概念做一個深度的剖析。‘新子學’和‘新儒學’的根本區别即在於: 它不認爲只有儒家、只有儒學才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構成,而是認爲,諸子百家才是中華文化的真正源頭。‘新子學’的‘新’,就是力圖尋找到中華文化的真正源頭,讓國人認識到我們需要傳承的文化内涵到底是什麽。”(12)郝雨《“新子學”與中華文化整體傳承》,《諸子學刊》第九輯。這裏,郝先生對照“新儒學”來定義“新子學”,將“新子學”的概念和“中華文化源頭與傳承”相結合,很典型地體現了現代文化學者理解“新子學”的思路。
陳成吒先生(筆名玄華)在“新子學”和“子學”的辨析上則給出了更明確的表述:“應該説,‘新子學’作爲一個固定符號,是指稱一個全新的概念,它本身不可以簡單割裂,更不能與此前的任何舊有概念相比附、對照。比如,將相關文字割裂爲‘新之子學’或‘新子之學’,那就是導向與所謂‘舊子學’的直接對照。這種做法是先入爲主之見,會造成‘新子學’内涵的狹隘化。”陳成吒定義“新子學”時依憑的不是“子學”而是“諸子學現象”,他認爲:“‘新子學’之稱作‘新子學’,並没有萬不能改的道理,但又之所以要如此自然地稱呼,則是因爲其與客觀存在的‘諸子學現象’有内在關聯。‘新子學’這個符號下所指的正是發掘於‘諸子學現象’又全面超越諸子學形式與内容的一種全新事物。”在此基礎上,陳成吒又對“新子學”自身的層次進行劃分:“大體而言,‘新子學’應該包括兩個層面,即哲學性‘新子學’和學術文化性‘新子學’。第一個層面,即理論層面,它是我們在面對自身與世界時基本思維方式的變革,是以此而産生的一種全新的哲學,可以稱之爲‘新子學’哲學。第二個層面,是指在這種全新哲學的觀照下,對學術文化所進行的重新發現、梳理、建構和發展,可以稱之爲‘新子學’學術文化工程。”(13)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江淮論壇》2013年第5期。在陳成吒的定義中,“新子學”與“子學”不再是單純的繼承發展的關係,它不再被“子學”附加有很强的規定性,它的源頭只是“諸子學現象”,該現象的内藴可由當代理論創造者自主“挖掘”,這顯示了它更多的創造性,故而可實現對諸子學的“全面超越”。依據這一思路,“新子學”便有了兩層屬性: 其一,它是一種哲學理論;其二,它是一項文化工程。前者是理念層面的思想探索,後者是現實層面的文化實踐,前者指導後者。
總的來看,陳成吒先生這種思路在“新子學”的諸多定義中也很有代表性,這一思路側重發掘子學的内藴,承其精神而不套其形式,由此而生的“新子學”是一種自成一體又呼應現實的思想體系,與上節中作爲學術新方法的“新子學”有所不同。王威威女士《“新子學”概念系統的建構》一文所定義的“新子學”也是致力於這種思想體系的構建,她指出:“‘新子學’並不是當代新儒家、當代新道家、現代新墨家、新法家各自獨立發展後的簡單相加,也不只是排除某家立場之後對各家思想的全面整理、研究和現代闡釋,而是在排除門户之見的同時,正視先秦子學由争鳴走向融合的思想潮流,從子學共通性的角度建構概念、問題和思想體系,並闡釋其現代意義。”(14)王威威《“新子學”概念系統的建構》,《諸子學刊》第九輯。這意味着,“新子學”亦可視爲由當代學者構建的全新理論,不是古代子學的簡單發展,也不是當代各思想派别的簡單整合,而是自成一套體系。楊國榮先生對“新子學”同樣表達了類似的期待,認爲“它意味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新的思想者和新的思想系統”,但楊先生更强調新思想者的重要性,指出“諸子之學是通過創造性思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通過外在或人爲建構起來的”,故而“新子學”應當是“新的歷史背景下對宇宙人生、社會歷史、現實問題的創造性思考的産物”(15)楊國榮《歷史視域中的諸子學》,《中華讀書周報》2013年5月8日第13版。。
所以,當我們立足思想史、文化史探討“新子學”定義問題時,會發現這一視角提供的視野十分寬廣,有多種關注點可供申發。上述介紹中,陳成吒、王威威等學者所關注的是從諸子學本身來發掘其精神從而創造新的思想體系,他們關注的是思想本身,而還有一些學者則關注生成這種思想的主體(即其創造者)或這種思想所面對的世界(即其發生環境)。
前一種關注“創造者”的思路以曾建華先生《“新子學”視閾下士人與子學的主體間性詮釋》一文爲代表,他指出“士是子學的發生主體”,“子學是建構於士人思想體系之上並有别於傳統元經學思想的新的學術理念”,“子學没有一個既定的中心,它誕生於士人對自我與他者關係的覺悟,並以此爲内核所形成的一個多元對等的思想體系”。這一論述,不再以傳統的諸子文獻和思想爲中心,而是凸顯了這些成果的創造者——士人,這讓我們重新發現了“子學”,也爲“新子學”的定義提供了新的靈感,曾文認爲“通過對子學與士的關係的釐定,我們不僅可以更好地理解新時代的子學與傳統諸子學的分野,而且能够更好地確定‘新子學’的研究範疇及其發展方向。就其範疇而言,‘新子學’不僅包括了先秦以來的諸子典籍之學,更涵括了自西周以來經史子集中所藴含的士人思想之呈現”。在這層意義上,該文認爲“新子學”便是“當代知識分子以當下所據有的全部學術資源實現對以子學爲主體的傳統學術的重新認知與整合,是傳統士人實現自我精神世界的重新建構的整個過程”。故而,曾文對“新子學”的概念給出了自己的概括:“總之,‘新子學’不是新之子學也非新子之學。就學術層面看,‘新子學’是以士人爲主體的子學的集大成,是立足當下、着眼未來,以期融通古今、貫注中西的子學文化工程;就思想層面看,‘新子學’是新時期士人(學科士人與公共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多元重構。”(16)曾建華《“新子學”視閾下士人與子學的主體間性詮釋》,《江淮論壇》2013年第6期。
後一種關注“發生環境”的思路則以聶學慧、劉兵(筆名劉思禾)《“諸子問題”與帝國邏輯的演繹》一文爲代表,該文提出了“諸子問題”這一概念,並進行闡發:“有諸子學,也有‘諸子問題’。一般來説,諸子學總是和子部文獻相關,按照儒、墨、道、法等各家的流别和經學對舉。而‘諸子問題’則是先秦諸子思想的内在問題意識,核心就是討論中國式的天下秩序如何建構(或者中華帝國的建構),這一問題既是面向現實,也充滿理論内涵。”可見,“諸子問題”便是諸子所處環境(春秋戰國時代)對學者所提出的核心問題,諸子學的産生便是當時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應答。顯然,該文的關注點在於諸子學與其發生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上,故而由此定義的“新子學”便有了獨特之處:“現代‘新子學’的開拓,就是繼承先秦諸子學的這種精神,以‘諸子問題’的關切爲中心點,面對現實,探索理論,在中國問題與中國語境中討論現代中國的可能性問題。我們認爲這是‘新子學’理念的内涵所在。”在這裏,文章是結合“新子學”所發生的環境——當代中國,來對其進行定義的。該文在最後又對“新子學”的概念進行了廓清:“先秦子學的根本就是面對時代課題而思考,今天的‘新子學’也要有這樣的期許。‘新子學’不是目録學意義的子部之學,而是一種藴含中國問題和表達方式的新中國學。而‘諸子問題’作爲中國政治與文化的元表達,是我們理解自身的初始境遇,也是面對現代性的思想起點。”(17)聶學慧、劉思禾《“諸子問題”與帝國邏輯的演繹》,《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在這一定義中,“現實”、“時代”、“中國”、“問題”諸詞一直是論述的核心,引領着我們將目光轉向孕育理論的外部世界,基於這種理解,“新子學”作爲“面對時代課題的思考”,它本身便是某種環境的産物,新的環境會形成新的理論,這便是該文所理解的“新子學”中“新”之所在。
3. 對各類説法的綜合分析
以上基本介紹了學界目前對“新子學”概念諸多界定中的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説法。這些定義有的立足於學術史的視角,有的立足於思想史、文化史的視角,在後一種視角中,又有不同的關注點,有的關注思想體系自身的構建,有的關注思想學説的創造者,有的關注思想學説發生的環境。其實,所謂立足學術史的視角,從本質上看也代表着一種關注點,即關注某種思想學説的研究者(接受者)。
可以説,由於關注點的不同,學界對“新子學”的定義呈現出四種截然不同的思路,這並非偶然,因爲這四類關注恰對應着一種學説的四個要素: 學説接受者、學説本身、學説創造者、産生學説的環境(18)此處參考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學活動四要素理論。。這四種要素相互影響,共同組成了學術活動的有機整體,其間具體關係可由下列圖表反映:
基於這種理論,可以將各類定義“新子學”的思路總結如下表:

表一 依照關注點對“新子學”相關定義的分類
對“新子學”的諸多定義的形成便是不同學者對這一存在的不同關注而進行不同的闡釋,故而每種定義都有其合理性,但又不能統概全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保持“新子學”概念的開放性,不斷豐富其形態,便是十分必要的(19)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探討先秦諸子學起源時所體現的思路,同樣與上文的理論相契合。陳柱先生指出後人分析諸子學起源有三種代表性説法: 王官説(《漢書·藝文志》)、時勢説(《淮南子·要略》)、道術説(《莊子·天下》)。可以發現,“王官説”關注思想學説的創造者,“時勢説”關注思想學説産生的環境,“道術説”關注思想學説本身。由此可見這種理論與子學的内在契合性,無論是研究傳統子學還是探索“新子學”,它都不失爲一個頗有參考價值的理論模型。。
(二) 對“新子學”範疇的討論
基於對“新子學”概念的不同認知,學界對“新子學”所涉範疇(即“新子學”所研究的範圍及内容)也有不同的界定。筆者《“新子學”構想》一文指出“具體内容上,則應嚴格區分諸子與方技”(20)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這個思路得到了界内學者的普遍認可。如高華平先生指出:“方勇先生的‘新子學’的構想,將天文算法、術數方技、藝術譜録等劃出‘新子學’的範圍,而‘側重思想’,這無疑正體現了現代學術發展的‘新’特點,是與現時代學術發展的規律相吻合的。”(21)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當然也有學者在這方面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問題,如譚家健先生論述道:“我希望進一步明確,‘新子學’包括釋家、道家和小説家嗎?我以爲,佛有佛藏,道有道藏,自成體系,似乎不必納入‘新子學’,但他們又是思想史資料,怎麽處理?小説家類乃古小説,不屬於思想史,方技中也有思想史資料,怎麽處理?”(22)譚家健《對〈“新子學”構想〉的建議》,《諸子學刊》第九輯。這些問題促使很多學者進一步思考,並給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劉韶軍先生立足於傳統的子部之學,認爲:“就目前看來,‘新子學’的内容構架最主要的部分應該是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獻的匯總、整理。因爲這三家的内容與中國歷史、文化、思想觀念、民族傳統的關係最深最密、影響最大,所以要列爲頭等重要的整理内容。”(23)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再如歐明俊先生,他主要針對“道”與“技”作了區分:“筆者以爲,兵學、醫學、道學(仙道學)是諸子學的‘題中之義’,天文、算法、術數等,大體上屬於‘術’,應重其‘道’的層面,具體的‘技術’可以不論,藝術、譜録可獨立。”(24)歐明俊《“新子學”概念的界定》,《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6月28日B01版。
以上討論的是“新子學”對傳統學術門類的涵括範圍,所側重的是“新子學”中的“學”,此外學界還討論了“新子學”中“子”所涵括的群體。《“新子學”構想》一文梳理子學發展時分别列舉了先秦兩漢時期一、二、三代子學元典和魏晉至明代的諸代子學(準子學)著作,可代表筆者對“子”所涵蓋範圍的理解。這種理解是比較通達的,學界也基本接受,而且還有不少學者希望再往前推進一步,如卿希泰先生結合明末清初的社會轉型,建議道:“這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迸發出來的啓蒙思想家的學説,是否也可以稱之爲近代的子學?對此,不知方教授意見如何?”(25)卿希泰、譚家健、王鍾陵、鄧國光、陳引馳等《“新子學”筆談》,《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11月2日02版。還有高華平先生更是明確指出:“還必須對這個‘子’再進一步明確界定,而不是如方勇先生那樣實際再回到經史子集之‘子’的老路上去。這就是,當下我們‘新子學’的‘子’,固然是以往中國思想史上的‘爲學’諸子,但更應該指當代具有獨立人格精神的知識個體(知識分子)。概而言之,‘新子學’即當代各個參與學術活動個體之‘學術’,每個參與當代學術活動的獨立個體都是平等的一‘子’,他們的學術就是‘新子學’。”(26)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高先生對“子”這一内涵的拓展有着很强的現實意義,上文列舉的“新子學”定義也有不少主張將當代學人納入“子”的範疇(可參考歐明俊等先生的文章),可見這種打通古今的思路的確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三) “新子學”與各學術門類的關係及自身定位
在“新子學”理論構建的第一階段,“新子學”與其他學術種類的關係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它和界定概念、範疇一樣,是學界探討“新子學”時必須要回答的基礎性問題。總覽學界以往的討論,與“子學”及“新子學”發生關係的主要有“經學”、“儒學”、“新經學”、“新儒學”、“西學”等學術或學説門類。在釐清這些關係的基礎上,一些學者還給出了“新子學”在國學體系及現代學科體系中的定位。以下將展開詳細介紹。
在《“新子學”構想》一文中,筆者對這些問題給出了初步的探索。關於西學,筆者認爲“‘新子學’將紮根傳統文化沃土,以獨立的姿態坦然面對西學”,之前的子學在西學的籠罩下發展艱難曲折,本文回顧了這段歷程: 民國時期,“學者多以西學爲普世規範和價值,按照西方思維、邏輯和知識體系來闡釋諸子。……結果是使子學漸漸失去理論自覺,淪爲西學理念或依其理念構建的思想史、哲學史的‘附庸’”;建國初期,“我國經濟體系、學術話語體系等,大都照搬蘇聯模式,對子學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改革開放後,學者大多“盲目崇拜、套用西方的價值觀念,照搬照抄西方的學術理論及評價體系。影響所及,諸子學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理論自覺,並導致了闡釋指向的扭曲。”(27)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所以筆者構想的“新子學”與西學間應有一個“不即不離”的關係:“我們需要擺脱二元對立思考的局限,以傳統子學的智慧與胸襟,坦然面對西方,正確處理好子學與西方文化學術的主次關係,才能真正構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新子學’體系。”(28)同上。
而“新子學”與傳統學術間的關係,更是筆者探討的重點。《“新子學”構想》一文認爲“‘新子學’將承載‘國學’真脈,促進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這一論斷是有充分依據的。古代的國學的確以經學爲核心,但經學逐漸僵化,尤其到近代更不能適應時代提出的要求,而“隨着近代學術的日益發展,子學實際上已逐漸成爲‘國學’的主導,這也彌補了經學作爲單獨力量存在時的種種不足”,所以,“如今,‘新子學’對其進行全面繼承與發展,亦將應勢成爲‘國學’的新主體。”(29)同上。
筆者這兩方面論斷得到了學界進一步的探討,以下將詳述之。
1. 關於“新子學”的定位問題
關於“新子學”在國學中的定位,學界的確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韓星先生的觀點是“在今天中國思想學術的多元發展中,新經學與‘新子學’之間也一直在互動,但新經學(儒學)無疑仍然起着主導作用”。進而韓先生給出了自己對“新國學”的設想:“道統的重建應該是‘新國學’的核心和目前的主攻方向,而道統的重建與學統又不能分開,是在學術基礎上的重建,具體説就是在經學基礎上重建儒家道統。”(31)韓星《新國學的内在結構探析——以新經學、“新子學”爲主》,《諸子學刊》第九輯。可以説,韓先生的觀點代表了傳統的聲音,是我們建構“新子學”理論時必須認真對待、辨析的一種論點。
針對這類傳統看法,郝雨教授則從現代文化學者的角度來評價“子學”與“新子學”的地位。郝先生認爲:“‘新子學’和新儒學的根本區别即在於: 它不認爲只有儒家、只有儒學才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構成,而是認爲,諸子百家才是中華文化的真正源頭。”(32)郝雨《“新子學”與“新儒學”之辨》,《諸子學刊》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這大致反映了“新子學”對自身定位的基本主張,它首先保持自身的多元,進而以此恢復中華文化的多元。
李小成先生則專門探討了“新子學”和經學的關係,提出“‘新子學’作爲國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其充滿活力的創造精神,應該是對中國傳統經學的超越”,這種超越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新子學’具有思想原創性”;“‘新子學’具有包容開放性”;“‘新子學’具有學術争鳴性”;“‘新子學’具有鮮明時代性”(33)李小成《“新子學”對中國傳統經學的超越》,《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該文是對傳統經、子關係問題的更專門的探討,在兩者的對比中我們可以對它們各自的“學術傳統”和“當代價值”産生更明晰的認知,對“新子學”定位問題的探討是有幫助的。
王昀、謝清果兩先生則從傳統文化傳播的角度來定位“新子學”:“‘新子學’在傳統文化傳播中的地位,應當主要體現在其構成了傳統思想史之主體,其提倡國學研究從‘儒家道統,子學系統’之轉型,既非否定儒學或經學價值,更非將子學地位絶對化。簡而言之,不應帶有價值高低評判來過度闡釋傳統文化資源。”(34)王昀、謝清果《還原、重構與超越——“新子學”視域下傳統文化傳播策略》,《諸子學刊》第九輯。
高華平先生則對筆者的觀點作了進一步修正,結合對“‘國學’性質”的探討給出了他的結論:“‘國學’原本是貴族子弟學校,它自然要傳播、灌輸統治階級的思想,教授那些凝結了統治階級正統思想的‘經書’而不可能是那些由民間士人在‘道術廢缺’、‘好惡殊方’情況下形成的‘諸子學’及其著作,很顯然,如果‘新子學’要成爲當今‘國學’的新主體的話,首先就必須使我們的‘國學’成爲‘新國學’。”(35)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
陸永品先生也對筆者的觀點進行了兩點補充:“其一,儒、道、墨、法是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四大‘顯學’,是中華文化的四大支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因此,《“新子學”構想》也應當强調法家的重要地位。其二,該文認爲在思想内容方面,‘道家於紛繁世界之外,清虚自守、澡雪精神’。然而,如此概括,似乎還稍嫌不足。應在‘清虚自守’、‘澡雪精神’之後加上‘勸善立德’、‘與時俱化’八個字。”(36)陸永品《〈“新子學”構想〉體現時代精神》,《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10月26日A08版。陸先生對“子學”内部各派的定位頗爲精到,能給我們定位“新子學”帶來很多啓發。
2. “新子學”與儒學、經學、西學的關係
楊少涵先生則由儒家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儒家是‘經’還是‘子’?”楊先生由此區分了“經儒”、“子儒”兩個群體,通過對比他指出“‘離經還子’或‘夷經爲子’的地位轉换並不會使儒學失去什麽,反而是從思想深層還儒學以本真面目”,由此他申明了“新子學”的學術態度,希望“儒學研究者都應當秉持各家思想學説平等交流、公開討論的態度,不要過多地期望儒學具有或應當具有對其他學説之籠罩性、壟斷性的‘經’的地位”。楊先生該文雖然關注的是儒學轉型,但他提出“平等交流”、“公開討論”的學術精神卻和“新子學”相一致,堅持這一精神,“新子學”和儒學間便會多些通融、少些壁壘(37)楊少涵《走出經學時代——儒家哲學現代化的範式轉换》,《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Qingdao harbor, Dong Jiakou port, bulk grain project. on the basis of this situation, to do this research on conveyor head or tail frame′s forces as follow shown in Figure 1.
陳成吒先生(筆名玄華)則立足客觀的學術史對“新子學”和儒學及經學間的關係進行了全新的探討,他指出:“歷史上,經學詮釋文本生生不息的動力並非源於其經學自身,而是來自子學。……子學對經學文本的解放與發展,表現在經學與儒學的關係上,不是經學吸納了儒學,而是儒學用子學精神與方法消解了經學。”(38)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江淮論壇》2013年第5期。這種認知雖具顛覆性,但又基於真實的學術史料,可以説他與持傳統觀念的學者面對的都是同一個學術現象,但該文通過理論思辨得出了新的觀點,在這一問題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歐明俊先生則例舉了“新史學”、“新文學”、“新經學”、“新儒學”作爲“新子學”的參考,並逐一進行對比,對我們定位“新子學”理論也有很大啓發意義。而且他還指出:“我們千萬要注意,不能以另一種專制獨尊代替一種專制獨尊,‘新子學’可争取在國學中的‘新主體’地位,也理應成爲國學‘新主體’,要突出‘新子學’的價值和地位;但同時强調,‘新子學’不應取代經學的尊崇地位。”(39)歐明俊《“新子學”概念的界定》,《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6月28日B01版。歐先生在定位“新子學”時指出了潛在的另一種極端,這對我們是有警示意義的。
孫以昭先生也對這幾個問題分别進行了討論。關於“新子學”與儒學,他認爲“‘新子學’與儒學的關係非常密切,而其間又有一個演變的歷史過程”,他列舉“論述及論及先秦學術流派的著作”14種,進而總結道:“可見,不但儒學原在‘子學’之内,常被排在前列,而且天文、算法、數術亦在其内,‘子學’内容極爲龐雜,而‘新子學’當然包孕更爲豐廣了。”之後他又提到“至於‘新子學’與經學的關係,則既經歷了由分到合,‘升子爲經’,再由合到分,‘離經還子’的過程,又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關係”。孫先生此處主要結合《論》《孟》《易》《書》《禮記》諸經進行論證。通過釐清上述關係,孫先生評價了“新子學”在傳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新子學’將融子學、儒學、經學、史學與文學爲一體,形成一種新的學術研究體系,從而將我國傳統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另一方面,“‘新子學’在傳播我國傳統文化方面,也負有不可替代的使命”(40)孫以昭《“新子學”與儒學、經學的關係及其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諸子學刊》第九輯。。
另外,孫先生還認爲“新子學”區别於“舊子學”的一點在於它對西學的吸納,他指出“新子學”需要“加强理論探索與參照,吸納與融入西學”,“就西學而言,除了吸納西方重要文論外,主要則是西方的科技知識和思維方式”。可見,相對於筆者的觀點,孫先生更强調構建“新子學”時對西學的融合,與之相近的還有高華平先生和譚家健先生的看法,高先生認爲:“我們構建的‘新子學’不應該成爲與‘西學’相對應的關係,更不是相對立的關係”,“在作爲整體的‘新子學’中,‘西學’應該已經融匯其中,並已成爲它的一部分或它的血肉。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子學’之‘新’,就在於它乃是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學術,至少理想形態的‘新子學’應該如此。”(41)孫以昭《“新子學”與儒學、經學的關係及其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諸子學刊》第九輯。譚先生在探討“‘新子學’如何面對西學”時則認爲:“推進思想史、文學史研究中的中西結合,多元互補,應該首先解決價值觀和方法論問題。”(42)譚家健《對〈“新子學”構想〉的建議》,《諸子學刊》第九輯。這些論點雖然不同於筆者提出的“以獨立姿態坦然面對西學”的想法,但它們更爲開放包容,亦不失爲一個有益的探索方向。
3. 對相關問題的再思考
基於學界對“新子學”在學科中的關係和定位問題如此火熱的探討,筆者於2013年發表了《“新子學”申論》一文,專門就這幾個問題再度進行闡發。文章開頭便指出:“‘新子學’的提出就在於反思四部分類和學科分類,明確國學概念的内涵,從而爲中國學術的自我認知提供一種可能。”這是强調對“新子學”的定位不能再參照舊有的學術體系,我們所追求的本來就是對中國學術的一種新的認知。由此,筆者針對經、子關係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新子學’以現代學術的標準重新界定經、子關係。……我認爲,四部分類法中經、子先後的劃分使用的是價值標準,推崇的是所謂‘常道’,而不是依據學術標準講‘學問’。……經學傳統在中國歷史上並非不重要,但在純粹的學術與思想的標準下,歷代子學才是主流,而且經學恰恰是在子學的滋養下發展的,是子學滲入經學體系之後再政治化的産物。”(43)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這段論述,可以看作是對學界之前相關質疑與異議的回應,通過這樣思辨地審視中國學術的歷史,能讓我們對“新子學”擔當國學主體有更多的信心。
“新子學”與西學的關係及其在現代學術格局中的定位問題也在該文中有探索。筆者指出:“‘新子學’是對現代學術分科式研究的修正。在現代學科框架下,子學主要是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學術界已經做了大量精深的研究,這一點有目共睹。……‘新子學’和現代學科框架根本的差别就在於: 究竟是依照某一外加的模型截取一塊研究,還是順應本來的内部肌理複合地研究?實際上古代學者就是按照内部肌理複合研究的,我們的問題在於先戴上了一副學科的眼鏡,自然無法直接體會那種通貫的思維方式。”(44)同上。可見,“新子學”對於現代學科分類體系是超越性的,它是現代學科分類體系的“修正者”而非“零部件”,這種具有超越性的定位意識是我們在構建“新子學”理論時一直要保持的。
“新子學”與“新儒學”的關係在之前探討中一直是熱點,筆者在《“新子學”申論》一文中亦有專門論述。筆者主要討論了“新儒學”與“新子學”的幾處分歧。首先,“中國學術傳統的主流是儒學一統還是複合多元?”筆者指出:“依照我們的觀點,儒學根本上還是子學的一個部分,或者説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個部分,與其他各家之學齊頭並進,又密不可分。……中國學術史上一直存在着儒家與道家、法家等學派的互動(當然也包括後來儒家與佛教的互動),這種互動有學術的,也有社會的和政治文化的。”其次,“現代中國的文明秩序是由儒學主導,還是百家共鳴”?筆者給出的答案自然傾向後者:“儒學是否還有能力獨自重建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我們認爲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新子學’而言,我們還是期待開掘出更多的學術資源,爲百家共鳴創造條件。在這裏,儒學也是‘新子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會一同參與到百家共鳴中來。”最後是“‘新子學’與新儒學在理解框架、學術資源和追求目標上的差異”,筆者强調:“‘新子學’倡導一種新型的理解框架,既非傳統四部式,也有别於現代的分科,這樣的觀念不同於新儒家那種儒家優先,甚至是儒家獨尊的理解方式,而願意以更謙恭的心態面對中國的學術傳統,發掘其中被忽略、被遮蔽的東西。”(45)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該文將兩種理念進行對比,並不是要貶低“新儒學”來推揚“新子學”,而是希望在對比中發現“新子學”的獨特價值,在此基礎上對“新子學”的理論構建提供更多的方向。其實這也可以算作是我們辨析“新子學”定位的終極動機: 我們這些努力並不是要給“新子學”争名分、抬地位,我們是希望通過其他學術門類的參考,來凸顯“新子學”的特質,由此生發出“新子學”獨特的理論内涵。這又可以回到開頭的比喻,樹木紮根最終是爲了主幹的生長,尤其是紮根的位置更影響着樹木今後的發育,懸崖上長不出挺拔的大樹,幽谷中見不到參天的巨木,“新子學”只有有了正確的定位,釐清與其他學術的關係,自己才能獲得獨立的生長空間,保證自己“主幹”和“枝條”的發育。
(四) 對“新子學”意義的探討
一套學説是否有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是交由學術界來裁定的,通過學術界的裁定,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理論的意義是什麽、在何處、有多大。這些“由學術界裁定出”的意義,也在某一層面上反映出了它在學術界的接受程度,而這些接受又會吸引更多學者的討論,這是其體系進一步建構的基礎,所以其意義的大小也關係着其生命力的强弱,本文之前用一棵樹的葉子來比喻一個理論的意義,其用意亦在此,因爲對於樹來説葉子是它生命力的象徵。
很有幸,“新子學”在還是小樹苗時,它的枝頭上已經開滿新葉了。學界對“新子學”的概念、範疇和定位等問題的認知雖然有衆多分歧,但是,對於“新子學”這一理念的基本方向卻是有普遍的認可,並從各方面指出了它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
郝雨先生指出了“新子學”在現代文化中的意義:“第一,所謂‘新子學’,就是要把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研究由原來的以儒學爲中國文化單一核心,轉變回歸到諸子百家……。第二,這樣一種文化研究的思路,同時也給‘五四’新文化運動找到了一個合理的邏輯前提和解 釋……。 第三,在全球化時代,通訊科技與新媒體高速發展,世界已經成爲‘地球村’,文化也只能是多元的。……‘新子學’給我們提供了現代文化環境中我們民族文化繁榮振興的一個重要參照,我們應該建立起如同當年百家争鳴的一個新時代……。第四,‘新子學’的提出,並不只是仍然把子學作爲一個學科來進行專業研究……。我們要從子學中尋找到真正使我們民族具有强大發展潛力的根本,最需要找到的就是藴含在諸子百家之中的中國智慧。”(46)郝雨《“新子學”對現代文化的意義》,《文匯報》2012年12月17日00C版。
卿希泰先生則結合當前問題指出了“新子學”的時代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我國社會經濟的飛躍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國際交往也日益頻繁,所面臨的各個方面的諸多社會矛盾也日益突出,因而迫切需要大批的思想家來發揮其智慧,系統探討如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理論和策略。這就充分地表明了: 時代需要‘新子學’!因此,方教授所提出的‘新子學’構想,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我很支持。”(47)卿希泰、譚家健、王鍾陵、鄧國光、陳引馳等《“新子學”筆談》,《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11月2日02版。
張洪興先生同樣是由時代的需要這一角度切入,認爲子學的基本精神是“實踐理性”,故而“尋找子學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契合點、發揮子學在修養人心、和諧社會、實現國家民族富强進程中的作用,正是‘新子學’的主旨。”(48)張洪興《“新子學”與中國文化芻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6期。這一論述説明了“新子學”的旨趣、目標所在,它們的實現需要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鄧國光先生則從宏觀的學術史角度來説明“新子學”的意義:“在集部,有新文學;在經部,有新經學;在史部,有新史學。但作爲時代理性思維象徵的‘子學’,獨落後於斯。可幸的是,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學’,如此整個四部學術能共同在相同方向上各顯輝煌。‘新子學’過濾蕪雜的僞飾,醇化子學的本質,重建中國學術話語,啓動思想,發憤人心,重振靈魂,積極解決新時代的深層次困擾,而期向未來生活世界的整體幸福。就世界文明格局的重新調整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49)卿希泰、譚家健、王鍾陵、鄧國光、陳引馳等《“新子學”筆談》,《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11月2日02版。
陳引馳先生則追求發掘“新子學”更深層次的思想價值:“相信‘新子學’不僅僅是一項學術探討,應當還有其更宏大的設想或方向。……多元的時代同時也是危機的時代,子學也是危機時代的産物。……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子學’是要提供一種思想資源來應對這樣的危機時代,因而是十分必要的。”(50)同上。
韓星先生則參考近現代的新道家、新法家等學派來明確“新子學”對於“子學”總結性的意義,他指出:“20世紀以來,相比較新文學、新經學、新史學,‘新子學’没有形成整體力量,只有作爲一家一派的分散子學,如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等,方勇教授現在提出‘新子學’的構想,首先把子學作爲整體凸顯了出來。在中國經過了20世紀諸子百家争鳴時代之後,方勇教授現在獨具慧眼,對近代以來的諸子復興思潮做出了整體性的概括總結,提出了‘新子學’構想,非常及時,非常必要。”(51)韓星《新國學的内在結構探析——以新經學、“新子學”爲主》,《諸子學刊》第九輯。
王宏圖先生則指出了“新子學”對現代文化的啓示意義:“我覺得,‘新子學’給我們的一大啓示是,除了將傳統資源發揚光大外,還應開展中國文化與各國文化全方位的對話,藉此啓動中國傳統内在藴含的活力,同時也大規模地汲取域外思想資源,以豐富、發展自己。”(52)郝雨、楊劍龍、葛紅兵、劉緒源、姜琍敏、王宏圖、徐國源、李有亮、何美忠、范松楠《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傳承》,《黄河文學》2013年第2 /3期(Z1)。
湯漳平先生從中華文明重構的高度來評價“新子學”,指出它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因而更適應時代要求,對中華文明的重構有着不可或缺的意義(53)湯漳平《“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江淮論壇》2014年第2期。。
陳鼓應先生則回顧中國歷史,提煉出了“子學興替關乎中國思想變革”的命題,進而指出:“‘新子學’主張特别具有思想創新與學術變革意義。”(54)陳鼓應《子學興替關乎中國思想變革——〈“新子學”論集〉序》,《光明日報》2013年12月16日第15版。
陳先生、湯先生對“新子學”抱有很高的期待,他們提到“變革”、“重構”之類的説法,一方面認可了“新子學”的意義,另一方面也點出了“新子學”的責任。學界認可“新子學”的意義,不是讓我們自滿,而是要激勵我們更努力地發揮“新子學”的價值。這時,一些方法論層面上的問題自然也成爲討論的重點,下文將展開詳細介紹。
(五) 對“新子學”方法論的探討
在探討方法論層面的問題時,學界對如何進行“新子學”系統構建展開了設想。
在《“新子學”構想》中,筆者設想了“新子學”系統建構的步驟:
我們結合歷史經驗與當下新理念,加强諸子學資料的收集整理,將散落在序跋、目録、筆記、史籍、文集等不同地方的資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時,深入開展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對原有諸子校勘、注釋、輯佚、輯評等的進一步梳理;最終,則以這些豐富的歷史材料爲基礎,綴合成完整的諸子學演進鏈條,清理出清晰的諸子學發展脈絡。依據子學發展的完整性,再進一步驗證晚清民國以來將《論語》《孟子》等著作“離經還子”的觀點,復先秦百家争鳴、諸子平等之本來面貌,並重新連接秦漢以後子學的新發展。(55)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
當然,以上還只是筆者設想的一個初步的藍圖,今後理論建構的方向和方法還需要學界的進一步探索。而事實也表明,學界在這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節將對此展開詳細介紹。
有許多學者着眼於實踐層面“新子學”該如何展開,爲此設計了詳細的方案。
張永祥先生提出了三個步驟實現從子學向“新子學”的轉型: 第一,集而成之;第二,化而裁之;第三,推而行之。並指出“化而裁之”是問題關鍵所在,爲此需要“有大子學的歷史眼光”,“有大學科的現代意識”,“大文化的宏觀視野”(56)張永祥《反者道之動——從子學走向“新子學”》,《諸子學刊》第九輯。。張先生的建議都吻合了當前學術研究的迫切需要,有助於我們將“新子學”構建成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學術理論。
劉韶軍先生則專門設定了“新子學”的工作構架:“簡言之,‘新子學’的工作構架,就是由文本基礎、學科協同、團隊組建、人員分工、成果發佈、品質判定等模块組成,使之成爲一個完善的動態系統,具有良性的生命活力,並能吸引凝聚更多的人才投身其中,使‘新子學’的學術研究事業長盛不衰。”(57)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劉先生的構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對於“新子學”理念的實踐有着很大的參考價值。
高衛華等學者在分析2012—2013年期間“新子學”理論構建情況後,給出了他們的建議:“(一) 認識‘新子學’意義、釐清‘新子學’概念;(二) 上行下達、傳道有方,實現‘新子學’多方位傳播。”關於第二點,他們又有如下設想:“首先,整理典籍、著書立説,豐滿‘新子學’的内容……。其次,塑造大家、吸引大衆,增加‘新子學’的傳道者……。再次,善用媒體、設置議題,提升‘新子學’的關注度。”(58)高衛華、楊蘭、董浩燁《我國“新子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諸子學刊》第九輯。與此類似還有蔣門馬先生的建議,他提出了“創建‘新子學’網站”、“探究‘新子學’中的經世之道”、“把‘新子學’元典翻譯成外文”等想法,也是頗有新意(59)蔣門馬《關於弘揚“新子學”的建議》,《諸子學刊》第九輯。。高先生、蔣先生等的幾點建議雖然着眼於“新子學”傳播的問題,但一個理論的傳播過程也爲它内涵的構建提供了實踐平臺,所以這些建議對於“新子學”理論構建有着切實的指導意義。
上述設想都以鮮明的實踐色彩見長,另外則還有許多學者的探索着重於思考“新子學”理論本身應有的特質,爲此也提出了許多設想。
歐明俊先生認爲“新子學”除了落足於“學術立場”外,還要有“當下關懷”,更要有“人文關懷”(60)歐明俊《“新子學”界説之我見》,《諸子學刊》第九輯。,歐先生提出的這三個層次的要求可以分别保證我們“新子學”能够穩健、迅速、長遠地發展,值得我們重視。
楊國榮先生則區分“照着講”與“接着講”兩種方法,認爲“‘接着講’更接近諸子學所體現思想突破這一内在品格”,但他同時也强調“新子學”的探索“在實質的層面應當注重思想發展過程中‘照着講’和‘接着講’的統一”(61)楊國榮《歷史視域中的諸子學》,《中華讀書周報》2013年5月8日第13版。。這同樣能給我們帶來很多啓發。
許抗生先生則指出了“新子學”在構建時其外在形態的多種可能性:“至於當代‘新子學’的形式,我認爲可以以‘子’學形式,也可以以‘家’學形式。如以‘子’學,可有新老學、新莊學、新孔學、新孟學、新荀學、新韓非子學等;如以‘家’學,則可有新儒學、新道學、新法學、新名學、新陰陽五行學等。總之,‘新子學’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多種多樣。”(62)許抗生《談談關於建立當代“新子學”的幾點想法》,《諸子學刊》第九輯。學界一直以來對“新子學”探討的重點都放在其内在意藴上,許先生關注到了其形式的問題,這是難能可貴的建議。
王威威女士則認爲:“‘新子學’的建構如果能够從提煉諸子共同的概念入手,也就能够更直接地找到子學中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繼而由點到線到面,探尋圍繞這些核心概念所産生的共同問題,分析對共同問題的不同的解決方式,進而對這些思想進行現代化的闡釋。”(63)王威威《“新子學”概念系統的建構》,《諸子學刊》第九輯。由此她提煉出了“天、道、理、仁、義、禮、法、性、心、虚與静、無爲、形與名等”一系列概念,通過探索它們來尋找“新子學”理論建構的方向。其實王女士這種做法不僅僅是一次探索,也是對“新子學”理論内涵的一次實質性構建,其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新子學”的理論主幹。
賴賢宗先生則結合勞思光先生的“基源問題研究法”與傅偉勳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來對“新子學”進行方法論層面的探討。文中指出:“以子學的多元開創的精神,而以道文化來統整,來回應當代的問題,這乃是‘新子學’的思想淵源與根本原理。”(64)賴賢宗《“新子學”方法論之反思——基源問題研究法與創造的詮釋學的知識建構過程》,《諸子學刊》第九輯。賴先生這一提法溝通了“傳統”和“當代”、兼顧了“多元”和“統整”,有助於我們全面地構建“新子學”理論體系,尤其是文中提出“以道文化來統整”,更是爲如何將“新子學”建構成整體、獨特的理論提供了思路。
可見,上文中王、賴等先生的探討不僅給了我們方法論層面上的啓示,也觸及了“新子學”主幹理論構建的問題,而這類問題將成爲“新子學”第二個發展階段中學界關注的重點。
四、 第二階段: 充實主幹、派生枝條
通過上文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階段學界主要關注的是“新子學”的一些基礎性問題,比如其概念、範疇、關係、定位等,這些探討回答了“新子學”是什麽(其中概念、範疇着眼於它内部構成,而關係、定位立足於其外部參考),但没有回答“新子學”有什麽。“有什麽”屬於一個理論的實質性問題,一個理論必須要有其核心思想和具體主張方能在學術界立足,否則只是空有其表。許多學者在反思學界第一階段的探討時,都提出了“新子學”核心理論缺失的問題。而這種核心理論的缺失又影響了“新子學”與其他領域的互動,使得“新子學”一直在單一的老路上發展。這種境遇就好比一棵樹木主幹未長成故而枝條也欠發育,因此“充實主幹,派生枝條”便成了第二階段的任務,筆者也將此設爲本節標題。
此處設定的第二階段在時間上的跨度大概是兩年,它的前奏是2013年的一些相關論文(即觸及“新子學”核心思想建構的文章),正式肇始於2014年“諸子學轉型高端研討會”上的會議主題發言和《“新子學”論集》序言及相關書評,其高峰則以2015年的“第二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的衆多會議論文爲標誌(65)這些會議論文多刊發在2016年的刊物上,本節所列2016年發表的文章多屬此類。。此外,還有很多相關的學術活動也爲探討“新子學”提供了契機,比如2014年在上海大學召開的“‘新子學’與現代文化: 融入與對接——新媒體時代‘子學精神’傳承與傳播學術研討會”吸引了很多傳播學界的學者探討“新子學”,再比如在韓國召開的“21世紀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方亦將“新子學”作爲專門討論的一大議題。經過2014—2015年舉辦的這些學術活動,學界又新增“新子學”相關文章約72篇(其中學術論文59篇,整理發表的會議發言1篇,書評2篇,會議綜述及報導11篇),它們基本被收録進《“新子學”論集(二輯)》一書中。而這些文章相比第一階段又有一些新特點,即開始關注到了“新子學”核心理論構建和相關領域延伸兩大問題,基於這種發展,筆者將這一時期劃定爲第二階段。以下將對其展開詳細介紹。
(一) 對“新子學”核心思想的探討
1. “子學精神”與“新子學”核心思想的構建
文章開頭提到過“(一個理論)内含的核心思想及由此生發的一系列理念主張和以之構成的體系,則對應着一棵樹木中部的主幹”。依照植物學的分類,没有主幹的樹不能稱之爲樹而應歸爲灌木,主幹在中間連接着根系和枝葉,是一棵樹之所以爲樹的標誌。同樣,核心思想對於一個理論來説也有象徵意義,比如古代某學派或某學説皆有其獨特的“家數”或“宗旨”,這是其開宗立派的前提。
針對“新子學”核心思想不明確的情況,筆者在2013年的《再論“新子學”》一文中便嘗試對此進行探討。筆者首先回顧了之前“新子學”討論的情況,認爲之前“關於‘新子學’概念的討論,主要集中於諸如‘新子學’是‘新之子學’還是‘新子之學’,‘新子學’的研究範圍應截止到清末、民國之前還是涵蓋當代等問題上”(66)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15版。。這便是上文所説學理概念層面的探討,對於一種理論來説,它們是基礎性的,卻不是核心性的,我們還要繼續超越這一層面,追求構建“新子學”的核心精神,凸顯它的文化、政治等關懷。所以該文便提出了“子學現象”和“子學精神”,並對其進行闡述:
就深層意義而言,“新子學”是對“子學現象”的正視,更是對“子學精神”的提煉。所謂“子學現象”,就是指從晚周“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運動”時期,其間每有出現的多元性、整體性的學術文化發展現象。這種現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現爲學者崇尚人格獨立、精神自由,學派之間平等對話、相互争鳴。各家論説雖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現實以深究學理,不尚一統而貴多元共生,是謂“子學精神”。(67)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15版。
此處提出“子學精神”,有其特殊意義。之前一些學者曾指出,“新子學”想發展成一種完善的理論,還需要克服一些困難,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首先,諸子内部各家異説,缺乏理論的統一,以此爲基礎的“新子學”該如何成爲一個渾融一體的理論;其次,“新子學”與其他一些思想流派分享共同的理論問題、存在相近的思想理念,該如何增强其標識性與獨特性;再次,“新子學”没有明確的主張,那麽,它又如何作爲一種理論指導實踐。其實,上述困難歸根結底可以總結爲“新子學”核心理論缺席的問題,而此處我們提煉出來的“子學精神”則恰可以充當“新子學”核心思想來分别應對上述困難: 第一,它體現了諸子各學派的總體特點,具有統攝性;第二,它由“子學現象”提煉而來,能反映出該理論的獨特性;第三,這種精神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有歷史事實爲參考,並加以頗具高度的概括,具備指導實踐的價值。
一個理論核心思想的形成,是個“博取而約收”的過程,提煉“子學精神”便是博取“子學現象”、約收其中的深層意藴,從而創生出對“新子學”能有標識性作用的思想觀念。從這個方面看,提煉“新子學”精神不失爲構建“新子學”核心理論的可行路徑。
基於這一思路,在“新子學”理論構建的第二階段中出現了很多針對“子學精神”進行的探討。
李桂生先生認爲,“‘新子學’的建構有賴於對子學精神的承繼”,“子學精神”主要表現在“獨立人格”、“思想原創”、“批判思維”、“入道見志”、“保持張力”、“和而不同”、“實踐理性”(68)李桂生《子學精神與“新子學”建構芻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李先生對各類精神逐一進行闡釋,相比筆者的論述更加詳細,其中“批判思維”、“入道見志”兩類精神更是對筆者觀點的補充,這很值得我們重視。唐旭東先生的看法亦與此相近,認爲諸子“其精神品格是傲然不群的獨立人格,深切的憂國憫世情懷,强烈的責任感和義無反顧的踐行精神”。故而“當代‘新子學’要繼承傳統子學的精神品格,以學術爲根本,以經國濟世爲目的,在强國復興的大業中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69)唐旭東《傳統子學精神與“新子學”的責任和使命》,《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唐先生是結合諸子的人格品質來談“子學精神”,又爲我們的探討增添了一個視角。與此相近的還有逄增玉先生的觀點,他是結合當代知識分子的品格塑造來進行論述,他指出“建立先秦時代的‘子學’精神,就是要建立獨特的、有自由和擔當精神的文化和心理結構,以及比較完整的人格結構”(70)逄增玉《重建當代知識分子的“子學”精神》,《名作欣賞》2015年第1期。。這一期許呼應了現實,有着獨特意義。
還有景國勁先生則將“子學精神”與“新子學”的“價值訴求”結合起來討論:“‘新子學’是一種具有‘策略性’的學術文化理念,顯然有着當代性的文化價值訴求。‘新子學’的文化價值訴求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有機整體觀與創生精神、參與精神和對話精神等。”(71)景國勁《“新子學”文化源流及其價值訴求》,《諸子學刊》第十三輯。景先生視角比較獨特,故而他總結出的“子學精神”也頗有新意,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歐明俊先生則對“子學精神”進行了更大篇幅的擴充,在《論“子學思維”與“子學精神”》一文的摘要中,他指出:“子學精神不同於求真求實的史學精神,最重要的是理論創造,是‘大丈夫’精神、執着精神、犧牲奉獻精神、尚氣節精神、仁愛精神、謙虚好學精神、科學精神、自由精神、獨創精神、争鳴精神、叛逆精神、懷疑精神、批判精神、擔當精神、會通精神、開放精神、和諧精神、自律精神、寬容精神等。”這可以説是目前總結“子學精神”最全面的文章。更可貴的是,歐先生還進一步探討,總結了一系列的“子學思維”,認爲:“相對於經學思維,子學思維是創新思維、理性思維、科學思維,如辯證思維、全息思維、中和思維、抽象邏輯思維、形象思維、直覺思維、相對思維、變通思維、否定思維等。”(72)歐明俊《論“子學思維”與“子學精神”》,《諸子學刊》第十三輯。歐先生對各類“精神”和“思維”都進行了細緻的闡述,本文不一一例舉。
總體來看,上述幾位學者都致力於在“子學”中發掘更豐富的精神,從而爲“新子學”填充更多的理論内質,他們這些努力讓“新子學”這棵大樹的主幹逐漸粗壯,對它之後的發展有長遠的幫助。
與上文分門别類地列舉不同,郭丹先生則追求直探子學與“新子學”的精神内核,他指出:“‘子學’即諸子之學,其最早的含義,是指先秦諸子之學。《文心雕龍·諸子》説:‘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入道見志’,不論是入哪家的‘道’,抒發的是什麽‘志’,諸子之學是闡發自己思想學説之學,是‘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説以廣播於天下者’,是針對當時的社會進行思考而提出的治理社會、有關人性的各種主張,是堅持‘立原創之見,倡導精神上的獨立與自由’。這就是諸子之學的精神内核。”在此基礎上,郭先生又參考“新儒學”與古代儒學的連續性,給出了“新子學”的精神内核:“同樣的道理,‘新子學’與傳統子學在精神上應有延續性和繼承性,而不是割斷的。愚意以爲,就宏觀的層面來説,統領‘新子學’的精神内核,從先秦時期肇始的子學精神是‘新子學’應該延續和弘揚的。”(73)郭丹《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淺見》,《諸子學刊》第十三輯。郭先生對“子學精神”的描述是從整體的角度着手,呈現給我們一個渾融的精神圖景,雖然没有詳細展開論述,但對“子學精神”的把握很準確到位。
還有很多學者的文章在思路上與郭先生類似,都是從某一特定“精神”的角度展開對“新子學”核心理論的論述。
林其錟先生借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原雜家》中的論述來説明“雜家精神”:“凡企圖把不同或相反的學説,折衷調和,而使之統一的,都是雜家的態度,都是雜家的精神。”雜家是子學中的一派,而且以匯通百家爲宗旨,這種“雜家精神”不僅是“子學精神”的組成部分,而且在其中有着特殊的意義。故而林先生總結時指出在當今“需要發揚雜家精神,即取鎔諸家之長,捨棄諸家之短(這裏的諸家自然也包括外來文化在内),這才能擔當和完成‘新子學’建構的歷史使命”(74)林其錟《“新子學”學科定位與雜家精神》,《中州學刊》2015年第12期。。張雙棣先生同樣認可雜家對“新子學”建構的意義:“我們現在討論‘新子學’,應該充分借鑒雜家吸納百家的做法,本着積極的、公開的、寬容的態度,對待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學説,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舍之。”(75)張雙棣《“新子學”與雜家》,《諸子學刊》第十三輯。雜家是諸子百家進入總結時期時産生的一種學問,它關注諸子的共通性,與我們要建構的“新子學”核心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故而兩位先生結合雜家進行的探討是極有意義的。
而張洪興先生在探討“子學精神”時則堅持將關注點放到儒、道兩家上面,他指出:“我們當下弘揚‘新子學’,一方面要整理文獻,梳理文本,但更爲重要的是培育以儒家、道家爲骨幹的子學精神,固本培元,革故鼎新,發揮子學在當下文化建設中道德修養、温養人心、社會和諧等方面作用。”張先生在文中從“學術背景與淵源”、“學術特徵與價值”、“政治與宗教因素”三個方面論證了儒、道兩家是“中國文化的根”,故而認爲“我們現在强調固本培元,首先需要培育中國文化精神,培育儒家、道家精神”(76)張洪興《固本培元 革故鼎新——儒道學説與“新子學”的發展》,《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儒、道兩家在子學中有獨特價值,在探討“子學精神”時對這兩家重點關注是合理的,不過在地位上我們還是要將它們和其他各家一視同仁地對待,千萬不可出現“獨尊”的局面。
還有曹玟焕先生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狂者精神”,將其視爲“新子學”理論構建的必要元素:“中國文化與哲學範疇中有許多和西方不同的部分。‘狂者精神’是其中之一。本文關注的是朱熹規定的‘志高而行不掩’中‘志高’所具有的優點。在全球化時代,要求多元性、開放性思維的今天,我們要從儒家的經學中心主義、理性中心主義中擺脱出來。現在是一個需要通過‘志高’和獨特思維去發展人類文明、具有創意性的人才的時代。因此有必要重新設定‘新子學’中追求‘志高’的狂者的地位。我認爲,對於狂者的適應時代要求的肯定性重釋是‘新子學’應當去追求的重要課題。”(77)[韓] 曹玟焕《“新子學”與“狂”的現代意義》,《諸子學刊》第十三輯。曹先生提煉出的“狂”字,作爲一種精神很能反映子學的特質,進而體現出“新子學”的理論獨特性。此外,耿振東先生專門針對“新子學”中的“關注現實精神”進行闡發(78)耿振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子學”之“關注現實”的思考》,《諸子學刊》第十三輯。,亦有精到的論述。曹、耿兩先生一個追求“志高”,一個立足現實,雖旨趣對立,但在“新子學”理論構建的框架下卻能融通互補,共同助力於“新子學”核心理論的全面建設。
在衆多關於“子學精神”的論述中,陳鼓應先生提到子學中的“人文精神”尤其值得我們重視。陳先生對道家中人文情懷的闡釋在學界影響頗深,而在此處陳先生進一步指出:“實際上,不僅僅是道家,先秦哲學的特質都在人文精神上。從中西哲學的對比來看,先秦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異之處,就是人文意識的自覺尤其早,而思考又尤爲圓通。”陳先生以老子、孔子等先秦思想家爲例,描述了先秦“人文思想彙集到人文思潮”的歷史進程,進而指出“先秦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對今天的世界有着非常大的啓示。自古至今,人類就不停地面臨三大衝突: 人與自然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人與自己内心的衝突。環顧今天的世界,這些衝突不但没有減緩,反而在一些霸權意識下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子學中藴含的人文精神與對話、和諧的精神,就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79)陳鼓應《子學興替關乎中國思想變革——〈“新子學”論集〉序》,《光明日報》2013年12月16日第15版。陳先生從子學中提煉出的人文精神以及對話、和諧的精神,是針對着當前世界三大衝突而發,頗具現實意義,同時它們又關懷到人類的歷史與未來,更體現了長遠眼光。陳先生的這些探討使“新子學”核心理論的構建又得到了一個新的突破。
2. 其他維度的構建路徑: 具象論述維度與抽象論述維度
以上學者在建構“新子學”核心理論時都是由“子學精神”作爲切入點,這有它的合理性,因爲“精神”既凝聚核心理念,又系聯相關現象,前者是集中的、抽象的,後者是廣泛的、具象的,“精神”這一論述維度恰好中和了兩者的特性。但學界的探討並非全部着眼於“精神”這個中立維度,而是又選擇了一些其他的論述路徑: 有些學者采用更具象的論述維度,這主要是指設置一些人物爲“新子學”楷模,以其具體“行事”、“主張”作爲“新子學”核心理論構建的標準;而有些學者追求更抽象的論述維度,嘗試了如“深層次問題”、“邏輯中心點”、“本體建構”等切入點。以下將對它們展開介紹。
嚴壽澂先生以章太炎先生諸子學成就爲主體展開論述,由此觸及“新子學”理論的構建。他認爲:“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資,是爲章太炎畢生之所主張,實乃中華文化復興必由之道。今日而倡‘新子學’,當於此取法。”(80)[新加坡] 嚴壽澂《“新子學”典範——章太炎思想論綱》,《諸子學刊》第九輯。文中總結的“依自不依他”與“求是致用相資”兩大主張緣起於章太炎先生對子學的研習,又落實於先生一生的學術實踐,故而該文將章先生的學術設爲我們當代“新子學”的典範,其合理性與意義自不待言。
李若暉先生則主張建構“新子學”要與經學相結合,他爲此樹立的典範人物是司馬遷,他論述道:“如何回到自由經學,並以此爲基礎重構子學?漢初司馬遷可以爲我們提供參考。《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贊:‘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太史公正是熔經鑄子,才能‘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史記志疑序》論曰:‘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81)李若暉《熔經鑄子:“新子學”的根與魂》,《諸子學刊》第十三輯。李先生的見解頗有啓發性,司馬遷作爲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本身具備豐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他對待六經的客觀態度,及“成一家言”的“子學式”著述路徑,更值得我們建構“新子學”理論時參考。
與上述兩位先生較爲具象的論述不同,張涅先生的論述没有結合具體人物,而是側重抽象層面的歸納。他總結出了之前子學及子學研究中共同存在的不足,這被表述成“三個深層次的問題”,即“對個體意義重視不够”、“對多元價值缺乏普遍認同”、“對形而上思維的考慮不周”,故而張先生提出“個體本位意識、多元價值觀念、形上思維形式等方面的問題顯然是當代‘新子學’研究可以作爲的方向”(82)張涅《對於當代“新子學”意義的思考》,《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張先生從子學存在的不足展開探討,這同樣透視到了子學的一些共通的特質,對於建構“新子學”核心理論是不可或缺的。
方達《先秦諸子思想中邏輯“中心點”存在的可能性》一文對“新子學”核心理論所作的探討則進一步抽象化,他提出了“先秦諸子思想中邏輯中心點”這一説法。他認爲“在先秦諸子百家時代的某一特定時期,由思想源點分化而出的各個流派思想應當又無限回歸接近這個源點……我們無論在任何歷史階段進行思想創新、變革,實際上都是在這個‘中心點’内部進行的。”進而,他指出“基於此,我們現在提倡的‘新子學’創新的方法,只能是先在傳統中回溯‘軸心時代’的‘傳統源頭’,然後再來尋找‘軸心時代’的‘中心點’”(83)方達《先秦諸子思想中邏輯“中心點”存在的可能性》,《中州學刊》2015年第12期。。顯然,他是希望通過對這一“中心點”的探索,尋找出一條貫通古今的線索,生發出一個統攝子學的體系,從而完成“新子學”核心理論的構建,重現“軸心時代”的“哲學突破”。文中將“軸心時代”思想匯集的“中心點”定爲“荀學”,這有一定的依據,至於是否完全正確,還要學界繼續討論。不過該文探尋“中心點”的嘗試卻很有意義,他在抽象層面設計了一個“中心”,有助於我們構建理論時形成共同的指向,而非零散支離的探索。而且,相比提煉“子學精神”的思路,“邏輯中心點”的提法更容易使學説一體化、體系化,畢竟“精神”這一論述維度提供的只是一種鬆散的聯繫,而“邏輯”則更有明確性、規定性,如果這種思路可以成功,那將是“新子學”核心理論構建的一次質的飛躍。
周鵬(筆名適南)《“新子學”的本體建構及其對華夏文化焦慮的對治》一文則嘗試進行“新子學”的“本體建構”,爲我們的探討又開闢了一個新思路。他指出了“諸子學在歷史上過於分散的現狀制約了‘新子學’的發展”,故而該文“試圖從先秦諸子的文本中爲‘新子學’提煉出三位一體的複合本體論,以解決‘新子學’理論體系的本體建構問題”。經過論證,文中對“新子學”的本體建構作了以下概括:“以流通性而言,謂之‘道(一)本論’,以認知性而言,謂之‘心(知)本論’,以全息性而言,謂之‘天本論’,一個本體,三重功能,這就是‘新子學’三位一體的複合本體論。”(84)適南《“新子學”的本體建構及其對華夏文化焦慮的對治》,《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周鵬這一“複合本體論”有助於奠定“新子學”理論的哲學基礎,並由該基礎生發出“新子學”核心的思想,故而不失爲一種有益的嘗試。
綜上,在學者探討“新子學”核心理論時,或依據現象提煉精神,或樹立典範作爲標準,或依憑思辨建構體系,每個人都依據自己不同的思維習慣進行着理論的構建,雖然形態各有差異,但都是在爲“新子學”填充實質性内容、核心性理念,這些努力都有助於“新子學”核心理論的最終形成。
此外,隨着“新子學”核心理論的逐漸成型,學界也展開了對其中一些關鍵元素的探討。比如“多元”這一概念,在學者們構建“新子學”理論時經常提到,由於這種基礎性地位,它也成了一個專門的研究對象。
劉兵先生(筆名劉思禾)結合古代學術發展的歷史,對子學中的“多元”提出了一些顛覆性的看法:“多元的實質是衝突的合法化,因而需要一種中立的構架來提供低烈度衝突的平臺。”但諸子其實每家都追求確立自己的學説爲唯一合法權威,爲此積極與諸侯政權結合,可以説,“諸子是一種事實上的多樣……諸子不是多元,而是無法一統”。這裏他否定了思想史中“多元”之存在,之後他又有對“多元”作用的否定,認爲“多元主義方案,對於中國古典時期的龐大帝國而言,未免太過反常”。而且他看到了諸子之學與王官之學的統一性,即它們“都在探討一統的秩序和方法”。基於上述認識,他得出了關於子學“多元性”的結論:“子學的確和多元主義的一些觀念很相近,但在根本上還是兩回事,説子學與多元主義相近,莫如説子學與經學相近,真正理解子學,還是要回歸中國語境之中。”(85)劉思禾《探索前期中國的精神和觀念——“新子學”芻議》,《河北學刊》2015年第5期。劉兵先生這種看法可以豐富我們之前對子學的一些簡單看法、認識到其中的複雜性,但該文同樣也有糾枉過正之嫌,因爲這一看法過於强調諸子“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中的“同歸”、“一致”的一面,於是忽視了子學現象中豐富多樣的形態。前文提到,劉兵先生在定義“新子學”時關注點在於學説所發生的環境及兩者間的互動,基於這種關注的探索必然會强調諸子各家面對現實世界時“務爲治”的同一目的,而對子學本身缺乏細緻的分析,這便造成了他對子學内部多元性的否定,將“子學”與“經學”等同起來。至於他將子學的多元闡釋爲“事實上的多樣”,亦可以結合他論述時的關注點進行解釋。我們認爲,子學不僅包括諸子本身的學説,還包括後世學者對其闡釋所形成的學問,諸子本人没有明確提倡多元,但後世研究者通過子學現象卻能體悟到多元的精神,這種體悟從古至今常有表述,成了子學不可忽視的一個傳統,我們在當代弘揚子學的多元性,是基於對學説研究者這一維度的關注,而劉兵先生關注點與我們在不同維度上,故而會有否定的意見,並用他的維度中的眼光來消解我們所建構的意義(劉文從“事實上”着眼,追求回溯至現象發生的時代環境中,於是富有文化内涵的“多元”就變成了僅能描述事實的“多樣”)。總之,劉兵對“多元”的否定本身就是我們“新子學”多元理念的實踐,作爲一種“多元”的意見,同樣值得我們深刻思考。
吴根友先生則將“多元”和“自由”相結合闡釋,更能代表一種普遍的理解。他指出“中國文化是多元並進的,在儒學内部也是如此。傳統文化當然有自己的主流,但並不因此而能過多地奢談‘正統’,争搶所謂的‘正宗’。思想與文化的發展恰恰要在諸子百家争鳴的狀態下,才能健康地向前推進。我們不贊成道統説,贊成子學多元的傳統。僅就思想史、哲學史而言,‘子學’其實是研究諸多思想家、哲學家的學問。中國傳統文化很少有西方思想界的‘自由主義’傳統,但諸子百家的争鳴在實質上就反映了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實質”(86)吴根友、嚴壽澂、李若暉、姜聲調、孫少華、李承貴《新子學: 幾種可能的路向——國内外學者暢談“新子學”發展》,《光明日報》2014年5月13日第16版。。對“正統”和“正宗”的警惕正是我們“新子學”所奉行的一大宗旨,吴先生此處的論述正切合“新子學”的精神。吴先生隨後又引用了著名哲學家蕭萐父先生的觀點,提到:“蕭先生將當今世界範圍内的各家各派的學術争論,視爲當年發生在中國先秦的諸子百家的争鳴。”既而認爲:“參與世界範圍内的諸子百家争鳴,是當代‘子學’發展的一個新方向。”這就將“新子學”的多元性拓展到了當代世界文化的範圍,極具現實意義。同時他又指出了“新子學”中“多元”的時代特性:“他(蕭先生)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及其前景的預測,不同於《莊子·天下》篇所悲歎的‘百家往而不返’的結局,而是趨向於‘同’,只是這種‘同’是以‘異’爲基礎的‘同’。”(87)同上。這種對“多元”的辯證思考值得我們構建“新子學”理論時重視。
以上僅列舉了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能涵蓋學界對“多元”這一問題的不同態度。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界不僅在着力構建核心的理論,也在對構成這一理論的各種元素作細緻辨析,宏觀、微觀兩層面的研究呈現着相互補充、共同推進的態勢,如果這種態勢能持續發展,筆者相信“新子學”必然能被構建成中心明確、結構宏偉同時又細密謹嚴的理論體系。
(二) “新子學”與其他領域的交叉研究
當一個理論概念及定位明確、主體理論成熟後,它自然會超出原有框架,影響到學者對其他領域相關對象的研究。“新子學”的發展也遵循這一規律,隨着自身的成熟,它的意義不再被諸子學這一傳統範疇所局限,而是從中走出,與各種研究發生了交叉,猶如大樹頂端生發的枝條一般,向各方向不斷延伸。以下將擇其要者進行分析。
1. “新子學”在政治學領域的延伸
“新子學”與政治學領域的交叉取得了比較矚目的成果,這體現在“第二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學者對這一方向的熱烈探討,關於這點,本次會議的綜述有詳細介紹:“‘新子學’的發展不僅是理念的提出,也體現在研究領域的實際推進上。本次大會的一個亮點是諸子國家治理思想的討論,共有16位學者撰寫了諸子政治思想的論文,形成了諸子學在政治治理領域的一個突破。……總的來看,此次會議在諸子政治學方面打開局面,初步顯示了諸子政治研究的重要性,爲今後的諸子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方向,可以説是‘新子學’在研究領域的一個實際推進,是本次大會重要的成果。”(88)劉思禾《發掘諸子治國理念》,《光明日報》2015年6月8日第16版。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交叉碰撞出了激烈的思想火花,“新子學”在政治領域的開闢有廣闊的前景。其實,這種現象是有其必然性的,因爲子學自發生起就重點考慮“天下秩序”、“國家治理”的問題,“新子學”作爲其新形態,再次進入政治治理領域是順理成章的事。只不過我們在結合兩者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條件,即需要突出時代性,讓“新子學”融入當代政治治理的研究中去。
在這方面,蔡志棟先生(筆名莊沙)的探索比較有代表性。其文章之題目定爲“儒家式和道家式:‘新子學’政治自由論的兩種建構路向——以康有爲和嚴復爲中心”,可見,該文選擇了近現代人物爲切入點,緊扣“政治自由論”這一當代政治熱點論題,由此與“新子學”結合,並最終歸結到子學中的兩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可以説既凸顯了時代又反思了傳統,在思路上值得借鑒。至於其中具體論述及結論,則亦有深刻之處,他指出“康有爲主要從儒家的角度詮釋政治權利的古典根源,揭示了自主之權和先秦思想之間的内在聯繫,將權利理解爲名分,又將之誤解爲利益,大加韃伐。嚴復明確地從道家那裏發展現代政治自由思想,他將楊朱和莊周等同起來,爲政治自由的展開奠定了個人主義的邏輯基礎,並將‘在宥’解讀爲自由,將老子詮釋爲民主之道,成爲了道家自由主義的濫觴”。該文的論斷不僅建立在對康、嚴兩人政治思想的準確把握上,也依憑着對儒、道兩派理論精髓的深刻體悟,基於這種發現,他便提出:“康、嚴兩位的詮釋顯示了‘新子學’構建政治自由論的儒家式和道家式兩種路向。”(89)莊沙《儒家式與道家式:“新子學”政治自由論的兩種構建路向——以康有爲、嚴復爲中心》,《諸子學刊》第十三輯。這種“路向”的探討無疑爲“新子學”在政治領域的開闢提供了啓發,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2. “新子學”與現代學術的互動
“新子學”與現代學術研究也有交叉,許多學者對此也展開了專題討論。孫少華先生關注“新子學”對學術“新傳統”的意義,認爲“‘新子學’之提出,可謂與胡適的‘新文學’、饒宗頤的‘新經學’、梁啓超的‘新史學’互爲犄角,成爲創建中國古代學術研究‘新傳統’不可或缺的部分。”(90)孫少華《“新子學”與學術“新傳統”建設》,《河北學刊》2015年第5期。之後該文從“新與舊”、“破與立”、“學與用”三個矛盾關係入手,分析了“新子學”與“新傳統”建設的可能性、路徑與方向問題。孫先生文中提到他“曾就21世紀學術‘新傳統’的建立問題,有所論述”,可以説他一直致力於“古典學術現代轉型”問題,孫先生此次的探討將“新子學”帶出了原有諸子學研究的範疇,使之融入了當今古典學術研究的新潮流中,意義不容忽視。此外,林其錟先生也從“新子學”的角度談到諸子學的學科建構,認爲它“應形成諸子典籍的整理、考究與諸子學概論及諸子學史。當然在此基礎上還可以派生諸多的分支研究領域。”(91)林其錟《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諸子學刊》第九輯。林先生這種設想立足於前人研究子學的成果,參考了現代學科門類的構成,對於“新子學”融入現代學術體系有着重要意義。
上文中,林先生提到了“分支研究領域”,這就相應地涉及了“跨學科研究”的問題。跨學科研究是現代學術研究的熱點,“新子學”與跨學科研究的關係也得到了很多學者的探討。筆者在2013年的會議發言時就曾呼籲學界應“突破學科限制,凝聚研究力量,在夯實‘新子學’的基礎上,探索諸子學研究的新範式。”(92)潘圳《“新子學”推動文化復興》,《社會科學報》2014年4月24日004版。在這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有孫以昭先生和姜聲調先生(筆名淩然)。孫先生首先指出“舊子學本身就是跨學科、多學科之作”,既而“以莊子其人其書爲例,闡述‘新子學’的跨學科、多學科的大文化研究”(93)孫以昭《“新子學”與跨學科、多學科學術研究》,《河北學刊》2015年第5期。,文中所舉例證説明了《莊子》一書中所藴含的物理學、養生學、生態學等方面的價值,彰顯了“新子學”與跨學科研究相交融的廣闊空間。姜聲調先生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則采用了更宏觀的視角,他認爲“從轉型到巔峰,必須經過一定的學術研究進程,把不同學科整合、貫通起來,以解除其間的相對局限性。爲此,在‘新子學’與跨學科學術研究上要有一種反思,才能正視存在的問題。關於‘新子學’學術研究轉型進程的問題,應該可以從規範化、多元化、普及化等過程來思考,其中以多元化、普及化爲重點,進行細節性的文學化與大衆化,應能達到預期的功效。進而還要從前人的學術成果中尋找一些相關範例,接受而後解構,建構進而發揮,從而全面深入地開展跨學科的‘新子學’學術研究。‘新子學’與跨學科學術研究是一個相涉互動的關係。正視時代趨勢的變化與要求,進行古今與東西對話、解構與建構工作,唯有學界與大衆相結合,才會實現跨學科的‘新子學’學術研究。”(94)[韓] 淩然《“新子學”與跨學科學術研究鳥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姜聲調先生的探討側重理論層面的分析與整體方向的規劃,與孫先生的論述相得益彰,兩位學者的研究都爲“新子學”與跨學科研究的互動提供了思路。
3. “新子學”與當代文化研究的融通
“新子學”除了與現代學術有交叉外,它與當代文化亦有密切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在“新子學”理論構建的第一階段就已經得到學者的深入探討。如郝雨先生首先明確提出“(新子學)並不僅僅是一個古代文化的研究範疇。它也爲現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學術方向”(95)郝雨《“新子學”對現代文化的意義》,《文匯報》2012年12月17日00C版。。在郝雨先生的倡導下,學界相繼組織了“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傳承——現代文化學者視野中的‘新子學’”(96)詳見郝雨、楊劍龍、葛紅兵、劉緒源、姜琍敏、王宏圖、徐國源、李有亮、何美忠、范松楠《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傳承》,《黄河文學》2013年第2 /3期(Z1)。、“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探源與經典傳播——‘子學精神’傳承與傳播”(97)詳見毛冬冬、劉凱《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探源與經典傳播——“子學精神”傳承與傳播研討會綜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兩次“新子學”學術研討會,皆由現代文化學者爲主導,着力探討“新子學”與現代文化諸方面的交融問題。楊劍龍先生指出“‘新子學’是一種歷史傳統、文化傳承,放在當下,肯定要有一種當下的意識”,而“‘新子學’闡釋的當代語境,應該崇尚以人爲本”,另外則“應該融入現代人的現代思考在内”(98)詳見郝雨、楊劍龍、葛紅兵、劉緒源、姜琍敏、王宏圖、徐國源、李有亮、何美忠、范松楠《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傳承》,《黄河文學》2013年第2 /3期(Z1)。。王宏圖先生則用“對話理論”這一現代文化成果來思考“新子學”,認爲“‘新子學’給我們的一大啓示是,除了將傳統資源發揚光大外,還應開展中國文化與各國文化全方位的對話,藉此啓動中國傳統内在藴含的活力,同時也大規模地汲取域外思想資源,以豐富、發展自己”(99)同上。。楊先生、王先生都爲“新子學”融進了現代文化的一些理念,這有助於“新子學”以更親和自然的姿態進入現代文化領域。
葛紅兵先生則認爲“‘新子學’如何與當代生活融入與對接,還需要多方面的梳理和新型的研究”,其中,“對‘元典’的梳理和闡釋”、“探尋‘子學’後來被壓抑的原因”以及“如何運用‘新子學’的精神踐行中國傳統的思想和倫理”都是學界嘗試對接二者時需要做的工作(100)葛紅兵《“新子學”: 如何與當代生活對接》,《名作欣賞》2015年第1期。。
王斐女士則專門探討了“第三極文化”中體現的“新子學”精神,並將它們概括爲三點: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創新精神;傳統文化的傳承性與當今文化的現代性相結合;中國文化的大品格是在困難中尋求自己的文化出路(101)王斐《“第三極文化”體現的“新子學”精神》,《藝術百家》2013年第7期。。“第三極文化”是由黄會林教授提出的一個現代文化概念,它是指“相對於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而言的中國文化”,黄教授提出這一概念是“對東西文化兩極論的反思和修正,是應轉型期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尋求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一種努力”(102)同上。。該文將“新子學”與“第三極文化”相結合探討,爲“新子學”進入現代文化領域發現了一個很好的結合點,相信基於共通的學術目標和文化底藴,這兩種理論必然能相互促進,共同致力於中國現代文化的建設。
張勇耀女士還提出了“構建‘新子學’時代新的女性話語體系”這一命題,認爲“新子學”與現代文化中的“女性主義”有相通之處,既而指出“如何從當代女性的視域出發,建構女性話語體系‘新子學’,這無論對子學學術層面的研究,還是對當代女性話語體系的傳播,都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新子學’女性話語體系構建就是要發掘和提煉傳統諸子學説中積極的女性觀並得到廣泛傳播。”(103)張勇耀《構建“新子學”時代新的女性話語體系》,《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對女性的重新認識是現代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張女士在這方面的思考無疑豐富了“新子學”在現代文化領域探討的成果。此外,“新子學”與文化傳播的問題亦是現代文化學者討論的熱點,本文將其放置於第三階段集中探討,此處暫不詳述。
(三) 對“新子學”基本問題的再思考
雖然學界在第一階段已經對“新子學”的基本問題進行了細緻的探討,但隨着參與學者的增加,這方面又有一些新觀點湧現,我們也必須要對它們給予重視。
關於“新子學”的概念和範疇,本階段有以下幾位學者的探討值得注意。
張涅先生側重以實踐性作爲標準界定“子學”與“新子學”,他指出:“‘子學’和‘子學研究’是兩個概念,‘子學研究’是純學術性的,而‘子學’更多地具有社會實踐性的品質。所謂‘新子學’,嚴格地説,是指在新的歷史階段對於社會政治的再思考和實踐。與此相應的‘新子學研究’,即晚清民國以來的吸收了西方學術思想和範式方法後的諸子學研究。”(104)張涅《對於當代“新子學”意義的思考》,《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張先生對“實踐”和“研究”的區分有着特殊的意義,這一定義能够突出“新子學”的實踐品格,使它更好地契合於當下社會。
劉兵先生(筆名劉思禾)則爲我們看待“新子學”又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他首先爲“子學”的定性尋求了一個新的路徑:“把子學視作前期中國思想的重要線索,以先秦諸子學爲中心,以漢、魏、六朝、隋、唐諸子學爲展開,而與經學並立。”(105)劉思禾《探索前期中國的精神和觀念——“新子學”芻議》,《河北學刊》2015年第5期。具體來説,他將中國的思想史以唐爲界分爲兩個時期,兩者特質可作以下表述:
前期: 中國自發思想,經、子分享共識——對社會的控制
後期: 中外結合思想,儒佛分享共識——對心理的控制
由此,他對子學的歷程就有一個四段分期: 先秦、兩漢—隋唐、宋元明清、晚清民國,既而他界定了子學研究的對象:“應把子學研究集中於先秦諸子之學,同時,應關注子學的第二期發展,重視子學和經學的互動關係,更重要的是,須把以上二者統一起來,來把握中國前期思想的基本特徵,對於宋明時期的子學(如朱子對先秦諸子的研究),並不是重點,而如何展開新時代下的子學研究,這是其關鍵所在。”(106)同上。劉兵先生這段論述不但回顧了子學的歷程,也由此呈現了“新子學”的某種本質,它是接續前期中國思想的一種努力,是諸子學發展歷程的一個新機遇。
郜元寶先生則對“新子學”的多層含義進行了區分,其一是“新的子學”,其二是“新子之學”。他指出“‘新的子學’是要把過去歷朝歷代的‘子學’研究根據今人新發現的材料和新建立的方法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而“新子之學”,則是指“我們已經出現了或應該出現或即使尚未出現但應該呼唤出現‘百家争鳴’時候那樣的衆多的‘子’,這些‘新子’各以其學説佈告天下,就是‘新子之學’,簡稱‘新子學’”。在此基礎上,郜先生還提出了“新的子學時代的精神”作爲對上述兩層次的超越,前文已論,此不贅談。郭丹先生同樣對“新子學”作了這兩個層次的劃分:“‘新子之學’側重於‘立説’之學;‘新之子學’則包含詮釋之子學。以這樣的理解,愚意以爲‘新之子學’與‘新子之學’,都是‘新子學’所應包括的範圍。”雖然“新子學”包含多個層次,但郭先生對“新子學”的範疇持有比較嚴謹的態度,不希望“新子學”成爲“包羅萬象的雜燴”(尤其在“新子之學”層面反對將近代許多學者歸入“新諸子”),而是將其限定爲“繼承從先秦諸子之學所延續下來的具有傳統文化意義的新學説”(107)郜元寶《對“新子學”三個層面的思考》,《名作欣賞》2015年第7期。。總之,郜、郭兩位先生探索了“新子學”概念的層次,這在第一階段也有學者論及,但兩位先生在此基礎上又分别有了“超越”和“限定”,這可看作是對第一階段探討的延伸和發展。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對第一階段“新子學”概念、範疇的討論作出了糾正。如之前學者提出民國時期子學研究可作爲“新子學”的一部分,孫以昭先生結合“新子學”中“新”字的内涵,對此予以了否定:“至於民國時期的子學著作,竊以爲不能稱之爲‘新子學’,如上所述,‘新子學’應有種種要求與標準,應自成體系,決不能僅因其著作中有新意,即視爲‘新子學’。”(108)孫以昭《“新子學”與跨學科、多學科學術研究》,《河北學刊》2015年第5期。學術的研究是一個“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的過程,一些基本的問題就是需要我們不斷的切磋、琢磨,才能得到更完美的答案,由此來看,上述探討並不是重複研究,而是有着不可或缺的意義。
對於“新子學”的自身定位和相關關係的再思考同樣是本階段探討的重點。劉兵先生(筆名劉思禾)强調“從經學、子學貫通的一面來把握子學”,他認爲在先秦時代“經學和子學同構並生”,其中“儒學有顯、隱兩條線”,顯的一方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儒家孟、荀等諸子,隱的一方是記載不詳的“傳經諸老”,這種顯隱關係在武帝之後則被倒置,“傳經”成爲顯學。故而劉思禾先生指出:“子學和早期經學的相互影響是實際存在的,其中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梳理其中的原委,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經、子關係,進而理解‘子學時代’,而有一個不一樣的諸子學。”之後,劉思禾先生又分析了秦朝之後經、子之間的政教關係,在這方面他給出了結論:“經不是儒家的專利,而只是對主流文本的稱呼而已。不是經學或儒學壓制了子學,而是總會有一種主流學説與政治系統結合,以維繫基本的文明秩序和社會秩序。”所以他對子學又有了一個新的定位:“什麽是子學?子學就是脱離於政教系統之外而又無時不與之關涉的精神和觀念而已。”(109)劉思禾《探索前期中國的精神和觀念——“新子學”芻議》,《河北學刊》2015年第5期。這篇文章看到了經、子相通的一面: 在“歷史關係”上,先秦經學、子學同時都存在於儒家學派中;在“政教關係”上,經學、子學同樣致力於某一政治系統的合法性論證,並有排除異己的傾向。筆者認爲這兩點的確豐富了我們對經、子關係的認識,但至於它們能否成爲經、子關係的主要構成内容,尚需要學界進一步探討。
與劉兵先生在經、子關係上持相近態度的還有李若暉先生,他以經學爲中心梳理了學術史,由此來辨析“經學”、“儒學”、“子學”、“哲學”數者的關係:“漢唐以經爲大道所在,諸子爲六經之支與流裔。然至唐宋之際,經學已陵夷衰微,實不足以達道。於是文士蜂起,倡言‘文以明道’。程頤則以經學與文章皆無與至道,義理之學方可進道。於義理之學中,又驅逐異端,獨以儒學爲正統。於是宋明理學起,而經學、儒學離。至晚清,西學東漸,儒學拙於應物,學者乃以諸子對應西學,儒學正統遂傾。近代經學沉淪,子學復興,但復興後的子學棄經學而附哲學,於是中國傳統義理之學的固有格局與内在脈絡被打散。”這段論述中,李先生以他的視角描述了“經”、“儒”、“子”三種學術在古代的離合過程,我們大致可以做以下歸納: 漢唐時,經學獨尊,結合儒學,附有子學;唐宋之際,文章之學興;程頤後,儒學正統,驅逐異端(子學),離棄經學;晚清近代,儒學衰微,子學興起,並棄經入哲。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中,經學是逐漸喪失統領地位,子學則迅速崛起應對時代,儒學則經歷了一個上坡又下坡的過程,那麽依照這一邏輯,就當下來説,經學只能代表曾經的輝煌,儒學現在的影響也只是餘音迴響,只有子學才能代表未來的方向。但因爲李先生一開始就堅持以經學爲中心,所以他對現代“新子學”發展的思路仍是希望“回到自由經學,並以此爲基礎重構子學”,這在文中被概述爲“鎔經鑄子”,强調“當代‘新子學’的建立,必須與經學相結合,以中華文化的大本大源爲根基,立足於中華文化自身,面對中華文化的根本問題,重鑄中華之魂,此即當代‘新子學’之魂魄所歸”(110)李若暉《熔經鑄子:“新子學”的根與魂》,《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當然,李先生“經子結合”的設想是很理想化的,這有助於“新子學”在國學體系中更平穩地立足,但我們如果將關注的中心由經學轉向子學再來審視上述學術史便會發現,子學的發展一直有依附性,只是對象由古代經學轉到現代哲學,我們現今提倡“新子學”就是爲了將其作爲一個獨立的主體凸顯出來,所以筆者認爲“經子結合”固然是好的,但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堅持“新子學”的主體性,經學可以作爲一個參考幫助“新子學”的構建,但學術絶不能再回到“諸子爲六經支與流裔”的時代。
劉、李兩先生的文章都揭示了子學和其他學術門類之間存在複雜的關係,這就需要學界對此展開更深入的探討。其中,如陳成吒先生(筆名玄華)撰有論述經、子、儒關係的專文。對於“經子關係”,該文指出“子學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發展出來的經學否定者”,而關於“儒學”,該文則認爲“儒學在本質上具有子學性,是子學消解經學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同時也是經學異化子學的主要對象,因此具有一定特殊性”。所謂儒學消解經學,是指儒學“能編修其文本”、“可轉化其概念”。而所謂“經學異化子學”,主要是指“經學在異化儒學”,包括:“首先,經學對儒學的異化,莫過於將自我附身於儒術,使後人經、儒不分。……其次,經學不斷將自身的一元專制意識形態滲透到儒學之中,使之爲其所用。……最後,經學也深入到具體的學術研究層面異化儒學。”(111)玄華《“新子學”對國學的重構——以重新審視經、子、儒性質與關係切入》,《諸子學刊》第十三輯。陳成吒先生此處指出了子學對經學的否定以及子學通過儒學對經學實現了消解,這些觀點在他之前的文章中曾經提到,但在本文中,他又進一步探討了經學對子學的異化現象,這是之前未曾談到的。大概是在這一階段學界出現了要求重視經學、融合經子的聲音(如劉兵、李若暉等學者的文章),使得學者反思之前理論,重新思考經學對子學的客觀影響。當然我們對待經學不能忽視也不能拔高,我們要客觀地考察它的影響,最終目的還是將其作爲參考來構建“新子學”理論。正如陳成吒先生在結論中所説的那樣:“‘新子學’當自覺此點,將儒學從經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並最終消解盤旋在傳統文化上空的經學陰魂。”(112)玄華《“新子學”對國學的重構——以重新審視經、子、儒性質與關係切入》,《諸子學刊》第十三輯。
五、 第三階段: 强幹展枝、迎接花期
“新子學”經過了上述兩個階段的發展,從2016年開始便進入了第三階段,從2016年至2017年筆者撰稿之時,學界又召開了兩次以“新子學”爲主題的學術會議,即2016年10月於臺灣屏東舉辦的“2016‘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13)詳見陳志平《海峽兩岸學者研討“新子學”》,《光明日報》2016年12月5日第16版。,和2016年11月於廈門舉辦的“‘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114)詳見李向娟《“新子學”將助力當代思想文化建設》,《福建日報》2016年12月6日010版。,以及2017年10月於臺北舉辦的“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和2017年11月在上海舉辦的“海峽兩岸‘新子學’座談會”。雖然目前第三階段剛剛開始,但形成的文章已有17篇之多。筆者之所以劃定2016年爲界限,主要是因爲從這時起學界逐漸將“新子學”的實踐問題提上議程,畢竟之前兩階段的探討已將該理論的概念和主幹等問題作了界定,此時已有了充分的準備把“新子學”帶給大衆,使它發揮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這種理論影響現實的過程,根據文章開頭的比喻,便是一棵樹開花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將會很曲折漫長,現在“新子學”的“花期”還只是一個美好的期待,爲了讓它早日實現,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强化它的“主幹”,延展它的“枝條”,只有將自身發育好,才能在時機到來時,實現自己的綻放。因而筆者將該階段的特徵命名爲“强幹展枝、迎接花期”。
2016年初筆者發表《三論“新子學”》一文,該文相比之前兩篇“新子學”專論,更加關注多元文明的視野下界定“新子學”在當代中國身份認同建構上的獨特價值,這種關注意味着“新子學”要在專門領域的延伸以及在此基礎上對現實發揮的影響,這是筆者踐行第三階段使命的嘗試。文中專門探討了“新子學”對傳統文化研究創新的作用,這主要表現爲由“新子學”主導的一系列創新實踐,即“追溯原點”、“重構典範”、“唤醒價值”三個方面。
“追溯原點”意味着“傳統文化研究創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國思想的原點,即先秦時代的諸子學傳統”,爲此我們需要擺脱古代經學心態的束縛,恢復“先秦學術的原初面貌”,同時又要走出近代哲學史學科的框架,定位到“原生的中國意識”,並輔以考古學新發現,回歸“中國思想原點”,在此基礎上實現創新。
而關於“重構典範”,筆者指出“學術要大膽創新,要適應時代,有必要對傳統作一番大的重構。重構的關鍵在於把握先秦時代思想的結構”。筆者在此梳理了先秦諸子學發展的歷程,又結合着諸子學探討了“六經”的價值,最終給出了關於“新典範”的設想:“‘新子學’認爲,關於元典時期的研究範圍實應涵括諸子各家,旁涉早期經學,這樣就能跳出經、子二分的傳統觀念,回歸原點。我們主張以《春秋》《周易》《論語》《老子》爲基礎,這可能是激發創造的新典範;再旁及《孟子》《荀子》《莊子》《墨子》和《韓非子》等其他經典,形成元文化經典的新構造。”(115)方勇《三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6年3月28日第16版。筆者的這一設想更注重這幾部經典的相通性,打破傳統的“儒道異同”、“經子尊卑”的看法,這是必然的選擇:“‘新子學’認爲,在面對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深入把握早期經典中的相通之處,熔鑄出新解,這當是學術創新的途徑。”
至於“唤醒價值”,這更是當今“新子學”需要努力的方向。筆者指出“站在‘新子學’的角度上,‘中國哲學’事實上成爲現代性叙事的構件,其在知識上的貢獻遠大於價值上的。中國古典學術與西方學術存在很大差異,其價值意義大於知識意義”,可見當前學術研究在哲學史框架内已嚴重脱離了實踐,但“傳統文化研究的方向應該是對治現代性,而非論證現代性”,已經成爲“現代性叙事構建”的“中國哲學”自然無法應對現代性的挑戰,這時就需要“唤醒價值”,即“在傳統價值中找到適應當代的形式,並與現代價值做有效溝通”。筆者認爲經過了“原理化”、“社會科學化”的“新子學”可以承擔這一使命。因爲“現代化的本質是欲望”,這是現代文化的基本弱點,西方結合自身的文化克服了它,但這些經驗並不適應於東方,我們要克服這個弱點,可以訴諸“對文明有深刻洞見、對人有深刻理解”的先秦諸子,在這方面筆者作出了以下結論:“假如我們把技術和資本的問題理解爲物,先秦諸子要處理的就是人如何應物的問題,這是傳統文化研究創新的根本點。”(116)同上。
以上便是該文的大致思路,相比較而言,之前筆者探討“新子學”的文章多就“新子學”本身進行學理層面的思考,而該文則結合“新子學”針對“傳統文化研究創新”問題給出實踐層面的建議,這種轉變可以代表第三階段的新特點,即上文提到的向更專門的領域延伸(“延展枝條”)與追求更多的現實影響(“迎接花期”)。除此之外,“强化主幹”在此階段亦是不減的熱點,學界對“新子學”核心理論的構建仍在繼續。以下將對這幾個方面作逐一介紹。
(一) 對“新子學”核心理論的進一步構建
在前文,筆者介紹了學界構建“新子學”核心理論的各種路徑,第三階段學界在討論該問題時,較少使用“精神”、“楷模”這類偏具象的論述維度,而是采用了“問題”、“道説”等有抽象色彩的論述維度。
在孫廣、周斌先生《從共同的問題意識探求子學的整體性——“新子學”芻議》一文中,作者首先指出“子學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一家一子之研究,没有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既而指出“‘新子學’在這方面的意義,就是凸顯子學本身的整體性和統一性”。而如何凸顯子學的整體性和統一性,該文又對古今曾經嘗試過的方法依次進行了評價,歸納其意,可分爲以下數類: 當今“新子學”探索者用“多元”、“狂”等具體理念來統攝,但這容易造成理論争端;古代儒家學者則認爲“諸子的相通之處,在於諸子皆‘資於治道’”;古代雜家學者認爲“子學的相通性也在於‘國體之有此,王治之無不貫’這一治國的問題意識”。對比上述各類探索思路,該文作者認爲:“(儒家和雜家)從共同的問題意識的角度來探求子學的統一性,無疑是可取的。‘新子學’要謀求一個整體性的‘子學’,這種視角是非常值得探索的一種路徑。”(117)孫廣、周斌《從共同的問題意識探求子學的整體性——“新子學”芻議》,《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3期。該文追求從一個新的高度來把握子學的整體性,將諸子之間存在的共同關注提煉爲“共同問題意識”這一涵括極廣的説法,這繼續了劉兵、聶學慧文章中對“諸子問題”的探討,並將其發揚光大,使之參與到“新子學”核心理論的構建中來。
周鵬先生《淺談“新子學”的角色定位和言説方式》一文則采用了現代西方哲學中“道説”這個概念來充實“新子學”的核心理論。據該文介紹,“道説”由海德格爾提出,可以理解爲“不是‘我’在説話,而是‘大道’穿透‘我’的存在而自行言説”。而“道説”對“新子學”的言説方式有着重要意義,周鵬先生指出:“‘新子學’要發掘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首先要實現‘言説方式’的革新,因爲我們的經典言説形態,幾乎全都是不同形式的‘道説’,一切説出來的關係價值,全是來源於‘道’的。”該文還指出:“‘新子學’的‘道説’者,在撰寫專著的同時,也可以試着采取‘對話’這樣一種鮮活的言説形式來展現自身。”同時,爲了更好地實現“道説”,周鵬先生强調“廣泛吸收”的重要性,認爲:“作爲今天‘新子學’的‘道説’者,則應該將這個範圍擴大到軸心文明産生的一切經典,並在此基礎上廣泛吸收一切優秀的著作來‘旁推交通以之爲文’。這樣的‘道説’,才能够契合‘新子學’自我標榜出的‘多元性’。”但此處該文也指出“多元性”是基於“道”的,故而文中最後强調“我們今天要展開‘新子學’的‘道説’,首先應該明確的,正是這一個共同的‘道’的價值源頭。”(118)周鵬《淺談“新子學”的角色定位和言説方式》,《諸子學刊》第十五輯。筆者在之前已經介紹到,該文作者曾對“新子學”思想進行過“本體論”層面的建構,其中便包括“道本論”這一範疇(119)詳見適南《“新子學”的本體建構及其對華夏文化焦慮的對治》,《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在該文中他又引用了“道説”這一概念,顯然是希望對他之前的理論作進一步拓展。筆者認爲“道本論”和“道説”兩種提法都爲“新子學”核心理論在哲學層面奠定了基礎,並且兩者相互補充,使體系更加縝密,至於其進一步的完善,還需要學界共同的參與。
“道”作爲哲學上一個生發一切的本體,自然也可以作爲一個核心内涵來統攝子學的各個部分,故而“道”成了構建“新子學”核心時常用的一個論述維度。李星瑶女士《從孔老對“道”的同質性理解談“新子學”的精神》一文也同樣追求從“道”這一層面展開探討,該文分别探討了孔子之“道”與老子之“道”的實質,進而指出:“總起來講,儘管老子的‘天道’似乎與孔子的‘人道’在取向上迥異,儘管老子以‘毁仁棄義’爲思想旗幟,但就其在‘道’中體現的對話主義實質而言,二者之間别無二致。”筆者認爲,該文論證孔、老對“道”的這種同質性理解,應該有助於“新子學”發展出它的核心理論。具體來説,它可以消除文化傳統中的對立因素,即該文所謂:“孔、老兩家學説在天人問題上的同質性給二者從對立走向統一,即把中國的倫理學與宇宙論加以匯通——提供了理論可能。”這便引出了“新子學”的内藴,即“‘新子學’不僅把儒、道兩家的倫理學和宇宙論加以整合,用‘道’這個命題概括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基本問題,而且作爲一種精神,接上了中國文化古老的源頭”(120)李星瑶《從孔老對“道”的同質性理解談“新子學”的精神》, 載於《“‘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6年。。這裏文章明確點出了“新子學”的核心構成——“道”這個命題,又將其精神源頭回溯至先秦時代,通過這種論述我們對“新子學”内部的統一性有了更多的理論自信。
不同於上述學者對“道”的關注,方達、王寧寧《論“新子學”何以成立——中西兩種視域的交融》一文致力於闡述“治”這一古典學術理念對於“新子學”理論構建的價值。該文提出“‘新子學’的根本願景是以先秦諸子時代的‘子學精神’回應當下的各種時代問題”,並以此爲中心分别探討了三個問題。首先,“子學精神”的内核是什麽?該文在“(諸子)務爲治”這一傳統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認爲“諸子務爲治的終極追求在形上層面的意義就是對最本質規律探求過程的展開”,並又將它引入當前語境來闡釋:“轉换到現代語境下,中國古典視域下的‘治’這種本質性的規律實際就是對個人(己)與外在世界(倫)終極和諧秩序的表述。”其次一個問題則是“時代問題的根源何在”,該文從形而上的層面將其歸結爲傳統形上終極追求——“治”與現代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核心——“確定性”發生了衝突,當代中國接受西方文化卻未得其核心“確定性”,擺脱傳統卻仍因襲以“治”爲終極追求,這造成了時代精神的困惑。那麽面對這種衝突,便引出了第三個問題,即“中國古典視域下的‘子學精神’回應現代性如何可能”,這也可以看作是對“新子學”核心理論應如何構建的探討。具體來説,針對上述“中西文化融合時的排異作用”,作者指出:“‘新子學’站在古典視域下對傳統與西方兩種文化‘分着講’也許恰恰可能成爲真正解決問題的良藥。”顯然,此處作者更看重傳統文化中的“治”對於“新子學”的獨特意義,後文便探討了該理念的價值。作者先是對“現代性”進行了剖析:“西方古典哲學後逐漸顯現的現代性問題,其實質正如前文所論,是由於長期對‘確定性’的追求而導致認知理性與實踐理性在内部逐漸呈現非同一性而造成的。”既而文中又通過詳細論證,結合以“治”提出了自己的對策,認爲“在中國古典視域下,表述爲外在顯現爲確定平衡的,而内在又可以産生多元化達成方式的‘治’,恰恰從根源上消弭了現代性所帶來諸多問題的可能性”。該文在最後指出:“綜上所述,‘新子學’的提出旨在能够真實、真正回應時代對於傳統,對於全球化融合的拷問。這便意味着‘新子學’所關照的衆多層面需要用一條内在的嚴密線索將之串聯。”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本文的内在思路,是希望以“治”作爲“新子學”的一個核心來應對當代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實現“對傳統的自覺意識的理論重構”(121)方達、王寧寧《論“新子學”何以成立——中西兩種視域的交融》,《人文雜誌》2017年第5期。。回顧上文的論述,可以説作者爲此所作的探索還是比較成功的,尤其是文中尋求到了“治”這個理念作爲中心觀照,不僅突出了“子學”的特質,也契合了當代的需要,在充實了“新子學”核心理論的同時,也論證了“新子學”在當代産生的必要性。
確定性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方達、王寧寧的文章將“確定性”作爲一個對比元素來凸顯子學的特質,還有一些文章則將其作爲主要研究對象展開探討。如孫廣先生《“新子學”思想理路》一文,以“不確定性”作爲“子學”的特質,認爲“西學的理路與經學是一致的,其思想體系都是以某種預設的終極的‘確定性’來對治世界的‘不確定性’。而子學的思想理路則恰好相反,其思想系統是試圖通過對治世界的‘不確定性’來求索終極的‘確定性’。他們提出的許多類似‘確定性’的概念,實際上都是處於未完成的狀態,只是代表了子學對終極‘確定性’的追求的一種‘象徵符號’而已。而子學的這種思想理路,實出於對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性的認識和嚴謹樸實的態度”。聯繫上文,我們注意到,方達、王寧寧將“確定性”的對立概念設爲“治”,而該文則將其設爲“不確定性”,這並不矛盾,方、王兩人傾向於從境界上尋找“確定性”的對立概念,而孫文則從認知上尋找與“確定性”相對立的態度,之間只是視角不同而已。孫文發現的這種子學與西學、經學間的區别對構建“新子學”理論極有意義,他指出:“我們提倡‘新子學’,就是要走出經學和西學的這種思想體系,重回子學的思想理路——通過對治世界的‘不確定性’來求索終極的‘確定性’。在子學的思想理路上,我們的國學甚至西學,才不至於受到任何預設的限制,才能在對治社會問題的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從而成爲真正的嚴謹之學,成爲倫常日用中的‘國民之學’。”(122)孫廣《“新子學”的思想理路》,載於《“‘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6年。作者此處將“不確定性”設置爲“新子學”的内在思想理路,可以看作是構建“新子學”認知論的一種嘗試,這和之前學者追求構建本體論的努力一樣,都爲“新子學”理論奠定哲學基礎提供了參考。
揣松森先生《“新子學”呼唤先秦諸子主體思維的回歸》則專門討論了子學中的“主體思維”,該文首先分析了《論語·子罕》“逝者如斯”章的闡釋歷程,由此引申出了古今思維差異的問題。對於這一點,文章指出:“先秦諸子以主體思維觀照人與世界,其學説是這種思維對世界觀照的反映。”所謂“主體思維”,文章解釋爲“主體思維就是主體透射到自然界,自然界通過主體而收攝進來,並且在主體内在當中獲得終極意義”。而關於這種“主體思維”在先秦諸子中的體現,文章主要以儒、道兩家爲例進行了説明: 一方面,“講道德的存有論和功夫論是儒家主體思維方式的體現”;另一方面,“道家講境界論,也講功夫論”。最後,基於傳統文化轉型和解答現代性兩方面考慮,文章認爲“‘新子學’必須召唤主體思維的回歸”(123)揣松森《“新子學”呼唤先秦諸子主體思維的回歸》,《諸子學刊》第十五輯。。該文在探討“新子學”理論時關注到了一種具體的思維方式,前文提到歐明俊先生曾爲“新子學”總結過一系列的“思維”概念,該文的探索是對之前總結的有益補充,而且其意義更爲獨特,因爲“主體思維”是中國所“特有”、先秦尤顯著的一個特質,以它來充實“新子學”理論更可以凸顯其中的諸子學色彩,增强理論的獨特性與標識性。
馮劍輝先生《錢穆的子學研究對“新子學”的啓發》一文則以錢穆的子學研究爲典範,來探討“新子學”理論的建設。文章歸納了錢穆子學研究比較有特色的幾個方面,並分别説明了它們對“新子學”的借鑒意義。一方面,是“基於史學層面,展現的平等、多元、會通的子學觀”,以此爲榜樣,“新子學”應該“以認識論的視角統貫諸子百家,將其内在價值與現代社會對接,並兼以各門類學科知識進行創新性接受,以應對現代性帶來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基於文化層面,對子學思想的載體——‘士’階層的研究,並將這種研究與其個人實踐相貫通”,這啓發“新子學”的構建者去思考“如何挖掘諸子背後共通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力量,同時博采衆長,以適應時代風雲的瞬息萬變”(124)馮劍輝《錢穆的子學研究對“新子學”的啓發》,載於《“‘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6年。。前文提到一些學者曾以司馬遷、章太炎作爲“新子學”的典範,該文繼承這一思路,發掘了錢穆子學研究中與“新子學”相通的理念,使“新子學”理論構建又多了一個典範。而且該文在分析錢穆子學研究的同時,亦着力於思考“新子學”構建應如何對其借鑒,並指出了明確的路徑,這些都值得我們去認真對待、積極嘗試。
之前,林其錟先生和張雙棣先生曾提出過“雜家精神”來助力“新子學”核心理論的構建,張涅先生沿此方向進一步探索,提出了“新雜家”的想法。在《新雜家: 新子學發展的一個方向》一文中,張先生對“新雜家”在“新子學”探討中出現的可能性進行了論證。他指出“‘新子學’的發展歷程與春秋末至漢初的子學思潮有相似之處”,並通過回顧晚周學術變遷,使我們看到“雜家是子學發展的必然”。那麽再回顧“新子學”的“歷程”(125)按: 此處取“新子學”的廣義内涵,張先生認爲民國時期興起的以先秦子學元典爲基礎的思想流派都是“新子學”。,可知“一百年來新儒家、新墨家、新法家等都以一家學説爲基礎,難以適應現時代的思想要求,需要綜合各家的思想因素加以發展。這與秦漢時期雜家的方式方法相近,可謂之‘新雜家’”(126)張涅《新雜家: 新子學發展的一個方向》,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B2-1~B2-13。。該文還對“新雜家”構建的原則進行了設想,提出了“陰陽性”、“實用性”、“綜合性”的要求,進一步增强了新雜家實踐的可能性。張先生描述的“新雜家”着眼於新時代各派思想的共通性、整體性,它是否能成爲“新子學”未來的形態,以及如何避免之前雜家的覆轍,這都是值得學界探討的話題。
歐明俊先生撰有《論作爲“新子學”核心資源的莊學理念》,該文將《莊子·天下》中的“道術”理念視爲“新子學”理論構建的最核心資源,文中指出“‘古之道術’爲‘古人之大體’,是對宇宙和社會、人生的根本性、整體性把握”,倡議學者“在‘道術’整體體系中研究‘新子學’,重視大本、大原、大體,追求學術的本源性、根本性和整全性”(127)歐明俊《論作爲“新子學”核心資源的莊學理念》,《諸子學刊》第十五輯。。另外,文中還用莊學的混沌思維、整體思維、相對思維、否定思維呼應了子學思維,用莊子的自由精神、批判精神、擔當精神呼應了子學精神。莊子是先秦諸子中極具特色與超越性的思想家,莊學亦是融匯了千年來中國學術的各方面智慧,對於“新子學”的理論構建是一筆寶貴財富。尤其是歐先生在其中抽繹出的“道術”理念,呼應着“新子學”對學術研究整體性、渾融性的追求,其價值不容忽視(128)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學與“新子學”之間的關係在該階段逐漸受到學者的關注,賴錫三先生也撰有專文討論臺灣新莊學與大陸“新子學”,其着眼點也是《天下》篇,而其關懷則落於學派間的多元與溝通的問題上,下節對此將詳細介紹。。
前文中還提到了一些學者注重思考“新子學”理論中的一些基本構成元素,其中討論較集中的當屬“多元”這個概念。在這方面,本階段一些學者也進行了深入分析。劉濤先生《平等多元: 從“我們的經典”到“新子學”》一文將“新子學”與李零先生“我們的經典”著作系列相對照,從中發掘出二者的相通之處,即“重歸古典、復興子學”。而具體來説,兩者對於“復興子學”都强調了其中的“多元”精神。故而文章指出“要復興子學,必須擺落經學的一元思維,大力弘揚諸子間及其内部所包含的平等多元思想,爲諸子學的復興培育一塊良好的精神土壤”。同時,在面對西學時,這兩種主張也都傾向於多元主義,作者認爲: 一方面,“須主張多元,提倡包容,抛棄專制獨尊的經學思維”,這樣才能發展子學使中國傳統和西學更好地對接;另一方面,“須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文明與野蠻,方能使二者和平共處,齊頭並進,這正是多元主義的主張”(129)劉濤《平等多元: 從“我們的經典”到“新子學”》,《諸子學刊》第十五輯。。這裏主要是强調在西學面前保持文化獨立性。此外,還有吴劍修先生《被遺忘的現實: 對於經學化思維的反思——以“新子學”的多元意識爲起點》一文,該文通過經學與子學的對比突出了子學的多元特質,文中認爲“經學思維的一個弊端在於,它在體驗現實之前就意圖用一套完美的理論體系去規範現實,從而導致了思想的僵化”。這裏的“經學思維”不僅包括傳統經學,還包括當代中國學界普遍的弊病,即“對西方理論的崇拜”,這也被視爲另一種“經學思維”。故而作者指出:“‘新子學’提倡多元精神,就是讓思想回歸現實,並從多維度去體驗現實,以期能够讓我們在對現實的體驗中實現某種價值的回歸。”(130)吴劍修《被遺忘的現實: 對於經學化思維的反思——以“新子學”的多元意識爲起點》,載於《“‘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6年。這兩篇探討“新子學”多元特質的專題論文,相比之前學者的論述,思考的角度更獨特,探討的層面更深入,並對“多元”在“新子學”理論體系中的價值作用進行了細緻闡發,這些都能够啓發學界在這個問題上的進一步思考。
(二) 對“新子學”基礎性問題的新見解
“新子學”基礎性問題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本階段在這方面的探討亦出現了一些新見解,值得我們注意。
揣松森先生《論“新子學”的内涵及其意義——兼談子學與經學之别》一文對“經子尊卑”的傳統觀念從新的角度進行了辨析,他提到:“典籍傳言‘經’用簡長二尺四寸,‘傳’半之,‘子’不盈尺,就是説根據内容的重要程度高低而用簡長度逐次殺減,可是從目前出土的竹書來看,也找不出這種差别和區分,所以這種説法很可能是後世儒者理想化的一種形態。”(131)揣松森《論“新子學”的内涵及其意義——兼談子學與經學之别》,《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 3期。這裏他引用現代出土文獻作爲實證,有助於我們回到最原始的學術生態中,重新估量經、子的價值,進而革新我們的觀念,爲“新子學”的發展開闢更大的空間。此外,該文還對“新子學”的意義從兩方面進行了剖析:“‘新子學’提出的原生態學術文化研究方式,爲中國學術文化研究本土化提供了一條出路,將是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一條出路;而‘新子學’所提出的‘子學精神’則根於人心,既是對中國傳統精神的提煉,又與當今時代精神相契合,可以承擔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價值功能。”(132)同上。這説明“新子學”一方面作爲一個學術理念,發揮着學術新範式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作爲一種思想理論,亦可以發揮價值導向的功能,爲社會各領域的實踐貢獻智慧。該文分别剖析了“新子學”對學界、對社會的意義,並且在這兩方面的探討都非常詳細,很具有參考價值。
李洪衛先生在《論經學、新子學與哲學的當代並立——從當代中國思想學術與文化建設相互關係的視角考察》一文中,將“新子學”與哲學和經學並置於當代中國思想格局中對比考察。文章首先區分了“禮序”和“理序”兩個範疇:“對社會秩序的期待是一種‘禮序’的求論,而禮序則源於理序的思考與研判,對‘道’或‘理’的探究是根本”,由此便可區分經學與哲學和子學的差異:“子學和哲學更多地顯示了思想活動本身的特性,它的現實要求是開放性、包容性,而經學則偏重於對社會秩序的規範性。”故而作者對經學、哲學和“新子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有着不同的期待: 關於經學,作者認爲“我們當從‘重建斯文’即‘禮樂文明’而不是‘禮制文明’的角度看待未來經學在社會秩序建構和學院建制中的位置”;關於哲學,作者指出“鑒於我們在整個歷史文明進程中‘説理’意識和訓練的嚴重匱乏,哲學思維對中國未來文明的建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關於“新子學”,作者强調“從‘求道’的層面看,‘新子學’作爲承接中國古代前賢對宇宙探索的再出發也是一個特别值得鼓勵和繼續努力的方向”(133)李洪衛《論經學、新子學與哲學的當代並立——從當代中國思想學術與文化建設相互關係的視角考察》,《人文雜誌》2017年第5期。。總體來看,作者認爲哲學與“新子學”之間的同質性更强(文中提到“新子學和哲學則是對‘道’的開放性的探究,它又是構成理序和禮序的思想前提”),經學則處於與兩者相對的位置,這與之前李若暉先生的論述形成了有趣的對照,李若暉先生認爲:“近代經學沉淪,子學復興,但復興後的子學棄經學而附哲學,於是中國傳統義理之學的固有格局與内在脈絡被打散,當代‘新子學’的建立,必須與經學相結合。”(134)李若暉《熔經鑄子:“新子學”的根與魂》,《諸子學刊》第十三輯。顯然,李若暉先生此處將“新子學”與經學並置於哲學的對立面。其實,“新子學”在哲學和經學之間的這種分合之争,其實質上反映了“新子學”的多面性(135)此外,兩位學者對“經”的不同理解也造成了這種分合之争,李若暉先生文中開頭便强調“經爲大道之所在”、“經爲中華傳統文明之核心”,這是將經學視爲真理載體,而李洪衛先生則認爲“僅就儒家的經學來説,它的規範性意義大於它的文化提升性意義”。,也許“新子學”未必就要有確定的歸屬,它應兼收哲學、經學之長,完善自身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從這方面看,李若暉先生和李洪衛先生的論述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陳鼓應先生對待子學和經學的態度則更爲開明,他指出:“當今時代,多元文明的觀念成爲常識,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經學、子學的高下作爲前提,也不必拘泥於六家或者九流之説。《詩》《書》《周易》是周人遺教,而《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以及《春秋經傳》《禮記》《易傳》都是諸子的著作,都可以視作先秦基本經典。這些經典是不同思想源頭融匯的成果,不應該分高下,也不應當存門户之見,而要一視同仁,觀其會通,這樣才能有一個通達的瞭解。這該是‘新子學’的氣象。”(136)陳鼓應《放眼世界,開拓“新子學”》,《名作欣賞》2017年第3期。陳先生看待傳統文化的眼光更加高遠,他提出的“‘新子學’氣象”理應成爲我們對未來“新子學”發展的期盼。
楊中啓先生亦采用了新穎的視角闡述了“新子學”的内藴,他撰寫的《“新子學”新解》一文分成了“新”、“子”、“學”三個部分展開討論,闡發了很多新見。關於“新”,他指出“問題意識與時代内涵是子學常變常新之關鍵”,具體來説,“‘新子學’之新就突出體現在對當下時代問題的中國式表達,是諸子問題意識在現代的迴響,也是我們重新理解自身境遇的現代起點。”關於“子”,楊先生對“什麽類型的人可以被稱爲子”這個問題進行了自己的總結:“首先,是人格獨立、精神自由”;“其次,是具備超凡的能力和獨到的見識”;“最後,諸子是對社會的發展無比關心的群體,是對文化的進程最爲牽掛的對象”。而關於“學”,則涉及了“新子學”範疇的問題,楊先生在認同筆者看法的基礎上,又有自己的補充:“個人覺得限制子學的範圍的確有些不妥,今日學術門類之分割、專業分工之密切,已經無法達至古人百科全書式的理解與掌握,故各領域各學科但凡取得成就而有思想之論皆可爲‘學’。”(137)楊中啓《“新子學”新解》,《載於“‘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6年。這個意見針對的是筆者《“新子學”構想》一文中“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録均不在子學之列”這一論斷,至於這兩種觀點哪種有利於“新子學”的發展,這需要學界進一步的討論。此外,楊先生還提到了“學”應有“對時代問題的真思考”、“不尚一統而貴多元共生”兩個特質,這些見解亦非常深刻。
徐志嘯先生《關於“新子學”的思考——以莊子學爲例》一文也闡述了對“新子學”内藴的獨特理解。對於“新子學”,徐先生認爲“它的根本特點在於新,要透過詮解、闡釋、分析,體現其在哲理和意藴層面的新意”,具體來説“‘新子學’與舊子學的不同,區别就在於從今天宏觀理論的立場角度,看待和分析、解釋子學中的實在内涵及其附加意義”,文中又以莊子學爲例,在現代社會的視角下,分析了“其在宇宙、世界、人生層面的藴含,以及其文學性的價值表現”(138)徐志嘯《關於“新子學”的思考——以莊子學爲例》,《諸子學刊》第十五輯。,這爲“新子學”展示了很多值得探索的空間。
陳成吒先生則對“新子學”自身定位問題作了進一步探討。“新子學”在新國學中應該處於什麽位置,這是“新子學”自産生伊始就被熱烈討論的問題,尤其是《“新子學”構想》一文提出“新子學”成爲“‘國學’新主體”(139)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的説法,這更是催生了無數話題。陳成吒先生《論國學觀念的歷史與重築及其“新子學”》一文則從國學觀念這一具體角度對此進行更深入闡發,該文討論了國學觀念的歷史及當前的重構工作,由此將“新子學”定位爲這個過程中重要的重構維度之一。作者指出“‘新子學’理念的提出與發展自然立足於一個更大的文化大地與時代背景,那便是‘國學’觀念的歷史及其當下的重築”。之後正文着重討論了國故學和國粹學對國學觀念的不同闡釋,既而指出在當前應在這兩種立場外開出一條新路,這時“新子學”便能發揮它的作用,具體來説,“對國學的結構、内容、方法等進行重新認識與建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構經、史、子、集四維,將它們從經學思維和體系中解放出來,轉化爲子學精神下的‘新子學’體系,且一新而四新,帶出新的經學、子學、史學、文學。由此而來在方法上也形成由經學範式到‘新子學’範式的轉變,包括考據、義理與詮釋學的結合,版本學與文本學的融合等”。同時,在這方面,作者還將“新子學”與“新經學”等對應理念進行的對比,指出“在此之前,新經學、新文學、新史學等各有倡議,不過在基本精神上或不離國粹舊見,或陷於國故窠臼,在具體建構上也局限於一維,未能真正實現‘一而多’的整體性認知與實踐,自然無法帶出系統性的新國學。‘新子學’則完全正視這些現實,並將自身作爲四維中根本性的重構維度而出場,將其精神貫徹在整個國學之中,一新而四新,帶出全新的國學”(140)陳成吒《論國學觀念的歷史與重築及其“新子學”》,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D2-1~D2-14。。從這種對比中,我們更能體會“新子學”在新國學體系中的特殊角色,對它自然會有更高的定位。
還有馬明高先生撰有《“新子學”與人類共同價值的建構》一文,着重探討了在“人類共同價值建構”方面“新子學”所能發揮的作用,文中將這種作用歸納成了“敬畏自然,愛護地球,‘天人一體’的宇宙觀”,“講信修睦,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的世界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和之道’的協調智慧”等七點。馬先生的這些歸納從“宇宙觀”、“世界觀”到“思想智慧”、“價值取向”(141)馬明高《“新子學”與人類共同價值的建構》,《諸子學刊》第十五輯。,可謂是由抽象的本源到具體的指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之前學界探討“新子學”意義多着眼於它對中華文明的價值,馬先生的論述則將其拓展到世界文明的層面,這説明一套有價值的理論不僅是屬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且還屬於整個世界、全體人類,它所藴含的道理具有普遍適用性,值得各國人民共同分享。
該階段還有一些文章探討了關於“新子學”研究的方法路徑,亦值得我們認真參考。歐明俊先生《跨界會通——論“新子學”的創新途徑》一文將“跨界會通”作爲“新子學”研究開展時重要的導向,而且作者理解的“跨”不僅是當前熱談的“跨學科”,還包括“跨越時代疆界,古今貫通,通古今之變”,這意味着“‘新子學’研究的目的不是爲古人,而是爲今人。當下發生的許多問題,皆可從古代諸子學中汲取智慧來解決”。歐先生還提出“新子學”應“跨越學術路徑,會通傳統的義理、考據、辭章、經濟之學”,這是從傳統學術的視角理解“新子學”的“跨”。文中亦爲“跨界會通”設定了基本要求和理想境界:“跨界會通要求學者會通衆學,通大義,識大體,作大判斷,破除藩籬,得其全,成其大,走返本開新之路,彌合學術分裂”,“跨界研究,目的不在於跨界本身,而是追求會通,追求‘見森林’式的整體學術,成一家之言,追求思想深度、理論高度,這是理想境界的‘新子學’”(142)歐明俊《跨界會通——論“新子學”的創新途徑》,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B1-1~B1-17。。關於“跨學科”、“通古今”、“並通義理考據辭章”這些理念前人在探討“新子學”時都或多或少地提及過,但多過於零散、不成體系,歐先生該文將它們提煉爲“跨界會通”的原則,更加具有統攝性,很精準凝練地指出了“新子學”研究的特色,“新子學”想要推出有創新性的理論成果,很有必要參考歐先生“跨界會通”的建議。
劉韶軍先生提出“新子學”的整合研究與歐先生的主張頗有妙合之處。在《論“新子學”的整合研究及其拓新意義》一文中,劉先生指出“整合研究就是全面地綜合一個時代的不同思想(諸子各家)的全部内容進行完整的關聯研究”。“先秦諸子是思考與回答同一個時代的共同問題的産物,所説有不同,所思則相同”,這是劉先生主張對諸子進行整合研究的最主要原因。劉先生又結合《莊子》研究作爲實例,展示了他整合研究的具體思路,其中包括對某一子的“内部整合”研究以及對各家學派及整個時代思想的“外部整合”研究。並且作者還對此進行歸納,認爲“整合研究方法就是强調通過比較而加以鑒别,只有通過多方比較,才能形成更爲深入而全面的認識”。在闡述的過程中,劉先生還引用了錢穆先生、張舜徽先生、李澤厚先生、陳鼓應先生等前輩學者的研究方法作爲例證,以説明“這種方法本來就是學者默然心會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該文則是“對這種研究方法的步驟和過程以及它的學術價值集中而明確地加以闡述”。劉先生用明晰詳實的操作和例證爲我們演示了諸子學中的整合研究,本身就是“新子學”的一個典範,對“新子學”學術開新意義重大,相信如他所言,“從内部整合到外部整合的不同層次,就是‘新子學’研究中的一條拓新之路”(143)劉韶軍《論“新子學”的整合研究及其拓新意義》,《諸子學刊》第十五輯。。
關於“新子學”的方法路徑問題,相關的文章還有劉思禾先生的《現代諸子學發展的學科化路徑及其反省——從胡適、魏際昌到方勇》。該文將“新子學”放置在現代諸子學的發展脈絡下來理解,作者指出“諸子學在現代社會的學科化,是進入到現代學術體系的路徑”,既而正文分三節論述了20世紀三代學人的諸子學研究路徑:“一、 胡適: 現代諸子學學科化的發端”,“二、 魏際昌: 先秦散文史形式下的思想史研究”,“三、 方勇: 諸子學的正名及現代學術形態的探索”,並總結認爲:“胡適最早建立了一個諸子學的學科化範式,魏際昌對此體系做了若干修正,而方勇則反思這一體系,倡導回到諸子學自身傳統之中。”其中,“新子學”的很多理念都被視作對這一體系的反思: 比如作者引用《“新子學”構想》中批駁民國子學研究的語段,指出“方勇對諸子學現代學術形態的反思,集中在對於近代以來以西方學術來比附上”;再如文中摘引《再論“新子學”》中强調探索中國性的語段,指出“不同於胡適以西方模式來組織哲學史,或者魏際昌以散文史形態講述思想史問題,方勇更自覺地回到對原始語境與原始問題的追問上”;此外,文中還摘引《三論“新子學”》中討論以“新子學”對治現代性的語段,指出“方勇還特别强調了諸子學的價值意義,這是在胡適、魏際昌之外,對於諸子學一種價值上的肯定”。文中最後指出“如果諸子學發展必須帶着學科化的鐐銬來跳舞”,爲了保證“其内在思想的原發性和表達方式的現代性”,可以有兩種思路來應對,第一種是“‘諸子學’自身作爲學科”,第二種則是“不拘泥於學科之名”,而是强調其“確切的理論性”,那麽,“新子學”正是沿着這條理路進行探索,這在文中有具體的論述:“諸子學是一個複雜的體系,不過追求理論性當是其核心。哲學史研究加强了諸子學的理論品質,但是代價是喪失了諸子學的問題意識。把諸子學的理論思考重新校正回到自身‘確切’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域之中,這或許是解決諸子學學科化問題的辦法。方勇關於‘新子學’的論説提供了一些線索,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144)劉思禾《現代諸子學發展的學科化路徑及其反省——從胡適、魏際昌到方勇》,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C5-1~C5-36。。劉先生的文章將“新子學”作爲新一代學者諸子學研究的新形態,在與前輩學者成果的對比中能發現自身的突破,同時文中提及的前輩學者所存在的問題也成爲寶貴的經驗警醒着“新子學”對於研究路徑和方法的選擇。
(三) “新子學”的多維延展與實踐構想
經過學界之前的探討,“新子學”超越了原有範疇,進入了許多新的領域貢獻出自己的智慧,使自身的枝條有了多維的延伸。在第三階段,學界更注重“新子學”在某些領域的深度交融互動,其中取得的成果亦頗爲豐碩。
1. “新子學”與傳統文化的傳播
前文提到了“新子學”研究與“現代文化”的交叉,在該階段又有很多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進一步探索。郝雨先生撰有《“新子學”與現代文化: 融入與對接》一文,作者將“新子學”視爲“我們的現代文化發展的總起點”,作者認爲“新子學”可以解決當今文化界“斷裂論”和“西化論”兩派關於“新文化運動”的争論,“因爲,傳統文化並非只有儒學一家。‘新文化運動’斬斷了獨尊一家的專制傳統,如今復興傳統文化,必溯百家之源”。基於此,作者提出了“現代文化”的理想狀態:“我們必須建立起如同當年百家争鳴繁榮局面的一個新時代。因此,我們未來的文化發展,必須要多元,必須要百家。唯如此,我們的民族文化才能永遠充滿活力,這就是‘新子學’構建的最爲重大的現代文化意義!”(145)郝雨《“新子學”與現代文化: 融入與對接》,《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3期。郝雨先生這篇文章更明確地指出了“新子學”在“現代文化”中的地位和意義,並參考“新子學”的理念爲“現代文化”的發展路徑作出了詳細的規劃,這種探索是很有價值的。
張永祥先生《中西方視野觀照下的“新子學”》一文則着眼於中西方文化的對比,探討“新子學”如何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建構中發揮作用。該文從“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實用理性”在中西方不同的發展情況來切入,指出“無論是牽惹我們無限鄉愁的價值理性,還是價值理性卵翼下舉步維艱的實用理性,都不過是成也儒學,敗也儒學”,故而“我們需要重新導入源頭活水,把獨立自由、活力無限的諸子學重新納入到‘再造文明’的工作中來”。之後該文便分析了子學在古代和當代的發展狀況,並提出了對“新子學”發展的建議,該文指出“它(‘新子學’)最終關注的是如何實現與現實世界的良好互動,如何促成東西方文化和諧共生,如何安頓我們的心靈。這種互動和安頓,並不是處心積慮地改造我們的實用理性以接近西方的工具理性,也不是回到宗教價值理性的立場而排斥實用理性的勢利與冷漠,而是超越東西文化之争後對人類未來的深沉思索”。張先生基於中西文化的本質特徵來探討“新子學”和當代文化的互動,更具有歷史積澱和世界格局,他提出的設想雖然高遠,但的確反映了“新子學”對當代中國文化的一種期盼,這是一個方向,激勵我們不斷前進,正如該文結尾所説“發揮子學在參與國家軟實力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構築中華民族永恒的精神家園,將是‘新子學’永恒的理論關切”(146)張永祥《中西方視野觀照下的“新子學”》,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C2-1~C2-17。。
在“新子學”與“現代文化”的交叉研究中,最矚目的成果當屬“新子學”與“文化傳播”之間的結合。在2014年學界便發起了以“‘新子學’與現代文化: 融入與對接——新媒體時代‘子學精神’傳承與傳播”爲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在2016年學界又舉辦了“‘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兩次大會都是以“新子學”的視角審視現代語境下文化傳播的問題,吸引了很多傳播學界的學者積極參與。
夏維波先生將新媒體時代“子學精神”的傳承問題表述爲“三個民間”的見解。“第一民間”强調“子學下鄉”,這一過程伴隨着崇高化與世俗化兩種看似對立的傾向;“第二民間”强調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中間型”空間性的特徵,即知識分子既是王官之學的維護者,又是民間之學的傳播者,認爲“新子學”應有明確的自我定位;“第三民間”則强調民間之學的異質性和多元性應得到保障,以維持民族的文化反省能力。文化反省需要思維工具,一種文化是否先進,應看其有無文化反省的工具,而中國的知識譜系有這樣的工具,儒、釋、道一體文化譜系具有一種發展的自洽性。(147)毛冬冬、劉凱《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探源與經典傳播——“子學精神”傳承與傳播研討會綜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夏先生認爲,以上三點都是符合新媒體時代媒介發展特徵的。
景國勁先生則認爲有三種精神是在新媒體時代的傳統文化傳播最需要具備的: 一是創新精神;二是參與精神;三是對話、平等、多元的思想(148)同上。。這些都與“新子學”中藴含的“子學精神”相通,“新子學”在這方面的影響值得深入探討。
王艷玲女士則從新媒體時代信息碎片化的問題談起,認爲文化經典作品應該放下身段,借助新媒體的多元路徑,在内容和形式上適應現代文化的旨趣,在一定程度上順應當前公衆獲取信息與知識的習慣。既而她指出“新子學”在傳播自身時也要符合這一趨勢(149)同上。。
朱劍卿先生《淺議新媒體時代“子學精神”與經典文化的傳播》一文對於“新子學”傳播的問題亦持相近的觀點,文中指出:“‘新子學’的提出引發了新一輪對經典傳統文化的思考和探討。其重大意義不容否定,但在新媒體語境下,傳播界如何完成對其高效的傳播值得探討。”該文系統論證了經典文化與新媒體之間的内在契合性,使“新子學”與新媒體結合的可行性得到印證,既而强調了這種結合需要注意的幾點地方: 第一,要符合新媒體特性,即“短、平、快,有新意和趣味的内容才會在新媒體上受到歡迎”;第二,規避新媒體“娛樂化”、“浮躁氣”的弊病;第三,合力辦大事,“合力”是指“集政府、資本、社會之力”,從而“建立起知名的文化傳播品牌,帶動出强大的經典文化向心力”;第四,注重互動,新媒體具有互動性,“新子學”在傳播經典文化時便可利用這一點,從而“及時地知道民衆對於現有傳播的態度,而後及時地調整自己的方向,逐步讓國民在最大程度上接受經典文化”(150)朱劍卿《淺議新媒體時代“子學精神”與經典文化的傳播》,載於《“‘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6年。。
王飛先生重點就“新子學”如何適應時代的需求和新媒體環境下“新子學”如何接地氣的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任何一個學術概念乃至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現實環境,而在新媒體環境下,“新子學”如何“接地氣”的問題值得傳統文化的研究者和傳播者思考。王飛先生談到圖書館中大量子學經典及各代學者所做的“集注”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太過艱深晦澀,而且人們對於這樣大部頭的作品是會産生閲讀心理障礙的。在新媒體環境下,如何把傳統文化中的經典作品以讓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表現出來,讓大家更容易去接受,這就是一個“接地氣”的問題。從歷史上來看,越簡單的學問越容易爲人們所接受。他舉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的例子,認爲在佛教諸多宗派中,净土宗之所以能够廣泛流行就是因爲净土宗專修往生阿彌陀佛净土法門,教義簡單,修行方法簡便,人人都能做到,故自中唐以後廣泛流行,而當今文化經典的傳播也應該對此有所借鑒(151)毛冬冬、劉凱《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探源與經典傳播——“子學精神”傳承與傳播研討會綜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
以上學者多就“新子學”如何在大衆中高效傳播進行了探討。此外,還有一些學者關注到了“新子學”對於信息時代新危機的對治作用。劉曉民先生指出了信息時代所出現的“信息洩露、網路暴力、網路倫理失控、人的異化等危機”。他認爲“中國古代‘子學’對於解決信息革命時代的難題有着豐富的思想資源,如敬天尊道、道法自然、重道輕器、重義輕利、慎獨修身、仁恕之道、反求諸己等”。故而在文中他呼籲大家來“挖掘繼承子學的核心精神和思維方式,利用新時代的學術標準和社會特點構建富有時代特色的‘新子學’以解決信息革命時代的人類危機”(152)劉曉民《信息革命時代與“新子學”》,載於《“‘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6年。。該文從信息時代的危機着眼來説明“新子學”在現代傳播中的價值,論述的視角比較獨到,可以説是在該領域又開闢了一片探索的天地。
謝清果先生的論述視角同樣很獨到,他將傳播學中的内向傳播理論與子學中的心性之學結合起來探討,結論頗有新意。他首先指出了“‘新子學’之‘新’在於以子學爲接引的思想資源,再造在當代的‘百家争鳴’。爲此,當重建子學時代的基本命題,亦即在學科融合發展的背景下,深化子學時代的思考”。這一闡述體現了謝先生跨學科的廣闊研究思路,而該文中所嘗試重建的“子學時代的基本命題”便是“心性之學”,爲此他引入了内向傳播理論視角以實現“學科融合發展”。該文以道家“見獨”理念展開探討,作者發現,“‘見獨’正是道家自我認知、自我反省、自我升華的内向傳播活動”(153)謝清果《新子學之“新”: 重建傳統心性之學——以道家“見獨”觀念爲例》,《人文雜誌》2017年第5期。,具體來説,它的運作機制是道我對俗我的召唤,俗我以道我爲鏡子來修身養性,而在這過程中,通過内觀、心静如鏡的一系列内向操作過程,終究能讓心靈焕發“天光”,以促成“俗我”向“道我”的轉化。可見,“見獨”觀念清晰地呈現了道家内向傳播活動是如何運作,及其怎樣營造良好運作的環境條件,作者將這種相通之處細緻地呈現出來,爲老子學説發掘了當代價值,也爲西方傳播理論找到了中國文化上的契合點,這種探討讓我們看到了中與西、古與今、人文與社科這些對立的範疇之間存在許多互通交匯之處,它們正是我們“新子學”要努力開闢的學術新增長點。
2. “新子學”對現實生活的關懷
筆者在《三論“新子學”》一文中提出,傳統文化研究的創新需要“唤醒價值”,這意味着我們提出“新子學”要與當下現實密切結合,而且這種結合不僅限於理論層面的解釋,還要給出實踐層面的指導,具體來説,“新子學”要創造一些直接對現實生活産生影響的事物,以此實現“唤醒價值”的目的。已有一些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他們對“新子學”的探究不純以學理爲目的,而是特别貼近當下人們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等領域,因此這些成果的預設接受者也由原來的學者群體擴展至社會各方面人士,“新子學”的現實影響力也隨之擴大。
“子商”概念的提出與探討屬於這類成果中比較突出的一項。早在“新子學”理論構建的第一階段,鄭伯康先生《“子商”構想》一文便率先提出了這一概念,他首先指出了“子商”與“新子學”之間的關係:“‘新子學’是把握子學發展的必然規律與時機後,對它所做的進一步開掘,‘子商’就是在這種精神照耀下,把諸子系統的思想精華與現代工業文明進行完美交融後律動出來的商道文化。”這一概念的提出亦與之前的“儒商”有某種對應關係,具體來説,“儒商”精神與當今社會發展並不完全適應,比如:“儒家思想中‘親親之愛’的家族觀念有着結構性的限制,其‘私相授受’和‘任人唯親’的思想觀念,與現代股份制企業的股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都是難以融合的。”所以作者指出“這就要求我們去構建集百家智慧又兼具現代性和世界性的‘新子學’和‘子商’思想體系,並作爲當代企業新的文化使命”。而“子商”在範疇上,則“顧名思義應當包括‘儒商’在内的所有諸子思想的精華”。由此可以看出“子商”對於“儒商”的超越性和相容性。同時,作者還説明了“子商”面對西方文化時的態度:“‘子商’作爲現代經濟體系下的商道文化,必須系統研究西方成熟的企業管理理念、流程控制體系、國際運行規則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同時也要優化我們自身有特色的實踐經驗,不盲信别人、不菲薄自己,以百倍的民族自信去迎接任何挑戰。”作者最後在總結時指出“‘子商’的商道文化就是‘新子學’思想在經濟領域上的綜合體現”,並且“‘子商’商道文化將隨着‘新子學’的發展而發展”(154)鄭伯康《“子商”構想》,《諸子學刊》第九輯。。該文奠定了“子商”的基本概念和定位,它産生於“新子學”理論構建第一階段,爲之後學界的探討和商界的應用打下了基礎。
在第二階段,鄭伯康先生又圍繞“子商”展開了進一步探討,撰成《再論“子商”》一文,正如《再論“新子學”》追求爲“新子學”填充主幹理論一樣,鄭先生該文的論述亦是致力於應答一些實質性問題,比如他在文中分别討論了儒、墨、道、法等家對於商道文化的具體理論貢獻(155)詳見鄭伯康《“子商”再思考》,《諸子學刊》第十三輯。,這類探索賦予了“子商”實質性的内容,讓它有了明確的理念和主張,從而爲之後的實踐鋪平了道路。由此,我們可以説“子商”是“新子學”與現實發生互動的重要連接點,它對諸子學智慧在現代的轉化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
到了第三階段,則又有鄭作先生所撰《以諸子思想之源建構企業文化之魂——“新子學”精神與商道文化的對接與融合》一文,該文的探索推進到了“企業文化”這一專門領域,正與本階段“延展枝條”的追求相呼應。作者憑藉對商業領域的諳熟,探討了許多超乎學理層面的内容,比如他在討論馬雲“實事虚做,虚事實做”的企業文化時,結合了馬雲讀《道德經》大發感懷之語的例子,指出“馬雲的話就是諸子思想與現代商道文化最好的注解,馬雲的英語和太極這兩崑崙,是鑄就其商業帝國的基石,也暗合了‘坦然面對西學’、‘承載國學真脈’、‘紮根傳統文化沃土,促進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的求真務實的‘新子學’精神”(156)鄭作《以諸子思想之源建構企業文化之魂——“新子學”精神與商道文化的對接與融合》,《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3期。。這種探討極有針對性與現實性,對於商業領域的人士有直接的啓發意義,能切實指導他們構建企業文化的實踐,而這便是“新子學”發揮其現實影響力、構建“價值典範”的重要途徑。
上述學者在經濟商業領域的探討側重於影響當今人們的物質生活,還有一些學者的嘗試則是追求切實地影響人們的精神生活。宋洪兵先生撰有《重建我們的信仰體系,子學何爲?》一文,該文着重於“探討當代中國重建信仰體系的過程中,作爲國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子學所具有的理論價值與現實功能”。這一課題的確切中了當下中國人的心靈需求,一直以來,作爲學者,我們都强調理性,也希望將這種精神普及給大衆,但宋先生指出:“信仰與理性不必二元對立。所謂‘信仰’,並不意味着交出自己的理性,而是對某種價值或境界擁有深切而執着的情感灌注。”這就强調了我們的研究不能再限於學理層面,而是要直面現實給予人們心靈關懷,實現與大衆的情感溝通而非完全的道理説服,説到底,這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宋先生結合着子學,將信仰進行了層次的區分:“宗教信仰,境界信仰和包括法律信仰在内的規則信仰。三種信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信仰體系。三者之間,前二者事關幸福,後者事關公正。……國學領域的道教、佛教組成宗教信仰,儒家與道家構成境界信仰,法家則專注於規則信仰。三者互動,對於當代中國信仰體系的重建,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意義。”(157)宋洪兵《重建我們的信仰體系,子學何爲?》,《諸子學刊》第十三輯。宋先生此處提出了“規則信仰”,討論了它和法家間的關係,這一探索極有創新意義和時代價值,它契合了現代社會法制化的趨勢,也針對着當代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問題和精神困境,現代的信仰體系有了它才會更完善。“重建信仰”是一個現實課題,“新子學”可以沿着該文的思路,依據當前的核心價值觀,爲解決這一問題貢獻更多的諸子學智慧。
黄蕉風先生《告别路徑依賴 構建大乘墨學——“新子學”視野下的墨學發展進路》一文則結合“新子學”爲“大乘墨學”的推廣、實踐作了更具體的構想,他指出“‘現代新墨家’在墨學之外的公共領域所能發出的聲音着實少得可憐”。面對這一現實,黄先生提出“當代新墨學的新生轉進,必須告别過往墨學研究的路徑依賴,轉向更深層次的義理新闡發,使墨學‘大乘化’,從而‘現代化’”。具體而言,“以墨學義理來介入宗教對話、全球倫理——即墨學的‘大乘化’;在回應社會熱點和當下議題上,大乘墨學則有自信進入憲政民主、普世價值等公共場域,建構一套脱離儒家言説傳統的墨家叙事方法——即墨學的‘現代化’”(158)(香港) 黄蕉風《告别路徑依賴 構建大乘墨學——“新子學”視野下的墨學發展進路》,《諸子學刊》第十三輯。。該文中黄先生構想了“新墨學”與現實熱點問題對接的方式,這對“新子學”如何“唤醒價值”未嘗不是一種啓發。
“新子學”兼有“承接傳統”和“貼近現實”兩種色彩,這使得它對當代大衆有着一種獨特吸引力,其影響範圍自然不會局限在學界中,上述文章已經體現了它在這方面的潛力,還有更多的事例可以説明它的影響已波及更大範圍。比如,在2014年的河南中原名校高考全仿真模擬考試中,語文試卷的出題者摘引《“新子學”構想》作爲閲讀題目,考察學生對於相關概念及論述的理解和辨析,這至少説明教育界人士已瞭解到了“新子學”的存在,並對其中藴含的價值觀念持認可態度。
總之,從“子商”到“大乘墨學”,這些極有實踐意味、現實色彩的構想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便會對我們的生活産生切實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新子學”將繼續探索,爲這些實踐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持,而隨着這個過程的深入,相信“新子學”也會深入到現實生活中,最終迎來“燦爛的花期”和“果實收穫季”。
(四) 在大陸學界之外影響的擴大
1. 相關成果的回顧與展望
在2016年之前,關於“新子學”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大陸學界内,期間有港、澳、臺等地及韓國、新加坡等國的學者參與“新子學”學術研討會、撰寫相關論文,加入到了大陸學界的討論中,總體來看“新子學”的影響還是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的範圍内。但從2016年開始,“新子學”的影響開始超出中國大陸的範圍,這主要表現在中國臺灣地區及韓國將於2018年6月召開的“第六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歐美學界針對“新子學”的回應文章。鑒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與中國大陸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新子學”的探討呈現出了一些新的面貌,故而此處專列一節對此展開介紹。
2016年10月,臺灣屏東舉辦“2016‘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0月,臺北舉辦“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2017年11月在上海舉辦的“海峽兩岸‘新子學’座談會”,幾次會議中,臺灣地區的學者對“新子學”展開了積極的探討,其中一些文章與發言頗能反映臺灣學者對“新子學”的獨特理解,以下擇其要者略作介紹。
賴錫三先生撰有《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合觀與對話——學術政治、道統解放、現代性回應》一文,賴錫三先生是臺灣地區“跨文化臺灣新莊子學”的中堅學者,該文便是“嘗試描述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基本精神和類似觀點”。文中認爲“兩者皆批判學術政治化所造成的一元獨尊,並嘗試恢復學術多元自主性的衆聲喧嘩”,其中,“不管是先期的王官學,還是漢後獨尊儒術的經學,或者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化儒學,以及港臺新儒家的心性道統論,皆被放在一個批判考察的位置上”。作者總結了大陸“新子學”和臺灣新莊學的共性:“大陸‘新子學’和臺灣新莊學,皆企圖解構‘以一御多’的文化中心論、本質論、主幹論,並由此解構而走向學術自由、文化多元的多音複調。”在正文中,作者從三方面對比了這兩種理論:“一、 學術與政治的分合辯證;二、 ‘以一統多’到‘多音複調’的道統解放;三、 通古今之變與通中西之變的現代性回應。”在“學術與政治的分合辯證”方面,作者主要分析了大陸新儒家和港臺新儒家關於學術與政治間分合的争議,但也指出了他們之間“類似性堅持”,即“以儒學道統作爲中國文化的主流根幹地位”,而大陸“新子學”和臺灣新莊學則“齊聲質疑‘以一統多’的道統論,主張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内在多元性甚至内部他者性,百家争鳴的多元並陳與互文生長,才是中國文化能保有創發精神的思想活力之所在”。在“多音複調”方面,作者首先“從巴赫金‘多音複調’、‘衆聲喧嘩’之文化轉型理論,闡釋‘新子學’回歸諸子百家、思想多元的主張”,進而又以《莊子》的《天下》篇來呼應“子學精神”,指出感歎“道術爲天下裂”的《天下》篇其實是“憂心諸子之間没有真正朝向多元對話來敞開(不能相通)”,“而《莊子》在《齊物論》的兩行觀點,才真正隱含‘對話理論’的多元性、差異性主張”,這一節中作者追求用“文化轉型”這一概念“讓巴赫金、《莊子》、‘新子學’三者産生有意義的觀察連結”,這種溝通與合觀是很有創見的。在“現代性回應方面”,作者討論了兩種理論面對跨文化的混雜現代性時如何通古今東西之變,作者大致認爲大陸“新子學”將“重點放在古典語境的‘返回自身’之重建工作上”,“持中國優位觀,有東西細微二分的前見”,而臺灣新莊學則“釋放了文化本質與國族主義的思考方式”,“主張由跨文化機遇來更新轉化傳統,從而産生内外語境交織的混雜現代性”,但對這種差異,作者仍秉持其所主張的“兩行”態度,認爲“學者依憑自身之學術訓練之側重面,分頭努力,相互加乘,只要持續保持彼此開放的對話態度,將來或有更深度相互交織的新共識”(159)(臺灣) 賴錫三《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合觀與對話——學術政治、道統解放、現代性回應》,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A4-1~A4-24。。該文通過對比近年來兩岸興起的兩股類似思潮(“新子學”、新莊學),揭示了一些深層的理論訴求,反映了兩岸理論界一些普遍的意向,同時,通過與臺灣新莊子學的這種“合觀”和“對話”,“新子學”也更鮮明地突出了自身的特質,對自身理論建構大有裨益。
賴先生通過“合觀”、“對話”很好地把握到了“新子學”的核心精神,而殷善培先生《開闔破立: 論“新子學”的願與違》一文則致力於評析“新子學”的整體框架和具體觀點。該文對《“新子學”構想》《再論“新子學”》《“新子學”申論》等文章進行分析,歸納出“新子學”理論的内在理路,進而沿着這條理路就一些具體的觀點進行評析,涉及的相關問題包括“子學精神”中的多元特質是否存在、如何面對各學派之間彼此争勝的情況、是否該反對具有通人之學特質的四部分類標準、是否該嚴格區分諸子與方技、如何面對經學傳統、如何面對現代學科體制以及如何面向世界,等等(160)(臺灣) 殷善培《開闔破立: 論“新子學”的願與違》,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B4-1~B4-8。。對於這些問題殷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在文中形成了很多處觀點的碰撞,這爲之後兩岸學界進一步的探討創造了很多對話的焦點。
臺灣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曾昭旭先生撰有《爲“新子學”定性定位》一文,這亦是一篇闡發了獨到見解的重要文獻。該文定性、定位“新子學”遵循着很清晰的思路: 首先以“新儒學”的定義作參考,所謂“新”,“是指對西方文化之衝擊有何回應之道”;而所謂“儒”,是指“能回到生活世界作實踐的回應,藉回歸生命人性之根源(即所謂‘道’)以解決生命與文化失本而造成之困局”;既而討論經子關係,“經者常也,即指人性之普遍常道”、“即‘人性之善’”,並且“只能以‘即事説理’的方式表示”,而“所謂事,又可有偏於理與偏於情之分,子部即人之生活言行中偏於理性思考或專顯理性思考一面之表現也”,“子部著作便是將實存於生活中而本質不可説的道,轉爲可説之理而予以表出”,可見曾先生將經作爲常道統攝史、子、集三部,子部是經部“常道”的表現與“即事説理”的補充;在此基礎上,“新子學”便被定性定位,所謂“新”在於對西方學術的回應,“實即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會通”,而所謂“子”,曾先生則從三點論述其特殊性格,如“即經即子之身份”(可理解爲“即整體渾全之道而凸顯其理”),“善用辯證思維”(即“靈活出入於道物之間終證成其即爲一體之思維方式”),以及子書編排的獨特(所謂“各篇皆可獨立,但内涵又可相互呼應滲透涵攝”)(161)(臺灣) 曾昭旭《爲“新子學”定性定位》,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A1-1~A1-8。。曾先生和殷先生一樣,比較重視“經”的價值,並論述了“人性之普遍常道”來籠括經、子、哲之間的關係,這與之前一些學者的觀點形成了對照,可以説是一種比較獨到的理解,很值得我們重視。
以上幾位學者文章中涉及的問題也是會議中學者討論的焦點,各家立場不盡相同,相互之間的觀點産生了精彩的碰撞。在經、子關係的問題上,不同於曾先生以“常道”區别經、子的想法,經學研究名家林慶彰先生在座談會中認爲“傳統中經學、子學之間的隔閡可以打破,就是不要刻意去立異。經學、子學都是春秋戰國時候社會思想混亂的反映。假如把它們當作先秦時代的材料來看的話,雖然有出入,但是都奠基於當時的社會文化,《論語》《孟子》今天也可以看作是子書。”(162)劉思禾《對話“新子學”——兩岸“新子學”系列學術對話紀實》,《光明日報》2018年1月13日第11版。再如“常道”與“新子學”的問題,楊祖漢先生也有與曾先生不同的看法,認爲:“儒家的道統被視爲人生日常生活中的常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些都是我們義務上該做的。儒學講究常道、道統,‘新子學’似乎就不能再將道統當作指導原則,其指導原則要定在道家的思想上。道家所謂的道是以無作爲普遍的原則,無便是去掉,把有意的、有爲的、故意的、偏見的想法,或者希望用思想壟斷控制人的想法通通無掉,剩下一個自然而然、空蕩蕩的、順應變化的生命。這種普遍意義的道可以作爲‘新子學’超越的指導原則。”(163)劉思禾《對話“新子學”——兩岸“新子學”系列學術對話紀實》,《光明日報》2018年1月13日第11版。楊先生在儒家的“常道”外又引入了道家的“道”與“新子學”相融通,與此相近,當代臺灣新儒家代表人物王邦雄先生是通過《莊子·天下》來對“新子學”展開思考,以此把握諸子百家的整一性,他提到:“今天我們講‘新子學’,是一家一家地講還是采用其他辦法?我認爲可以按照《莊子·天下》篇的意思,讓諸子百家回到原來的神明聖王整體是一、道術整全的大傳統中去,這樣才能各得其所,走向文化的整合,創造美好的未來。”(164)同上。
賴錫三先生文中提到“通古今中西之變”的問題(165)詳見賴錫三先生《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合觀與對話——學術政治、道統解放、現代性回應》文中第三節“臺灣新莊子學與大陸‘新子學’的通古今東西之變: 跨文化的混雜現代性”。,這也是會議中學者多次談到的話題。林明照先生認爲:“無論是港臺‘新儒家’還是‘新子學’,面對東西方文化都有一種二分的預設,這種二分似乎會影響東西方之間的理解和對話,‘新子學’作爲對傳統學術範式的革新,這些固有觀念也是值得它去反思的。”(166)劉思禾《對話“新子學”——兩岸“新子學”系列學術對話紀實》,《光明日報》2018年1月13日第11版。方萬全先生則提到諸子研究中一個“機會主義”的方法,指出:“無論是概念的取得還是理論的使用,只要適合所要研究的對象,無論古今中外,都可以拿來運用。”(167)同上。方萬全先生强調他對於中西學術的匯通持有樂觀態度,呼籲大家對於西方理論大膽接受,如果出現問題,自然會有後人糾正,這也正是學術發展的過程。高柏園先生也認爲文化交流和衝擊會産生一些變動與思潮,“新子學”對這些無從反對也無須反對,關鍵在於有没有可能不受制於西方的觀點,用自己的觀點來理解。而何乏筆(Hebel Fabian)先生則進一步質疑“新子學”是否能回歸“中國性”,他認爲現在的我們要面對跨文化語境的挑戰,所謂“跨文化”就是能通古今中西之變,看到這四種文化元素在演變中的複雜交織,而這種情況和現代性結合,就涉及了所謂的“混雜現代化”,尤其是在中國等非歐美國家表現得更爲典型。那麽,何先生質疑,什麽叫作以中國爲本?中國在百年來選擇了西化的路線,那麽這時“新子學”倡導以本土爲主,這又將是一個怎麽樣的“本土”(168)何先生的相關論述可參考劉思禾《對話“新子學”——兩岸“新子學”系列學術對話紀實》,《光明日報》2018年1月13日第11版。?以上幾位先生在這一問題的立場上與賴先生有相通之處,在潛意識中似乎都認爲“新子學”對待西方學術文化有些“保留與保守”(169)賴錫三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新子學”有“中國優位的關懷與東西細微二分的前見”,故而似乎“對‘即中國即世界’的非二元論之跨界文化交織,顯得相對保留與保守”。,大陸“新子學”研究者劉思禾先生對此有相關回應,他認爲“新子學”對文化傳統内有一個多元性的判斷,同時也不放棄對“中國性”的堅持。他指出在中國思想内部,的確存在着不同的脈絡,進而形成多元的格局,承認這種格局是“新子學”有别於後世經學、儒學的一個基本特點,這是和臺灣“新莊子學”接近的地方;同時,“新子學”並不接受進一步的推論,即當代的文化關係可以跨越文明體的界限,而在全世界的思想語境下做無限制的交流會通。反而,“新子學”認爲基本的文化邊界需要維繫,“中國性”仍舊是一個必要的術語。故而,作爲“中國性”的一個新解説,“新子學”對文化内部資源來講是一個解放,而對外部文化資源則意味着某種堅守(170)相關内容請參考劉思禾《對話“新子學”——兩岸“新子學”系列學術對話紀實》,《光明日報》2018年1月13日第11版。。總之,劉先生强調“新子學”對於西方學術的態度是一種謹慎的開放態度,而根本上則致力於當代中國文化認同的建構(171)方達先生也有類似回應,他主要是針對賴先生的觀點進行了理論的對話,並進行了詳細論證。本文將其置於下面“不同理論間互動與對話”一節中進行詳細介紹。。相信“新子學”的一些主張能給臺灣學者在相關問題上帶來一些新的解讀方式,正如會議主辦人王俊彦先生所提到的,“臺灣近幾十年來的學術一直在西方學術的影響下,現在需要回歸中國傳統,‘新子學’提出的重建諸子學傳統的主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視野,有助於豐富臺灣學界的研究”(172)劉思禾《對話“新子學”——兩岸“新子學”系列學術對話紀實》,《光明日報》2018年1月13日第11版。。
總之,會議中臺灣學者們對“新子學”的獨到闡釋再次説明了“新子學”在新的文化背景中會得到新的討論,從而引發新的話題,促進兩岸學界的進一步交流,並讓“新子學”在這個過程中完善自身理論,這正是“新子學”走出大陸、對話港臺、面向世界的意義所在。
除了對話港臺,“新子學”同樣是面向世界的,尤其是在第三階段,其國際化趨勢更加明顯,在韓國、新加坡等國,很多學者參與了“新子學”的討論(173)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嚴壽澂先生撰有《“新子學”典範——章太炎思想論綱》《新諸子學與中華文化復興》系列文章,再如韓國圓光大學姜聲調先生(筆名淩然)《“新子學”與跨學科學術研究鳥瞰》《在韓國如何推廣“新子學”》,以及韓國成均館大學曹玟焕先生《“新子學”與“狂”的現代意義》,還有韓國國立江陵原州大學金白鉉先生《21世紀“新子學”與新道學的研究課題》,都從獨特的視角討論了“新子學”。,“新子學”在那裏已經有了一些基礎,而在2018年6月份,韓國還會召開“第六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届時會有更多新的聲音在“新子學”這個平臺上出現,相信“新子學”理論由此會得到進一步豐富。
甚至遠在歐美學界,也對“新子學”理論有所回應,德國海德堡大學Viatcheslav Vetrov先生撰有專門的討論文章——China’sNewSchoolofThought-Masters(Xinzixue):AnAlternativetoSinologism?(《“新子學”: 漢學主義的替代者?》)。本文核心的理論關懷在於探討認同建構(identity construction)與政治表態(political statement)之間的關係,該文指出:
The present study defends the idea that any discussion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identity constructions, any act of drawing boundaries, as any criticism against drawing them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political statement and that they become every time problematic when they are accompanied by an explicit negation of politics or when they are not reflected upon as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本文捍衛如下觀念: 對於任何認同建構的討論,任何劃定邊界的行爲,以及對這種劃界行爲的批評,這些都可以視作爲一種政治表態。因此,每當展現出對政治立場的明確否認,或者並未反映出已經介入政治,這些研究每每都會出現問題。)(174)Viatcheslav Vetrov.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 (Xinz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J]. Asiatische Studien, 2016(03).
基於這一視域,該文展開了對當前中國相關理論流派的論述。正文第一節PartⅠ:Fromorientalismtooccidentalism(一、 從東方主義到西方主義)討論了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在中國的接受情況,該理論傳入中國後,中國學者相應地提出過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對薩氏説法批評、修正,典型研究如張寬、王銘銘等學者的文章;正文第二節PartⅡ:Sinologism:Afarewelltopolitics(二、 漢學主義: 與政治告别)則評述了在這方面更加典型的研究,即顧明棟先生關於漢學主義(Sinologism)的批評;以上研究都是上文所提到的因爲“出現對政治立場的明確否認”而“每每都會出現問題”的“認同建構”研究,正文第三節PartⅢ:Xinzixue:Fetchingthestonesfromtheothermountain(三、 “新子學”: 取他山之石)則分析了“新子學”在這方面比較客觀恰當的立場,這正呼應着本文的標題:“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Xinz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具體來説,作者認爲“新子學”能以恰當的姿態對待西方學術文化:“The dialectical turn of the xinzixue-advocates opposes any blind adoption of foreign identit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promotes the idea, according to which good knowledge of foreign identiti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one’s own successful identity building”(“新子學”倡導者主張辯證轉化(175)所謂“辯證轉化”是指“新子學”主張正視、熟悉“西方”這個文化上的“他者”能幫助中國文化更好地反觀自身,促進“自身認同”的建構,該文主要通過分析玄華文章的觀點對此進行説明,詳見該文PartⅢ第四段,此不贅述。,反對盲目接受西方認同,但同時,他們又推崇這樣一個觀點,把握好西方認同對於成功建立自身認同非常重要),同時作者也認爲“新子學”對知識和權力、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有着較明晰的認識:“Common for them all is also the awareness of the political component pertaining to discussions on national identity. The academia does not appear as something politically neutral or independent of political issues, nor as participating in a conspira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but as a subject of an open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issues.”(同樣地,他們都意識到,討論有關民族認同時總包含着政治性内容。學術界既不是政治上的中立者或者獨立於政治議題之外,也不參與到知識與權力間的合謀中,而是作爲公開討論政治問題的主體。)如何看待中西文化間的互動及知識權力間的關係是作者關切的核心,是他用來評判文中各類學説的標準,在他看來“新子學”在這些方面較之之前同類理論有着較大突破,故而題目中用“替代者(Alternative)”一詞表示自己對“新子學”的期許。
總體來看,該文是以“認同”(identity)與“政治”(politic)爲主線貫穿全篇,由此分析對比一系列的學術現象(如對東方主義的批判、對西方主義的批判、對漢學主義的批判及“新子學”運動等),該文引言對這一思路有較爲鮮明的、概括性的表述:
Since the early nineties, Said’sOrientalismhas remained a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orientation in the discussion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on their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global context. It is a big paradox that many of the studies, which rely heavily on Said and take the issue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as a matter of politics, are also very critical of Said. On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se criticisms is that, turning against various epistemic distortions produced by Western scholars about China, they simultaneously try to neutralize the political side of their own position, to overcome politics, to make it non-present. Such attempts are either implicit (as in the case of Wang Mingming’sTheWestastheOther:AGenealogyofChineseOccidentalism, 2014) or explicit (as in Gu Mingdong’s various critical studies on Sinologism.) The present study means to call into question the advisability of these attempts. It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 Masters (xinzixue 新子學),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urrent movements in the Chinese academia. If Gu Mingdong, who stresses the necessity for scholars to reject political concerns, takes his monograph on Sinologism to be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present study raises the question, if the proponents of the xinzixue, who rather suggest the impossibility of such a rejection, are on their part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a more plausible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自九十年代初期以來,在中國知識分子全球化語境中討論自身文化認同時,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保持着重要的指向作用。然而非常吊詭的是,許多研究非常依賴薩義德的理論,並將他者視作政治對象來看待,同時又非常嚴厲地批判薩義德。這些批評者的一個典型特徵是,他們反對西方學者在各種中國認知上的曲解,同時又嘗試使自己處於中立的立場,以此來克服政治,使之不在場。這種嘗試或是暗示性的(如王銘銘的《西方作爲他者: 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或是明確的(如顧明棟對漢學主義的各種批判性研究)。本文意圖對這些做法的合理性提出質疑。本文最終的論述涉及到“新子學”的討論,這是當下中國學術界最重要的學術運動之一。如果説顧明棟强調學者拒斥政治關懷的必要性,並以他的漢學主義論著取代東方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研究,那麽本文的問題便是,當“新子學”的支持者更傾向於認爲拒絶政治是不可能的事,那麽“新子學”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取代漢學主義的新選擇。)(176)Viatcheslav Vetrov.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 (Xinz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J]. Asiatische Studien, 2016(03).
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是西方學界的熱點,該文以此爲基本視域探討“新子學”的意義,這一思路較爲獨特,對我們極有啓發。一直以來研究者在相近的文化圈中討論“新子學”,雖然熱鬧,但格局容易被局限,路徑容易導向偏執。該文從西方學術的立場,以一定的距離審視這場中國的學術運動,自然有山外看山的效果。
2. 相關特徵的總結與評析
上文對於近期大陸之外的“新子學”研究成果主要選擇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内容進行介紹,這些研究呈現出一些特徵,它們可能會是今後“新子學”向外拓展時經常會遇到的狀況,故而下文嘗試對它們進行總結,以期更好地幫助“新子學”走向更廣闊的天地。
(1) 客觀描述與主觀解讀並存
“新子學”對於大陸以外學界來説還是一個較爲陌生的概念,故而這些學者談論“新子學”時,大多會對“新子學”發展的情況作一個簡要描述,如殷善培先生指出:“近年來,‘新子學’後來居上,短短數年内引發數百篇討論文章,衆聲喧嘩(heteroglossia),成功引領了當代學術史上的熱議及反思。這一現象當然與催生者方勇教授的當仁不讓、一肩承擔的使命感有關,更重要的是方勇‘新子學’有相當完整的論述與實踐策略,開闔破立之間,結構佈局嚴密,各種挑戰與詰難其實多不出方勇教授的設想。”(177)(臺灣) 殷善培《開闔破立: 論“新子學”的願與違》,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B4-1~B4-8。賴錫三先生亦給出了自己的描述:“據筆者初步觀察,方教授個人對‘新子學’的論述仍在持續深化演變中,而大陸諸多學者彼此間的觀點,則是同中有異、深淺互見。看來這股思潮的勢頭雄健,但也仍在摸索發展當中,還待時間醖釀其深廣度與成熟性。但不可否認,這股思潮具有革新企圖,帶有一股清新氣象,其基本思想的批判性主軸乃可以清晰辨識。”(178)(臺灣) 賴錫三《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合觀與對話——學術政治、道統解放、現代性回應》,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A4-1~A4-24。Vetrov先生論述時亦涉及了他對“新子學”發展現狀的認識:“Within the current Chinese academic landscape, a special attention deserves a large movement, which during the last four years has found supporters all over China, and even far beyond China — the xinzixue, or: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放眼中國當代學術界,有一種重大學術運動值得關注,它在過去四年中在中國各地甚至海外都贏得了支持者——這就是“新子學”,即中國諸子研究的新學派。)可見,這些學者對“新子學”的成果都有着較爲客觀的描述,對於“新子學”的前沿動態有着一定的瞭解。
除了客觀描述“新子學”發展狀況,爲了方便讀者的理解及自身觀點的闡述,大陸外的學者還會針對“新子學”相關文本進行解讀。這些解讀中有從局部到整體的歸納(179)如殷善培先生在分析《再論“新子學”》一文後便對“新子學”的内在理路進行歸納,指出“由上述扼要歸納就可知方勇教授對‘新子學’相關的議題是經過透徹的認識且深刻的反省,所以能從‘子學現象’尋繹出‘子學精神’,再由‘子學精神’深化爲‘新子學’主張。從兩個框架跳脱,一方面破除尊經傳統的制錮,一方面解開西方學科思維中對中國傳統的曲解。再以全新的姿態面對西學回應世界”。,也有對具體語詞作以小見大的闡發(180)如Vetrov先生文中的一些語句頗有代表性:“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use of rhetoric of health, as in the case with the critics of Orientalism and Sinologism,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one’s own program as an epistemological restructuring.”(他們之所以和東方主義及漢學主義的批評者一樣都使用“健康”這個修飾語,是因爲他們將自己的事業理解成一種認識論的重建。),也包括曾先生文中直接針對“新子學”命名而進行的全新論述。這些解讀則呈現出了一種主觀的視角。這裏所謂“主觀”,並非指視野的偏狹,而是説各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理論關懷,按照自己的理路來把握“新子學”思想的脈絡。比如曾先生以“常道”爲基礎解讀“新子學”中“新”和“子”的内涵,這體現了臺灣新儒學的理路,而賴錫三先生則强調了“新子學”對道統論的批駁,這體現了臺灣新莊學的理路(181)另外,賴先生對“新子學”還有一番獨到的觀察:“方教授對‘新子學’的呼籲,有三個連續性發展: 對《莊子》學史的長期學術史研究;主持‘子藏’編輯之學術文獻整理工程;由學術史與文獻整理再深入子學現象之闡發、子學精神之推動。筆者個人最有興味的是,莊學精神能否呼應於子學精神,甚至深化‘新子學’的核心主張。”這裏,更鮮明地體現了賴先生由新莊學理路來闡發“新子學”。。再如前文提到了Vetrov先生闡發“新子學”時基於“知識·權力”的基本視域,這有很鮮明的福柯理論的色彩。
這種現象有其必然性,並會在之後港、臺乃至國際學界討論“新子學”的歷程中一直存在。因爲與大陸學界不同,當代港、臺和韓、日、歐、美學界理論流派數量多,各自又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發展,學者大多已有自己的流派歸屬,再觀察“新子學”這種外來新理論時,必然帶有“前見”,由此形成富有個性的解讀。我們對此應理解,並積極吸收他們的獨到見解來充實我們的理論。這時,我們就需要繼續探討下一個話題: 不同理論間的互動與對話。
(2) 不同理論間的互動與對話
面對着大陸外學界的“理論叢林”,“新子學”必然要與不同理論流派展開互動與對話,這已經成爲“新子學”外拓歷程中的一個特徵。例如,臺北“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便被王俊彦先生稱爲當代的“鵝湖之會”,這爲我們展示了“新子學”在臺討論時各種理論之間互動的精彩程度之高與思想價值之大。
總體來看,這種互動一般以較明顯的方式呈現,比如Vetrov先生文中對東方主義、西方主義、漢學主義及“新子學”諸多理論的依次論述與對照,再如賴錫三先生將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合觀,並用大陸新儒學和港臺新儒學與兩者對比分析,還有曾先生借用新儒學的定義來定位定性“新子學”,這也是兩種理論的互動。
在這些互動的例子中,能形成對話的首推賴先生等學者關於“‘新子學’與新莊學合觀與對話”的探討。賴先生探討了兩者共同的價值訴求:“面對學術文化‘以一統多’的道統説主張,大陸‘新子學’和臺灣新莊學皆采取批判質疑立場,認爲歷史的扭曲現象,不能等於學術健全發展的合理性。”(182)(臺灣) 賴錫三《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合觀與對話——學術政治、道統解放、現代性回應》,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A4-1~A4-24。這一探討尋找到了兩派的共識,爲之後進一步對話創造了平臺。同時,賴先生在對話中也注重展現新莊學與“新子學”各自的獨特性,比如他提到臺灣新莊學還有“對‘語言權力’的批判反省”,他指出“從臺灣新莊學來看,任何一套言説系統本身,當它嚴密地環繞自我中心而居爲道統主幹時,這種學説便具有自我獨尊的封閉性格,將有妨於學術的豐富多元、兩行交織的差異化發展,並遠離諸子百家思想勃發之原創處境”(183)同上。。再如賴先生也分析了“新子學”與新莊學面對當代中西文化碰撞交織時的不同態度:“目前來看,方教授領軍的‘新子學’研究工作團隊,似乎以返回中國性的‘新子之學’爲主要工作目標,而臺灣的跨文化新莊學則以中國性和世界性的互文交織、以創造‘新之子學’爲主要工作目標。”基於這種差異,賴先生在“中國優位”和“多元開放”間矛盾的問題上對“新子學”提出疑問和進一步對話的期待:
方教授的“新子學”主張,在面對“世界性與中國性的糾結”這一跨文化處境時,除了明顯站在中國性的優位這一端,多少也仍然預設了(細微的)東西二分架構,亦即中國性與世界性的本末優次二分之架構。而正是這種中國優位的關懷與東西二分的前見,可能使得“新子學”在擺脱舊有理念束縛的“原創精神”,融會當代新理念的“處士横議”,以及中國學術如何進行世界性回應的“多元開放氣質”,容易停留在觀念上的呼求,並對“即中國即世界”的非二元論之跨文化交織,顯得相對保留與保守。如此一來是否使得“新子學”的果敢與回應當代的新文化轉型課題,在觀念與實踐之間産生徘徊猶豫與不易跨越的間距?這將是值得觀察與對話的課題。
這種疑惑同樣存在於臺灣新莊學另一位代表人物何乏筆(Hebel Fabian)的論述中(184)上文簡單介紹過何乏筆先生在這方面的態度,具體來説,他在會議中指出: 所謂“跨文化”就是能通古今中西之變,能看到這四種文化元素在演變中的複雜交織,而這種情況和現代性結合,就涉及了所謂的“混雜現代化”,尤其是在中國等非歐美國家表現得更爲典型。那麽在這種脈絡下什麽叫作以中國爲本?中國在百年來選擇了走徹底西化的路線,那麽這時“新子學”倡導以本土爲主,這又將是一個怎麽樣的“本土”?可以説,這個本土已經不是中國本質上的本土,它已經包含了很多西方的東西,這是一個混雜的“本土”。所以“以本土爲主”的主張,必須要把跨文化、混雜現代化等問題思考進來。。這涉及“新子學”理論自洽性的問題(185)尤其在賴先生看來,“新子學”堅持多元理念,這與新莊學相同,但“新子學”又堅持“中國優位”,將中國作爲叙述主體,理論本身存在對主體性的追求,“多元性”和“主體性”能否共存,這是他在學理層次上對於“新子學”的困惑與質疑。,需要“新子學”研究者的回應,從而形成一種深層次的對話。
方達先生針對這一問題做過較爲具體的回應,他認爲,“新子學”所提倡的中國“主體性”和“多元性”是一種需要深入辨析的概念。“主體性”意味着對中國作爲一個叙述主體的承認,“多元性”意在表達先秦諸子思想的基本形態,以及構成中國文明架構過程中的具體作用與意義;另一方面則是着眼中西文明碰撞的層面,尋求一種在此交互過程中凸顯“新子學”自身意義的價值立場。“主體性”和“多元性”如何溝通,“新子學”還需要在理論架構的層面上給予詳盡的界定與論證。既而方達先生提到,在賴錫三、何乏筆兩位先生看來,“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基本精神和觀點相似,都批判學術政治化所造成的一元獨尊,並嘗試恢復學術多元自主性的衆聲喧嘩,皆試圖解構“以一御多”的文化中心論、本質論、主幹論,並由此解構而走向學術自由、文化多元的多音複調。也正因此,兩位先生對“新子學”同時所堅守的“主體性”表示出疑惑: 在消解中國傳統思想舊有架構,認識到“混雜現代性”境遇中不得不面對的“多元化”的同時,“新子學”在學理層面上,如何可以宣稱自身具有“主體性”呢?對此,方達先生則指出,實際上,先秦思想的核心問題意識便是司馬談所説的“務於治”,而司馬氏所謂的“治”不僅僅是現實的社會治理,更反映了先秦諸子時代的基本文明形態,即先秦諸子對“人”與外在世界交互和諧狀態的普遍性追尋,而這種“交互”的方式又意味着作爲思維載體的“人”,始終對變動不居的現實境況保持相應的思考與解決的辦法。“新子學”對諸子思想的整體概括顯然已經跳脱出傳統的“經子關係”,在承認以“六經”爲代表的“繼承”與相應的“重構”具有相同價值的基礎上,諸子思想不僅在達成最終理想秩序狀態的方法層面上,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而且還在相互詰辯的過程中體現出對周文系統“主體性”的繼承。换句話説,雖然諸子在具體思想主張上體現出極大的差異性,但從未出現過對中國文明主體性的否定,而只不過是在達成方式上具有批判與反批判的“反思精神”。因此,“新子學”所説的“主體性”是站在中國文明的層面上,在認爲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型構具有不同形態的基礎上提出的,而“多元性”則是在特定文明内部的方法論的意義上展示出來。“新子學”的“主體性”與“多元性”在學術層面上的意義在於: 在堅守自身文明“主體性”的同時,對構成文明的學術思想始終保持一種反思與批判的態度,並由此相應地通過方法論上的“多元化”,規避“主體”自身的獨斷與僵化。如果直接以“去中心化”思維模式來觀看“新子學”,其所提倡的“多元”與“主體性”確實無法呈現出自洽性。但二者的問題在於,這種普遍化的“去中心化”思維模式,是否可以越出思維的界限,直接作用於實實在在的傳統經典文本之上,並由此得出相應的包含了對現實判定的學術結論。换句話説,這種“去中心化”的思維模式是否已經在“人”實際的運用過程中得到了反思與批判。正如《再論“新子學”》一文所説,這種没有共識的“多元化”就是缺乏自我批判的“多元化”,其到最後只能呈現爲一種完全碎片化,甚至虚無化的面貌。而對於“共識”中的“多元性”與“主體性”,“新子學”恰恰給予了自己的回答。
可見,在這種對話中,新莊學展現了自身獨特的學術主張,“新子學”也完善了自身深層的理論體系(186)此外,劉思禾先生也深入辨析過新莊學和“新子學”在中國性與世界性問題上的立場差異,很多内容也涉及上述問題,只是没有進行詳細論證,這在“相關成果的回顧與展望”一節有介紹,此處不贅述。,可以説是一種良性的學術互動。尤其是賴先生文中對於兩派相關差異性的尊重,更是值得我們學習,他認爲:“總之,當前面對中國性與世界性的争論課題,我們或許仍可學習《齊物論》‘和以是非’、‘以應無窮’的‘兩行’態度,讓‘新子之學’與‘新之子學’分工合作(187)按: 賴先生前文中曾提到“目前來看,方教授領軍的‘新子學’研究工作團隊,似乎以返回中國性的‘新子之學’爲主要工作目標,而臺灣的跨文化新莊學則以中國性和世界性的互文交織、以創造‘新之子學’爲主要工作目標。”故此處“新子之學”指“新子學”的思路,“新之子學”代指新莊學的思路。。學者可以依憑自身之學術訓練之側重面,分頭努力、相互加乘,只要持續保持彼此開放的對話態度,將來或有更深度相互交織的新共識。”(188)(臺灣) 賴錫三《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合觀與對話——學術政治、道統解放、現代性回應》,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A4-1~A4-24。賴先生的論述展現了學術對話中開放、包容的態度,“新子學”今後的研究也應該以此爲期許,對相關的評述及時地回應,並進一步展開與其他理論流派的積極性、建設性對話,在對話中尋找共識、理解差異,這不僅是“新子學”完善自身理論的必要手段,也是促進兩岸文化交流乃至代表中國思想在世界舞臺發聲的重要門徑。
(3) 中西文化問題成爲關切點
回顧以上所舉例文的主題,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新子學”文章中純粹討論子學研究革新的内容少了,討論文化問題尤其是中西文化互動及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内容多了。這種特徵的形成也有其深層原因,因爲“新子學”在外拓的歷程中將要面向的是世界性的大平臺,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互動甚至碰撞都是需要它正視的現象,故而中西文化問題在大陸外學界受到的關注更多,探討的視角更獨特。港、臺地區因爲歷史原因,中西文化的混雜性極强,該地學者討論“新子學”時一直將西方文化作爲一種核心關注。比如曾先生將“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會通”、“與西方哲學平等對話”作爲“‘新子學’所以爲‘新’之所在”(189)(臺灣) 曾昭旭《爲“新子學”定性定位》,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A1-1~A1-8。,而殷先生在論述“新子學”脈絡時,則將“新子學”的終極願景定爲“以全新的姿態面對西學回應世界”(190)(臺灣) 殷善培《開闔破立: 論“新子學”的願與違》,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B4-1~B4-8。,而賴錫三先生對於“新子學”面對中西文化時的態度則更爲關切,文中專列有一節進行分析,上文已經介紹,此不贅述。其實,諸位學者對西方學術文化的關切,從更深層次上講,最終是反映了他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當今發展這一問題的永恒思考。正如報道中所總結的那樣:“在此次系列學術對話中,兩岸學者體現出的開通和善意,是基於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對當代文化建設的熱忱。學者們都認識到,傳統文化研究既不能封閉自守,也不能以今釋古,而要在古典與現代之間作一種會通,爲建構中國文化認同提供助力。”王邦雄先生指出:“我們有幾千年的傳統,不是文化沙漠,讓西方文化如入無人之境,我們不能接受。大陸已經崛起了,我們期待大陸在世界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作爲中國人,大陸“新子學”研究者與臺灣學者都關切着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如何在我們這一代傳承,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正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正因爲有着同一個目標,所以上文提到各派對待西方文化態度上的差異不應成爲對話的隔閡,而應作爲一種資源互補、互見。
歐美學者則立足於西方文化來看待“新子學”,“新子學”被理解爲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明進行自身“認同構建”的一種嘗試,Vetrov先生將“新子學”放置於當代中國文化認同構建的進程中來理解:
The name xinzixue refers to the revival of ancient Chinese schools of thought and scholars (Laozi, Kongzi, Zhuangzi, Guanzi, Huainanzi etc.), who, due to the current global challenges for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course in the eight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conomic boom and the contrasting rather slow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 are made subject of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take a key position in the debates concerning China’s cultural identity.(“新子學”是指古代中國思想學派和學者(老子、孔子、莊子、管子、淮南子等)的復興。20世紀80年代改革以來,經濟初步騰飛和文化自覺意識發展相對緩慢,當前面臨全球化挑戰之時,諸子學在中國文化認同的論争中成爲思想闡釋的新主題,進而占據了重要的地位。)(191)Viatcheslav Vetrov.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 (Xinz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J]. Asiatische Studien, 2016(03).
The word new accentuates the important connections between this agenda, the current cultural identity problem, and the globalization consciousness (quanqiuhua yishi 全球化意識). The role of the xinzixue studies in the process of current Chinese identity building is explained in terms of cultural peculiarities pertaining to Chinese thought-masters of antiquity.(而“新”字强調了重視當代文化認同問題和全球化意識之間的重要聯繫。在當前中國文化認同建構中,“新子學”的研究旨在表明諸子學經典的文化特性。)(192)Viatcheslav Vetrov.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 (Xinz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J]. Asiatische Studien, 2016(03).
“文化認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每個國家都需要應對的挑戰,我們學者構建“新子學”理論也是致力於這一目標,只是對此没有專門明確的表述。Vetrov 先生致力於中西方跨文化研究,故而從“文化認同”這一角度來理解“新子學”(193)另外,該文也指出除了“新子學”外,參與當代中國“認同構建”的還有新儒學,它之前一直都是主導力量:“Whereas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ighties and 2012 — the year, when the first manifesto for xinzixue, Fang Yong’s 方勇 article ‘Xinzixue gouxiang’‘新子學’構想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 was published, — was marked by the so-called ruxue-fever and by the predominance of (Neo) Confucianism in various program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s.”(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2年——該年方勇教授發表了《“新子學”構想》一文,成爲“新子學”的第一份宣言——這段時間中,在各種中國文化認同構建活動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所謂的儒學熱以及新儒家的主導地位。),在“中國—世界”這一維度上探討“新子學”的意義,這種來自異質文化圈的審視能幫助我們反觀自身,啓發我們在之後的探討中更多地思考“新子學”如何幫助中國文化以一種恰當的姿態融入全球化浪潮。回顧近數百年的世界史,會感覺隨着地球“變小”,其内部各種文明逐漸接近、接觸乃至碰撞融合,譬猶地理學理論中不同大陸板塊之間經由獨立漂移轉而互相碰撞衝擊,這是歷史必然,中國人開始會驚異迷茫,但現在則勇於正視應對,“新子學”可被視爲一種應對的嘗試。所以,今後的“新子學”探討應進一步擴大自身的格局,以更好地面向世界發聲,更好地應對中西文化乃至世界多元文明間的互動與碰撞,這是“新子學”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以上對“新子學”五年以來的發展歷程作了大致的梳理,學界的探討還在繼續深入,“新子學”的理論建構還會迎來更新的階段,本文會繼續關注它的發展、記録它的成長,筆者相信“新子學”有着無限的生命力,這將是一篇永遠没有“結語”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