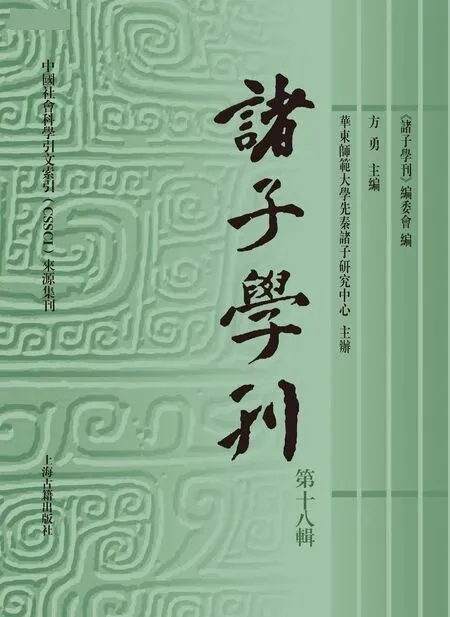無和有: 跨亞洲之眼
——老子的女性主義
(臺灣) 趙衛民
内容提要 諸子必有其哲學形態。道既先於天地而生,而且“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把道視爲谷神、玄牝,神秘的陰性成爲天地的根源。老子又常常自比嬰兒,故云“貴食母”,由母子關係取代父子關係,以是可論老子的女性主義。
關鍵詞 有 無 空虚 玄牝 母親 嬰兒 女性主義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跨歐洲之眼”讓他認識到“印度哲學是唯一與我們歐洲哲學平行發展的哲學”,而海德格爾(Martin Heidgger, 1889—1976)在某種程度上熟悉中國道家和日本禪宗核心文本的德文翻譯(1)[德] 萊茵哈德·梅依著,張志强譯《海德格爾與東亞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相對於他們而言,當我們研究老子時也必須有“跨亞洲之眼”。或許海德格爾藉以突破西方傳統形上學的,正是中國道家和禪宗;而運用海德格爾的哲學概念來詮釋老子哲學,也可使其概念思維更爲清楚。不僅是海德格爾,甚至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潮中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等在某種程度上屬於法國新尼采思潮的人物,也可以在概念上構建老子的思維。
《道德經》開篇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一章)
此章一般順着王弼注作解:“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也就是説可道可名不是本常的大道,道是不可道不可名的。道與名分居一、二句的主詞。如果道是不可道,名也應是不可名。如果一、二句的主詞是道,那麽名顯然是來解釋道的。我們總要記得《史記》中的記載:“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2)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台北興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141頁。著書爲説道和德,自隱無名當然是道德的根本要務。所以《道德經》第一章可能的説法也可以是: 道是可以言説的,但不是平常的言説方式;要言説道,就要給它命名,但也不是平常的名字。以“無”命名天地的開始,以“有”命名萬物的根源。王弼注曰:“凡有皆始於無。”這樣就提煉出“無”和“有”兩個概念,是用以對道來命名的方式;而且無通無名,有通有名。
不唯如此,常在無的心態,以觀察大道的奥秘;常在有的心態,以觀察大道的邊際。這樣第一章除提煉出無和有這一對非平常言説的概念來論述道以外,也提出了名言和欲望的問題。但不論是無、無名、無欲,或者有、有名、有欲,總歸屬於無和有這一對概念,“同出於道”,這才是“玄之又玄”。爲何?因爲無和有在字義上相矛盾。怎麽可以用字義上相矛盾的概念來指涉道?故而在第二章云: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天下皆知”是社會的常識背景,這裏對社會的常識背景似有批判的意味。社會的常識背景所提出的美、善標準,會轉變爲惡與不善。何以如此?尼采説:“任何地方‘高貴’,‘貴族的’在社會的意義中,是基本概念,由此必然發展出‘善’在‘帶有貴族的靈魂’,‘高貴’,‘帶有高級的靈魂’,‘帶有特權的靈魂’: 一個發展平行於另一個將‘普通’,‘賤民’,‘低下’最後轉化爲‘壞’(bad)的概念。”(3)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by Walter Kaufman, and R.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p.27~28.尼采認爲這是社會的偏見(prejudice),也就是社會定義的價值標準: 都包含着貴族和賤民,高貴與低下的判斷,好與壞就包含這樣的階級意識。尼采《道德系譜學》影響福柯等甚鉅。對於海德格爾,他的基本存有論也同樣形成對日常性的批判:“我們在一日常的方式下理解我們自己……不是從我們自己存在最極端的可能性來的連續性,而是不真實的,我們自己的行爲只是作爲我們而不是自己的,我們在事物中和人群中失落自己。”(4)Martin Heidgger, 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 trans by Albert Hofstadter,USA: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p.160.在日常方式下,我們在事物和人群中失落自己,我自己不再是我自己,而是“我們”,故而日常的理解是在人群中,是不真實的(not authentical)。這也同樣是對“天下皆知”的批判。
老子既規定有無互相生發,故有是無中有,無是有中無。也就是既然在天下皆知的常識背景中,美會轉爲惡,善會轉爲不善,那麽不如由天下皆知的常識的有回到無中;由有名、有欲的狀態回到無名、無欲。既然一雙對立的概念可以互相生發,互相産生,似乎動力的生發也主宰着一切對立的二元概念。這是在道論中或存有論中的生發關係。在我們日常的二元概念中是價值概念,含有階級概念。如尼采談的高貴與低下;但在老子以道的動力作旋轉軸,高與低互相傾軋,傾軋成爲高與低的動力裝置。難和易,長和短,前和後,這些都含有價值意義,並且前者壓倒後者,即上位概念壓制下位概念。至於音和聲,前者應是音樂,後者是聲響或噪音;音樂是上位概念,壓制聲響的下位概念。現在用道的動力隨着二元邏輯,以化成“成”、“較”、“隨”、“扣”的動力。
打破社會所定義的二元標榜。尼采是以韻律概念來説明兩者之間只有一種拍子的相異。而衆所周知,德里達提出“延異(differance)概念也是針對語言的二元邏輯。延異運動産生的不同與區别是標記我們語言所有對立概念的共同根源,僅舉幾個例子,例如感覺的/理解的,直覺/意義,自然/文化等。作爲共同的根源,延異也是這些對立被宣稱於其中的相同要素(與同一有所區别)”(5)Jacques Derrida, Position, trans by Alan Bass,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1, p.19.。所以德勒兹視延異是二元邏輯的相同要素,但視爲動力根源而不是同一。他舉的三個例子,理解的、意義和文化都是上位概念,而感覺的、直覺和自然都是下位概念,而延異既作爲二元對立的根源,那麽延異的動力亦可解消二元對立。
老子既知“有”的發展,也就是價值標榜的樹立會導致崩壞,“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所以由有轉入無中。現在無又是“無爲”與“不言”,相對而言,有就是“有爲”與“有言”。那麽體道的聖人在無爲和不言的狀態下,任萬物生長而不干涉,讓萬物生長而不佔有,爲了萬物而不自恃,成就萬物而不主宰。對萬物有功而不居功,正因爲不居功,所以才有功勞。這與日常生活的常識背景是有差異的,即“出而有,爲而恃,長而宰,自居其功”。佔有、自恃、主宰、功勞有“有爲”與“有言”上的發展,將破壞人爲樹立的價值標榜。
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三章)
佔有、自恃、主宰、居功歸結爲兩項: 尚賢和貴難得之貨,其一是對人的關係,其一是對物的關係。尚賢是使賢者有賢名,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著名黑格爾現象學研討班,利用海德格爾來詮釋黑格爾,卻成就了人類中心主義。“對我而言,他者是一種現象和客體;同樣,對他者而言,我也是一種現象和客體。這一鬥争最終通過一場統治權的戰鬥得以解決。柯耶夫對主奴關係和争取承認的鬥争的使用,幾乎毫無困難地適用於笛卡爾模式。”(6)[美] 伊森·克萊因伯格著,陳穎譯《存在的一代: 海德格爾哲學在法國1927—1961》,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0頁。簡言之,人類社會的精神動力就在於争取别人的承認而奮鬥到死,那麽就成爲自我與他人的生死鬥争。當自我成爲主體時,他人就成爲現象與客體;自我與他人易位時,就造成相反的現象。自我與他人爲争取承認而鬥争。崇尚賢能就帶來名聲,亦引發争取名聲(有名)的鬥争,對老子來説,難得之貨也是物的異化(alienation),是人爲的。物的使用價值對人是如此根深柢固,財貨更成爲佔有與争奪的目標。對人的關係是名,對物的關係是利;名利的根源在欲望。不顯現可欲之事,人心就不會受到激蕩而散亂。
聖人治理天下,顯然虚弱心智,而强調肉體。肚子吃飽而筋骨堅强,以保全生命爲第一義。心智對肉體的支配關係被顛倒,這是與《論語》可以作對比的。《雍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顔淵之賢是道德意識高,這是意識對肉體的支配,是忍受貧苦的“顔淵樂處”。老子卻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欲望的社會化,成爲社會意識追求的目標,反而使視覺、聽覺、味覺的自然本能全都受到人爲的社會局限而喪失。最後是貴族“馳騁畋獵”的高貴,對比於底層階級的低劣,人心受到社會意識的激盪而發狂。所以“常使民無知無欲”是爲了避免自我意識的擴張,欲望導致機巧,自我意識形成主體概念。老子批判主體概念,或許可以從尼采的批判找到原因: 這是一個術語,因爲我們相信統一在於實在最高感覺的不同衝動之下;我們理解這信仰爲一個原因的結果——我們在我們的信仰中如此肯定,爲了這原因我們想像“真理”、“實在”、“實體”各方面。主體是虚構,在我們之中許多相似的狀態是一個基礎的結果: 但是是我們首先創造了這些狀態的“相似性”;我們調整它們使它們相似才是事實,不是它們的相似性。——那毋寧是該否認的——(7)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by Walter Kaufman and R.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7, p.269.尼采認爲在實在高度感覺的不同衝動之下没有統一,而尼采和老子同樣認爲主體是人爲信仰的結果: 相信統一。故而此處不是反智論,而是反主體。
一、 何 謂 事 物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首先是工具或裝備。在這裏首先可以説明工具和裝備都是爲了人的便利,這就是有用,有利。但老子偏偏要把道的概念“無”和“有”套入工具和裝備中,打破日常生活的慣性思考。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十一章)
車輪中心必須空虚來容納車軸,這才有車的作用。搓揉陶土來做成器具,容器必須保持空虚的形態,才能有容器的用途。鑿門窗做成屋子,必須保持空虚,才有屋的用途。這是從我們的工具、裝備中找出無的存有論結構。最後的結論是有其便利,但無是使其保持空虚,才能有其用途。容器的空虚甚至成爲萬物的範型,包含人。《老子》二十一章:“孔德之容,唯道是從。”王弼注曰:“孔,空也。唯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8)《老子四種·老子王弼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孔是孔竅的空虚,容貌是從孔竅中的空虚浮現;無論如何,以空虚爲德,才可以道爲依歸。
海德格爾是將工具和裝備擴大爲工具物全體。“嚴格地説,並没‘有’這樣作爲‘一個’工具物的事物。工具物全體常屬於任一工具物的存有,在此中,工具物才能成其爲工具物。工具物本質上只是‘爲了’什麽的某物。工具物的全體是由多種‘爲了’的方式而構成,諸如可服務性、可管理性、可用性、可操縱性。”(9)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Macquarrie and EdwardRobinson,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p.119.“爲了”當然是爲了人的需要,爲了人要達成某些目的;任一工具物就有整個工具物全體的脈絡。在這多種“爲了”的方式,老子顯然着眼於“可用性”的用途。但有只是有工具的便利,用途或功用卻是由無來確保。海德格爾在日常世界中雖本以無來説明工具的存有,但卻以另一種方式來説明工具物的功能是作爲世界的模式。“發現一個工具物不見了,在海德格爾的解釋裏,顯露了工作實是作爲世界的模式。這擾亂使我們覺察到工具物的功能,和它適應於實踐脈絡的模式。”(10)Martin Heidgger, 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 trans by Albert Hofstadter, USA: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p.99.一個工具物不見了,就是不可用,無法使用,但隨之而來的是發現整個工具脈絡停擺。而這正是一個契機,發現“工作室是作爲世界的模式”。這裏的契機是存有論的,即是省悟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工具而工作,使我們對世界的了解是以工作室的方式,這是日常世界的模式。而事物在日常世界中不論對老子或海德格爾,首先皆是以工具或裝備的形式來到眼前;即使依海德格爾,我們以工作室的方式作爲世界的模式,我們會不會以看待工具物的使用方式來看待其他的人、物乃至世界?答案是顯然的。“不真實性是加强日常的自我主義,真實性是對它的減損”(11)Michael E Zimmerman, Eclipse of the Self, Athens: Ohio University, 1986, p.47.,那麽以日常的自我主義爲起點,就是一種以使用、可用的方式看待世界,還包含了可服務性、可管理性、可操縱性。
日常的自我主義,可以視爲道的前識觀。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三十八章)
前識是道所開展的花朵,也是愚笨的開始。薛蕙注此條云:“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乃道之華也。非以爲愚,而乃愚之始也。”(12)引自潘栢世編著《老子集註》,臺北龍田出版社1977年版,第71頁。你知道,我知道,他知道,這叫“前知”(pre-understanding),這亦可以用福柯的“認識體系”來説明:“把不同話語類型相聯繫,並與某一特定時代相對應的關係整體。”(13)[法] 朱迪特·勒薇爾著,潘培慶譯《福柯思想辭典》,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頁。顯然在老子時代的認識體系是由仁、義、禮所建構的特定時代的關係整體。日常的自我主義的感受是仁,仁落在人心上,由仁到義到禮是不斷加强的自我主義,也是大道不斷淪降的過程,是不真實的。義如是社會正義,正逐漸外在化,至禮爲止是社會所樹立的價值標榜如美和善轉向惡與不善的開始;忠信越來越薄弱,成爲天下大亂的開始。何以故?上文説:“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上禮如果以無禮來回應,上禮甩在一邊,以無禮來對應;這就成爲亂的開始。故日常的自我主義(仁)可以向前發展,也可以向後回歸。向後回歸是回歸於德,再回歸於道。這就是處於厚重,處於質實;不浮薄,不花俏。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治理國家仍從日常的自我主義開始;到天下大亂,美善的標榜已轉换惡與不善時,就不能再用正面的方法,而要出奇兵。忌諱的事太多,人民就越來越貧窮;朝廷太多利害的手段,國家就更加昏亂;人民更多伎倆,邪門的事物就孳生。這難道不是國家爲了“可服務性、可操縱性、可用性、可管理性”而使用它的人民嗎?在減損日常的自我主義下,以無的概念、無的工夫,我無所作爲而人民自己變化,我無所事事而人民自然富有,我没欲望而人民自然樸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十八章)
政治沉悶無爲,人民却可恢復淳厚;政治苛察精明,往往民不聊生。社會不斷發展,幸福所依托的是災禍,災禍又隱藏在幸福之後,這種變化是没有極點的。並没有正面的發展,正面變成奇邪,善良變成妖孽。人的迷惑,由來久矣。只知道增强日常的自我主義。所以聖人方正而不鋭利,清廉而不傷人,真實而不放肆,含光而不耀眼。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有道、無道是日常的自我主義回歸或向前發展。有道時,不讓馬馳騁疆場,却用來給田地施肥;無道時,連母馬也拉上戰場,只能在戰地生産小駒。災禍源自欲望不知滿足;最大的罪咎是佔有財物。增加的自我主義會帶來災禍和罪咎。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十三章)
寵辱是外在的聲名,在社會上生存的動力從精神上説是争取别人的承認,故而寵爲下。但從老子來看,二者俱是身外之物,故而與生存無關。身體是保存生命,故而要把大的災患視爲可能使身體遭致毁傷。我們之所以可能遭致災患,無非是來自有身體而産生的欲望。故没有私人的欲望,就是把身體寄托給天下。
重點是,如果老子以手邊的工具物或裝備均含有無和有的存有論結構,其他事物是不是也是如此?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
故道的動力在於反,所謂回歸,不是順着有的發展往而不返,而是由有向無回歸。道的發用在於柔弱,不是争强鬥狠,有是有中無。道的生發萬物,明含無、有、物三層,這是生發萬物的程序。而無和有也成爲物的存有論結構,柔弱是無中有,回歸是有中無。對人來説同樣是有無的結構,“‘人是懸擱到空無中’,或‘人是站在空無中’……人作爲一存有物,不僅站在存有的中央,也發現自己暴露在非存有物的可能性中。在此義上,他能超過他的事實面”(14)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Netherland: Martinus Nijhoff, 1982, p.391.。海德格爾和老子一樣,認爲人有無和有的結構。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六十二章)
道是萬物之奥秘,老子以無和有的概念來説明這奥秘。善人以此奥秘爲寶貝,不善人也靠這奥秘來保全生命。美好的言語有市場,尊貴的行爲可以加在别人身上;不善之人,又没什麽好抛棄的,我們仍可以學習如何去保全生命。這是“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四十九章)。不善者也有得之於道的特殊動力。雖有尊貴的爵位,貴重的拱璧和駟馬,都不如坐進此道。求道可以免去罪咎,而求道是回歸的求得。
致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静,是爲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
回歸的求道,要通過“致虚守静”的工夫,那麽虚静的工夫下在哪裏,無非是日常的自我主義。這是無化的工夫,以免日常的自我主義往有的方向往而不返。萬物生長動作,我用心觀察到回歸的現象,“復”就是回歸。這種觀察,即是沈思,顯然是因致虚守静的工夫而有,虚静是在心上作,減損日常的自我意識。這時才得以有一沈思,有一觀察;沈思和觀察到萬物都會回歸到生命的根源。如果把無放在主觀心境上來講:“依這心靈狀態可以引發一種‘觀看’或‘知見’(vision)。境界形態的形上學就是依觀看或知見之路講形上學(mataphysics in the line of vision)。我們依實踐而有觀看或知見;依這觀看或知見,我們對這世界有一個看法或説明。”(15)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版,第130頁。這種主觀的進路將使道由一個聖人來保證,看脱漏了“萬物並作”四字,换言之,不是由“一復”來保證“一切復”,而是由“一復”得以觀到“一切復”。萬物並作是在有中發展,萬物也定然回歸生命的根源。依照主觀的進路講老子,將使道没有客觀的實際意義。
萬物紛雜多樣,各自回歸到其根源;這表示萬物本有無的結構,不僅是人有無的工夫。在道家的主場,並非人爲萬物之靈,而是人是萬物之一。回歸到其根源,叫做静。動時説有,静時説無。回歸到自己個體特殊性,是回歸自己的命運,重複自己的命運。很奇怪的,這個體特殊性並非個人的風格,而是在個人之前的根源。“只有隨着尼采,依德勒兹,單義性的快樂,才被適當地思考,和這是因爲尼采想像了一個‘先個人的特異性(singularity)’之世界,及没有‘誰’或‘什麽’有許多特質;也没有某人或某物是或存在(is),每一差異不同的力量,没有差異事件成爲任何他者的根據或原因。必通過這差異的肯定,而且的放棄任何在差異之前的根據或存有,尼采和德勒兹達到了永恒回歸(eternal return)。”(16)Adrian Parr, The Deleuze Diction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5, p.83.這裏“前個人的特異性”正是永恒回歸所回歸之處。對人來説,不是主體;對物來説,不是實體。德勒兹單義性的快樂是指單義性的存有。按照老子來説就是道。换言之,道是單義的,免於個人的局限,故帶來快樂。既是先個人的特異性,没有“誰”指的是海德格爾義的個人的存有(man’s being),没有“什麽”指的是個别物的存有(thing’s being)。故而,先個人的特異性雖是單義性的道,但是由先個人的德開始説。這種回歸是一種重複,也帶出先個人的特異性,一種差異的力量;即重複自己的命運帶來差異的力量。
重複自己的命運,王弼注曰:“復命則得性命之常。”也就是説由先個人的特異性的力量,帶出個人性命的常道。這個“常”字不是普通的常法常則,而是帶着差異性的力量,故能了解個人能量的方向與分際。“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静,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英譯云:“All things flourish , But each one return to its root. This return to its root means transquillity. To return to desting is called the eternal (Tao). To Know the eternal is called enligntment.”(17)陳榮捷《中國哲學資料書》(Source 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9, p.147.明顯順着“萬物並作”的物講,“復”是回到先個體的特異性。但翻譯漏了“吾以觀”三字,簡單説是我(用“萬物並作”)以沈思回歸(復)生命根源的現象,但“常”能不能翻成“eternal”呢?河上公注云:“能知道之所常行,則爲明。”常爲經常義,是經驗的綜合而後以超越。但這邊還不説道,而是説德的先個人的特異性。知道萬物(人)的差異性常這樣運行,叫作智慧。王弼注“常”曰:“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皦眛之狀,温潦之象。”是常法常則之意,失之模糊,河上公注則較簡潔。不知道個人、個體差異性的力度和限度,恣意妄爲就帶來凶險。知道個人個體經常運行或運作的力度和限度,就較能包容、寬容。包含萬物的差異性,才會真正公平。真正公平才能成爲天下之王,天下之王才與天相通;與天相通才是道,道才會長久。這樣即使王死了道也不會瀕於危殆。而到“天乃道,道乃天”,説的才是道。
二、 道和德(宇宙論)
道和德的關係何在?天和地的關係何在?無和有的關係何在?
我們不要忘記“失道而後德”(三十八章),道、德的區分有其層次。先看何謂道。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十四章)
這也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四十一章)。視覺、聽覺、觸覺均與道無關,命名爲夷、希、微,混合爲一爲道,而且由無名、無物來説道。故道是先於命名,先個體的狀態,無形亦無象。道對人來説,是恍惚的狀態,無以見其首尾。但老子説道乃古道,古道可以駕御今天日常的自我意識(有);而且古代的開端,是道的紀元。或許這可於海德格爾找到對應,海德格爾喜在存有的希臘字字源義中説明其意義,例如:“希臘人把‘存有’解爲ousia,或更完全地parousia,我們的字典錯誤地把這字翻爲實體(substance)。……ousia指穩定的、忍耐的存有。存有在其動態面向是physis(我們物理學的字根)。海德格爾説哪一個都不能被‘存在’這術語取代。”(18)George steiner, Heidegger, London: Fontana, 1987, pp.49~50.故存在是日常的自我意識,海德格爾在希臘史的開端找尋存有的涵義。紀元不是現實的歷史,是道的歷史。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閲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二十一章)
王弼注:“孔,空也。唯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以空虚爲德的容貌,才能以道爲依歸;空虚之德,從於道。在視覺、聽覺及觸覺所不及處,有形象也有某種事物;其實德是先個體的特異性已是如此,但老子的德是以空虚爲性。深遠幽冥,其中有更精細的物質。這更精細的物質如此真實,它的活動也是信實的。我們或可由當代量子物理學的發展來補充:“原子是由粒子組成的,這些粒子卻不是由任何有形的‘材料’組成的。在我們觀察它們時,決不會看到任何物質。所看到的只是不斷地相互轉化着的動態圖像——能量的繼續‘舞蹈’。量子理論表明,粒子並不是孤立的物質顆粒,而是概率的圖像,是不可分割的宇宙網絡中的相互聯繫。”(19)[美] 卡普拉(Fritjof Capra)著,朱潤生譯《物理學之道》,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頁。此段由原子到粒子可解釋“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是能量的繼續舞蹈。道無論其名爲何,總是存在着。王弼注“衆甫”爲“物之始”,道的活動在萬物的開始處,此處即爲德,thing’s being。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粒子本身的雙重面貌存在: 如是粒子,則是實體;但又是波,能量的波動。現在老子解釋道先於天地而生,孤寂深遠,獨立運作而不止息,可以成爲天下的根源。天地是自然義,天下是社會義。道周遍運行,成爲天下的根源。天地較天下有優先的含義,因爲海德格爾認爲存有在希臘文字根是physis,義即爲自然。老子不知它的名字,稱之爲道。但如果强爲之命名,命名爲廣大,它周遍運行。大總是合於道,“執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大象即大道,故“大象無形”(四十一章)即周遍運行於天地萬物,故曰消逝。廣大之道是人無法獨佔的,故曰遥遠。只有離開人來設想,即離開人文主義來設想,這消逝之道、遥遠之道才是回歸之道。一連串命名,以廣大之道爲首要,但這只是强爲之命名;爲免定於一名,成爲有名,故舉其他特性再爲之命名。道既然先天地生,宇宙論生産的序列應是道然後天地,然後是天下萬物。天地既在萬物之前,天亦大,天覆蓋萬物;地亦大,地承載萬物。天地的意義在此只是簡便地説。在道的領域中,道家聖人的王也居其一,成爲四大。大地是我們生活中所開展的現實空間,我們在大地上生、老、病、死,河上公注曰“人當法地,安静柔和也”。另外可注意者:“老子之言守雌,法牝,守母皆爲陰物,亦世所謂坤道,地道之所在之物。”(20)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香港新亞研究所1973年版,第291頁。不過,他認爲法牝或守母均有不足。暫時只能説到這裏。其實對應點是“知常容”(十六章),知道先個人的特異性經常運行的力度和限度,就知道包容萬物的差異性。大地是包容萬物的差異性,再法天的蕩然公平。天則法道,天還是效法廣大之道;道還是效法自然,道還是自然而然。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四章)
道沖而用於萬物之上,這樣消耗或不會盈滿。河上公注:“道常謙虚,不盈滿。”用其不盈滿之意,既是道,不需將其擬人化爲謙虚。既是道將能量沖流於萬物,所以道是深淵,象萬物之宗主。道也是深淵之道。此段解釋道與萬物的關係,挫去萬物的鋭利,解去萬物的紛雜,調和萬物的光芒,混同萬物的塵跡。湛原來即水深之意,道深深地好像在萬物中存在着。道先於上帝存在,至少在道的領域中四大: 道、天、地、王中没有上帝的位置,那麽上帝是萬物中的超越者,最高物。
道是深淵(abyss),什麽是深淵?“給深淵的字——Abground……我們應該思考Ab——爲根據的完全缺席。根據是打擊根基並去站立於其中的土壤。當依據無法來到的年代,懸置在深淵中。”(21)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by Albert Hofstad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92.如果土壤可視爲大地,大地一般被視爲穩定的根據,但大地有其隱蔽的方式,即深淵。根據的完全消失,現實原則的缺席,甚至理性原則的崩塌。
深淵最後等於水,沖而用之,故善利萬物。“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争,處衆人之所恶,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争,故無尤”(八章)。最佳的善是像水一樣,水“善於”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争,就很接近道了。水利於萬物,如道生發萬物。“善”是存有論的“善於”、擅長(is skilled in; good at),人只要像水一樣保持低下的位置,就善於、擅長把相遇的人、物調和成存有論事件。居於妥善選擇之地,充滿生機。心保持像廣大的深淵,善於包容。給與善於保持真情(仁),了解人的需要。言語善於保持人的誠信,政治善於治理,行動善於選擇時間。因爲從來不與人相争,故無怨尤。深淵是廣大包容,水是善於使萬物得利。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六章)
山谷中的空虚是谷神,山谷中的神靈。山谷中的空虚,是天、地交會,既然是空虚,不是實物故不會死亡。這就是神秘的陰性(玄牝),神秘陰性的門户,生天地是天地的根源。這裏類似性愛存有論,微弱的存在,怎麽使用也不會耗盡。“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是可與“沖而用之”相比較,故谷神亦即深淵,提出陰性存有論,Abground的没有根據,只是空虚。也就是在日常自我意識的實體形上學下,在“男、女”的二元邏輯中,策略性地翻轉,反日常自我意識之道。道即是深淵、谷神、玄牝;水近於道,也是陰性,老子是最早的女性主義。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六十六章)
山谷的水都匯流入大海,就是江海善於保持低下。所以聖人欲在民之上,言語必謙卑低下;欲在人民之先,身體必退讓在後。所以聖人在上,人民不感到沈重;在人民之前而人民也不謀害他。所以天下人樂於推崇他而不厭倦。因爲他不與人相争,所以天下人没有能與他争的。江海與深淵,二而一也。“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三十二章)。天下猶川谷,道猶江海,川谷之水匯流入江海。道是谷神或玄牝,道是深淵和江海。谷神或玄牝都是指山谷中的空虚,而爲天地的根源。另一説法是:“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虚而不屈,動而愈出。”(五章)天地之間像空虚的風箱,卻無法窮盡,一動蕩就生出風來。這説法在莊子“大塊噫氣”(《齊物論》)一段得到較大的發揮。老子較偏重江海和深淵。方東美在説明“道體”上,頗得其要。“道體: 道乃是無限的真實存在本體。(a) 道爲萬物之宗,深淵不可測,其有在乃在上帝之先。(b) 道爲天地根,萬物之所由生。(c) 道元一,爲天地萬物的一切之同具。(d) 道爲一切活動之唯一範型及法式。(e) 道爲大象或玄牝,抱萬物而蓄養之,如慈母之於嬰兒。(f) 道爲命運之最後歸趨,謂之‘歸根’。”(22)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3年版,第168頁。其中“道元一”或可改成“道生一”(四十二章);我們也尚未説明慈母與嬰兒的關係。“生”字如此重要,就是海德格爾義的生産(poiesis)(23)陳榮灼《海德格與中國哲學》(英文書),臺北雙葉書廊1986年版,第127頁。。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五十一章)
道生之的“之”自指德,因爲道“獨立而不改”。德者德也,故“之”字指道,只是蓄存道的動力。道沖而用之,在德上蓄存道的動力,而成爲先個體的特異性,故在德上已帶有萬物之特殊性。在道與德上,基本上是存有論的,也就是屬於道的,是天地,是自然。由於先個體的特異性,形成了物,物也就有了形體,“之”字爲語助詞;由物所占有的空間,成就現實的勢力,這“之”字仍爲語助詞。在物與勢上,基本上是存在論的,人亦屬於萬物;是天下,是社會。在道上説無,在德上説有;在道、德上説無,無形無名;在物、勢説有,有形有名。尊道,道是存有;貴德,德是人的存有,物的存有。因爲《老子》全書幾乎都在解釋這四個字的關係,故將此四個概念是爲萬物的道論結構。
道生産萬物,通過德而發生;德只是蓄存道的動力,帶着萬物的先個體特異性。這是道的尊貴,德的珍貴,没有什麽能主宰而常自然發生,使萬物成長並作育萬物,使萬物成熟,並養護萬物。故生産萬物而不佔有,對萬物有所作爲而不仗恃,使其成長而不主宰,是神秘的德行。
母子關係道、德、物、勢四個概念可收斂成二組關係,簡化之就是道對天下。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五十二章)
天下的開始當然是道,這是天下的根源(母),直説是天下的母親亦無不可。既得其根源,就可以了解自己所生産的。把道對天下的關係,直接認爲是母子關係。既了解自己的孩子,又守住自己的母親,終身也不會有危險。“兑”簡單説,就是“説”,把嘴閉緊,把門關閉,終身也不會勞苦;打開大門,使事情成功,終身都無法救治了。見到微小是智慧,守着柔弱是剛强;這難道不是母親的德行嗎?老子以道對天下的母子關係取代了儒家以仁、義、禮直面天下的父子關係。用道的光照回歸到智慧,這叫做學習常道。道是母親,谷神不是實體,就成爲神秘的陰性(玄牝)。不唯如此,道是母親,而德是嬰兒。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博。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和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日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五十五章)
嬰兒是蓄存道(母親)的動力,非常豐厚,關係親近;天下萬物皆有其德,不是含德之厚。含德之厚就接近道。毒蟲不螫咬他,猛獸不捉他,鷹鵰也不抓他。這是因爲他筋骨柔弱而握得很牢,不知男女交合的事而生殖器勃起,精力達到極至。整天哭嚎而不沙啞,和氣到了極至。知道和氣是常道,知道常道叫智慧。對生命有益叫吉祥,以心放縱怒氣是好强。萬物壯盛則衰老,是謂不合乎道,不合乎道的很快就結束。嬰兒是德厚而靠近道,物壯是物順勢發展;兩者是柔弱與剛强對比的極端。所以“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四十章),道的運動與物、勢相反,物要反歸其德;道的發用是柔弱的。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二十八章)
知道天下是要稱雄,卻守着雌的柔弱,成爲天下的溪谷。這裏雄雌關係也套進來,並以雌爲得其常德。溪谷、山谷、深淵、谷神,都是神秘的陰性(玄牝)。不離開本常的德,又回歸到天真的嬰兒。
男人、女人的對比,成人、嬰兒的對比,在這裏被翻轉;以女人、嬰兒爲不離常德。男人剛强,女人柔弱;取女人。成人世故,嬰兒天真;取嬰兒。知道天下都要顯揚自己,卻守着昏昧黑暗,成爲天下可效法的;本常的德性不過分,又回歸到没有極限。知道天下的光榮,卻守着屈辱,成爲天下的山谷。成爲天下的山谷,本常的德性乃充足,又回歸原木。原木拆散成爲器具;聖人用原始的素樸,成爲百官之長。所以大的制度不能拆散分割。樸: 原木,是原始天然,是質樸。
母親與嬰兒的關係,成爲道與德的關係。“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二十章)我獨自漂泊在没有朕兆的地方,好像没有成爲孩童的嬰兒。散散漫漫無所歸依,因爲天下没有我可歸依之處。……澹泊得像大海,漂蕩好像不會停止,……我和别人不一樣,我看重食用大道(母親)。視道爲母親,而德爲嬰兒,德之向道回歸,則如嬰兒歸回母親的懷抱。“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24)“成器長”一語,王弼注:“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河上公注:“我能爲得道人之長也。”均非。故緊接其後:“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證明所論是死活問題。。”(六十七章)得道的聖人則把自己想爲母親,而天下爲嬰兒,慈愛分明是母親的德性。母親的勇敢是慈愛子女的勇敢。母親節儉,所以能珍惜各種事物,這才能達到廣大的德性。不敢在天下争先,所以能保存自己的生命,得以長壽。器是把身體視爲保存生命的器具。這是“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七十三章),勇於不敢,則活得長久。第六十七章後文:“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這就是以母親慈愛的勇敢,戰争才得以獲勝,守衛得以堅固。“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十章)專注於柔和之氣,能達到嬰兒的狀態嗎?河上公注:“治身天門謂鼻孔。”開闔就是呼吸的狀態,故而並非盛氣凌人,仍然是柔和之氣,這是母親與嬰兒的關係。道對天下,是雌與雄的關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四十三章)天下最柔弱的東西,入於天下最剛强的東西,這又是雌雄關係了。以空虚的東西進入没有間隙的東西,這是無爲的益處。“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勝牡,以静爲下”(六十一章)。這豈非陰性的安静,勝過陽性的剛强,以柔弱勝剛强的道理。結果就是“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母親、嬰兒的柔弱,是水的柔弱。
道的生産萬物:
(無: 無爲) (有: 有爲)
道的動力在反:
(母) (嬰兒) (子)
(柔 弱) (剛 强)
不過剛才在十章的引文中頭一句是:“載營魄抱一”,承載着魂魄抱着一,一字顯然與“專氣致柔”有關,但什麽是一?
三、 何謂一、二、三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四十二章)
一、二、三是神秘的數字。如果按照“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五十一章)言之,則在道與物間只有一個德字,那麽在德的概念上往後反和往前伸發生了一、二、三的數字。“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無、有、物三層可否與道、德、物相配,好像不清楚。但無和有“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第一章),總是同生於道,故無和有也在一、二、三的層次上産生。無和有同出於道,但無生有。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三十九章)。天和地是“域中四大”之天大、地大,大過萬物。神是萬物之至高者、超越者。谷如果得一就成爲谷神。王得一就是域中“四大”之“王亦大”。此章對“一”有些指示:“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三十九章)一是低賤和卑下。此亦“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二十二章)之意。但王弼在四十二章有個精彩的注釋:“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一即是無。河上公此章注:“一生陰與陽也。”這是“一生二”。將兩注合觀,可否説無生出無和有,陰生出陰和陽?不唯如此,徐復觀解“一生二”時説“即是一生天地”(25)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335頁。,那麽就是地生出天地。如此説得彆扭,簡化一點就是,因爲“有生於無”,所以一生二是無生出有,所以二是無加上有。那麽陰生出陽,二就是陰加上陽。地生出天,二就是地加上天。這樣的話,“二生三”就變得容易,無、有是存有論概念,存有宇宙論的“三”是無有之玄;陰、陽是氣化概念,故氣化宇宙論的“三”是沖氣之合。天、地是自然概念,故日常宇宙論的“三”是天地相合。“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三十二章)。簡單地説,“三”是無、有、玄三者,玄是無和有互含;“三”是陰、陽、氣三者,氣是陰陽沖和;“三”是地、天、水(甘露)三者,水是天地相合。
這樣,“一”可以是無、地、陰三者;但我們要注意,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生産結構,一、二、三幾個字帶有三重的概念,即存有宇宙論的,氣化(物質)宇宙論和生活(精神)宇宙論的。如果以回歸的方式看“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六十五章),玄德是由德向道回歸,但道是“獨立而不改”(二十五章),玄德只能是回歸到道與德的中間地帶,德之神秘化就是玄德。那麽“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二十二章)就是抱玄了,就是由有向無回歸,才産生互含的動力。同理,由陽向陰回歸,“一”就是氣;由天向地回歸,“一”就是水。這樣,道是江海之道,深淵之道;道也是谷神之道,玄牝之道。甚至直説是母道,亦無不可。道亦是氣化之道,水之道,玄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