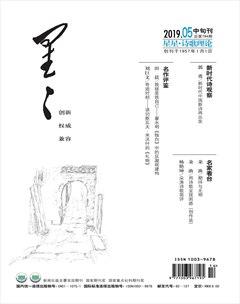光明的对称
[希腊]奥德修斯·埃里蒂斯
人们时常不无道理地发问:地中海世界——主要指爱琴海,我诗歌的主题之一——怎么会和超现实主义在同一人物或诗歌上发生联系;还说这委实叫人感到蹊跷。然而,任何事情都取决于你观察它的方法。在我看来,爱琴海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指纹(正如某评论家准确指出的那样)。我与我的同时代人——塞弗里斯应算在内——千方百计地寻找希腊的真实面目。这样做十分必要,因为迄今为止,它一直被欧洲人眼里的那个希腊所冒充。为了去伪存真,就必须废除统治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超现实主义在文坛出现后不久,就对我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超现实主义的许多方面令我无法接受,比如它的狂言和对信笔直书的庇护。然而,撇开这些不论,它是唯一的、想必也是歐洲最后的追求精神健康并且反对那种充斥大多数西方人头脑的理性主义思潮的诗歌流派。自从超现实主义的狂飚摧毁了这种理性主义,我们面前的土壤就被洗刷一新;我们亦能够自然地与我们的区域连在一起,在不受文艺复兴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成见影响下,正视希腊现实。但这仍不完全是事实。超现实主义以其反理性主义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根据自己对希腊现实的理解来进行一种革命。同时,它所具有的某种超现实因素,使我们能够创造一种由纯希腊成分构成的文字形式并以此进行表达。
这种解释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超现实主义、尤其是它的理论,会对我们产生如此大的引力,以及与此同时,我又是如何运用一种希腊的方法将其付诸实践的。几年前,我接受了一位姑娘的采访,她以“法国和希腊的超现实主义”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尽管年纪尚轻,她却敏锐地察觉到关键所在:“超现实主义之所以在希腊开花结果,是因为希腊的超现实主义者并不简单地模仿法国的老师,而是将超现实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才是真谛。任何一位真正的希腊超现实主义诗人都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恩皮里考斯、恩考诺布罗斯、卡佐斯以及莎克杜里斯各有创见,而我则独树一帜。显而易见,我从来就不是正统的超现实主义者。然而,我却认为超现实主义是一个垂死的世界里仅存的氧气,起码对欧洲来说是这样。
超现实主义极其重视感觉。这也使我们大受启发。事物通过感觉被感知,而我也是通过它,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引入诗歌的。诚然,古希腊人早就这么做了,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具备随着基督教诞生而产生的那种圣洁观念。我力求融合这两种观念,即每当我提到最佳感觉中的事物时,总认为它们同时具有纯洁和神圣的两重性。我在寻求这两种观念的统一。严格地讲,我算不上基督徒,但我却努力将基督徒的圣洁观念与感觉世界融为一体。了解这一特点,是正确领悟我的诗歌的前提。比如说,我在诗集《光明树》中总是借助于感觉来谈论极其抽象的事物。对我来讲,既然感觉散发着圣洁的芳香,就毫无必要在爱情上大肆延伸,而应上升到圣洁的高度。
对我来讲,希腊性不是民族或区域的问题。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我的心目中,希腊有着某些能够在任何场合中丰富世界精神宝库的价值。作为希腊人,我正努力使这些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展示,但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上述言论,我曾发表过一种对称理论。在我的《公开信》一书中,有一篇关于毕加索的法语论文,其中谈到了对称。我笔下的对称具有如下意念:比方说,画家画出的一条线绝不局限于这条线本身,而是同精神世界保持着某种对称。当我们发现山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形状时,他们肯定对人的精神有所影响,肯定也有其对称的一面。一旦你们接受了这种理论,就会明白我对希腊河山的关注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比喻上的探索。我曾经读过一位著名法国建筑师的一句话:雅典山峦起伏的线条在巴台农神庙的三角门楣上得到再现。看,一个完美的对称!
人们往往称我为快乐诗人或乐观诗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归咎于我的对称理论,同时也带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相信,诗歌在一定的完美水平上就不再分为乐观或悲观的了。它也许代表着第三种精神状态。在那里,矛盾的对立面消失了。对立面在一定高度上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诗歌就像好坏难分的自然那样,不过是一个存在而已。由此可见,以往划分诗歌的陈旧方法再也不中用了。
我相信希腊语无法容忍那种被法国人称为maudite(可诅咒的)的生活态度,也无法接受那种maudite诗。要想对此解释清楚,真是太难了。我曾在《公开信》中做过这种尝试,但在希腊读者身上收效甚微。这里我再简要地概括一下:毫无疑问,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定的内容。我感到,我们正经历着在语言问题上转变态度的时期。这是极其危险的。长期以来,语言仅仅被当作一种书写符号、一种表达观念的手段或大众传播的媒介。然而,真正的诗歌永远是语言内部而不是其外部运动的产物。思想正是随同它们语言表达的产生而产生的。语言的因素起到巨大的作用。我再重申:我相信每一种语言都迫使诗人去表达具体的事物。这也许令人难以琢磨。此外,希腊语言无法接受类似表现主义这样的东西。在它看来,这意味着多余的拔高。希腊语是一种表达细腻内容的细腻语言。如果这种解释还不能使诸位满意,那么我只好把我的全部论文都摊放在你们面前!换句话讲,我曾下过这样的结论:我是个不被允许在生活中诅咒的人。对待生活现象,希腊语言始终保持着一种柔和的态度。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是错的;但它终究是我观察事物的方法。恐怕正是这一基本态度,促使人们把我看成了“乐观诗人”。实质上,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抵制maudite态度,那么对他来说,结果将会奇迹般地显得乐观。请大家相信,我从来就不简单地提笔把事物写得像这或像那!我永恒的观念是,在想象的王国里寻求自然和语言的对称。对此,超现实主义也同样给与了高度重视。每一事物都取决于想象,即既取决于一个诗人与你们一起观察同一事物,然而又有别于你们的方法。
现在我要强调另一个问题。我从不按照习惯方法运用古代神话。对希腊诗人来讲,古代神话的运用无疑会带来许多益处,因为这样他就更易于被外国读者所理解。希腊诗人每当提到安提戈涅或俄狄浦斯,总是活动于一个相当熟悉的范围内。他们能够借助这些神话形象影射现代事件。希克里诺斯是这样做的,塞弗里斯更是如此。这对后者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他不仅受到希腊文化遗产的影响,而且还深受艾略特的感染。里佐斯在最近一个时期也使用了神话及悲剧形象。我曾经相当自觉地抵制过这种做法,因为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简单化了,甚至包括悲剧演出在内。众所周知,许多法国及其他欧洲作家也在改编关于依莱克特拉的神话。鉴于我的首要意图是要寻找新希腊世界的源泉,我保留了神话产生的机制,而放弃了具体的神话形象。请允许我对此解释。我有一首诗,题为《夏日的躯体》。它把夏天的特征拟人化,使之成为一个夏日的躯体。在我早期的一首诗里,有一个少女演变成了柑子;而在另一首诗中,一个少女在某个早晨变成了石榴树。这就是我所使用的拟人化机制——神话产生的机制,如果你们更喜欢这种提法——而不插入任何神话形象。瑞士评论家希尔弟曾正确指出,在《对天七叹》中,那个对罗马人意味着善德女神的丽德,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小姑娘。哪里有罪恶,她就挺身而出;哪里有黑暗,她就放射光芒。这里我又运用了抽象思想拟人化的机制,而没有让思想转变为具体可辨的形象。这也许会给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主要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你们能够发现上述情况。
为什么我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我并非有意按照此种方法划分我的诗集。我只是在写完这一切之后,才发现是这么回事。在初期创作中,自然和变形占主导地位(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它始终相信事物的变形)。在包括《理所当然》在内的中期,历史及道德的觉悟更加强烈,尽管还没有丧失创作初期的那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对我来讲,世界至今未变。然而我却努力在表现上有所更新。我不愿在創作上老调重弹,否则会使我产生雷同的感觉。我希望发现新的形式,新的表现手法。长诗《玛丽亚·奈弗丽》属于后期。我对初稿并不满意,准备进一步加工。它的篇幅与《理所当然》基本相同,而结构却复杂得多。我知道,普通读者一般不去关心某首诗下隐藏的草图。然而,我却有目的地给自己设置障碍,为的是能够超越它们,限制自我,并义不容辞地在可行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我要谈“结构设计”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曾在《公开信》中阐释过。一个人难以想象卡尔特大教堂会建在提洛岛上。自然和语言一旦确定在某一具体形态上,它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对称关系。建造一座教堂需要一个确定的建筑模型,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结构复杂的长诗。诗人有必要将相应的各部分合理对照,以便勾勒出一个确定的结构草图。
我从来就不是超现实主义流派的追随者。我不过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合理成分,并把他们注入了希腊的光明之中。《公开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欧洲人及西方人总是在黑暗和夜色中发现神秘,而我们希腊人则是在永恒的光明中找到它。”我要以三幅画面说明这段话。一天中午,我看见一条蜥蜴爬上了一块石头(当时我并不害怕,因为我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地站着)。在这烈日当头之际,它跳起了真正的舞蹈——一连串可爱的、难以置信的小动作。当时我深深感到光明的神秘。还有一次,在帕斯岛和纳克索斯岛之间的海面上,我猛然发现一群海豚从远处游来并超过了我们。它们跳出海面,足有甲板那么高。这又是一次对光明神秘的体验。最后一幅画面描绘了一个少女。她在晌午走向大海,袒露的乳房上停落着一只蝴蝶。空气中充满了蝉鸣。光明的神秘再一次被发现。我们希腊人完全可以领悟并创造这样的神秘。也许这是该地区得天独厚的产物,也许在此地得到较好的领悟,总之,诗歌能够在无所不包的世界里揭示它。每当我谈及太阳的超自然,指的正是这种光明的神秘。
我不能接受头脑的清晰这种提法,这在法国人那里被称为“la belle clarté”(高尚的透明)。我认为,甚至最无理性的诗都有可能是透明的。今天,透明也许是唯一占据我的诗歌的东西。评论家马诺尼蒂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我的诗集《光明树》中存在着令人惊诧的透明。我讲的透明意思是在某个具体事物后面能够透出其他事物,而在其之后又有其他,如此延伸,以至无穷。这样一种穿透力,正是我努力追求的。我认为这体现了希腊的某种实质。透明,这个从物理观念来看仅存于自然界的东西,如今被移到了诗中。然而,正如刚才讲的那样,透明的东西同时又完全可能是无理性的。我个人的这种清晰绝不同于逻辑的或理性的清晰,也不同于法国人以至欧洲人接受的那种clarté(透明)。
作为谈话的结束,我来读一段事先准备好的话。它基本概括了我的诗歌创作意图:诗歌是一个充满革命力量的纯洁源泉。我的使命就是要将这些力量引入一个我们的理智不能接受的世界,并且通过更迭不断的变形,使这个世界与我的梦产生和谐。这里提出了一种现代的魔力。它的功能将引导我们去发现真正的现实。因此我相信,从理想主义出发,我将步入一个迄今未被触摸的世界。我希望能够成功地摆脱一切束缚,发现一种与永恒的光明相互吻合的正义。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最终,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导致基督教的圣洁。
[译者附言]
埃里蒂斯的这篇文章摘要最初于1975年秋天刊登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杂志《海外丛书》上。1978年10月由希腊杂志《树》第四期转载。本文译自《埃里蒂斯自选诗集》,阿可蒙出版社,雅典,1979年11月第三版。
(本文摘自由漓江版社出版的《国际诗坛》1987年第2辑)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