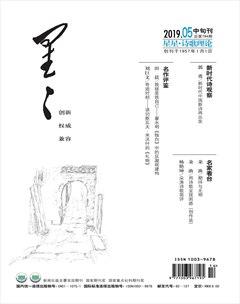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新诗再出发
郭勇
在21世纪的年轮即将转过20年的轨迹之时,中国新诗也已走过了它的百年历程。百年辉煌同时伴随着百年争议,百年之后再出发,中国新诗成绩如何、路在何方?这恐怕是诗人们和一切爱诗之人共同关心的问题。直面这些问题,努力寻求解答,是我们应当担负的责任。对于21世纪以来的新诗,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诗的轨迹上前行,个人化写作仍在继续,“盘峰论争”引发的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写作之争、《星星》诗刊《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诗歌教材的讨论》引起的反响,都延续到了21世纪。如今回顾21世纪以来的新诗,它给我们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对此,谢冕的评价令人深思:一方面,他认为“诗歌没有陷落”,诗人们仍直面时代,但另一方面却是“奇迹没有发生”:“中国新诗诞生于二十世纪,它给那个世纪留下了可贵的诗歌遗产,那也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二十世纪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人们总有殷切的期待,期待着如同二十世纪初期那样,从世界的各个方向,也从中国的各个方向,诗人们赶赴一个更为盛大的春天的约会。而奇迹没有发生”。[1]奇迹之所以没有发生,应该与新诗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相关。
新诗合法性焦虑与“世界中”的新诗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最难攻破的堡垒就是诗歌,但到了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宣布:“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2]从实际情况特别是新诗发展来看,胡适未免过于乐观了。事实上,直到新诗百年之际,关于新诗的论争都完全没有平息,论争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新诗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新诗作为一个自“五四”以来正式登台亮相的新生事物,总是被拿来与有着几千年辉煌历程的中国古典诗词作对比,也不必说新诗在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方面饱受争议,甚至连“新诗”这一名称,都受到了质疑。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质疑恰恰是“新诗人”提出来的:在2013年12月杭州“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上,徐敬亚提出,“五四”时期诞生的白话诗称为“新诗”,契合了时代氛围,如今“新诗”这个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现在时的意义上停止使用。流沙河则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这一论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3]
另一方面,围绕新诗而召开的诗歌会、诗歌节、论坛、评奖,特别是新诗编选,却又屡屡成为诗歌界、学界、出版界的热门话题。在世纪历程中,各种新诗选本层出不穷,也曾掀起过几次高潮,特别是21世纪以来,总结新诗百年的大型选本也开始推出,这对于新诗经典化而言自然是很大的促进。但在新诗编选越来越热闹的时候,对于新诗选本本身的“冷思考”却显得薄弱,关于新诗和新诗选本的争议也一直未曾停息,洪子诚认为:“对新诗史,特别是在处理当前的诗歌现象上,最紧要的倒不是急迫的‘经典化,而是尽可能地呈现杂多的情景,发现新诗创造的更多的可能性;拿一句诗人最近常说的话是,一切尚在路上。”[4]
吴思敬也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似乎感染了经典焦虑症。他借用了西方学者“恒态经典”(Static Canon)与“动态经典”(Dynamic Canon)的区分:前者指经过时间的淘洗,已经获得永恒性的文本;后者则是指尚未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不稳定的、有可能被颠覆的文本。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杰作属于恒态经典,而绝大部分以“经典”名之的新诗名篇,只能属于动态经典。因此,就新诗而言,与其说已诞生了可垂范百世的经典,不如说新诗的经典还在生成之中。[5]的确,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关于新诗经典的选本就层出不穷,这里透露出的,恐怕不是对新诗经典的自信,而是对新诗经典化的焦虑,说到底,仍是对新诗的合法性缺乏自信。“新诗三百首”“新诗十九首”“现代诗经”等提法,能让人感受到以古代经典选本之名来为新诗张目的意图,但这种古为今用,彰显的是自身的底气不足。这也就可以解释郑敏在1993年发表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及中国新诗创作》以及2013年流沙河宣称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会激起诗界如此强烈的争论。
因此,在这种或隐或显的合法性焦虑之下,诗界对于新诗也处于不断的探索中,既有创作方面,也有理论分析,既关乎诗歌体式,也涉及写作姿态。这里对于“新诗”的命名,也是极其关键的一个枢纽。对“新诗”之名的争论,包含着对新诗根本特质的思考,它不仅仅影响到新诗创作、接受与研究,也同样深深影响了新诗选本的编纂。但是,新诗/白话诗的提法,存有两个弊端:一是关注得更多的是“白话”而非“诗”,二是建立起了二元对立模式:古典/现代、文言/白话、旧/新、保守/进步等,并且后一項对于前一项是带有压制意味的。到了90年代,不断有海内外学者对此加以反思,奚密(Michelle Yeh)与王光明提出的“现代汉诗”概念即是此种实践之一。1991年奚密的英文著作《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出版,她提到此书目标有二:一是“企图揭示中国诗在学界受到不公平的忽视的一部分:1917年左右至今的现代诗”;二是“了解现代汉诗独特的革命性本质,探讨它在若干关键层面——从理论的建构到实际的表现——如何有别于古典规范”。[6]
国内学者以王光明对现代汉诗的倡导和研究最为显著。1997年召开的首届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上,王光明提出将20世纪中国诗歌划分为“白话诗”“新诗”和“现代汉诗”三个阶段,他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的命名,意味着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同时隐含着偏正‘新诗沉积的愿望”。王光明以此强调新诗是以现代汉语铸就的现代诗歌,回归新诗本体。[7]
“汉语新诗”也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2004年朱寿桐正式提出“汉语文学”,他也是从语言入手,强调语言的相通对于文化认同的意义,破除文学中的国族界限、地域分割及自我中心主义,他认为“汉语文学”概念“更少国族意识,更少‘中心色彩,更具有一般科学概念的写实性和中性色质”。[8]此后,他进一步提出“汉语新文学”“汉语新诗”等概念。
就各家表述而言,“现代汉诗”与“汉语新诗”的提法,其实沒有实质性差异,它们都是以语言为突破口,将自己的研究限定于汉语文学,同时也是以汉语为文化认同的纽带,将不同地域、国内外的汉语新诗作品贯通起来加以考察,既考察不同地区新诗的发展,也探讨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影响。而无论是以“现代”还是“新”来命名,其实都表明了他们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文化传统的认同(“现代汉诗”的“现代”,更主要是指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因此,这样的思路,实现了对“世界中”的新诗的观照,以一种世界眼光把握新诗,探讨中国新诗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发展情况与特点,改变新诗研究与编选中的本位主义、条块分割,也进一步从外部深入到新诗本体。这种“世界中”的文学观念,在姜耕玉主编《20世纪汉语诗选》“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9]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世界中”的新诗还可以表现为另一个维度:面向世界的传播。1936年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与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是中国新诗最早的英译本。而自1963年许芥昱编译《二十世纪中国诗选》以来,汉诗英译逐渐改变了重古诗、轻新诗的局面。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有更为自觉的意识,同时也加强了与海外汉学界的合作,如张智编《百年诗经——中国新诗300首》、奚密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等。但是,这种观念落实起来仍有难度:首先,要实现不同地域新诗的融会贯通并不容易。很多诗歌选本做了这方面的努力,但效果不理想,这些选本或者是将各地新诗分类编排(多数分为大陆、台港澳、海外),这就变成了各地新诗的叠加、罗列,条块分割的缺陷没有改变;或者是将各地新诗整合起来,按诗作时间线索来编排。但这就又变成了一个大杂烩,既没有展现各地新诗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也没有揭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影响。编选者的本位主义也很难完全打破,大陆编选者以大陆的新诗为中心,台湾学者又偏向于台湾诗作。可见,“世界中”的新诗编选,仍然是一个有待努力实现的目标。
从新诗命名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年来的中国新诗仍或隐或显地挣扎在合法性的焦虑中。但是,新诗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学界的共识是,中国新诗就是用现代的中文来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体验的结晶。诗人们当以此自勉。
新媒体时代的多元化样态
21世纪的一大特点就是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与普及,网络技术带来了资讯、信息的空前膨胀,世界被收入到全新的虚拟空间中。在新媒体时代,文学创作是零门槛,借助于网站、短信、微博、微信等平台,网络文学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2005年3月,国内第一部短信诗集《我只在我眼睛里》出版,首印3万册,开创了近些年来诗集出版首版印数的最高记录。特别是2015年的余秀华事件,使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诗歌,再次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草根诗人也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但是,公众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诗歌事件而非诗歌本身。诗歌大众化潮流在相当程度上是猎奇心理、商业运作在起作用。这是需要警惕的。
对于网络时代的诗歌创作,李少君提出了“草根性”的概念,他认为“20世纪只是提出了一个‘新诗的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和现代进步、民族复兴、精神启蒙、思想解放等宏大叙事捆绑在了一起;那么,21世纪才真正出现了新诗本身的兴盛,新诗回到了诗歌的本体,回到了作为个人抒发情感、呈现日常生活、升华自我精神和个体灵魂安慰的自由自然自发状态”,“草根诗人”多来自民间,如杨键、雷平阳、江非、江一郎、郑小琼、谢湘南、余秀华、郭金牛、许立志等。李少君指出,“草根性”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加速以后,在已经向外(西方)学习之后,需要再向下(本土)、向内(传统)寻找资源和动力,从而最终向上建立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世界,包括生活的、美学的世界。”[10]
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与编选、传播是相辅相成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诗歌的编选与传播也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一是编选创意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市场上选本众多,往往出现重复编选的同质化倾向,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这对于新诗的传播十分不利,品味新诗佳作、了解新诗发展历程、探索新诗创作艺术等等,就都成了一句空话,这样的选本也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上成为赢家。因此,无论是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新诗编选者都注重指出自己在编选上的新意:例如注重当下社会现象、热点,强调时效性,如微博诗选、微信诗选、打工诗选、北漂诗选、草根诗选、新世纪诗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年度诗选等。运载平台也多种多样,如“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诗歌是一束光”“第一朗读者”等一批诗歌微信公众号的走红,《诗刊》《星星》诗刊等纸媒刊物的网上运作,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在这种多元便利的条件下,21世纪以来的诗歌编选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为诗人们提供了新的便利:传统的编选,通常是诗人、专家个人或集体商议,对诗歌文本进行挑选、评点,形成选本,进而出版。这是一个较为封闭、平面化的活动,而21世纪以来的编选,往往是走出书斋,通盘策划、多方合力的运作,编选与诗歌评奖、诗歌节、诗歌论坛、见面会等结合在一起,面向社会和公众,诗歌编选成为立体的、开放的、动态的文化事件。2013年,号称是“中国第一本微博诗选刊”的《中国微博诗选刊》创刊,而此前主编高世现就在腾讯微博策划了“首届微博中国诗歌节”,发起“微诗体”,多家门户网站对此进行了报道。“微诗体”所辖的微博专题、微诗接力成为网络诗歌重要的发布平台。2017年4月,中国第一部《北漂诗篇》由中国言实出版社推出,通过网络公开征集而诞生,被誉为诗歌版的“北京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态的事件。5月,中国言实出版社、《北京文学》月刊社联合主办了“《北漂诗篇》暨新诗百年诗歌朗诵会”。中国言实出版社社长王昕朋在讲话中表示,正逢新诗百年之际,中国言实出版社关注到“北漂诗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试图为“北漂诗人”搭建一个更加广阔的、展示自我的平台。
新诗选本的编选活动,同样也能演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化事件而非闭门选诗。2009年5月,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在西安举行,为此次诗歌节专门编选的《诗韵华魂》丛书出版,王泽龙主编其中的《现当代诗歌精选》,这套选本成为诗歌节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中国新诗论坛在沙溪举行,新诗经典化成为论坛讨论的焦点。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评选新诗十九首。而从2011年6月开始,《扬子江诗刊》就开始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推荐。评选结果揭晓后,《新诗十九首——中国新诗沙溪论坛推介作品赏析》于2013年出版。
在这个过程中,新诗选本还能借助于诵读活动、扫码技术,与照片影像的聯合,可读、可看、可听、可感,引导读者进入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等共同构筑起来的新诗世界。
当然,新诗诵读要走进公众生活,还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新诗编选主打温情牌、青春牌,能起到以情动人的效果。果麦《给孩子读诗》、北岛《给孩子的诗》、杨克《给孩子的100首新诗》带来的是温情风。而邱华栋主编、周瑟瑟编选的《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诗》,是一部“致青春”的作品,以回忆、温情打动读者,向新诗百年致敬。人民日报出版社还携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青年文学联盟共同主办的《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诗》新书发布暨“致敬诗人”诗歌朗诵会在北大举行。中国诗歌网是这本书全部朗诵音频的大陆授权发布平台。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认为这是传统出版与移动互联网的一次完美的诗意结合。
不过,对于读者大众而言,新诗选本的种种变革、包装,仍然还是外在的因素。看上去热闹、花哨、炫目,但是精品意识与深度阅读还显得不够。要使读者能够领略新诗艺术,还是需要在作品赏析上下功夫,编选者尤其要以自己的编选眼光和精辟阐释,充当读者的引路人。因此,新诗选本的另一条路数就是,深入新诗文本,通过细读、品鉴,展现出编选者对诗人诗作的理解,引导读者进入诗歌的内在世界。因此,新诗选本的编选、解读必然打上选家的印记,越是有自身个性、艺术眼光的选家,选本的特色越是鲜明。
担当、情感、语言与传统
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人,面对新的时代环境,首先需要有的是直面时代的担当意识,敢于为大众代言、为时代立言。正如沈浩波所说,“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我们不能集体对这个民族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11]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诗人都会缩进一隅天地,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令人鼓舞的。“911”事件发生后,胡丘陵的《2001年,9月11日》对此予以了强烈谴责,展现的是对公义的坚守。2008年汶川大地震,王平久的《生死不离》、苏善生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在网上迅速流传,引发多少人的同声一哭。2017年由《星星》诗刊编辑出版了《不忘初心——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全国诗歌征文作品选》,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由《星星》诗刊杂志社龚学敏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推出的《十年——汶川地震十周年诗歌作品集》,说明在新时代,诗歌从未缺席。
但是,更为常态化的情况是,“绝大多数诗人都开始了书写一种短暂的感受、一种自我的情绪——像一个小小的容器,像整日生活在高层楼房中足不出户、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一群人,没有热情、激动与感动,这种写作似乎注定无法进行大面积的铺陈,因为思想、意识以及情绪仅仅是轻微的浮动,所以,诗歌本身也只能做到戛然而止。在这种流行的创作形式中,不能说没有生活,只能说写作者本人将生活本身进行了窄化的理解。小格局、小规模,进而在模式化的叙述中千篇一律,‘小情绪的简约与泛化堪称当前诗歌基本面貌。”[12]
有论者对此表达了深深的焦虑。这种焦虑当然有其合理性。不过,面对大时代,诗人们仍然需要通过自我的感受来抒怀,也完全可以书写一己之思,二者并非水火不容。只要直面人生、正视自我,抒发出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自我与时代就是相互融通的。针对网络时代的诗歌创作,刘波认为,诗歌“有感而发”的抒情本质不变:“‘诗人的诗与‘大众的诗的契合点还是‘为人生的写作,只有生命的情感互通,才能实现诗人与大众的心灵交汇,才能引发创作和阅读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微信等自媒体平台来传播诗歌,不仅仅是提高诗歌对大众的影响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借此传递一种精神能量,让我们的灵魂不至于太庸俗,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太功利,唤醒每个人精神深处的诗意”,“有艺术追求的诗人仍需保持从容的格调和写作的尊严,沉下来写入心之诗,写人生之诗”。[13]
此外,语言问题也成为新诗遭受争议的焦点。自新诗诞生后就出现的自由体、格律体、半格律体等体式之争,贯穿了新诗百年。近年来的口语化写作出现了散漫无边的倾向,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语词的表现力、意象的凝聚力显然十分欠缺,因此,坚持民间立场的杨克在《中国新诗年鉴》出版10年之际,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反思,他认为“灵动鲜活的口语绝不等于‘口水化和市井俚语,而是要探索将新的日常语言转化为新的诗歌语言的可能性”,他由此解释“民间”概念的包容性:它“当然属于那个为这一观念的创立而‘付出过的诗人群体,但同时也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或别的‘旗号的写作,更属于广大的‘无名的写作者”,因此“民间”是“一种艺术心态与艺术生存状态,其实它只是返归从《诗经》开始的千百年来中国诗歌的自然生态和伟大传统。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经验,在这个敞开的、吸纳的、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没有人能独占它的含义,也没有人能够说出它的全部真理”。[14]
回望百年,新诗的路途上辉煌与灰暗并存,荣耀与争议同在。在未来,新诗的路还很长,如何走出属于中国新诗自己的坦途,展现自己的风采,是中国诗人们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现代新诗的经典化研究(16BZW141)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 谢冕:《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1-436页。
[2]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8页。
[3] 韩庆成:《年度诗歌观察:站在新诗百年的门槛上》, http://culture.ifeng.com/insight/special/2013shige/。
[4] 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5] 吴思敬:《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江汉论坛》2006年第9期。
[6] 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页。
[7] 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1997年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论文汇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8] 朱寿桐:《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文学”》,《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
[9] 姜耕玉:《20世纪汉语诗选》(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0] 李少君:《一个世纪后,新诗终于回归了“草根”》,《文汇报》2015年3月13日。
[11] 沈浩波:《诗人能否直面时代》,杨克主编:《2006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12] 张立群:《“小情绪”的简约、泛化及其他——当前新诗发展的困境与难题》,《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
[13] 刘波:《“有感而发”的抒情本质不变》,《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5日。
[14] 杨克:《中国诗歌现场》,《〈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