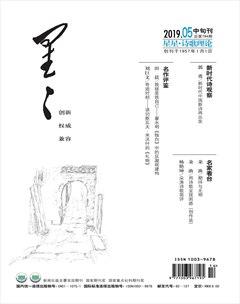朵渔诗歌简评
杨艳坤
《物》这首小诗,看似写物,实则写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生如聚物之乐,收缩着自己的/空间,以便腾出地方给那些无用之物”,这是朵渔式的冷静洞察与思考。人极尽毕生之力去占有空间,用大大小小的物填充它,然后再试图去占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物。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人占有物的必然过程,从出生到成年直至老去,我们从未停止占有。然而,诗人告诉我们,人占有物的过程,同时也是被物件占有和支配的过程。物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大,人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小,直至被挤出这个空间,生命走向终结。因此,朵渔写出了“聚即是散/占有便是消耗,/当我们终于无物可聚/人生也便走到了终点”这样富有思辨色彩的诗句。在《物》这首诗中,朵渔以坦诚的写作态度和精准的语言描摹了人的生存状态,道破人与物之间的秘密关系,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人生。当朵渔提出人与物之间这种“主客颠倒”的关系时,我们也开始对照自己的人生,也开始认同这样的关系。朵渔的这首《物》似乎具有一种强大的气场和魔力,诗中处处都是静默和淡然,从不说教提点,却自然而然引发读者的反思。
《椅子和风》记录了一次物的“死亡”。这首诗画面感极强,朵渔在现代诗里融入了白描的技法,句子短促,简洁跳跃,寥寥几笔,诗意便自然生发出来。夕阳下,路边的一把旧椅子,拨动了诗人的心弦。它旧了,破了,终究逃不过被人遗弃的命运。遗弃意味着它作为椅子的使命已经完结,接下来,它便静静地躺在路边,直到完全消亡。死亡究竟是不是这把旧椅子最终的归宿?面对这个问题,朵渔告诉我们,椅子结束自己的“生命”,走向“无用”之时,正是它重获自由之时。它摆脱了被命名时所承担的“用”之责任,回归到无名无用的状态。夕阳下这把被废弃的椅子,和风一样,纵然一无所用,却也最自由洒脱。椅子和风的自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无边无际、无所拘束的自由,绝不是“一只苍蝇遇到了一块玻璃”的自由(朵渔《厌世者说》)。
《天才只为抵制一个幸福的晚年》是朵渔对常玉和罗伯特·瓦尔泽的艺术化致敬,充满了梵高式的孤独和骄傲。1966年夏天,常玉绘制了最后一幅油画《奔跑的小象》,因煤气泄露意外死在了工作室,在他去世后很多年,其画作的真正价值才被发掘。拥有类似命运的还有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1956年的圣诞节,瓦尔泽照例在午餐过后独自出门散步,永远倒在了阿尔卑斯山的雪地上,多年以后,瓦尔泽才被冠以文学大师之名。天才总是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离群索居,穷困潦倒,生前不被赏识,难道只有突然的毁灭和绝美的死亡方式才能与他们孤绝的才华匹配吗?常玉所绘制的那头在无边无沿的沙漠里奔跑的孤独小象,映照的似乎就是画家自己,在茫茫黄沙中孤独地奔跑,随时都有可能被吞噬。当瓦尔泽与白茫茫的雪地融为一体时,我们或许应该赞同叔本华的那一句“天才从根本上就是孤独存在的”。整体上看,这首诗里呈现出朵渔一以贯之的悲悯和孤独的精神特质,这或许可以说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情结。
《期待与无明》是朵渔对《尤利西斯:一段独白》所作的注脚,诗人的诗意化阐釋之后,句句鞭辟入里。这首诗没有直接触及死亡,荣格论《尤利西斯》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做是诗的开头,整首诗由“那么”一词自然地联结起来。又一个事实被朵渔击中了,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几乎能完全窥探到潜藏在人们心中的秘密。贪欲和期待时刻存在我们的头脑中,人们以为这份期待在下一秒钟就能兑现,于是继续满怀期待,并不断地攫取眼前的一切。期待越来越多,等待也变成无尽的等待,我们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朵渔在诗中创设出一个从粗鄙中间起身的智者,智者从期待变为“无待”,此时我们才发现,在这个紧张而又无奈的期待过程中,外在世界里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源于我们头脑中的欲望在作祟。事实上,朵渔在其他诗作里也常常思考人的欲望,在《树活着》这一首中,朵渔直言人做不到像树一样“无欲无求的淡定,就像是/另一种活”;在《该如何》中,朵渔发问:“该如何,不受低处的诱惑/去过一种充满戒律的生活”?在这些诗歌中,我们能感受到,经过长期不断地对自己的拷问,朵渔的思想和精神更加决绝、彻底,诗中那个想象出来的智者形象,便是诗人最终的抵达。
丹纳曾告诉我们:“艺术家从出生至死,心中都刻着苦难和死亡的印象。”作为诗人,朵渔有着更为灵敏的感受力和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他在诗中构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对死亡进行理性思考,摆脱对死亡的痛苦、绝望的初始印象,同时也消弭掉死亡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朵渔试图通过这样的想象告诉读者——完整的生命历程不单只有“生”,“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惯常地执着于生,却忽略了如何从容地直面死亡。在诗歌里探讨死亡,清算生命,是走到人生中途的朵渔必须解决也正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在面对《羊城晚报》记者提问时,朵渔能豁达地说:“你必须为来路买单,担负起一个‘人的形象;你必须为归途负责,承担起一个‘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