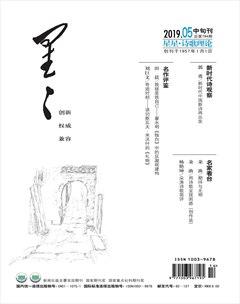奇迹时刻
刘巨文
礼 物
【美国】切斯瓦夫·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西川 译)
“它意味着一种专心致志的状态,即善意地对待自然和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所有细节,不会因为分心而与之擦肩而过。”这是米沃什讨论“用深心(Mindfulness)”诗歌时所讲的一段话。在米沃什看来,“用深心”的诗是一种佛教思维的体现。与技术文明思维恰恰相反,它因为专注能使诗人进入一种与书写对象相互依存的体悟,进而可以维护自然状态和此时此刻,获得肯定性意义。这首《礼物》完全可以作为“用深心”诗歌的范例。但是,如果了解米沃什的出身、天主教精神取向及其特有的流亡经历,我们从这首诗中就不难同时体察到一个天主教信徒如何见证和转化苦难,甚至重返伊甸园的意义。
诗歌的题目是“礼物”,英文译为“Gift”,波兰语为“Dar”。“Dar”有三重意义:其一,为礼物(present);其二为天赋(talent);其三为向灾难受害者的捐赠(donation)。考虑到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诗人出身于天主教传统深厚的波兰,波兰语“Dar”本身的内涵也许能够更准确地呈现米沃什这首诗丰富的意义指向,即这首诗可以理解为带有佛教顿悟色彩的上帝赐予和诗人对苦难奉献的礼物。如果只理解成现代汉语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致意的“礼物”,则过于简单,犹如彩色照片被扫描成黑白照片。
诗歌主体只有九行,但仍然具备严谨的结构和坚实的发展过程。第一行是诗歌的第一部分。“如此幸福的一天”,以“如此”修饰“幸福”和句号结尾,构成一个极为确定的判断,统辖整首诗,且为诗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起点。这种开始犹如课堂上提出一个数学命题,须要给出具体有力的证明和阐释才能成立。那么,为什么这一天如此幸福呢?接下来的两行给出了部分答案,“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雾的消散意味着“我”不再身处模糊难辨的混沌之中,而是处于光明之中。意味深长的是我在花园中的劳作与蜂鸟停在忍冬花上的并置,暗示他们都从劳作中得到了甜蜜回报。这两行诗看似平平无奇,但是,诗人要对提出的命题做出更多的证明和阐释,诗歌的进一步发展赋予了它们更多意味——幸福光照中的甜蜜劳作与若隐若现的痛苦纠缠在了一起。“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这意味着曾有什么诗人想要占有,有人让他羡慕,不过,此刻的顿悟让他去除了占有和羡慕的欲望。接下来是“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作为见证者和幸存者的诗人所经历的残酷与苦痛也被消解了。“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虽有情感和认知的差异并不会让他难堪,同样是顿悟带来的澄明。“在我身上我没感到痛苦。”则是做进一步的承接,收起第二部分,即无论是精神和肉体上,此刻诗人都处于一种和谐之中。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和谐的喜乐绝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对一切苦痛的承认和理解基础上的。最后一行是第三部分,“当挺起身来,我看到蓝色的大海和帆影。”呼应诗歌开始的第一行,承接上面,诗人站立了起来,在视野的展开中,把此刻顿悟的精神经验进一步提升,扩张至更为广阔的世界。
这首诗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是它所渗透出的安宁、从容和喜乐。但是,这种品质又是如何获得的呢?首先,与米沃什从佛教精神吸收的营养有关。诗人描写和沉思的并置,个人劳作和自然景物的并置,以及个人所遭受苦难和对苦难的超越并置构成一种相互对话和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平等的,是彼此间善意的相互成就和依存。其次,米沃什还从天主教传统中获得了支撑。如果我们熟悉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马上就会意识到米沃什在诗中似乎通过苦难的转化完成了向伊甸园的回归。亚当和夏娃因原罪被放逐,必须承担劳苦,被必死的有限性所折磨,远离乐园。而在米沃什的《礼物》中,诗人的劳作和所遭受的苦难,犹如被炼金师施加了魔法,被转化成一种赞美的力量。由此,诗人迎来了带有强烈的抚慰性力量的奇迹时刻,在现实世界完成了和解。这种和解是一种伟大的平衡,是詩人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获得的品质。最后,这首诗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日常生活写作的难点并不在于它的日常,因为日常也可能带来平常,甚至平庸。《礼物》的立足点是一个日常生活片段,但米沃什并没有把这个片段孤立和密封起来,而是让它成为坚实的中继点,接受广阔时空的流动和穿越,由此超越自身,进而打开一个立体、开放、丰富、带有无限意味的诗意空间,让诗人和读者都可以挺身站立,体悟自身“用深心”的奇迹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