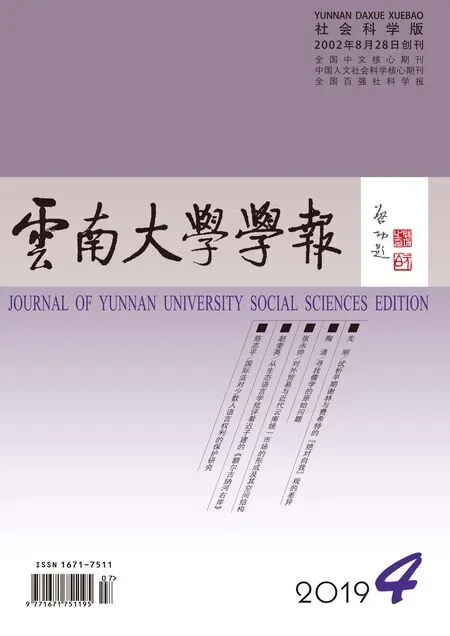本原的二重性与统一
——论谢林最终的哲学方案
王 丁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430074]
谢林最后的哲学尽管以“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为题,并因而造成了许多望文生义的误解,但究其实质,在这两个名目之下的实际上是他对“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区分,以及在此区分上构造哲学更高统一性的努力。虽然谢林最后的哲学可以从许多方面入手来讨论,但本文仅限制在“本原(Prinzip)”问题上,这一方面是由于本原问题是德国唯心论自其诞生之初就始终纠结的问题,并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德国唯心论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围绕本原进行的争论;而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对本原问题的讨论,谢林作为德国唯心论真正终结者的形象才能得到切实刻画。因此本文将会:1.论述本原自身的二重性疑难以及由它所引发的谢林与黑格尔间的争论;2.分析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3.在此基础上阐述“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之区分的必要性;4.讨论谢林对这两个哲学路向进行统一的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说明,谢林如何通过对本原概念的完成超越了唯心论。
一、本原的二重性与谢林、黑格尔之争
一般理解的德国唯心论,是一条从费希特开始,经由谢林通向黑格尔的进路,这条进路也被刻画为“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和“思辨唯心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刻画不无道理,但过于片面。实际上就本文所着眼的问题来看,这一进路也可以被刻画为“主观本原”“客观本原”和“以反思代替本原”。众所周知,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任务是构造哲学的统一性,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个作为本原的极点出发构造整个体系,以避免康德所陷入的二元论,按照谢林自己的阐述就是“(康德之后)不可避免的一步是……不假定任何从别处而来的现成之物,一切都应从那个唯一的普遍在先者中被推导出来”。[注]F. W. J Schelling, Sämmtliche Werke.14 Bände, hrsg.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Cotta, 1856-1861=SW, XIII, S. 51.而康德留下的三个理性理念——“世界”“灵魂”和“上帝”——则给出了本原得以被构造的可能性。首先是费希特从作为“自我”的“灵魂”出发的尝试,也就是以作为行动者和知识者的人类自我意识为基础来演绎出整个哲学体系,接着是青年谢林从作为“世界”的“自然”出发对费希特的补充,这就产生了在谢林那里“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分裂状态,这种分裂促使谢林继续沿着康德的思路,从作为“世界”和“灵魂”这两者之上的最高绝对者的“上帝”出发来构造本原,或者也可以说,如果“自我”是“主观的一”,“世界”或者“自然”是“客观的一”,那么上帝则是摆脱了主客对立的“绝对的一”。[注]Wilhelm. G. Jacobs, Schelling lessen,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2004,SS. 74-75.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客观唯心论”这个称呼其实只适用于谢林的“自然哲学”,而不适合谢林从“绝对的一”出发的“同一哲学”,在它1801年的出版提要里,谢林就强调自己“多年来看作真正的哲学的,乃是唯一的一门哲学”,自己只不过是“尝试从作为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去阐述它”而已,对他来说,“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两者单独地都不是哲学体系自身,只不过是片面的阐述”。[注]SW, IV, S. 107-108.而“同一哲学”的出发点则是作为“主体和客体彻底无差别”的“绝对理性”,而哲学本身的立场,就是这种“理性的立场,哲学的认识就是如事物自在地那样,也就是如其在理性中地那样去认识事物”,并且“在理性之外无物存在,一切都在理性之中”,而要进入这一立场“必须从思想活动中抽离出来,对进行这种抽离活动的人来说,理性就会直接终止指向某种主体性的东西”。[注]Ebd, S. 114-115.
很明显,谢林的“同一哲学”是一种柏拉图—斯宾诺莎式的哲学方案。[注]Beierwaltes很明确地看出,谢林的柏拉图主义立场也让他接过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问题:“一切的唯一根据也是不是一切,它并非‘得到了规定的某物’,谢林接过了这一悖论:绝对的一是一切,是存在者总体……是对一切对立的取消,但同时也不是一切在自身中反题式的对立。”(W. Beierwaltes,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0, S. 205).具体来说就是:1.在作为“绝对无差别”的“理性”中蕴含着尚未作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者整体,也就是“自在”的存在者整体。2.理性自身并非人的认识能力,而是超越了反思、并使反思得以可能的非—主体性的“绝对的一”,当柏拉图通过辩证法得到最后的“通种”时,不得不继续超越思辨,上升到这个超越于一切的“一”那里,在形而上学传统中,它对应的正是“上帝”,也就是谢林为了从最高的本原出发而从康德那里接过来的第三个理念;同样,在谢林这里,理性不是对象性的“思想活动”,而是从它那里“抽离”。3.这个“一”是绝对超越的,也就是说,它绝不可能“作为”自己进入反思,也就是作为一个对象去存在,因此,谢林区分了“一”的“本质”和“形式”。就其自身而言,也就是据其本质而言,它是超越的;但它的存在形式则是同一律“A=A”:“绝对同一只存在于A=A这个命题的形式下,或者说这一命题是直接通过绝对同一的存在被设定的。”[注]SW, IV, S. 119.换句话说,作为超越者的绝对同一处在一切存在的彼岸,它是对一切有所规定的存在的否定,但它自身并不是绝对的“无”,毋宁是使得一切具体存在得以显现的“视域”,因此可以说,“绝对同一”不存在,而是使存在得以可能,一切最终表达在同一律中的存在者自身及其整体关联,都以绝对超越性的“一”为前提,一切谓述都指向它,它以非—存在的方式为得到展开的存在者整体奠基,但若无后者,它也不可能得到显示,因此谢林才说同一律是跟它被一道设定的。
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在谢林对“绝对同一”的描述中,出现了两个相矛盾的特质:它既是作为超越者的“一”,也是作为存在者整体的“全一”,对应于谢林的说法,它既是超越了反思的绝对者,也是处在自在中的存在者整体,因此,“绝对同一”中的“一”其实具有两重意义。如果取消超越性而只着眼于“全”,像黑格尔那样把本原的超越性理解为“全”对自身的超越,也就是历史性地以扬弃的方式实现自身,那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把神消弭在了存在者整体中,[注]SW, X, S. 160.或者说,这就以不断超越自身的方式取消自己的超越性,如此一来,超越性自身就是一个可被扬弃的要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使扬弃得以可能的东西自身又如何能被扬弃?若没有这一超越性,这个“全”也就没有动力展开自身,甚至自身也不可能作为“全”得到完成,否则那就要像斯宾诺莎那样,用僵死的逻辑必然性像几何学那样得出存在的样态,正是这个超越性的“一”对尚未展开的“全”给出的最初否定,使后者可以展开自己。[注]F. Halfwassen, “Jenseits von Sein und Nichtsein: Wie kann man für Transzendenz argumentieren?”, in Gottesbeweise als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moderne Vernunft, hrsg. von Thomas Buchheim, Tübingen, 2012, S. 97.因此,超越性自身既不能被扬弃的,也不可能内在于“全”中。除此之外,如果没有超越性的“一”,“全”就会落入恶无限,而不能作为得到了完成的、有其边界的整体。反过来,“一”如果不以“全”来映现自己,那它就是一个空的东西,因此,“一”和“全”并非相互冲突,而是互相需要、以悖谬的方式共属一体。因而本原自身也必须同时兼有超越性和全体性,它必须同时不—是存在者整体和是—存在者整体。这其实构成了谢林一以贯之的问题,但1801年体系的缺陷就在于,谢林过于强调 “一”,而没有去积极言说它作为“全”的展开过程,甚至以“不解释”的方式来搁置这个问题:
某物从这一绝对的整体中或者在思想中自行殊异化,这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在此还没法回答,因为我们毋宁只是在证明,如此一种殊异化自在地是不可能的,从理性的立场来看是错误的。[注]SW, IV, S. 128.
实际上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谢林之所以“不解释”是因为根本没法解释,在1801年的方案里,他把超越性的“一”和作为“全”的“一”不加区分地当成了同一个东西,或者也可以说,他把使存在者得以存在的东西和存在者混为了同一个东西,说到底,他没有注意到本原自身包含的“存在论差异”。因此可以说,黑格尔在1807年《精神现象学》中对谢林的批判其实是一个尝试,也就是试图以“全”这一方面为主导,来解决本原内部的二重性张力,那句耳熟能详的“黑夜观牛”根本就没有切中要害,相反从上面的分析出发可以看出,“黑夜观牛”是对谢林的一个误解,因为按谢林的说法,同一律实际上包含了差异,只是还没有展开而已,并且同一律只不过是跟绝对者一道存在,但它自身并不是绝对者,绝对者也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知识”,而是使知识得以可能的“非—知识”。[注]Ebd, S. 123.相反,黑格尔所谓的“批判”其实体现在他对本原问题的重新理解上:
开端、本原或者绝对者,最初直接说出来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普遍者……没有陈述出包含其中的内容……比这些词语更丰富的东西,即使只过渡为一句话,也包含着一种必须被重新收回的自身转变,即一种中介活动。[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这里的“中介活动”,无疑就是潜在地能够展开为如其所是的存在者整体的“全”对自身的反思,它以命题的形式来展开并扬弃自身,在这个过程里,命题的谓词作为主词的他者,其实就是主词自身,随着命题系统的展开,作为谓词的他者不断得到扬弃,主词的丰富性也得到了显示。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批判”其实使本原的两重特质更加明确了:1.本原不是体系之中的体系开端,或者说在作为“全”的“一”中,并没有序列起点意义上的开端,本原自身并不进入存在者。2.“一”的超越性不可能被扬弃和掩藏,而是必须被保留,否则无法指出“中介活动”,即“反思”的动力何来,也就是说,黑格尔根本没有解决“本原”疑难。
综上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推动谢林与黑格尔之争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思辨性的“同一与差异”。[注]Philipp Schwab, “Vom Prinzip zum Indefiniblen. Schellings Systembegriff der Weltalter und der Erlanger Vorlesung im Lichte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egel”, in Systemkonzeptionen im Horizont des Theismusstreites (1811-1821), hrsg. von Christian Danz, Felix Meiner Verlag, 2018.这只是一个次一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本原自身的二重性。作为“全”的“一”当然是黑格尔喜欢强调的“同一与差异的同一”,因为全体就是处在一中的多。但关键的是,本原自身的二重性所带来的张力始终悬而未决,也就是说,共属一体的超越性和全体性如何统一、并且互不消解地发挥作用才是问题所在,而这也是谢林本人如此看重1801年体系的原因,在1841年去柏林接替黑格尔教职的首场演讲中他就强调,这一体系方案是自己“为哲学史成功写上的一页”。[注]SW, XIV, S. 359.而这一页的意义就在于,德国唯心论的两大诉求——超越性和全体性——在本原问题上得到了最高的聚集,进而给出了谢林晚期区分“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动因,但在此之前仍需看看谢林是如何回应黑格尔对他的批判的,以使得根本问题的张力得到进一步突显。
二、谢林的黑格尔批判
在《精神现象学》出版两年后,谢林发表了他著名的“自由论”,尽管文中对黑格尔只字未提,但谢林认为,自己在这部著作里已经对黑格尔进行了“无声的反驳”。[注]“自由论”即《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谢林的这个说法见他致贝克尔的信:F. W. J Schelling, Aus Schellings Leben. In Briefen. Band 3, hrsg. von G. L. Plitt, Leipzig, 1869-1870, S.113.关联于本原的二重性疑难,这一“无声的反驳”其实体现在“自由论”中关于“同一律”的讨论和对“无根者(Ungrund)”的指明上。
首先,关于“同一律”,仿佛是为了回应“黑夜观牛”的挖苦,谢林强调,同一律中的“主词和谓词”不是“同一回事”,而是“先行发生和后来发生的东西”,在谓词里所包含的,是在作为概念的主词中“包含的一些个别特性”,因此,主词和谓词的关系就是“内涵和外延”。[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页。谢林并不否认,存在者得到言说就是主词的内涵不断被谓词展开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跟黑格尔并无不同。甚至在《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前,在1806年的“驳费希特”中,谢林就说:
作为一而存在的东西,在其存在本身中,必然有一条为作为统一者的它自身,与作为自身之对立物,或者说作为多的它自身的纽带,一条作为与自身同一者的存物者,与作为多,也就是这一存在物之实存的纽带。[注]SW, VII, S. 55。“驳费希特”即Darlegung des wahren Verhältnisses der Naturphilosophie zur verbesserten Fichteschen Lehre(《对自然哲学与经过了改良的费希特学说间真正关系的阐述》)。
很明显,谢林所强调的,不是黑格尔强调的“思辨同一性”又会是什么呢?因此,在“自由论”中,谢林用自然哲学的方式重述存在者整体展开的过程并非随意之举,为了展开这一过程,谢林做了著名的“实存”与“根据”的区分,也就是“外显”和“内涵”两重趋向的区分,两者间的互相斗争使存在者得以出现。[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页。抛开谢林这个时期运用的神智学术语不谈,在对“全”展开过程的阐述上,谢林并不比黑格尔缺乏思辨性。但更重要的是,在“自由论”的最后,谢林重新提出了本原的超越性问题,他强调,在“根据与实存之先”还有一个“源初本质”或者“无根者”,它不是两者思辨性的“同一性”,而是超越于两者的“无差别”,它是“无谓词的”,如果没有它,就没有对整体进行着构造的“二元性”。[注]同上,第96页。可以看出,经过这最后的强调,谢林在“本原”问题上的进展就在于:1.明确地把本原的超越性和全体性区分了开来。2.对超越性和全体性的作用也有了明确的说法,具体来说就是,超越性的方面使得构造性的、也就是全体性的方面得以可能,前者是“超存在论的”,后者是“存在论的”。3.在谢林区分“作为自身的神”和“神之中的自然(他者)”时,本原内部存在论差异的作用方式也就明显了:[注]同上,第34页。a.本原自身同时是超越者和全体,这个意义上“是”的意思是,两者的共属一体,或者说两者的无差别;b.超越性作为自身得到彰显(作为自身的神),需要存在者整体(自然)也得到彰显,因此两者必须在共属一体的情况下各自作为自身“分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原自身同时是两者”的意思就是使得两者各自的其所是,也就是使两者分开,各自发挥作用。c.超越性的彰显和全体的展开过程只是“对应”,而不是以泛神论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但在此过程完结之后,本原自身仍然是一个“隐匿者”,它让一切“是”的方式是自身永远“不—是”。[注]“那么体系的原则是什么,那个贯穿在一切之中却不驻于一切的唯一主体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称呼它,怎么道出它呢?……它并非它仿佛是的东西,亦非它仿佛不是的东西。它处在一种不可中断的运动中,不可锁闭在任何一种形态里,它是不受强制者,不可把握着,真正的无限者。”(F. W. J Schelling, 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H. Bouvier u. CO, 1969, S. 16.)或者也可以说,绝对者自身的超越性分为两个层面,即它自身的绝对超越性和相对于全体而得到显明的超越性,前者是超越于全体性的“外层”,而后者则是划定全体边界和使全体得以可能的“内层”,但不管是“外层”还是“内层”,它都是同一种超越性。
因此可以说,在“自由论”中,本原的内在二重性张力和作用得到了明确的界说,而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世界时代”时期,谢林一直都在努力使之得到清晰的阐述,上面总结的三项进展其实就是谢林从“世界时代”开始一直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本原自身的二重特质如何可能得到展开?展开的动力在哪里?或者说,作为两者之“无差别”的本原如何走出这种封闭状态,使存在得以发生?[注]先刚:《永恒与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3页。但在这一整个时期,谢林的表述是混乱的,为了直接走向谢林最后的哲学方案,必须着眼于本原问题直接跳到他在1833/34年的“近代哲学史”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上。
在这个文本里,除了再次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跟自己的“同一哲学”在关于全体的展开问题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外,谢林的黑格尔批判主要集中于三点:1.逻辑学开端;2.使反思得以可能的前提;3.全体性和超越性的差异和次序。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逻辑学开端是“纯存在”,也就是一个最为贫乏、有待充实和谓述的存在。根据上面的讨论不难看出,这个“纯存在”就是尚未得到展开的全体,也就是说,它是包含着对象化潜能的存在。因此谢林才有理由说,这个“纯存在”并不纯粹,而是一个“特定的存在”,它的“特定性”并不在于它在开端之际就已经有了谓词,而是在于它“可被规定”,而真正的“纯存在”是一种“非对象性的、纯粹本质性、处在纯粹源初状态下的存在”。[注]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9-160页。在谢林的这一批判中可以明显看出,本原自身的二重性和存在论差异得到了再次彰显,本原自身的存在是超越的、不指向对象的,而指向对象的存在总是处在全体中的、可谓述的存在,也就是进入了思想、能以反思的方式展开的存在。
前文已经说过,黑格尔掩藏了反思的真正开端,他把反思称为“对思想的思想”,而在谢林看来,黑格尔所谓的“对思想的思想”并非一种“现实的思想”,思想的力量在于“克服与它对立的东西”,而黑格尔所谓的纯粹思想“根本就没有克服任何东西”。[注]同上,第170页。在全体的展开过程中,思想的行动是“反思”,而这个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理性”,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可以说,对思想的思想就是存在者对自身的反思性展开,这一点谢林并不会不赞同。但这一批判的重点在于,思想或者说理性是如何开启的,这种“反思”活动如何得到最初的推动,这是黑格尔含糊过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思想要是有力的,那么必须追问思想的开端,必须积极言说本原自身的超越性,进而不把全体的展开当作不言自明的事情,也就是要去追问本原自身的运作方式:
整个世界仿佛都是置身于知性或理性编织的重重网络之内,但问题始终在于,世界是如何进入到这些网络之内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很明显还有另外某种东西,某种相比纯粹理性而言多出来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某种突破着这些限制的东西。
无疑,这一“多出来的东西”乃是使存在者得以可能的东西,也就是超越性,否则全体无法在理性中得到展开,因此,超越性必须优先于全体性,这就引向了谢林对黑格尔在“逻辑学”最后“外化”这个说法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者整体在逻辑学中得到了概念上的完成,这个时候黑格尔的难题就是,逻辑整体如何成为现实整体?对此黑格尔运用了“堕落”、“外化”、“决断”这样的字眼,但这在谢林看来,已经脱离了“逻辑学”的有效范围,在得到了完成的理念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动它……再次降格为单纯的存在”,黑格尔的理念“仅仅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本身不可能是开端”。[注]谢林:《近代哲学史》,第158、187页。实际上,黑格尔在“逻辑学”最后所要求的,正是对“全体”的超越,只不过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这种“超越”只能是“逆向的”,也就是说,黑格尔囿于“全体性”而强行掩藏超越性的后果就是,他不得不最终越过“全体”,用一些模糊的字眼悄悄把“超越性”再次引入,“逻辑学”最后所要求的这种使理念现实化的超越性,已经不再是全体对自身的扬弃式的超越性了,而是真真切切的“逻辑的他者”。在“启示哲学导论”中,谢林更为明确地表示:“黑格尔所阐述的那种哲学是被驱到其界限之上的否定哲学,它并不把肯定性的东西排斥在外,而是自以为已经使它臣服在了自身之中。”[注]SW, XIII, S. 80.这里所谓的“否定哲学”就是只关注“所是(Was)”,即以思辨性的展开方式言说存在者整体的哲学,而“肯定性”关注的则是“存在者如此存在的实情(Dass)”,也就是黑格尔所要求的“逻辑的现实性”,它是“肯定哲学”的课题。[注]Ebd, S. 58.因此可以说,伴随着对本原自身二重性愈发清晰的认识以及对黑格尔的批判,谢林最终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哲学路向,而这就是他最后的哲学方案。
三、“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区分及其统一性
“否定哲学”是“理性的科学”,也就是在理性中构造“存在者自身”科学,在对“否定哲学”的阐述中,谢林甚至接过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把它表述为“能够存在者”,也就是指向存在者的“非—存在者”,存在者对自身的展开过程就是对自己先前层次的逐步否定的过程,因此,否定哲学最终达到的“存在者自身”,或者说“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只是以否定性的辩证方式达到的“非—非存在者”。[注]Ebd, S. 71.在这一点上,谢林和黑格尔并无不同。但对黑格尔来说,在逻辑学中达到了完成的理念仍需“外化”,而谢林更为清晰地表明,“存在”不仅是对存在者进行的思辨—谓述性展开,更是“一个发生的事件”。[注]Ebd, S. 89.实际上,从上文可以看出,在对“全体”的思辨性展开上,两人间的差别只是表述上的。黑格尔在逻辑学的最后所要求的,正是那个使理性得以现实化的理性的“他者”,它让在理性中“是”的东西“是(存在)”起来,因为不管是“决断”还是“堕落”,都不可能是“反思”自身可以做到的事情,毋宁说,它们撕裂了思辨同一性,完全从它之中“绽出”了,因此,在“否定哲学”或者“逻辑学”的最后,理性其实走出了自身,看到了一个不可谓述的东西,或者说不以作为存在者的方式而存在的东西:
理性只能把这个存在着东西(在它之中完全没有任何从概念、从“什么”而来的东西)设定为绝对的自身之外者(Ausser-sich)……理性由此也在这一设定活动中被设定在了自身之外,处在绝对的绽出(ekstatisch)状态中。[注]SW, XIII, S. 163.
对理性来说,这个超越者是绝对的“他者”,因为理性对它是无力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被收摄到思辨同一性中,这是谢林真正超越了黑格尔的地方,但这一超越并不是谢林“克服”了黑格尔,而是说,谢林最终清晰地指明了黑格尔的缺陷,进而以区分两重哲学路向的方式穷究了本原问题。既然作为理性科学的“否定哲学”无力面对本原自身中的超越性,那么“肯定哲学”的引入就是必要的,如果说理性科学的工作是在概念中把握存在者整体,也就是先天地把握存在者自身,那么:
肯定哲学则专注于不可先天把握之物;但它专注于此恰恰只是为了把这一不可先天把握之物后天地转化为可把握之物;在神中,不可先天把握之物就成了可把握之物。[注]Ebd, S. 165.
根据之前的讨论,本原的超越性要先于全体性,也就是说,肯定哲学的对象要先于否定哲学的对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谢林也把肯定哲学的对象称为“绝对的在先者”。[注]Ebd, S. 153.既然它是理性的他者,那就不可能先天被认识,故而只能被后天地认识,因为所谓绝对的在先者,就是在它之前不可能还有在先者的非思想对象,谢林也把它称为“不可预思之在(das unvordenkliche Sein)”,它是“肯定哲学”的直接出发点,而肯定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它之中“找到持立于一切之上的本原”。[注]SW, XIV, S. 337.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谢林强调,这个绝对的超越性在神中得到了把握,所以与对本原的确立相对应的就是神成为神的过程。[注]对谢林来说,神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神不是绝对的在先者,只是存在者整体的“开创者”(SW, XIII,S. 173),但神得以成为神,或者说神的自身化是“本原”自身的运动结果,神以本原中的绝对超越性为自己的“在先者”(SW, XIII, S. 160)。在神中,本原的超越性和全体性才得到彰显。很明显,这个意义上的神,既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传统的“最高存在者”,因为本原不—是存在者,也不是某种神秘主义的遁词,而是使本原成为本原去发挥作用的枢纽,或者说,使本原自身的二重性得以显明的一种“发生机制”或者“存在事件”,联系上文可以看到,这就是谢林自“世界时代”时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本原内部的二重性得到了界说之后,构造真正的、能开启存在的本原,也就是构造把二重性涵括在自身中的“一”,而哲学的统一性正在于言说这个真正的“一”,故而可以说,哲学自身的统一性就在于本原中两个方面的统一性,既然这一统一性发生在神的自身化中,那关于本原的最高哲学也就是对此“存在事件”的言说,但切不可以误会,哲学就是“神学”,因为谢林并没有把神当作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把神视为本原成其自身的发生事件。
本原的超越性首先表现为它的“不可预思之在”,这个“存在”不可被理解为一个与主体对立的东西,而是彻彻底底超越了主体的东西,它存在于神的自身化之前,是神必须去克服的“永恒存在”:“神存在于其中那个存在,乃是永恒的,甚至在神自身思想它之前就存在了。唯有走出他的永恒,神自身才能以其永恒为对象。”[注]SW, XIV, S. 340.与这一存在并列的,还有本原自身的“全体性”,也就是“另一个存在的可能”。[注]因为“全体”对应的是在逻辑的先天可能性中以概念把握的东西,所以谢林笼统地把它称为“可能”,这不是逻辑模态中“可能”(SW, XII, S. 244; XIV, S. 340)。存在使得神可以自由地面对可能,以保持他的超越性,使之不必卷入其中。而可能则给出了神走出这一“永恒存在”的可能性,使他不会囿于超越性而无力开启全体。这两个方面给予了神双重的自由,即“不去存在的自由”和“去存在的自由”。[注]SW, XIV, S. 340.而真正意义上的神,或者本原,也就是“同时自由于两者的第三者”,也就是支配了超越性和全体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谢林也把神称为“存在的主宰”,也就是同时主宰着作为自己超越性方面的“不可预思之在”的本原,和主宰着作为自己全体性的“另一个存在之可能”的本原。[注]Ebd, S. 354.可以看到,在“存在的主宰”这个概念里,本原一词的含义才最终得到了穷尽,它的希腊词源arche本身就有“主宰”的意思[注]神的自身化过程在本文中无法展开,这是一个过于繁复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谢林最终的哲学方案也是对“本原”概念的完成,具体来说是三重意义上的完成:1.相对于全体性的超越性;2.相对于超越性的全体性;3.作为主宰支配着这两重要素的绝对超越性。因此,本原自身其实就是在三重意义上得到了完成的自由:1.不去存在的自由;2.去存在的自由;3.去存在且不去存在的自由。[注]SW, XIII, S. 261.可以看出,谢林用自由概念分别解决和保持了本原自身的二重性所带来的悖谬和张力,使本原真正成为了支配性的“一”,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柏拉图传统在德国唯心论中的完成。在最终的哲学方案里,谢林终于实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追求:“一切哲学的开端和终点都是自由。”[注]SW, I, S. 177.或者也可以说,自由和体系(从本原出发的整体)终于达成了一致,所以谢林最后的哲学是一种“自由的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本原的内在张力使自由本身得到了三重展开,而自由也藉由本原自身的二重性张力消解了这一悖谬带来的否定性,使之转化为肯定性的,自由不再是思辨同一性中的“必然即自由”,而是出入存在整体的“最高自由”,本原真正的超越性在于自由,而它使全体得以展开的动力也是自由。唯有在这个意义上谢林才可以说:“对我们来说,自由是最高者,是我们的神性,我们意愿它是一切事物的最终原因。”[注]SW, XIII, S. 256.
四、谢林与唯心论的终结
在最终的哲学方案里,谢林虽然仍从本原出发,但这个意义上的本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开端,一个自明的真理,或者一个命题。伴随着谢林对本原之沉思的,乃是对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瓦解,也就是对近代形而上学基础主义的瓦解。具体来说就是,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都在寻找一个稳靠的出发点,保证整个存在—知识的真理性,但谢林藉由“不可预思之在”表明,这个最确凿无疑的东西,这个“先于一切可能的绝对的在先者”,并不指向存在者,并不指向理性中的全体,而他在对黑格尔批判中也同时表明,全体不可能为自身提供存在的基础,否则它就要超出自身的思辨同一性。近代哲学的两大诉求——基础和真理——根本就是相悖谬的东西,解决这个悖谬只能诉诸在自由的三重层次中得到完成的本原,但自由也同样意味着“无根基”,意味着存在的发生是一个无根据的“事件”,意味着存在者整体的偶在,也意味着充足理由律的断裂,因此可以说,“自由体系”的底色就是彻彻底底的“虚无主义”。
如果说谢林的黑格尔批判道出了后者在思辨唯心论中隐藏的事实,进而终结了一般意义上的德国唯心论,那么他在对本原的重构中,通过完成这个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中具有中心地位的词语,也同时终结了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唯心论传统,即“在场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是“存在者是什么”,也就是以“同一律”为存在者整体的基本规则来言说存在者,尽管在柏拉图主义传统中,有“善”或者“神”这样的超—存在者来为存在者整体存在的事实进行一种比喻性的说明,但“在场形而上学”仍然用对待存在者的方式对待它们。而谢林通过本原的二重性和对“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区分,指明了囿于“同一律”的“在场形而上学”混淆了对存在者进行言说的谓述意义上的“是”,和作为存在发生事件的“是”,同时也指明了,让存在者存在的那个东西,自身不可能是存在者,它根本就在“同一律”——不管这种同一律是思辨得还是非思辨的——的范围之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以“存在者是什么”为其开端的形而上学在谢林这里得到了诊断性克服,而他以“肯定哲学”为主导方向的“自由的体系”则指向另一重可能的开端:

也就是说,只要本原是自由,自由始终在发生,那么从本原出发的哲学,就是一种朝向未来的“希望哲学”,主导性的问题不再是“存在者是什么”,而是“存在者将是什么”。[注]Ebd, S. 204..每个哲学家毕生都只有一个主导性词语,谢林的主导词语正是“本原”,这个词让他回溯了形而上学的开端,把他引到了对形而上学的克服上,或许在黑格尔的影响如日中天的时候,谢林的晚期哲学显得不合时宜,但这并不妨碍,在他之后会有倾听者和“同道中人”。[注]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不可预思之在与本有——晚期谢林与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王丁译,载于《哲学分析》,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