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以宋代小说为考察中心
□ 李建军
内容提要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结构要素,也是“具有真正人性轮廓”的伦理载体,通过人物塑形切入叙事伦理可以纲举目张。从共时性层面看,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叙事伦理在文言与白话文本中有不同呈现,就宋代而言,传奇与话本中士人塑形的悲喜格调之别,折射出叙事主体关于“乐”“教”孰先的伦理考量,女性形象塑造的情理意蕴之别,凸显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同为男性性别叙事对女性的伦理诉求之异。从历时性层面看,与唐代相较,宋代小说的叙事主体有更精准的伦理介入,使文本有更显明的意图伦理。综合来看,宋代传奇与话本互动而使叙事技巧更为丰富、士人伦理与市民伦理互渗而使文本伦理更趋世俗,从叙事和伦理两个维度推动着叙事伦理的变迁,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叙事伦理是当代叙事学研究“伦理转向”的重要产物,也是文学伦理学研究“叙事转向”的必然结果,①更是小说研究超越传统道德批评和叙事形式分析、绾合叙事与伦理的新颖视角。关于叙事伦理的内涵与分类,东西方学者有不同理解,代表性观点如表1 所示②:

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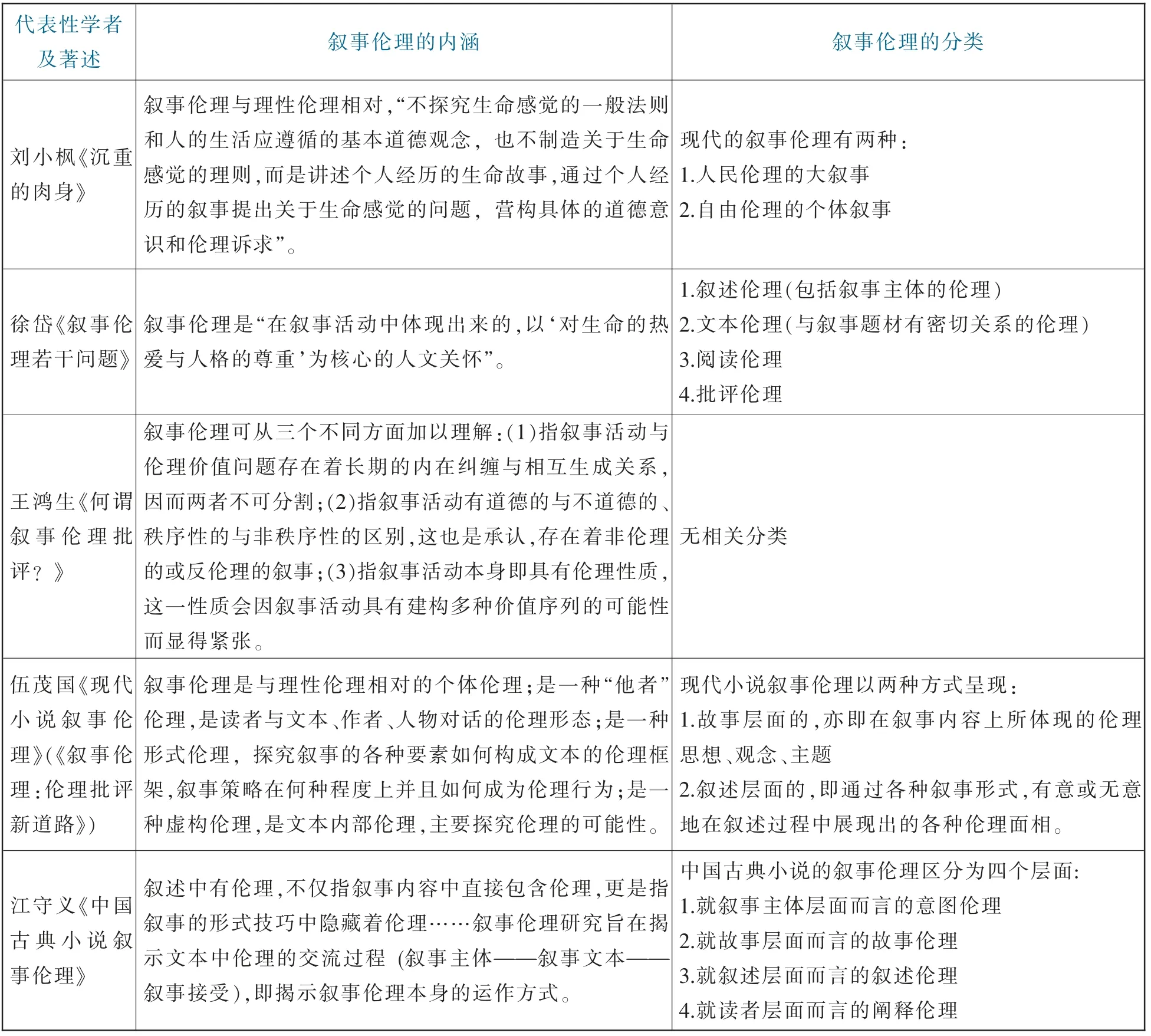
代表性学者及著述叙事伦理的内涵叙事伦理的分类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叙事伦理与理性伦理相对,“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1.人民伦理的大叙事2.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徐岱《叙事伦理若干问题》叙事伦理是“在叙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以‘对生命的热爱与人格的尊重’为核心的人文关怀”。1.叙述伦理(包括叙事主体的伦理)2.文本伦理(与叙事题材有密切关系的伦理)3.阅读伦理4.批评伦理王鸿生《何谓叙事伦理批评?》叙事伦理可从三个不同方面加以理解:(1)指叙事活动与伦理价值问题存在着长期的内在纠缠与相互生成关系,因而两者不可分割;(2)指叙事活动有道德的与不道德的、秩序性的与非秩序性的区别,这也是承认,存在着非伦理的或反伦理的叙事;(3)指叙事活动本身即具有伦理性质,这一性质会因叙事活动具有建构多种价值序列的可能性而显得紧张。无相关分类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叙事伦理:伦理批评新道路》)叙事伦理是与理性伦理相对的个体伦理;是一种“他者”伦理,是读者与文本、作者、人物对话的伦理形态;是一种形式伦理,探究叙事的各种要素如何构成文本的伦理框架,叙事策略在何种程度上并且如何成为伦理行为;是一种虚构伦理,是文本内部伦理,主要探究伦理的可能性。现代小说叙事伦理以两种方式呈现:1.故事层面的,亦即在叙事内容上所体现的伦理思想、观念、主题2.叙述层面的,即通过各种叙事形式,有意或无意地在叙述过程中展现出的各种伦理面相。江守义《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叙述中有伦理,不仅指叙事内容中直接包含伦理,更是指叙事的形式技巧中隐藏着伦理……叙事伦理研究旨在揭示文本中伦理的交流过程(叙事主体——叙事文本——叙事接受),即揭示叙事伦理本身的运作方式。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伦理区分为四个层面:1.就叙事主体层面而言的意图伦理2.就故事层面而言的故事伦理3.就叙述层面而言的叙述伦理4.就读者层面而言的阐释伦理
综合上述各家观点,笔者认为,叙事伦理是与理性伦理相对的个体伦理,是叙事活动中主体、文本、受众等因素在价值维度交互影响所呈现的伦理现象,叙事伦理主要探讨“故事以及故事讲述领域与道德价值的交叉性”。具体到中国古代小说,笔者基本赞同江守义教授对叙事伦理的四分法(意图伦理、故事伦理、叙述伦理、阐释伦理)。
实际上,叙事作品的核心是人物,叙事伦理的各个层面都与作品中人物设计和形象塑造即人物塑形息息相关,通过人物塑形切入叙事伦理可以纲举目张,这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尤其如此。
一、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要素,东西方学者尽管对小说的构成要素意见不一,但大都认为人物不可或缺。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指出:“小说的分析批评通常把小说区分出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③布鲁克斯、华伦《小说鉴赏》认为:“我们一般同意称之为小说的所有作品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情节、人物和主题。”④《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长篇小说是由情节、人物、场景或背景、叙述方法与观点、篇幅、神话/象征主义/意义等六个要素构成,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些法国新小说的创作者故意贬低人物这一因素,主张优先考虑对象和过程。但是真正的长篇小说家依旧是人物的塑造者”。⑤西方无论三要素说还是六要素说,人物都是核心要素。中国学者一般同意这样的观点:“环境、人物、情节构成小说的三大要素,人物是小说的核心。”⑥可见东西方学者大都意识到人物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黄霖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点就是‘原人’,不但从‘人’出发和最终服务于‘人’,而且其理论的构建也是与‘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的面貌密切相关的。”并进一步引申道:“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与小说理论时,是否能走自己的路,探索与总结一种立足在本土的而不是照搬或套用西方的、以论‘人’为核心的而不是以论‘事’为中心的理论呢?”⑦诚哉此言,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不能重“事”而轻“人”,仍旧需要“原人”(以人为本原)。
人物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不是仅仅充当行动元、发挥叙事中的结构作用。西方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常将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抽象化、符号化为结构成分,罗兰·巴特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人物的概念是次要的,完全从属于行动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说,可能有无‘性格’的故事,却不可能有无故事的性格。这一观点曾经为古典文学理论家们所重新阐发。人物直至当时只是空具其名,只是一个行为施动者……结构分析从一开始就极其厌恶把人物当作本质来对待,即使是为了分类。”⑧菲尔拉拉指出:“在虚构作品中,人物是用作结构成分的,即虚构作品的事物和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人物而存在的,而且事实上,正是通过与人物的关系它们才得以具备使自己产生意义并可以理解的连贯性和合理性的。”⑨但这样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另有学者仍将人物视为人性、个性、心理本质、性格类型等因素的载体,如乔治·卢卡契说:“人物只有在我们共同体验了他们的行动之后,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面貌,获得具有真正人性的轮廓。”⑩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力图将上述两种观点融汇,如里蒙-凯南说:“在本文中,人物是语词结构的交节点,在故事中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前)语言的抽象物或构造。”詹姆斯·费伦将人物看成叙事的一个因素,但同时具有三个维度——模仿的(作为人的人物)、主题的(作为观念的人物)和综合的(作为艺术建构的人物)。笔者赞同里蒙-凯南、詹姆斯·费伦的观点,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结构要素,也是“具有真正人性轮廓”的价值载体。
小说的人物塑造在展现“真正人性轮廓”之际,必然涉及人之为人的伦理属性。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援引署名阿伦的法国批评家观点,指出小说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表现“纯粹之热情,诸如:梦想、欢乐、悲哀以及一些难以或羞于出口的内省活动”,并认为“历史,由于只注重外在行动的缘故,必然要受命定论所左右。而小说则不同,一切都体现着人性,认为现存的一切情感都是有意识的,甚至连热情、犯罪和悲痛也没例外”。强调小说“一切都体现着人性”,表现“一些难以或羞于出口的内省活动”,这就必然涉及人物的道德考量和伦理判断。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更为直接显豁。荀子云:“人之所以为人者,非持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又云:“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有辨”“有义”等人的伦理属性一直是中国文艺作品表现的重点,宋代陈郁《藏一话腴》指出:“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从写形、传神、写心三个递进的层面,强调展现人物“君子小人”之分、“贵贱忠恶”之别的伦理面相。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往往都有较为明确的伦理用意。先看文言小说。洪迈撰《夷坚乙志序》明确提出“不能无寓言于其间”,其写人“丑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见之”、“丑而姓名不可不著者显揭之”,寓意则在“惩凶人而奖吉士,世教不无补焉”。洪迈“寓言于其间”之论在文言小说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古代文言小说功能在“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其中“助名教”主要就是通过叙述人物的善恶与遭际的吉凶,托寓作者劝善惩恶的伦理用意。再看白话小说。罗烨《醉翁谈录》作为宋人说话资料汇编,开篇《小说引子》即云:“自古以来,分人数等:贤者清而秀,愚者浊而蒙。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恶。好恶皆由情性,贤愚遂别尊卑。”从伦理道德层面区分人之贤、愚、秀、蒙、好、恶。接下来《小说开辟》论及小说功效,又云:“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论及说话艺人通过塑造“国贼”“忠臣”的人物形象,感动观众的同时又寓教化于其中。说话是中国白话小说的重要源头,说话艺人通过人物塑形而托寓劝惩的叙事技法对白话小说影响深远。
小说在人物塑形中的伦理考量、伦理呈现乃至伦理教诲,是贯穿多数小说叙事伦理的一根红线。叙事主体(主要指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层面的意图伦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技巧在文本中或隐或显地凸显出来,其中通过命运展示、遭遇讲述、关系设计、人物对比、人物评论等关涉人物塑形的方式呈现出来,无疑更为形象、效果更好。故事层面的故事伦理,虽然侧重于分析小说题材、内容本身所蕴含的伦理意蕴,但人物塑形往往是故事外壳包裹中的内核,故事的伦理意蕴多数时候关联于人物善恶贤愚之品性及其决定的沉浮穷通之命运。叙述层面的叙述伦理,关注叙述交流、叙事视角、叙事时空等叙事形式层面的伦理表达,也与人物塑形密不可分,因为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往往是多种叙事形式综合运用的结果,通过还原人物形象的伦理建构过程即可管窥到相应的叙述伦理。读者层面的阐释伦理,关注读者阅读、接受文本过程中的伦理体验、伦理判断和伦理认同,其中人物性格及遭遇、人物伦理面相及命运,往往是读者进行伦理衡量的核心要素。总之,从叙事主体、叙事文本到叙事受众整个链条,从意图伦理、故事伦理、叙述伦理到阐释伦理各个环节,人物塑形往往都是叙事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叙事伦理的重要依托和载体。
人物塑形和叙事伦理密切相连,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主体塑造的同一阶层(如士农工商)人物形象可能面貌迥异,叙事伦理也随之判然不同。此处有必要说明一下,小说的叙事伦理具体到某个文本,也许“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但某个时代的小说文本的整体,还是会在叙事伦理上呈现出带有共性的时代特质,并涉及“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基本道德观念”。从人物塑形的角度观察,某个时代、某类文化主体的小说文本在塑造某个阶层、某类形象时,会在叙事伦理上呈现某些共性。通过人物塑形寻绎出这些共性,可以勾勒出叙事伦理的时代演变轨迹,并从中管窥到“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的迁异曲线。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伦理在唐宋之际有一个转折,通过唐宋小说的人物塑形比对可以寻绎出这种转折。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小说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两类小说的人物塑形、叙事伦理各具面貌但又有时代共性。立足宋代小说的人物塑形探讨叙事伦理,可以管窥中国从中古走向近世过程中的伦理迁异及其文学影响。宋代文言小说可以分为笔记体和传奇体,其中人物塑形比较鲜明、叙事伦理比较显明者还是传奇体,故而笔者选取宋传奇为考察对象。李剑国《宋代传奇集》辑录宋代130位作者创作的传奇391 篇,囊括宋传奇的精华,本文即以此为据。宋代白话小说即话本小说的判定,学界有较大争议,笔者综合胡士莹、程毅中、陈桂声等诸家观点,认为《碾玉观音》等35 种小说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等3 种讲史话本、另有1 种说经话本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共39 种话本小说的主体内容完成于宋代,虽后世有增删修润,但仍应判定为宋话本。笔者下面即以这391 种宋传奇、39 种宋话本为基本素材,考察宋小说中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二、宋代小说的士人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与话本的编创主体、接受主体有士人与市民之别,两类小说分别反映着不同主体的文化精神和伦理意识。有学者已经指出:“文言小说基本属于由正统文人创作的士人文学,突出反映着士人意识和士人生活,与文人诗文具有相同的文学渊源以及相通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宋传奇的创作和阅读基本上是在士人圈中,属于士人叙事。宋话本的口传环节是典型的市民叙事,编写环节虽然经过书会才人等文人的加工润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文人叙事的情趣和印痕,但主导性的还是市民情趣,因此宋话本的主体还是应归入市民叙事。
(一)宋传奇与话本中士人形象之异
我们首先考察宋传奇与话本中的士人形象差异。从功名事业层面而言,宋传奇中的士人大多数命途多舛、沉沦落魄。或皈依佛道,如《青琐高议·慈云记》中的袁道因病误考而落拓之际,被僧人用巨瓮幻化之事点化而遁入空门;或愤世嫉俗,如《青琐高议·王寂传》中的王寂落魄不售,后走上杀官造反之路;或遇鬼而亡,如《云斋广录·无鬼论》中“蹉跎场屋十余年”的黄肃欲著《无鬼论》以解天下之惑,却屡屡遇鬼,最后暴卒。
与宋传奇中的士人命运逆多顺少相反,宋话本中的士人则多能逢凶化吉、发迹变泰,如《赵伯昇茶肆遇仁宗》中的秀士赵旭初因一字差错而落第,后于茶肆遇君而发迹;再如《范鳅儿双镜重圆》中的范希周原是读书君子,后陷于贼中并与吕氏成婚,王师进剿之际夫妻分离,再后范氏招安到军中任职,并与吕氏破镜重圆。当然,宋话本中的士人也有落魄不偶者,如《陈可常端阳仙化》中的不第秀才陈可常被诬陷与郡王府中侍女新荷私通,致招杖楚,后于沉冤得雪之际坐化;又如《西山一窟鬼》中的落第秀才吴洪娶鬼妻、遇群鬼,后舍俗出家、云游天下。但这些话本中的士人落魄遭遇最后都有一个神奇的解释和光明的结局:陈可常是五百罗汉中名常欢喜尊者,“只因我前生欠宿债,今世转来还。吾今归仙境,再不往人间”;吴洪是上界甘真人采药的弟子,“凡心不净,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堕落。今生罚为贫儒”、“备尝鬼趣”,“今既已看破,便可离尘办道”。概言之,都是“上界仙人有失误——谪下凡世为贫儒——受尽劫难重为仙”这样的叙事逻辑,故事中的落魄士人前途还是光明的。
从情爱婚恋层面而言,宋传奇中的士人只有少数能够得遂所愿,其余大多数则情缘夭折:或人鬼(妖)殊途而分离,如《越娘记》中书生杨舜俞与女鬼越娘的始合终离;或门第有别而劳燕分飞,如《王幼玉记》中豪俊之士柳富与青楼女子王幼玉,彼此中意却不能成为眷属;或家庭干涉而酿成悲剧,如《青琐高议·远烟记》中士人戴敷因家资耗尽,其妻被岳父夺归而亡,夫妻只能人鬼相逢,最后戴敷亦入水而亡。
与宋传奇中的士人婚恋多以悲剧告终不同,宋话本中的士人婚恋常以喜剧收官。如《风月瑞仙亭》中成都秀士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两情相悦,于瑞仙亭做成夫妇,恐文君之父卓王孙怪罪,两人连夜私奔成都,以开酒肆度日;后司马相如以辞赋为皇帝所激赏,征召于朝廷,卓王孙闻讯,即至成都,与文君父女相认;再后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劝谕巴蜀,衣锦还乡。又如《张生彩鸾灯传》中越州书生张舜美与丽人刘素香始合、中离、终团圆的离合喜剧。再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西洛才子张浩与东邻之女李莺莺私定终身、暗度陈仓,而后历经波折、终获幸福的爱情喜剧。
宋传奇中的士人形象,从功名事业层面而言是多否少泰,从情爱婚恋层面而言是多离少合;而宋话本中的士人形象,从功名事业层面而言则多发迹变泰,从情爱婚恋层面而言则多如愿以偿。两相对照,可见宋传奇中的士人形象更多悲情色彩,而宋话本中的士人形象则更多喜剧情调。这种人物塑形的差异可能与士人与市民的审美心理歧异有关。士人可能更多的以悲为美,创作者通过讲述本阶层人士的悲情故事、塑造士人的悲情形象,书写自己对于同类之命运的悲情感喟,并在感喟中获得美感,阅读者也从悲情故事的咀嚼、悲情形象的体认中获得美感;而市民可能更多的以喜为美,创编者和阅读者都乐于在浅俗的喜剧故事中获得虚幻的心理满足,而宋话本中的喜剧故事多以士人为主角,也隐隐透出当时市民阶层对士人的艳羡。
(二)士人形象差异的叙事伦理分析
宋传奇与话本中士人形象塑造的悲情色彩与喜剧情调之别,从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层面分析,会有更深的认识。
宋传奇中负心婚变甚而存心骗财骗色的士人不在少数,叙事主体在塑造这类人物时大多会有比较显明的伦理判断,或者借助文本人物之口评价,或者通过篇末议论等方式进行公开的伦理介入。《夷坚志·满少卿》中的满生,本为淮南望族,后因跅弛不羁、浪游四方而陷入困顿,幸得焦大郎相助。满生私通焦大郎之女,既而事露,受到焦大郎的斥责,满生于是娶焦女为妻。后来满生进士及第还乡,被严毅的叔父安排迎娶官宦人家女子为妻。满生的负心婚变导致焦氏父女抱恨而亡,最后自己也被冤魂索命。对这样一出士人负心婚变招致冤报的悲剧,叙述者通过文本人物之口进行了明确的伦理评价。当满生私通焦女之际,即被焦父斥为“何期所为不义若此?岂士君子之行哉”;当满生被索命后,焦女托梦给满生之妻云“满生受我家厚恩,而负心若此,自其去后,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继沦没,年移岁迁,方获报怨,此已幽府伸诉逮证矣”。叙述者借文本人物之口对满生“不义”“负心”的道德谴责,已经清楚表达出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另外,《青琐高议·龚球记》中的官宦子弟龚球骗财致人死命,后被冤魂索命,叙述者进行了公开的伦理介入,通过篇末议论“议曰:冤不可施于人,阴报如此,观者宜以为戒焉”表达了清晰的意图伦理。《青琐高议·李云娘》中的士人解普先骗财、后害命,亦被冤魂索命,叙述者首先通过李云娘之口对其进行了道德鞭挞,“我罄囊助子,子不为恩,复以私计害我性命,子之不仁可知也”;文末又通过议论“议曰:逋人之财,犹曰不可,况阴贼其命乎?观云娘之报解普,明白如此,有情者所宜深戒焉”,进行公开的伦理介入,表达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
宋话本中有轻诺寡信、儿戏婚姻的士人,但叙事主体并不进行伦理介入,反倒将其视为文人风流。《苏长公章台柳传》叙苏轼为临安太守时,宴请佛印之际,召妓女章台柳祗应清唱,苏轼赏其文才,醉中允其从良,并答应娶之。章台柳在家专候一年,却不见来娶,只得另嫁他人。又过一年,苏轼方忆起章台柳,寻其芳迹,知其已嫁,于是写诗责其“终身难断风狂性”。章台柳回书一绝,以“一任风吹不动摇”表明其志。苏轼读罢连声赞叹,遂请佛印等共观之,每人各有题咏,诗罢,众人大笑,尽欢而散。故事中的苏轼居高临下、言而无信,但说话人并未切责之,而是将其作为文人吟弄风月的笑谈,这从散场诗“至今风月江湖上,千古渔樵作话传”可知。
宋话本中还有讲述名士前世乃是触犯色戒之僧人的“诨话”,叙事主体也不进行明显的伦理介入,而是着眼于此人此事的娱乐性。《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五戒禅师奸淫禅寺收养的女子红莲,其至交明悟禅师知道后,作偈讽谕,五戒羞惭圆寂。明悟恐其来世“不得皈依佛道”,于同日圆寂“赶”去。五戒禅师托生为苏轼,明悟禅师托生为佛印。佛印与苏轼形影相随,谈禅论道,终于使得苏轼“因此省悟前因,敬佛礼僧”。后来苏轼离世得为大罗天仙,佛印圆寂得为至尊古佛,二人俱得善道。说话人对五戒禅师奸淫红莲之事并无公开的伦理介入,相反还通过诗词骈语竭力铺陈细节,将此事作为娱乐观众的“猛料”,于此可见叙事主体的伦理意识是让位于娱乐需要的。当然,说话人也有劝惩意图,那就是嘲笑起初“不信佛法”的苏轼不过是前世触犯色戒的禅师转世,而后来的苏轼“省悟前因,敬佛礼僧”就得“善道”,离世得为大罗天仙,说话人通过这样的故事逻辑劝导受众“敬佛礼僧”。但这样的劝惩仍是建立在人物的谐谑故事基础上的,娱乐性仍是文本的首要因素。
由上可知,宋传奇与话本中士人塑形的悲、喜格调之别,往往蕴含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考量。宋传奇通过士人的悲剧故事和显明的伦理介入,有强烈的劝善惩恶意图;宋话本偏重叙述士人的喜剧故事、风流故事,虽也有一定的劝惩意识,但伦理介入并不显明,叙事的优先考虑是娱乐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评价《京本通俗小说》“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其中“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云云点出了早期话本乐(“娱心”)重于教(“惩劝”)的文本特征。《苏长公章台柳传》、《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等宋话本用苏轼等士人的风流故事做猛料,并不是要从伦理上进行劝惩,而是借此娱乐观众,正是乐重于教的典型体现。
三、宋代小说的女性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与话本中的女性形象千差万别,同一类型的女性形象也往往面貌殊异,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其中丰富的文化意蕴。我们不妨把宋小说中主要的女性形象分为情女、贞女、仙女、浪女和娼女五种,下面分类考察传奇与话本人物塑形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叙事伦理。
(一)情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清尊录·大桶张氏》《夷坚志·鄂州南市女》《投辖录·玉条脱》与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下简称《闹樊楼》)皆述“盗冢复生”故事,情节模式雷同,并都刻画了痴情女子形象,且文本间有承传关系,可以进行对比分析。三种传奇文本中,《玉条脱》刻画最细,故以之为考察对象。《玉条脱》与《闹樊楼》的故事情节和叙事时间安排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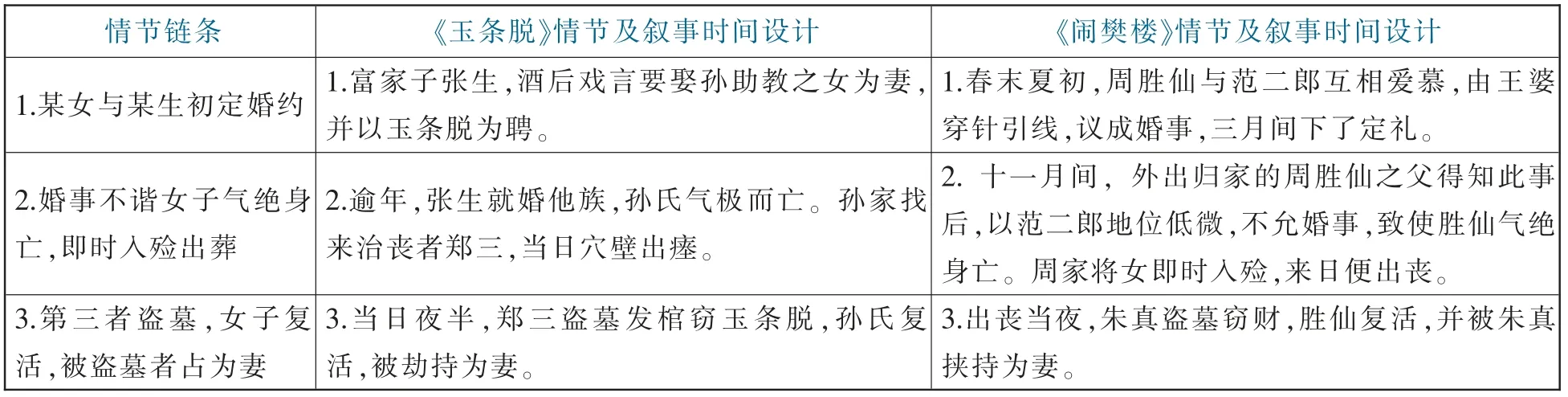
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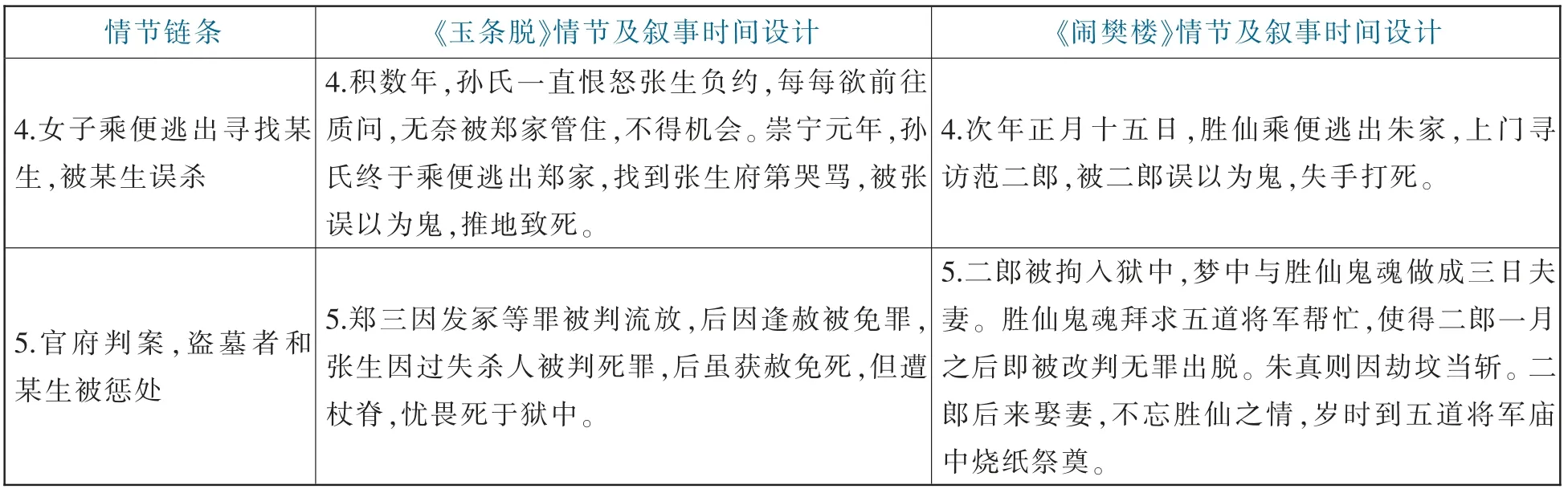
情节链条《玉条脱》情节及叙事时间设计《闹樊楼》情节及叙事时间设计4.女子乘便逃出寻找某生,被某生误杀4.积数年,孙氏一直恨怒张生负约,每每欲前往质问,无奈被郑家管住,不得机会。崇宁元年,孙氏终于乘便逃出郑家,找到张生府第哭骂,被张误以为鬼,推地致死。4.次年正月十五日,胜仙乘便逃出朱家,上门寻访范二郎,被二郎误以为鬼,失手打死。5.官府判案,盗墓者和某生被惩处5.郑三因发冢等罪被判流放,后因逢赦被免罪,张生因过失杀人被判死罪,后虽获赦免死,但遭杖脊,忧畏死于狱中。5.二郎被拘入狱中,梦中与胜仙鬼魂做成三日夫妻。胜仙鬼魂拜求五道将军帮忙,使得二郎一月之后即被改判无罪出脱。朱真则因劫坟当斩。二郎后来娶妻,不忘胜仙之情,岁时到五道将军庙中烧纸祭奠。
由上可知,《玉条脱》乃是富家子张生负约别娶,致使孙氏一腔期待化为泡影,进而气绝身亡,该篇隐寓对张生儿戏许婚、致人死命的谴责,这从文本安排张生忧畏死于狱中的结局可知。另外,篇末议论“因果冤对,有如此哉”,亦可见叙事主体公开的伦理介入。《闹樊楼》中,悲剧起因乃是胜仙之父不同意其女与地位低微的范二郎的婚事,致使胜仙气绝身亡,该篇当然隐寓对周父的谴责,但重心却在刻画市井男女生死以之的爱情追求,散场诗“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道出了该篇主“情”的叙事旨趣。从人物塑形的角度看,《玉条脱》中的孙氏与《闹樊楼》中的胜仙同为痴情女子,当然,后者对爱情的追求更为主动、执着,更显市井女子机智泼辣、热情大胆等性格特质。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两个文本的叙事时间设计有伦理意蕴。《玉条脱》的故事时间跨越数年,这从“逾年”“积数年”等较模糊的时间陈述可知,而文本仅千字左右,因而文本呈现出快速叙事的趋势,其实这两点(较模糊的时间设计、快速叙事)也是大多数文言小说的共性。《闹樊楼》在改编文言小说之际,将故事时间设计为有较清晰的起讫时刻,即从春末夏初到次年二月间,总时长缩短为不到一年,而文本共七千字左右,因而文本呈现出缓速叙事的趋势,当然这两点(较清晰的时间设计、缓速叙事)也是大多数话本小说的共性。《玉条脱》故事时间的长时段设计,最核心的是孙氏复活后“积数年”“每言张氏,辄恨怒忿恚如欲往扣问者,郑每劝且防闲之甚”,可见孙氏对张生的怨怒“数年”犹存,这里反映出张生负约别娶带来了严重后果,折射出文本对张生儿戏许婚的道德鞭挞。《闹樊楼》故事时间的缩短,有利于提高文本密度,凸显市井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急切和炽热,而将道德劝惩暂时隐退。
(二)贞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和话本中都有不少的贞女(贞妇)形象,既有忍辱负重最终复仇者,也有刚烈不屈守贞完节者。先看前者。《青琐高议·卜起传》叙卜起之妻在丈夫被从弟德成杀害,自己被迫改嫁凶徒的情况下选择隐忍,后来当儿子长大、德成不在家之际,母子到官府告发,使德成伏诛。卜起妻对于复仇时机的选择,透露出一种隐忍中的智慧。类似的这种智慧在话本中表现得更为鲜明。话本《错斩崔宁》中的刘贵之妻(刘大娘子),在丈夫被贼人杀害,崔宁和刘小娘子冤死后,衣食无靠,同仆人收拾包裹回娘家。路遇强盗静山大王,仆人被杀,刘大娘子急中生智,假称被杀之人乃自己被媒人哄骗而嫁的丈夫,自己极不中意,如今被杀亦是为己除害,还表示情愿服侍静山大王。后成为压寨夫人,得知静山大王乃是杀害前夫刘贵的真凶,心头暗暗叫苦,但表面上欢天喜地。等次日捉个空,便径直到临安府告官,使得静山大王伏诛。刘大娘子“看决了静山大王,又取其头去祭献亡夫”。刘大娘子的坚韧、机智和忍辱复仇,充分展现出市井妇女的斗争智慧。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万秀娘也是一位忍辱复仇的市井妇女。传奇中的卜起妻,话本中的刘大娘子和万秀娘,都是经历人生惨祸又被迫委身于凶徒的妇人。她们的忍辱复仇是一致的,但相较而言,话本中的刘大娘子和万秀娘更能屈能伸,更富于生存智慧,更深谙斗争策略。究其原因,可能与卜起妻为官宦家眷、刘大娘子和万秀娘为市井妇人息息相关,也与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文本道德观念之强弱颇有干系。刘大娘子和万秀娘的委身从贼、伺机复仇,文本的赞许态度足以呈现市民叙事的志趣。
再看传奇和话本中刚烈不屈守贞完节者。吕夏卿《淮阴节妇传》叙淮阴妇因年少美色而被里人骗娶,其夫被害。淮阴妇得知真相后,诉于官,使里人伏法。之后,淮阴妇痛悔“以吾之色而杀二夫”,“遂赴淮而死”。话本中也有类似的贞妇,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的汴梁秀才之妻张如春。张在丈夫赴任途中被猢狲精申阳公劫走,宁死而不受辱,最终在紫阳真人帮助下逃出魔掌、夫妇团圆。仔细比较淮阴妇与张如春的贞烈之举可以发现,前者痛悔“以吾之色而杀二夫”“遂赴淮而死”的举动可能更为刚烈,体现出士人叙事更为浓烈的道德意识。
概言之,不管是忍辱负重最终复仇者,还是刚烈不屈守贞完节者,宋传奇与话本中的贞妇形象都有差异。比较而言,传奇中的女性有更强的道德意识,话本中的女性则有更强的生存意识。另外,话本中的女性更有斗争策略,更有市井女性的机警和坚忍。
(三)仙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花月新闻》与话本《董永遇仙传》都刻画了下嫁人间男子的女仙形象,可以进行对比分析。《花月新闻》叙姜寺丞肄业乡校时,偕同舍生出游神祠,睹捧印女子塑容端丽,戏解手帕,系其臂为定。后来该女主动到姜家为妇,家人呼为仙妇。不久,仙妇在道士帮助下,击杀怀忿前来行凶的昔日相好。姜母及妻相继亡故,女抚育其子如己出。靖康之变,不知所终。文中仙妇可谓非凡之人,身上集中了端丽多情、贤明孝顺、友善多才、尊礼有义、宽厚慈爱等诸多优点,反映了士人基于男性视角的审美理想和情爱期待。
话本《董永遇仙传》叙东汉丹阳人董永,卖身于傅财主为佣以葬父。玉帝感其至孝,遂差织女降下凡间,与董永为妻,助其织绢偿债,百日完足,依旧升天。董永至孝事,被府尹表奏朝廷,董永被封兵部尚书。织女本是奉玉帝之命下嫁董永的天仙,但话本中的形象却浑似市井女子,风流绝妙、自荐枕席又颇有脾气,还能以非凡之技帮助夫君,反映了市井细民基于男性视角的审美理想和情爱期待。
《剑仙》中的仙妇与《董永遇仙传》中的织女,都是由于某种因缘而下嫁人间男子的女仙,两者皆有美艳之貌,都有相夫之功,反映了男性作家们共同的心理期待。当然,两者又有细微差异,前者(仙妇)具有贤明孝顺、宽厚慈爱等宗法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道德油彩,后者(织女)则更具市井女性较少道德约束的自在风习。两者的“同”反映出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同为男性性别叙事对女性的情爱期待,两者的“异”则反映出宋代士人与市民在女性伦理上的不同诉求。
(四)浪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传奇《鬼董·陈淑》与话本《刎颈鸳鸯会》中的女主角都是水性杨花导致数位男人丧命的浪女典型,可以对读。《鬼董·陈淑》叙美而慧的陈淑,不满丈夫困窭而私通富家子刘生,丈夫欲执之见官,陈淑恨怒,将夫灌醉,杀死并肢解,后来陈淑被处死。文末有云“刘父见淑……乃械以陈邑,淑竟论死。嘻,异哉”,叙事主体用伦理介入的公开方式,清晰地表达出善恶有报的伦理评判。
《刎颈鸳鸯会》叙乡村女子蒋淑珍先与邻居阿巧偷情,后嫁与某二郎为妻,又与家中教席偷情,奸情败露后被逐归娘家。再嫁商人张二官,又与对门店中朱秉中偷情,终为张二官所知,被杀身亡。话本将蒋淑珍主动诱引三位男人的经历叙述得活灵活现,充分展现了蒋淑珍的放浪成性。当然,蒋淑珍的放浪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己被丈夫张二官持刀杀死。话本最后议论道:“故知士矜才则德薄,女衒色则情放。若能如执盈,如临深,则为端士、淑女矣。岂不美哉?惟愿率土之民,夫妇和柔,琴瑟谐协;有过则改之,未萌则戒之,敦崇风教,未为晚也。”清晰地点出了文本借蒋淑珍放浪致死、作茧自缚的悲剧,以“敦崇风教”的伦理意图。
《鬼董·陈淑》中的陈淑与《刎颈鸳鸯会》中的蒋淑珍,都是因偷情而致使数人丧命的淫妇典型,两个文本都通过女主角的毁灭表达了惩戒之意。但不同的是,陈淑与刘生的私通可能并非女方主动,文本云“(陈淑)过刘氏肆,刘子见之喜,呼入饮之,还其衣,予之千钱。他日复来,又益予之,寖挑谑及乱”,点出是刘生的挑谑导致了两人私通。而话本中的蒋淑珍,先后主动与三位男性偷情,显得更为放浪。实际上,如蒋淑珍等更为放浪的女性形象,可能才更加符合市井细民的审美情趣。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到,在塑造荡妇形象之际,士人叙事往往是穷原究委、重在惩劝,而市民叙事则是铺陈细节、劝百讽一。
(五)娼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代文言小说集《贵耳集》《浩然斋雅谈》和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以及话本《宣和遗事》,都涉及北宋末年名妓李师师,但形象差异极大,其中的伦理意蕴叵耐咀嚼。下面用表格呈现上述四种文本的主要内容(见表3):

表3
从上图可知,就故事情趣而言,《贵耳集》《浩然斋雅谈》两种文本,均将争风吃醋的狎妓丑闻美化为诗词风骚的文人雅谈,而《李师师外传》更是避开庸俗的三角情爱,叙述师师初“幸”于徽宗、后自杀保节之事,更显文人情趣和风节,这些文本都透露出士人雅趣,是典型的士人叙事;《宣和遗事》则津津乐道于李师师与宋徽宗、贾奕三角纠缠的低俗情节,充溢着市井俗趣,是典型的市民叙事。
就人物形象而言,文言小说文本中,《贵耳集》《浩然斋雅谈》《李师师外传》三种文本所塑造的李师师形象,或为雅妓,或为义妓,或为风雅义妓,都是文人妙笔将市井娼妓美化、典型化的结晶。相对于文言小说文本中的雅妓、义妓,话本《宣和遗事》中的师师则是一位矫情卖俏的俗妓、精明狡狯的黠妓、重利轻义的陋妓,这是市民叙事中不是美化、而是俗化的人物原型,也许这才是市井娼妓的本来面貌。
就叙事伦理而言,《贵耳集》《李师师外传》中叙事主体通过篇末议论进行的伦理介入,大义凛凛,鲜明表达出文本借师师其人其事,讽谏朝政、匡正伦常的政治用意和伦理用心。而《宣和遗事》相关内容中的叙述者介入,当然也有伦理用意,但主要还是市民阶层的世俗告诫,与《贵耳集》《李师师外传》伦理介入的高度不可同日而语。
上面考察了宋传奇与话本中五类女性形象塑造及其叙事伦理,总起来说,士人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涂抹了更厚的道德油彩,寄寓了更多的伦理诉求,有更显明的意图伦理,折射出士人阶层的审美理想;而市民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少道德羁绊,更为接近人物原貌,折射出市民阶层的情爱期待。
四、人物塑形与宋代小说叙事伦理特色
宋代小说人物塑形的叙事伦理特色,通过唐宋对比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小说题材中,婚外恋、青楼恋与世俗伦理冲突最为激烈,其中人物塑形的伦理考量最堪玩味。
(一)唐宋婚外恋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唐传奇《非烟传》与宋传奇《双桃记》都是讲述婚外恋的名篇,然两者的伦理意蕴大相径庭。《非烟传》叙步非烟为功曹参军武公业的爱妾,才貌俱佳。邻家子赵象窥其容貌,为之倾倒,特厚赂阍者传递相思诗函,非烟亦悦其人,两人诗函往来、互通情愫。一日,趁武公业在外值夜,非烟约赵象逾墙相会,尽缱绻之情。自后两人常约会于后庭,终被武公业知晓,赵象跳墙逃逸,非烟被缚于柱上鞭笞而死。非烟“垂髫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本来就很不幸,后来遇到“大好才貌”的赵生传情而点燃婚外恋情烈火,也是情有可原。非烟在恋情曝光被悍夫“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之际,还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可见她对这段恋情的生死相依。该篇在叙事之际,并没有对这段婚外恋情进行谴责,相反倒是对非烟遭遇的深深同情。该篇文末叙洛阳李生有诗句“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嘲讽非烟,结局是:“其夕,梦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叙事主体用非烟的反驳和李生的暴卒,回应了对非烟的道德谴责。因此可以说文本自身并未透露出明显的劝诫意味,而是充溢着婚外恋悲剧所带来的审美震撼。值得注意的是,篇末附有作者议论,曰:“噫,艳冶之貌,则代有之矣;洁朗之操,则人鲜闻乎……非烟之罪虽不可逭,察其心,亦可悲矣。”对赵象和非烟的婚外恋情予以批评,有垂诫之意。但篇末议论的主旨判断“非烟之罪虽不可逭,察其心亦可悲矣”,与文本透露出的同情非烟之不幸而并不责之罪之的真实心态,两者是存有张力、油水分离的。简言之,篇末垂诫只是强加上去的“蛇足”,文本自身并不在伦理化的劝诫,而是诗意化的审美。
唐传奇中婚外恋题材的非伦理化倾向,在宋传奇中被颠覆了,李献民《双桃记》即为典型。文叙已有妻室的李生见到待字闺中的萧娘姿色冠众,乃厚赂同里老妪为通其情。萧娘感其诚,约李生逾墙相会,尽缱绻之情。李欲出妻而娶萧娘,被萧娘劝阻。后萧娘被许嫁刘氏子,至迎亲之日,萧娘自缢于室。篇中叙事有较浓的伦理批评色彩,开篇介绍李生时即云“有里巷李生者,世系颇著,不欲书其名,讳之也”,又云“生赋性不羁”,这里为其讳名的作法和“赋性不羁”的评判已经暗示李生婚外恋的逸出常轨与不合伦理。当李欲出妻而娶萧娘时,萧娘的回答则是伦理气息极浓的说辞,其曰:“不可。夫男子以无故而离其妻,则有缺士行;女子以有私而夺人之夫,则实愆妇德。显则人非之,幽则鬼责之,此非所宜言。愿君自持,无复及此。”后来,萧娘自缢之前的告白更反映出她的伦理困境和情理抉择,其曰:“文君一寡妇也,慕相如之高义,卒往奔之,遂见弃于父母,取讥于后世,为天下笑。此我之所不能也。绿珠一贱妾也,蒙石崇一顾,当赵王伦之乱,犹能效死于前,义不见辱,后世称之。我纵不为文君之奔,愿效绿珠之死,以报李生遇我之厚也。”文本的伦理气息已经很浓,文末的议论更是直白的道德劝诫,曰:“呜呼!人之有情,至于是耶!观其始与李生乱,而终为李生死,其志操有所不移也。使其不遇李生,以适刘氏之子,则为贞妇也明矣。可不尚欤!”既批评萧娘与李生之乱(婚外恋),也肯定其为李生殉情而体现的“志操”,但落脚点还是维护伦理纲常而假设“其不遇李生,以适刘氏之子,则为贞妇也明矣”,因为“贞妇”才是宋人真正称颂的榜样,而萧娘这样为婚外恋殉情的女子只能是惋惜的对象,这样的垂诫真可谓“严冷”。概言之,该篇从文本故事到篇末议论都充溢着浓烈的伦理气息,呈现出典型的宋人面目。
同为婚外恋故事,唐传奇《非烟传》篇末议论(垂诫)与文本倾向(同情)的歧异,反映出叙事主体在伦理判断上的彷徨,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伦理评价上的矛盾,削弱了该篇的伦理力度;而宋传奇《双桃记》篇末议论与文本倾向的高度一致,使得该篇惩戒婚外恋的意图伦理非常显明。
(二)唐宋青楼恋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唐传奇《霍小玉传》与宋传奇《谭意哥》都是讲述青楼恋的名篇,但两者的人物塑形和叙事伦理差异甚大。
《霍小玉传》中的青楼女子霍小玉多情、明智而又刚烈。当李生登科授官将别之际,小玉自知倡家非匹,乃陈短愿,冀以八岁为期尽其欢爱,然后听益另选,自当剪发为尼,可见其多情而又清醒;当李生负约使其抱恨成疾、撒手人寰之际,小玉痛斥李生,并发誓“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又可见其刚烈;当李生为之缟素、哭泣甚哀,小玉又托梦李生,感其相送之情,还可见其刚烈之中的柔情。从伦理角度着眼,该篇并未赋予小玉形象过多的伦理意蕴,而主要是通过悲剧结局,谴责李生背盟负约的伦理背叛。
《谭意歌》中的青楼女子谭意歌自尊自立,渗透着宋人强烈的伦理意识。谭意歌由一个困苦的孤儿被卖为妓女而不甘堕落,凭借才学赢得太守称赞而成功脱籍。后遇茶官张正宇而托付终身,已有身孕后不料张“内逼慈亲之教,外为物议之非”而另行结亲高门。谭闻讯后并未悲观,而是私蓄置产,躬耕教子,自力更生。后三年,张妻谢世,张向谭再三请婚,谭坚持明媒正娶,方有可能。张乃如其请,两人终成眷属。谭意歌为娼并不自贱而是自尊,被弃并不自悲而是自立,散发着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光辉。该篇末尾云:“意治闺门,深有礼法。处亲族皆有恩意。内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后又生一子,以进士登科,终身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茂,呜呼!贤哉!”通过叙述者评论方式进行公开的伦理介入,褒扬意歌之“贤”。
如果说唐传奇《霍小玉传》的意图伦理主要是惩男主角之“过”,那么宋传奇《谭意歌记》则主要是扬女主角之“善”。实际上,叙述青楼恋之宋传奇大多是扬女子之善,如钟将之《义娼传》中的长沙娼“慕少游之才,而卒践其言,以身事之,而归死焉,不以存亡间,可谓义倡矣”,《王幼玉记》中的王幼玉“爱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观之,莫不怆然”,再如前述《李师师外传》中的李师师“烈烈有侠士风”。
婚外恋、青楼恋题材的伦理差异基本可以折射出唐宋传奇的伦理选择,概言之,可谓唐人更宽松、宋人更严苛,唐人或不将劝惩作为文本重心,或进行伦理判断时彷徨游移、出现篇末议论与文本倾向的歧异,宋人则通过叙事主体精准的伦理介入,使文本的意图伦理非常显明。
鲁迅曾评价乐史《绿珠》《太真》二传“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则宋人积习如是也”。其实,该评语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展,用于评价整个宋传奇。“篇末垂诫”可以扩展为“篇有垂诫”,因为宋传奇的垂诫不仅体现于篇末议论中,也化身于文本故事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篇有垂诫”并非宋传奇的专利,前之汉魏六朝和隋唐五代小说,后之明清文言传奇,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宋传奇“篇有垂诫”的独特性在哪里呢?“增其严冷”可谓恰中肯綮。宋代志怪传奇中劝诫意识的浓烈、伦理要求的严苛、垂诫话语的冷峻,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当然,“篇有垂诫”“增其严冷”既是宋传奇的特色,可能也是其短板。鲁迅云:“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指出宋人小说(特指文言小说)“理学化”“多教训”的特色和“修身教科书”的倾向,最终戕害了小说的文艺功能。鲁迅之言,洵为的论,宋传奇的伦理化倾向,既是宋人的特色,也是宋人的不幸。
相较唐传奇,宋传奇人物塑形中有更为显明的意图伦理,叙事主体有更为精准的伦理介入,反映出宋代士人叙事更为强烈的伦理诉求,当然这只是宋代小说叙事伦理的一个侧面。另一面是宋话本所反映的市民叙事“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人物塑形的道德羁绊较少,伦理诉求逊于娱乐需要。宋代士人叙事的教重于乐与市民叙事的乐先于教,构成宋代小说叙事伦理的丰富面相。
值得注意的是,宋小说还存在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双向互动的情景,传奇借鉴市井文艺而呈俗化之势,话本吸纳士人文学而有雅化之风,但总体趋势则是叙事文学更为世俗化,士人伦理有向市井伦理滑动的趋势,世俗化传奇如《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等作品中士人气质的平民化、士人伦理的市井化堪称典型。宋代小说中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的互动,使叙事技巧更为丰富,士人伦理与市民伦理的互渗,使文本伦理更趋世俗,这就从叙事和伦理两个维度推动着叙事伦理的变迁,使得宋代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①尚必武:《从“两个转向”到“两种批评”——论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的兴起、发展与交叉愿景》,《学术论坛》2017年第2期。关于叙事伦理,较早关注者是美国学者基于小说修辞角度的相关论著。首先是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思(Wayne C.Booth)于1961年出版《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有专章“非个人叙述的道德性”论及小说叙事中的伦理问题;1979年发表《批评的理解》(Critical Understanding),多涉及小说伦理问题;1988年出版《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An Ethics of Fiction),构建了小说伦理学的整体框架。接着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1989年出版《阅读叙事:形式、伦理、意识形态》(Reading Narrative:Form,Ethics,Ideology),1996年出版《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Audiences,Ethics,Ideology),都论及叙事中的伦理问题。美国学者还从多个角度探讨叙事伦理,如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n)1987年出版的《阅读伦理》(The Ethics of Reading)。明确提出“叙事伦理”概念的是亚当·桑查瑞·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1997年出版的《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此外,法国学者保罗·利科在(Paul Ricoeur)《时间与叙事》(1983年)、《从文本到行动》(1986年)、《作为他者的自我》(1990年) 等著作中提出“叙述的同一性”问题,关注叙事活动的伦理历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穆勒(Wolfgang G.Muller)《伦理叙事学》(An Ethical Narratology, 2008)、劳拉·柏林(Nora Berning)《建构批判伦理叙事学:跨媒介文学非虚构作品的价值建构分析》(Towards a Critical Ethical Narratology:Analyzing Value Construction in Literary Non-Fiction across Media, 2013)、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unning)《叙事学与伦理批评:同床异梦,抑或携手联姻》(Narratology and Ethical Criticism:Strange Bed - Fellows or Natural Allies? 2015),从伦理叙事学的角度论及叙事伦理。中国学者中,较早关注叙事伦理者是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1999),其后,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2003)、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2008)、谢有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2010)、徐岱《叙事伦理若干问题》(2013)、王鸿生《何谓叙事伦理批评》(2015)、江守义《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2016)等著作和论文对叙事伦理都有精当阐发。
②纽顿《叙事伦理》相关内容见Adam Zachary Newton.Narrative Eth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1~33;费伦《叙事伦理》相关内容见James Phelan.Narrative Ethics[A].In Peter Huhn et al.(eds.)Handbook of Narratology[C].Berlin: De Gruyter, 2014;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相关内容见该书《引子:叙事与伦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徐岱《叙事伦理若干问题》,《美育学刊》2013年第6期;王鸿生《何谓叙事伦理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6期;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叙事伦理:伦理批评新道路》,《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江守义《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③[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向愚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
④[美]布鲁克斯、华伦:《小说鉴赏》,主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⑤《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 卷第259页。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 册第535页。
⑦黄霖:《〈中国小说写人学〉序》,载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学》,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⑧[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4页。
⑨[法]菲尔拉拉:《虚构作品结构分析理论和范例》,转引自[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3~64页。
⑩[匈牙利]乔治·卢卡契:《叙述与描写》,转引自王先霈等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