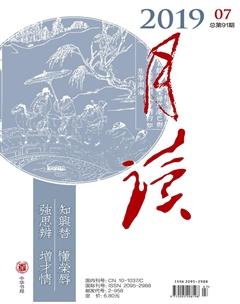钟鼎金文中的书法意蕴
葛承雍
中国古代文化经过商朝的大发展,到周朝达到了一个高峰。贵族们为了夸耀祖先征伐的功绩和显示自己的权力地位,铸造了许多体现统治者威严、力量和意志的青铜器,并饰以饕餮为突出代表的兽面纹样,目的是以超世间的神秘威猛的动物形象,体现出统治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肯定。这种顶礼供奉的青铜礼器,在殷商时代已大量出现,只不过大多没有铭文。商代青铜器较早的铭文一般只有一个或几个字,有的是标明器主的族氏和祭祀的对象,有的是记载商王和贵族对器主的赏赐,还有一些只是说明器物的用途,到了商末才有连贯的铭文,最长的有44个字。商代还在青铜器铭文笔画里镶嵌绿松石,使其更为美观。这种在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叫做“钟鼎文”或“金文”。
然而,殷商、西周的工匠们在青铜器上铸刻这些文字时,并没有有意识或自觉地追求书法的线条艺术,特别是在殷商早期,钟鼎金文经常铸刻在不易为人所见的器物底部等处,根本没有考虑到艺术审美。以实用为发展动力的青铜铭文,仅仅是暗藏着书法文化的底蕴,历史地孕育、融化着人类千百年的聪明才智和审美经验。
金文是甲骨文的升华,整齐的直线被多变的曲线所取代,方正的空间亦为欹侧的结构所取代,圆润、饱满、丰腴、厚实的曲线美受到重视,反映出西周敦厚、质朴的时代书风。内在的骨骼力度与外形的稍有松散,使先民们铸刻的钟鼎金文经过翻模而变得无意圆润却丰富多彩。
进入周代以后,青铜器开始出现洋洋洒洒的长篇铭文,但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及其铭文特征,较商代晚期并没有大的变化。周人灭商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了平定内部叛乱、征服方国部落、迁徙殷民贵族、分封大小诸侯等一系列措施,还无力集中力量发展文化事业,周初文化仍然继承着商文化。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形制厚重,铭文深沉,铭文的字体凝重,行笔方整,有竖行而无横行,大小不匀,与殷代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没有明显的区别。以成王时的《令彝》《大鼎》,康王时的《大盂鼎》(图1)为例,其铭文与商代《骨匕刻辞》《帝辛四祀卣》等对比,就可以看出它們许多笔画相同,大都首尾尖细,中间较粗,形成了西周早期金文特有的头尖、腹大、尾尖短的蝌蚪尾巴状笔画,而且周初各种钟鼎铭文的内容仍是甲骨文同类内容的扩大和记事范围的拓展,即贵族为彰扬自己的功德和战绩而作的祭祀、征战、册命、赏赐等的记录而已。因此,青铜器上庄严的文字和狰狞的饕餮共同显示着“天意”和权力的神秘,而书法本身潜伏着的一切美的内涵,似乎都被这庄严神圣的外在形象湮没了。

随着西周社会的不断发展,周人的文化也获得进步,尤其是其文化思想体系逐渐与商人脱离。虽然统治者在客观上还要利用至上的“天”作为统治的工具,但主观上却强调着人力;他们以天道为统治百姓的思想,以德政为操持政策的机柄,在思想文化中贯彻相应的礼乐制度。在这种思想体系的指导下,周人日益重视文化的作用,文字的艺术功能也开始有了明确的记载。《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书”即识字、写字。《汉书·艺文志》:“《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保氏,乃史、巫之官,国子是贵族子弟,由此看来,书法已逐渐从较纯粹的巫术功能中解放出来,被最早的一批文化人所广泛应用。同时,作为一门技艺,书法自身含有的美的因素也逐渐脱离文字的概念而表现出来。
幸运的是,历史似乎对书法特别关照,在青铜钟鼎上,文字和饕餮在显示庄严神圣意味的同时,又散发着美的魅力。尽管周人对此恐怕还没有自觉的意识,但在他们朦胧的观念中,文字毕竟成了装饰的一部分。如果拿殷代的金文和周代相比,前者更近于甲骨文,后者到了中期,如宣王时著名的《毛公鼎》(图2)的铭文长达497字,已像一篇精美的书法作品了。其实,这一过程从昭王时已经开始,越到西周后期,青铜器制作得越精美,铭文也更趋成熟,其代表作品如昭王时的《宗周钟》、共王时的《墙盘》、恭王时的《裘卫鼎》、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厉王时的《散氏盘》等,都达到了金文艺术的极致。

当时要把许多冗长的文字刻铸到青铜器上,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从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行款布局大小错落又自然朴实,凝重严谨而又富于变化,表面上似乎漫不经意,实际上却是精心安排的结果,这说明当时已有一批经验相当丰富、专门书写铭文的人。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特点是:笔势圆润,变行笔的方整转折为圆匀;结体严谨,构架紧密平正而有稳定的规律;讲究章法,全篇布局纵横有行距,疏朗开阔;尤其是无所顾忌的穿插和任笔为形的粗细交叠,无不显示出一种恢宏的格局。这些特点构成了后世书法艺术中篆、隶、楷、草用笔、结体、章法的初步格局。此外,风格也开始分化,各派纷出,字体或长或圆,刻划或轻或重,如《大盂鼎》《智鼎》《周公彝》等铭文风格与甲骨文相近,凝练厚重,雄奇挺拔;《毛公鼎》《颂鼎》《宗周钟》等铭文明显表现出大篆已趋成熟,圆润工整,柔和健美;《楚公钟》等铭文则与中原流派不同,当是荆楚间的一种字体;《虢季子白盘》等铭文,质朴端庄,遒健舒展,已开辟了向小篆演变的道路。风格的多样化,反映了当时文化人对书法的初步追求和造诣,这样,钟鼎金文便由开始的图画形体向后来着意舒展的线条美发展,由开始的单个或几个字铭文向后来铭功记事的长篇巨制发展。它们或方或圆;或结体严正,章法雄劲而刚健,一派崇高肃毅之气;或结体沉圆,似疏而密,外柔而内刚,一派开阔宽厚之容。它们又都以圆浑沉雄的共同特征区别于殷商时期的尖利直拙,但仍缺乏人为的巧饰,野逸而博大的风格使人心震神慑,钟鼎凹下的阴文和凸起的阳文显示出独特的款识风度。后人常常误以为在玺文时期只有书体变化而没有个性风格的变化。而在这些“无意于佳”的韵致和经天纬地的线条组合面前,这种看法实是一种误解!
宗白华先生早就指出:“至于殷代甲骨文、商周铜器款识,它们的布白之美,早已被人们赞赏。铜器的‘款识虽只寥寥几个字,形体简约,而布白巧妙奇绝,令人玩味不尽,愈深入地去领略,愈觉幽深无际,把握不住,绝不是几何学、数字的理智所能规划出来的。长篇的金文也能在整齐之中疏宕自在,充分表现书家的自由而又严谨的感觉。……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章法的美,令人相信仓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1期)随着文字的增多,文字由原来的图画模拟,逐渐变为抽象的线条和结构,这种净化了的文字线条,不是一般青铜器上图案花纹的静止形式和规范装饰,而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内含和表现人性意识的一种文化。甲骨文、金文之所以能开创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不是“依类象形”的方块汉字有着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形式,而是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每一幅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不作机械地重复,也没有僵硬的规范。在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下,文人把多样流动的自由观念倾注到文字的书写里,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因此,中国书法艺术在它的萌芽期里,就既状物又抒情,兼具抽象模拟的造型和抒发情感的表现,这两种因素和成分在以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文化的灵魂。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占卜用的甲骨文字在周初并没有因金文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1954年山西洪赵县(今属临汾市洪洞县)坊堆村出土了刻有八个字的西周时期完整左胛骨,辞例和商代卜辞近似。1956年陕西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刻着极细的两行文字,与殷商甲骨文字相似。这些甲骨的发现,可以作为周人继承殷商文化的佐证。
随着周代文化思想的活跃,“天人”观念取代了“上帝”观念,甲骨文字也有了新的变化。1977年春至1978年夏,在陜西岐山凤雏村发现的西周甲骨文(《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有不同的单字360多个,记述了文王、武王至周公摄政时期的重要史实,还有被认为是八卦起源的由“五、六、七、八”四个特定数字组成的符号。这些甲骨文的主要特征是字体细小,在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卜甲上竟能刻二三十个字,最小的字直径仅一毫米,字小如粟粒,笔道像发丝,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这种“微雕技术”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相比,它的字虽小,但结构更为严谨,工整秀丽,雕刻刚劲有力,刀笔运用自如,通过契刻刀痕的不同,可以窥探出周人的文化修养。甲骨文字风格或粗犷遒劲,或纤细谨密,或一丝不苟,或略肆草率,轻重、粗细、刚柔的变化乃至章法布局,一见便知事前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反映出周文化在商文化基础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