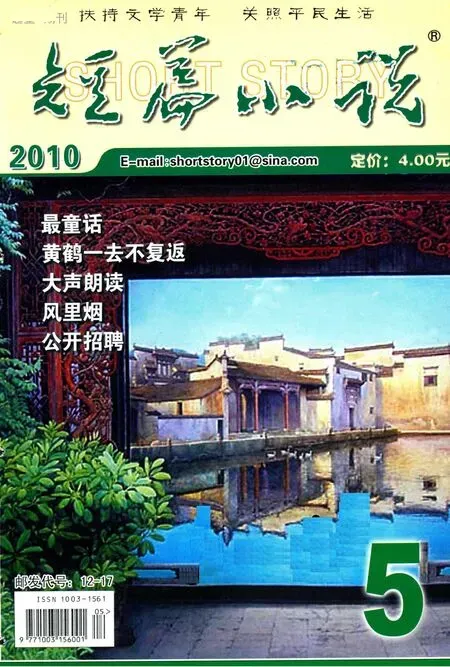斜坡
◎邱 力
袁鲤走进儿子就读的英才中学时,天色已晚。一些学生和袁鲤擦肩而过,操场边的教学楼里各班教室亮如白昼。远远望去,教室窗户透出的光亮如同无数双焦虑惊慌的眼睛在闪烁。这会儿,上晚自习的儿子肯定已经坐在教室里了。儿子不必像其他学生一样每天行色匆匆地在家和学校之间奔波。当初张艳将自家市区的房屋出租,到儿子的校区内租了一套教师公寓,毅然投身高考陪读大军。这个决定现在看来真是英明神武。要不儿子怎能从全班第34名一跃而成为第29名,前进了5名啊。儿子一小步,高考一大步。更何况还有继续前进的可能。九个月后的高考兴许就是袁鲤一家让所有持怀疑态度的人见证奇迹的时刻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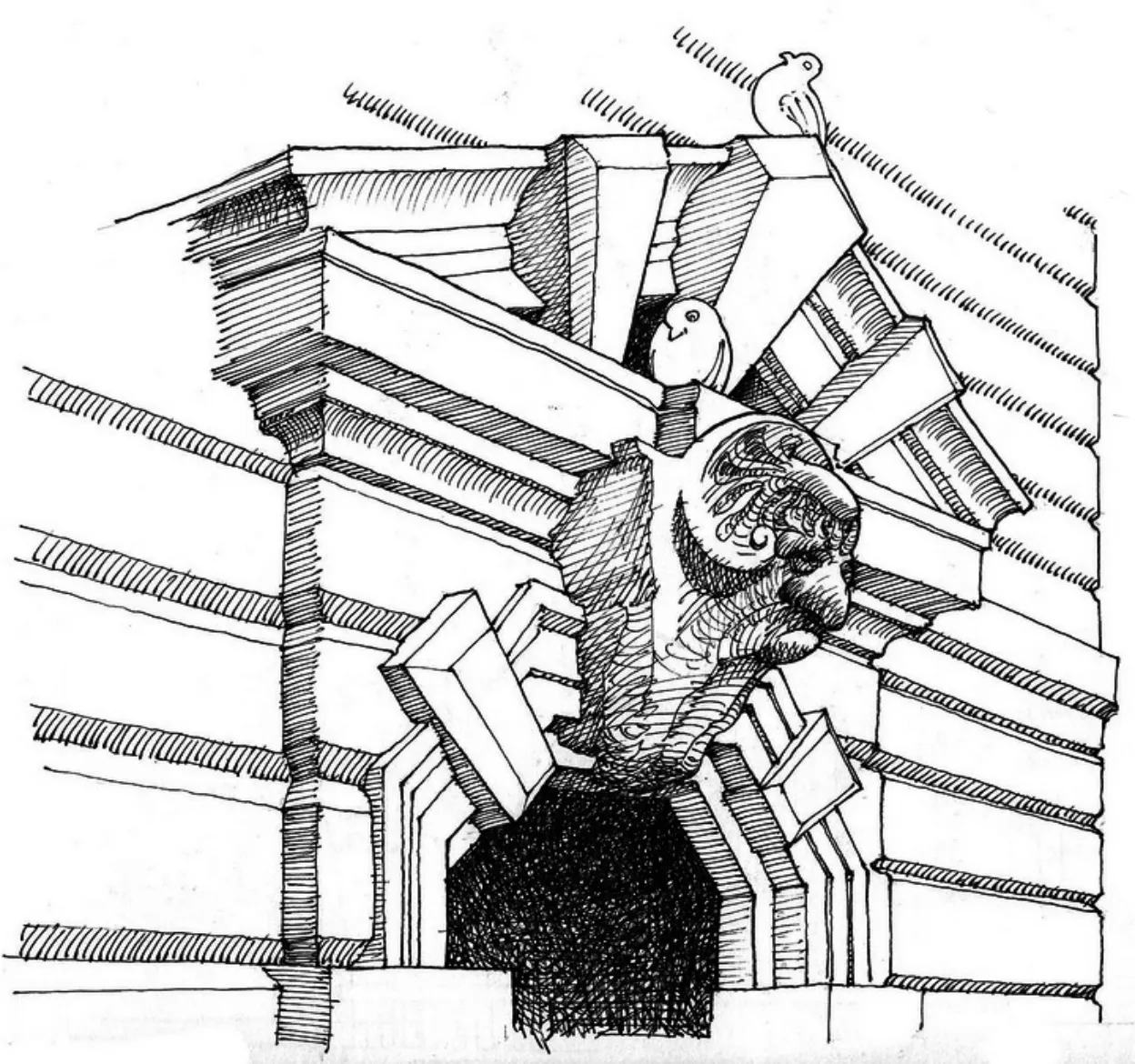
袁鲤和张艳两地分居,袁鲤在新竹县,张艳在乌的市。他们在市区有一套当初张艳父母遗留下来的房子。每周五,袁鲤下班后,乘坐近一小时的火车,傍晚抵达乌的市。作为一个勤俭的男人,单位又是清闲自在的文物管理所,袁鲤有时候可以提前下班,去菜场逛逛。碰到新鲜的时令蔬菜,正宗的乡下土鸡鸭这些城里难得买到的东西,就顺便买上带到家里,第二天一家人再慢慢拾掇分享。他们分居了八年,彼此都适应了这样的日子。转眼,儿子竟然就要面临高考了,两口子一商量,干脆就以下一代的前程为理由,再次向单位领导提出工作调动。申请调动期间,他们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把该跑的关键人物都跑到位,该动用的关系都用到位。结果这次调动申请是出乎意外的顺利。袁鲤的接收单位是市广电局,上周三调令就发到了袁鲤的单位,通知下周一正式到新单位报到。看来,聚少离多的日子真的将一去不复返了,生活正在向他们一步步预示许多值得期待的惊喜。
通往他们租住的那栋楼房是条向上的斜坡。八月底的一场暴雨后,水泥路面更加坑洼不平,杂草和野花发了情般在坑洞间葳蕤。袁鲤前些日子就不小心把脚崴了。还有一天夜里袁鲤竟找错了房门,都怪这些老旧的教师公寓楼房惊人的相似度让外来者迷惑。张艳闻到袁鲤身上浓烈的酒味。她迎上去给袁鲤倒了杯糖开水:“人还没正式调过来呢,就想把身体喝垮啊?电话也不接,所里说你一早就请假外出了?”袁鲤没言语,转身进了卫生间。生锈的水管在滴答滴答地往下滴着水。在解裤下蹲时,袁鲤摸到了腰间柔软黑亮的“登喜路”皮带。这是刘丽送他的新皮带,旧的那条袁鲤扔在了回来的路上。袁鲤两手湿漉漉地出来,接过张艳手中的玻璃杯,一口气喝干了糖开水。
“你忘记拉上裤门了。慌里慌张的干吗啊?”
“嗬,一高兴,喝高了……广电局的人客气,说是提前给我接个风……手机也不知咋的搞成静音了,嗨,你说我是不是小人得志啊?”
“还指望你调上来后,多陪陪我和儿子呢,看来没门啊。”
“艳子,你否定谁也不能否定你老公啊。明天我将功补过,去清泉河水库钓鱼,犒劳你和儿子。不钓满一桶我决不回家。”
袁鲤说着就朝张艳身上凑,手上动作也随之热烈起来。在这间租住的陌生房间里,袁鲤突然产生了一种类似偷情的新鲜刺激感。在与张艳欲迎还拒的故作姿态进程中,房间里的空气很快就酿成了53度的酱香型白酒,让人陶醉喜悦。伴随着阳台外吹来的阵阵热风,袁鲤和张艳的情欲蒸腾开来。张艳低头又看了眼袁鲤的下面,那儿早已是呼之欲出了。这是多年以来,他们夫妻间屈指可数的一次和谐房事。事毕,儿子刚好回来。儿子少年老成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草草洗漱一番,便闷头走进小卧室,关严房门不再出来。面临高考,几乎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如临大敌。袁鲤和张艳有别于其他家长的是,除了担忧儿子的学习考试成绩,还担忧儿子从小就犯有的一种难以启齿的病症:尿床。一开始,袁鲤和张艳以为儿子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尿床只是某个阶段的毛病。不料直到十八岁,这毛病仍然屡禁不止。被子三天两头就得换洗,内裤和外裤更是准备了好几套。儿子一紧张,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正走在路上,小便就会失禁。儿子的成长始终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尿臊味的阴影。从幼儿园到高中,同学们把儿子的毛病当成笑柄,儿子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全家人这一路走来真是如履薄冰。袁鲤和张艳特意带着儿子去北京上海求过医。住地下室,在排成长龙的队伍里苦苦等候,被医托诈骗,这些都认了。关键是那些大专家们开出的药方全都无济于事。儿子恣意妄为的小便简直就是在嘲笑专家们自诩的医术。看似一切正常的儿子,仿佛一栋被潦草地验收合格的楼房,安装了一套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下水管道,说漏就漏,任性得很。这也是袁鲤和张艳面对儿子时小心翼翼的原因。
不过,现在,二人日常紧张的情绪暂时缓解了。
“袁鲤,你说咱们一家人是不是真不容易啊?”
“是啊。”
“八年了,你每个星期都这样来回地跑,换作是其他男人,早跑到别的女人身上去了。”
“那是。”
“咱们再坚持半年啊,等儿子高考一结束,就去碧水蓝天新天地看房。我算了下,要个120平米左右的房子,按揭15年,每月还贷大概3300,你调上来后,工资啊福利啊都会涨,还贷后每月还可以存个几千块。也该享享福了啊。”
“好的。”
“嗨,袁鲤,我说了半天,你就只会哼哼叽叽地敷衍啊?”张艳嗔怪地轻轻捶了袁鲤一拳。
袁鲤微阖双目。他想,明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里那些晚宴上的暧昧照片删除,千万别让张艳发现。
第二天,袁鲤早早收拾好了一整套专业鱼具。他在微信群里向钓友老炮发出召唤,赶紧来吧,不然好窝子就要被别人霸去了。袁鲤和老炮都是“愿者上钩”微信群里的钓友,两人年纪爱好相仿,很谈得来。袁鲤在乌的市唯一的朋友就是老炮。片刻,老炮在微信里回复了一个笑脸和一句话,别急,又不是去钓美人鱼。袁鲤冲着仍然睡在床上的张艳说了句:“老炮已经侦查到清泉河水库最近才放了一大批鱼,承包水库的那个老板和老炮是熟人。你和儿子就等着吃全鱼宴啊。”就提着渔具下了楼。
星期六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特别是在水库钓鱼,有讲究。不能是连续大晴天,这样水体温度会升高,水中微生物大量繁殖会加剧氧气消耗。阴天鱼儿们也容易缺氧。而眼下,经过几天的雨后,又阳光普照,水中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你就瞧好吧,鲫鱼、鲤鱼、草鱼、鲢鱼、鲈鱼这些平时狡猾的家伙,会争先恐后地游离老窝,冒出水面,酣畅淋漓地呼吸充沛的氧气。还有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猪嘴鱼胡子鲶青鱼鳙鱼们,它们只要闻到诱人的鱼饵,就会马上憨头憨脑地自投罗网,才懒得理睬尖锐的鱼钩正恭候它们哩。晴朗的天空白云飘,白云下面,奔跑着载有老炮和袁鲤的五菱面包车。袁鲤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最值得炫耀的本事也是钓鱼。这种本事和爱好仿佛与生俱来,可以追溯到袁鲤的父辈乃至祖上。从他父亲给他取的这个名字“鲤”可窥见一斑。袁鲤在新竹县便是个钓鱼界的名人。他的野钓技艺被众多钓友称道不已。老炮呢,三年前脱离婚姻的轨道后,为了做个快乐的单身汉,半道出家当上钓鱼客。钓龄短不说,又悟不到门道。花去大量钱财和时间,始终不得要领,经袁鲤指点迷津,才品到钓鱼的妙处,死心塌地爱上了这一口。
从城区出发,老炮和袁鲤心情舒畅。一路向西,清泉河水库约摸30公里的车程。行进途中,袁鲤的手机响了。看了眼屏幕,没接听。一会儿,手机又倔强地响起来。
“接吧,老弟。是相好吧?没关系,你们只管亲热,就当哥哥不存在。”老炮一脸坏笑。
袁鲤露出惊佩的表情:“嘿,你这家伙。钓鱼不咋的,猜测别人的隐私倒是比较靠谱啊。不过也不算是相好。还有点儿距离。”
“老弟,实话告诉你,哥哥我现在要不是改邪归正了,钓女人啊是一钓一个准。你看手机那种表情,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遇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女人了。”老炮越发得意,将嘴角边的香烟咂得吧吧响。
怎么说呢?还真让老炮猜对了大半。
来电话的女人叫刘丽,即将成为袁鲤的新同事。“登喜路”皮带就是她送的。一年前,袁鲤在一次业务交流会上与之相识。如果硬要给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下个定义,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介于朋友和相好之间。不过,就在昨天,他们两人的朋友关系似乎朝着成为相好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周五早上,袁鲤的确是向单位请了假,出门去办事。他办的事除了上午全程陪同刘丽去办理离婚相关事宜,下午还和刘丽一起去赴新单位的接风宴。整整一天,他都和刘丽在一起。如果不是袁鲤在最后一刻的犹豫胆怯,昨天晚上他应该和刘丽在城区的某个宾馆开房,继续将晚宴上的激情燃烧下去。一年来,袁鲤从新竹县到乌的市出差办事,因工作上的需要常往市文广局跑。有时候也就留下来跟局里的一伙混饭吃。席间,袁鲤发现每次只要自己在,刘丽也会在。要知道,刘丽可是局里公认的冷美人,平时很少和大伙打成一片。但在袁鲤面前,刘丽变得异常活跃,丝毫不顾忌大伙儿开的荤玩笑。对刘丽的情况,袁鲤知道个大概。
听说她丈夫是个市政府的一个官员,对刘丽是百依百顺,两人有个七岁的女儿。近期,刘丽的丈夫频频亮相于电视和报纸的时政要闻,仕途看好。而自己除了长得还算俊朗挺拔,并没有多少资本值得炫耀的啊。袁鲤不想也不敢在婚姻的轨道上节外生枝。这些年,他亏欠张艳娘俩的太多。所以每次饭后局里的年轻人吵嚷着要去K歌或吃宵夜,袁鲤都推辞掉,独自打道回府,去陪老婆儿子。在这次工作调动上,袁鲤向张艳隐瞒了一个起关键作用的人:刘丽。是啊,如果没有刘丽暗中斡旋,借助丈夫的关系网,凭袁鲤和张艳的能耐,恐怕这辈子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上周,当调令下来,刘丽在电话里祝贺袁鲤时说:“袁哥,请我家那位吃饭?免了吧。我帮你忙,你现在也帮我个忙不就两清了。”袁鲤说:“尽管说,能帮的肯定帮,不能帮的我创造条件也要帮。”电话那头,刘丽笑过后,突然就哭了起来:“我要你陪我去离婚。”袁鲤心头一惊,以为是听觉出问题了。两人见面后,才知道刘丽正在办理离婚这事是真的。袁鲤看着刘丽乞怜的眼神,心头一热,就应允下来。刘丽害怕在办理离婚手续过程中,遭受即将成为自己前夫的那个男人动粗。因为据刘丽宣称,那个男人有家暴倾向,且离婚涉及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分割。
周五早上,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袁鲤来到乌的市曙光路街道办事处对面的马路等候。袁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露面,除非是刘丽不幸遭受了家暴——袁鲤才会挺身而出,制止暴力行为,主持公道,让离婚手续正常进行下去。如果刘丽的前夫要质问袁鲤是何许人也,就谎称是刘丽的同学,路过巧遇而已。袁鲤甚至在出门时还带了把裁纸刀,等候过程中,想想不妥,又将刀子扔了。袁鲤就像个间谍一样,藏身于一间小超市的门口,看着刘丽和那位即将成为刘丽前夫的矮个子男人在办事处进进出出。
一会儿去一家打印部复印相关证件和资料,一会儿又站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那个男人不像是个擅长家暴的人,袁鲤也想象不出他们之间的婚姻怎么会瞬息万变?这起离婚案又涉及多少金额的财产?他只是临时充当一个潜伏在角落里的护花使者,一个莫名其妙的旁观者。事情从头到尾都有点儿荒谬,但看上去还算顺利。等刘丽向袁鲤大步走过来时,袁鲤看见刘丽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中午,他们二人在附近餐馆吃了顿便饭。刘丽将“登喜路”皮带递给袁鲤,说是表达谢意和祝贺调动成功。在刘丽热辣辣的目光注视下,袁鲤心跳加速,红着脸解下旧皮带,系上新皮带。
接风宴很是热闹,刘丽破天荒地向席上众人逐一敬酒,仿佛她才是宴席的主角。大伙借机起哄,撺掇袁鲤和刘丽来个交杯酒。没想到刘丽竟主动将手臂缠绕在袁鲤的脖颈上,和袁鲤来了个交颈酒。在众人的满堂喝彩声中,手机的摄像头对准二人频闪,留下许多让人浮想联翩的照片。袁鲤的脑袋晕晕乎乎的,他不是被酒精弄晕的,是被刘丽柔软的身体和诱人的香水弄晕的。散场后,袁鲤借着上洗手间的机会用冷水抺了把脸,在心里为今后是否仍和刘丽保持关系,以及如何将这种微妙的关系进行下去纠结了大约五分钟。然后,他摇晃着身子出来,步伐零乱地在路边招手要了辆的士,避开刘丽烫人的目光,一猫腰,钻了进去。
“喂,刘丽。你好。”
“袁哥,酒醒了吧?今天约了几个闺蜜,庆祝我和你的生活翻开崭新一页。”
“在忙去新单位的杂事呢。这不,我正在和单位同事办理工作移交手续。”
“哟,星期六一大早的,又回新竹了啊?啥时候过来呀?我开车来接你。”
“说不准。可能今天回不来了。”
“那行,反正咱俩是一个单位的了。来日方长啊。”
应老炮要求,袁鲤的手机开着免提。老炮听完,双手快乐地拍打着方向盘,还仰脸用鼻子在空中嗅:“闻到了啊,老弟。我的个乖乖,我这鼻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好一个来……日……方长啊。你这个相好的味道骚得相当正宗啊。都后悔拉你来钓鱼了,钓人多舒服啊。”
“老炮你尽胡扯。只是个一般朋友而已。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刚挂单,有车有房有情调——你不上我上了啊。哈哈。”
到达清泉河水库时,太阳刚好钻出云层。朝霞出平湖,波光粼粼的水面像铺了床柔软厚实的金色蚕丝被。早晨的风拂过水面,送来阵阵清爽。几只不知名的白鸟儿在水边栖息,见到有人来,呼啦啦地一下飞向两边的山林。除了风声,清泉河水库此时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水库的出口处筑了道坝,坝外就是乌拉河。河水清澈,流速舒缓。听说政府渔业部门每年都会将上万尾鱼苗投放入河,以保护鱼种的多样性和河流的水质。炸鱼、电鱼以及放细眼的拦河网都在渔业部门严禁范围内,但总有人屡禁屡犯。水库承包方雄心勃勃,初步规划将水库建成全市钓鱼爱好者们的乐园,一根钓杆收费50元,可以钓一天,钓上来的鱼全部归钓鱼人。周边的山林搞林下养鸡和种果树,逐步修建成农家乐。届时,提档升位的“清泉河欢乐谷”将是全市最有特色的近郊旅游休闲胜地。
袁鲤和老炮在水库门口见到那个胖老板。老炮说:“我们应该是来得最早的了吧?”胖老板笑眯眯的,用下巴指了下旁边的一对母子说:“你们四个人来得都一样早。早起的鸟儿有饭吃。谢谢捧场啊。鱼憨得很,随便乱钓乱得。”袁鲤瞅了眼那对母子。那男孩和儿子的年纪相仿,也是佝偻着背,神情呆滞,脸色苍白,像是身患疾病的样子。那女人肩负着防水袋、渔具,手里拎着红色的塑料袋和红塑料桶,点头冲袁鲤礼貌地笑了笑。真有意思,现在钓鱼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沿着山脚一线可见到几个稀稀拉拉的人影。老炮紧跟在袁鲤后面,看袁鲤在水库边选钓位、打窝诱鱼,把两根自制的5.4米手海两用竿取出来,眯着眼睛向水面瞄。在钓鱼这上面,老炮永远是袁鲤的徒弟,不服气不行。但是这天非常意外,临近中午,他们仍然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远处,那对母子静悄悄的,也不知收获如何?
老炮沉不住气了,顺手抓起垫屁股的石块,扔进水里:“鱼都跑哪儿去了呢?跟老子玩失踪?他妈的!”骂骂咧咧地在水边来回窜动。太阳升高了,阳光垂直而下。水面的热量裹挟着地表温度扑面而来,让人猝不及防。袁鲤让老炮帮忙撑开遮阳伞,老炮说:“等哈子,我找老板问个明白,净给老子撒谎,说什么鱼多得随便乱钓乱有。”说完气呼呼地走了。袁鲤只好独自把遮阳伞撑开,然后点了根香烟,看白雾漂浮在平静的水面,有些虚幻。水面上几只叫做写字虫的长脚虫,正把水面当成了巨大的宣纸,用细细长长的腿脚书写比甲骨文还难认的文字。袁鲤观察了半天,那些神秘的文字符号似乎是在透露一个关于鱼类脱钩的秘密?或者是暗示鱼类此时藏身何处的信息?鱼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失踪呢?鱼总要上钩的,也许是投放的生鱼太多,警觉性变高了?再耐心等会儿吧。抬眼望去,老炮正在和那个胖老板说话,指手划脚的,距离太远听不见说些什么。胖老板再次给老炮点上根烟后,用手指着那对母子。老炮就甩着两只细长的胳膊,朝那对母子走去。
袁鲤心想,兴许今天钓鱼的失利跟自己仓促上阵有关?
早上出发时,什么设备都备妥了,唯独忘记带上自制的鱼饵。这东西是袁鲤的独门秘技,尤其在水域宽广的水库,打窝放饵更是关键。可回头一想,难道袁鲤对即将拉开帷幕的新生活就准备就绪了吗?分居八年,他和张艳过着名不符实的夫妻生活,身患怪病、性格乖张的儿子与他从不交流。每周五的团聚更像是一场演给众人看的戏,他入戏太深,从内心希望就这么一直演下去。但是现在换场锣鼓敲响了,新的角色需要他去扮演,新的剧情需要他去面对。昨天的接风宴上,新单位的几个同事展示出了不同于老单位的风格。他将工作的部门是局里的文化稽查队,平时的工作重点是巡查网吧、酒吧和散布在城区各个地段的娱乐场所。活儿看似轻松好玩,实则套路颇深。从设宴的规格和同事们抽的烟喝的酒侃的关系网上,可以看出这个部门油水不错。这不正是张艳一直盼望的吗?有了丰厚的油水,就意味着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会相应得到提升。儿子即便明年考不起理想的学校,花点儿钱找个好的培训机构再次冲刺,再按揭套环境好些的房子,这一切都将是指日可待啊。当然还有刘丽,老炮话丑理正。在老炮这种生活的哲人面前,自己对刘丽最后的那点抵抗充满了矫情和虚伪,妥协与交媾将势所难免,说不定还引以为荣哩。
“老弟啊,你猜我刚才遇到什么高人了?”老炮总是先声夺人,喜欢用设问句。待走至跟前,扔了根烟给袁鲤,继续自问自答,“那对母子真有意思。对,你别用这种暧昧的眼神看我啊。那个儿子,我第一眼就晓得脑筋有问题。但这小子是个神钓,真神!晓得没,我们这边一条鱼儿没上钩,人家都钓满一桶了。那鱼听话得很,简直像作弊。更神的是,这小子,把钓上来的鱼统统都放生了,放完又钓。你说是不是有病?那个当妈的呢,专门负责给儿子上饵、说话、递水。我刚才还隆重介绍了你。要不,你也去跟人家切磋切磋?”
男孩和女人静静地坐在一个小土包上,男孩神情专注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女人则递给男孩一个小圆面包和一瓶矿泉水,这会儿是午饭时间了。浮漂一动,男孩很随意地将鱼竿提了起来,一条肥硕的鲤鱼上钩了。男孩小心地取鱼下钩,放入旁边的红塑料桶里。女人神态安然,和袁鲤点头笑了笑,就顾自低头捏鱼饵。男孩晃眼望去,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细一看,就会发现男孩的眼神有点儿定定的痴痴的。袁鲤一下子想到了儿子,即便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又怎样?儿子的尿床注定将为自己的未来涂抹上不理想的色彩。他蹲在男孩身旁,拿上一点鱼饵在鼻子下捻着闻,那女人递给袁鲤一瓶矿泉水。瞬间,袁鲤的心中升起一种多年渴盼得到又始终虚无飘渺的做父亲和丈夫的感觉。他们三个人紧紧挨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正在享受的一次愉悦的郊游。男孩再次抛竿,顺手将刚钓的那尾鲤鱼放进了水里。鲤鱼滑入水中,鱼尾扑打水面,发出啪啪声,像巴掌拍打在袁鲤的脸上。稍顷,端正身躯,黑色背脊绷成一条直线,肚皮朝上翻卷出一朵漂亮的水花,噗的一声,再也不见。
女人拉了下袁鲤的衣服,示意到一边说话。
“大哥,你别见怪啊。我儿子就这样子。你看他钓鱼的时候多安静,一在家里和其他地方发作起来可不得了啊。”女人边小声说话边觑着男孩。
“他得的啥病?没去找好一点的医院看看啊?”
“看了的,没用。他爸几年前跳进这个水库死了后,他就变得呆呆的了。动不动就胡言乱语,还乱砸东西乱打人。学也退了,真不知道以后咋办?”
“那他怎么就迷上钓鱼了呢?”
“他非说他爸藏在水底,不来钓鱼的就不安静。唉。”
男孩可能听见他们的对话了,就转身扭脸看着袁鲤,一字一句地说:“叔叔,我爸就在水底,你听,我爸正在和我说心里话哩……”
男孩说话的时候,无数细小的面包屑从嘴角边纷纷扬扬地坠落,像冬天的雪花。袁鲤俯下身子,将脸贴在地上。蓦地,好像真的听到了什么声音。
在老炮的催促下,袁鲤收竿回家了,第一次从钓鱼场空手而归。到了通往他们租住的那栋楼房前,袁鲤突然感觉脚下沉重,他放下渔具,坐在那条斜坡上。风声、鸟声、水声,从四面八方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