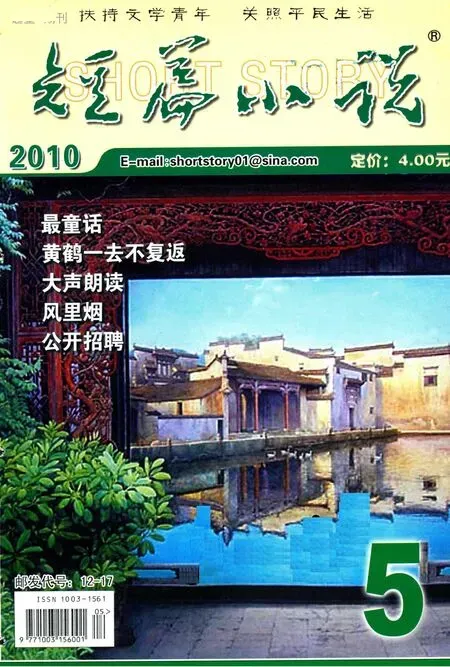住院
◎魏 鹏
一
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四肢酸痛无力,竟下不了床了。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一夜之间竟病成这样?这是什么病?我左思右想,就像小学生做试题似的,先假设,后排除,急得满头是汗,仍找不到答案。
我试着翻转身子,想用两只胳膊把上半身撑起来,可身子转不动,两只胳膊只能虚张声势,徒劳地挥舞,身体像段木头似的横在床上,一动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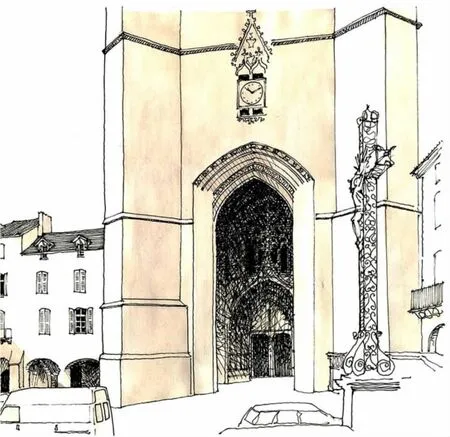
这时,我想到了死,但又觉得不像,快死的人头脑不会这样清晰。我只是身子不听使唤而已,就像床头的小闹钟,只要上上劲,走得还是很准的,并没有坏掉,只是,我无力给闹钟上劲了,无力给自己翻身了。
死,我倒不怕,只是没想到死会来得这么快。想想,我才刚到八十岁,还没活够呢,我还想再活二三十年呢。上几天看家史,才知道我家祖祖辈辈都长寿,祖父活了一百一十四岁,父亲百岁时还骑自行车呢。我才多大?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可对我们家来说,百岁不稀罕,七十正当年。这样一想,死,似乎离我还很遥远。
假如真的死了,也应该死在医院里,让亲邻们知道,儿子已尽了孝心。
可是,我平生最怕去医院,不到万不得已,医院是万万去不得的。可谁又能料到,一觉醒来,已是万不得已了。
“儿子,我是不是快死了?”我给儿子打电话,说自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也许是快要不行了吧。
“吃不愁吃的,穿不愁穿的,干嘛非要死呢!”儿子见我果真躺在床上,像快死的样子,就连忙给我送进了县人民医院。
县人民医院有两座高楼,东边一座是内科大楼,西边一座是外科大楼,两座高楼中间的楼房只有四层,和内科外科二十多层的高楼比起来,这里已算不上是大楼了。设在这里的是肿瘤科和儿科,大夫们不说肿瘤科也不说儿科,叫这里为综合楼。综合楼和两肩的内科外科大楼都贴上了白瓷砖,白晃晃地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医院的门诊部设在外科大楼的一楼。一楼大厅人声鼎沸,待诊病人的呻吟声,病人家属的哭喊声,穿白大褂的呵斥声,声声交织在一起,杂乱无章,听不清头绪。
在大厅里,儿子忙着为我挂号,一个穿白大褂的问:“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白大褂对医院的科室设置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如练口技,又似提示儿子。儿子说:“不知道……”
白大褂从玻璃窗口伸出头来,看了一眼儿子背上的我,又问:“什么病?”
我说:“不知道……”
“挂内科吧。”
“好的。”
内科门诊有六七间房子,分别为内科一、内科二、内科三……内科一在二楼楼梯附近,屋里有一张办公桌,桌后边坐着一个男大夫,男大夫正在摸一个人的大腿。男大夫边摸大腿边抬起头来,示意儿子把我放在墙角的一张床上,躺着,等着。
男大夫摸完了大腿,才挂着听诊器来到我躺着的床边,这时我才看清这个男大夫只有四十来岁,脸庞清瘦,但两眼放光,有神,一口白牙像镶嵌的白瓷砖,冰冷,刺眼。白大褂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整整大了一圈。白大褂的左肩下有个小口袋,口袋里装着一支铅笔和一支签字笔。口袋上方印有四个蓝色的隶体小字:主治医生。再往上靠近肩头的地方,有一滴黑色的墨水,像一泡鸟屎。
男大夫解开我的上衣纽扣,像探囊取物似的把听诊器伸进羽绒衣里边,边听边问:“老爷子是怎么回事?”男大夫竟称我为老爷子,这亲切的称呼一下子拉近了男大夫和我的距离。
“今天一大早,老爷子给我打电话,说他下不了床了。”儿子回答说。
“噢,是这样。老爷子你现在能下床了吧?下来,来,这样,对,就这样,走两步,让我看看。”男大夫收回听诊器,就让我下床走给他看。我满头大汗,如履薄冰。
“怎么样?”男大夫忍着笑,问。
“大夫,疼、疼,浑身都疼,像散了架似的,寸步难行……”
男大夫听了哈哈大笑,笑得露出了满口白牙,笑得脑门上的三五缕头发乱颤,笑得大了一圈的白大褂窸窸窣窣。
“哈哈哈,哈哈哈,太像卓别林了!老爷子真逗,再给老爷子一把伞杆当拐杖,简直就是卓别林转世!”男大夫差点笑岔了气。
我活八十岁了,还从没见过这么爱笑的大夫,也从没见过这么能笑的大夫。在我的记忆里,有过一个爱笑的朋友,后来当了大夫,当了大夫就再也不会笑了。在我五十五岁那年,他从医院跳楼自尽了。
“这样吧,”男大夫和我儿子商量说,“先住下来,给老爷子彻底检查一下。”
儿子点了点头,就给我办了住院手续。
二
接下来的三天里,儿子用担架车推着我,抽血化验,查大便查小便,查B超查彩超,查CT查MRI,用医院原装进口设备通通查了一遍。男大夫拿到检查报告单之后大笑不止,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再不笑就没有机会似的,笑得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然后才拍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吧老爷子,没事!只是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还有就是大脑供血不足,有轻微的脑萎缩,没有生命危险。”接下来就是让护士给我打吊针,输活血化瘀的红花、丹参、杜仲、陈皮等药水。
我向来瞧不起没有骨头的人,对骨质松软者也不视为同类。从年轻时起,我就盼着骨质增生。在所有的疾病中,我最喜欢的莫过于骨质增生了,一听这名字就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想不到八十岁了,果真患上了骨质增生,增生就增生吧,可偏偏又压迫到哪根神经了,让我浑身酸痛,寸步难行。
男大夫每天都要带着男男女女的一群实习大夫和护士长到病房里看我。男大夫让护士给我洗洗头,刮刮脸,剪剪指甲,有时还拉着我的手,笑着问:“老爷子,好些了吗?”
“好多啦,似乎能下床了!”
“不急!不急!既来之,则安之。”男大夫笑着说,“我父亲和老爷子同岁,前一阵子,也得了和老爷子一样的病,在这里只挂了几个月的水,就好啦。现在在家还能接送孙子上学呢!”
凭良心说,我的疼痛是减轻了一些,但并不是好多啦。我说好多啦,是对大夫医术的肯定和鼓励。
“难道我也要像大夫父亲那样,在这里挂几个月的水?”我在心里问自己。
病房里共有三张床铺,我躺的是里边的一张,中间一张躺着的是一个小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他对我爱理不理的,我也很少和他搭讪。听儿子说,我躺的这张病床,原是他想留个他的一个亲戚的,后来被男大夫安排给我躺了,他自然不高兴。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
最外边一张床铺躺着的是一位远乡人,看样子已年过花甲了。他很健谈,常常隔着中间的床铺和我拉家常。他说他得的是肝癌,最后一次检查才确定是误诊。
那天查房,男大夫的后脚跟刚跨出房门,他就欠了欠身子对我笑道:“这个大夫真有意思——我刚住院时得的是肝癌,怕是活不多久了,可大夫说他父亲和我一样的年纪,也和我患一样的病,手术后已能提着篮子到市场买菜啦。今天他又说他父亲和你一样的年纪,也和你患的是一样的病。真有意思!”
我听了微微一笑,心想,这大夫真会和病人套近乎呀!
我生病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都赶到医院来看望,仿佛要赶来和我见上最后一面似的。他们有的给我送来了花篮,有的给我送来了水果,有的干脆向我的枕头底下塞钱。
刘老头把儿子拉到病房外,避着我叽叽咕咕好一阵子,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
张大婶已八十有五了,是我的老邻居。她见我就止不住地落泪,像遗体告别似的。我连忙安慰她说:“大夫说啦,没事,没生命危险的。”
“该吃吃,该喝喝吧!”张大婶抹着眼睛,哽咽着说。
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睡着了,迷迷糊糊地听到棋友老李看我来了。
“我跑了外科大楼,又转到了内科大楼,想不到你老爸住进了肿瘤病房!”老李气喘吁吁地对我儿子说。在我们这里,所谓肿瘤,基本上都是恶性的,和癌症没什么两样,肿瘤多发地所谓的肿瘤村、肿瘤乡,其实就是癌症村、癌症乡。
“门诊时,遇到了一个爱笑的男大夫,谁知道这个大夫是看啥病的,当时也不知道老爷子得的是啥病,那个男大夫就安排老爷子住进了肿瘤病房。”
“现在知道是啥病了?”
“知道了,是骨质增生压迫到神经了,不是肿瘤……李叔,你放心,我爸病好了还会和你下棋……”
“不是肿瘤还住什么肿瘤病房?怪吓人的,赶紧转骨科吧!”
我醒来后,儿子又把老李的意见给我说了一遍。这时我才知道大家劝我该吃吃该喝喝,怕我来不及吃喝了,原来是以为我患上了肿瘤,活不多久了,也难怪张大婶一见我就不停地抹眼泪。
我对儿子说:“老李说得对,就照老李的意见办,赶紧转骨科。”
儿子找到男大夫说:“大夫,你看老爷子的病……”
“老爷子的病不是好多了吗?你不要着急……”
“可是,老爷子不是肿瘤病人,老住在肿瘤病房,怕是不合适吧?能不能把老爷子……转到骨科?”
男大夫眉头一皱,露出满口的白牙,似乎碰到了疑难杂症。男大夫两眼直直地盯着墙角的一个垃圾桶,然后用听诊器敲着桌面对儿子说:“老爷子是我的病人,我对我的病人向来是负责到底的,决不能半途不管!懂吗?”儿子点了点头,但依旧站在男大夫面前,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男大夫又敲了敲桌面,对儿子笑道:“老爷子的病,我不会撒手不管的。我们还将与骨科大夫一同会诊,会让病人安心的,会让亲人放心的,会让大家都满意的。”
第二天,男大夫就让儿子把我在医院拍的七八张片子拿到骨科。骨科在外科大楼八楼,儿子从肿瘤病房的三楼下去,又上到外科大楼八楼。听儿子说,骨科的一位实习大夫见了我的片子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笑得儿子莫名其妙。
“大夫,你看……”
“哈哈哈,没有办法了吧!骨科的病人也敢收!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哈哈哈,没有办法了吧!”
“大夫,你看……”
“我看啦,病人需要推拿!”实习大夫斩钉截铁。
儿子回来告诉我会诊 (这就是男大夫所谓的会诊)的结果,说:“需要推拿。”又告诉男大夫说:“骨科大夫说啦,老爷子的病需要做推拿。”
“推拿就推拿吧。”男大夫微笑着对儿子说,“你用担架车把老爷子推下去,再转到外科大楼,乘电梯上到外科大楼八楼,在骨科做完推拿后,再推回来!”
“这个……只是……老爷子浑身都疼……太麻烦了!”
“哈哈哈,为老爷子看病,哪能怕麻烦呢!如今的人啊,孝心都让狗给扒吃了!”
什么孝心不孝心的,我儿子不愿听。
儿子又转到骨科,请那个实习大夫想想办法,如何才能让老爷子住进骨科病房。
“哈哈哈,没办法了吧,骨科的病人也敢来抢!哈哈哈……”实习大夫依旧是大笑一阵,接着才说:“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既然住进了肿瘤科,肿瘤科会咬住不放的;从骨科和肿瘤科的友好关系上来说,我们让病人转进骨科,这是极不道德的,也是骨科所不为的。”实习大夫像老大夫似的,看了一会地板砖,又看了一会天花板,才意味深长地笑道:“要说办法嘛,也不是没有,天无绝人之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是不是?”实习大夫向儿子招了招手,把嘴巴凑到儿子的耳朵上,仿佛说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让老爷子出院,然后再进来,挂个骨科,包你住进骨科病房!”
儿子给我一说,我就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呢,”我对儿子说,“出院后,我们就不再进来啦,我们进中医院。中医院虽然没有人民医院名气响,整体医术也不敌人民医院,可那毕竟是全县第二大医院,单说推拿,水平比人民医院还高呢!”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出了人民医院就去中医院!”儿子说。
三
天空灰蒙蒙的,飘着毛毛细雨。风吹在脸上还是冷飕飕的,虽是早春,又不像早春,我一丝都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来临。
在中医院门口,我们遇到了曾到人民医院看望我的棋友老李,我忙对老李说:“谢谢你到医院看望我,我儿子听了你的话,想把我从肿瘤科转到骨科,可转不进,没法转,只有出院后再挂骨科,才能住进去。我想,与其这样繁琐,不如来中医院,听说中医院的推拿水平比人民医院还神呢!”
老李乐呵呵地笑道:“你这病其实也算不上个病,只要年龄超过七十,谁没有个轻微的脑萎缩?谁没有个大脑供血不足?谁没有个骨质增生啥的?这要是病的话,现在满大街上跑的都是这种病人。”
听了老李的话,我的心放得更宽了。老李还说:“来到中医院,你也不必挂骨科的。这里新成立一个科,叫什么啦,你看我这记性,对了,叫康复科,似乎是专门为人做推拿、按摩、拔罐、针灸什么的,效果的确不错。上回,我家老太婆腿疼腰酸,弯不下身子,在这里推拿了两个礼拜,就能弯腰系鞋带啦!”
“谢谢你!老李,我们这就去康复科。”
儿子把我背到了康复科,给我看病的是一位女大夫,三十来岁,齐耳短发,看上去很精神。
女大夫像是例行公事,又像审问犯人似的问我姓名性别年龄……我儿子在一旁忙向女大夫介绍情况,说我们是从人民医院来的,因为在人民医院住的是肿瘤病房,没能住进骨科,我们才来中医院的。听说中医院新近成立了这个康复科,推拿水平特神,妙手回春,手到病除,而老爷子的病正需要推拿,所以,所以我们就来康复科了。
女大夫一边听我和儿子说,一边在我的病历上写下姓名、性别、年龄……当我说到自己八十岁时,女大夫禁不住哈哈大笑了。她放下手中的蘸水笔,问我:“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这话,老爷子听说过吗?”
“嘿嘿,嘿嘿嘿,”我笑道,“那都是老古语喽!”
女大夫又看着我的儿子说:“不管怎么说,老爷子是被人民医院推出门外的病号,我们也不敢接收。”
儿子忙说:“大夫,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在人民医院,老爷子住的是肿瘤病房,需要转骨科进行推拿,可转不进骨科,我们才要求出院的。老爷子并不是人民医院推出门外的病号!”
“哈哈哈,”女大夫笑道,“谁知道呢?也许真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也许,事实就是那样的!”
“谁知道呢?”
“大夫,我还能对你说假话吗?”
“谁知道呢?”
“大夫,老爷子八十岁了,会说……”
“谁知道呢?如今什么人没有?把病危的老人推进医院,病人稍有不测,就趁机敲诈医院一笔,这样的事我们见得多啦!”
“大夫,你的意思是,老爷子不能住院啦?”
“你看,都这岁数了,还……”
儿子急了,四处给同事和朋友打电话。我在一旁悲哀地想,如今什么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连进火葬场,也要有熟人朋友才能及时火化,要不,想变成一缕青烟都难。
儿子恰好有一个朋友,这朋友和院长是麻友,关系不一般。朋友一个电话打给了院长,院长就给女大夫来电话了。
“院长,是这样,老爷子已八十多了,而且是人民医院推出门外的病号,我怕康复科收下老爷子,要是有个什么意外谁负责任?”
“这是朋友介绍来的病人,并不是人民医院推出门外的无法医治的病号。”
“这是他们自己说的,谁知道是真是假?”
“你看情况吧。能接受就尽可能地接收下来,不要为难病人,要一切为了患者,要为了患者的一切,要为了一切患者,救死扶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手机是免提的,院长的声音像作报告。
“好的!好的!好的!”
女大夫边点头边连声说好的,连说了三个好的就挂了电话。然后转身对我说:“像你这样高寿高危的病人,我不担心别的,我最担心的是你的心脏,怕禁不住折腾。要不这样吧,我把你介绍给内科,内科有重症监护室,一旦出现意外也好及时抢救。至于推拿嘛,老爷子你放心,我会派人每天都给你去做推拿的。”
还能说什么呢?我看了女大夫一眼,又看了儿子一眼。儿子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似的,同时把两臂伸着,差一点就要拥抱女大夫了。
四
“你就是康复科介绍来的老爷子吧?”内科大夫问我。内科大夫是个男的,逢人就笑,嘴角挂着笑,眼里含着笑,态度温和得像幼儿园的阿姨。内科大夫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病情,儿子就把我在人民医院拍的大大小小的片子递给了内科大夫,内科大夫一张一张地拿过去,对着灯光看了一遍,问:“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片子?”
“两周前吧,这片子上都有日期的。”儿子提醒内科大夫。
“哦,噢,”内科大夫点了点头,“来到中医院,还要检查一次的。”
“大夫,在人民医院,不是才检查过吗?”
“人民医院不等于中医院,要不,老爷子为何要从人民医院转到我们中医院呢?再说了,昨天检查没问题,不等于今天检查也没问题。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绝对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拿老爷子来说,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下不了床了。所以,我们要对老爷子彻底检查一遍。再说了,这也是对老爷子负责嘛!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第二天就不让我吃早饭了,开始抽血化验,大便,小便,彩超,B 超,CT,X……用中医院原装进口设备,通通检查了一遍。当内科大夫拿到检查结果时,依旧笑道:“这样,你放心,我放心,大家都放心了!”
接着,内科大夫就给我开药输液,输的依旧是活血化瘀的红花、丹参、杜仲、陈皮、桔梗、甘草等药水,几乎和人民医院输的一样,只是颜色略显淡些。还有,就是让我口服一种“清脑复神液”,一日三次,每次10毫升。
每天上午,内科大夫也会带着一群男男女女的实习大夫和护士长来查房。我住的病房里依旧有三张床位,我依旧躺在里面的一张床上。凭良心说,内科大夫查房非常仔细,每天都要对病人询问三五个问题。在我们的病房里,内科大夫几乎每天都要问另外两床病人:“早饭吃的是什么?吃了多少?大小便次数?数量?服药后有什么反应?输水后有什么效果?”等等,等等。在陪护听来,又繁琐又啰嗦,又老生重谈。但到我跟前就简单多了,有时连问也不问,有时只是隔着中间的床位向我点点头,就算是招呼过了,有时只在出门时,向我回头一笑,就算查过房了。
同病房的病友们都感到奇怪,私下里责怪内科大夫对我太不负责任了。我向他们解释说:“我不是内科大夫的病人,我是康复科的病人,内科大夫当然不肯费心了。”而康复科给我看病的女大夫,一次也没有到病房来看过我。
我知道,内科大夫已把对我的责任推给康复科了,而康复科的女大夫又把责任推给院长了,所以女大夫也就对我不管不问,连形式上的走过场也都免了。
女大夫可以对我不管不问,可儿子不能对我不管不问的。儿子每天下午都要到康复科催推拿师来给我做推拿,有时忙不过来,就打电话催。好在打了三四次电话,好像从没有超过五次,康复科就会派推拿师来给我做推拿了。
给我做推拿的推拿师一共有四个,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一个姓王,一个姓刘。她们个个都爱说爱笑,个个都年轻貌美,最大的也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我叫她们推拿师,她们不同意;我叫她们大夫,她们也不同意;我叫她们小姐,她们仍不同意。她们说:“小姐的称呼已经给污染了,让人听了莫名其妙,也让被叫的人脸红发烧。晓得的人晓得我们在康复科做推拿,不晓得的人还以为我们在洗头房拉客呢!干脆就直呼其姓吧。”于是我就叫她们小张、小李、小王、小刘。
小张给我做推拿时手头较重,做半个小时,我也要歇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气来。小王给我做推拿时手头较轻,推拿了半个小时都没有什么感觉,推拿和不推拿没什么两样。小刘做推拿的手法不得要领,找不准穴位,时轻时重,效果也时好时坏,好坏都反弹。有时我故意问她几个穴位,她都说得模棱两可。只有小李手法最高,轻重适中,穴位也推拿得准。因此,我就叫儿子找小李来给我做推拿,可小李太忙,需要推拿的病人都喜欢找她。小李的服务态度特好,她常说:“病人只要找到我,哪怕是加班加点,我也会给病人做完的。”我就经历过好几回,都是她用加班加点的时间给我做的推拿。
在小李给我做推拿时,儿子就在旁边跟着学。小李也很乐意把自己的推拿技术传授给我的儿子,有时干脆让儿子给我做推拿,她只是在旁边做指导。几乎每天上午,儿子都要在我的脊背上、腿上、胳膊上敲敲打打一番,像敲打被褥、敲打死人的送老衣似的。
或许是儿子的敲打歪打正着了吧,或许是小李的推拿技术果真高超吧,谁知道呢?也许是红花、丹参起了作用了吧,也许是口服的“清脑复神液”确有疗效吧,谁知道呢,总之,我骨头的疼痛是一天天地减轻了,一个月之后,我就能下床行走了,一个半月之后,我就康复出院了。
出院这天,风和日丽,窗外的花草都向我点头含笑,玉兰枝上的几只麻雀也都欢快地蹦跳着,远远地就和我打着招呼,似乎还要陪送一程。
在走廊的拐弯处,我们遇到了康复科的女大夫,这是我在中医院一个多月来第二次见到她。女大夫大概早已把我给忘记了,她见我就如同见了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如同见了从另一个世界里走过来的人。我连忙和女大夫打招呼:“大夫,你看我……”女大夫依旧大笑,但面部表情复杂,有三分之一的肌肤的确在动,但另外三分之二的脸皮已经僵化了,笑得怕人,像个女鬼。
在我转身离去时,我听到女大夫在我的身后说:“看看,这个老爷子就是被人民医院推出门外的高龄高危的不治病人,经过我们康复科的推拿,已康复如常了……看看,老爷子走路的架势,比好人还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