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
◎李仁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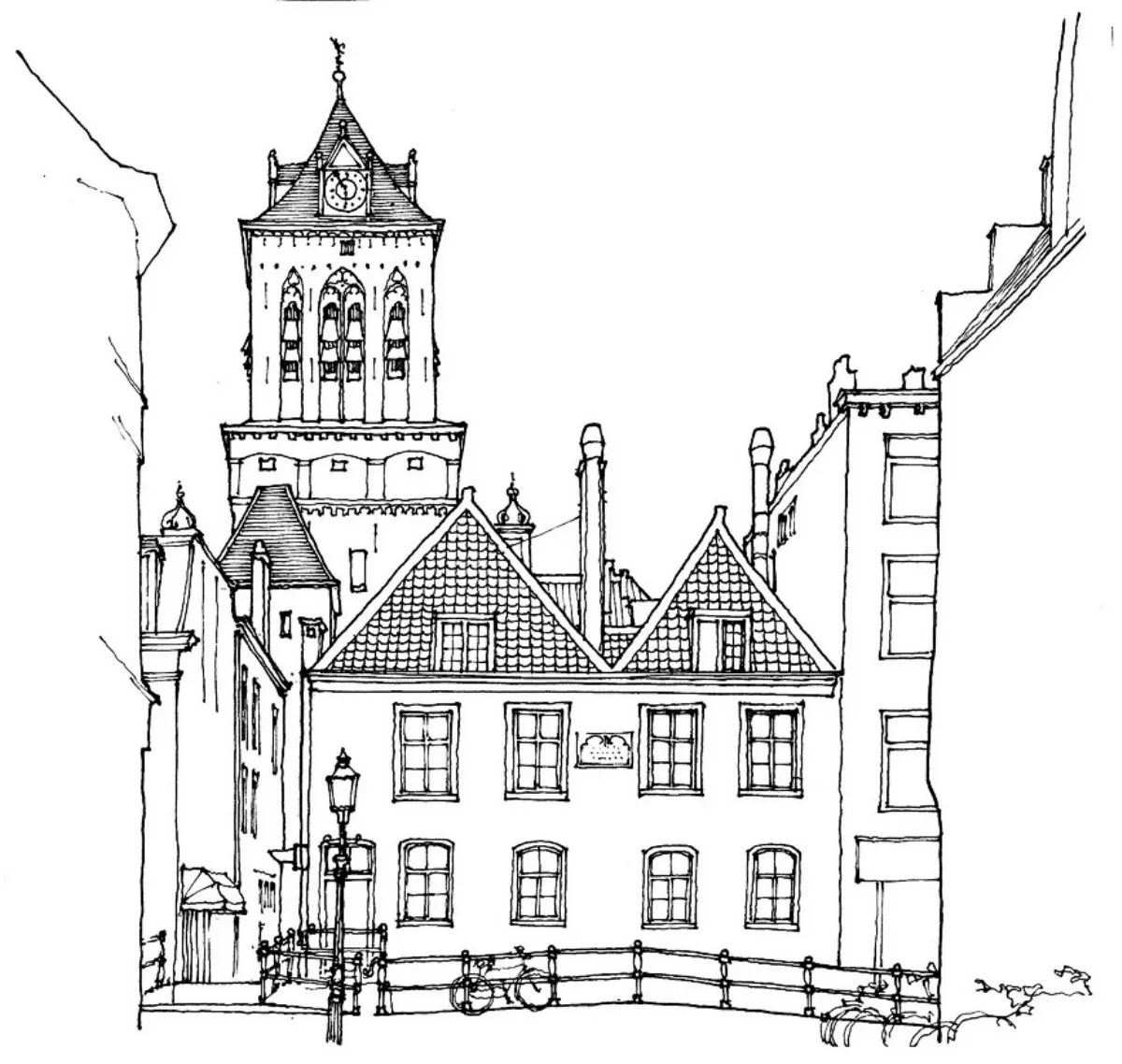
1
天气一寸寸转暖,风儿一丝丝柔软了,城里的女人们睡莲般地醒来,纷纷攘攘地绽放。女人街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满大街都是走秀似的女子,到处都是优雅的脚步和摇曳的花枝。望着满地翻飞的脚步,娃娃总是特别留意别人脚上的鞋——鞋来了,也就意味着他的生意来了。黄定平总是两眼嗖嗖地在人丛中寻找美女,看见漂亮女子便两眼发亮,印戳子似的盖上去,盖在人家肉垛子上就拔不下来了。乔芳见他蚂蝗似的紧盯美女不放,忍不住就气了,说,瞧什么瞧?有胆子你就上去抱着人家啃两口!
黄定平嘿嘿地笑,涎着脸说,牛走在垄上还朝旁边的青苗子撩一口咧——我又没撩妹,不就多看了一眼吗?
乔芳曼声叹道,唉,你这双贼眼就是犯贱!你能不能像人家娃娃,别那么恶心好不好?
黄定平乜一眼娃娃,绷着脸呛道,我要是像他个小皮匠,你乔芳不早就成潘金莲了?
娃娃是个侏儒,平时最怕人说他是武大郎了。黄定平张口就喷,喷得娃娃满脸是霜,蔫蔫地抬不起头来。
娃娃跟他俩都是乡下来的,且租住在城郊的同一个屋檐下,又同在女人街的鞋城脚下摆手艺摊子。
娃娃是个鞋匠。因为修鞋多以皮件为补料,所以鞋匠的传统称呼也叫皮匠。眼下,鞋匠这宗传统手艺其实早已过时不香了——人们越来越奢侈,鞋还半新不旧的就扔进了垃圾桶,谁还会穿个打了巴子的破鞋呢?
娃娃起先是在乡下修鞋,随着乡下的脚步乌泱泱地往城里走,村头巷尾和田间地头就剩几双老迈蹒跚的布鞋了。乡下变得几乎无鞋可修,于是开年以后,娃娃尾随潮水般的脚步,屁颠颠地也进城了。城里人多,满大街都是匆匆的脚步,可奔他修鞋的人仍然是寥寥无几。不过,娃娃还是挺执着的,因为这宗手艺是他爸亲手传他的——娃娃他爸是个老皮匠,生前也做钉履补鞋这一行。起先,娃娃死活不肯传承他的衣钵,嫌这活儿脏,整天捧个鞋子闻人家脚丫子臭,实在太丢人啦!老皮匠抚着娃娃怎么也长不高的身子骨说,娃呀,三十六行咱皮匠排位十五。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连诸葛孔明见了咱都甘拜下风,咋能说丢人呢?
黄定平和乔芳是一对小两口。黄定平刻得一手好字,擅长戳字雕章。但雕章一行也不景气了。现在都兴电脑刻章,眨眼工夫就能克隆一片。可电脑刻章技术一出笼就被人垄断了,他黄定平即使削尖脑袋也未必挤得进去。好在黄定平脑子灵光,见势不妙就立马转舵改行了。眼下黄定平之所以仍然据守这个摊子,其实是拿雕章做幌子,招徕其他生意而已。
黄定平一般不会到摊子这边来,平时都是乔芳一个人蹲守。如果有人过来悄声问她一句,办证吗?乔芳便赶紧四下里巡睃一遍,接着细声回道,办,通办!一个模子磕出来的,包你满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乔芳收了订金,立马捂着手机打电话。不一会儿,黄定平骑着摩托一溜烟就赶过来了。
今天女人街人多,就像大马哈鱼洄游似的,特别热闹。可能是在出租屋里宅腻了,黄定平一到街上就眼花缭乱,领了活儿也迟迟不肯离开。
其实,娃娃也爱看漂亮女人,只是不像黄定平那般过分罢了。娃娃看美女只是愉悦地一瞄就转移了,目光很快滑落到对方脚下——脚上的鞋才是他最关心的!
现在是女人街的客流旺季,娃娃指望修鞋的生意也能随之旺相一点。早上天刚麻亮,黄定平还在搂着娇妻酣睡,城市的街灯仍然瞪着毛黄的眼睛,娃娃已经挑着担子晃晃地出门了。担子一头挂着木箱,一头挂个“铁公鸡”。箱子里头鸡零狗碎地装着一些补鞋用的皮渣、鞋钉、胶水和绱鞋用的木楦子等物件。“铁公鸡”就是钉鞋用的铁拐顶,立在地上就像个打鸣的公鸡,所以一般人形象地称之为“铁公鸡”。
到了鞋城,娃娃先把铁公鸡歇在地上,然后趴在箱子口上戳点一番,看修鞋的小物件都带齐了没有,接着转身进楼梯间搬出乔芳的“办公桌”,又拿抹布擦拭了几遍,最后才吁一口气,坐在箱子上眼巴巴地等生意。
往往要待街上的脚步稠密了,乔芳才拎个包从人丛里钻出来。乔芳从包里取出一块布来,哗地一抖,雪白地展开,围裙似的将桌子罩住,前面帷子上还晾出几个字来:雕章处。乔芳将几枚样章和印料子往桌上一墩,接着就坐在娃娃的箱子上,跟娃娃闲闲地聊扯起来。乔芳问他开张了没?娃娃摇一摇头,样子有些沮丧。乔芳见满大街闹春似的,花儿样的美女一茬接一茬,又问他想不想女人?娃娃又摇摇头。乔芳定定地看他,说他虚伪,说不想女人就不是好男人。娃娃只好羞赧地点一点头。乔芳抿嘴一笑,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娃娃既没摇头,也没点头,脸倏地红到了脖颈。乔芳说,要想找媳妇你就得多挣点钱——还是赶紧改行吧!又说,城里灰尘多,人又爱体面,鞋子擦得勤——你不如干脆改行擦鞋子算了!
娃娃不吭气。其实,娃娃也想改行,可一想起那天给人擦鞋的事来,心里就发怵,对擦鞋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和抗拒。
那天,乔芳回去午休了。娃娃坐在箱子上困得直打哈欠,一会儿便啄米鸡似的拜起了瞌睡。迷糊之中,娃娃忽然觉得箱子沉了一下,睁眼一看,发现是个陌生女子坐在身边了。他忙不迭起身,问那女子是不是要修鞋。女子面无表情,没搭理他。娃娃转而看她脚上的鞋,立马就尴尬了——那是一双红鲤鱼似的高跟鞋,溜光锃亮非常打眼,显然就是方才逛鞋城买的,而且这种喜红的鞋,一般只有做新娘子的才会穿它。娃娃打量女子,那女子果然一袭靓装,脸上还浓墨重彩地抹了戏妆,模样很妩媚,却又显得十分冷艳。
女子见娃娃愣愣地瞧她,兀地就火了,说,你眼瞎呀?好生瞅瞅,这可是咱刚买的新鞋——哪儿破了?我看你不是要修鞋,是想找修咧!
娃娃知道自己冒昧了,正要给她赔个不是,却发现自己被人老鹰抓小鸡似的叼到了半空。他四脚踢腾地挣扎了一下,一个头上扎着一撮毛的男子旋即进入眼里。
一撮毛拎着他瞧了瞧,凛冽地笑道,嗬,原来是个小地精呀!你他妈胡诌,老子一脚把你踩成照片!
说着,一撮毛将他重重地扔下台阶,然后一屁股砸在箱子上,翘起二郎腿,冲娃娃勾着手指头说,三寸丁,赶紧过来给老子擦鞋!
娃娃跌在地上崴了一脚,趴在台阶上咧着嘴说,我是修鞋的,不会擦鞋,再说手里也没鞋油咧……
一撮毛冲自己鞋上啐了一口,说,这就是鞋油——擦吧!
一撮毛两眼血红,像个斗鸡似的瞪着娃娃。娃娃吓得浑身直哆嗦,无奈之下只好拿来抹布,含着泪珠子给他擦了起来……
这一幕赶巧让乔芳回来看见了。乔芳上前将娃娃一把拽起,冲着一撮毛气咻咻地嚷道,你这样欺负一个弱小,觉得有意思吗?
一撮毛愣怔地看了乔芳一眼,乔芳母鸡护雏似的将娃娃揽在一边,鄙夷地瞪着他。一撮毛自知理亏,拉着那女子便灰溜溜地走了。娃娃抱着乔芳丰腴的大腿,鼻子一酸,竟然孩子般地哭泣起来了……
2
找娃娃修鞋的,几乎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抑或是在城里打粗活的民工。而女人街是条时尚的青春街,老人和民工平时很少往这里光顾。娃娃之所以选择到女人街摆摊修鞋,其实当初也是受了乔芳的鼓动。乔芳说女人街人流量大,人多脚多,生意也就自然很好。其实,乔芳主要还是想娃娃过去给她搭个伴儿,身边也好有个说话解闷的人。
其实,娃娃也有自己的名字——王大魁。乔芳打从认识娃娃以后,总觉得叫他“王大魁”就像在挖苦他似的,于是干脆就叫他“娃娃”了。
乔芳做梦都想要个娃娃。她跟黄定平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尽管黄定平勤奋得像头公牛,恨不得每晚都要吭哧吭哧地犁她一回,可种子下去,地里就是不见动静,馋得她看见孩子就忍不住想抱一抱。
乔芳喜欢娃娃,甚至还当着黄定平的面抱过娃娃咧!她把娃娃亲昵地搂在怀里,水汪汪地望着她。娃娃闭着眼,两颊熏红,似乎有些眩晕。
其实,除了长得袖珍一点,娃娃还是挺帅气的,眉清目秀瓜子脸,形象要把武大郎甩过几条街去。除了帅气,娃娃还很单纯,像个孩子似的天真无邪,跟他说话做事不消设防。而且,娃娃也挺暖男的,时常买些她爱吃的水果,悄悄地放在她桌子的抽屉里,让她一坐下来就会获得一份喜悦和感动。这使她油然而想起中学时代的那个同桌——那个男生总是偷偷地将一些时令的花儿草儿放在她搁书本的课桌里,春天有金色的油菜花,夏天有洁白馨香的栀子花,秋天有黄亮的银杏叶片儿,冬天还会恶作剧地放一把雪花。只是那些花儿草儿最终还是蔫了。后来,乔芳偶尔想起,心里还会泛起一丝甜蜜和淡淡的忧伤。夜深人寂的时候,逼仄的出租屋里一片漆黑,身边鼾声如雷,她在烦躁之中偶然也会冒出一种奇怪的想法来——要是躺在身边这个男人不是黄定平,而是那个浪漫的同桌又会怎样呢?也许她的后来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至少不会这么鬼鬼祟祟地蹲街觅食,把自己整得活像个专干坏事的女特务。
尽管黄定平一直努力瞒着娃娃,其实娃娃早就发现他俩的秘密了。乔芳信得过娃娃,这天,闲聊之中,乔芳干脆就把他俩做假证件的事告诉他了。娃娃听了一点也不惊讶,只是担心她会不会被人逮着,逮着了会不会坐牢?乔芳说,不就是替人做个假吗,不至于吧?其实,乔芳心里也没底,听娃娃这么一问,心里倒是嗵嗵地打起鼓来了。
乔芳心里忐忑,忍不住把娃娃说的话讲给了黄定平。黄定平沉吟了片刻,皱着眉头说,这小人儿会不会把咱俩的事捅出去?
乔芳断然摇头,说娃娃绝对不会做伤害她的事。
黄定平说,你是他娘啊,还是他媳妇,敢这么肯定?见乔芳不吱声了,黄定平忽然自我检讨起来,说他平时太轻慢娃娃了,得贿赂一下他才行。接着问乔芳,娃娃喜欢什么?
乔芳反问,你喜欢什么?
黄定平挠头想了想,讪讪地笑道,哦,知道了……
这天晚上,黄定平将一个包裹递给乔芳,叫她给娃娃送过去。那包裹用胶带封着,捆扎得很严实,显然是走物流快递过来的。乔芳有些好奇,问里面是啥?黄定平一本正经地说,衣服!我在网上买的,还挺贵咧,也很时髦——娃娃见了一准喜欢!
乔芳高兴地说,我正琢磨着给娃娃买几件衣裳咧,看来咱俩想一块儿了。只是娃娃的衣服太难买了,他那年龄段身材既不能穿童装,市场上也找不到适合他的成人装,也不知道你买的这衣服合不合他的体?
黄定平一口笃定地说,肯定合体!我亲自量过他晾在屋檐下的衣服,照他的尺寸报过去的。而且质量也是绝对没问题,人家可是专门定制袖珍人服装的品牌店咧——你瞧瞧,这上面还有那个品牌的名字咧……
乔芳定睛一看,包裹上果然模糊地写着几个字:欢乐娃娃!
乔芳说,还是你自己送给他吧!这样不是更能表达你的诚意?
黄定平立马推脱,那可不行,我平时对他就没啥好言语,这会儿突然送个礼包过去,他还不怀疑我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还是以你的名义送过去吧,他肯定不会拒绝!他接受了你,也就等于是接受了我——我俩谁跟谁啊,你说是不是?
乔芳觉得黄定平说得在理,于是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娃娃就住隔壁。晚上,娃娃收摊回来的时候,乔芳一个转身就到了娃娃的出租间。她将包裹递给娃娃。娃娃问那是啥?乔芳说是衣服,是她特意买了送给他的。娃娃迟疑了一下,有些难为情的样子,但看得出来,娃娃心里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是受宠若惊。乔芳本来想将包裹打开,让娃娃当着她的面试穿一下再走,不料黄定平已经在那边疾声催促了,叫她赶紧回去做饭……
3
第二天,娃娃仍然起得很早,可他一脸疲态,怏怏的老是打不起精神。乔芳问他是不是感冒了?说着还摸了摸娃娃的额头。娃娃低头不语。乔芳问他衣服打开看了没有,娃娃的两颊刷地就红了,支支吾吾地说看了。乔芳又问合不合体?娃娃的脸膛腾地燃烧起来。乔芳知道娃娃平时就很腼腆,而且她还知道,越是腼腆的男子,骨子里越发多情。乔芳担心娃娃生出一些误会和别的想法来,于是也就不再问衣服方面的事了。
这天夜里,黄定平依然鼾声如雷,乔芳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她非常纳闷,今天娃娃是怎么了?整天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也不跟她说一句话,见了她就慌神忙乱地埋下头去,像做了什么丑事似的。
娃娃跟她只有一墙之隔,出租屋之间的封闭性并不是很好。娃娃刚住进来的时候,黄定平的鼾声也是扰得他非常难受,好长一段时间他才慢慢适应过来。黄定平每次向乔芳索爱,乔芳也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弄出动静来惊扰了娃娃。娃娃虽说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可那毕竟是一汪早就成熟透了渴望着开镰入仓的麦子,一阵风儿吹过,或许都能哗哗地挠下许多麦粒来。也许娃娃尚还没有那方面的经历,但对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情他未必不懂。
上半夜的时候,娃娃那边一直都比较安静。到了下半夜,乔芳在睡意朦胧之中,隐约听见娃娃那边有窸窸窣窣的响声,接着是鼻息很重的喘息声。乔芳觉得那声音有些怪异,于是侧耳细听,居然听见娃娃在幽幽地啜泣,而且啜泣之中还在呓语似的喊叫什么。虽然这喊声十分压抑,细若游丝,但乔芳还是清楚地听到了两个字——那就是她的名字,乔芳!乔芳心里猛地咯噔一下,接着怦怦乱跳。乔芳已然意识到娃娃在做什么了,顿时觉得浑身燥热起来,心里一下子变得凌乱。乔芳心里五味杂陈,终于忍不住地咳了一声,那边的声音顿时戛然而止,一切都在漆黑中归于平静……
乔芳大抵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第二天清早,乔芳估摸娃娃已经挑着担子走了,于是呼地掀开被子,狠狠踢了黄定平一脚。黄定平见她憋得满脸涨红,就像着了火似的,问她怎么了?乔芳问他到底给娃娃灌了什么迷魂汤?黄定平问她啥意思?
乔芳问,你送给娃娃的到底是衣服,还是毒药?
黄定平诡谲地一笑,说,欢乐娃娃呀!
乔芳似乎悟过来了,一扭身便下了床。当她走近隔壁屋子,推开门的时候,顿时就傻了。娃娃的屋子里已经是空荡荡的了,除了床头柜上放着的那个包裹之外,衣服、被子啊什么的,凡是属于娃娃自己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了——娃娃显然已经搬走了。
乔芳赶紧往女人街寻去,可娃娃已经不在鞋城脚下了。乔芳知道娃娃的手机号,立马给他打过去,娃娃没接。乔芳望着娃娃放箱子的地方,想他每天呆呆地坐在箱子上等生意,又想他时不时地将一些水果默不作声地塞进她的抽屉里,眼泪啪嗒啪嗒地就掉下来了。
乔芳郁郁地回到出租屋,哽咽地对黄定平说,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做假了——我要回去!
过了两天,乔芳真的就走了。乔芳走后,黄定平没了帮手,只好白天亲自往女人街蹲摊守点,晚上回屋黑灯瞎火地赶做夜活,累得就像个盗掘金矿的贪心贼似的。不久,黄定平果然叫人逮进去了。乔芳去看他的时候,黄定平气哼哼地说,肯定是那个小地精告发的!乔芳叫他别冤枉人家娃娃。既然进来了,干脆就安心地待在里面,好好琢磨一下以后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