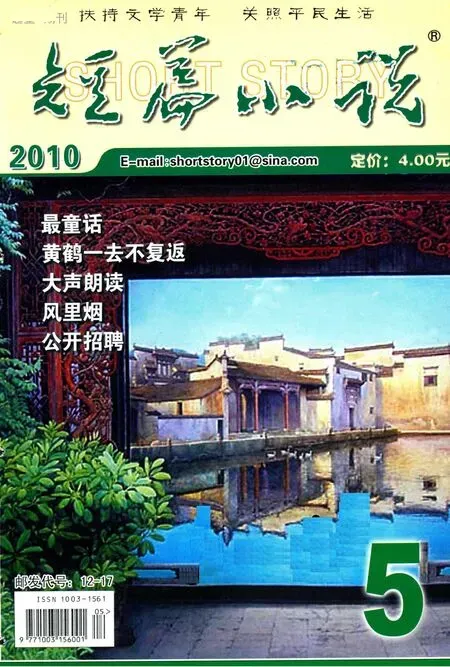秋事
◎刘志红
一
秋分一过,地里的玉米棵子就像一个个即将结婚的女子一样,一天一个样儿地往成熟里蹿。今天还穿着绿衣裳,羞答答地吐着红樱子,一夜过去,那绿衣裳已换成了黄装,红樱子呢,也成了酱黑色,好似急不可耐地等着主人来把它们领回家。
玉秋取了镰刀往地头走,这几天她每天至少要去看两次,等那一群女子完完全全地换了装,她就要开镰。这个时候,她每天除此以外,还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这个节骨眼上可要不得阴雨天,一旦摊上阴雨连绵的天气,这即将收获的庄稼就该大受损失了。

按捺不住激动心情,庄稼们的气息已循着一切可能的路子,曲曲弯弯绕过许许多多的障碍物跑到村子里来了。还没出村,玉秋就闻到了她们的气息。成熟的、热烈的、甜腻的、馥郁的、清凉的……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气息。玉秋对这种气息再熟悉不过了,也喜欢得不得了。她贪婪地撮起鼻子吸起来,唯恐体验得不够彻底,干脆微微闭上眼睛,把嘴角弯成了一个好看的弧度。
到得地头,玉秋揪住一棵玉米棵子,不由分说就亲了起来。她用脸碰它的穗头子,那酱红的樱子扫着自己的眉毛眼睛,酥酥的,让她陶醉。她用鼻子嗅它的全身,沉醉地眯上眼睛,脸上呈一种忘我的神情。末了,干脆拽过一片长叶子咬到嘴里,用牙齿轻轻撕下一缕,卷到嘴里嚼着,似乎这是什么好吃的果子。她喜欢她的庄稼们,就连庄稼的叶子,她也觉得它们亲厚、可爱、迷人。
如今,人们都追求效益最大化,村里已没有几个人安心、认真地侍弄庄稼了,尤其是像她这样的中青年人。在这个地方,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惯就是男人外出打工挣钱,女人看孩子种地,农忙时男人回来帮女人收庄稼。这样的习惯不知何时起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女人们也不再安分守己在家种地看孩子了,而是把孩子扔给父母,跟着丈夫出门挣钱。一想到这些,玉秋的心里就恨恨的,不觉就骂出一句粗话:娘的,都到外面浪去了!
要不是这些不安分的女人,罗现军会被那个不要脸的勾去?要不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自己哪会落到今天这形单影只的地步?玉秋一想到这些,胸口那儿立刻就像被谁填充了啥充实物,堵得那口气简直要上不来了。玉秋赶紧劝自己:不是说早就翻过去了吗?又在翻,又在翻,看你这出息!她用手啪地给了自己一巴掌,说,以后记住了,不许再想那个姓罗的,更不许想那个骚狐狸!给我记住了,你可!她自己又给自己答应,记住了!
二
玉秋再也想不到,这天,说下雨就下雨了。天气预报上明明说是多云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天爷居然自作主张、毫无预兆地下起来了。而且是滴答滴答,显得很有耐心的那种下法。要是电闪雷鸣一阵,呼啦啦下一会儿,倒也好了,就怕这样的下法,滴答滴答,滴滴答,摆开了无休无止的架势。
玉秋打了伞站在地头,看那雨滴一滴一滴劈头盖脸打在玉米棵子上。已然成熟的玉米棵子颓然垂了头、低眉顺眼地站在那儿,一副无辜的、逆来顺受的模样。每一片叶窝子那儿都汪了一摊黄水子,积累到承受不住时,便微微倾一下身子,呼啦啦把那汪黄水子泼下去。
玉秋看着一地被雨水浸淫的玉米棵子,心疼得不住地叹气。
四野里一片灰蒙蒙的,灰蓝色的天幕似乎在不远处已与地连在了一起,一时半会儿怕是分不开,分不开那雨水子便一时半刻不会停下,这就急人了。如果再这样下上三五天,玉米穗子怕是要在包衣里开始烂掉了。玉秋不觉在心里祈祷着,老天爷,别下了。
也不知是玉秋的祈祷起了作用,还是老天爷自己累了,也或许是怜悯玉秋这样视庄稼如命的人儿。总算在连续下了五天后偃旗息鼓了。这不,天刚亮,淡黄色的太阳便羞答答从东方冒出了头。
玉秋急急地揣了镰刀往地里走,到达村口,迎头撞上一辆乳白色宝马X4小轿车,玉秋张皇失措地赶紧躲避,嗤……一声尖利、悠长的刹车声伴随着一个女人低声但清晰的骂声传入耳鼓,没长眼啊!玉秋抬眼看清楚了,端坐在驾驶座上的正是自己的丈夫罗现军,旁边那个打扮入时,一副狐媚妖冶相的黄头发女人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女人了。那句蛮横的叫骂声正是从她那张猩红性感的厚唇里发出来的,她怀里搂着的不用说正是他们野合而生的那个野种了。罗现军只向玉秋瞄了一眼,呼啦啦扫过一些个被玉秋品味得出的不屑、鄙视,同时昂起他那高傲的头颅,把自己足够的傲慢、强势、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渲染得神气活现。他一定看清楚自己了,他嘴角那丝嘲讽的笑已经足可以证明。看着这一对不可一世的、把自己的人生抛向深渊的男女,玉秋心中竟然是满满的怯懦和羞惭。巨大的自卑让她觉得矮了他们一头,似乎,做错的倒不是他们,倒是自己了。玉秋立即从心里纠正自己:不许这样想!是他们的错,这一对狗男女的错,与你玉秋无关,知道吗?你!你这个贱骨头,动不动就把错揽到自己身上了。玉秋往耳后抿一抿头发,弹一弹宝马车带到衣服上的灰尘,昂首向地里赶去。
湿漉漉的玉米地里氤氲着一股温吞的甜腥气和庄稼棵子被雨水浸淫后的腐烂气息。一些长势慢,还不够成熟的玉米肯定已经随同玉米皮子一起腐烂掉了。哎,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呀,天气的事只有天做得了主,哪个人又能管住天呢?玉秋发了一会儿感叹,开始割玉米。
玉秋一手抓住玉米棵子,一手挥舞镰刀,咔嚓一声,又咔嚓一声,一声接一声的咔嚓声,带着某种希望、欣喜、执着的色彩,给人鼓舞、让人兴奋。随着玉秋的身子不停地扭动,她的身后很快横躺下齐刷刷的一排玉米棵子。
玉秋干活手快、利落。用当初婶子大娘们夸她“出活儿”。其实,不仅仅是出活儿,还好。无论做哪种农活儿,横的竖的、圆的方的,凹的凸的,她都要让它们有棱有角,看起来顺眼、美观。
齐整的玉米棵子在阳光的蒸腾下,冒出腾腾的热气来。玉秋蹲在玉米铺子上掰玉米。左手摁着玉米穗的根部,右手往下一撇,一穗玉米就脱落下来,她瞅准不远处的一块儿空地,嗖一声扔过去。玉米穗子带着包衣,划着优美的弧线,不偏不倚,正巧落在了玉秋预想的空地上。第一个需要眼睛跟踪过去,后面的就凭感觉,她只管低头嚓嚓嚓地掰,随手一抡,那玉米穗子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嗖一下就飞到了玉米堆里。
三
玉秋干起活来常常不以时间为界限,而是按农活儿的需要来分早中晚饭。现在,她刚掰完那一块儿玉米地,早已过了午饭时间。
她像往常一样去厨房盛饭,一掀锅盖,却是锅干盆净,她不觉就怔住了。以往,农忙时婆婆都要很上心地为她做一日三餐,无论她回来得多晚。大米饭总是在电饭锅里热着,菜也在煤炉上温着。逢到天热,婆婆还常常专门熬了绿豆粥晾到适合的温度装到暖瓶里,等玉秋从地里回来,立即喝一碗,那脸上的汗珠子便会减少不少,浑身从里到外透着说不出的清爽与舒坦。
不夸张地说,婆婆是拿她当女儿疼了。而她又何尝不是拿婆婆当娘待呢?嫁到这个家里十六年了,还从没跟婆婆翻过脸呢!
玉秋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怎么上过学,勉强认得几个字而已。然而他们却知道遵从老祖宗遗传下来的老规矩。玉秋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娘一句一句叮嘱她:公婆也是爹娘,甚至应该待他们比爹娘还要亲,要孝敬他们。有好吃的尽着家里人吃,自己到最后,少了就不吃了。嘴是过道,不吃过老。有活儿抢着干,力是奴才,使了再来。姑娘家,在家里懒一点,嘴馋一点,还没啥,做媳妇的可千万要勤,不能懒,要紧着嘴,不能贪吃……
玉秋假装撅着嘴,撒娇地嚷嚷着娘你好唠叨啊,却是在心里边暗暗记住了。
玉秋按着娘的教导,一做就是十六年。
十六年来,玉秋不但按娘的教导做到了,而且做得比娘要求的还要好。不但家里家外做得好得没得说,而且还常常给公公婆婆洗衣服,包括内衣和袜子。
街坊邻居,时不时有媳妇因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婆婆争吵、摩擦,有的甚至闹得鸡飞狗跳的。婆婆们聚到一起,便直夸玉秋,说也不知她婆婆上辈子怎么修的,修来这么个好儿媳。婆婆的骄傲、自豪便明晃晃写在了脸上。谦虚一句:就那样吧。又觉得委屈了玉秋似的,赶紧再追加一句:我们家玉秋,说实话,真是没的说,待我们,那真是比亲闺女还亲,说良心话,比我们家青梅(玉秋的小姑子)强多了。
玉秋一直是作为标榜式儿媳妇被村里人夸赞的。
望着空空的锅灶,玉秋的心凉了、灰了。看来这段时间以来,自己的预感一点没错。
罗现军刚在外面有了那女人,回来嚷嚷着要离婚时,公公婆婆一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公公告诉他想离婚没门,除非我死了。
罗现军闹了几次,看爹娘不松口,玉秋也哭着闹着求着不要离婚,也就不再提,只是不回家,直接在晋城市——他通过房地产发迹的城市买了房养起了这个女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似乎是从那个女人有了那个小野种,一切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先是,婆婆居然默许了罗现军带着那女人和孩子回家了,虽然常常只作短暂的停留,并不过夜,但这依然是对玉秋的一种防线的悄然摧毁。以前,婆婆从不允许他带那女人回家,更别说带女人回来了,连想都不要想,若哪一天真带那女人回来,迫使玉秋离婚了,就先把自己的葬礼办了,再办跟那个女人的婚礼。婆婆的这些个硬邦邦的话儿时过五年,还清晰地响在玉秋的耳畔。
玉秋用手背抹一下顺着脸颊淌下的热辣辣的眼泪,失望像山洪暴发一样一下就把她淹没了。从嗓子眼那儿发出一声只有自己听得见的怪叫,她忽然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肚子疼般弯了腰跑向自己屋里,蒙上头嚎啕大哭。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女儿边用小手推她,边喊。
玉秋抹一抹眼泪,翻身坐起来,强装着说没啥。女儿说妈妈你撒谎,你都哭了还说没啥。妈妈,你到底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你告诉芊芊,芊芊帮你揍他。
不待玉秋说话,女儿把手里提着的塑料袋子递给玉秋说,这是奶奶让给你带的午饭,我们跟爸爸到酒店里吃饭了,刚回来。
一个大塑料袋里装了两个小袋,一个盛着大米饭,一个是大杂烩菜。红的黄的黑的白的绿的紫的,一股脑儿混在一起,它们来自不同的盘子,不同的菜品,强凑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别扭。不用尝就知道,这样的菜肯定是咸的甜的辣的麻的香的酸的混合味道,不肖吃,就把胃倒了。玉秋肚子里虽然饿得咕咕叫,但她一看那包菜,胸口那儿就开始一涌一涌地翻腾,玉秋让女儿赶紧送出去,说自己吃过饭了。
女儿并未离开,小嘴还在那儿叨叨着:妈妈,爸爸还带着一个阿姨和一个小弟弟,那个小弟弟还喊爸爸爸爸,喊奶奶奶奶,我警告他那是我爸爸,我奶奶,不许喊我爸爸爸爸,也不许喊我奶奶奶奶。他说那是他爸爸和奶奶,也不许我喊他爸爸爸爸,喊他奶奶奶奶。奶奶和爸爸居然都不管他,还笑。妈妈,你说,他们这不都不讲理了吗?
玉秋的泪再次汹涌而下。她扭过头强装着,告诉女儿自己不舒服,要歇一会儿,让她到奶奶屋里去。
女儿边往出走,边嘟囔着,爸爸坏,爸爸去给那个小弟弟当爸爸了,不回来了,我让他跟我回来,他开着车就拉着阿姨和弟弟走了。
四
玉秋把玉米棒子装到蛇皮袋子里,再一袋一袋搬到独轮小推车上,她要凭自己的一双手,一身力气慢慢把这一地玉米棒子运到家里去。
邻居翠珠路过,说玉秋你这是何苦呢?村里的三轮摩托车多得是,你随便叫一辆来,突突突,三五次就给你运完了,何苦用你这样蚂蚁搬家样何时才能运完?
玉秋笑笑,说,反正没事,慢慢运嘛。
村东头的韩老爹到老还是没改掉咋咋呼呼的脾气,远远地就嚷嚷着,我说玉秋你这孩子,咋这么拗呢?你买辆三轮摩托车要咋了?用得了几个钱?看你家现军都开上宝马了,难道还缺那个买三轮摩托车的钱?
玉秋尽量把嘴咧得像笑的样子,而且还不是苦笑。说,这不是推这个小推车,推习惯了嘛,就推这个就挺好的。
哎,你看你,这算什么嘛,咱这山坡路,你一个人,哎……
说话间,玉秋已把四蛇皮袋玉米棒子绑到了小推车上。她蹲下把车襻搭到脖子上,两手在车把手那儿把车襻拧了两下,确定稳实了,才鼓了一口气猛地站了起来。地头连接水泥路处是一个浅浅的小坡度,玉秋离地头还有好几米远就开始小跑起来,以便一下能冲上那个坎儿。已经走过去了的韩老爹一扭头看到了,边摇头叹息,边快速过来想帮玉秋拉一下。结果他非但没能捉住车头挡棍,反而被小车过猛的冲击力一下带翻了。
韩老爹跌坐在地上,哎呀起来。玉秋赶紧放下小车去扶他,他却站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哩哩啦啦从地里收工的乡邻纷纷帮玉秋一起搀扶起韩老爹,韩老爹一路哎哟着被大家送到卫生所,医生说这是墩坏尾骨了,需要到镇卫生院做个小手术然后躺着慢慢养。
玉秋不得不天天往卫生院跑,抽空再去地里收玉米。晚上常常还要加班把玉米棒子撕了皮,用留下的缨子编成玉米穗子甩到院子里的树上,让它们慢慢风干。
玉秋从地里回来得晚,吃过饭坐到玉米堆前,就已经是电视剧的播出时间了。婆婆屋里的电视机音量开得很大,玉秋能清楚地听到主人公们的台词。
只听一个女的哭哭啼啼的,哽咽着说,求你,别走……
一个男的,用一种厌恶的声音说,放开我!
接着响起一串叮叮咚咚的脚步声。
女的歇斯底里放声大哭起来。
又是一阵汽笛声、街市声,接着又传来这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的调笑声。
玉秋正纳闷婆婆从来不瞧这样的节目的,婆婆最恨人们说的小三、二奶了,今天婆婆怎么忽然就换口味了呢?
婆婆走过来了。拖过一个凳子坐下,开始帮玉秋撕玉米皮。婆婆边撕边漫不经心地打听韩老爹的情况,玉秋说放心吧,他已经好多了,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沉默了一会儿,婆婆忽然喊了一声,玉秋。
玉秋猛一怔,待明白婆婆确实是在叫自己时,赶紧哎了一声。
婆婆说,玉秋你看,把这季玉米收了,咱就别种地了,让有人的人家种,你看咱家,现军不在家,我和你爹老了,也帮不上你的忙,里里外外都是你一个人在忙,娘这心里过不去呀。况且,现军早就不让种地了不是?又不缺买粮的那个钱。
婆婆的话听上去贴心贴肺的,很熨贴很暖心。然而,玉秋的心里却乱得厉害,像是,她正干着自己最喜爱的事,忽然有人要从她手里夺走工具一样,让她莫名地心慌。
玉秋稳一稳神,说,娘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别可是了,听娘话,咱不种了啊。
沉默了一会儿,玉秋说,娘,我想种……
五
三亩地的玉米穗子硬是被玉秋那一双手挂到院子里的树上了。
枝杈粗大的梧桐树杈上,是一串串玉米穗辫子,枝杈较细的香椿树上是两穗缨子交叉系在一起的姐妹串儿。
金黄的大玉米辫子在阳光的抚慰下,活泼泼地泛着灼人眼球的光芒,放眼望去,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向人们眨眼睛。一阵风过,树叶子呼啦啦翻动着,像给玉米们披了一件绿色的纱裙,玉米们这时又成了一副羞答答的半抱琵琶半遮面的大家闺秀模样。
玉秋望着树上的玉米们,心里充盈着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幸福,它们从种到收都是经她的这双粗糙的手抚弄过的,于她,跟自己的宝宝也别无二样了。
玉秋望着她的玉米宝宝们,满足地笑着,那口雪白的牙齿在玉米与阳光的交相辉映下闪着迷人的色彩。
于庄稼人来说,一季一季的收获与播种就像一场接一场的战斗,然而这战斗,却是令人喜悦的、叫人痛快的。
玉秋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播种小麦的事宜了。机器开到哪个地块儿,她就用小推车把化肥运到哪块儿地头。她在机器前头撒肥,大把大把的碳酸氢铵像一团团雪沫子被她撒得呼啦啦飞,她喜欢这种感觉,就连呛鼻的化肥气味于她,倒没觉得多呛人,反到觉得有种别样的亲切,她似乎能从这种气味里嗅出麦香扑鼻的麦子的味道、甜香的暄馒头的味道。
耕地机轰隆隆从撒过化肥的地上碾过、身后的齿子把板结的泥土翻掘过来,一股新鲜的泥土气息立即取代了残留在空气中的秋庄稼的气味,忽然就给人一种改天换日的翻天覆地感,这种感觉让人莫名兴奋,平添力量和希望。
今天一天耕了三块地,这块儿刚撒完化肥,有人就来喊玉秋耕车已开进另一块儿地里,让她赶紧过去撒肥。从天微亮到夜幕完全降临,她一天没顾上吃一顿饭,只在一次回家推化肥的时候喝了一杯凉白开。
人们常常说的累得像散架一样,玉秋这会儿真切地体会到了。她匆匆洗漱了一下,倒头就躺下,就在她即将睡着时,婆婆来了。婆婆说,玉秋啊,不是我说你,你这是何苦呢?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看你累的。
话明明是心疼自己的,玉秋却从婆婆的语气里听出另一种味道来,这是责怪的味道,是嫌自己不知好歹的味道。在玉秋,像被人夺饭碗的感觉。
玉秋说,娘,我知道你心疼我,可不让我种地我又能干什么呢?
不是不让你种,而是不够大,你瞧瞧,韩老爹这次住院花去的医药费够你种几年地的收入了?
可是,别可是了,一句话,不要再种地了。
婆婆撂下这句话就走了,玉秋傻愣愣地看着天花板发呆。她不明白,之前一直支持她种地的婆婆为什么如此强烈反对她再种地。她心里明镜似的,韩老爹的意外事故只是婆婆的一个借口罢了。
六
翻耕过来的土地,暄腾、细腻,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一种温润的土腥气,这是养庄稼的味道,也是养人的味道。
玉秋抓一把在手掌心里,让它们细细地流淌,如泉似溪,更像生命的细流。
播种机突突着,随着一缕缕灰色的烟雾升向遥远的天际,屁股后头播下一地的希望。
玉秋今年买的麦种是龙大三十二万粒,听着气势就大,想来产量也一定不错。据说抗虫抗病抗旱抗倒伏能力超强,亩产量可达一千四五百斤,真是一个喜人的数目。
这边播种的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希望,那边的失望却是日胜一日。
罗现军这次回来居然住下了,玉秋很不适应,虽则依然是分房睡,于玉秋仍然是折磨。她对他现在简直是恐惧了,她害怕看到他那无时不在的洋溢在嘴角的嘲弄的笑,更怕他俩嘴片儿一翻一覆,口气硬厉的离婚二字蹿出来。已经多少次了,她感觉自己就要招架不住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天吃过早饭,玉秋拿了铁耙正准备去地里把机播没掩盖好的小麦埋好。
罗现军拦住了她的去路。玉秋欲躲一躲绕出去,罗现军说话了,怎么?不敢见我了?今天,咱们该好好谈一谈了!
罗现军的语气透着不容置疑的质地,有着压倒人的气势,玉秋的心像被谁的手爪子拽了一下,突突突地跳荡着,她把铁耙子顿到地上,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故作轻松地说,谈就谈,有什么好怕的!
王玉秋啊王玉秋,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是不是离开我罗现军就再也寻不到男人了?离开我罗现军的家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家,而要像一条流浪狗一样到处流浪了,啊?你说是不是?
你……
玉秋的脸霎那间变得煞白,巨大的屈辱让她忍不住把手里的铁耙劈头盖脸向罗现军扔过去。
不许你侮辱我!
罗现军轻轻一跳躲过铁耙子,脸部的嘲弄变本加厉,从翻动着的俩嘴皮里蹿出来的话更加气人。
啥叫侮辱,是你让我屈辱好不好?我跟小凡都爱了五年了,却生生被你这个不要脸的泼妇拦着挡着揪着拽着死死不放,让我的小凡和儿子至今进不了这个家门,没有个名分。
之前,玉秋光听说过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再也想不到这世上居然真有这种睁着眼说瞎话的人,而且就是自己曾经一心一意爱着的丈夫!
玉秋感觉胸中一团火已经旺旺地烧起来了,这火把她的脸烧红了,肿胀了。她瞪着罗现军,那架势像一头准备扑向猎物的猛兽。
玉秋吼出一句,闭上你的狗嘴!
你敢骂我狗,我看你连只狗都还不如呢!狗还有廉耻心,骂它一句还知道走开,你呢?就会死缠!
你个王八蛋!离就离,谁怕谁!
让玉秋心寒的不仅仅是罗现军的无情,还有婆婆和儿子。
这次在和罗现军离婚过程中,婆婆从始至终居然没有过问一声,一直是不知道这回事,或者说是默默支持儿子的样状。
巨大的气愤让玉秋不管不顾地答应了罗现军只带一双儿女净身出户的苛刻条件。然而,十五岁的儿子龙龙却说啥也不愿意跟她。龙龙说,我不要离开家,我要守着我的家。过后,玉秋觉得还是儿子这样对,要是都跟着自己,就凭自己一天五六十元的工资,除去房租、吃饭,还会剩多少?哪儿还有力量供俩孩子上学?这么多年与罗现军在一起,她已深深领教了罗现军的无情无赖嘴脸,她知道,就算离婚协议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每年要罗现军支付孩子抚养费的,但他绝不会给。玉秋铁了心再也不想与他有任何纠缠,下决心苦死累死自己养女儿,决不去求他。
七
玉秋感觉真像罗现军说的那样,自己简直就是一条被主家遗弃了并一棒子打出去的落荒而逃的流浪狗,狼狈不堪地从自己钟爱的土地上逃到小城里来。租房子、为女儿办入学、找工作……又因各种原因数次搬家。在四处飘荡中,时光居然悄悄走过了四季。
尽管城里没有庄稼,玉秋凭着数十年与庄稼们的相厮守的经历,依然能在不同的季节里隐约闻到各种农作物的气息。这个时候,应该是麦收刚过,玉米该下种的时候了。
院子里有一大块没水泥硬化的土地,堆满了住户们的垃圾,其中有人捡的各种废品:五颜六色的塑料瓶、废纸箱子、废铁皮种种,还有一些塑料袋、被主人丢弃的旧衣物、破桌子烂板凳等等。
玉秋见不得这样的邋遢,刚一住进来她就挽起袖子收拾起来。不能用的一趟一趟抱了送到街上的垃圾箱里,住户们攒的垃圾,她一一给规整了放到角落里。一块儿黄色的板结土地立即呈现在眼前。玉秋把鬓角垂下来的一缕头发抿到耳后,擦一把脸上的汗,露出了离开家后的第一个笑容。
玉秋看着这块儿土地,蓦然从心底升腾起一股欢欣来。她扭身进屋取出带来的镢头、铁耙。玉秋真是奇怪,那天被罗现军用激将法气走,气头上的自己一分家产都没要,只带了女儿出来时,怎么居然会不忘带这俩家伙呢?街上站着看好戏的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他们一准在心里想这女人是被气糊涂了,脑子有病了,否则怎么会不给自己争取一点家产,却偏偏带了人家不要的俩铁家伙呢?
百万家产哪!嘁!
就是,玉秋这女人看着机灵,其实真傻。
不傻的话人家现军也不会不要她呀!
现军也真是,咋就这么狠心呢?一分钱也不给她。
玉秋走过时隐隐约约听得见人们的议论。
玉秋一镢头一镢头地开始筑地,尽管刚下过雨,那地还是板结得每一镢头下去都无比艰难,坚硬的土地每每把镢头嘣得老高,震得虎口麻酥酥的,甚至数次把镢头震落在地。玉秋往手心里啐一口唾沫,使劲儿把着镢把,一下,一下,再一下,一次只能吃进去一厘米,蜗牛爬行般。汗珠子随着她的挥舞动作啪嗒啪嗒滴到泥土里。筑完,又用铁耙子仔细地篓过,玉秋还嫌土地不细腻,干脆蹲下来用拇指和食指俩指头肚把一些小土坷垃细细捏了,再用铁耙子刮土修畦。玉秋简直是把这一小块儿地当作她曾经劳作的大块儿土地来对待了。平整完,玉秋又站在地头仔细瞅了,确认无瑕疵了,才擦着汗满意地笑了。
接下来,玉秋给土地下种了。
她一丝不苟地刨八叉,认认真真地点种子。接着按一切种玉米的规律,间苗、施肥、锄草。玉米棵子乘着风、就着雨,呼呼地往上蹿。
秋分一过,那种农村里特有的成熟庄稼的味道立即开始往人鼻子里扑,玉秋每每捕捉到这股味道,便要揪着鼻子、闭上眼睛,狠狠地吸上几口,陶醉一番。
收获了百来穗玉米,玉秋分给邻居们一些,其余的都给女儿煮着吃了。女儿边啃玉米棒子,边开心地喊着,妈妈,好吃,妈妈,真好吃!邻居们也纷纷说可比街上卖的好吃多了。
女儿忽然冷不丁地说,妈妈,我将来要考种地的大学,我要像你一样,种地,就能吃上玉米棒子了。
玉秋本来满足地看着女儿啃玉米的,一听女儿这样说,忽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说你给我住嘴!不许说种地,不许考种地的大学,种地最没出息!听见了没?
女儿嘴里那一口玉米还未咽下,被妈妈厉害的模样吓愣怔了。在她的记忆里,妈妈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厉害过呢,即使是爸爸当年又找了漂亮阿姨,不要妈妈了,也未见妈妈这么对自己凶过。嘴里的那没有咽下去的、嚼得半拉子的玉米颗粒很快催生出两行热泉,顺着女儿的面颊蜿蜒而下。
玉秋一下心软了,她流着泪一下把女儿抱在怀里。喃喃地说,小玉,对不起,妈妈不该吓你,可是你要知道像妈妈一样会种地才是没出息的呀!你可千万不要学妈妈,而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在城里工作、生活,做个城里人才是啊!
九岁的女儿擦着眼泪,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答应着,又用小手帮玉秋擦泪,说,妈妈不哭,以后芊芊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芊芊长大以后决不种地,种地没出息!
当女儿说出这样的话,玉秋的心底又翻涌上来一股难言的悲情。
夜里,玉秋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中,女儿农业大学毕业了,回老家跟自己一起种地了,那漫天遍野的绿一下子把玉秋高兴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