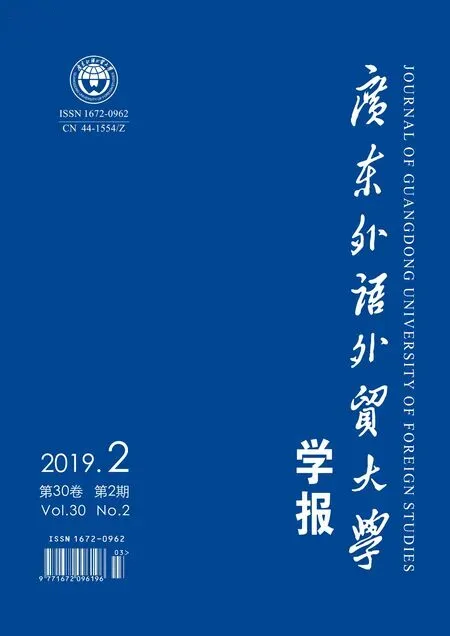网络文本交流的二语促学机制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
张宏武
(嘉应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一、引言
网络文本交流已成为流行而普遍的人际交流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中介交流(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技术进入二语(L2)课堂教学领域,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CMC分为实时交流(Synchronous CMC,SCMC)和非实时交流(Asynchronous CMC,ACMC)两种,本文主要讨论SCMC的二语促学作用。SCMC通常又被称为网络文本交流(以下简称“文本交流”)或被通俗地称为“网聊”(Text Chat)。它是通过键盘输入或指尖触屏的方式进行在线的、非视频的、无声的网络交流。这种交互方式与面对面(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FtF)交流有何区别、能否在L2促学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二语习得(SLA)研究领域对文本交流的互动特征及其二语促学功能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从SLA视角,对文本交流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剖析其二语促学作用及复杂性,同时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文本交流未来研究趋势提出一些思考和设想,以期对中国外语教学产生有益启示。
二、文本交流与面对面交流的异同及各自相对优势评价
作为人际互动方式,面对面交流(FtF)和文本交流(SCMC)的二语促学效果一直受到SLA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L2文本交流研究也沿用了传统的FtF交流的研究模式。例如,研究者把人际交流中的“Trigger-indicator-response-reaction”四步协商互动模式(Varonis, et al, 1985)应用到L2文本交流的分析中,成为SCMC研究的主要分析方式。FtF交流中的常用互动策略,比如澄清要求、理解核查、重铸、接应(Uptake),语言相关片段(Language Related Episode, LRE),也同样适用于L2文本交流文段的研究。此外,FtF交流研究中建立的“词汇协商第一”(Negotiate-over-lexis-first)原则也应用到L2 SCMC的协商研究之中 (Ortega, 2009)。可见,L2 SCMC研究沿用了FtF的研究范式,体现了两种交互模式在互动本质上的相同之处。
尽管两种交流模式的研究范式相同,但在交流性质上,L2文本交流具有其显著特征。其一,与FtF形成鲜明对比的是,SCMC话语具有不连续性(Non-sequential)。这是由网络信息传递的固有特征所决定,即信息按照顺序依次上传系统,无法考虑是针对哪条信息的回应。正是由于这种不连续性,SCMC互动话步通常呈现不连贯现象,即在协商互动模式的四个步骤之间可能会出现多个话轮的延误现象。例如,由此导致的交际失败发生(Trigger)后,可能难以获得及时的指示信号(Indicator);或在信号发出后不能获得即刻响应(Response);或在响应后要过几个话轮才能获得最终反应(Reaction)。其二,文本交流仅仅通过视觉通道来呈现和获得信息,传统的FtF交际中使用的韵律和副语言标记(如重音、切分、音调)则无法应用到文本交流中去。文本交流中的交际故障只能通过显性的语言材料和书写形式(如表情符号、星标、标点、大小写、拟声词)来标记,这也是SCMC区别于FtF的一大特征。这些差异在二语促学方面体现了FtF和SCMC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见表1)。

表1 FtF与SCMC两种交互形式的优、劣势对比
文本交流的L2促学优势似乎得到更多关注。首先,文本交流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际空间,FtF交流中常有的情绪紧张、话语权不均、自信心受损等负面情感因素在文本交流环境中可能会降到最低程度。由于交际者拥有较为均等、公正的话语权,因此学习者使用二语进行交际的机会较多。其次,文本交流使学习者获得更理想的L2训练。这主要是由文本交流的固有性质所决定。与FtF不同,文本交流使学习者拥有相对宽松的、可自主支配的时间,因而会有更多时间考虑输出话语的多样性。此外,通过文本交流产出的话语具有“可视”和“永存性”,这种优势可避免面对面交际时可能出现的“听过即忘”的弊端,学习者效仿、参照对方语言形式的自由度较大,容易产生协同效应,因而更有利于二语学习。相关实证研究表明:(1)与FtF交流相比,外语学习者在文本交流时语言输出更多,且形态句法和话语功能更为复杂(Chun,1994);(2)文本交流中的语言使用要比FtF交流中语言的准确度更高(Salaberry,2000);(3)中国英语学习者由于实际使用英语的机会少、实际操作能力较弱,普遍存在焦虑情绪和自卑心理。文本交流为学习者提供的虚拟交际空间能够增强他们驾驭语言的自信心,克服焦虑,战胜自卑(卢植、刘友桂, 2005)。总之,与FtF相比,SCMC在L2促学方面的相对优势可初步概括为:创造比较轻松愉快的交流环境、提高学习者参与度、增加学习者语言输出量、促进语言学习结果的迁移、促使学习者对语言形式的注意,因此可能会提高语言使用的准确度。
三、文本交流二语促学功能的复杂性
以上简述了文本交流与传统FtF交流的异同。那么文本交流所具有的特征和相对优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L2学习呢?我们将从意义协商、负面反馈、关注形式等方面考察文本交流的二语促学功能,并对其复杂性进行客观剖析。
(一)影响意义协商的多重因素
意义协商指交际双方为弄明白谈话的意思而进行的意义上的商讨。意义协商,尤其是能够触发本族语者或高水平者做出“交互调整”(Interactional Modification)的意义协商可促进L2习得,因为这种交互调整把输入、学习者内在能力(特别是选择性注意)和输出以话语产出的方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Long,1996)。意义协商促学L2的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者获得负面反馈,对话语进行调整,因此可能会产出正确的目的语形式;二是由于需要澄清说过的话语,学习者要进行输入加工,这会帮助其理解和习得新的语言形式。意义协商的明晰度可能是SCMC互动的一大优势,但交互的不连贯性又可能使L2促学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多人在线互动时,由于会话参与人有细读、略读甚至不读信息的自由选择,也可能因为阅览信息的顺序与书写、提交信息的顺序不吻合,导致一方发出的协商或负面反馈得不到对方的回应。
那么,文本交流能带来理想的意义协商吗?部分研究结果表明,SCMC能够为学习者创造良好的意义协商机会(如Smith,2004;Kotter,2003;Tudini,2003),而其他研究结果则相反,即SCMC带来的意义协商很有限(如Blake,2000;Blake, et al,2003;Fernandez-Garcia, et al, 2003;Lai, et al,2006;Jepson,200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多变而复杂的结果呢?我们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分析,发现以下因素会影响意义协商的L2促学效果:
1.任务。针对以上研究呈现两种不同结果的现象,可从任务设计角度给予解释。高协商比率的研究普遍在任务设计上有较严格的控制。通常情况下,含有具体任务的交流同自由聊天相比,更容易催生意义协商。例如,Smith(2004)要求14对ESL学习者通过互动来完成拼图和决策相结合的任务,结果在对其文本交流语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在1455个话轮中,关于词汇的意义协商占到492个,比率为34%。出现如此高频率意义协商的原因与任务设计有关。在Smith的任务设计中,学习者首先需要弄清对方所使用新词的意义才能完成相关任务。Pellettieri(2000)以5项精心设计的SCMC任务考察了5对西班牙语学习者的互动情况,发现在所有话轮中,意义协商比率占到31%。相反,如果没有明确任务要求,尤其在聊天室考察SCMC时,意义协商发生的概率则很小。例如,Jepson(2005)收集了素不相识的L2学习者的交流记录,把文本交流与有声会话语料比较后发现,有声交互中的意义协商相对较多,而文本交流中的意义协商只出现在6个片段的交际语料中,远远少于有声互动中的36个意义协商片段。一般来说,任务越明确,会话参与者越要付出努力去弄清对方话语的意图,意义协商就会相对频繁。
2.协商策略。一些协商策略可能比其他策略更容易被采用。在Kotter(2003)的研究中,来自两个不同地域(德国和美国)的被试被编成8个小组(3~4个被试为一组),通过MOO平台互动来完成自主选择项目。在信息量大、语句复杂的含有184,000单词的庞大文本交流语料中,Kotter发现1,549个含有澄清要求(Clarification Request)的话轮,占到所有话轮的12%。 这可能是因为交际者认为澄清要求比其他协商策略更便于交流的进行,比较适合文本交流方式,而理解检查(Comprehension Check)则常用于口头交际。
3.交流类型。意义协商的有与无、多与少,似乎同交流的种类不无关系。与FtF相比,SCMC交流中意义协商似乎不占优势地位。例如,在Fernandez-Garcia等(2003)的实验中,参与FtF互动的L1-L2配对交际者在理解对方话语方面经历了更多困难,出现较多意义协商,而在同样话题的SCMC交际环境中,意义协商则很少。此外,在18个配对SCMC交际模式中,原始数据显示协商频率很低,平均每对交际者在每项任务中的意义协商还不到1次,相当于FtF互动的一半。在Lai等(2006)的研究中,被试在完成寻找差异任务中,SCMC互动中意义协商的出现频率明显低于FtF中意义协商的频率。其他关于SCMC互动形式的质性描述和分析研究也显示很低的意义协商频率(如Fernandez-Garcia, et al,2002;Kitade,2000)。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FtF交流的真实语境更易使会话参与者开展意义协商。
4.互动交流的真切程度。观察一下更多实证研究的结果,不难发现:意义协商在整个L2文本互动中出现的几率很小,而且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不论在二语还是外语环境,在课内还是课外,以配对形式,还是在小组甚至整个班级内开展互动,不管是否将其结果与FtF互动形式进行直接比较,都无法避免意义协商缺失的现象(Ortega,2009)。例如,Blake (2000)考察了基于拼图任务的25个中级水平的西班牙语学习者SCMC交流情况,结果发现,含有意义协商的话轮只占到全部929个话轮的3.8%。Blake等(2003)采用同样的拼图任务对11对族裔西班牙语者(Heritage Spanish Speakers)与中级水平的西班牙语学习者的文本交流进行观察,发现在一个小时的交流中每个小组只有平均2.7个意义协商的话步。这种现象可能与L2 SCMC交互的特点有关。由于文本交流是无声的、书面的、借助网络平台进行的远距离交互,互动环境的真切度远不及面对面的有声交流,加之会话者采用键盘或指尖输入文字的方式进行对话,主要精力用在文字的输入和意义的表达上,意义协商自然较少。
(二)负面反馈
负面反馈在教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L2促学作用也得到了充分肯定。许多学者(如Long,1996; Gass,1988;Schmidt,1990)认为负面语言证据(Negative Evidence)能促进语言学习,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样的课堂教学,有纠正性反馈比没有纠正性反馈会使学生的表现更佳(Lyster, et al,2013)。负面反馈的另一个作用是它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Swain,1995)。
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反馈发生的频次可能受到交际类型和交流环境的影响。例如,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中,L2学习者与NSs进行面对面会话,有1/3到1/2的不合语法话语可能得到某种形式的负面反馈(Mackey, et al,2003)。然而,在L2 SCMC交互环境中,负面反馈受到的关注远远低于意义协商(Ortega,2009),而且不同研究结果显示的负面反馈也存在高度的不一致性,总体上少于FtF交流环境中所发生的负面反馈。
运用L2进行文本交流,部分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反馈的发生频次较低,尤其是在公共聊天室中,负面反馈的频率更低。Kotter(2003)在含有184,000词汇的文本交流语料中,发现只有29个重铸反馈,其中只有一个重铸是由较高水平者做出的;Jepson(2005)的公共聊天室的有声和文本数据几乎没有显示负面反馈;Fiori(2005)对两个西班牙班级进行了一个学期的观察,发现在SCMC交流中,教师启动的负面反馈较少,两个班级获得的负面反馈分别是23次和15次,而且多数反馈以重铸的形式出现。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也有研究显示了高频率负面反馈的结果。例如Sotillo(2005)考察了5位(2个NSs和3个NNSs)TESOL受训教师分别与5位ESL志愿者的多模态互动。这5个小组在9周内完成了5项交际任务。结果发现每小时就有6次纠错反馈,其中NNSs受训者话语中语误纠正比率高达41%。在另一项研究中,Lai等(2008)对含有290个重铸反馈的语料进行分析,发现这些重铸反馈是一名研究者向17个ESL学习者做出的,平均每位参与者得到17次重铸反馈。
为何负面反馈在不同研究中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分析表明,上述两项研究出现高频率的负面反馈,与研究设计有关:Sotillo(2005)的研究是在特殊的教师培训环境中展开,受训教师扮演了明显的教学指导角色,出现较多负面反馈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而在Lai等人的研究设计中,研究者参与了实验,而且根据要求,尽量向被试提供反馈,以便顺利完成寻找差异的任务。显然,这种特定环境下的高频反馈不能代表L2文本交流互动的一般性特征。
(三)关注形式
学界普遍认为,单靠交际并不能帮助教学环境下的学习者获得理想的准确使用语言的能力(Loewen,2015:57)。关注形式(Focus on Form,FoF)的目的是在交际的大环境下把学习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语言形式上来。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FoF是在基于内容的或以意义为导向的课堂交际环境中展开。自交互法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获得认知转向以来,关注形式就成为研究领域和理论探讨的中心议题,尤其是注意(Noticing)和意识(Consciousness)的实证研究。这方面的成果颇丰,影响力最大的当推Schmidt(1990)的“注意假说”。该假说认为L2习得不会在无意识中发生,必须在意识到语言形式的情况下发生。此外还有Robinson(1995)的“注意和记忆模式”。根据此模式,只有短时记忆中的察觉和练习才能导致长时记忆的编码。二语习得领域研究注意的一种方法是从“接应”(Uptake)角度开展的研究,即会话一方听到反馈后是否能引起注意并作出话语调整,这被看作是注意发生的指标(Lyster, et al, 1997)。另一种测量注意的方法是收集内省数据(Collecting Introspective Data)。L2 SCMC的研究也是采用这两种方法来探讨关注形式的作用。文本交流由于具有加工时间充裕、文本可视性和永存性等特点,故学习者对语言形式可能会引起更多关注。
1. 文本交流中注意的研究。二语文本交流中有关注意的研究起步于近10年,Lai等(2006)比较了SCMC与FtF两种交互模式下6对ESL学习者对协商和重铸反馈的注意量,发现在10个注意到协商的参与者中,其中6个在SCMC环境下的注意量大于FtF,体现了SCMC的微弱优势。Lai等(2008)采用刺激回忆和有声思维的方式收集了17个ESL学习者数据,发现高达46%的重铸反馈被注意到。他们同时也考察了重铸反馈的随机性是否会影响注意,以及工作记忆是否会调节此效果。结果发现,随即重铸(Contingent recast)要比非随即重铸(Non-contingent)更易被注意到;工作记忆和注意有很大的关系,参与者的工作记忆越强,越能注意到非随即重铸反馈。其它几项研究也从接应的角度探讨注意。例如,Smith(2005)考察了来自12个ESL配对小组的数据,发现较高的接应率,即42.4%的词汇被成功吸收和确认;未获得接应的只有15.2%。研究同时表明,延迟接应(Delayed Uptake)是文本交流的典型特征。Sotillo(2005)和Tudini(2003)的研究也获得较高比率的接应。然而,与FtF相比,SCMC中的接应率仍相对较小。例如Loewen等(2006)的研究表明,在89个重铸反馈中,接应只有8次,即9%的接应率。总体来讲,反馈能否获得接应,还需更多、更系统的研究。从现有研究来看,文本交流环境下的反馈获得接应的比率呈现出高度不一致现象。
2. 文本交流中的监控研究。监控(Monitoring)与注意都是认知心理加工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关注形式就是通过这些步骤来实现的。在互动过程中,自我纠错(Self-correction)被认为是监控的指示器(Kormos,2000)。根据Krashen的“监控模式”(Monitor Model),只有学得的规则才用作监控,其功能是对习得系统产出的话语进行编辑和修正。L2 SCMC研究领域基本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实时在线互动可能会促进学习者的自我纠错能力,但现有实证证据只局限在粗略的观察之上。例如Pellettieri(2000)通过对学生使用退格键(Backspace Key)的观察发现,自我话语修补意味着学习者在进行着大量的自我监控工作,同时他们通过使用退格键来修改和丰富句法结构,进而提高句法的复杂度。Lee(2002)在96个学习者的文本交流片段中,发现涉及性、数一致问题的55例自我纠错。Lai等(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完成同一任务的情况下,文本交流的参与者比面对面交流的参与者更能频繁地进行自我纠错。目前这种通过键盘退格键的观察研究还比较少。随着键盘记录软件的使用,自我纠错的过程就可在使用退格键时被记录下来,这将会对未来研究带来便利。
四、文本交流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趋势
以上我们梳理了文本交流在二语促学方面的研究状况。自从SCMC出现在教学领域以来,研究者对其充满兴趣,它的实时性和便利性令许多研究者对其在二语学习中的应用前景持乐观态度(Warschauer, 1996)。这些研究显然对二语教学会产生有益的启示,比如明确SCMC中的任务目标可能会使学习者更好地开展意义协商。然而实证研究表明,SCMC的L2促学作用似乎没有先前声称的那么乐观,而且情况要复杂得多,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1)SCMC相对于FtF所具有的特征对L2学习会带来何种影响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仍需系统的、历时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在能否创造交互修正机会的问题上,SCMC相对于FtF的优势并不明显,至少在数量上如此。SCMC中有关负面反馈、关注形式、注意、监控的研究还需继续进行,现有研究所提供的关注形式促学的证据远远不够。2)研究的效度有待提升。许多L2 SCMC研究在实验设计方面严密程度不够,样本较小,持续时间较短(王洁卿, 2012)。历时研究相对较少。学习者在进行SCMC交流的同时还参加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故把学习成果仅归因于文本交流的结果与事实不符(Chapelle,2007)。3)有些SCMC研究设计不够科学、严谨,导致研究结果带有明显的主观导向性。例如,在教师培训班中开展的负面反馈调查,得到的结论就不具普遍性。同样,要求教师尽量给被试提供负面反馈的实验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4)文本交流提供的书面语言交际渠道单一,导致口语产出和听觉理解信息的缺失,故凭借有限的视觉渠道获得的信息,得出的结论难以客观描述L2能力的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对未来的研究趋势做如下思考:
1.认知心理层面的研究还需要深入和加强。交际过程中如何把注意力转移到语言形式上始终是互动研究的焦点。SCMC环境下的“注意”研究有待深化。交互中对方是否“接应”被认为是注意发生的重要标志,具有促进二语学习的作用。句法启动(Syntactic Priming)作为“接应”的一种替换方式(Ferreira, et al,2006)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因为句法启动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模仿,而是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过程,因而在SCMC环境下仍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此外,工作记忆是“注意”的一个重要调节器,也是SCMC未来研究中的需要考量的因素。语法和词汇的习得依然是SCMC关注的重点。FtF互动中的“词汇协商优先”原则在SCMC模式中会有何种表现也值得继续关注。在关注形式的外部任务要求下,学习者可把富余的认知资源投放在语法形式上,SCMC所特有的文本可视性、永存性、加工时间充裕特征都可能使词汇、语法学习更具优势,其学习效果如何,以及词汇和语法学习效果有何差异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2.拓展研究领域,采用多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如前所示,文本交流环境下的L2学习过程和结果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答案需要到影响文本交流的各种语境变量因素中寻找。这些语境变量(比如交际者类型、任务类型、教师的经历、交际参与者人数及性别、教师的参与与缺席等)都可能会对交互修正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例如,不同任务可能导致不同数量的意义协商;跟同一交际对象开展长期交流可能会提升互动质量,进而增加在线交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从单一的认知心理视角对L2 SCMC互动模式进行研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要求,需要把研究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层面,关注社会的、文化的、人际的、历史的交际语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认知的、心理的层面。互动的研究也可采用跨学科方法。由于SCMC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交际活动,从新的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并对L2学习带来新的启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文化理论、动态系统理论、语言社会化理论、语言身份以及会话分析等都可能成为未来文本交流研究的新视角。
3.深入开展跨模态语言能力迁移的研究。L2 SCMC交流是单一的书面文本交流模式。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SCMC与FtF对比研究开展的同时,SCMC与L2口语产出之间的跨模态(Cross-modality)语言能力迁移研究也相继展开,而且有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记忆能力较弱的学习者能把滚动屏幕信息应用到自己的口语产出中(Payne, et al, 2005)。这种现象被称为SCMC的“自启效果”(Bootstrapping Effect)。正是由于SCMC提供了一个降低L2认知需求的机会,口语能力才得以迁移,同时提高了学习者产出语言的复杂度。网络技术的发展,文本、声音、图像、录影等多种模式的应用,为跨模态研究提供了可能,为不同种类学习风格、认知特征、交际方式提供了技术支持。今后的研究仍有待扩展,将跨模态迁移的研究延伸到语法能力、语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文本交流的二语促学机制,梳理了相关研究成果,从意义协商、负面反馈、关注形式等维度探讨了文本交流对二语学习的作用。与面对面人际互动相比,文本交流虽然具有加工时间充裕、信息可视永存等优势,但其二语促学作用仍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部分现有研究在任务设计、效度、被试选择、研究视角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上的不足和瑕疵,导致我们对文本交流的二语促学功能的认识不够准确和全面。对此问题,我们认为未来研究需要深化文本交流的认知心理机制研究,同时也需要拓宽研究领域,采用多学科视角探讨网络文本交流的二语促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