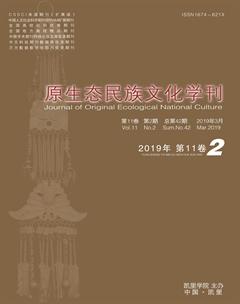主持人语:地方立法的民间法维度
谢晖
地方立法在我国的推进,尽管遭致学界不同的评论,如有的学者因为地方立法存在的种种乱象,强调“地方立法可以休矣”(周永坤);有些学者担心地方立法的急速扩容,会给人以“冒进之感”(秦前红),但如今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截至2018年,全国拥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已达354家(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9个较大的市,240个设区的市,30个自治州和4个未设区的地级市)。因此,即使以上学者颇有见地的反思及所担忧的情形照旧,但要阻止、收回、甚至减缓地方立法的事实和进程,怕绝非易事——更何况赋予地方以立法权,对于多少稀释自秦皇以来的中央专制集权、释放地方积极性,把地方有机地结构在、而不是强制地控绑在国家体系中,明显是种有益举措。
可见,与其继续检讨扩大地方立法的种种不是(尽管这很重要),不如认真寻求健全并完善地方立法之道。那么,健全并完善地方立法之道从何入手?自然,由于地方立法之层次、对象、效力范围、地方需要及与地方发展的适应程度等的多样性,兼之地方立法人才、经验、技术等的明显欠缺和不足,学者们在此问题的研究中得出人云亦云、不一而足的结论理所当然,但无论如何,地方立法对其所处之地既有规范的关注——无论赖此而移风易俗,还是借之而因革传承,都是必须直面的话题。之前,我曾在本专栏的主持人手记中发表过《地方立法的日常生活取向》一文,本文所阐述的,可谓是接着前文讲——如果前文侧重于日常生活的文化视角,那么本文则侧重于日常交往的规范视角。
所有的地方,只要它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只要在该地方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特定的人群生活其上,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规范缺席的。哪怕一个地方生活的主体不过是新近才“类聚”而成的,但只要聚集在一起的人们能够平和地生活、生产和交往在一起,则必定会有相应的规则相伴随——无论该规则的表现形式是成文的、话语的还是行为的。立法者理应在从事立法时,对这些规范予以关照,尤其对地方立法而言,更是如此。这种关照,既是地方立法者的重要任务,也是其立法的“事实程序”。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能谓之立法者的敷衍塞责或狂妄自大——它不是为一方的民众而立法,而是为满足立法者自身的偏好而立法。这样的法律,即便有严谨的逻辑、系统的法條、精确的语言,也不能获得一方民众在观念和行为上的自觉响应与支持,反而赖此导致“法律越多,秩序越坏”的局面,并不罕见,甚至法律不但不是新社会秩序的构造者,反而是既有社会秩序的解构者。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所以赋予地方以立法权,端在于地方事务、或者地方规定性的千差万别。对这种千差万别的地情,科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规则,看似能够整齐划一,实现那种“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的大一统效果,但其代价是地方主体性的丧失。近代以来,主体性理论大行其道,成为结构近、现代社会交往的逻辑前提。但主体性理论不仅及于个体主体,而且理应及于诸如地方、族群等这样的主体之上。尤其在区域差异明显、族群特征分明的国度,立法只有保有对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个体”主体性,才能实现在这种主体性之上的国家认同、同构和团结。地方立法的重要作用,除了在细节之处贯彻国家统一法律之外,还在于从地方“情节之处”体现其地方特色。即便地方在细节之处贯彻国家统一法律的举措,也要借助地方之“情节”,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都需要地方立法关注既有的地方规范,关注民间法在地方立法中应有的作用。纵使一定的民间法之于地方立法并无价值,也只有认真地查找并梳理之,才能有效地剔除之,以便更新的地方立法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民间法之于地方立法,不但不是什么障碍因素——无论吸收、认可民间法作为地方立法的内容,还是排除、否定民间法在特定地方法规中的作用,民间法都不是一种障碍,反之,只有通透地了解、把握、认知民间法,才能更好地或吸收之,或排除之。可见,民间法是地方立法不可或缺的因素,它构成地方立法的民间法之维。本期刊出的2篇论文分别是徐晓光、徐斌的《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碑刻习惯法研究》,周忠华、黄芳的《土家族现代习惯法伦理观念调查研究》。2篇论文虽皆未涉及民间法与地方立法之间的关系,但透过这些文章所提供的规范资料、所描述的规范内容以及所指的规范价值,都能帮助读者更好理解本文所提出的话题。
[责任编辑:吴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