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版《林语堂传》:“他是一个自由人”
毛翊君
中国现代作家里,林语堂是活跃于文坛大半个世纪的一位。因为最早用中文译出“幽默”一词,他在上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至今,更多被大众所知的是一部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小说《京华烟云》。而在学术领域,对他的研究始终沉寂。
很长的时间里,林语堂陷于争议,其中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对幽默文学的褒贬不一。抗战期间林语堂远在海外,两次回国逗留时间都有限,被质疑为脱离中国实际、不食人间烟火。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用20年的研究,在新作《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中论述,林语堂是足以探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问题的“棋子”。比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在批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冷静修正彻底反传统的激烈论调,并成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输出国门。
钱锁桥认为,林语堂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批评家,以及发明中文打字机的科学家,“鲁迅和胡适其实并不能和林语堂并称,鲁迅和胡适都是20世纪中国的,林语堂不仅是20世纪的,还属于我们21世纪,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钱锁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揭开被遮蔽的
1985年的深圳被粤语充斥,跳迪斯科的人留着长发,年轻人谈诗和哲学,摆脱被灌输在脑子里的东西,心比天高。22岁的常州人钱锁桥刚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到深圳大学外语系做外事秘书,周围聚在一起的有很多诗人,大家聊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感觉这样的话题是前卫的。
偶然在书店随意翻书时,钱锁桥看到一个汉译本《中国人》,原著《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作者叫林语堂,是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可他从没听说过。“80年代实际上还是延续五四的话语。”他感觉,书中对中国、中国人的话语完全是一套新的说法,好像对中国文化有所批评和反思,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消化。
问题被暂时搁置,直到后来,因为机缘巧合进入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就读,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对比的研究,才慢慢理解这些。
追求新知识的80年代,译书是头等大事。一次,一位美国外教借了他一本《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他像发现了新世界。随后,他把书译成中文,译稿拿去台湾出版后,他给原著作者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罗·拉比诺写信,说译书之后受益匪浅,想去拜师读博士,可自己是个学士,而且一分钱没有。1990年,钱锁桥如愿以偿,被推荐到了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系。
理论课程里,钱锁桥选择现代中国文学做主要研究方向,受福柯从当代角度抨击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他转而关注中国的现代文化。起初,林语堂在政治方面的内容是他业余的兴趣,在图书馆找出来随意翻读。
做亚美研究专业助教赚生活费的时候,钱锁桥又在本科一年级英语教材里发现林语堂。这里面有两种声音,既把林语堂称作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先驱,又对其“不以美国为归依”的“政治不正确”猛烈攻击。
这激起钱锁桥对林语堂一探究竟的兴致。从图书馆的“亚洲研究”和“美国研究”两个分类里都能找林语堂的作品,通读后,钱锁桥终于意识到,林语堂在中国国内一直是被遮蔽的,他想去揭開。
“看中国现代的历史,有知识分子各种言论,林语堂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1994年上半年,钱锁桥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定下林语堂的研究方向。借着短期担任南师大外语系客座副教授的机会,钱锁桥回国搜集资料。
这时的国内,对于林语堂,开始有了些许理性的研究。最初,是在个别高校中文专业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研究鲁迅的学者延伸出对林语堂的研究。林语堂的一些作品重新被翻译、出版,“幽默文学”从战争年代的“堕落文学”慢慢开始被正视。钱锁桥收集了所能找到的文章,内容并不算多。
1961年,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关于林语堂的内容只有一页。1983年,时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施建伟发表对幽默文学的看法,肯定之余,也批评过誉了“幽默”文学价值。钱锁桥又在家乡常州一家新华书店里,找见一本《林语堂在海外》,赶紧买回家拜读,结果发现基本是照抄了林语堂女儿林太乙所写的《林语堂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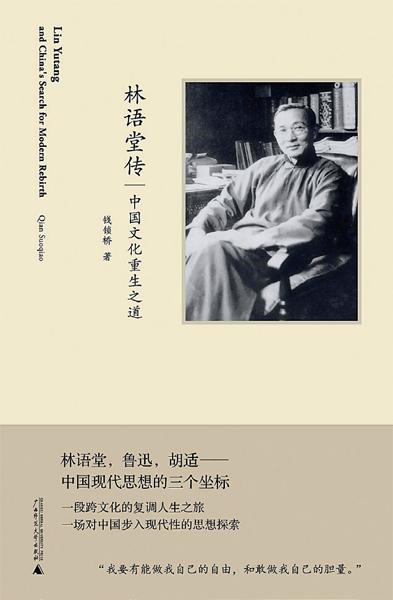
钱锁桥版《林语堂传》封面。(资料图)
钱锁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资料都是在意识形态下对林语堂的界定,而没有写出真实的林语堂。
美国语境
论文最后写得不算满意,钱锁桥觉得“只是从文本到文本”。关于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资料表明,在1925年底,林语堂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游行,也向警察扔了石头。他发表批判北洋政府的言论,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后,被政府列入第二批黑名单,而同在黑名单上的《京报》主编邵飘萍已被枪杀。国民革命后,林语堂不再热衷革命,投入对“幽默”文学理论的研究,但也因此被批判为与民族危难的主流战争意识不相符。
而在美国能找到的内容,更多只是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文本诞生的原因和背景他不得而知。“美国对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研究,有几本书,只是讲美国人怎么看中国,比较泛。”钱锁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激起钱锁桥对林语堂一探究竟的兴致。从图书馆的“亚洲研究”和“美国研究”两个分类里都能找林语堂的作品,通读后,钱锁桥终于意识到,林语堂在中国国内一直是被遮蔽的,他想去揭开。
写完博士论文,钱锁桥到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员,接着研究华裔美国文学课题,算是从林语堂研究项目中延伸出来的。曾经结识的哈佛教授维尔纳·所勒斯和其门下弟子尹晓煌对他的研究颇为支持。一次,尹晓煌告诉他,普林斯顿大学有一批庄台公司的档案,还没人去看过,或许有用。庄台公司是由哈佛毕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华尔希创立的出版公司,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等多部作品由其出版。华尔希和他的妻子、著名作家赛珍珠也是林语堂的重要朋友。钱锁桥随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天天开车从曼哈顿到普林斯顿,查出他认为是最富增量的资料——流水账一样的文件里有诸多林语堂和华尔希、赛珍珠的往来信件,他一盒一盒地整理出来。
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赛珍珠曾凭借创作小说《大地》,先后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小说描写中国农民勤俭持家的生活,1931年通过庄台公司在美国出版后,美国读者反响激烈,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遭到批判,林语堂则在自己的《论语》杂志上表示对赛珍珠的盛赞。之后,林语堂被朋友引荐与赛珍珠见面,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赛珍珠立马写信把林语堂推荐给了庄台公司。
华尔希察觉到中国题材在美国有很好的出版市场,出版《大地》之后,准备策划推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是本讲中国文化和生活精髓的散文集。华尔希和赛珍珠通过写信跟林语堂沟通编辑意见。起初,关于原稿第二章的内容——痛批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乱象,林语堂对是否删去曾长时间犹豫不决,而华尔希非常喜欢,建议保留。在1934年7月到9月的信件里,林语堂先表示,“这一章,可都是赤裸裸的苦口,而且我也不想裹糖衣。”之后,他几度考虑到政局不稳的原因,决定不发表,担心被指责“不爱自己的国家”,并提及自己的好友也劝说不要发表。1935年3月15日,林语堂最终还是决定保留,意在“稍微删改”挪作“结语”。
武汉的新文化阵地《国民新报》的严厉批评随之而来,指责林语堂“卖国卖民”。林语堂在给华尔希的信中提到自己对此的感受,“我早就料到这种东西,自卑感强盛的中国‘爱国者专利。”但林语堂还是怕将这部作品译成中文,他告诉华尔希,“你能想象我用中文把书中写的都说出来?那我还不被那般中学毕业的‘普罗作家给碎尸万段了?”
“因为信件不可能说假话,你就看到了他的整个生活方式、脾性,很多东西都是反映出来的。”钱锁桥感到一下子开阔了眼界。但那个时候,钱锁桥还没想到要为林语堂写一本传记。
1999年,他去了趟台北,到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走了一次,发现没人管理,资料散乱。2000年后,钱锁桥到香港城市大学执教,碰上时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来访问,钱锁桥讲了自己的研究,龙应台邀请他到林语堂故居做驻馆作家。
2004年,钱锁桥在阳明山上待了一两个月,把馆里的资料整理了一遍,挖掘出一些有用的内容。“林语堂在美国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后,他就会付钱给一家公司,那个公司专门剪辑所有报刊上相关的评论给他,馆里就有这么一叠资料,能看出美国媒体当时是怎么看林语堂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后,他遇上台湾民间做林语堂研究的秦贤次,对方分享了自己手头的资源。
直到2009年,他回美国做访问学者,终于完成了首部专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于2011年出版。
自由的延续
首部专著完成前,钱锁桥开始想到要写一部林语堂的传记,“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之前二十年所收获的资料都成为积累。
作家东东枪在读过钱锁桥的《林语堂传》后感慨,“一生爱慕自由、追寻自由、捍卫自由的作家林语堂其实从未曾自由。”而钱锁桥觉得,林语堂有财务自由,也有学术言论自由,还能实践跨行搞发明创作,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要说林语堂比较可惜的地方,钱锁桥认为是其后期在美国应该写出更好的作品,“不该写那些为市场而写的小说,但他要维持生计,是情有可原的。”林语堂投入十多万美元成本制造“明快打字机”,最后因无人投产而欠下大笔债务,甚至变卖了公寓。“他是一个自由人、自由作家,那就得先挣钱养活自己,这是基本的,而不是靠官方养活。”钱锁桥说。
对于自由,林语堂始终认为,在中国的传统里有这一部分。他会举出晚明袁宏道、李贽做例子,再追溯,还有苏东坡。而林语堂在1947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不少评论指出,将苏东坡塑造得太过完美。钱锁桥在写林语堂传记的过程中,理解林语堂的角度,“苏东坡对他来讲,是中国文化产生出来的一个最好的模板。而且这个模板,就是他写出来的这样的苏东坡。在他看来,苏东坡的精神是现代的、永存的,是在他身上得到的,就等于是延续的。这个就是自由精神。”
钱锁桥向《中国新闻周刊》谈及,林语堂创立的《论语》杂志社的一位助手后来回忆,说起林语堂在40年代回国时到重庆,整天谈的是国际外交,根本不理解身处抗战的重庆的文人是怎么样的生活状况。而钱锁桥看来,“40年代,好多左翼包括巴金都写得凄惨兮兮的,但是林语堂不是。可以说他的视野不在这,他关注的是国际外交,这个是决定战争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他是在前沿。”
1940年2月,林语堂决定回国时,做过长久留下的打算。他在给华尔希的信件里讲,要“作为一个普通个人回国,在后方从事建设工作,仍然保持一个作家的自由……”他想过“在《大公报》开一个英文专栏”“用英文写个系列,叫做‘来自重庆的幽默”。他也做了心理准备,“我想战时肯定管制更严,但我可以接受,一切为了战争。不管怎样,我也会用中文写作了……”
只是,林语堂一家在“重庆大轰炸”时到达那里。之后,林语堂重新思考自己在战时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并就这个问题去信給宋美龄。三个月后,出于被动和主动的原因,他接受了“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的虚职头衔,回到美国。
由于三十年身处海外,没有直接处于中国的环境中,晚年归国又是定居台湾,林语堂的爱国情怀屡遭质疑。但钱锁桥认为,林语堂永远都是一个亲历者,“可以说,他在国内本身就是隔空观察的。”出生于基督教背景的家庭,继而在圣约翰大学受教育,经历一个完整的西化成长环境之后,林语堂在毕业来到清华教书时意识到对传统文化的弥补和钻研——“所以他永远是在两边世界当中。他是既生活在里面,同时又有一定的距离。这实际上是非常独特的视角,中国现代性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视野。”
“叙述者永远都是要选择的。”就像林语堂写《苏东坡传》的时候其实在写自己,钱锁桥对用诸多素材呈现出的林语堂,也进行了自己的选择,“把自己的意识和东西放进去,也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