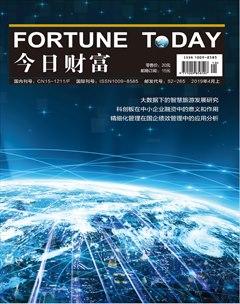成都周边地区土地规模化经营中的农民地权保护调查
吉媛 杨静
我国农民地权易受侵害长期惹人关注,土地权利模糊被公认为罪魁祸首。农地权利“物权化”则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然而成都实验表明,确权颁证后,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然有受到侵害的可能,农地权利主体的自由意志仍然会让位于政府推动的土地规模集中的政策意图。因此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能是造成农民地权被侵害的主要诱因。
一、 问题的提出
2003年,成都市正式决定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自此,成都市开始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试验(以下简称成都实验)。虽然成都市的实验是从统筹城乡的整体视角出发的,但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必然是农村土地制度,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成为其他改革推进的抓手或前提。正如有学者评论那样“成都实验走出了一条既能满足城市化用地需要又能相对有效防止征地冲突的农村土地产权市场化创新之路,其基本思路就是‘管住规划,放开产权”。成都实验之所以要“管住规划”,是为了防止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确保土地用途管制不被破坏。而“放开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地产权制度,为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以及农村房屋产权流转创造前提条件。2013年成都基本完成了确权颁证的工作,农村土地也的流转也开始加速。那么,这一过程中农民地权保护如何呢?本文的研究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土地流转中的“行政”色彩是农民地权的潜在威胁
在成都实验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作为实现农业规模适度集中的重要手段,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成都实验中是通过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手段纳入了市、县、乡政府以致村组考核体系的。以2007年为例,成都市当年确定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60万亩的目标,共涉及226个乡镇,并将目标任务全部分解落实到村组,由专人负责,并实行目标考核。不难看出,成都市农地流转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根据张洪松(2010)的调查,虽然近年来成都市的农用地流转面积持续增长,但仅有56.64%的農户倾向于流转其土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成都市的土地流转需要政府在背后推动,因为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进行土地流转的化是不可能达成政府土地流转目标计划的。由此成都实验中的土地流转并非市场自发形成,即便农地流转可以为传统农业带来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以及规模效益等要素的注入,但其收益仍然不足以激活市场的自发需求。这也反映出了成都试验中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因主要还是政府的强力推进。这就必然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更多的服从于政府的需要,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意志则必然处于次要的位阶。
三、从农地流转的纠纷数据看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按照政策的逻辑,成都的土地流转是建立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之上的。而确权颁证实际上是《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地产权纳入物权范畴的一个自然延伸。而《物权法》之所以要将农地产权纳入物权的保护范畴,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对抗其他势力对农村土地权利的侵害,其中政府一直被认为是侵害农民土地权利的主要势力之一。而成都实验的逻辑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即政府通过确权颁证确立农民的土地权利之后,又通过行政手段大力推进了土地的流转,虽然政府推行土地流转的目标取向之一是为了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仅就这一点上来看,是可能获得多数农民支持的。但在如此大的土地流转规模之下,农民因土地流转而发生的纠纷并未明显增加。根据张洪松(2010)的调查,在其调查的总样本中坚决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农户只有4.59%。而自2005年以来,成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7%,仅2006年度和2007年度,成都市土地流转面积净增数就达到了38.4万亩和81.87万亩。而如果按照我国农村户均10亩地的水平来匡算,2006年度和2007年度成都市土地流转净增面积涉及农户约为3.8万户和8.2万户。涉及规模如此庞大农户的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土地流转类纠纷在两年间仅出现了7例,低于土地承包类纠纷和征地补偿类纠纷。这从侧面反映出,即使确权颁证后,政府行政手段加上村社自身的传统权威体系仍然可以有效的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成都实验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的增加本质上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利益的输送。虽然这种利益输送对统筹城乡发展以及提高农民收入而言具有无可争辩的积极意义,但距离农民土地权利的完全保护仍有距离。因为,虽然政府主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目的与农民利益的取向基本吻合,但如果一项涉及农民劳动力再生产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政策能符合99.9%的受众的支持,显然不太符合常理。而本文基于张洪松(2010)的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匡算,在两年、涉及近12万户农村居民的土地流转中所产生的土地流转类纠纷仅为十二万分之七。显然,对成都试验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呈现出的这种整齐划一的结果有必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四、结论
成都市“确权颁证”、“还权赋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尴尬之处在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破除农地产权模糊弊端进而解放农民因地权保护不足而无法释放的土地流转需求,但在“确权颁证”改革后,仍然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动土地的流转,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农民的土地权利产生了冲突。可见,土地权利清晰与否并非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成都实验表明,农民土地权利“物权化”并非是保护农民权利的灵丹妙药也非必要。(作者单位:1.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2.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
本文系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校级一般调研课题《成都周边地区土地规模化经营中的农民地权保护调查》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SCJD2018DY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