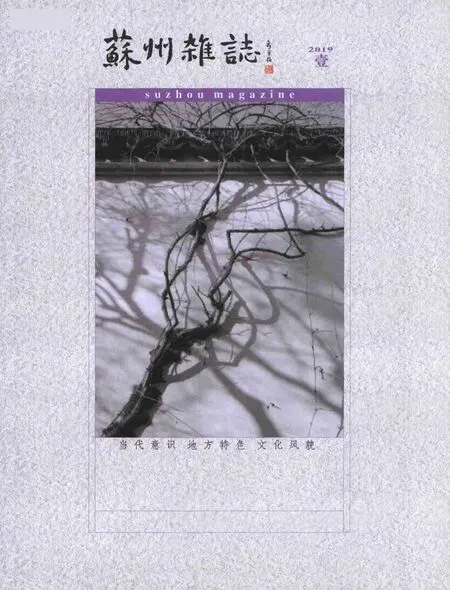一个人的出走
奔跑

顾炎武故居
一
“近腊月下,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者,携手赋诗……”
1682年腊月二十八,山西曲沃县韩村的一座安静的宅院里,墨已经磨好。70岁的顾炎武先生来到案前,沉吟片刻,挥毫书写了一幅流传至今的立轴,内容是唐代诗人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的一段。
句子戛然而止,情景历历在目,带着淡淡的感伤。老先生抄写王维的文字,是在怀念哪位朋友呢?
没有预兆,十天后,正月初八,顾老先生前往参加朋友聚会,上马时失足,摔倒在地,一时旧病并发,不幸于次日去世。
至此,顾炎武离开昆山千灯镇故里已经整整25年,其间从未回去过。关山万里,留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二
“千灯的人不会太多”,在嘈杂的上海,我收到江南文旅作家应志刚先生这样的回复,我的千灯之旅终于成行。而读到王维的这段话时,我已经下榻在古镇河边的一家民宿里。我的所在,地理上距顾氏老宅不过百步之遥。时间上,距离那个曲沃小除夕却已是300余年了。

王维的这封信约写于唐开元二十年,即公元732年。那时,王维隐居在陕西蓝田的辋川别业。一封闲信,经历一个人的抄写,在一个闲人的追踪下,不觉间完成了一次跨越1300多年的传递。多么奇妙地穿越!
客栈老板、青年雕塑家天佑先生以他上好的红茶招待我。天佑来自上海,像很多艺术家一样,脑后扎着小辫。他与夫人一道,打理着一个主营城市园林雕塑的公司。
现在的生意不好做,他说,如何安顿自己,很困惑。他是否与我一样,年纪尚未老,在努力打拼的间歇却常不自禁地考虑退休后该怎样生活。
天佑的眼光很独到,他认为顾炎武是这里的一张名片。这些年来,江南水镇的开发潮对顾炎武似乎是一个不经意忽略,以至于在这古镇水边连一个像样的旅馆也难以找到,直到天佑的到来。
他的项目得到古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个包括住宿、茶道、工作室和画廊的复合型文化空间已经初具规模。
在江南俊杰中,顾炎武最不应被忽略。尤其是他45岁时离家出走、远游华北的漂泊岁月,颇具特立独行的意义。
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于1613年7月15日诞生于千灯镇,在这里度过优渥的读书生活。他屡试不中,27岁时断然放弃科举,转而遍览群书,辑录研究有关农田、水利、矿产等记载。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被南明朝廷授兵部司务,但尚未赴任,南京即为清兵攻占,遂与好友归庄、吴其沆投笔从戎。吴其沆战死,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右臂,两个弟弟被杀,嗣母王氏绝食殉国。国难当头,家难并起。因家族财产纷争,1657年,顾炎武被迫变卖家产,揖别故乡,掉头向北。
在长达25年的游历生活中,顾炎武游历考察了河南、河北、山东、京师、山西、陕西等地,自称“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而且著述等身,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漂泊江湖的士人多了,但像顾炎武这样的恐怕绝无仅有。人届中老年时期,他一不做官,二不依附权门,三不接受馈赠,而是自食其力,坚持独立的学术活动。即使是现代来看,这都值得惊叹!
三
荣格说,“人是一个事件,它是无法自性判断自己的,而是或好或坏,得由他人来作出这种判断。”
而对顾炎武这个“事件”做点“判断”,很困难,也很有趣。
多年来,他在世人眼里是一个“遗民”、一个处心积虑“反清复明”的“爱国者”,而我首先关注的,则是他在游历中的经商。
一个读书人如何实现财务独立,才是他首先要面对的最大人生挑战。
与我在古镇石板路上想象的不一样,顾炎武没有做贸易。在江南仇家逼迫期间,他“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贩卖过布匹和药材。北游期间,他将家产变卖的部分资金用来放贷,这恐怕是他最便于操作的理财方式了。也因此他进入了农垦领域,并成为他最重要的经营事业。
在山东章丘,顾炎武放贷给田主谢长吉,谢因故无力偿还,顾炎武最终获得了其抵押品,十顷庄田。这里成为顾炎武北游后的第一个垦殖基地。此事大约发生在1665年,顾炎武时年53岁。
此处田产为他带来一笔稳定的收入。由于顾炎武四处出游,他采取了“委托管理”的方式。他曾给受托人的信说到:“……此庄向日租银每年一百六十两,若安排庄头办课之外,尚可宽然有余,此为久策。”
他的农垦与其遗民、学术活动交织在一起。1666年,他与山西学者傅山等二十余人集资,于雁门关北垦殖。他亲自策划,采取了股份制的方式,并从南方聘来能工巧匠,引进水车、水磨等生产工具,教会农民开展水利灌溉。在给弟子潘耒的信中,他说:“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泽中有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这个垦殖项目的经营绩效据说“累之千金”,颇为成功。
1679年迁居陕西华阴后,顾炎武购置了田产。清代学者全祖望记述:“先生置五十亩田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按全氏的解读,顾炎武将章丘、雁门垦殖收入作为其学术、遗民活动的专项基金,将华阴田产收入供日常生活所需。不难看出,此时的顾炎武同时经营了章丘、雁北、华阴3个大小不一的垦殖项目。
这些项目支撑了顾炎武较为庞大的生活与学术开支,包括日常花销、旅行盘费,尤其是投入较大的购书、刻书等等投入。
也可见当时资本借贷是有保障的,土地可以私有和买卖,事业经营似乎也较自由。没有这样的条件,顾炎武将寸步难行,更遑谈万里北游。
四
千灯之行后,我一度为顾炎武的矛盾所困惑:
他十多次拜祭明陵,穷极“刁遗”行状,但他的挚友中不乏清政府官员,他甚至愿意为他们在工作上提供某些指导。
他多次断然拒绝到清廷任职,甚至以死相抗,但并不反对他的外甥徐乾学等近亲参加科考和担任政府要职。
他尊经,倡导回归“六经”,但并不为其章句所累,而是坚持了“六经皆史”的传统,并用以指导自己行走山河、观察历史,在筚路蓝缕中开一代实学风气。
他复古,讴歌尧舜“三代”理想社会,所倡议的社会治理方案夹杂着宗法色彩,但他又石破天惊地重释“周室班禄爵”内涵,认为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平等,他们之所以得到俸禄,是他们因承担服务民众事务而无暇耕种。他承认“人之有私,情固不能免”,主张保护私人财产,鼓励经商,藏富于民。在一个专制政治极度腐朽的时代,他的思想与近代政治学说不谋而合,达到十七世纪中国知识者思想的巅峰。
他有家仇国恨,四处漂泊,反复“图谋”,但他所提方案的实现途径却不是武装斗争,而是进行分权制衡的渐进改革,包括了重新调整君与臣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刑法与教化的关系,尤其在乡村自治和庶民议政方面,给予了浓墨重彩的论述。
他的超越理性一直不被人所真正认知。他对历史的观察和提出的社会主张,远远超越“刁遗”的狭隘视野,而具有三千年的历史纵深。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超出“政府”、“国家”的范畴,上升到了社会、文化的高度。
他的脚踏实地一直难以被人所真正仿效。他依靠事业经营获得经济来源,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格。他常常用两匹骡、两匹马驮着书卷资料旅行,一路实地考察、访问土著和亲历者,对已有的记录进行核对与更正。《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经过这样反复考证而写成的巨著。
也许因为他身处巨变的时代,使他本身色彩斑驳。也许其实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各种矛盾纠葛,他的观察者往往被自己的时代焦虑所蒙蔽。
顾炎武,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就被懂得的灵魂。
五
顾园有一副对联给我印象深刻:莫放春秋佳日过,最是风雨故人来。
古镇一夜无梦,我因此联,次日一早再次游览顾园,对顾炎武与山西曲沃的缘分一度好奇,终究在此联中感悟到个中滋味。
曲沃过潼关,距离华阴约二百余公里。从记载看,顾炎武因讲学与访友,前后五次访问曲沃。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1681年8月至1682年1月9日。
“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踪终马世情疏。”顾炎武一路向北再向西,是他的治学规划所致,实际上无形中也为他的友人踪迹所牵引。
1662年,顾炎武自河北游山西,在太原三晋书院结识著名理学家、曲沃人卫蒿,此后便与曲沃结下不解之缘。顾炎武有《赠卫处士蒿》诗云“与君同岁生,中年历兴亡”,可见两人的相知并非泛泛而言。
定居华阴后,1679年来曲沃访卫蒿,下榻在其主持的绛山书院,后因嫌城内嘈杂,搬到县城南五里的东韩村韩宣的宜园。韩宣,字旬公,进士。在宜园,顾炎武与傅山、卫蒿、李二曲等名士畅谈切磋,撰写了大量研究讲稿,并在此完成其扛鼎之作《日知录》。
1681年2月,顾炎武再次来到曲沃访问老友们,受到新任县令熊僎的热情款待,相处甚欢。熊僎,江西新淦人,进士,勤奋好学,对顾炎武非常敬仰。当年秋八月,顾炎武再次来到曲沃,熊僎相迎到县城西三十里的侯马驿。至曲沃后,顾炎武未料“大病,呕泄几危”,于是在宜园长住下来养病,与老友们的相见倒是更为方便了。
1682年正月初八,先生早起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上马失足坠地,病情恶化,“竟日夜呕泄不止,初九丑时捐馆”。朋友们为他办理了丧事,并护送灵柩归葬昆山。至此,一代大儒终于魂归故里。
再伟岸的灵魂,也似乎只有在柔软的友情中才能真正回归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