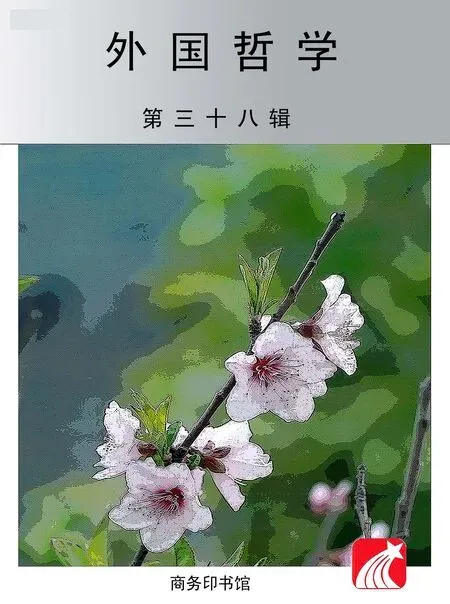论理性事实的感性特征
王一鸣
内容提要:第二批判的论证构成了康德在之后的实践哲学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基础,而这一论证的核心即在于对理性事实的诉诸,但康德关于后者的论述却不免晦涩不明之处。首先,康德将实践法则(道德法则)和对此法则的意识都称为理性事实,但二者显然又有不同,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其次,在理论哲学中,直观构成了先天综合命题的必要条件,而康德却在第二批判中强调先天综合命题不可以建立在任何种类直观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命题应当如何成立?最后,康德又指出理性事实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又应当如何理解?在本文中,笔者将论证感性在实践哲学中以不同于其在理论哲学的方式(非直观对象)充当着一种特殊角色,恰恰通过对这种角色的揭示才可以帮我们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理性的事实①关于factum(本文姑且译为“事实”)的观念史考证已经由Pauline Kleingeld 与Owen Ware 分别以不同类型但却同样有力的方式所完成,二者均指出,factum 至少可以在三种意义上得到理解:(1)与法律有关的行动;(2)由行动所产生的事实;(3)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就已经启用的教学性的法学术语。Kleingeld 结合诸多学者对第二批判中factum 的不同解读做出了评述,最后将事实理解为“理性行动的事实”(P.Kleingeld,“Moral Consciousness and ‘Fact of Reason’”,i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 Critical Guide,edited by Andrews Reath &Jens Timmerman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60-65);Ware 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不过他对观念史的考察更为详尽,他更倾向于将理性的事实理解为“我们关于道德法则思虑的必然性之现实意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解释在一定的意义上更接近 Kleingeld 的说法,只不过是更突出这种事实的必然性。(O.Ware,“Rethinking Kant’s Fact of Reason”,Philosophers Imprint, 14,2014,pp.2-9)本文对factum 的看法在理性方面和二者类似,故姑且将factum 在实践理性活动的结果意义上来理解,所以仍然将之译为“事实”。关于本文的具体观点,详见下文。作为揭示纯粹理性之实践品性的线索提出,又主张后者自身提供的实践法则作为道德法则(CPrR 5:31;164)乃是确系自由的条件(CPrR 5: 34;167)。①本文引用康德著作的方式依然基于学术界惯例,本于《康德全集》的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版,在引用时也依然引用书名的缩写,然后表明所处全集的册数,例如《实践理性批判》处于全集的第五册,并且著明在全集中页数,如“CPJ 5: 241”。另外,本文所采用《实践理性批判》版本本于剑桥英译本(I.Kant,Practical Philosoph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Grego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并也会标注所引的英文版页数,最后则表现为“CPrR 5:30;163”。对其他文本的引用亦使用此格式,但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而言依据学界惯例引用为CPR A**/B**,而不再注明其英译本页数。另外,本文也参照了邓晓芒和李秋零先生相应的中译本。因此,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目标:(1)通过理性的事实说明纯粹理性是实践的。(2)通过实践理性的法则(道德法则)完成对自由的演绎②事实上,正是康德自己主张只有通过“德性[实践理性]首先导致了自由概念”。(CPR 5:30;163)。事实上,由于这种主张还关系到第二批判的论证与《奠基》第三节论述方式,诸多学者对之评价不一。大体而言,以Allison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第二批判从道德法则演绎出自由标志着一种真正的进步(H.E.Allison,Kant’s Theory of Freedo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30);而以Guyer 和Wood 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理性的事实只不过是道德主义者的吆喝(moralistic bluster)和气急败坏跺脚的形式(a form of footstamping),并主张这种论证远不如《奠基》中的论证更为有利。(P.Guyer,“Naturalistic and Transcendental Moment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Inquiry,50,2007.p.462;A.Wood,Kantian Eth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35),也就是通过道德演绎出作为道德必要条件的非道德因素——自由。③实际上,这种自由最好在其“薄”(thin)而不是其“厚”(thick)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因而后一种意义上的自由,按照交互性论题(reciprocal thesis),作为自律的意志自由自我设立的法则就是道德法则。(参见H.E.Allison,op.cit.,pp.201-210)因此,根据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或道德法则所推出的自由,最好要在其薄的、消极上得到理解,一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所指出的:因为我们只知道自由(正如我们通过道德法则才能认识的那样)是我们的一种消极的属性,即不受任何感性的规定依据的强制而去行动。(MM 6:226;380)同样的说法也见于《宗教》(Rel 6:50;69)。又因康德将纯粹实践理性等同于纯粹意志,并将后者等同于自由意志①同样,这里的自由意志最好仍然在积极的自由亦即自主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因为自由在这里被理解为自由的因果性,其客观实在性乃是与在纯粹理性的先天法则中紧密相连。(CPrR5;55;184)。实际上,在另一处著名的文本那里(CPrR 5:29;162),康德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自由与无条件的道德法则乃是交互呼应的。”(CPrR 5:5;141),所以甚至自由(在其积极的意义上)的演绎得以成功也是径直以理性事实为基础的。②尽管Kleingeld 对理性事实、自由、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看似与本文这里所指的自由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也貌离神合。她指出,尽管康德的论证以理性的事实为起点,但必须通过前者“在信仰的基础上”证成自由的假设,方可证成理性基础法则的有效性,并认为由此可以规避从道德推导出自由,又从自由推导出道德的循环(P.Kleingeld,“Moral Consciousness and ‘Fact of Reason’”,pp.58,72)。由此,自由就必须是不同于理性法则的东西,这看上去与在本文于此指出的自由有所抵牾。但由于她也承认交互性论题:对意志的自由与无条件道德法则的交互性关系(Ibid,pp.58-59);且她在这里所指的自由的假设又是一种理性行动者的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更一般的自由(Wille),其也包含了自由消极的一面(这是她在这里更加强调的),所以这与本文的观点并无直接的冲突。至此,理性事实在第二批判乃至在以后康德实践哲学中所处的核心位置也不言而喻。③事实上,无论在《道德形而上学》还是在《宗教》中都可见康德对第二批判观点的接受(本书第237 页注释③)。归根结底,康德的理由仍然在于实践认识而非理论认识之优先性的立场:“我们关于无条件的实践的事情的认识从何开始,是从自由开始,抑或从实践法则开始?它不能从自由开始,因为我们既不能直接意识到自由,盖源自由的最初概念是消极的,也不能从经验中推论出自由概念,只因经验让我们认识到自然的机械作用、自由的对立面。因此,正是我们(一旦我们为自己拟定了意志的准则,立刻就)直接意识到道德法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道德法则就径直导致自由概念。”(CPrR 5: 29-30;163)由此,既然由理性事实所揭示出来的实践立场实际上一直贯注在康德的实践哲学著作中,我们就不能同意O’Neil 与Lukow 将理性事实仅仅打发为解释了实践理性如何在一般人的一般生活中展现出来,而不是第二批判中的主要论证部分。
但康德关于理性事实的论述不一更加令人困惑。在第二批判八段关于理性事实的文本中,贝克已然指出康德关于理性的事实有六种不同的刻画:(1)对道德法则的意识;(2)对意志自由的意识;(3)法则;(4)道德性原则中的自律;(5)单纯的法则概念对于意志之不可避免的规定;(6)以无条件的因果性为前提的某一行为的现实情形。④L.W.Beck,A Commentary to“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4,pp.166-175.即便我们诉诸实践法则与积极自由的交互性论题暂且抛开内容上或此或彼的论述,但形式上主观(对法则或自由的意识)与客观的(法则或自由本身)的区别却仍然存在。①L.W.Beck,A Commentary to“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p.166.但问题是,康德本人似乎对这种区分也没有丝毫的意识,乃至于绝口不言。其原因为何?这是否意味着康德认为这两种区分没有实际的差别?如果是,那么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可以将二者等同起来?还是说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理性事实,只是康德将之无视了?
另一方面,在康德于CPrR5: 31 进一步揭示理性事实的内在本性时,康德也刻画了作为意识的理性事实自身的七个特征:(1)非先行材料;(2)先天的;(3)综合的;(4)非直观(既非感性也非理性);(5)非给予②Ibid.,pp.166-167.;(6)纯粹理性的;(7)唯一的。尽管我们可以把非给予性理解为非先行给定的材料,因而将(1)与(5)等同起来,并且根据非经验性的特征认为(2)是对(6)的刻画。但(3)(4)(5)的同时出现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困惑,一种既非所予又非直观性的东西如何能在同时是综合的?起码在理论哲学的语境,这种东西的可能性似乎不能找到落脚之处。但是,如果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或者可设想性都不存在,那么理性的事实就只能被视为一种大脑的幽灵(phantom),而被加以拒绝。一旦如此,道德以及对人类自由的演绎都一并烟消云散,那么康德的道德哲学论证也就基本瓦解了。
此外,为何康德可以宣称理性事实的唯一性?尽管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康德,认为理性事实之唯一性乃是为了其与多样的经验事实的之不同③P.Kleingeld,“Moral consciousness and ‘fact of reason’”,p.60.。但既然康德在这里强调的关于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追问是否可能还存在其他的理性事实,这就让我们回到了(但不局限于)关于理性事实的主观客观类型之区分。
针对以上的诸多问题,本文首先试图为康德关于理性事实的论述提供辩护,指出贝克指出的所谓主观与客观区分,对于康德并无实质性的差别,毋宁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次,本文将继续指出,康德关于理性事实(3)(4)(5)特征的论述,尽管可能在理论哲学中寻找其定位存在困难,但其却真正开辟了实践哲学的独有领域,而关键在于“感性的”在实践哲学中的独特含义。最后,本文将论述康德关于理性事实唯一性的论述可以依据突出理性事实的感性一面得到更好的理解。
一、法则与作为法则意识的不可分离性
当把法则与对法则之意识理解为主观与客观①这里所指的主观与客观,更多的是指一种意识和与意识相对立的法则,换言之,即便任何人都没有对道德的意识,仍然无损于(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的存在,这种法则类似于一种道德实在论的超验道德事实。(参见L.W.Beck,A Commentary to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p.168)的区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种理论的考虑。当我们做出这种考虑时,我们实际上在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区分判断一个现象。但问题是,这种第三人称理论式的二分是否适用于实践语境?Owen Ware 通过引证文本已经有力地论证康德的实践哲学立场乃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并说明了实践视角在实践领域的优先性。②O.Ware,“Rethinking Kant’s Fact of Reason”,pp.14-17.这都在提示我们要以第一人称的实践视角重新检讨关于理性事实所做出的区分。③阿利森指出,相较于将理性事实径直理解为道德法则,首先将之理解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更可接受的。(参见H.E.Allison,Kant’s Theory of Freedom,p.233)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康德在实践哲学的语境中对讨论主观与客观所预定的实践立场:
实践诸原则是这样一些包含着对意志一般规定的命题,其把诸多实践规则纳入到它之下。当这个条件[对意志的规定]被主体视为仅仅适用于他的意志,他们[实践原则]就是主观的或者准则;当这个条件被认识为客观的,也就是,被视为适用于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他们就是客观的或者实践法则。(CPrR 5: 19;153)
在这里,由于实践原则是对意志一般规定的命题,而意志又被理解成“产生与表象相符合的对象的一种能力”(CPrR 5:15;148),因而是一种行动能力,所以实践原则实际上揭示了某个意志在表现为行动时所遵循的规则。主观的实践准则与客观的实践法则乃是实践原则的主客两面,而主观与客观的差异在于意志规定是否具有普遍性。①值得说明的是,神的意志并不适用于当前的讨论。主观准则与客观法则的区分对于神圣意志并没有意义,神圣意志所履行的准则就是法则,并且也不存在背离法则的可能性。因为道德原则或理性的实践法则对于神圣意志而言完全是分析的。因此,如果具有普遍性,那么实践原则就是实践法则,如果不具备,实践原则就是实践准则。由此主观与客观的差别实际上乃是针对实践原则的适用效力而言,还并不直接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区别。
但康德这种描述只是使我们了解了原则、法则和准则的联系,以及准则和法则的联系,却没有说明实践原则与法则、准则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的可能性。事实上,只有通过这种区分确立实践原则的本性或其内在机制,我们才能明晰康德在第二批判所据以出发的实践立场是怎样的。
既然实践法则与实践准则的差异意味着规定意志方式的不同,而实践原则又是涉指对意志的规定,那么评定实践原则是否具有普遍性实际上是从规定意志的方式,因而从内容方面对其进行评价。因此,当谈论不同于实践法则与准则的实践原则时,我们最好将实践原则理解为实践法则与实践准则的形式。②尽管形式在这里看上去比较空洞,但是如果将对意志基础的规定纳入考虑中,那么这种形式也在向我们提示一种不同于道德行动者的理性行动者的能力,阿利森将之称之为纳入论题(Incorporation thesis)。由于这种实践原则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理性存在者为自己所设立的③在实践知识中——也就是,必须与意志的诸决定性基础打交道的认识——一个人为他自己制定的原则还尚不是他不可避免遵循的诸法则,因为理性在实践中必须与主体打交道,也就是与它的欲求能力打交道,这种欲求能力通过它的特殊构造可以对规则做出多样的调整。(CPrR 5: 20;153-154),加之这种原则本身不具备确定的内容,所以其最好被理解为提示着理性存在者自身规定意志的一般过程④康德有时也将其称之为“拟定准则的过程”(CPrR 5: 30;163)。,虽然在第二批判一直隐而不发,但这实际上已经是康德在《宗教》中昭然指出的选择的自由(the power of choice):
选择能力的自由具有这样的、完全为其特有的特征,即它不能通过任何动机被规定来行动,除非这个人把其纳入为其准则(使之成为对他自己而言的普遍规则),只有以这种方式,无论可能是什么,才可以与选择能力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共存。(Religion 6: 24;49)
康德把选择的自由理解为纳入准则的过程,由于在这里完全忽略了动机的内容,所以选择的自由实际上也就忽略了决定规定意志的诸基础,所以这种纳入准则的过程(不虑及其结果)就是理性存在者为自己确立原则的过程。由于在选择的自由中,行动者必须自己纳入不同的选项,所以选择的自由必然伴随着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康德也将选择区别于低级的欲求能力:如果它[欲求能力]与自己产生客体的行为能力的意识相结合,那它就叫作选择。(MM 6: 213;374)。既然选择确立原则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意识,而原则又是法则或准则的形式,所以无论是实践法则还是实践准则都必然伴随着意识。①值得说明的是,即便我们在这里指出康德在实践语境下预设了选择的自由,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直接完成了康德对自由的演绎的目标。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在纳入准则时可以纳入不同的动机(规定意志的基础),但我们的这种纳入动机的过程仍然不能排除被决定的可能。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明确地指出了这点:“但是,理性本身在它由以制定法则的这些行动中是否又为别的方面的影响所规定,亦即就感性冲动而言叫做自由的东西在更高的和更遥远的作用因方面是否又会是自然……这是一个纯然思辨的问题。”(B831)
但意识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伴随着实践法则仍然是不明的:其是否只是如我思或者先验意识伴随着一切表象,而不管这些表象的来源(经验的还是先验的)以及如何获得这些表象(被动接受的还是主动自发的),因而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自身没有任何内容的意识;或者是实践法则本身仍然要求一种为其所独有的意识,正如统觉的综合统一与分析统一的相互性关系一样,以至于没有实践法则就没有这种意识,没有意识也没有实践法则,因而充当实践法则充要条件的意识?我们可以将前一种意识伴随的模式称为“形式伴随”,而将后一种理解为“实质伴随”。并且实质伴随实际上以形式伴随为基础。以经验知识的形成为例,为了形成知识,就必须要诉诸我思凭借其范畴功能对直观所予的材料进行综合整理。但在整理之前,这些感性所予必须首先为我思所伴随而成为属于心灵的表象,因为我思必须伴随我的所有表象,否则这些表象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对我来说是无。所以,就范畴是否启用于意识伴随的过程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实质伴随”与“形式伴随”,这也分别对应于康德的“经验判断”与“知觉判断”、“概念中的再认知综合”与“直观中的领会综合”的区分。虽然语境有所不同,但既然意识出现在实践语境,我们就不妨借助这种区分来尝试理解实践语境下的意识,以及其与实践法则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检讨意识在实践语境中是否也有可类比的实质伴随。
首先,基于形式伴随模式的意识仍然不能担保实践法则不是从类似思辨理性推演(如上帝、灵魂)的东西强加给意识,因而对实践法则的意识依然很可能是从“理性的先行材料中”“给与”我们。①康德在这里似乎在隐秘地批评《奠基》第三节的观点,证伪从自由演绎出道德的论述正可以被理解为从理性的先行材料推演出道德法则以及处于道德法则下的意识。这显然与康德在CPrR5:31 对理性事实的理解相冲突:
我们可以把关于基本法则的一个意识称作理性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并不能从理性的先行材料中,例如从自由意识中(因为这种意识不是被给与我们的),把它推演出来。而且还因为它……把自己自为地施加给我们……为了避免将这种法则理解为被给予的起见,我们还必须注意:它不是任何经验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凭借这个事实宣布自己是源始地立法的。(CrR 5:31;164-165)
康德于此特别申斥对基本法则的意识并不可以从自由的意识中推演出来,毋宁说它直接将自己施加给我们,这些都在突出对法则意识的非派生的原初性。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不能将实践法则理解为被给予的,因而实践法则并非从某个神秘的地方不分其来源地被给予(given)意识,而是根源于(有待被证明的)纯粹实践理性,而后者得以证明则是通过对法则的意识展现出的原初立法(lawgiving)。因此,既然实践法则并非作为某个既定的东西被动地给予意识,而是主动地表现在意识中,所以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康德在这段文本中所强调的乃是基于实质伴随模式的意识。
但即便我们的分析是真的,我们还必须解答这种实质伴随是如何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意识的实质伴随乃是以意识形式的伴随为基础(我们上文已经解答了形式伴随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必须考察使这种实质伴随得以可能的根本性因素——实践法则的本性,正是这种考察才真正能揭示出实践法则与某种意识的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联系,并指出这种实践伴随模式的意识本身在实践哲学中的意义。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实践法则的普遍性在于其以不同于实践准则的方式规定了意志,康德将这种规定的根据进一步理解为理性的形式法则(实践法则的形式),而非意志的对象(实践法则的经验性质料)(CPrR 5:27;160)。但通过理性的形式法则规定意志无非等同于说纯粹理性自身已经是实践的(或者说我们具有一种高级的欲求能力),这正是康德所证成的结论,而非所据以出发的前提。①Allison 正确地指出了Beck 在这一点上犯的错误(H.E.Allison,Kant’s Theory of Freedom,p.233),即主张康德在第七节所完成的论证实际上乃是取决于对理性实践能力的依赖(L.W.Beck,A Commentary to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p.169),但这样无非是犯了乞题的错误。因为无论是在序言还是导言中,康德自己都明确主张以“如果理性是能够实践的”表述强调一件事情,理性的实践性只是一个假设,而第二批判的目的正是说明(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证)这种能力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如果实践理性的法则具备某种实在性,那么纯粹理性是实践的,或者等同地,理性存在者具有高级欲求能力。因而问题就在于实践法则如何具有实在性。
依照文本理所应当的是,意志的自律应当成为探讨实践法则实在性的首要考虑对象,因为康德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诸原理》一节开头明确诉诸这一点:
这个分析论阐明,纯粹理性能够是实践的,亦即能够独立地、不依赖一切经验性的东西来规定意志,虽然这是通过一个事实,在其中纯粹理性在我们这里表明自己实际上是实践的,亦即通过理性规定意志去行动所借助的道德原则中的自律。(CPrR 5: 42;173)
但康德在第二批判中对自律的界定却不免循环定义之嫌。他径直将自律理解为意志的根据,不是被经验性的因素,而为理性的纯形式所决定。但主张这种自律可以被意识到实际上就已经直接在意识中承认了理性的纯形式对意志的决定性,因而已然承认了纯粹理性的实践性。据此而言,如果康德仅仅直接诉诸在第二批判中的自律,那么就很难避免乞题的错误。实际上,考虑到康德在(CPrR 5: 31;165)诉诸提出意志立法(“自律”)时,仍然诉诸的是一种应当的具备普遍性的规范意识,那么,自律更应当被理解为对应当的意识做的先验解释:
但是在这里这条规则[对意识]说:人们应当绝对地以某种方式行事。因此这条实践规则是无条件的,从而是作为实践的定言命题被先天地表象出来的,借此意志绝对地和直接地(通过在这里也是法则的实践的规则自身)、并且客观地被决定。因为纯粹而自在的实践理性在这里是直接立法的。意志被设想为独立于经验条件,从而作为纯粹意志,由单纯的法则形式决定的,这个决定根据也被看做是一切准则的最高条件。
通过对“应当做某事”之意识的分析,康德指出这种意识所要求的无条件性并不可以在经验的条件内寻找规定意志的依据,那么这种意志的依据就只能在非经验、具有普遍性的理性中寻求。因为任何以意志的经验对象为基础的实践规则所具有的普遍性都是有条件的,无论是就影响的类型(愉悦、不愉悦、中立)还是就影响的程度而言。所以,单纯诉诸经验性的解释应然意识要求的无条件性。康德又通过著名的“伪证”例子进一步说明,在这种应当的意识中,我们甚至意识到自己可以克服任何经验性的欲望,甚至是最为重要的求生欲望,而不去做伪证。这种不做伪证的要求只能在不同感性的层次中寻求。
因此,如果在应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无条件的普遍性并非幻觉,那么这个意识的产生就必须在一种“纯粹而自在的实践理性在这里是直接立法”的意志中寻找。因此,意志的自律揭示的乃是应然意识的内在机制。①这一点也更明显地为康德在GMM 中点出:人们看到人由于自己的义务而受到法则的约束,但却不曾想到,人仅仅服从他自己的,但尽管确实如此普遍的立法,而且人仅仅有责任按照他自己的、但就自然目的而言普遍的立法的意志而行动。(GMM 4: 432;82)所以,我们在实践场景下具有一种规范性意识时,在这种意识背后理性的立法已经悄然发动了:“纯粹理性凭借这个事实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因此,对于实践法则的意识实际上就是应然的意识,没有应然意识所要求的无条件之普遍性,作为自律形式的实践法则就无从谈起;反之,如果没有作为自律形式的实践法则,那么应然的意识就不免沦为一种大脑的幽灵或心灵的错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断定应然意识才是以实质的方式伴随着实践法则。
仿效康德对自由与实践法则关系的论述(CPrR 5: 5;140),我们可以说“理性事实”亦即对普遍无条件性的规范性之意识乃是实践法则内在运行机制的认识理由(ratio cognoscendi),而后者乃是前者的存在理由(ratio essendi)。而认识理由与存在理由的关系才是正确理解Beck 关于主观与客观划分的关键。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处理这个问题:为何这种在应然意识里出现的无条件法则可以被理解为先天综合命题?
二、实践语境下的感性与先天综合命题
在CPrR 5:31 说明了规范性意识的原初性之后,康德又以命题的方式对这个意识的特性进行了说明:
因为它[理性的事实]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把自己自为地强加给我们,而这个命题是既非建立在纯粹直观上面,也非建立在经验直观上面的;是否如果我们设定意志自由,这个命题就同时是分析的?但是对此,自由作为一个肯定的概念,就需要一种理智的直观,而在这里我们完全不可以认定这种直观。
这段话无疑是令人疑惑的。因为康德在这里认为可以用先天综合命题来理解这种意识的特性。但他通过拒绝任何种类的感性直观作为理解先天综合命题的钥匙;又否定了理智直观对我们而言是可获得的,并且指出,如果存在这种直观,这个命题就可能是分析的①在这里康德似乎采用了他在批判前时期所持有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式的观点,主张对神而言,一切命题都是同一分析的。,那么他实际上是拒绝了通过直观来理解命题综合性的途径,而这与他在第一批判中的观点相左。
以主词与谓词(均作为概念)的关系为讨论的出发点,康德将谓词包含在主词中或已经在主词中被想到的判断定义成分析命题,因而分析判断主词与谓词的关系式是通过统一性被思维的(A7/B10)。与之相对,综合命题则被理解为谓词没有包含在主词中,而是添加到主词上,与主词具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可以通过同一性来思考。(A6-7/B10-11)。在论述一切经验命题都是综合命题时,康德将经验命题理解为对感性直观的综合联结。由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在主词与谓词联系的形式上并没有差别(S 是P 的形式),那么,正是(经验性的)直观使得综合判断不同于前者②这种形式的根据也依然最早要被理解为知性的运行,一如康德在第一批判已经指出的,为一个判断中的各种不同表象提供统一性的同一种功能,也为一个直观中的各种不同表象的纯然综合提供统一性。因此同一个知识,而且同一个知性,而且通过它在概念中凭借分析的统一而造成一个判断的逻辑性时的同一种行动,也凭借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把一种先验内容带进它的表象(B105)。我们不妨将知性的这种特性类比于理性,即:理性在实践方面既表现为纳入准则的能力,也表现为自身立法的能力。,正是直观打破了分析判断中主词与谓词的蕴含关系。尽管康德在接下来也说“在先天综合判断中这种帮助的途径[经验]是完全缺乏的”(A9/B13)。但这充其量说明了在感性范围内经验直观与纯粹直观的不同。实际上,康德在空间的先验阐明一节以作为纯粹直观的空间奠定了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几何学。③实际上,要通过直观而非通过非同一性的关系来理解判断已经为阿利森敏锐地洞见到,参见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Yale: Yale University,2003,pp.89-94。(B40-41)质言之,在第一批判中,直观乃是综合判断或命题的本质与必要条件①直观不能作为知识综合判断的充要条件,乃是因为即便是诉诸直观,如果不借助于知性的运作,因而将诸多经验性直观(借助于再生的想象力)联系起来,那么这也不能达到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对将判断理解为知识命题的做法。关于作为经验性表象不能达到知识的说明,见《导论》中康德关于知觉判断与经验判断的说明。;没有直观,综合命题就是不可能的。据此,康德也在第二批判中直接点出:
在后者[纯粹思辨理性]那里,最初的材料不是原理,而是纯粹的感性直观(空间与时间),后者使知识先天地可能,虽然这种知识只限于感觉对象。出于单纯概念而无直观的综合原理是完全不可能的。相反,综合原理只有在与感性的直观相关联时,从而只有在与可能经验的对象相关联时才能发生,因为唯有与这种直观相联结的知性概念才使我们称之为经验的知识。②舒远招倾向于将综合的根本性质归于范畴,他举例说明因果性范畴才是将两个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的第三者,并试图引用第一批判(B35-36)的引文支撑他的观点。尽管他将未知之物X 理解为范畴的文本解读是可以接受的,但他忽视了范畴之所以可以将两个不相关的东西在实存上联系起来,正是通过与直观的结合(依正文引文可见),这正是先验演绎的任务所在。就此而言,我也不敢认同他对先验图示作用的认识,因为范畴只有通过先验图示才能应用于直观,才可以具有综合的性质。否则,因果概念就会作为形式逻辑的概念,表现为以假言的方式连接直言命题,因而表达的乃是命题或判断之间的关系。关于他的观点,可参见舒远招:《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CPrR 5: 42;174)
既然在理论哲学的框架中,综合命题的达成不能不借助直观,那么康德为何以及何以可能在论述理性事实时强调一种不借助于直观的先天综合命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牢记康德关于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区分的教导是十分有益的。
确实,如果我们单纯从理论理性的角度来审视理性的事实,那么我们便很难在理论中找到其位置,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理性事实作为实践知识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此,康德在阐明实践理性奠定了先验自由之实在性(尽管局限于实践领域)时点出了理论语境与实践语境的区别①实际上自第二批判开始,康德就经常基于自然概念的理论与自由概念的理论来说明这种不同。:
凭借这种能力[纯粹实践理性],先验自由从现在起也就确立了起来,……但思辨理性只能将自由概念以或然的,即并非不可思维的方式树立起来,而不能确保它的客观实在性,而且思辨理性如此办理,只是以免将那些它至少必须承认可以思维的东西,假定为不可能,从而危及了理性的存在,使它陷入怀疑主义中。(CPrR 5: 3;139)
据此,即便是从思辨理性的角度来看,在实践语境下得到确立的先验自由也并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尽管不可避免地缺乏在理论经验知识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但这种自由依然是可以思维的,其客观实在性可以在实践上得到证实。据此,在理论知识上无效的东西,只要仍然是可思维的,那么其或许可以在实践知识上得到证实。所以,如果从理论知识方面将理性事实理解为先天综合命题是不可能的,而理性事实又(至少在实践语境下)已然存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审视在实践语境下是否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以至于其可以使康德在拒绝直观的情况下仍然承认理性事实的先天综合性。
幸运的是,尽管康德在第二批判中没有给出更多的论述,但他在《奠基》第三节的开头就提示了如何在实践语境下理解先天综合命题的线索。②实际上,他在《奠基》第二部分的结尾就已经正面地提出了问题:“这样一个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是如何可能的?”(GMM 4:445;93)在指出道德的原则始终是一个综合命题后,康德进一步指出:
但是这样的综合命题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两种认识都通过一个第三者的联结而相互结合起来,它们都可以在这个第三者中发现。自由的积极概念造就了这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不能像在自然原因中那样是感性世界的本性。……这个第三者是什么,在这里还不能立即指明。(GMM 4: 447;95)
康德在这里指出两种认识,亦即通过分析意志自由的观念可以得出道德及其原则与通过分析一个绝对善的意志的概念并不能发现与法则在任何时刻相符合准则的属性,尽管该意志本综合地具备这样的属性。由于自由意志与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所以两种认识的区别乃是在于:第一种认识乃是指出不完善的自由或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的关系,而第二种则是指出这种意志与准则的合法则性的关系,所以综合命题的可能性也就在于不完善意志自身(在客观上)所遵循的道德法则与其(在主观上)所履行的准则的关系。尽管关于二者是否冲突以及如何解释已经引起了无数的争论①Allision 在参照国外学者的解释基础上,对此作了详细而富有洞见的考虑与讨论。详见H.E.Allison,Kant’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ommenta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79-285。就国内学界而言,关于如何理解“两种认识”,以胡好和舒远招为代表的学者将之理解为定言命令的主谓词,并将之进一步理解为“一个绝对善的意志”与“其准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视为普遍法则”或“准则的合法则性”。这种考虑有其道理,因为康德在谈到两种认识之前所讨论的是综合命题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从综合命题的内在构成要素(在这里表现为主词与谓词)似乎是一个理所应当的结论。就此而言,胡好和舒远招的看法则无可非议,并且他们将这里涉及的绝对善的意志理解为属人的、不完善的意志亦属正确。本文之所如此解释两种认识,在根本上是为了突出这一点:就不完善意志而言,准则合法则性的不可分析性和道德法则的可分析性(因为其是自由意志)的联系与张力构成了综合命题的可能性,这一点并不与二者矛盾,甚至与舒远招教授借助GMM:412-413 的文本对综合命题的见解类似,尽管在强调的方面稍有不同,详见下文。(参见舒远招:《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此外,主词与谓词并不足以构成认识,因为至少对于康德而言,认识都是以命题或判断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我尽管同意他们在义理上的理解,但却不能接受他们在文本上的解释。,但清楚的是,康德在此借助一个“第三者”来说明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而这个第三者与自由的概念关联,因而不仅具有感性世界的本性。尽管他在这里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个第三者究竟是什么,但三节之后,在说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时,他终于给出了答案:
这样,定言命令就是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为一个理智世界的成员;因此,如果我只是这样一个成员,我的一切行为就会在一切时候都符合意志的自律;但既然我同时直观到自己是感官世界的成员;所以这些行为应当符合意志的自律;这个定言的应当表现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我被感性欲望所刺激的意志之外,还加上了同一个意志的理念,但这同一个意志的理念,但这同一个意志确实属于知性世界的,纯粹的、对于自身来说是实践的。(GMM 4: 454;100-101)
在这里康德诉诸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两重决定根据或“两种立场”①尽管我更同意同一个意志有两重决定性依据的说法,因为两个世界所隐含了存在论假设在根本上不符合康德批判哲学的品格。(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可参见Allison 的《康德的自由理论》与《康德先验观念论:一种解读与辩护》)但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仍然将采用两个世界的说法。,毋宁说是以两种立场的统一来解释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定言命令之可能性。重要的是,单单诉诸任何一种立场都不能解释理性事实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如果仅仅诉诸理性世界成员的立场,那么应当的意识就还不能出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意志的原则与准则完全是一致的,因而我们的意志在实践层面就相当于神的不可错的意志:理性单单通过自身在实践上必然性的规定者意志(GMM 4:413),或者借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术语,这种意志只具有欲求的高级能力,而不具有低级能力,所以不存在违背道德法则的可能。实际上,应当的意识还需要我同时肯认自己感官世界成员的身份。另一方面,如果单纯诉诸感性世界成员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完全是被自然法则所决定的,尽管在这个领域存在理论的先天综合命题,但由于缺乏先验意义上的自由,应当更无从谈起。因此应当的意识仅仅适用于作为两种身份统一体的有限理性存在者,而这种存在者的意志既受感性触发(而非决定)又有被纯粹理性所规定的特性,正是充当综合命题得以可能的“第三者”。②本文在对第三者的解读上更接近于胡好的解读,尽管我不能同意他认为可以从自由演绎出道德法则的观点,因为他论证两个最重要的诉求都不是如此可靠:(1)他直接诉诸康德理性具有实践理性的一面不免独断,因为康德正是在自觉面对实践理性可能是(由于各种强版本的自然因果决定论)幻觉的怀疑下,在第二批判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质言之,理性的实践性一面从来不是无须证明的。(2)他主张“自由具有原因性”也并不是一个自明的主张,因为这种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并不能直接从消极自由中推导出来(这也为阿利森正确地洞彻到,认为《奠基》的核心缺陷所在。而胡好却不知为何,径直认为这种指摘没有道理。在此我不敢苟同),如果这种说法要成立就不得不诉诸实践理性的存在,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决定论或者至少是怀疑论的威胁下,这从来就不是无须阐明的。(参见胡好:《康德定言命令式的演绎》,《道德与文明》2012 年第2 期)
胡好关于“第三者”的五个特征做了十分精辟的总结,我们可以参照这些标准来检验我们的结论是否准确,并回应学界的相应质疑。其五个特征如下:(1)第三者能将两种认识包含在自身中;(2)积极自由揭示出第三者,它不同于单纯感性世界的本性;(3)我们对第三者先天地有个理念;(4)第三者是同一个意志;(5)第三者与自然知识的综合方式具有类比关系。①同上。
在前文中,我们已然指出,两种认识乃是在于道德法则的可分析性,和准则合法则性的不可分析性。既然准则的合法则性是不可分析的,那么其也就没有实践上的那种必然性。在这种情形下,要么康德在文本中所指的意志是神圣式的意志(因而突出了实然的必然性),要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准则的合法则性并非实然的必然性,而是在规范意义上的应然的必然性。
但是,在前一种模式下,意志的法则与意志的准则在概念上就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康德对被思维成仅仅具备理性成员身份的人类所断言的那般,根据这种身份完全可以不借助直观(对自己感性世界成员身份的观察需要感性直观)而直接推演出这种一致性。但既然康德强调准则的这种属性不能通过概念分析的方式得出,所以这种意志只能是不完善的意志。并且我们也看出,神圣意志根本也不适用综合的方式来描述。因而,当康德断言不完善的意志在其准则任何时候都包含着可以被视为法则的准则时,我们更应当将之理解为对准则的一种要求或者规范,其在任何时刻都应该符合道德法则。所以,能将这两种认识揭示起来的恰恰是不完善的意志。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舒远招将第三者等同神圣意志的解释,尽管他关于两种认识的一些见解是十分有见地的。舒氏通过引用相关文本(GMM 4: 412-413;66),指出了两种认识分别关联于道德法则或原则的必然性(客观的必然性)以及行动准则的必然性(主观的必然性),否决了不完善意志作为第三者的可能性。尽管他将两种认识关联于原则和准则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他所诉诸的前提:“理性完全决定意志”①舒远招:《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如果理性完全决定意志,实践准则的合法则性就完全可以以概念的方式从这种神圣意志中分析出来,这显然与康德在《奠基》第三节所诉诸的综合性相悖。而且如果要通过神圣意志作为定言命令式的条件,无异于诉诸神来保证道德哲学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威胁着康德伦理学理性存在者为自己立法的特征:作为定言命令的道德法则的可能性不是通过我们的意志,反而必须借助于一个超越的存在。这样一来,如果这种神圣意志不存在,那么道德法则甚至是积极自由便都不存在,这也与康德在第二批判中以自由奠定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的说法不合(CPrR 5: 4;139)。
此外,关于第二点,亦即第三者具有不同于感性的本性,由于不完善意志已经具备了超感性的一面,所以我们也不能直观到它本身,而只能观察到其感性的表现。在这种意义上,第三者的本性确实不同于纯然“感性世界的本性”。而且,这个意志的肯定是与对应然的意识一并成立的,前者乃是后者的存在理由,后者乃是前者的认识理由。②所以,即便康德在第一批判中主张我们的意志可以不受感性的决定(A532/B562)似乎已经提供了第二批判的论证基础,但由于他还没有阐明意志的自律(纯粹理性的实践性),所以至多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没有提供这种意志以(实践上)的实在性。所以这时期的实践理论仍然只是处于“半批判”的时期。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个得到承认的意志不再仅仅具有纯粹理性立法的身份,而同样具有受感性刺激的特征,所以是同一个意志。③至于舒远招所谓的第三者与定言命令的主词重合问题:将受感性刺激意志理解为不完善的意志会产生用已蕴含在主词中的谓词谓述主词的情况(参见舒远招:《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我们只需要认识到,被感性刺激的意志并不在概念的必然性上意味着其遵循道德法则,意志主义或存在主义就可以承认意志被感性刺激但不必遵循道德法则,所以不完善意志并不等同于被感性刺激的意志。因而,尽管没有诉诸直观,但感性在实践领域仍然以另一种作用充当了综合命题的必然条件。另外,在理论哲学中,尽管直观是综合的必要条件,但是综合的充要条件则需将直观与概念结合的能力或作用,所以其兼具直观与概念的双重属性。由于直观与概念在理论哲学中分属感性与知性,所以综合的充要条件也是感性与知性的统一。在这种意义上,先验想象力及其产物先验图示乃是与不完善的(受感性刺激又被理性指引)意志存在可类比的地方。
至此,我们已经澄清了理性事实主观与客观方面的联系以及其先天综合命题的性质,这些都是理解理性事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可以处理康德关于理性事实的进一步论断——理性事实的唯一性,并指出同理性自律的理性特征一并构成这种唯一性的感性特征。
三、理性事实的唯一性与敬重
康德在CPrR 5:31 再次指出了理性事实的唯一性:
为了避免将这个法则误解为被给予的起见,我们还必须注意:它不是任何经验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凭借这个事实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
在之前,我们将法则的非给予性理解为理性事实(应当意识)背后的运作机制:只要应当意识出现,那么法则就已经自动运行起来,我们意志的决定性依据就不再仅仅为欲望偏好所主导,而必须考虑纯粹理性的要求,即便我们仍然有可能不出于纯粹理性的要求行事。现在,康德在这里强调理性事实的唯一性。由于康德在这里将理性事实区别于任何经验性的事实,所以一种自然的解读就是,康德在这里仅仅是为了将理性事实区别于多种多样的经验事实,如对人的经验性格的总结(社会丛林法则之类),因而关于理性事实之唯一性更多强调的是其不同于经验事实的一面。①P.Kleingeld,“Moral consciousness and ‘fact of reason’”,p.60.这自然是十分敏锐而具有说服力的说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强调尽管是正确的,但康德在这里强调的是关于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换言之,事实的唯一性乃是针对理性而言,所以尽管经验性的事实不同于理性的事实,但这也不必然得出理性事实只有一个的结论。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部分也指出理性对各种知识的调节有出自自身的原理(同质性原理、具体化原则与形式的连续性原理)(A649-668/B677-696),那么至少关于理性事实唯一性的说法是可怀疑的。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也至少有两种可辩护的策略。一种策略是通过强调理性本身自律的特征作为理性的唯一事实,而其他的理性原则只是理性自律原则的不同表现,这一出于康德学说整体性考虑的思路已经为以奥尼尔为代表的学者们大加发扬。①O.O’Neil, Construction of Reason: Explorations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University,1990,pp.51-65.但这种思路很难说十分适合于对此段文本的解释,因为康德在这里显然更多地诉诸实践语境,尚未上升到其对理性系统性的考虑。因而,这种唯一性最好被理解为关于实践理性的唯一事实,而康德也明确在《奠基》中表示“自律原则是唯一(sole)的道德原则”(GMM 4: 440;89),而所谓的普遍法则公式(FUL)、人性公式(FH)与自律公式(FA)“在根本上是同一个法则的三个公式”(GMM 4: 436;85)。鉴于自律原则揭示了纯粹理性如何是实践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接受康德关于实践理性事实之唯一性的论断。但既然这种理性事实是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并且有限理性存在者受感性刺激意志充当了先天综合命题的基础,自律仅仅解释了其理性运行的部分,所以要想阐明理性事实的唯一性,我们还必须考虑理性事实的感性特征,亦即康德所指出的唯一的道德情感——敬重。
关于敬重,康德在《奠基》和第二批判中都有过论述,并指出了敬重的两个核心特征:(1)敬重是由实践理性产生的,以及(2)敬重充当使这一法则成为主动准则的动力。(CPrR 5: 76/GMM 4: 401)。但这两个特征看上去都非常可疑。首先,如果康德坚持感性与知性或理性的二分,那么敬重作为一种情感如何能是一个理性的产物?其次,即便承认前者,如果道德法则必须通过敬重的情感才能规定意志,那么康德仍然不能摆脱道德情感论(尽管是间接的)的风险,因而这很可能意味着实践理性直接提供了一种敬重的情感,并且通过这种情感在与自爱情感的竞争中取得优胜来促使我们将实践理性提供的法则当成我们行为的准则。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就能力的二分而言,单单通过对实践理性或理性成员身份的分析确实不能得出情感。但就有限理性存在者而言,由于其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体,其意志既受感性刺激又被理性引导,便使得理性以其意志为枢纽产生情感得以可能:如果意志是完全自律的,那么就会产生敬重的情感;如果意志是他律的,产生的就只是出于偏好的快感、不快或漠不关心。进而言之,由于意识一直伴随着意志的选择过程,所以其本身具备意志的感性与意志的理性两种样态。应然意识所要求的无条件的普遍性乃是意识的理性样态,而敬重作为一种情感则是意识的感性样态。①Allison 也指出,关于敬重这种道德情感并不能被认为是通过对道德法则责任力量的意识不经意产生出来的心理状态,毋宁说是这一个意识的感性一边。(参见H.E.Allison, Kant’s Theory of Taste: A Reading of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Judg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30)
关于第二个问题,应当澄清的是,尽管康德确实指出敬重充当了道德法则得以践行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法则不能直接成为意志的根据,而必须借助于敬重的情感。确实,康德强调当道德法则作为意志的决定根据时会损害偏好,而由于一切偏好和感觉都是建立在情感上,他进一步得出理性瓦解偏好的方式对情感的否定作用本身亦是情感,似乎在文本上支撑了理性通过敬重来成为行动者动力的说法。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种说法实际上预设了比文本更多的东西,即敬重作为一种情感乃是实践理性直接作用于感性的结果,而实践理性是依据这种感性结果的强弱与否践行或不践行出来(这取决于敬重的情感能否战胜其为感性天生所具有的一切情感)。但这种看法很难说是十分可靠的,因为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敬重是实践理性作用于感性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种结果是否还需与感性的其他偏好争胜,还是已经是实践理性作用于生来具有偏好的感性的结果?很明显的,康德所持的乃是后一种观点:
相反,那构成了我们一切偏好基础的感性情感虽然是我们称为敬重的这种感受的条件,但这种情感的决定原因存在于纯粹实践理性之中,并且就其源泉而论这种感受不是本能的,而必定意味着是出于实践作用的。(CPrR 5:75;201)
在这里,由于作为敬重条件的感性已经包含了一切偏好的可能性,所以当纯粹实践法则作用于感性时,便已经贬损了这些偏好,由于在感性中没有先天倾向道德的情感(至少康德式如此主张),所以这种贬损也是必然的,而敬重则是实践理性作用于感性的(至少对我们这种其意志受感性刺激的理性意志而言的)必然结果,所以敬重实际上是道德法则在感性上的表达。①据此,瑞斯(Andrew Reath)的洞见无疑是正确的,这个作为结果的道德情感以成为某种东西,就像我们在其中经验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活动的方式而告终。(A.Reath, Agency and Autonomy in Kant’s Moral The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0)类似的观点也可参见G.Banham,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From Critique to Doctrin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3,pp.93-118。又由于意识始终伴随着这种过程,所以敬重实际上是对道德法则的感性意识。由于这种意识的必然性,康德将敬重理解为一种我们可以先天推断出的情感:“一言以蔽之,依据法则的理智原因,对于法则的敬重就是一种可以先天认识的情感。”(CPrR 5: 79;204)
综上所述,由于我们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身份,只有将应然的意识与敬重情感合言才能揭示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的核心基础:受感性刺激的理性意志。应当的意识乃是侧重从理性的方面揭示了实践理性的运行,敬重则是从感性方面完成了这一点。由于意识始终伴随着这种运行的始终,而且从根本上这种意识又是关于道德法则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意识理解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道德自我意识,而这也是唯一的实践的理性事实的应有之义。②本文的写作初衷乃是源于南星老师在上课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理性的事实”是否可以在康德理论哲学内部找到落脚点,康德在第二批判中的理性事实是否背离了第一批判中的知识论?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促使我写成了此篇论文。在修改和定稿过程中,南星老师和祁箫同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