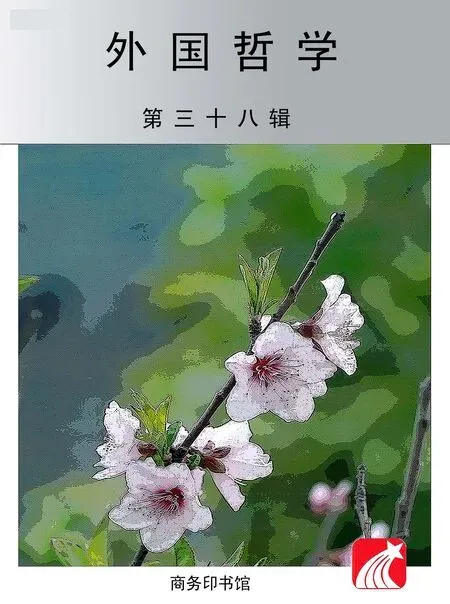作为“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准则”及其谱系学效应*
姬志闯
内容提要:作为实用主义的诞生标识,“实用主义准则”一经提出,叙事者们对之的释义便从“学说”和“方法”这两个基本维度上展开。然而,无论是哪一个释义维度,似乎都难以在完整统一的意义上获得普遍认同,要么无法在其源生语境和经典表述中找到完美的证据链条,要么因为衍生了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实用主义”风格和版本而无法融贯地统摄整个古典实用主义进程。事实上,无论是皮尔士的逻辑学、符号学、科学语境及其对“实用主义准则”表述的修正,还是之后古典实用主义进程中对其的拓展和运用,都表明“方法论”才是“实用主义准则”的本质要义。而当我们将其作为谱系线索纳入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建构时,其效应也更为凸显:不仅可以在“具体方法”和“方法论”的辩证互动中融贯地说明和统摄叙事的各种“断裂”和“分野”,而且也将在一种崭新的意义上实现对“古典实用主义”的概念廓定和形象刻画。
随着威廉·詹姆斯1898 年对其作为“实用主义”创始人的归认,皮尔士在1878 年的论文《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中对“实用主义准则”的提出和首次表述便被公认为实用主义的诞生标识。然而,这个经典表述却并不意味着“实用主义准则”释义的终结和完成,在某种意义上,“实用主义准则”的释义甚至根本没有沿着皮尔士的原初意义构想前行,而是随着实用主义进程的推进从不同的维度上得以广泛展开。无论是威廉·詹姆斯、杜威、米德等经典作家,还是之后的其他实用主义叙事者们,都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问题关注进行了个性鲜明的释义和解读,就连皮尔士本人也因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和对被滥用的不满对其表述进行了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以至于早在1908年洛夫乔伊就得出了“存在13 种实用主义”①参见A.O.Lovejoy,The Thirteen Pragmatisms,and Other Essays,London: Oxford Press,1963。的结论。尽管这些释义,都因为对“实用主义准则”作为实用主义诞生标识的认同和首次表述中对“澄清概念意义的方法”的明示,而相对集中于“学说”和“方法”这两个基本维度,但无论哪一种维度的哪一种释义似乎都难以获得普遍认同:要么无法在其提出者皮尔士的原初语境中找到完美的证据链条,要么不能对皮尔士本人表述的修正性历程和古典实用主义的实际进程给出融贯合理的说明。不仅因为无法达成释义的统一而衍生了各种风格迥异甚至相互冲突的“实用主义”版本,也因为以此为据而人为判定的各种叙事的“断裂”和“分野”而无法在谱系学意义上完成对古典实用主义整体叙事进程的融贯统摄。究其根源,就在于上述两个维度都没能在“原则表述”和“叙事进程”的动态结合意义上发现并触及“实用主义准则”的另一个释义维度,即“方法论”维度。实际上,无论是从其逻辑学、符号学、科学的源生语境,还是皮尔士对“实用主义准则”表述的修正以及之后古典实用主义进程中对其的运用和拓展看,作为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论”才是“实用主义准则”的本质要义,而这也正是其能够作为谱系线索,承诺古典实用主义乃至整个实用主义百年叙事谱系的融贯建构的关键所在。
一、“实用主义准则”的“学说”和“方法”释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自威廉·詹姆斯1898 年在伯克利所做的题为“哲学的概念与实践效果”的演讲开始,皮尔士提出的“实用主义准则”便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实用主义”为标签的哲学运动。然而,关于这场运动的灵魂和理论后果的“实用主义”的理解却从一开始就没有达成统一。虽然早在1907 年发表并被公认为标志实用主义运动趋于成熟的著作《实用主义》中,詹姆斯就曾试图整理当时人们对“实用主义”含义的种种混乱理解,但却收效甚微,以至于伍德布里奇在随后对“实用主义”的评论中就这样总结道:“到目前为止,连实用主义的含义都没有一个精确而公认的说法。”尽管如此,他仍然在详细分析各种释义之后将其大致归为“方法”和“学说”两类,即:“首先,实用主义是一种探究手段,也是一种对概念意义进行规定阐释的方法;其次,实用主义是连接事实和观念的哲学理论。”①参见F.J.E.Woodbridge,“Pragmatism and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view,1907,XXXIV/3,pp.227-228。事实上,这种“方法”和“学说”的归类,不仅是对早期实用主义释义的总结,也同样适用于作为其精神源旨和标识的那个“实用主义准则”,并因此构成了其释义的两个基本维度。
尽管作为哲学运动标签的“实用主义”比“实用主义准则”更为宽泛,而且皮尔士的最初表述和詹姆斯等经典作家们也都一致指向并认同它“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使我们的观念清晰的方法”,但作为这一哲学运动的肇始标识和思想核心,尤其是在20 世纪初与“唯心论”和“实在论”等流行于美国的哲学流派的对照和互动背景下,“实用主义准则”仍然被自然地作为哲学流派的代名词而被解读为一种“哲学学说”,因而学者对之进行了内容和特征的概括总结。除了根据不同的问题线索将实用主义按照内容观点直接称作“意义理论”“真理论”或“宗教学说”等之外,更为普遍的是对其思想特征进行概括总结以确认其学说身份。譬如,莫里斯视之为“最具美国民族特征的哲学”,从方法论、价值论和宇宙论三个层面考察了其基本思想①参见C.莫里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世界哲学》2003 年第5 期,第92—100 页。;普拉特则归之于对“交互作用、多元论、共同体和生长”等美国本土哲学原则的继承②参见S.L.Pratt,Native Pragmatism: Rethinking the Roots of American Philosoph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p.20。;维纳围绕古典实用主义的“实质性论题”概括了其五个特征,即“多元经验主义、对实在和知识的暂时论(temporalist)说明、对实在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t)说明、对物理和社会规律的或然论观点和民主世俗的个人主义”③P.Wiener,“Pragmatism”,in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edited by P.Wiener (Di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p.553.;塞耶尔基于对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层面的更多考虑,将其特征描述为:作为哲学和科学中的准则、一种知识论和实在论、一种理论观④参见H.S.Thayer,Meaning and Action: A Critical History of Pragmatism,Indianapolis: Hackett Pub.Co.,1981,p.431。;舒斯特曼则综合了两者将其归纳为十条原则,即实用主义的变动本性、行动和心灵的目的性、不可还原的自然主义、反笛卡尔主义、共同体、经验主义倾向、心灵产物和概念的前瞻维度、社会改良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⑤参见R.Shusterman,“What Pragmatism Means to Me: Ten Principles”,Revue Française d'Études AMéricaines,2010 (124),pp.59-65。;而罗森塔尔则从古典实用主义与现象学、分析哲学和所谓的“新实用主义”的关系出发,进一步将其核心观点扩充为十二个⑥参见桑德拉·罗森塔尔:《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陈维纲译,开明出版社1992 年版,第9—24 页。。毫无疑问,这种“学说”内涵是基于对“实用主义”的源旨与核心而被赋予“实用主义准则”的,然而,且不说这种解读维度是否符合皮尔士对其作为方法的原初构想和经典表述,即使是对其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的思想特征和基本内容的概括自身,也会陷入“统一和全面的两难”,即:面对实用主义复杂多样甚至相互冲突的“全面”观点,不仅难以在归纳概括的意义上实现“统一”以统摄差异;而且即使做到了当下的“统一”,也很难涉及并涵盖可能出现的新观点,并在面对未来问题的无限展开时趋于失效。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很难给出一个作为哲学学说的“实用主义”的统一形象,以至于最终只能将之归于“诸叙事的冲突”而草草了事。而在谱系学意义上,这种困境将会进一步放大,因为面临莫衷一是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归认,我们甚至连“什么是实用主义?”“哪些哲学家是实用主义者?”都无法确定。
与“学说”维度相比,“方法”释义似乎更符合“实用主义准则”的基本意义构想,因为,作为一种“方法”,不仅可以在实用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初表述中找到根据,而且也在实用主义的发展进程及对之的应用中得到了认同和呼应。皮尔士将其描述为“一种用以弄清楚一些难解的词或者抽象概念的意义的方法”①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44 页。,詹姆斯则强调它“是试图探索其实际效果来解释每一个概念”②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26 页。的方法,并最终在杜威那里落实为一种自然的探究;而在古典之后的发展尤其是“新实用主义”复兴进程中,无论是作为“分析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冲动”的C.I.刘易斯,还是作为“新实用主义的肇始者”的蒯因、古德曼等,其“方法”意义都得到了应用性阐释,即使在语言转向中呈现出了某种激进后果,也在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那里得到了“回归性”倡导和呼应。苏珊·哈克出于对以罗蒂为代表的“庸俗实用主义者”对古典实用主义的过度阐释的反对,表达了对皮尔士的感激和“回归”倡议③参见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陈波、张力锋、刘叶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2 页。;而N.雷谢尔则基于避免实用主义的危机目的,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转向”诉求中强烈呼吁“回归皮尔士”④参见N.Rescher,Realistic Pragmatism: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 Philosophy,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p.78。。然而,虽然所有这些基于“方法”维度的释义都把“实用主义准则”解释为“方法”,但仍然因为不同的解读和应用而出现了理论后果的差异甚至冲突。皮尔士首先将其应用于“观念的确定”,并因为对某种“滥用”的不满而在对“实用主义准则”最初表述的不断修正中愈加强调“实践效果的客观性和经院实在论立场”;詹姆斯则将其应用于真理和宗教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其“彻底经验主义”的语境中完成了“经验转向”,也因为更强调“在实际证实过程中使之为真的具体真理”和信念的“兑现价值”而呈现出了一种更强的“唯名论风格”;而杜威则因为像詹姆斯一样对特殊真理及其实际证实过程的强调①参见孙咏:《美国实用主义:演变及其当代走向——苏珊·哈克教授访谈录》,《广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2 期。,与皮尔士的实在论格格不入,并因此被归入詹姆斯实用主义的承续之列。苏珊·哈克认为,“如果说皮尔士哲学在逻辑和实在论的风格中趋向成熟,那么,詹姆斯哲学则在更为心理学和唯名论的格调中发展演变”②苏珊·哈克:《导论:新老实用主义》,陈波译,载苏珊·哈克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7 年版,第14 页。,而雷谢尔、莫恩斯和布鲁克则直接将之区分为“客观的与主观的”“实在论的与反实在论的”③参见H.O.Mounce,The Two Pragmati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7,pp.2,29。“操作主义与推理主义”④参见F.T.Burke,What Pragmatism Wa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3,p.3。的对立版本。更为严重的是,当我们把这种基于“方法”释义的风格和版本差异置入实用主义的整体叙事进程时,对各种叙事的不同版本归属和风格认定,则会直接导致古典实用主义乃至整个实用主义叙事进程的断裂和分野,并因此造成实用主义谱系的不融贯和“统一形象”刻画的不可能。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方法”释义却带来了如此的后果差异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前述“方法”释义更多聚焦于其作为“具体方法”层面,而没有触及和呈现其“方法论”维度,因此,也就只能在其“具体应用”的问题语境中并根据其理论后果做出差异和分野判断,而无法在“具体方法”的应用和对“方法论”内涵的反哺的辩证互动中审视和考察实用主义的整体叙事,进而在整体谱系意义上完成对具体差异的合理说明和融贯统摄。那么,“实用主义准则”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呢?
二、作为“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准则”何以可能?
如前所述,虽然作为一种哲学运动的标识和核心,把“实用主义准则”解读为一种“学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其“方法”释义也能在对其的经典表述和实际运用中找到根据并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两种维度的释义却并非其意义的全部。因为,无论是从其提出的科学、逻辑学、符号学、认识论等原初语境,还是从皮尔士对其表述的修正历程和实用主义的整体发展进程看,“方法论”都是“实用主义准则”的本质要义,而这也正是古典实用主义经典作家们视之为实用主义哲学核心承诺的关键所在。
首先,从其提出的科学、逻辑学、符号学和认识论的原初语境看,“实用主义准则”从一开始就具有“方法论”意义,或者说,就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而提出的。对于作为科学家的皮尔士而言,“实用主义准则”是对“科学领域中各种实践中的成功科学方法”的理论概括。正如他坦承的那样,“简单来说,我的哲学可形容为,一个物理学家基于先前哲学家的成果,试图对于宇宙的构造做出科学方法所允许的一些猜测”①C.S.Peirce,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Vol.1,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para.7.,它不仅源自各种具体的“科学实验”,也通过确立科学的意义结构揭示了科学方法的一般模式②参见桑德拉·罗森塔尔:《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陈维纲译,第26—48 页。;不仅以“确定信念的方法”的形式刻画了一般的科学探究过程,也以认识上的“可错论”最终指向“科学知识的增长”,并服务于包括各种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在内的宏大科学体系建构。虽然在最初的表述中以一种“弄清楚一些抽象概念和词汇的意义的方法”的具体形式被呈现出来,但在皮尔士的逻辑学语境中,“实用主义准则”却同样被构想和设定为一种严格的“逻辑推理准则”。因为,真正的推理是通过消除怀疑、确定信念而由已知通达未知,并将其结论的持续检验指向未来实践效果的探究过程,而且,“我们的思想要根据我们准备去做的事情来解决,逻辑学……必定是伦理学即关于我们有目的的选择做什么的学说的一种应用”①C.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Vol.2,edited by Peirce Edition Project,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142.,所以,尽管每一个具体的推理过程都指向某种特殊信念的确定,但作为逻辑推理总方法和一般探究法则的“实用主义准则”却不仅适用于科学推理,也适用于常识、道德和宗教的一切推理;不仅作为具体方法适用于概念,也作为“方法论”适用于形而上学、实在等对象;不仅适用于理论推理,而且也作为“实践推理”的法则构成了生活“习惯”的指导原则。如果把这种逻辑学植入符号学语境,那么,“实用主义准则”的“方法论”特质则更为明显。因为,在符号学视域内,逻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或者当时的数理逻辑,而是一种广义的“准必然的或形式的符号学说”②C.S.Peirce,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Vol.2,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para.203.和“有关符号一般法则的科学”,并且本身就“具有三个分支:(1)理论语法,或关于符号本性及意义的一般理论;(2)批判论,旨在划分论证并确定每一种论证的有效性和强度;(3)方法论,旨在研究在探究、阐释和应用真理时所应遵循的方法”③C.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Vol.2,edited by Peirce Edition Project,p.260.,所以,作为逻辑推理准则的“实用主义准则”,不仅本身就具有“方法论”意义,或者说就是一种“方法论”,而且,也因为刻画了整个符号过程而“使得思想活动成了一种有关符号新陈代谢的生动推理”④C.S.Peirce,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Vol.5,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para.402,n.3.。如果说推理是对符号的解释,并作为主要方法提供知识,那么,面向未来行动并将结论的持续检验交付于实际效果的“实用主义准则”,必将在与认识论的统一中归于一种认识上的“可错论”,进而在对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双重克制基础上为人类的认识提供一种新路径。
其次,从皮尔士对“实用主义准则”表述的修正历程看,每一次改变和重述都是对其“方法论”内涵的强化和充实。众所周知,皮尔士关于“实用主义准则”的首次表述完成于1978 年的论文《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即:“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概念的对象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具有一些可以想象的实际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①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第95 页。在这个表述中,虽然皮尔士把概念意义交付于其带来的实际效果,但并没有对这个实际效果做出“经验”和“理性”的明确的界分,甚至还基于对科学实验精神的忠诚表现出了对“经验效果”的强调和关注。正如莫恩斯所言:“当他撰写1878 年的论文时,皮尔士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没有超越经验的现实”②H.O.Mounce,The Two Pragmatisms,p.27.,因此,对于此时的皮尔士来说,与康德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相比,经验主义似乎更占上风,而“实用主义准则”,也因为具体适用于“概念”并同时被构想为“逻辑推理准则”而兼有“具体方法”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然而,詹姆斯1898 年后对“实用主义准则”的通俗阐释,以及在运用于“真理”问题的讨论时对“特殊真理”“经验效果”和“兑现价值”的强调,却引起了皮尔士的不满。于是,皮尔士在1905 年的两篇论文中对之进行了重述,即:“一个概念,即一个词或其他表达式的理性意义,完全在于它对生活行为产生一种可以想象的影响”③涂纪亮,前引文献,第4 页。和“任何一个指号的全部理性内涵就在于合理行为的各种普遍模式的总和,它依据于各种可能的、不同的环境和愿望,从而引导人们接受这个指号”④同上书,第22 页。,并以一个“丑陋到足以防止被诱拐”的名字“实效主义”(pragmaticism)以示区别和修正。在这里,皮尔士基于其业已成熟的符号学理论表达了对概念的“理性意义”的强调,并将其明确规认为超越“经验当下”的“对生活行为产生的可以想象的影响”和“合理行为的各种普遍模式的总和”,因为概念的意义取决于“实际效果”,所以,这种规定也是对“实际效果”的理性规定。不难看出,随着“实际效果”的“经验性”的削弱和“理性化”的加强,“实用主义准则”也逐渐从对“具体特殊”的关注走向对“理性一般”的强调,并因此更多地拥有了普遍的“方法论”内涵。然而,修正并未终止。如果说前两次重述还只是集中于“概念意义”或“实际效果”,那么,皮尔士对“实用主义准则”的最后一次表述:“我把实用主义理解为一种用以弄清楚某些概念的意义的方法,不是所有概念的意义,而仅仅是那些我称之为‘理智的概念’的意义,也就是说,是那样一些概念的意义,一些涉及客观事实的结论可能以这些概念的结构为依据。……理智的概念——它们是那种被适当地命名为‘概念’的唯一指号负荷——从本质上说具有某种涉及有意识的生物或者无生命的对象的一般行为的意义,因而传达某种不只是感觉的东西,而是传达某种比任何存在事实更多的东西,也就是传达习惯性为的‘would-acts’(‘将会如此行动’)、‘would-dos’(‘将会如此行事’)”①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第44—45 页。,则对概念对象和实际效果进行了双重限制,进而完成了对“经验当下”的完全剥离,也因此完成了“实用主义准则”的“方法论”意义的最终充实。从以上进程不难发现,皮尔士基于其理论成熟度对“实用主义准则”的每一次重述和修正,都是对其“方法论”内涵的充实和完善,而从另一方面看,每一次充实和完善,实际上也都是对其作为“实用主义准则”本真内涵的强化和确认。
如果说“方法论”作为“实用主义准则”的本质要义被确认的话,那么,这种释义也在实用主义进程以及对其的拓展应用中得到了呼应。尽管因为对“实用主义准则”的通俗阐释以及应用于真理讨论时对“感觉经验”和“兑现价值”的强调,而在理论主张和立场风格(唯名论和实在论)上出现了差异,但无论是在“具体方法”还是“方法论”意义上,詹姆斯和皮尔士都并不冲突。詹姆斯将“实用主义准则”作为“具体方法”的应用从“概念”拓展到“真理”和“宗教”,不仅本身就是对其“方法论”意义的贯彻和承诺,而且,在他借用意大利实用主义者G.帕皮尼的“走廊”比喻中也可见一斑,毕竟,走向每一个房间的“具体方法”都必须穿过作为“方法论”的走廊。①参见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第33 页。与前两者一样,杜威不仅主张对“实用主义准则”“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应用,应用到各种不同的争议、信念、真理、观念和对象”②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1899-1924,Vol.4,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2008,p.101.,而且基于“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立场将其归于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自然探究理论。除了其“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更加趋近于皮尔士的“实在论”和“批判常识论”之外,杜威的“探究五环节”也与皮尔士的“怀疑——信念——行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也坦承其是对皮尔士观点的自由转述。
至此,无论是提出的原初语境、皮尔士对其表述的修正,还是实用主义的发展进程,都向我们表明:除了作为“具体方法”之外,“方法论”也作为其不可或缺的释义维度构成了“实用主义准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正是这种“方法论”意义,才承诺了“实用主义准则”作为实用主义方法在哲学上的核心地位,不仅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用主义谱系线索的首选,而且也为前述“学说”和“方法”释义维度上的困境解决和实用主义的谱系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行路径。
三、“方法论”视域下的“古典实用主义”叙事及其谱系
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准则”不仅作为诞生标识承诺和归聚了实用主义的自然历史生成,也作为实用主义方法在哲学上的核心而引发和统摄了其叙事逻辑的展开,这种“历史和逻辑的融聚点”的特质和地位也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用主义谱系线索的首选。然而,如前所述,以“实用主义准则”为线索展开的叙事描述和谱系建构,却在“学说”和“方法”的释义维度上造成了实用主义内容、版本和风格的巨大差异,不仅因此带来了叙事的各种冲突、断裂和分野,也无法给出一个融贯统一并得到普遍认同的实用主义谱系。那么,在“方法论”的释义维度或视域下,又如何审视和看待这些断裂和分野并以此为线索进行古典实用主义谱系的融贯建构呢?
如前所述,基于“学说”释义维度对古典实用主义的描述,都是围绕把“实用主义准则”作为具体方法应用于具体问题时所产生的“理论后果”展开的:要么以“所讨论问题及其理论后果”为依据直接将实用主义描述为意义理论、真理论、宗教学说或者符号学理论等,要么则是以“内容”的特征概括为基础对实用主义进行整体的归并描述。前者导致内容的差异和冲突显而易见,因为问题的不同必然带来理论后果的差异,而且,即使是相同的问题也同样会带来理论后果的差异,譬如,希尔就以皮尔士并没有像詹姆斯那样把“实用主义准则”应用于真理概念为依据而把前者的主要贡献排除在了实用主义之外①参见托马斯·E.希尔:《现代知识论》,刘大椿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367—368 页。;而后者则会因为不同内容所呈现的不同特征而陷入差异甚至冲突,并因为“统一和全面”两难而无法实现“整体特征”的统一归并。实际上,这些差异和冲突在“方法”维度上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为,所有这些将“实用主义准则”作为“具体方法”应用于具体问题讨论时所带来的具体理论后果及其特征的差异,在“方法”意义上或者就“方法”本身而言,不仅没有任何不同,而且正是作为目标指向对其“方法”意义的贯彻和印证。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释义都必然带来叙事的融贯,正如前文中指出的那样,尽管同样是从作为“方法”的“实用主义准则”出发,但以苏珊·哈克、雷谢尔、莫恩斯和布鲁克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叙事者却基于其“具体应用及其结果”中所呈现的不同风格和立场区分了不同的实用主义“版本”,并因为对之的叙事归属而导致了叙事谱系的“断裂”和“分野”。与前述“学说”维度相比,虽然这种“方法”释义并没有过多的集中于作为内容的“具体理论后果”,而是更关注作为“方法”的实用主义本身的风格,但仍然没有逃脱“具体方法”的限制和囿困,因为,这种“风格和版本”的不同界定仍然是以其“具体应用”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所呈现出的“风格和立场”为依据的,换句话说,尽管都不是直接针对结果而是指向“方法”本身的,但也都是以“结果”对“方法”的反向影响和印证为根据做出的。譬如,之所以对皮尔士和詹姆斯做出“实在论——反实在论”“客观——主观”的区别,就是因为皮尔士在对“概念”意义的讨论中更关注实践效果和最后结果的“理性一般”,并因此表现出了更强的“实在论和客观”风格,而詹姆斯则在讨论“真理”问题时因为更强调“经验当下”“特殊真理”“兑现价值”而凸显了更强的“反实在论和主观”倾向。然而,“实用主义准则”却不仅仅是一种具体方法,也是一种方法论或者元方法,作为方法论或者元方法,“实用主义准则”指向任何对象,但又不针对任何一种特定对象,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具体(后果)意义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差异只会在“具体方法”层面出现,而在方法论或者元方法层面,则始终保持探究(实验)精神的统一,因为,制造这些后果差异的具体方法都出于并最终归于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而方法论原则又通过将自身的统一异化为差异而呈现和完善自身。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实在论、唯名论”风格只是“具体方法”应用语境及其后果中形成并持有的立场和风格,并不指向“方法论”,或者说,在“方法论”意义上并不构成差异并导致叙事的断裂和分野。因为,皮尔士的“实在”本身就不是绝对的本体论概念,真理与实在都是假设性的,“实在是一个当我们发现一个不是在的东西、一个虚幻的东西时,才会第一次产生出来的概念。……实在的东西就是信息好推理或迟或早终将导致的东西,……它没有确定的限度,只有确定的知识的增长”①C.S.Peirce,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Vol.5,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para.311.,真理也“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不多不少就是遵循该方法将引导我们达至的最后结果”②Ibid.,para.553.;而詹姆斯基于唯名论倾向对具体真理和经验的强调,也并不必然导致与皮尔士相反的“主观主义”甚至“唯我论”真理观,因为真理“对眼前一切经验是方便的,未必对后来的一切经验能同样的令人满意”③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第114 页。。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实用主义准则”从一开始就兼具“具体方法”和“方法论或者元方法”两种内涵,并通过两者之间的持续变奏和互动——前者是后者指向特定对象时的具体应用和实践展开,同时又通过这一过程及其理论后果完成对后者内涵的诠释、充实和完善——主导并贯穿了整个古典实用主义的叙事进程。不仅保证了古典实用主义整体叙事的连续和融贯,也作为线索选择承诺了其谱系的统一建构。在这种视域下,就作为“具体方法”的“实用主义准则”而言,如果说皮尔士的“概念意义的澄清方法”是对其作为一种“具体方法”的首次表述和应用,那么,威廉·詹姆斯则进一步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到“真理”和“宗教”,而杜威和米德则将其扩展到包括教育、民主、社会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问题讨论。不仅完成了其应用范围的极致拓展,也产生了包括意义理论、真理论、宗教理论、民主和教育理论等在内的诸多具体理论叙事,尽管因为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导致了实用主义的“版本”和“风格”差异以及叙事的“断裂”和“分野”,但都作为叙事主体成就了古典实用主义“理论内容”上的辉煌;另一方面,在“实用主义准则”的“方法论”意义上,实际展开的每一种“具体方法”的应用及其理论后果,又是对其“方法论”内涵的反哺式诠释和充实,并随着应用对象范围的持续拓展实现最后的升华和完善。如果说在皮尔士那里,把“实用主义准则”作为“具体方法”应用于“概念”将其方法论内涵限制在“语言转向”语境并更多体现在认识论层面的话,那么,詹姆斯扩大范围的应用及其“彻底经验主义”语境中对“经验”的纯粹化和本体论归置则将其提升至“存在论”层面,而杜威对其全方位的应用及其从生命与环境的交互出发赋予的“生存论”意蕴则促成了其方法论内涵的最后升华和完善,并因此将古典实用主义的“方法旨向”推向了巅峰。至此,古典实用主义的众多叙事,不仅被作为“具体应用”的理论后果纳入了“实用主义准则”的“具体方法”内涵的展开,进而在消解差异、冲突、断裂和分野基础上统摄了古典实用主义理论内容的融贯生成,而且,也被当作反哺式诠释的素材和载体纳入了“实用主义准则”的“方法论”内涵的充实,进而在其作为实用主义方法在哲学上的核心地位的强化中确认了古典实用主义的“方法旨向”。事实上,正是也只有在“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的统一意义上完成其整体叙事的合理归置和描述,才能保证古典实用主义谱系的成功建构和融贯统一。
四、结语
无论是作为实用主义的诞生标识,还是作为实用主义方法在哲学上的核心,对“实用主义准则”及其内涵的准确解读,都毫无疑问构成了实用主义的元问题,并作为出发点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所有关于实用主义的讨论和话语,尤其是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建构和“实用主义”自身特质和身份的厘定。在这种意义上,前文对“实用主义准则”“方法论”内涵的论证和确认,不仅在“方法”基础上补足了其释义维度和内涵的完整性,也作为谱系线索,把古典实用主义的所有叙事都作为“具体方法”及其应用的理论后果纳入了两种内涵的变奏和互动中,并最终通过把“具体方法”的差异和冲突消融于“方法论”的一以贯之而承诺了古典实用主义谱系的统一和融贯。更为重要的,“方法论”维度及其内涵的发现和确认,也在两种释义维度上实现了对实用主义何以成为并被冠以“古典”的创造性回答和重释,即:“古典”并不仅仅是作为“具体方法”的应用拓展及其理论成果的“内容”辉煌,而更是其“方法论”内涵的最终完善和确认所标识的“方法”巅峰,是“具体方法”的展开和对“方法论”内涵的反哺式充实的双重统一和实现。因为,所有实用主义叙事都源出于“古典”,所以,对“古典”的这种谱系厘定和意蕴重释,不仅会为“古典实用主义”自身以及诸多古典叙事的“实用主义”身份判定提供基本依据,也将为实用主义的“新——老”之分和实用主义“后古典”叙事的“新实用主义”身份归属提供明确界标(因为论题所限,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专述)。而在“两种内涵的变奏和互动”中对实用主义的“古典”谱系和意蕴做出“融贯统一”承诺的“实用主义准则”,也必将成为“新实用主义”乃至整个实用主义百年叙事谱系建构的线索首选,并因此在持续扩展的“新”视域和“新”面向中进一步放大和凸显其谱系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