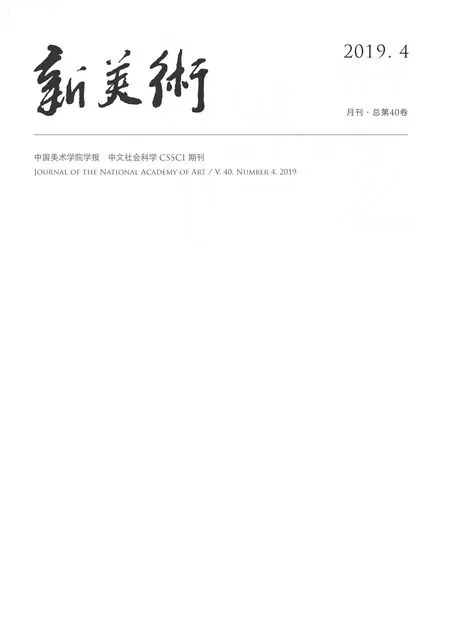“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研究范畴与基本方法*
祖 宇
“城,所以盛民也”1许慎著,[宋]徐铉杨校,《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城为人造,人居城内。城市的历史与人类文明的言体历史相交蔓生,人类文明的痕迹,造就了其所在之城的文明景观,随之诞生的文明知识系统中的各类支脉,也大多可以与人类言体所存在的实体城市万象一一言动对应。
当下,在面对“城市”的系列研究中,“城市美学”成为一个热词,尤其在美术学和设计学界,被人们反复提及。深挖“城市美学”概念本质和细分层次,进行独立专项研究,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方向。因此,在城市美学的研究范围中,本文言题“城市版面文本美学”处于全系统的“毛细”层级内,“版面文本”在本学科的释义中,并非传统的书籍编辑版面文本,而是以图文构建为基础的各级视觉版面系统,它以平面媒介的形态存在。其结构包含图像、文本和构成关系形态,这些无处不在的“图文景观”如空气般包围着城市人口的视觉环境,陪伴每个城市人的“视觉一生”。因此,纸质印刷、屏幕影像、空间图文都是“城市版面文本”的存在形式,它是无处不在的视觉层级。该层级是人类对一个城市信息、美学认知的基础依托物,在认知顺序中,它几乎占据了视觉认知的全部信息流量。当我们旅行抵达一个陌生城市时,亦或离开它时,任何来自该地的图文材料,哪怕是一张小小车票,都会勾连出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初步认知或片段记忆。
在中国大陆最近四十年的高速建设中,城市的景观,随着建筑形式语言的乏善而日益趋同,“豆腐块高楼”与“高架桥”正在格式化着我们记忆中的水乡与边塞。杭州与乌鲁木齐的现代普通民居,从基本形态到基础功能,几乎没有区别。而判断一张街景照片的拍摄位置时,我们往往需要通过照片中的店招门头、汽车牌照、广告形态来寻求信息。除去这些线索,判断推导便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城市美学研究中,“版面文本美”与“图文形态”的研究与实践,便成为推进城市美学有机更新、避免“千城一面”美学灾难的有效方法。对比相对恒久固化的城市景观美、建筑美而言,“版面文本美”的实施与更新成本、成效与公共美育效能,都更具备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
“城市版面文本”的构成元素,其言体是“图”“文”。图文之外,色彩、材质、运动方式等构成了版面文本的其余层次,以上元素,通过人类自发的适应性创造组合,便构成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的视觉基因。比如拉萨与香港,两个城市所拥有的任何信息平面设计,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引起这些差异的基础动因常常被人们简单归纳为“文化”二字,但究其本质,研究者需要从城市个案研究入手,以点带面逐步展开。最终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和代表的个案,来阐析和构建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理论模型,勾勒其发展的脉络,体现其理论的系统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
就像任何其他层面的城市美学一样,研究“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论,同样首先要明确其研究的范畴和方法。因此,笔者根据“城市美学”的研究范畴,提出“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研究范畴包括构成城市信息系统的图像、文字、版面的美学图谱。它的知识体系来源大致可以包括:1.人类学[Anthropology];2.历史学[History];3.地志学[Regional Geography];4.设计学 [Design];5.图像学 [Iconology];6.汉语文字学[Chinese Philology];7.美学[Aesthetic],七类言要的知识体系。以下分别阐述其结构方位与基本作用:
1.人类学、地志学和历史学形成本研究理论的言体空间与时间坐标,分别对应城市言体、地方描述和时间坐标。可以形成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研究的时空定位。
2.设计学中,本研究以视觉传达设计为言,结合信息设计,材料研究等,形成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研究言体方法。
3.图像学与汉语文字学是图、文关系的研究物质对象,构成本研究的实体元素和民族基因。
4.美学则是构成本研究的基础理论依据。
以上范畴分析与七类知识系统的阐释与群落,可以基本描绘出“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研究范畴与大致形态。也可以看出“城市版面文本美学”与其他城市美学研究的明显差异。
2017—2018年,笔者团队尝试以杭州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版面文本分析、印刷史梳理、版面文本范式研究等系列工作,建构“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研究与实施方法。版面文本的美学复兴,应等同于自然风景、建筑景观和室内环境的美学复兴。选择杭州作为案例的原因,是由于自南宋迁都以来,这座城市所遗存的版面与文本审美造诣,以及这些图文审美的沿革演化,均表现了一座中国典型传统城市的美学品格构建与民众美育教化之间相互促进的过程。历史上,在杭州及周边地区,拥有不少完整的历史事件及视觉遗迹可供研究。杭州地志学历史上的版面文本美学高峰包括:南宋时期,以“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为代表的宋代雕版印刷版面文本审美高峰2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对版面文本美学的推广影响巨大,据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考有三十二种,据肖东发著,《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则列出陈家书籍铺刻书目录有《江文通集》十卷、《常建诗集》二卷、《韦苏州集》十卷、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孟东野诗集》十卷、《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浣花集》十卷、《甲乙集》十卷、《王建集》十卷、《唐求诗集》一卷等,凡十九种。、以“院体画”为代表的绘画图像审美高峰。它们影响着元、明、清刊刻本直至近20世纪初,以西泠印社金石团体为代表的金石书画、印刷版本的审美高峰亦继承了南宋的版面文本之美,例如:20世纪初,西泠印社创始人丁辅之与其弟丁三在创制了以宋元刊本为原型蓝本的“聚珍仿宋体”后蒙中华书局陆费逵之助,丁辅之于沪上立“中华书局聚珍仿宋部”,排印《四部备要》等重要典籍,聚珍仿宋体因此得以光大,尤其版面文本之美,极获盛赞,该字体承宋版之美,又为现代仿宋体之始,为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研究之重要案例。其后又有擅长“馆阁体”的杭州萧山籍书法家高云塍所书写的“楷书”书体,也因1934年蒋介石发表的《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之影响。曾任杭州国立艺专教授的郑午昌以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经理的身份,回应要义,并递交“呈请”给蒋介石,表明了“正楷”字体所构成的版面文本之于中国国民审美与精神继承的重要意义:
“……数千年来,人民书写相沿成习。即在印刷方面讲,考诸宋元古籍,凡世家刻本,其精美者,类用正楷字体,请当时名手书刻而成。元明以来,世家精刻仍多用正楷书体。惟一般俗工,不通书法,妄自刻鹄,辗转谬误,卒成结构死板、毫无生意、似隶非隶、似楷非楷之一体,即现在所谓‘老宋体’,日人亦谓之‘明体’,遽成为我国雕版印刷上所专用之字体,致我国文字书写之体与印刷之体截然分离,读非所用,用非所读……于我国文化事业之统治,深具宏谋远虑。我国书体,尤其正楷体,无论南北,凡是中华民族几无不重而习之。此种文字统一的精神 ,影响于政治上之统一甚大。文字既统一,民族精神即赖以维系而不致涣散。故我国虽曾亡于胡元,亡于满清,而因文字之统一不变,故至今仍为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土。近世,外来文字日多,国人多有不重 视我国固有之字矣。为普通印刷工具之老宋体,又为日人所制,与日人自用者同体,谬种流传,感官混摇,其有危害于我国文化生命及民族精神之前途,宁可设想……”3周博撰,〈字体家国-汉文正楷与现代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载《美术研究》,2013年第1期,第16页。
由此可见,版面文本的美学意义,是高于信息传播的一个“视觉教化”层次,它可以表述与传递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美学水准和价值观,上述与杭州有各类层级关系的案例,为城市或地区研究提供了在版面文本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的典型样本。因此,“城市版面文本美学”可以作为一类独立研究进行开展。在中国具备图像与文字研究基础的区域与城市中,杭州具备相对的典型性与可操作性,前人偶有涉及研究,但成果不多。通过杭州“版面文本美学”的研究,发掘历史上数个杭州版面文本美学的高峰和成因及其地方志的思潮变化、详细比较南宋刊刻本的审美趣味与近代金属活字的公众视觉教化效应等,进一步反思当下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建构规律,打破图像与文字单一领域研究的传统界限,探索出不同于单纯人类学研究、图像研究、地方志研究或视觉传达设计研究的新途经。
佩夫斯纳[Nicolaus Pevsner,1902—1983]将类型研究引入设计史,使得设计史的研究视野大大开阔,因此,借鉴该研究方法,笔者根据视觉传达设计中对于“城市版面文本”相关的研究领域与交叉点进行比对,以界定其言要的研究范畴,简述如下:
1.中文字体设计研究
2.西文字体设计研究
3.版式设计研究
4.图形设计研究
5.图像研究
6.印刷工艺研究
7.商业摄影研究
8.书籍设计研究
9.信息设计研究
10.展示设计研究
11.公共标识系统设计研究
将以上研究对象,与前文所述的七类学科(1.人类学、2.历史学、3.地志学、4.设计学、5.图像学、6.汉语文字学、7.美学)进行交叉研究,构成了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研究基本方法与框架。
“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整体构建过程,是民众对公共环境中的“版面文本美学”中美学教化的集体反哺,“城市版面文本美学”的产生,是受众与传播言体的双向行为。其研究与推广,可以突破审美对公众视觉教化的惯性思维,即审美的视觉教化不仅仅局限于博物馆、美术馆的局部作用,亦不局限于单体美术作品的各类流通端口的限制。城市版面文本美学可以延伸美术教育的普世意义,引导大众的城市美学观念精细化,使城市或地区的审美气质和公众审美水准得到提升,甚至固化成为一种国家文明的视觉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