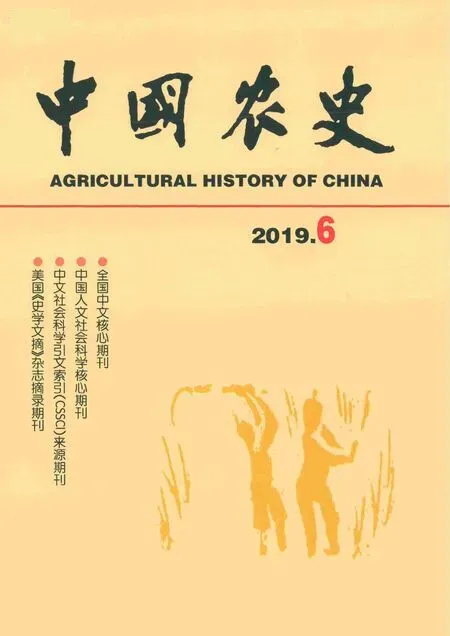丝路沿线出土粟特文文书研究述要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20)
粟特文是中古时期伊朗使用的文字之一,源于阿拉美(Ahrimans)草书,是一种不注明元音的音节文字,有19 个辅音字母、3 个特殊字母(β、δ、γ)。用这种文字表达的粟特语(Sogdian),曾一度是中亚等地使用的语言①关于粟特文的介绍,可参阅[法]高梯奥(Robert Gauthiot)著,冯承钧译:《窣利语字母之研究》,《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 年第4 期(后收入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 年。原刊见《巴黎亚洲协会会刊》第2 类第17 册);[日]白鸟库吉著,钱稻孙译:《粟特国考》,《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 年第4 期(后收入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商务印书馆,1940 年,第397-109 页。原刊见《东洋学报》第14 卷第4号,1924 年);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 年;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龚方震:《粟特文》,载傅懋栗主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4-62页。。操粟特语、使用粟特文的粟特人,他们善于经商,其足迹遍布古代丝路沿线,近年在蒙古发现的碑刻①该碑早在1956年就由蒙古考古学者朶尔祖仁发掘出来。相关研究可分别参阅:[苏]S.G.Kljaštornyi(克里亚什托内尔)and V.A.Livišc(里夫什茨).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Acta Orientala Academie Scientiarum Hungaricae.26/1(《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6 卷第1 期),1972.PP.69-102.(汉译文见龚方震译《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蒙古布古特碑中的突厥和粟特人》,《世界民族》1987年第5期;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44-358页)。,中国新疆、甘肃敦煌出土的粟特文献以及内地发现的唐总章二年(669)史诃耽墓(宁夏固原南郊,1981)②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 年。亦可参阅石见清裕《ソグド人漢文墓誌訳注(2)固原出土「史訶耽夫妻墓誌」(唐·咸亨元年)》,《史滴》2005年第27卷,第153-183页。、隋大业六年(610)史射勿墓(宁夏固原小马庄村,1987)③罗丰、郑克祥、耿志强:《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隋开皇二十年(592)虞弘墓(山西太原市王郭村,1999)④张庆捷、畅红霞、张兴民、李爱国:《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陕西西安市炕底寨村,2000)⑤尹申平、邢福来、李明等:《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 年第6 期。尹申平、邢福来、李明:《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第4-26页。、北周大象元年(579)史君墓(陕西西安市井上村,2003)⑥杨军凯、孙武、刘天运等:《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陕西西安市炕底寨村,2004)⑦寇小石、胡安林、王保平等:《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天水石马坪石棺床(1982,北周至隋)⑧张卉英:《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关于石棺床的时间,邢福来先生指出“对墓葬出土实物进行了观察,石屏风图案中侧面者明显为胡人,且构图与安伽墓有明显相似之处,墓葬中出土的铜镜、瓷罐等具有北周至隋初的风格,另外天水地处西域通向长安的要道,所以墓主人属昭武九姓粟特人也不无可能,埋葬年代为北周至隋”。见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随葬用围屏石榻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增刊《汉唐考古》。据天水市文化馆退休人员即拍摄当时图片的牟天生先生介绍,“石棺床搬来以后,就在我们文物室的贮藏室放下了,放了那么长时间,大概是两个来月,就开始整理。弄着出来在院子里用水冲了一下,把那些泥巴就冲掉了。实际上,那个石棺床上整个是贴金的,由于时间长了干的翘起来以后,用水一冲,整个金箔就顺水都流了。好多天了,在外面看去,一下雨地下都有金箔。”在此感谢天水师范学院雍际春教授分享石棺床高清图片,相关介绍亦可参阅雍际春《天水出土石棺床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甘肃日报》2018年1月2日第9版。等诸多墓葬,以及在中国西南⑨姚崇新:《中古时期巴蜀地区的粟特人踪迹》,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182页。姚崇新:《中古时期西南地区的粟特、波斯人踪迹——兼论西南与印度、西亚的古代交通》、《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火祆教遗痕》,皆参阅姚崇新《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79-348页。胡耀飞《五代蜀地粟特系沙陀人考》,《第八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论文集》2012 年(收入刘亚娟主编《燕园史学》第21 期,北京大学历史系,2012 年5 月)。李瑞哲:《粟特人在西南地区的活动追踪》,《西部考古》2019 年第1 期。感谢刘文锁先生、刘勇兄分享传递电子版。、东南⑩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第42-53页。另见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8-152页。此文中还提到了日本吉田丰、法国葛乐耐等国外学者对南方粟特人的相关研究。另见姚潇鸫《东晋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补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近年西北大学刘勇兄也撰文对此有论述,见刘勇《唐〈安玄朗墓志〉述考》,《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4期;刘勇,陈曦《唐五代岭南西部粟特人踪迹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发现的粟特遗迹,都是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活动的迹象11目前关于粟特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辛姆斯·威廉姆斯、吉田丰、荣新江等,而中国的粟特研究主要集中在: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 年;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荣新江、罗丰《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当然,还有很多研究粟特的学者及其论著,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这些粟特文献主要收藏在德国(发现最早、数量最多,学者研究最为集中)、英国(收藏有敦煌发现的8封粟特文古信札)、法国(主要是粟特文佛典)、俄国(包括穆格山粟特文书,还有在我国敦煌、吐鲁番收集的残片)、日本(西严寺橘瑞超收藏品),近年在中国各地博物馆分藏的粟特人墓葬品,也显著成为粟特文献的一部分。①参阅:[英]西蒙斯·威廉斯著,田卫疆译《粟特文书收藏情况简介》,《民族译丛》1984年第4期(原文发表在《亚洲杂志》1981年第269卷)。库尔班·外力《吐鲁番出土公元五世纪的古突厥语木牌》,《文物》1981年第1期。伊斯拉菲尔·玉苏甫《新疆新发现的古文献及其研究》,《新疆文物》1999 年第3、4 期(合)。[日]吉田丰著,山本孝子译《有关新出的粟特文资料——新手书记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兼介绍日本西严寺橘资料》,《敦煌学辑刊》2010 年第3 期。刘文锁《新疆古代语言文字资料的发现与整理》,《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1期。
从目前出土的文物遗迹等来看,粟特文有书简、羊皮、钱币、印章、碑刻、壁画等多种载体,其中粟特铭文疑似最早,时间约在公元1 世纪;1907 年英人斯坦因在中国敦煌发现的8 封古信札,被认为是较早的粟特文书,而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比斯坦因更早发现粟特文,二人于1902-1905 年在中国吐鲁番连年发掘,获得多种粟特文经典;粟特文的消失约在11世纪,即是说目前发现的粟特文时间范围大致在公元1-11世纪②关于粟特文消失的时间,学术界持一致意见。但对最早的粟特铭文时间,黄振华先生认为是公元1世纪(《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第29页),杨富学老师认为属于2-3世纪(《粟特文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与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8页),在此笔者持公元1世纪说。。根据学者的研究,粟特文的书写曾受过景教文字、汉文字的影响,如字母中间由原来的分写变为连写,由从左到右的横写变为由上向下的坚写。随后,粟特文又促成了回鹘文的形成,间接对契丹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的形成有影响③[法]高梯奥(Robert Gauthiot)著,冯承钧译:《窣利语字母之研究》,《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 年第4 期(后收入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原刊见《巴黎亚洲协会会刊》第2类第17册)。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年。徐文堪:《粟特文明与华夏文化》,《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第1期。徐文堪:《略谈伊朗语文及波斯语在中国的传播》,《文汇学人》2016年1月29日。。如果说粟特人主要居住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话,那么粟特文被发现的地点我们不妨用“本土”和“外地”来表述,“本土”主要是指中亚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以东60 公里、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东约20 公里的穆格山城堡遗址,1932年苏联人弗列依曼(A.A.Freiman/Фрей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 Арнольдович,另有弗赖曼、弗莱曼、傅瑞曼等汉译名)在这里发现了大批粟特文献,如银币、棉织品、器皿、皮革、印记、纸简等,其中97份年代属于8世纪的粟特文书简成了以后学界争相研究的焦点④黄振华先生在《粟特文及其文献》中称“约80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第31页);马小鹤先生在《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中称“约90 件文书”(《中亚学刊》第3 辑,中华书局,1990 年,第109 页。亦可见马小鹤《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367 页);张小贵、庞晓林在《穆格山粟特文婚约译注》中称92件(《唐宋历史评论》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最近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家博物馆保护区首席专家格尔鲁克·拉克马托娃(Rakhmatova Gulrukh)撰文《粟特语书写的丝路历史》(《光明日报》2019年5月10日)称97份。拙文以时间最近者为准。,除了穆格山(Михаил),还在喷赤干(pnčykn´δh//Panjikent,即片治肯特)、阿克伯申、阿弗拉西亚布(Афанасия)等中亚其他地方发现了粟特钱币、粟特文印章、壁画等。在“外地”发现的粟特文文献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新疆和敦煌,还有蒙古杭爱省呼尼河流域的布古特⑤[苏]S.G.Kljaštornyi(克里亚什托内尔)and V.A.Livišc(里夫什茨),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Acta Orientala Academie Scientiarum Hungaricae.26/1(《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6 卷第1 期),1972.(汉译文见龚方震译《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5-53页)[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蒙古布古特碑中的突厥和粟特人》,《世界民族》1987年第5期。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后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以及日本的西严寺橘瑞超藏品⑥[日]吉田丰著,山本孝子译:《有关新出的粟特文资料——新手书记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兼介绍日本西严寺橘资料》,《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实际采自中国),其中以1907 年英人斯坦因在中国敦煌以西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8 封粟特文古信札最为出名,可以将其与穆格山发现的粟特文书称为粟特研究的“两朵金花”,然在中国这朵“金花”的年代归属上,学界主要围绕第二号书信的内容展开讨论,后面再作介绍。
1932年发现于穆格山的粟特文书及其他文献,主要由当时的苏联学者弗列依曼(A.A.Freiman)及其学生里夫什茨(V.A.Livshits/Лившиц Владимир Аронович,另有李夫什茨、利维希斯特、列夫斯基、利夫希茨等汉译名),还有波哥留波夫(M.N.Bogolyubov/Боголюб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斯米尔诺娃(O.I.Smirnova)等人作了考释与研究。穆格山文书主要是围绕一位粟特领主迪瓦什梯奇的身份展开,它透露的信息使得学者们从阿拉伯文献或者汉文文献来作证。众所周知,粟特在历史上没有建立统一的强国,繁盛时期顶多是政权林立,像我们熟知的康国(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米国(片治肯特)①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7年。、石国(塔什干)、拔汗那(费尔干纳)等等,中国史书对其最早的称呼是“粟弋”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粟弋》,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页。(这个词是被德国学者夏德根据“Sogdiana”对音发现的,后来白鸟库吉、伯希和等人又进行了详细的考证③参阅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魏书》始称“粟特”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玄奘称其为“窣利”⑤[唐]玄奘、辩机撰,范祥雍汇校:《大唐西域记汇校》卷1《窣利地区总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页。(sūlik)。粟特先后被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唐、萨珊波斯、阿拉伯等政权统辖⑥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因此,文书对研究公元8 世纪左右的粟特及其与阿拉伯、唐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对穆格山文书的发现及其概况,里夫什茨等人于1934 年作了介绍⑦А.А.Фрейман,Опись рукопис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извлеченных из развалин здания на горе Муг в Захматабадском районе Таджикской ССР около селения Хайрабд и собранных Таджикистанской баз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Согди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Л.,1934,стр.33-51.另参阅Grégoire Frumkin.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Leiden/Köln:E.J.Brill,1970,p.71.转自张小贵、庞晓林《穆格山粟特文婚约译注》,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之后他们相继出版了《粟特文论集》(弗列依曼著,1934)、《穆格山所出粟特文书》(共三册:第一册为弗列依曼著《穆格山文书的说明、刊布和研究》,1962;第二册为里夫什茨著《法律文书和书信》,1962;第三册为波哥留波夫、斯米尔诺娃著《经济文书》,1963)、《穆格山文书》(影印原件,1964)等⑧参阅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9 期第31 页。《粟特文论集》:Sogdii,Skii Sbarnik,Sbarnik statei pamyataikax Sogdiiskogo yazyka i kultury naidennyxna Gore Mug v Tadjikskoi USSR,Leningrad,1934《.穆格 山 所 出 粟 特 文 书》第2 册:Лившиц Владимир Аронович,Согдий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горы Муг.Чтение,перевод,комментарии.Выпуск II(Юрид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письма),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2 г.。英国学者辛姆斯·威廉姆斯在其出版的《伊朗碑铭丛刊》一书中收入了苏联学者里夫什茨的一些英文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大有裨益⑨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Tom Stableford,ed.By Nicholas Sims-William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2015,pp.17-37.。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在其老师白鸟库吉的指导下,亦撰文介绍了苏联学者对穆格山文书的初步研究情况,并发表在《东洋学报》,该文后被万斯年汉译发表在《大公报》上⑩[日]岩佐精一郎《唐代ソグド城塞の发掘と出土文书》,《东洋学报》第22 卷第3 号,1935 年,第451-461 页。汉译文见万斯年《唐代粟特城塞之发掘及其出土文书》,《大公报·图书副刊》1936年第120期,后收入万斯年编译《唐代文献丛考》,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140-162页(该书1957年再版)。。跟本文有关的是,穆格山文书中有一份借券文书,虽然裂为二片,但提到了“同保人”字样,且保人为多个,这对粟特文契约文书中的担保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马小鹤先生《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结合传世文献,对穆格山文书中涉及的重要人物迪瓦什梯奇的身份从十个方面详细有力地进行了论述①马小鹤:《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后收入氏著《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7-408页。。值得注意的是,穆格山文书中有十份关于迪瓦什梯奇纪年的文书,三份汉文文书提到了交城守捉、大斗守捉和伍涧,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法国学者葛乐耐(Frantz Grenet,另有格瑞纳、瑞和纳特等汉译名)、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利用穆格山文书,对阿拉伯帝国征服片治肯特之前的历史作了研究②[法]Frantz Grenet and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8,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Kamakura,2002,pp.155-196.。龚方震先生汉译了克里亚什托尔内和里夫什茨关于蒙古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碑铭的考证③[苏]克里亚什托内尔、里夫什茨著,龚方震译:《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原文见:S.G.Kljaštornyi and V.A.Livišc.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Acta Orientala Academie Scientiarum Hungaricae.26/1(《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6卷第1期),1972.pp.69-102.,徐文堪先生对苏联学者里夫什茨的生平及其研究成果作了评介④徐文堪:《悼念当代最杰出的粟特语专家》,《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6月30日。。在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中,有一份编号为Nov.3的婚约文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篇幅最长的粟特文法律文书,张小贵先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该文书又作了转写、汉译与注释,文末附有四张相关图片⑤张小贵、庞晓林:《穆格山粟特文婚约译注》,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3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另外笔者在微信上看到一篇题为《八世纪穆格山粟特语婚约》的文章对该婚约文书作了翻译发表在豆瓣日记(2019年5月11日)作者名为“卡丹”,但不知即张湛真实姓名。张兄后来还以《粟特语古信札1-5》为题,对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古粟特文信札作了译释,仍发表在其豆瓣日记上。。德国学者德金(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女士利用粟特法律文书研究了侨居地的粟特女性⑥[德]Desmong Durkin-Meisterernst,Sogdian Women in the Diaspora.汉译文见:德金著,胡晓丹译,荣新江校《侨居地的粟特女性》,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81-95页。。关于穆格山出土的这份婚约文书,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文书中的一个人名尼丹(Niδan),它是否与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书、塔里木盆地于阗遗址发现的佉卢文书中的人名为一人?而后两者文书的人名,据林梅村先生在《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指出,敦煌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书信的作者Nanai Vandai 和于阗佉卢文书(Kh.661)中一位粟特人同名同姓。这是英国学者布腊夫(J.Brough)首先发现的”⑦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接着他从四个方面作了论证,在论证之前,林先生在该文中还提及:“据亨宁和哈尔玛塔的解读,写信人Nanai Vandai 乃是粟特驻华商团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这三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关联的话,那么这对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古书信的断代会有重新的认识。
1907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了8封粟特文古书信,引起了学界的轰动,因第二封书信相较其他书信内容完整,故成为众多学者参与讨论的焦点。这封信的大概内容是:一位叫Nanai Vandak的写信人,向远在撒马尔罕的同胞描述商业活动的情况(似乎不容乐观),信中提到了中国内地的敦煌、肃州(酒泉)、姑臧(武威)、金城(兰州)、洛阳(有争议)和邺城等,还提到了当时遭受战争的情况。该书信应该是运送途中丢失的。对于信札的年代,学者们探讨较多,不过有两种观点是以纸质鉴定得出的:第一种是英国斯坦因、匈牙利哈尔玛达等人根据维斯尼(J.von Wiesner,另有维斯勒汉译名)“古信札所用之纸揭示了纸浆改革的早期阶段”的结论,提出了“公元2 世纪”说(斯坦因认为公元105—137/153 年之间,哈尔玛塔认为公元196-197 年);第二种观点是法国伯希和、英国亨宁等人以法国学者戴仁(Jean-Pierre Drege)在对古信札所用纸做出技术鉴定后提出的,即“公元4世纪”(伯希和提出信文有“洛阳被毁灭”的内容,亨宁在1948 年认为书信年代在公元312-313 年)①关于纸质鉴定的内容,参阅: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法]格瑞纳、[英]辛姆斯·威廉姆斯著,王平先译《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紧接着,藤枝晃②[日]藤枝晃著,翟德芳、孙晓琳译:《敦煌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语文书》,载氏著《汉字的文化史》,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70-71页。作者虽短短数语,但对4世纪说作了驳议,从纸张判断应为6世纪左右。、榎一雄③[日]榎一雄:《西方人记录中所见的敦煌》,《敦煌讲座》第一卷《敦煌的自然和现状》第四章,(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 年。作者将哈尔玛塔关于粟特文第二号信札的译文全部译为日文发表。参阅: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88页;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5年第7期,第18页。、森安孝夫④[日]森安孝夫著,陈俊谋摘译:《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史研究之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4 期。原载日本《史学杂志》第89编第10号,1980年。等人据纸质年代提出了“公元6 世纪”说。中国的大多学者亦结合传世史料作了不出于以上三种年代的推论,唯李志敏先生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后晋天福二年(937)”的观点,并做了断代考论⑤李志敏:《有关地名研究与斯坦因所获粟特信札断代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据黄先生介绍,英国学者考利(Arthur Ernest Cowley)和法国学者高梯奥(Robert Gauthiot,另有哥底奥、郭提奥、戈蒂奥、高修等汉译名)最先解读了该粟特书信,分别撰文《新疆所出另一种不认识的语言》《斯坦因—考利发表的未识文字语言考》,皆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1)⑥转自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9 期第32 页。其中,斯坦因认为书信年代为105—137 或153 年之间。见[英]斯坦因著,赵燕、谢仲礼、秦立彦译:《在烽燧T.Ⅻ.a 发现的纸质粟特文书》,载氏著《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236-250 页。又见[英]斯坦因《塞林迪亚》卷二,牛津,1921年,第673-752 页(Serindia Ⅱ: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and Western most of China.Oxford 1921),转自[法]格瑞纳、[英]辛姆斯·威廉姆斯著,王平先译《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9 年第1期,第118页。。参与书信年代讨论的学者主要有:国外学者诸如德国莱赫尔特(Hans Reichelt)⑦[德]Hans Reichelt(莱赫尔特),Die Soghdischen Handschriftenreste des Britischen Museums.Ⅱ.Teil:Die nicht buddhistischen Texte und Nachtrag zu den buddhistischen Texten.Heidelberg:Carl Winters University tsbuchhandlung.1931.(《英国博物馆藏粟特文写本残页》)作者初步解读了书信。转自麦超美《粟特文古信札的断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四辑,2008年,第236页。、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⑧伯希和撰文评述莱赫尔特文章,指出第二封书信有洛阳被毁之说,《通报》1931 年第28 期。参阅: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第32页;[法]格瑞纳、[英]辛姆斯·威廉姆斯著,王平先译:《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0、118页。、英国亨宁(W.B.Henning,另有恒宁、汉宁、赫宁等汉译名)⑨[英]W.B.Henning(亨宁),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Source: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Cambridge University of London,Vol.11,No.4,1946,pp.713-740.[英]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Source: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Cambridge University of London,vol 12,No.3/4,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Presented to Lionel David Barnett by His Colleagues,Past and Present,1948,pp.601-615.(《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12 卷第3-4 期,1948 年)作者译释了第二封粟特信件的一部分,并推翻前人成说,认为书信年代为312-313年。、匈牙利哈尔玛塔(János Harmatta)⑩[匈牙利]János Harmatta(哈尔玛塔),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1979,pp.153-165.(《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的粟特文史料》,《前伊斯兰中亚史料序说》,布达佩斯,1979 年。同时以《一件丝绸之路史的新原始材料》为题发表在《经济史年鉴》1972年第2期)转自[法]格瑞纳、[英]辛姆斯·威廉姆斯著,王平先译《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9 年第1 期,第118 页。哈尔玛塔著,朱新译:《粟特文古信札年代的考古学证明》,《新疆文物》译文专刊,1992 年(译自哈尔玛塔主编《伊斯兰时代以前中亚史料导论》,布达佩斯,1979 年)。他认为写信的年代为196-197年。、法国葛乐耐(F.Grenent)、英国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①[法]格瑞纳、[英]辛姆斯·威廉姆斯著,王平先译:《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9 年第1 期(原文见Grenet and Sim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1987,p.109)。[英]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著,毕波译:《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西北民族论丛》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32-50 页(原文见A.Cadonna、L.Lanciotti 编《中国与伊朗:从亚历山大到唐代研究论集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佛罗伦萨,1996 年,第45-67 页)。[法]Frantz Grenet(葛乐耐)、[英]Nicholas Sims-Williams、[法]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魏义天),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Ⅴ.Source: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New Series,Vol,12,Alexander’s Legacy in the East Studies in Honor of Paul Bernard,1998,pp.91-104.[英]辛姆斯·威廉姆斯:《粟特文古信札Ⅱ号》,2001 年,第269-273 页(原文见Nicholas Sims-Williams,The Sogdian Ancient Ⅱ.Schmidt,M.G.and Bisang,W.(ed.),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Historia,Pluralitas,Universitas.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Geburtstag am 4.Dezember 2001.Trier: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2001,pp.269-273)。[英]辛姆斯·威廉姆斯著,Emma Wu 译:《粟特文古信札新刊本的进展》,载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中华书局,2005年,第72-87页(原文见Nicholas Sims-Williams,Towards a new edition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Ancient Letter Ⅰ.De La Vaissière,étienne et Trombert,éric.(ed.),Les Sogdian en Chine.Paris:école fran aise d’Extréme-Orient,2005.)。[法]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粟特商人史》(Sogdian Traders:A History,Leiden,200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美国安妮特·L·朱丽安娜(Annette L.Juliano)②[美]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茉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Ⅱ)号》,《考古与文物》2003 年第5 期。原载《僧侣、商人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珍宝》(Monks and Merchants: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2001年。作者认同葛乐耐、辛姆斯·威廉姆斯公元313—314年之说。、苏联里夫什茨③[俄]Vladimir Livshits,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Ⅰ,Ⅲ).Iran and the Caucasus,Vol.12,No.2,2008,pp.289-293.关于里夫什茨的一些论著(含俄、英文),笔者烦请哈萨克斯坦友人Aizhan帮忙搜集了一些,在此表示感谢,将其介绍并译为汉文是日后努力的方向。等;我国学者有黄振华④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作者提出建安六年(201)说(第33页)。、依不拉音·穆提依⑤依不拉音·穆提依:《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84页。原文(维文)发表在《新疆史学》1980 年第1期。关于敦煌发现的粟特古书信年代,作者认可亨宁公元四世纪说(第69页)。、陈连庆⑥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109页。作者在文中反驳了汉末说,持东晋大兴三年(320年)说(第91-92页)。、林梅村⑦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的概述》,载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8-17页。作者在注释中认为粟特文书的时间“不应晚于汉代”(第8页)。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王冀青⑧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作者在文末认为信札写于东晋初年的可能性较大。、陈国灿⑨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5 年第7 期。后收入氏著《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60页。、李志敏⑩李志敏:《有关地名研究与斯坦因所获粟特信札断代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第157-172页。、荣新江11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载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57-172页。后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19-36页。作者认为古信札年代应在四世纪初年。又见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孟凡人①孟凡人:《敦煌粟特古书简第二号书信的年代及其与661 号佉卢文简牍年代的关系》,载氏著《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477页。作者认为西晋末年四世纪初期。、刘波②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麦超美③麦超美:《粟特文古信札的断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8年,第219-238页。作者认为书信年代是西晋末年(四世纪初)。、毕波④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第2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73-97页。另见氏著《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264 页。毕波女士对翻译和介绍英国学者辛姆斯·威廉姆斯的论著贡献较大。等,国外学者对第二号书信的相关研究大多被译为汉文发表,或者在中国学者的论著里提及介绍,读者可参阅注释。中国学者对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书信,除了以上列举者外,研究者甚少,多为介绍性质。即是说,不论对穆格山粟特文书,还是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相关的研究皆始于国外;不论是出土资料,还是话语权的掌握,仍然受制于外,中国的相关研究学者凤毛麟角。
除了中亚穆格山、中国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之外,在中国的新疆也陆续发现了一些粟特文书,大多是在古代高昌(吐鲁番),还有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丹丹乌里克、老达玛沟、麻扎塔格、安得悦)、楼兰(且末、若羌),北缘的温宿(图木舒克)、龟兹(库车)、焉耆等故地不同程度地发现了粟特文献。有的粟特文书是用在其他方面,如摩尼教经典。对于这些发现的粟特文书,吉田丰⑤[日]吉田丰著,柳洪亮译:《粟特文考释》《伯孜克里克摩尼教粟特文书信的格式》,载柳洪亮《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作者认为柏孜克里克发现的摩尼教粟特文书信的格式与敦煌以西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以及中亚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有相似之处。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著,柳洪亮译:《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新疆文物》1993 年第4 期(原文见《麴氏高昌时代ソゲドタ女奴隸売買文书》,载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编《内陆アゾア言语の研究》Ⅳ,1989 年,第1-50 页。对于这份粟特文买卖奴隶文书,林梅村、乜小红、刘戈等先生撰文均有论述,下文将重点讨论。[日]Yutaka YOSHLDA(吉田豊),Three Manichaean Sogdian Letters unearthed in Bäzäklik,Turfan.(ベゼクリク千仏洞出土のマニ教ソグド語手紙文研究),(京都)臨川書店,2019年1月。、马小鹤⑥马小鹤:《粟特文t´inp´i(肉身)考》,载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 辑,中华书局,2005 年,第478-496 页。作者根据1981 年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65 号窟发现的三件粟特文书对摩尼教的身体观作了研究。马小鹤:《摩尼教宗教符号“珍宝”研究——梵文ratna、帕提亚文rdn、粟特文rtn、回纥文ertini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姜伯勤⑦姜伯勤:《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摘要)》,《敦煌研究》1988 年第2 期,第82-84 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ド上のソグド人》(一、二、三),《季刊东西交涉》第5卷第1、2、3号,(东京)井草出版社,1986年,第30-39、26-36、28-33 页。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5 章,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150-263 页(作者在这一章分四节来阐述,第一节重点讨论了敦煌吐鲁番所见的两类粟特人,第二、三、四节分别讲了与粟特人有关的“白银之器”、“粟特锦”、萨宝制度及“胡祆祠”)。又见《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节选)》,载《姜伯勤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1-202页。、荣新江⑧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 年第2 期。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载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57-172 页。后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19-36页。又见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段晴①段晴:《西域的胡语文书》三《关于粟特语文献》,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讲座》第2 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第36-62 页。作者先是介绍了粟特文的特征,紧接着展示了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和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发现的粟特文书图片。在被提问后,作者解释道:粟特语有多种书写方式,根据信仰的不同,摩尼教、基督教、佛教所使用的字体不一样,皆有自己的书法(第60页)。、辛姆斯·威廉姆斯、毕波②[英]Nicholas Sims-Williams、毕波:《尼雅新出粟特文残片研究》,《新疆文物》2009年第3-4期。开始学界将其定为“羊皮佉卢文文书”,经过与敦煌楼兰地区发现的粟特文文书比对,最后确定是一件粟特文残片,推断年代在公元3 世纪后半到4 世纪初。这是首次在尼雅发现粟特文文献,补充了丝路南道上粟特人活动的证据。Bibo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I:Four Economic Documents.Journal of the America Oriental Society,Vol.130,No.4(Octorber-December 2010),pp.497-508.(汉译文见毕波、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四件经济文书》,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187-200 页。)Bibo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II:Letters and Miscellaneous Fragments.Journal of the America Oriental Society,Vol.135,No.2(April-June 2015),pp.261-282.(汉译文见毕波、辛威廉《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书信及其他残片》,载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 年,第306-325 页。)和田发现的这13 件粟特文书,经过中国人民大学毕波博士的修订后,再次出版,详见毕波、[英]辛威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另可参阅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人对其进行了介绍与研究。下面将重点列举一份吐鲁番阿斯塔纳135号墓出土的粟特文买卖奴隶契约文书,这份文书先是被日本学者吉田丰释读并用日文发表,紧接着柳洪亮先生将其译为汉文发表,后来林梅村先生、刘戈女士、刘文锁先生、乜小红、侯文昌等诸位先生皆对这份文书进行了讨论与研究③[日]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合著,柳洪亮译:《麹氏高昌王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新疆文物》1993 年第4 期。原载日本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编《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1988 年。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刘戈:《回鹘文买卖契约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58-172页。乜小红:《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契》,《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乜小红:《中古西域民汉文买卖契约比较研究》,《西域研究》2011 年第2 期。刘文锁:《新疆发现契约文书与中古西域的契约实践》,《西部蒙古论坛》2018 年第3 期。侯文昌:《中古西域民族文契约之立契时间程式研究》,《陇东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这份文书相较其他粟特契约文书,不仅内容完整,而且格式规整,因此显得格外重要。现将这份粟特文买奴券转摘如下:
岁在神圣的希利发高昌王延寿十六年、在中国说是猪年五月廿七日,粟特历十二月。
在高昌市场众人面前,张姓’wt’的儿子沙门y’nsy’n 用波斯铸纯度很高的银钱一百二十文,向tws’kk 的儿子wxwswβyrt,买了cwy’kk 姓的女人在突厥生的康国的女奴隶,名字叫做’wp’ch。
沙门y’nsy’n 买回的女奴无欠债,不再是原主的财产,不能追夺,不得非难,作为永久财产包括她的子孙后代都被买下了。因此沙门y’nsy’n 及其子孙后代,可以任意支配女奴,包括打她、虐待、捆绑、作人质、出卖或赠送。如同世传家生奴、旁生奴及用银钱买回之财产一样,卖主对此女奴不再有约束力,脱离一切旧有关系,不得再过问。此买女奴券对行者、居者、国王、大臣均有效、有信服力;拥有此券者,即可收领、带走此女奴。写在女奴文书上的条件,就是这样。
在场的有cwn’kk 的儿子tysr’t;xwt’wc 的儿子米国的n’mòr;krz 的儿子康国的pys’k;nnykwc的儿子笯赤建国的nyz’t;何国的□。
此券经书记长pt’wr许可、经女奴同意、在买主要求下,由书记长之子wxw’n书写的。
高昌书记长pt’wr的印。
(背面书写)
女奴文书 沙门y’nsy’n①此处引文转自乜小红《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
可以看出,此份粟特文契约除了官府认可钤印发给外,格式与佉卢文契约很相似,立契的时间很特殊,不仅有高昌王“延寿”年号,而且有突厥授予高昌王荣号“希利发”,还有十二生肖纪年、粟特历。林梅村先生已指出,此高昌王即麹文泰,延寿十六年即唐贞观十三年(639)。刘戈、乜小红二位先生对该纪年有分歧,在“猪年”的解释上,刘氏认为是十二生肖纪年,乜氏认为是亥年,是受汉文契约影响,即“‘己亥岁’省去天干的结果”。然细读粟特文契约文书,联系该文书所处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刘戈先生的看法比较符合粟特文的时代背景②关于这一点,侯文昌先生亦持相同论点。见侯文昌《中古西域民族文契约之立契时间程式研究》,《陇东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通观乜先生对契约文书的其他相关论文,她的立论点皆在于汉文契约影响了少数民族契约。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一条复杂的线路,处于这条丝路上的高昌,在历史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高昌的建置来看,它历经西晋(265-317)、高昌郡(前凉至北凉,327-460)、高昌国(460-640)、唐西州(640-8 世纪末)四个时期,在这漫长的六个世纪,高昌还与其他民族政权有来往,不可能单独受中原王朝的控制和影响,因此粟特文契约文书自然也受到印欧契约文化的影响,即使没有,但与佉卢文契约、于阗文契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在这份契约文书的开头出现如此多的形容高昌王的词语,以及纪年时间就不难理解了。
显然,该契约在描述契约的主体时比较详细,买者为张姓“’wt’”的儿子“y’nsy’n”,是位沙门;卖者为“tws’kk”的儿子“wxwswβyrt”,特意说明家族共同承担的一种责任。交易物为来自康国的女奴隶。价值为波斯银钱一百二十文。交易完成后,女奴属买者沙门“y’nsy’n”的私有财产,任他处置,在“虐待”“捆绑”“出卖”等修饰词上跟佉卢文契约如出一辙,似有一定的关联。强调此契一旦生效,在国王、大臣那里都有效,可见契约程式的法律性。不过,这份粟特文契约中并没有提及悔约后的惩罚规定,可能跟官府文券的性质有关,即证明了奴隶来源和买卖的合法性,故无必要谈悔约的问题。
另外,契约末尾写有“经女奴同意”字样,如果翻译没问题的话,这就比较有意思,为何女奴被卖的时候还被征求是否“同意”呢?检阅十六国至唐代的汉文买卖奴婢契,发现唐代的契文中有“准状勘责,问口承贱不虚。又责得保人石曹主等伍人款,保不是寒良詃诱等色者。勘责状同,依给买人市券”③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省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九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页。的记载,由此可见,应该是官府查验奴婢的来源,以防逼良为贱或者被诱骗,故而有“经女奴同意”之说。这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官府在人口买卖行为上是不允许买卖良民的。④可参拙文《论清代的略人略卖人》(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管窥古代人口买卖的行为。
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发现的这份奴隶买卖文书弥补了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在高昌国时期没有经官府许可发给的奴隶买卖文券的认识,从契约格式及内容看,这份粟特文契约虽与同时期的汉文契有相似性,但区别甚大,需要辨别的是,契约文书中出现的“买奴契券”是指私人之间买卖奴隶时订立的契约,而“买奴市券”则是交易完成后经官府认可后发给的公验,在十六国至高昌国时期的汉文买卖奴隶契约中,出现有私人交易的买卖券,而由官府钤印的文契并未发现⑤乜小红:《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契》,《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截止这份粟特文契约的发现,才得知高昌国时期官府对民间奴隶买卖进行干预。
综上所述,粟特文契约在文书格式上与佉卢文契约、于阗文契约比较接近,明显带有印欧文化的烙印,也受到了中原汉文契约的影响,但独具特色。目前学界对粟特文契约的研究,尽管不像佉卢文契约、吐蕃文契约、回鹘文契约、西夏文契约那样有系统的专著出现,而且至多皆是零散的引用。但是,粟特文契约的格式是个很好的典型,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最能代表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碰撞、互动、交融的现象。我相信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粟特文契约文书的研究会达到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