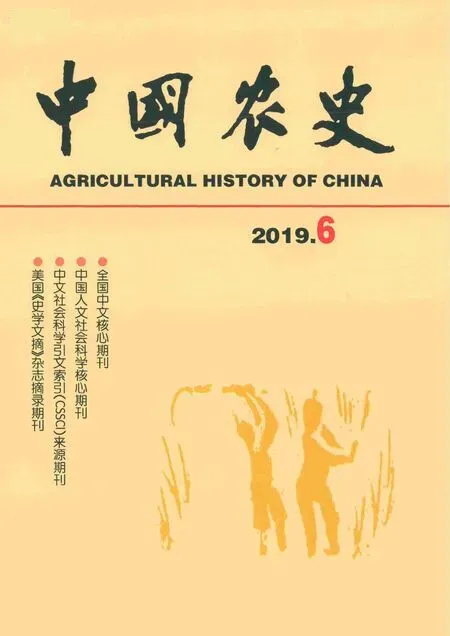汉代粮仓艺术表现研究:回顾与思考
(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美国纽约10028)
两汉时期是中国转向农耕社会的关键时期,其中仓作为粮食贮藏的主要工具不仅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是汉代墓葬中广泛出现的艺术母题。除了目前发现的数量众多的陶仓以外,其他材质的仓形明器、墓葬壁画及相关铭文也将仓作为重要的表现题材。仓的艺术形式也因此成为学界多年以来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成果涉及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史与民间丧葬信仰交织的多个层面。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同学科依托各自的方法论对如何从这批材料入手展开探讨,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然而,既往的研究分隔于各类表现形式的壁垒中,且并没有将粮仓作为一个统一的题材看待,这使得讨论趋于离散,也因此忽略了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针对以上状况,本文将对现有研究做一回顾,以期为后续更为全面地研究粮仓艺术表现问题奠定基础。
一、农耕社会缩影的粮仓艺术表现研究
艺术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下,对粮仓艺术表现研究的一大趋势是将其看作汉代社会,尤其是处于转向农耕文明时期农业经济生产的缩影。前贤学者尝试从这批材料入手观察农业发展、社会阶层、区域互动等问题。
以考古学为代表,学者多以建筑明器中的陶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区系类型学的方法探讨仓所反映的汉代社会原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突出陶仓明器在两汉这一特定时间段内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在各地域之间进行比较以解释其中的区别与联系。张勇在河南博物馆编著的《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中发表了三篇相关文章①张勇:《河南汉代建筑明器定名与分类概述》《河南汉代建筑明器类型学与年代学研究》《建筑明器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河南博物院编:《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99-278页。,涉及到定名、分类、类型学、年代学和起源等诸多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与此研究思路类似,另有学者对不同地区的陶仓进行类型学分析,如武玮对河南汉墓出土陶仓楼的考古学探索②武玮:《河南汉墓出土陶仓楼的考古学探索》,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逯鹏对岭南汉墓出土陶屋的分析③逯鹏:《岭南汉墓出土陶屋的初步分析》,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考古学界对仓的区系类型分析也在地域范围上不断拓展,超越以中原地区为主的限制而基本覆盖了汉代的边疆各地区。梁启政主要分析了东北地区高句丽壁画中的仓和该地区出土的陶仓④梁启政:《高句丽粮食仓储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熊昭明和韩湖初对出土于西南边疆、以合浦汉墓为主的铜仓进行了介绍⑤熊昭明:《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仓灶》,香港历史博物馆:《瓯洛汉风:广西古代陶制明器》,2014年,第26-33页。韩湖初:《合浦汉代文物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45页。;他们还将图像学与粮仓主题结合,考证了合浦黄泥岗一号墓出土铜仓表面錾刻的四神形象;广东省考古所的朱非素整理了广东地区出土的各类材质的仓⑥朱非素:《考古发现及汉代广东农业管见》,《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在汉代的北部边疆,在披露重要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李雪欣、魏坚通过比对内蒙巴彦淖尔地区的陶仓与周边的陶仓揭示了二者之间类型和风格上的联系⑦李雪欣、魏坚:《巴彦淖尔汉墓陶仓区域特征初步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先贤的研究涵盖了汉代各边疆地区,对于在更广大的范畴内探讨仓的艺术表现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对大量现有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学者们也试图探究与现象紧密联系的各类问题,从而引入社会因素的视角。汉代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发端,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经济⑧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与特性》,王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与此息息相关的粮食贮藏问题自然也成为关注的焦点。朱顺龙通过汉墓明器研究汉代农业经济⑨朱顺龙:《从汉墓明器看汉代农业经济》,《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滕雪慧从汉晋南朝时期湖北与江东地区经济开发的比较,对出土谷仓模型进行了探讨⑩滕雪慧:《汉晋南朝时期湖北与江东地区经济开发之比较——以出土谷仓模型为基础的探讨》,《农业考古》2010年第2期。,两人均强调可以通过建筑明器和模型重现汉代农业社会的现实状况。张勇的三篇文章虽然并没有专门探讨粮仓的问题,但与陶灶、陶井、厕所、猪圈等器物的组合,说明仓类明器的随葬反映了中原地区的经济甚至整个农耕社会的状况。他认为这与汉代大一统后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空前繁荣有关。在粮食连年丰收的情况下,人们为长期保存而修建了各种贮粮设施,从而催化了陶仓明器的繁盛。从社会背景的分析方法来看,武丽娜试图从更多的方面展开思考,也将研究带入更为细化的层面①武丽娜:《秦墓出土陶囷模型研究》,《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通过对各墓葬陪葬器物组合和墓主身份的复原,武丽娜认为土地制度及土地授予方式、生产工具变革、先进生产技术的引入和社会阶层流动都可归为仓类明器陪葬的推动力量。除了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之外,学界还致力于探究器型渊源、流向等相关的社会问题。其主要方法是以区系类型学的比较来考察器物背后的人口迁移、文化互动、交流与融合,性别研究等社会问题。例如德国学者谢藏(Armin Selbitschka)通过梳理战国至西汉墓葬中出土的陶仓,追溯其从秦墓中诞生到大一统后逐渐向东传播并在汉代初期的洛阳地区产生了五谷仓这一变体的过程。另外,他的文章还探究了使用这类明器陪葬的墓主社会等级和性别问题②Armin Selbitschka.“Quotidian Afterlife:Grain,Granary Models,and the Notion of Continuing Nourishment in Late Preimperial and Early Imperial Tombs”,in Müller Shing and Selbitschka,Armin,ed.Über den Alltag hinaus:Festschrift für Thomas O.Höllmann zum 65.Geburtstag.Wiesbaden:Harrassowitz,2018.pp.89-106.,虽然目前证据尚显单薄,但他归纳出陶仓多由身份较高的成年男性墓主使用的规律,而在陪葬的女性墓中则较少发现。
除社会因素以外,环境条件也是研究粮仓艺术表现不可或缺的方面,将粮食贮藏置于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形态中,也为学界的探讨带来了新的启示。汉帝国的版图横跨从朝鲜半岛到帕米尔高原、从蒙古草原到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域,边疆的生态气候也有着从亚寒带到亚热带的巨大差异。因此,适于各地的经济生产形式也各有不同。北方长城附近的边境主要涉及到农牧业交叉地带,而西南地区则由于气候和高山地貌的影响而存在着更为多样的经济形态。朱宏斌的博士论文就以地理区域为界,详细介绍了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以及其在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的战略位置的差异而导致了区域农业开发的共性和时空差异③朱宏斌:《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朱文的视角充分重视了疆域内各区的差异,从而促进理解农作物仓储在其中的可能具有的细微认知差别,以及这种环境上的影响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墓葬中仓的艺术表现。
在粮仓艺术表现反映农耕社会这一框架之下,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充分理解粮仓在汉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一问题早已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他们首先利用史料详细揭示了汉代粮仓的设置、管理和法律等问题。例如蔡文进认为西汉基本沿袭了秦代的粮仓规划,即与政治体制相关在都城和各郡县设置粮仓,从而建立自上而下多层次、广分布的完整制度④蔡万进:《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粮仓的建筑与设置》,《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卲鸿考证了汉代文献与仓相关的内容,提出西汉都城及附近有太仓、甘泉仓、华仓(京师仓)、细柳仓和嘉仓⑤卲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并与其他较小的粮仓一起由中央直接管辖。而在地方,西汉郡、县两级行政均有常设之仓,在史籍、出土仓印、简牍中均有体现。日本学者太田幸男也利用《睡虎地秦简》对地方级别粮仓的设置和管理进行了细致的考证⑥[日]太田幸男:《湖北睡虎地出土秦律の倉律一》,《東京學藝大學紀要》1980年第31期。。依托于传世文献和睡虎地出土简牍,学者们总结出秦汉粮仓入仓、封隄、出仓、核验、增积、贮藏与相关人员的交接等一系列过程⑦宫长为:《秦代的粮仓管理——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2期。李孔怀:《秦代的粮仓管理制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印鉴在粮仓管理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整理和研究,萧高洪认为封印与锁共同使用,以防奸萌⑧萧高洪:《仓印与古代粮仓的管理》,《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睡虎地“仓律”的法律性质提供了研究的另一个角度。Moonsil Lee Kim 从法制史入手追溯了粮食出入仓、记录、汇报的规章制度和对于仓令手续、责任、违规行为的详细惩治措施①Kim,Moonsil Lee.Food Redistribution during China's Qin and Han Periods:Accordance and Discordance among Ideologies,Policies,and their Implementation.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2014.。其次,粮仓的储存效能同时还被置于粮食生产、分配、消费的中间环节,其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位置也得到了先贤的深入探讨。蔡万进的《秦国粮食经济研究》一书以秦代的仓廪制度为主要线索意图展示秦国农业经济的全貌②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年。。其中《粮食仓储管理》一章阐发了粮仓承前,即粮食生产及启后,即在分配、运输、贸易、加工、消费、价格中的作用。Moonsil Lee Kim 则更注重于仓与粮食分配的联系。她结合睡虎地、张家山、里耶和悬泉简牍的法律文献,说明地方粮仓在粮食配给的过程和数量上的作用并非在于根据规定分配食品,而在于规范地方官员对待国家仓储的行为③Moonsil Lee Kim.“Discrepancy between Law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An Analysis of Granaries,Statues and Rations during China’s Qin and Han Period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59:555-589.2016.。另一关注焦点在于仓与粮食运输的关系。蔡万进详细论述了秦国粮食运输的特点和方式,并强调与粮食运输有关的粮食转运之仓储体系④蔡万进:《秦国粮食运输政策探略》,《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沈颂金更指出粮仓是漕运设施的中心,在食品输送系统中的地位尤为重要⑤沈颂金:《秦代漕运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将现有丰富的汉代粮仓研究与其艺术表现的物质文化遗存相结合,能够更好地理解后者产生和流行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揭示仓在汉代农耕社会的含义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上所提及的研究虽然以陶制建筑类明器为主,并未涉及到其他材质的艺术表现,但代表了探讨中的一大重要取向,即将陶仓这类器物看作是汉代历史的镜面反射,其出现、变化和衰亡都直接反映了农耕文明大背景下的问题。然而,观点成立的前提是艺术表现是否能作为历史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需要分情况讨论且需重视的问题。因此,与文献考证相结合对粮仓在社会中的位置进行复原,将有助于理解艺术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可靠的历史材料,它们又以怎样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
二、复原汉代农业贮藏建筑的粮仓艺术表现研究
同艺术表现反映社会的观点一样,出土的仓类器物和图像也被认为是储粮建筑的直接反映,对其功能性的重视也体现出农耕文明的另一个层面,即对于粮食贮藏的关注。由于部分作品对建筑结构做了细致的描绘,建筑史学者也将粮仓艺术表现看作复原汉代建筑的有力证据,并通过了解粮食贮藏类建筑,进一步深化对农耕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农业情况的理解。
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不易长存,目前发现最早的地面建筑仅能追溯到唐代。因此,为将古建筑复原推进到更早的时段,学者依托这批材料推测汉代储粮建筑类型、结构、技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首先涉及到考古学层面对明器类陶仓的分类和形式分析。杜葆仁以其为根据追溯粮食贮藏建筑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在各时期的特点⑥杜葆仁:《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而在与禚振西同著的文章中提出汉代的粮仓或与明器一致,可细分为圆形的囷、方形的仓(包括干栏式、露天式和仓楼式)、地下的窖三类⑦禚振西、杜葆仁:《论秦汉时期的仓》,《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6 期。地下储粮设施见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上)》,《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以明器为参照的研究方法尤其反映在对粮仓遗址的考察中。在发掘西汉京师仓之后,杜葆仁参考同时期的陶仓复原现已不存在的地面结构①杜葆仁:《西汉京师仓一号仓复原探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76-79页。。通过地面遗存与建筑明器的交叉考证,京师仓应为夯土台基的长方形三室木结构建筑,由基础、檐墙、柱、梁、桁架、屋顶等部分组成,整体面积可达1662.5平方米。三个仓门均位于东面,为活动板门以利于粮食进出仓。仓内安有架空地板,以两道东西向的墙为分隔。在杜葆仁复原研究的基础上,呼林贵也通过参考陶仓模型和壁画详尽分析了京师仓建筑的储存功能,包括防潮、防暴晒及过冷,保持恒温,通风散热,宽敞坚固,防雀害、鼠害,防火以及防盗自卫等各个方面②呼林贵:《西汉京师仓储粮技术浅探》,《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并提出这些细节在仓类建筑中的表现,体现出对于贮藏功能的重视,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在农业社会,粮食的安全是关系民众生活和国家存亡的重中之重。
从建筑史的角度而言,考察仓类建筑明器对复原汉代实体建筑及各细部的结构功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建筑通史类书籍中汉代部分大量涉及到出土的建筑明器,例如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③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及其后由刘叙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 卷)④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另外也有对于仓的位置布局⑤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建筑细部结构⑥刘叙杰:《汉代斗拱的类型与演变初探》,《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2-229页。、斗拱承托技术等更为深入的讨论。这一趋势在西方学界也有所反映,例如托马斯·霍尔曼(Thomas Höllmann)⑦Thomas Höllmann.“Pfahlhäuser im alten China”,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2(1981):45-86.的研究都同样以陶仓为依托,从建筑史的视角讨论汉代建筑的形制、结构、装饰纹样等问题。在运用明器类材料的同时,二维的图像材料也被纳入考量的范围。在夏南希(Nancy Steinhardt)撰写的中国建筑史⑧Nancy Steinhardt.Chinese Architecture:A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中充分利用汉画像石图像分析汉代地面建筑,而早在1974 年,罗哲文就针对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丰富的建筑图像资料进行介绍,并细致阐释了其中粮仓在整个宁城和护乌桓校尉幕府中的位置、建筑制度、结构以及布局逻辑等方面的内容,尤其强调仓与营舍、幕府堂院和库房之间的互动关系⑨罗哲文:《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文物》1973年第1期。。而罗哲文与前文述及的观点类似,也认同描绘粮仓表示当时幕府内部储存有大量粮米的现实情况,表明这一问题在汉代城镇中的重要性。
建筑学上的考量在以粮仓艺术表现为建筑复原真实写照的基础上,也逐渐开始重视材料的考古属性。换言之,如果说前期的研究是完全站在建筑史的角度讨论的话,近年来的研究则开始重新认识陶仓及粮仓图像作为明器、出土文物或壁画墓图像等的真正内涵。如刘临安、曹云钢、张旖旎从汉代明器看建筑斗拱的特征⑩刘临安、曹云钢、张旖旎:《从汉代明器看建筑斗栱的特征》,《建筑师》2008年第1期。,周学鹰从出土文物探讨汉代楼阁建筑技术11周学鹰:《从出土文物探讨汉代楼阁建筑技术》,《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现任教于澳大利亚的国庆华所撰写的英文专著《中国汉代陶制明器建筑:建筑表现与被表现的建筑》12Qinghua Guo.The Mingqi Pottery Buildings of Han Dynasty China,206 BC–AD 220:Architec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Represented Architecture.(Brighton:Sussex,2010).(作者译)着重突出明器的特殊性质。国庆华尤其强调建筑学与考古学的互动,讨论建筑类明器在墓葬中的位置、摆放顺序、器物组合及观者等一系列问题。虽然这类著作的出发点仍然基于建筑史的探讨,行文论证中也偏重对建筑结构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但已初步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可喜趋势。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不断反思将艺术表现看作历史真实反映的方法,认识到这批材料与汉代社会状况及建筑形制可能存在的差异,继而重新审视这批材料的艺术属性。早在梁思成赴美学习期间就曾对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的汉代三层陶制仓楼进行研究。在细致观察和描述的基础上,他发现该器物对于建筑结构的表现与实际功能性不符,例如楼阁中没有柱子,转角斗拱也存在问题等等,但梁思成并没有进一步深究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①梁思成:”A Han Terra-Cotta Model of a Three Story House”,载《梁思成全集》(第1卷),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8-12页。。傅熹年则提出应先观察器物或图像表现手法上的特点,总结其中的规律,分析工匠画师对于建筑空间结构的转换方式②傅熹年:《战国青铜器上的建筑图像研究》,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94页。。这一探索方向也被目前的研究者所继承,例如张薇薇基于对四川画像砖中建筑图像的观察,指出观察角度与透视方法对建筑表现的影响。她发现构图为方形的宅院图像并非意味着庭院本身的形状,而是受到方形砖面和俯视角度下的散点透视双重影响③张薇薇:《亦有甲第,既丽且崇——四川成都“宅院”画像砖反映的东汉居住建筑形象》,《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
尽管建筑学者们开始逐渐重视考古、艺术表现的双重性质,但同考古学的方法类似,以出土器物或图像鉴证和复原历史为前提,即将其看作汉代建筑的真实写照这一观点仍然根深蒂固于研究之中,从而对材料不加严格分析地使用。基于汉代粮仓现已不存的事实,学者面临着将出土资料与现实建筑进行对应的困境,从而很难判断其中的异同。而仓作为与农耕社会息息相关的艺术题材也被不加区分地直接纳入汉代建筑的广泛范畴内,未能就其表现方法或考古原境是否与其他器物或图像存在差异展开详尽的讨论。另外,对仓的艺术表现与粮仓实物和其他题材的比较所反映的历史状况、政治生态以及相关人物的心理动机也鲜有研究涉及。
三、丧葬语境下的粮仓艺术表现研究
墓葬作为仓的艺术表现的主要来源,是学界长期以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在将其看成是历史反射的同时,研究者们也意识到丧葬语境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两种取向虽然各有侧重,但绝非完全分离,更多的是处于并存及互动的状态。二者的交融在近年来的论文中均有体现,例如吴晓阳对战国西汉墓随葬陶仓、囷的考古学观察④吴晓阳:《战国西汉墓随葬陶仓、囷的考古学观察》,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武玮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汉至西晋模型明器的研究⑤武玮:《黄河中下游地区汉至西晋模型明器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以及陈玉婷对广西汉代陶建筑明器的研究⑥陈玉婷:《广西汉代陶建筑明器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等等,在此不做赘述。以张勇的研究为例,他对河南地区出土陶仓的分析就是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基础上进行延伸,认为随葬品中仓的出现与灵魂不死的死亡观念有关。在灵魂永恒存在的地下世界,仓和其他明器类器物可以更简便地帮助人们实现在死后的世界继续享受世上豪华生活、拥有生前一切权力和财富的愿望⑦张勇:《建筑明器起源及相关问题讨论》,河南博物院编:《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 年,第269-278页。。他的文章基本继承了汉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看法,宏观地总结了仓大量出现在墓葬中的原因。针对粮仓艺术表现的丧葬语境,不断有学者以不同的材料从各个角度展开更为细致的探讨。
(一)陪葬明器的丧葬属性
仓是汉代明器中常见的器型之一,而明器作为专为亡者设计和制造、专门用于墓葬的器物则是研究随葬品及死亡观念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于明器的整体性研究有助于从这一角度加深对陶仓丧葬功能的理解。这首先涉及到如何看待明器的本质这一理论化的问题。巫鸿引用荀子之言,将明器概括为“貌而不用”,即“保持实用器的形式但是拒斥其可用性”①[美]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施杰译,三联书店,2010年,第92页。。而回到墓葬的角度来看,这个界定一方面有助于思考在丧葬功能引导下仓的各类艺术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随葬品内在逻辑入手,展开对粮食贮藏类明器与其他类型的随葬品的综合分析。针对后者,陶仓与其他明器器型在墓葬中的组合形式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仓在汉代墓葬中多与灶、井、厕等明器伴出,形成一套典型的明器组合。黄晓芬在《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专辟一节集中探讨了这种形式,通过分析数量众多的墓葬资料探寻背后的观念性意味,提出明器器型的组合方式为两汉时期的天地思想和阴阳风水观所主导②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217-227页。李思思除了认同墓葬中建筑明器组合具有特殊意义之外,更进一步地分析了它们如何与其他墓葬元素重组地下世界的空间和秩序。此外,她也以墓葬属性为出发点,主张将仓等建筑明器视为表现建筑的艺术形象和与丧葬相关的理想型建筑,因此在丧葬语境的讨论中,仓型明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汉代人对建筑和建筑结构的认知,但可能并非是现实建筑的真实再现,而更多寄托了亡者对于死后世界的向往③李思思:《汉代建筑明器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
(二)图(物)文对应的研究方法
在对粮仓艺术表现的研究中也有学者主要针对图像或器物所带铭文,采用二者对照的方法探寻仓在汉代丧葬礼俗中的礼仪性作用。以洛阳地区出土的陶仓为主要研究对象,谢藏整理了仓表面的铭文并指出其与汉代流行的“五谷“观念有关,例如董仲舒所提之“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他认为,这些明器陶仓通过铭文的方式被转化成了真实的粮食储藏设施,从而为墓主在死后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④朱顺龙:《从汉墓明器看汉代农业经济》,《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除此之外,研究的另外一个焦点集中于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墓葬壁画中粮仓图像多伴有的“天仓”“太仓”铭文。此类图文结合的表现方式大量出现在两汉时期,就具体铭文而言存在细微差异,例如还有“大仓”“大苍”“太山仓”等写法,句式也有所不同,有“皆食太仓”“食就大仓,饮江海”“皆食太仓,急如律令”“龙蛇牛马,皆食太仓”等等。针对仓类铭文在墓葬中的含义和作用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假设。陈直最早以河北望都壁画墓中的文字提出太仓代指汉代的太仓令,是全国藏粟最多之处,因此在这里比拟死者禄食不尽之意⑤陈直:《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考古》1962年第3期。。李发林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这是一种流行于汉代的吉祥语⑥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齐鲁书社,1982年,第99页。。巫鸿也在解释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石棺的“大苍”时持同样的观点,指出人们以此表现数量巨大的粮食储备,其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生者与死界的区隔,即“希望墓中的人物动物向大自然获取饮食,而不与生者争夺食物”⑦[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郑岩、王睿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122页。。信立祥则将仓与墓主车马出行图像中常见的“都亭”题记相联系,认为“太仓”不仅代表墓主在生前是从官府领取俸禄的官僚,在天国也会延续同样的身份地位⑧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27页。。这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对死后生活的美好愿望,即墓中仓的图像和文字并不能反映墓主的社会等级,而是对人的祝愿“祝愿他成为吃皇粮的上等人”⑨周到、郭太松:《河南汉画像题记研究》,韩玉祥编:《汉画学术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37页。。杨爱国和姜生则从道教信仰的角度入手,援引《太平经》关于天仓的描述提出太仓之粟可能代表着不死药,而太仓则是升仙之所⑩杨爱国:《“此上人马皆是太仓”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编:《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7-548,568页;姜生:《汉代天厨贻食信仰与道教施食炼度科仪之起源》,《中国道教》2016年第1期。。以上诸观点各有侧重,但都从汉代民间信仰,尤其是从丧葬礼俗的角度出发,探究仓的艺术表现在墓葬中大量出现的现象,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四、结论与思考
粮仓的艺术表现为理解汉代农耕文明的特点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而学者们长期以来也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开展了探索。目前的研究虽然呈现出跨学科的总体特点,但不同学科仍然以自身的话语体系、研究对象和理论关照为前提,也存在以材料而非题材为主导、以物为史、墓葬功能先行、地域分隔等问题。
没有突破各表现形式上的壁垒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往研究未能以跨媒介的视角看待粮仓这一备受汉代民众关注的表现题材,导致研究囿于明器、墓葬壁画、汉画像石、画像砖中的一类或几类而没有进行全方位的互通。与此同时,艺术表现形式也应与实际的粮仓遗址、建筑形式以及粮仓背后的社会问题开展更有机的结合,而不是在忽略其艺术创造属性的基础上用来复原汉代历史状况。这与充分理解这批材料的丧葬语境相关,但也不应把它们简化成完全为汉代丧葬礼俗而生的产物,全盘从死后世界的视角阐释,而应针对具体不同案例将多个方面结合进行分析。
虽然不断有学者致力于全景式的讨论,但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地区限制,对边疆材料的系统性研究工作还没有充分展开。这一局限体现在未能充分探讨甚至整理粮仓这一表现题材。由于中国的考古发掘长期以中原地区为主,有关边疆的仓的话题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甚至有大量案例至今未有学者撰文讨论。既有的针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成果中多限于各地区之内,忽视了宏观历史构架而未能将各个边疆地区的案例放在同一个时空网络中,与当时本地区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探究其艺术表现与边疆开发、政府管理、经济生产、认知意识、丧葬观念等各个层次关系上的共性、差异与联系。缺乏对于各个地区全面性的认识和探讨,从而忽视了粮仓及其艺术表现在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生产系统中的差异性。
整体来看,对粮仓艺术表现的研究已有较为深厚的基础,未来可以联系农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突破区域局限,并在环境与储藏功能的关系方面进行拓展和突破,以期能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学科互动和更为全面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