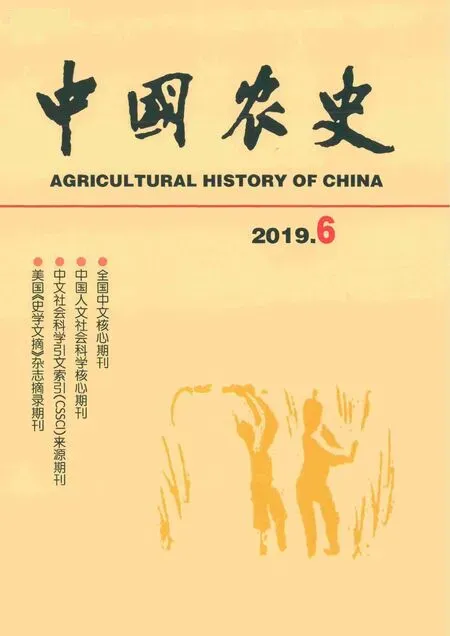紫花苜蓿引种中国的若干历史问题论考
李鑫鑫 王 欣 何红中
(1.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2.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95)
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以下简称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早在赫梯时期(1700B.C.-1200B.C.)的泥板文书中,苜蓿已被人们视为高营养的动物饲料①BoltonJ.L.,GoplenB.P.and BaenzigerH.,1972,“World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In Hanson C.H.(ed.),Alfalfa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dison,pp.5.。汉文“苜蓿”一词为古代伊朗语busuk、buxsux 的记音字②[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页。,这说明苜蓿是引种中国的域外植物。目前,学界对于苜蓿引种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种植、使用情况的研究较为充分①BoltonJ.L.,GoplenB.P.and BaenzigerH.,1972,“World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InHanson C.H.(ed.),Alfalfa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dison,pp.1-34;[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30-44页;向达:《苜蓿考》,《自然界》1929年第4期;谢成侠:《二千多年来大宛马和苜蓿传入中国及其利用考》,《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5年第3期;范延臣、朱宏斌:《苜蓿引种及其在我国的功能性开发》,《家畜生态学报》2013年第4期;孙启忠、柳茜、那亚:《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草业学报》2016 年第1 期;孙启忠、陶雅、柳茜:《汉代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考述》,《草业学报》2016年第12期。,但关于苜蓿引种中国的具体时间、人物、地域等问题尚未定论,本文拟在先贤时彦基础之上,尝试对此进行初步讨论,不妥之处,请读者、方家指正。
一、苜蓿引种中国的人物与时间
关于苜蓿的起源,学界大多倾向于伊朗西北部、外高加索山区、小亚细亚②Bolton J.L.,Goplen B.P.and Baenziger H.,1972,“World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In Hanson C.H.(ed.),Alfalfa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dison,pp.1-2.,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等地③Sinskaya E.N.,1961,“Flora of Cultivated plants of the U.S.S.R.Perennial leguminous plants”,Part1,Translated by Israel Program,Jerusalem,pp.21.。公元前一千纪后,苜蓿从外高加索地区开始向外传播,据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所著《植物志》记载,米底王国征战希腊,从而将苜蓿带至希腊④Theophrastus,1916,Enquiry Into Plants and Minor Works on Odours and Weather Signs,VolumeⅠ(Books 1-4),translated by Arthur Hor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21.;之后,罗马帝国又从希腊获得苜蓿。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前2500—前2000年),发源于土库曼斯坦科佩特山脉以北的纳马兹加(Namazga)农业文化⑤纳马兹加位于土库曼斯坦科佩特山脉以北,该地被视为中亚青铜时代农业文化代表。纳马兹加文化以纳马兹加德佩(Namazga-Depe)、阿尔丁德佩(Alty-Depe)为中心,共分为六期,时代约为公元前4800-前1500年。开始衰落,伴随人群的不断向东迁徙,带动了包括苜蓿在内的农作物扩散至中亚索格底亚那及东方的费尔干纳盆地⑥Masson V.M.,1992,“The Decline of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and Movements of the Tribes”.In Dani A.H.(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Ⅰ,UNESCO,pp.343.。
文献记载中,中国是在西汉时期于中亚引种苜蓿。《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⑦[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3页。《汉书·西域传》之“大宛国”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⑧[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5页。以上两条史料在证明苜蓿于西汉进入中国的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于苜蓿由何人引入中国的争论。而由于引种人身份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苜蓿引种中国具体时间的争论⑨孙启忠、陶雅、柳茜:《汉代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考述》,《草业学报》2016年第12期。。概而论之,目前学界对此问题主要形成了张骞引种与汉使引种两种不同观点⑩除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是大宛之战后由李广利等引种,但所认同者较少。可参考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页;陈舜臣:《西域余闻》,吴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薛瑞泽:《秦汉晋魏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一)张骞引种说
由于《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见闻,因而后世据此将苜蓿引种中国的功绩归于张骞①BoltonJ.L.,GoplenB.P.and BaenzigerH.,1972,“World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In Hanson C.H.(ed.),Alfalfa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dison,pp.6;[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7页;孙醒东:《中国几种重要牧草植物正名的商榷》,《农业学报》1953年第4期;卜慕华:《我国栽培作物来源的探讨》,《中国农业科学》1981年第4期。。因此,有相当学者认为张骞两次出使归国的时间(公元前126 年或前115 年)是包括苜蓿等西域植物进入中国的开始②孙启忠已将相应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细致分类,详细信息可参阅孙启忠、陶雅、柳茜:《汉代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考述》,《草业学报》2016年第12期。。
实际上,遍览《史记》《汉书》并没有张骞带回苜蓿的史实记录。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汉时(前126年),被匈奴所羁押,后乘匈奴内乱逃脱,按其处境险恶的仓促之状,不可能携回许多物种。张骞第二次西行(前119-前115年),本人只到了乌孙,他分遣各地活动的副使,也没有携回物种的记载③殷晴:《物种源流辨析——汉唐时期新疆园艺业的发展及有关问题》,《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张骞回程时,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④《史记·大宛列传》,第3169页。,如若张骞欲使乌孙知汉广大,携带西域物种则似乎于理不合⑤石声汉:《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4期。。
考诸史籍,最早明确提出苜蓿是由张骞引种中国的观点出自于东汉王逸。王逸曾任东汉校书郎、侍中等职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618页。。贾思勰首先在《齐民要术》中引王逸所言:“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⑦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卷3,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2页。而《太平御览》中载“《正部》曰:‘张骞使还,始得大蒜、苜蓿’”⑧[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977《菜茹部(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4329页。,由是可知《齐民要术》所引源自王逸所著《正部》一书⑨[北宋]李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第12页。。
此后,从《博物志》《西京杂记》《农政全书》《本草纲目》《授时通考》等博物、农业、本草、杂记类史籍,乃至《太平御览》《渊鉴类函》等官修类书中,苜蓿由张骞引入中国的观点不断出现,这样的认知逐渐成为一种典范性知识。
后世史家也有对此说法表示出怀疑。任昉在《述异记》中说“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蒲陶胡葱苜蓿,盖以汉使之中,骞最名著,故云然”⑩[南宋]罗愿:《尔雅翼》,黄山书社,1991年,第89页。,即是一例。《植物名实图考》中,关于苜蓿,吴其濬的评论是:“按《史记·大宛传》,只云‘马嗜苜蓿’,《述异记》始谓‘张骞使西域得苜蓿菜’”,也表达了吴氏对张骞引种苜蓿的怀疑11[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3,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71-72页。。夏如兵认为,后世文献往往将早期外来作物的引入归功于张骞,多出于臆测12夏如兵、徐暄淇:《中国石榴栽培历史考述》,《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张骞是苜蓿引种中国的第一人,这样的知识建设,实际上是一种“附会”行为。中国固习每有功归圣人的想法,后人多袭其说13张宗子:《葡萄何时引进我国》,《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由于张骞开通为内地民众所陌生之西域,因而其逐渐被塑造成神话式人物。史籍中还有诸如张骞曾乘槎至天河与织女相会,引入“酒杯藤”等神奇物种的传说14[晋]崔豹撰,牟华林校注:《古今注》,线装书局,2015年,第166页。。按东汉王逸,出身本为文学家,故于其私著中添入民间大众的传说故事也不足为奇,其说张骞引进苜蓿因而只是推测之言15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魏晋时期文人多好清谈,言物必及掌故与神怪,实为一时风尚16石声汉:《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4期。。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张骞带回苜蓿的概念形成,并深入人心①孙启忠、柳茜、那亚:《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草业学报》2016年第1期。,并最终成为传说故事的中心人物,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因此他终于被推尊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②[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7页。。
李希霍芬(Richthofen)对此总结道:“我们不能假定所有这些植物和种籽都是张骞自己随身带回来的,因为他游历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而且被匈奴囚禁了一年……但是张骞建立了关系,使得其后几年里能把栽培的植物传到中国来。”③F.F.Richthofen,1877,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Vol.I,pp.459.此言无疑是对张骞与西域物种之关系所做最为中肯的评价。
(二)汉使引种说
张骞引种苜蓿归国的观点受到质疑的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观点——苜蓿是由上述《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中出现的“汉使”带回。《大宛列传》记载在张骞过世后,汉“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④《史记·大宛列传》,第3170-3174页。《西域传》于“大宛国”下亦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
石声汉认为,《史记》《汉书》已交待得很清楚,苜蓿是张骞死后,汉使从大宛采来⑤石声汉:《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4期。。孙启忠在仔细清理了历代史料的基础上认为,苜蓿由汉使引入我国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而张骞带回苜蓿,虽然广为流传,但缺乏直接的史料证实⑥孙启忠、柳茜、那亚:《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草业学报》2016年第1期。。此外,桑原骘藏、陈竺同、张荫麟、长泽和俊等学者也认为正是这些不断西使的汉使拓宽了中国与西域的交通联系,由是使得苜蓿、葡萄等物种进入中国⑦[日]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49 页;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页;[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24页。。
实际上,《史记》《汉书》中的“汉使”是一群体称谓,既包含了西汉所派出的官方使节,同时也包括了多种身份的民间人士。例如,周伟洲即认为上述“相望于道”的汉使中,内有不少是商人⑧周伟洲:《两汉时期新疆的经济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此外,姚鉴、唐启宇、葛剑雄、樊志民等学者主张除去官方使节,西域物种的引入应当与张骞之后前往西域等地的商人、官员、兵士等密切相关,不能够将“汉使”的理解范围仅等同于“使节”,此说可信⑨姚鉴:《张骞通西域》,《历史教学》1954年第10期;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00页;葛剑雄:《从此葡萄入汉家》,海豚出版社,2012 年,第42 页;李荣华、樊志民:《“植之秦中,渐及东土”——丝绸之路纬度同质性与域外农作物的引进》,《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
然而,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按《大宛列传》行文,汉使大规模西行与采种苜蓿、葡萄发生在大宛之战爆发前,而《西域传》则记载大宛之战后,“宛人斩其王毋寡首……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⑩《汉书·西域传(上)》,第3895页。由此,学界对汉使是在大宛之战爆发前或战争结束后带回苜蓿展开了激烈争论11[日]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第49页。。
考察《大宛列传》《西域传》对于苜蓿介绍的相同之处,都与大宛马有着重要关系。《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书·西域传》之大宛国曰:“大宛左右……俗耆酒,马耆目宿”。因而,学者们认为作为大宛马的牧草,苜蓿与大宛马同来中国的可能性极高,所以大宛马进入中国的时间应与苜蓿引种中国的时间一致①于景让:《汗血马与苜蓿》,《大陆杂志》1952年第5期;裕载勋:《苜蓿》,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年,第6-8页;高敏:《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高荣:《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由此对于苜蓿进入中国时间的考察遂转向大宛马何时入汉的研究。
二、宛马来归与苜蓿引种中国的时段
沙畹、谢成侠、余英时、张波与候丕勋等学者依据《汉书·西域传》,认为西汉在大宛之战后获得大宛马,同时采种苜蓿、葡萄归汉②[法]沙畹:《中国旅行家》,载冯承钧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 年;谢成侠:《二千多年来大宛马(阿哈马)和苜蓿传入中国及其利用考》,《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55 年第3 期;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侯丕勋:《汗血宝马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虽然《史记·大宛列传》的真伪窜增问题一直是学人讨论的中心③朱润东:《史记考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188页。,但仔细研究《汉书·西域传》内容,多以《史记·大宛列传》为基础,而《汉书》编者在叙述西域情况时,时间性较为模糊,《大宛列传》则确实保存了若干重要的时代特征④[日]榎一雄:《史记大宛传と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关系にっいて》,《东洋学报》1983 年第64 期;余太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的关系》,载王元化编:《学术集林》卷11,远东出版社,1997年。。因此,研究汉代西域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不可或缺。
按照《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述,苜蓿与大宛马进入中国的时间当在大宛之战爆发前。《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⑤《史记·大宛列传》,第3169页。。此后,张骞从乌孙返汉时,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⑥《史记·大宛列传》,第3169页。。乌孙既然遣使入汉并以乌孙马为礼物,因而不能排除大宛同样以大宛马作为礼物奉献汉廷的可能性。如此,大宛马与苜蓿有可能于此时进入中国⑦[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425页。。至于入汉时间,张骞与乌孙使节于元鼎二年(前115 年)返汉⑧[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675页。,一年后,张骞逝世(前114 年),“……其后岁余,骞所遣大夏之属皆颇与其人俱来”⑨《史记·大宛列传》,第3169页。,可知张骞所遣前往大宛等地的副使在他过世一年多以后返回汉地,时当元鼎四年至元鼎五年(前113-前112年)⑩李炳泉:《西汉河西四郡始置年代及疆域变迁》,《东岳论丛》2013年第12期。。所以,如若上述推论成立,公元前113—前112年,将是苜蓿引种中国的时间上限。
此外,《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过世后,“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11《史记·大宛列传》,第3170页。。汉使大规模的出行存在两种可能:第一,大宛马已入汉,但数量较少,于是汉廷加派使者前去获取;第二,大宛马尚未入汉,武帝急切的想得到大宛马,于是大批汉使西行前去搜寻。因为出使的频率与人数较多,除去张骞,其他汉使都没有留下姓名,最后留下了大宛之战前“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的记载。因此,即便大宛未在前113-前112 年间向汉廷进献大宛马,在汉使随后大规模的出使活动中,大宛马与苜蓿也有极大可能性入汉①祁韵士对此表达了质疑:“疑武帝所得西域之马,未必皆出大宛,持以大宛马善,故随处有此名,其实凡属行国,无不产马。”然而,祁韵士并未提出相应的论据以论证其说。可参阅[清]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12《渥洼马辩》,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02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558页。。
上述沙畹等人的观点则明显忽视了在大宛之战前,汉使频繁西行存在将大宛马与苜蓿带回中国的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理解偏差,是因为该观点将大宛之战汉军所获的大宛马中的“善马”“贰师马”,等同于大宛马而做出的判断。《大宛列传》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②《史记·大宛列传》,第3174页。,《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如是说。对于“善马”,余太山与侯丕勋二先生认为即“贰师马”,即世人所熟知的汗血马③“贰师马”(Nesaean horse),古良马名,首见于希罗多德《历史》,原产于外高加索地区,分布地区大致西起伊朗西北部,东至费尔干纳盆地,南北沿阿姆河两岸分布。。侯丕勋认为,“善马”名称,并不包涵特别的涵义,就其本意而言,犹如汉语的“良马”“名马”之类,它是由张骞及后代人意译为汉名的④侯丕勋:《汗血宝马研究:西极与中土》,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62、72页。。从张骞言大宛“多善马,马汗血”之说可知,“善马”所指当是大宛马中最好的马,即汗血宝马。“贰师城善马”与“贰师马”,二者意在说明“善马”产于大宛国贰师城周围地区⑤余太山先生认为“贰师城”由“贰师马”得名,关于此内容可参阅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121页。。
关于关于贰师城的地址,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其地为Jizzax(今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⑥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92-293页。;另有人主张Ura tübe(今塔吉克斯坦粟特州乌拉秋别)⑦[日]内田吟风:《月氏の迁移关地理的年代考证(下)》,《东洋史研究》1938 年第3 卷5 号;[日]桑原骘藏:《大宛国の贵山城に就て》,引自氏著《东西交通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44年;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21-123页。。西汉时期的大宛国,其势力范围主要包含费尔干纳盆地,无论贰师城地处乌拉秋别或吉扎克,其地都当是西汉时大宛国的西境无疑⑧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第283-284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21-123页。。因而我们可以明确,随着汉使不断深入大宛国,汉使也逐渐获知“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嗜好骏马的汉武帝知其不可易得,于是遣使携带千金与金马前去求取贰师马。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大宛之战后,“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⑨《史记·大宛列传》,第3177页。的内容可以看到,即使大宛国都贵山城中也仅有“数十匹”善马⑩余太山先生认为这数十匹“善马”即“贰师马”,参看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22、145页。,而《西域传》载大宛之战后,“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11《汉书·西域传(上)》,第3895页。,可见贰师马即使对大宛而言也是十分稀有的宝马。
因此,在大宛之战前,西汉已有极大可能获得了大宛马,但只是一般的大宛马,至多类似贵山城中汉军一次所获的三千匹“中马”。学者轻易地将贰师马等同于一般的大宛马,然后根据《西域传》记载,便得出了大宛之战后大宛马与苜蓿始入中国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忽视了即使是一般的大宛马也嗜苜蓿,二者极有可能已于大宛之战爆发前进入汉朝的可能性。
总之,根据现有材料与前人研究基础,笔者认为公元前113年至公元前104年大宛之战爆发前,最有可能是苜蓿以及大宛马的入汉的时段。从现有的材料出发,在这个时段内,精确界定某一年为大宛马与苜蓿入汉时间都是极为困难的尝试。例如张平真在这个时段内界定元封六年(前105年)是苜蓿进入中国的准确年代①张平真虽有此论,但未举其所据,具体内容可参阅张平真:《中国蔬菜名称考释》,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此说是源于《资治通鉴·汉纪》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当年,安息、驩潜、大益、扜弥等国家遣使入汉,安息国进献给汉朝大鸟卵以及黎轩魔术艺人,大宛也有可能于此时进献宛马和苜蓿。实际上,从《史记》行文即可知安息等国的使节实际上是同张骞所遣副使一起来汉的,时间为公元前113年—前112年②《史记·大宛列传》,第3173页。,这与我们所推论的苜蓿进入中国的初始时间相符合。
三、中国引种苜蓿来源地“大宛左右”初释
对于汉使获得苜蓿的地点,《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汉书·西域传》之“大宛国”载“大宛左右……俗耆酒,马耆目宿。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基于这两条史料,我们可知中国是在“大宛”或“大宛左右”取得苜蓿的种籽③BoltonJ.L.,GoplenB.P.and BaenzigerH.,1972“,World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In Hanson C.H.(ed.),Alfalfa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dison,pp.7.。但目前学界尚缺乏对“大宛左右”所指的明确研究。
笔者认为,“大宛左右”实际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地理概念。它包含了两层地域意义,其一指的是大宛国与周边区域;其二或指大宛王都周围,即大宛国势力范围。首先我们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所载汉时大宛国周边国家作为考察对象,来考虑“大宛左右”所指的地域范围。按上两书载,汉时大宛其东有乌孙、扜弥、于阗、姑师等国;其西则为安息、条支与黎轩等国;南面为大月氏、大夏、身毒、难兜、罽宾等国;北面则为康居、奄蔡等国。
在所列的这些周边国家中,唯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④《汉书·西域传(上)》,第3885页。。因而也有学者认为,西汉采种苜蓿当源自罽宾⑤Chmielewski J.,1961,“Two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Rocznik Orientalistyczny,24.Ⅱ,pp.69-83.。从所传气候,地形和物产来看,汉代罽宾国的中心地区为犍陀罗(Gandhāra)的可能性最大,其盛时疆域包括喀布尔河(Kabul)上游与斯瓦特河(Swart)流域⑥[日]津田左右吉编:《白鸟库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第6 卷,(东京)岩波书社,1970 年,第295-359 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217页。。而汉时赴罽宾,乃自皮山前往,途中经过名为“縣度”的天险⑦杨巨平:《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路南道的开通》,《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西域传》描述縣度:“险阻危害,不可胜言”⑧《汉书·西域传(上)》,第3887页。。正是由于縣度路程艰险,难以通行,所以,汉廷往往送其使者至縣度而还。因此,西汉引种苜蓿当不会舍弃地理坦途的大宛而翻越縣度天险求于罽宾。
而关于罽宾与西汉的交通年份,《汉书·西域传》载“武帝始通罽宾”,余太山认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对于罽宾都未提及,因而只能推论罽宾与汉之交通发生于前114年和前87年之间⑨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229页。。但《史记》当中却无罽宾的相关记载,可以肯定至《史记》完成时(前91 年),中国方面对它还知之甚少,甚至无所知晓⑩杨巨平:《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路南道的开通》,《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因此,《汉书·西域传》所载罽宾的详细信息因源自《史记》成书之后。因此,根据上节所推断苜蓿引种的时间,可知西汉获知罽宾也出产苜蓿的情况,似当在引种大宛苜蓿归汉之后。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汉时罽宾虽产苜蓿,但似为黄花苜蓿,而非本文所讨论的紫花苜蓿①张平真:《中国蔬菜名称考释》,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西汉时期的条支、安息等地处于苜蓿初始起源地区的外高加索地区以及土库曼斯坦,因而其时出产苜蓿当属无疑。但在张骞之后,西汉与其交通并不十分顺畅,后来出现了“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②《史记·大宛列传》,第3173页。的情形,因此一定程度上不具备引种苜蓿的文化环境。至于大宛东面的乌孙等国,目前考古与文献材料都无法证实公元前113 年左右或更早时期,苜蓿已传播至乌孙地域。故而,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目前讨论西汉时期中国引种苜蓿的具体地域时,似当仍以汉时大宛国势力范围为最理想的地理区域。
对于汉时大宛国地域,白鸟库吉、藤田丰八与布尔努瓦均认为,应位于今天费尔干纳盆地③[日]津田左右吉编:《白鸟库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第6 卷,(东京)岩波书社,1970 年,第229-294 页;[日]藤田丰八:《大宛の贵山城と月氏の王廷》,引自池内宏编《东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东京)荻原星文馆,1943年,第1-43页;[法]吕斯·布尔努瓦著;耿升译:《天马与龙涎:12世纪之前丝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第12页。,然而,从《史记》《汉书》记载可知,汉时大宛国实际疆域则不止于此④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83页。。据余太山所考,西汉时大宛国疆域,其北面以塔拉斯山—吉尔吉斯山为界与康居相邻;其南则以阿赖山脉中的Karategin 与大月氏为邻⑤汉译喀喇特勤,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南部达拉乌特库尔干邻近区域。;其东以Kagart、Yasii 山脉与乌孙为界⑥汉译喀噶特山与亚辛山,两山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中部。;其东南以Terek、Talduk 与休循、捐毒国为邻⑦Terek 汉译为铁热克,该山口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苏菲库尔干(Sufi-kurgan)东南方,別迭里山口东北;Talduk汉译塔尔德克,该山口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萨雷塔什(Sary-tash)北。;其西面势力范围则至Tashkend-Ura-tübe 一线⑧Tashkend即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部;Ura-tübe汉译乌拉秋别,今塔吉克斯坦粟特州乌拉秋别。。岑仲勉的看法与余太山有所不同,他认为大宛国西面的势力范围可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吉扎克(Jizzax)⑨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83-284页。。二者的分歧在于,西汉时期大宛的西部势力范围是否能够突破锡尔河以西地区⑩或可认为,张骞离开大宛北上康居,再南下大月氏途中经行贰师城,由此得知大宛“多善马,马汗血”。相关研究可参阅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83-284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45页。。
《史记》《汉书》中记大宛国境有“属邑大小七十余城”,11《史记·大宛列传》,第3160页。但目前仅留下郁成、贵山(王都)与贰师三城的信息,这三城中贰师城是西部边塞。关于郁成的地理位置,主要有Osh(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城)与Uzkand(今吉尔吉斯斯坦乌支根Özgön)两种看法12白鸟库吉主张为奥什,岑仲勉认为在乌支根,余太山先生认为二说难分优劣。具体内容可参阅[日]津田左右吉编:《白鸟库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第6卷,第229-294页;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第294-296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23-124页。。这两地距离并不遥远,两地构成的地域扼守阿赖山与费尔干纳山交汇孔道,由此向西便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向东北、东南翻越以上两山脉即可前往西汉时的乌孙、捐毒、休循、疏勒等国,因而郁成无疑是西汉时期大宛国的东部要塞。
汉使出使大宛国,其王都当为出使最为频繁之地,也当是获得苜蓿等物种可能性最高的地区。目前对于大宛王都贵山城的地望,一种观点认为其地在kāsān(汉译卡散塞,城址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西北三十公里处);另有意见认为贵山城当为Khojend(今乌兹别克斯坦苦盏),目前这两种意见优劣难以判断①主张kāsān的主要有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与我国岑仲勉先生;主张Khojend 的主要有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我国学者余太山。相关论述可参阅[日]藤田丰八:《大宛の贵山城と月氏の王廷》,引自池内宏编《东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东京)荻原星文馆,1943年,第1-43页;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第288-292页;[日]桑原骘藏:《大宛国の贵山城に就て》,第118-142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16-121页。。最新的研究中,余太山先生提出地理距离等六条论据来论证汉时大宛贵山城当属苦盏无疑②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16-121页。。
笔者欲补充的是,从地形条件与城市历史来说,苦盏作为大宛王都似胜于卡散塞。苦盏扼守费尔干纳盆地西部出入孔道,为索格底亚那北方门户,锡尔河由此转北,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波斯居鲁士大帝于公元前545—前539 年攻占河中地后,沿锡尔河设立七个要塞,其中的核心要塞便是位于苦盏的居鲁士城(kyropolis)③[美]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三联书店,2017年,第58-60页。。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占据索格底亚那后,于苦盏设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Eschate)④Arrian,1983,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Translated by BruntP.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VOL.Ⅱ,pp.56.。继承马其顿帝国疆土的塞琉古王朝可能对该城重建,仍保留原名⑤G.M.Cohen,2013,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pp.252-255.。公元前141 年左右,锡尔河北的游牧人群——吐火罗人开始南下,吐火罗的Gasiani⑥Gasiani 属于吐火罗四部之一,首次提及吐火罗四部活动的是斯特拉波《地理志》。Strabo,1928,Geography,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VolumeⅤ(Books 10-1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49-250.部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建立大宛⑦吐火罗人南下索格底亚那问题可参阅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78-91 页;吐火罗建立大宛的历史,可参阅:余太山《古族新考》,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59页。。大宛王都贵山(kushan)即Gasiani的对译⑧E.G.Pulleyblank,1966,“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Jounr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1.Ⅲ,pp.9-39.。很有可能,当时南下锡尔河的吐火罗Gasiani部于苦盏立都,并以部族名号称该城“kushan”,汉译“贵山”。
从《大宛列传》《西域传》记载大宛“其俗土著,田稻麦”⑨《史记·大宛列传》,第3160页。,“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⑩《汉书·西域传(上)》,第3894页。;安息“其俗土著,耕田……城邑如大宛”11《史记·大宛列传》,第3162页。;大夏“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12《史记·大宛列传》,第3164页。来看,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似共处希腊文化影响范围内13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希腊化的马其顿帝国、塞琉古王朝是否将其势力挺进费尔干纳盆地内部尚缺乏资料支持,而苦盏所在的索格底亚那,则处在马其顿帝国、塞琉古王朝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辖范围。另外,苦盏、撒马尔罕等地丰富的定居农业文化遗存证明当时该地域具备文化一体性,而地处费尔干纳盆地内部的卡散塞较为薄弱的考古遗存则不具备上述文化特质14P.Bernard,1994,“The Great Kingdoms of Central Asia.In Janos Harmatta&B.N.Puri,G.F.Etemadi(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Ⅱ,UNESCOPublishing,pp.103;齐小艳:《索格底亚那农业经济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7年第1期。。
随着纳马兹加农业文化的衰落,青铜时代中晚期,该地区的农业文化人群已东徙北上,由此将小麦、葡萄或者包括苜蓿等作物传播至索格底亚那以及费尔干纳盆地。汉使出行大宛及其西、南部各国都要自大宛东境郁成向西横穿费尔干纳盆地到达贵山。在汉使由郁成至贵山途中必经行众多的“属邑”,这些希腊化的城邑的周围一定种植着小麦、葡萄等农作物①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因而汉使由此获得苜蓿存在一定可能性。
总之,从现有材料与研究工作中,笔者认为汉使在公元前113—前104年在“宛左右”所引种的苜蓿,极有可能在郁成至苦盏之间的地域,其地当今费尔干纳盆地中部,且尤以大宛王都贵山城可能性最高。目前,费尔干纳盆地与索格底亚那地区均尚未出土有关苜蓿的考古遗存,但索格底亚那地区深厚的农业文化传统早已为考古与文献工作所证实②齐小艳:《索格底亚那农业经济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7年第1期。,因而我们仍然不能排除汉使突破大宛国境于苦盏西南部引种苜蓿的可能性。未来进一步的考古与研究工作,会对汉使引种苜蓿的具体地域有更准确的解释。
四、苜蓿引种中国的多元历史情境与文化象征
布尔努瓦在解释丝绸之路上物质文化的传播原因时,将其分为自然传播与人为活动两方面,其中人为活动主要包括使节、商人活动以及王室通婚、军事战争等因素③[法]吕斯·布尔努瓦:《天马与龙涎:12世纪之前丝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耿升译,《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从史籍记载来看,苜蓿引种我国主要是由“汉使”完成的,但若从当时的历史情境追寻本相,我们发现苜蓿引种中国还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且更具独特文化象征意义。本节即从政治与地理等方面对此做一粗略分析,并尝试对西汉时期苜蓿初入中国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简略探讨。
政治方面,自西汉建朝,蒙古高原的匈奴就威胁着汉朝的北方边境。在双方的对抗中,西域地区的归属尤为重要。对于西汉来说,稳定河西四郡、北边边疆安全,就需控制西域诸国。而对于匈奴,除去军事价值外,西域的商贸收益与物产在匈奴游牧经济中占相当重要位置④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页。。公元前176 年,匈奴在攻击月氏的过程中,“定楼兰、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⑤《史记·匈奴列传》,第2896页。,从而在名义上控制了西域地区,进一步加深了西汉的边疆危机。武帝继位后,西汉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⑥《史记·大宛列传》,第3168页。,达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此外,丝路诸国在汉武帝和西汉统治集团看来,除具有助攻匈奴的战略价值外,主要就是盛产奇珍异宝⑦薛海波:《西汉经营西域中亚丝路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因而,汉廷不断遣发使节前往西域地区,以了解那里的山水、道路、社会、族群与物产、风俗,在此过程中,葡萄、苜蓿等域外植物也为汉使所携回。由此可以看到,苜蓿的引入,是在西汉国家边疆战略向西开拓的背景中实现的。
其次,在西汉时期,马匹当时是战争的神经中枢,也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支柱之一⑧[法]吕斯·布尔努瓦:《天马与龙涎:12世纪之前丝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汉文帝时,汉朝推行“马复令”,一匹战马即可免除三人兵役。景帝时,西汉开始于西北边郡设“牧苑”,“始造苑马以广用”⑨《汉书·食货志(上)》,第1135页。。武帝时期,“天子为击胡故,盛养马”⑩《汉书·食货志(下)》,第1161页。。武帝同时健全了马政的管理机构,并设天子六厩,厩马达四十万匹11[唐]杜佑:《通典》卷25《职官(七)》,中华书局,1988年,第705页。。苜蓿未入中国时,汉朝对于马匹的饲料采用粟、菽、麦等谷豆类作物,但这些精饲料,使得马匹“苦其肥大,气盛怒”12《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3070页。。同时,马匹消耗粟麦也侵夺了百姓的食粮,《盐铁论·散不足篇》就说:“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①[西汉]桓宽:《盐铁论》卷6《散不足篇》,陈桐生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297页。。出于对马匹的重视,汉使出行西域时便对当地的马匹与食料颇为留心,这是苜蓿作为大宛马的附属而被配套引种到汉地的直接原因②邓启刚、朱宏斌:《苜蓿的引种及其在农耕地区的本土化》,《农业考古》2014年第3期。。
地理方面,得益于张骞的出使,西汉与产有苜蓿的大宛的较早的建立了联系。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时,被匈奴所羁押,后从漠北西行至巴尔喀什湖南下,首先到达的西域国家就是大宛③关于张骞两次西使的路线,可参阅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3年第1期。。此后他以大宛为中心,北上康居南下大月氏、大夏,归国时则沿西域南道的于阗、扜弥等国经河西走廊返汉。《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归汉后向汉廷描述西域诸国的情况即以大宛为地理中心展开,“其(大宛)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弥、于阗”④《史记·大宛列传》,第3160页。。
同时,在叙述西域诸国之间的道路里程时,有半数以上国家间的里程计算以大宛为基点,大宛的王城距长安里数实际上是计算各国赴长安行程的基数⑤余太山:《〈史记〉〈汉书〉所见西域里数考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院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由此可知,当时西汉对于大宛的地理情况有充分的认识,大宛当是西汉认知西域的地理中心。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由于匈奴浑邪王降汉,以致“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⑥《史记·大宛列传》,第3167页。,张骞便从西域北道的楼兰、姑师、龟兹向西北到达乌孙,随后遣使分赴以大宛为首的葱领以西各国。
此后,由于乌孙与汉建立了联系,西域北道由此成为西汉连接葱领以西地区的主要通道⑦张德芳:《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对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支撑》,《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张骞以后的汉使便可沿此道先至乌孙,“若出其(乌孙)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⑧《汉书·西域传(下)》,第3903页。。道路的畅通,使得汉朝“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⑨《史记·大宛列传》,第3170页。。汉使前往这些国家大都要经行乌孙、大宛。对于大宛地理情况的熟悉、较为充分的历史联系与双向道路的畅通无疑是后续大宛马及苜蓿能够顺利引种中国的地理条件。
苜蓿引种中国,对于中国马匹的改良与牧草的丰富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苜蓿初入中国时具备的独特文化象征含义。对于大宛良马入汉,芮传明认为:“是因为帝王有德,才获得了宝马;它们的来归,表明大汉威名遍布天下,象征远方四夷对大汉的臣服。”⑩芮传明:《“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8页。笔者认为,此说同样适用于与宛马一同入汉的苜蓿,它们都是标志汉朝“威德遍于四海”11《史记·大宛列传》,第3166页。的象征符号。
苜蓿初入中国时,武帝“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使其适应中国的风土环境。伴随着西汉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西域各地使节云集中国,武帝命人于“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史籍记载西汉时期的离宫别馆位于关中地区,“前乘秦岭,后越九嵕。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12[南朝梁]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页。。可见当时面积广大的苜蓿田地已成为一种地理文化景观。武帝在邀请使节观看葡萄、苜蓿田地的同时还带领他们巡游各地,“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武帝的这些做法,无疑是一种夸耀性的“文化展演”13关于“文化展演”的定义及其学理分析,可参阅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299-306页。。此时面积广大的葡萄、苜蓿地作为汉朝对外展示中国土地包容西域物种的文化象征符号,使西域使节产生“中国有一独特之处,宇宙间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种植”的心理与文化认知①[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7页。。
因而,从表象来看,武帝邀请西域使节观看汉朝繁荣的城市,秩序的礼仪,广阔的葡萄、苜蓿田地是在向西域使节展示汉朝的富饶,以吸引丝路诸国与汉朝建立经济联系,实质则是从经济、文化区分华夷,从心理上对其造成“倾骇之”的文化冲击,以强化华夏在与西域诸国互动中的中心地位,使其倾心仰慕,纳贡称臣。
五、结语
张骞引种苜蓿的看法实际是源自王逸撷取与民间塑造,苜蓿引种中国的功绩应归功于《史记》《汉书》记载中的“汉使”群体。在苜蓿传入中国的时间方面,学界所提倡的大宛之战后,大宛马与苜蓿同入中国的观点实际将大宛“善马”“贰师马”混同于一般的大宛马,从而忽视了普通宛马与苜蓿在大宛之战前引进中国的可能性。
综合各方面信息,我们认为公元前113 年至公元前104 年最有可能是大宛马与苜蓿进入中国的时段。引种地域方面,费尔干纳盆地中部可能是汉使引种苜蓿的中心地区,尤以大宛王都贵山城的可能性最高。由于该地域的考古遗址中尚未有苜蓿种籽出土,因而不能够排除汉使突破大宛国境,于索格底亚那等地引种的可能性,这项工作还需今后进一步的深化研究。苜蓿引种中国的历史地理条件方面,汉朝北部边疆战略的实施,对于马匹与改良牧草的重视,以及对大宛地理情况的熟悉和前往西域道路的畅通是主要条件。
此外,苜蓿引种后种植于“离宫别观”的行为具有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它实际已成为中国土地包容西域物种的文化象征符号,以强化华夏在与西域互动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