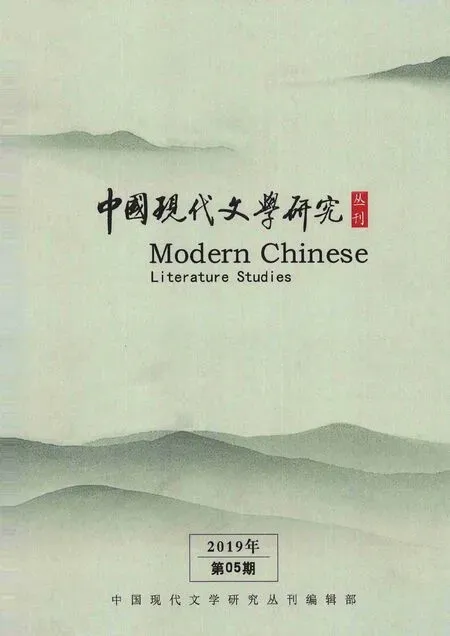风中的修为:论李修文《山河袈裟》
金 理
内容提要:《山河袈裟》中,纪实、虚构、抒情与想象等手法、文类联翩而来,熔炼成一种自由而开放的体式。李修文通过写作恢复了“人民”的肉身性与丰富性;而他笔下的抒情,正是顶礼心中两座神祇——人民与美——时的信靠。阅读《山河袈裟》,我们仿佛见证了一个人站在风中的修为,让“性”与“道”相互交融,由此领受进而理解历史、自然、人心与天道的消息,由此发抒情志、修己立人。
“像一面风旗”
在《山河袈裟》里面,经常出现一个失败的作家形象——“几年来写不出一个字”(《夜路十五里》),“这不过是一场失败的写作生涯掀开了序幕,但彼时之我却茫然不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写出过一些小说,更多的时候则是什么都没写,真相是,什么都写不出”(《别长春》),“一如既往,我仍然未能写出一个字”“心猿意马的呆坐,不光没有令我多写一个字,反而还将之前写下的全都删除殆尽”(《堆雪人》)……如果我们暂且为文类定位松下绑的话,可以这么说,这个失败的“我”,是《山河袈裟》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文本内部,“我”被创作焦虑症和愧疚感重重围困;在文本外部,已经十年没有创作发表的李修文捧出了一部大获赞誉的散文集。兴许可以这么认为,文本外部的“我”,通过《山河袈裟》的书写行为,拯救、赎回了文本内部、身陷重围的“我”。
已有论者注意到了这番有趣的情形,给出的解释依然遵循文类殊途的窠臼:“小说的虚构性以及叙述方法、技巧让他不是更深地进入了世界,而是让他轻巧地远离了世界……于是,他以散文的笔墨直抒胸臆,撷取生命中的片段与细节。”很多人认为,在与现实世界所签订的契约中,散文的真实性效力远高于小说;所以新世纪以来,当意识到小说在阻碍我们“更深地进入世界”时,顺理成章地向非虚构的散文呼救。观察当代文学中文类的起伏升降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且不说远的,我们也曾经被糟糕的散文败坏过胃口,那是1990年代,一个散文“大繁荣”的时代,顶着性灵、隽永、博雅、意趣等名号粉墨登场。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散文里,我们没有看到生活,看到的只是关于生活的姿态,而且是无比板结、单一的姿态;我们也听不到活的心跳声,因为这些散文家早在“骸骨的迷恋”中自缚手脚。对了,他们把上述姿态和迷恋视作自我赏玩、顾影自怜的趣味。真应该让蒂博代的黄钟大吕震荡一下90年代散文家们的耳膜:
我再重复一遍,趣味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东西。一位趣味过多的艺术家甚至会缺乏足够的勇气,不敢到大浪中去游泳。创造首先需要的是激情,而趣味却是对激情的限制。狄德罗写道:“激情有属于它自己的路线,它对别人走过的路不屑一顾。胆怯而慎重的趣味不停地在它的四周望来望去,它不敢冒一点险,它想讨所有人的喜欢,它是多少世纪和人类连续劳动的成果。”换句话说,趣味只作用于业已存在的东西,即已经完成的作品。如果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东西,孤立的趣味是无能为力的。
我注意到李修文对“雅趣”的否定:“我们一定要提防某种审美陷阱,它们往往是被那些所谓的风雅之气挖掘而成的,似乎每一回望,眼界里就只有晚明、小品之类的雅趣,但那些都是死的,这些雅趣背后所躲藏的离乱兴衰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结合蒂博代的话,李修文“到大浪中去游泳”,在冒险中创造,时刻聚敛着精锐之气去探索自由写作的高度。自由写作与何种文体并无直接联系,一颗苍白僵滞的心,掩藏在任何文体背后都不会有所作为。相反,在纪实之外,《山河袈裟》中也不乏虚构与想象,李修文过往文学实践中所熟稔的抒情(尤其见于《捆绑上天堂》《滴泪痣》这样的小说)、戏剧等手法、文类联翩而来,将《山河袈裟》熔炼成一种自由而开放的体式。所以,李修文并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文体家,这么说吧,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虚构抑或非虚构,倘若文体自足所构造的安全域,已经促使作家无法感知时代洪流中的鲜活讯息,那不如破壁而出,“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这几句话借自鲁迅,时在1925年,对于文士通人们的“雅趣”,鲁迅也是不胜其烦。虽是激愤的言辞,用来形容《山河袈裟》,竟无比妥帖。
李修文再三致意的诗人,还有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登高》),这种“在路上”的写作,也与《山河袈裟》神和。杜甫的伟大,不仅在于“忧国忧民”,所谓“诗史”并不只是道德评价,也应当是美学评价,重点在于诗人如何以个人命运水乳交融地接引社会现实,将一己心迹与行迹叠印于山河中,也同时芥子纳须弥,“古人的文章,只是他们生存和挣扎于世的证据,他们向山水张开,向时间张开,最后,他们让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去接纳山水、历史与时间,同时,又让自己的身体作为一根强劲而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着它们,最终,他们通过这种相遇,完成了对自己的命名,也完成了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共鸣”——李修文的这番评价,当可移用于杜甫,且堪称知己之论。所谓“诗史”,在生动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之外,可千万别忘了那根“强劲而敏感的神经”的感受力和创造力。我们都承认,文学作品的形式与社会环境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这一联系绝非机械被动的。一方面,形式的变化固然映照出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文学形式之于使其得以成型的历史语境,又能产生某种近乎“逆袭”的效果。杜甫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破坏固有的文学秩序和固定的形式,创造性地将传统中视为“非诗”的题材“果敢地写入诗中”,“杜甫不是被动的诗人,而是能动的诗人。不是顺从的诗人,而是叛逆的诗人。作为所谓现实性的文学家,他具有令人吃惊的写实能力、描绘能力,而另一方面,在他纵横的笔力之下,并不一定原封不动地顺从地描写作为素材的存在事物。即使对自然他必加以变形,或者他自己能动地创造出新的自然”。
我们同样应该这样来理解《山河袈裟》的“现实性”与“能动性”。现代作家中对杜甫别有会心的还有冯至,他为杜甫写过传记,同时留下过这样的诗句,在《十四行集》的最后,祈愿自己的那些诗,能够“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山河袈裟》也是一面风旗,活泼、跃动、开阔,“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能动地创造出新的自然”。
重新镀亮一个词
“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自序》)“人民”是《山河袈裟》的关键词,李修文重新镀亮了这个词。
“乡愁是对具体之物的想往,而不是对抽象的祖国的热诚”:对纳博科夫来说,俄罗斯存在于“脚踩在雪上吱吱的声音”;对于斯特拉文斯基而言,俄罗斯存在于“卵石路上的马蹄和车轮、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圣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声,还有马林斯基剧院中的嘈杂声”。如同乡愁之于流亡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李修文恢复了“人民”这个词的肉身性与具体性。在《山河袈裟》中,“人民”是这些人:风月场上唱着黄梅小调的陪酒女(《郎对花,姐对花》);木桥边放生一笼野鸽的年轻喇嘛(《青见甘见》);暴雨中被驱赶出墓园的疯子(《扫墓春秋》);城乡结合部的小医院里,病友认作师生,清洁工情若母子(《长安陌上无穷树》);湘西小镇祭鬼仪式上,拼命守护一盏油灯不灭(油灯代表不幸早夭的女儿)的归乡父亲(《鬼故事》);黄河岸边,将“我”解救出穷途末路、唱着花儿的弟兄们(《阿哥们是孽障的人》);东京神社昏暗灯下的盲眼酒友(《紫灯记》)……“人民”的背后,跃动着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也许身陷穷愁困苦,但总在泥海中挣扎向上,绽放出活的意欲与痛烈的追求;这些失意者的心灵并不枯竭,依然跃动着鲜活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生活逻辑,仿佛山上激流,尽管迫压在乱石峭壁间,但迸珠溅玉地去摸索流向,而任何一种流向,都代表着绝望中打开生活可能性的一种尝试。
更重要的是,李修文并不是作为旁观者在书写人民的故事,而是就在人民的故事中修行、成长,“所以,我并不是在朝一个庞大的词汇去靠拢,相反,我是在收紧我的道路,我要将‘人民’变成一扇我个人写作的窄门,而后一意向前,不管不顾”。今天的文学圈、知识圈里不少人自居为底层、大众的代言人,实则只是为了抵抗内心无处不在的虚无情绪而刷一下自身的存在感和道德优越感,失去了与具体的人、具体生活的实际交往和情感联系,任何发言只是一种空洞而抽象的姿态。《山河袈裟》中的“人民”并没有停留在概念和立场,转而如盐入水般溶化在一个个血肉饱满的故事中,这是人民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是“我”不能自已的、感性的文学实践要求,“通过这去和人民的内容深刻地结合,把握它,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使思想要求经过人民的内容的考验以后,成为更是人民的也更是自己的东西,使思想要求和人民的内容对立而又统一地形成血肉的‘感性的活动’”。
恢复“人民”的肉身性与丰富性之后,与人民结合的事业还未完成。“看着他们离去,我的身体里突然涌起一阵哽咽之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在今夜之前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并且亲若母子?由此及远,夜幕下,还有多少条穷街陋巷里,清洁工认了母子,发廊女认了姐妹,装卸工认了兄弟?还有更多的洗衣工,小裁缝,看门人;厨师,泥瓦匠,快递员;容我狂想:不管多么不堪多么贫贱,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迎来如此一场福分?”(《长安陌上无穷树》)李修文追求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会恨、有爱,而且还能超越一己局限,对周围人的境遇感同身受,由此,一个个具体的、鲁迅所谓“人各有己”的人民构成情感共同体。
为什么在人民共同体中,自我与他人的连带感必须饱含感情认同?我们可以通过《山河袈裟》中一则罕见的反面故事《一个母亲》,并且和鲁迅的《祝福》加以对读,来回应上述问题。在《祝福》里,四婶看待祥林嫂是出于做工得力(“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婆婆看待祥林嫂是出于交换(“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周围人群看待祥林嫂是出于“咀嚼赏鉴”的乐趣;连代表着现代启蒙价值、作为知识分子的“我”面对灵魂有无的追问时,也只是一再敷衍,甚至事后为敷衍寻找自我宽宥的借口(“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相比于礼教杀人的现成结论,在今天的时代里重读《祝福》,笔者更倾向于将祥林嫂的悲剧根源理解为工具理性的交往方式,只在乎榨取他人的实用价值,彼此之间无法袒露内心生活。祥林嫂根本不是麻木不仁的底层代表,强烈的生活痛感一再于她内心搅起波澜与悸动,她有倾诉甚至嘶喊的欲求,也曾作出种种突围的尝试。但祥林嫂从未得到过周围人的理解与呼应,相反,被那层层叠叠的冷漠与隔膜压迫着,最后,“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这样的世界里,“难见真的人”,要么缄口不言,要么戴着假脸嘻嘻哈哈。《一个母亲》再写了祥林嫂的悲剧,这位母亲“喘息着,拼命折断了一根竹子当作拐杖”,这番情形瞬间让我联想起电影版《祥林嫂》中艺术家袁雪芬的扮相,白发披散,踟蹰而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源于儿子,“儿子疯了之后,被人围观着指指点点,早就变得像种庄稼一样熟悉了”,除开这群围观者,同样还有一个随众敷衍、知识分子的“我”……缺乏爱和同情的纽带,社会就只是鲁迅所谓“沙聚之邦”。“人离开自然状态,不是因为与他人打交道对彼此更加有利,而是因为若没有共同的目的和一种共享的生活,就无法想象自己会活得好”,人之尊严的基础以及人类社会的本质是由“一系列广泛的依恋和关怀结为一体的”。
从《祝福》到《一个母亲》,给我们的启示是:缺乏情感滋润的社会人际生活与精神生活,仿佛干涸龟裂的大地丧失活力、寸草不生。尤其今天这样的时代,社交工具泛滥,但人人都深刻地感觉到“人群中的孤独”;日常交际活动并未中断甚至花样翻新,但人们很难在充分的情感联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深度交流。我愿意一遍遍重温《阿哥们是孽障的人》中的场面:寒冬腊月的黄河岸边,“我”和一面之缘的打工者们痛饮开怀、情如兄弟,当他们护送“我”脱险后,一声声花儿破空而来,如同不绝的情感长流,奔腾在浩荡山河间,“那歌声,既猝不及防,又撕心裂肺,就算有妖孽正在经过,那歌声也足以使它低头认罪,还等什么呢?如遭电击之后,我也扯开嗓子,跟着弟兄们一起嘶喊”……我还想说的是,《山河袈裟》中的这个场面,不仅是现实,也是李修文的美学。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曾反省何以“日本人不懂社交”,这里所谓的社交精神并非仅指呼朋引伴、群居终日,“而是每个人经常具备的、尽量想法子让彼此的对话更加具有普遍性、更加充实的一种念头”,所以在一个日趋“私性化”的时代里,文学的意义越发重要,“并不是说物质材料方面充足完备,我们生活的精神方面就会自动地丰富起来。如果没有想从生活中创造出‘诗’的主观能动性精神,那么无论到何时都是老样子”。我愿意再次重复上文中的评价:李修文是这样一位“能动的诗人”。
景语和情语
《山河袈裟》中有一些书写风景的篇章,于作者而言或许无心插柳,笔者却一再击节赞赏,比如这段:“白杨树站立在公路两边,就像一支清洁的朝觐队伍,一路铺展,朝着阿尔金山进行过去,在它们头顶的天空里,别无其他,只有蓝,透明和深不见底的蓝;这大海倒悬般的蓝也在阿尔金山的头顶,映照下来,却使得山顶上的白雪横添了淡蓝光芒,所以,这不光是我未曾遇见也从未听说过的淡蓝白雪,而且,随着阳光渐渐强烈,在那天际处,白的愈加白,蓝的愈加蓝。”(《青见甘见》)又如这段:“清晨时分,在兴安岭的密林中,我刚刚从梦境里醒转,山河之美便透过黎明的曦光铺面而来:举目所见,河流和群山全都被大雪覆盖,红与黑,牲畜与人民,怨憎会与爱别离,世间物事无一不像在母亲怀中哭泣过的孩子,安静,沉醉,不作抗辩,不发一言。”(《堆雪人》)据考,“风景”一词最早见于晋文,其初义“本来并非单指目中所见之物而已,还包含有温暖的感觉这层意义”,《说文》里“景”字本义原是“光”。但中唐以后,“风景”的词义发生变化,“景”字完全失掉了光明的含义,仅仅成为“景象”、“景致”的同义词,当时的诗人们使用“清景”“诗境”“幽景”等词,“这意味着和外界隔绝而自成范围的一个孤立的世界。这里所称的外界就是官场、尘俗的世界。这一群诗人把自己关闭在这孤立的世界里,与此同时,也就不管世间俗务,独来独往,专从大自然挑选自己喜爱的‘景’并以此构筑诗章”。这群关闭在孤立世界里的诗人延及后代,可能就演变成柄谷行人所谓“内在的人”,“只有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不过我们切莫忘了,在“风景”的源头,是山河与人心交相辉映的“温暖的感觉”。还是王国维说得斩截,一切景语皆情语。
《山河袈裟》中的抒情,百转千回,又浩浩荡荡,但绝不陷于个人的感伤自恋、浪漫耽美。如上文所言,情感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连接,是共同体的润滑剂。李修文重新召回了本雅明笔下“讲故事的人”传统,在民间大地行吟,一唱一叹间,唤起同情共感,调和伦理关系,凝聚社会人心的能量。
李修文笔下的情,是他顶礼心中两座神祇——人民与美——时的信靠。借李泽厚的话说,中国式的“情本体”根柢即在于“对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珍惜、眷恋、感伤和了悟”。《山河袈裟》让我们确信:中国民众内心依然葆有对生命意义感、对人与人内在连通感的诉求。这情的郁结与勃发,正是绵延于吾土吾民心中尽管微茫曲折却振拔向上的精神气脉。
领受与交接
《山河袈裟》是一本关于“领受”的书。
书中在在可见奇迹、神迹的降临:“我当然是从神迹里走出来的。因为直到第二天清晨,这场神迹还在延续”(《阿哥们是孽障的人》);“世间名相,数不胜数,各自无由相聚,再无由分散,但就在这无数聚散之间,真理和道路却会自动显现,此种流转,正好证明了做人一场的美不可言”(《苦水菩萨》)……寻常人难得一遇的气运,在《山河袈裟》中仿佛就是各种不期而至的风自行运送而来,好比周作人所谓“结缘”,“不必于冥冥中去找红绳缚脚”。这实在是让人嫉妒,何以天地独厚于他,何以上苍的开示与恩典总是垂青“这一个”。
还是回到李修文笔下的“我”,少年时代被病入膏肓的牛贩子骗去看苹果,一路上琐碎的经历在回忆中闪现出别样光芒(《看苹果的下午》);甚至在小镇破败庙宇里,目睹一条哀鸣的狗奋起反抗恶犬,也能转化出一番自我教养(《苦水菩萨》)……我们在冯至的《十四行集》中见证过这种“领受”的态度:“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时刻“准备着”的开放性态度,甚至被纳斯鲍姆总结为人类伦理生活的条件:“这种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种极为脆弱但其独特之美又与其脆弱性不可分离的东西),而不是一颗宝石。”见证奇迹的时刻是如何发生的?首先,人应该赤身“暴露在世界中”,迎接四面八方吹来的风。我们经常会刻意地“选择和拒绝”,但是里尔克认为“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入诗,只要它是真实的存在者”,“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所以其次,有缘领受奇迹的人,他的生命状态必是敞开的,唯有敞开,奇迹才能进入生命之中。进入愈深,感动愈深,就愈能超越个人利益限制,使一己之“我”触摸到与万物的依赖、与世界的联系。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宇宙的召唤、应答、渗透、融合,这一切似乎不免神秘色彩;但就像纳斯鲍姆提示的,更像平凡甚至脆弱的植物,而非珍贵的宝石,对一个虚己敞开的人来说,奇迹与神迹的发生,原就落实为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的迎来送往。
《山河袈裟》中有八面来风,这风仿佛自《庄子·齐物论》中涌出,“似鼻,似口,似耳,似析,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偶然邂逅的人与事、人事中的万千机运,机运中的“重负与神恩”……都在幕天席地的风的吹拂下开枝散叶。这个过程中,世界自在呈现,人心自行吐露;而文中的“我”,就在风中与人世交接。“交接”并不只是出于存在的被动与偶性,古人的意思要丰富得多:“与万物交,而尽兴以立人道之常。色、声、味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声、味也以性,色、声、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交接就是一个人站在风中的修为,让“性”与“道”相互交融,由此
领受进而理解历史、自然、人心与天道的消息,由此抒发情志、修己立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