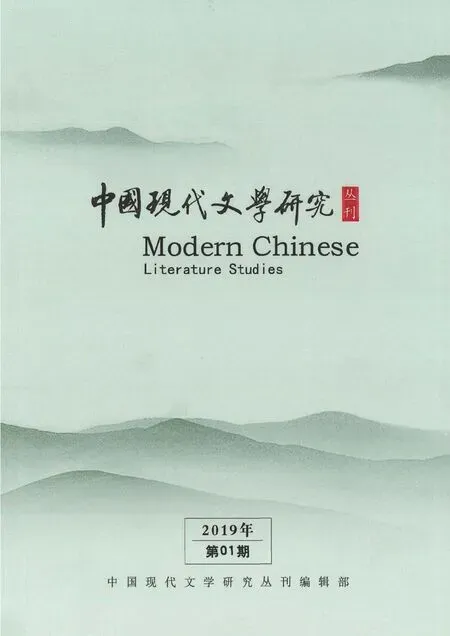《洗澡》中的两种“洗澡”和历史的同情
内容提要:《洗澡》中存在两种“洗澡”,一种是革命政权主导的公共“洗澡”。知识分子主要在语言层面参与“洗澡”,通过语言改造落后思想,通过语言表达进步理念,通过语言检验“洗澡”成效。另一种是以许彦成、姚宓为代表的自我“洗澡”,它不借助语言进行,在自我精神灵魂层面展开,不具有公共性。杨绛在《洗澡》中肯定知识分子精神改造和“洗澡”的必要性,但希望以“自觉自愿”的方式进行,以“完善自我灵魂”为目的。两种“洗澡”之间的分歧,也是普遍社会政治实践的要求和个体精神自由完善的要求之间的分歧,应以“历史的同情”的眼光看待这些分歧。
杨绛作品中,《洗澡》无疑是受到关注和评论最多的一篇。不只因为它是杨绛唯一的长篇小说,更因为它是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材的作品。作品中,“洗澡”也就是改造的代名词。在诸多评论中,似乎多从革命政权对知识分子改造这一主题切入分析,或立足知识分子道德形象去评价作品人物,而对《洗澡》中实际存在两种“洗澡”,两种“洗澡”的不同开展方式和手段,许彦成、姚宓为何也赞成“洗澡”等更为隐蔽的问题有所忽略。本文试图一一回答。
一 怎么说话:承载历史使命的语言
《洗澡》中这么说道:“在新中国,‘发言’是‘出面宝’。人家听了你的发言,就断定你是何等人。”①确实如此,在小说中,我们多次看到各色人物在公开场合的大段发言,尤其是在第三部“沧浪之水清兮”,“洗澡”正式开始,文学社一干人等轮番登台受“洗”。而这个被洗的过程,就是发言的过程,让自己的语言接受群众的检验。讲新话、用新词、表决心,大家的心思都在语言的表达上下功夫。语言的效用,随着革命的进程,逐渐被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言行本来是可分,且有时甚至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两个层面,但在革命推进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言之用渐渐地取代了行之用。仅仅依靠语言,就可以证明自己的内心和行为的性质。语言过关了,“洗澡”就过关了。
语言的效用为何被如此重视?语言如何成为“革命”中的通行证和护身符?为什么革命政权仅仅依靠语言就可以对个体做出是否改造成功的判断?人们又如何利用语言在改造中达到各自的目的,甚至与革命政权周旋?这是杨绛藏在《洗澡》中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要从意识形态和个体语言的关系中去理解。语言承载内容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不是将其归结于个体“讲大话、讲谎话、讲丑话、讲真话”的道德品质的评判。实际上,仅仅依靠讲大话,编谎话,是难以“洗澡”过关的。《洗澡》中最擅长扯谎的余楠,就碰壁数次,险些过不了关。丁宝桂式的夸赞伟大新政权的“好话”,朱千里式的贬损自身的“丑话”,以及第二次“洗澡”坦白陈述事实的“真话”,只要对于这个意识形态链条无用,就是“洗澡”不能过关的语言。
语言,是革命政权检验个体是否接受革命意识形态的试金石。马克思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②他强调,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的。革命政权确证个体是否已经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最直接办法,就是检测其语言,看其语言是否能成为传达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所以我们在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文化建构的历史看到,“语言”是其中的关键核心。
从《洗澡》中知识分子所处的“三反时期”而言,革命政权需要建构的意识形态思想,其实是一个话语程序,其中有四个关键意思:一是个体如何沾染了旧时代的丑恶;二是个体如何反映了旧时代的丑恶;三是表现“新时代好,旧时代坏”这个根本主题;四是反映出思想转变,即与旧时代划清界限的决心和投入新时代怀抱的渴望。
“洗澡一次性过关”的“标准美人”杜丽琳,就在这次运动中,成功地通过语言,完成了个体语言向宏大意识形态语言的链接与过渡。她先说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是大老板,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导致她“不知民间疾苦”,“只知道崇洋媚外”等,这是第一层意思,即个体如何沾染了旧时代的丑恶。在她身上,反映出的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女性”,具有相应的一切特点:“浅薄,虚荣,庸俗,浑身发散着浓郁的资产阶级气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信念。”个体的外表和旧阶级的特点挂上了钩,从个体的脓血中化验出旧时代的种种病菌和毒素,这是第二层意思。看到了新中国的朝气蓬勃,看到了朴素的、高尚的、要求上进的女同志是多么美,“和她记忆中那个腐朽的旧社会大不相同了”。这是第三层意思,新旧社会的对比。第四层意思最能反映出“洗澡”的效果,杜丽琳的发言也在这里最为“出彩”,她剖析了自己在旧时代的思想,着重描述了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又后悔又害怕”“苦苦思索”“想来想去”,直到有一天她“豁然开朗,明白群众并不要和我算什么账,并不要问我讨什么债。他们不过是要挽救我,要我看到过去的错误,看明白自己那些私心杂念的可耻,叫我抛去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留给我的成见,铲除长年积累在我心上的腐朽卑鄙的思想感情,投身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她转变的方向就是“不再迷恋个人的幸福,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努力顶起半边天,做新中国的有志气的女人”。③
旁听的许彦成也不得不承认,“丽琳很会说该说的话,是标准的丽琳”。关键就是,杜丽琳说了“该说的话”。哪怕许彦成认为这些话“只是空头支票,她的认识水平还很肤浅幼稚”,但是,这些话是“该说的”,让革命群众们通过她的语言看到她“决心要抛弃过去腐朽肮脏的思想感情,愿意洗心革面,投入人民的队伍”。所以革命群众们“是欢迎的,于是热烈鼓掌,表示欢迎”。④
那些夸奖革命的“好话”,恶心自己的“丑话”,掏心窝子的“真话”,或貌似深情的“谎话”,它们都过多纠结于“说什么”,而没有把重点放在“怎么说”上。其实革命政权对知识分子考察的重点是,要在他们说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其心路历程和思维转变,在发言中是否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论、辩证法,由此才能判断他们是否洗干净了,是否改造成功。革命政权在乎的不是说的事实,而是说的方式。没有把握正确语言表达方式的“浴客”们,只能呆坐一旁,面对一次过关的杜丽琳,徒有羡鱼情了!
二 灵魂之洗:个体精神的自我完善
杨绛并不是站在反对“洗澡”和反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立场来写作《洗澡》的,恰恰相反,杨绛明确表示了知识分子们确实需要“洗澡”和改造,她借许彦成之口说:“我愿改造思想,因为知识分子不改造思想,中国就没有希望。我只是不赞成说空话。”⑤在杨绛看来,革命政权主导的改造并不是不应该有,而是方法不当,成了说空话的“语言之洗”,没有达到改造的效果。她在《洗澡》的新版前言说,“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
对于杨绛的这个说法,笔者想阐述两个意见:第一,经过对知识分子的“语言”之洗,革命政权应该是达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至少清洗和建构了意识形态的载体——语言;第二,其中有部分的人在自觉自愿地“洗澡”,不过不是在做“语言之洗”,而是真正进行“灵魂之洗”。他们与“语言之洗”的知识分子有本质不同。
第一个不同之处是对人生外部事业追求的不同。杨绛对《洗澡》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做了较为夸张的处理,他们没有将学术作为事业的追求,给读者的感觉不过是整天琢磨着如何借文学社的场地,学着新时代的话语来实现个人上位的或大或小的野心。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的是一种“权斗之欲”,一种和学术主旨毫无关系的“事业追求”,学术最多是他们施展权斗的、运用娴熟的“职业”手段和工具。这些知识分子对学术的尊重和重视,还远不如《洗澡》中作为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如马任之、范凡等人。这些知识分子忙于在意识形态权力中周旋、利用、斗争,怎么可能会有能力或精力从事于学术本身呢?
倒是真诚将自己的事业定位在学术领域的许彦成,要冒着很大的政治和道德风险。他未将政权体制内的职业设计作为个人理想,也没有热情介入利益权斗。学术不是手段,是可以作为终极目的的存在,是可以带来价值满足的源泉,学术是一种“精神自足”,是一种不需要通过政治意识形态意义来背书的、来颁发许可证的价值存在。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许彦成甘心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狗窝”——说得好听点是“自己的园地”,甘心以学术为事业,甘心住“狗窝”。许彦成对此境遇怡然自得,颇有颜回之志的风范。在官职的诱惑前,如文学社领导请他出任图书室主任一职,他看清了背后将出现的人事斗争,清醒地予以婉谢。
姚宓同样如此,对于权斗之事,对于物欲之流,对用阶级论的观点研究西洋文学,她毫无兴趣。在她为了照顾病中的母亲,不但没有随同未婚夫出国,且连同未婚夫一块唾弃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姚宓的追求所在——不是个体的荣华富贵,不是权势地位——这些俗物难以寄予姚宓。而在当时文学社号召大家以阶级斗争为指针研究文学作品的大形势下,姚宓却以对人性论的挖掘作为论文的研究思路,自觉地把文学与政治分开。
第二个不同之处是内在精神世界表达方式的不同。《洗澡》中余楠一类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职业专长”,口若悬河、新词迭出、夸夸奇谈。由于在谈论言说方面,知识分子显得高人一筹,渐渐地就会产生一种在实践上同样高人一筹,进而以言语可以代替实践、以外界言谈代替内在思想的“幻觉”。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应该言语,只是不应该把暴露隐私以求改造的言语表达和内在精神世界的表达同等看待。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首先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行为实践来到达内部精神世界所需要的高度,而不是通过对语言的熟练运用来完全替代内部灵魂的升华。“洗澡”本应是针对灵魂的净化行为,而不是“语言词汇的替换游戏”。
可是内部世界存在的真实面貌,又是无法用外在的言语来真正表现和衡量的。杨绛通过许、姚二人,有意地表现出这一特点:一是许、姚之间心灵的交流,用的是书面文字的表达,不是用相互的语言表白;二是在“洗澡”中给了其他知识分子大段的语言表白,但是却有意省略了许、姚的“洗澡”发言过程;三是许、姚在书中唯一一次面对面、彼此直达心灵的语言交流,也被有意地一笔带过,二人具体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杨绛似乎有意不让发言成为表现许、姚二人真正精神世界的载体,这也是对语言之洗的又一种隐含的质疑,以此抗议对“当众发言”作用的“神化和滥用”。而这种将“当众发言”等同于个体内部精神世界的做法,其实就象征着“当众发言”所表达的内部精神世界,容易陷入虚假、多变、矫饰和夸张的境地。
三 历史的同情:现实没有完美的答案
许彦成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出发点,是对个体道德思想境界的要求,有种自古就有的圣贤意味,是一种高扬个人主体性的思想改造,手段是自觉自愿,目的是培养一般道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个体,他们实现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完善。
但革命政权对这种“洗澡”并不认同,因为革命政权在这种改造方式中,革命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无从介入。革命需要通过改造达到的目的是:树立革命主体对知识分子个体的绝对权威,从而达到最大效率开动国家机器这个“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目的。许彦成的改造法,不但无助于革命政权达成革命之目的,反而背道而驰。知识分子重视自身精神世界独立的个体价值理性和革命政权重视国家机器功效强大的工具理性,这两种理性历史中的剧烈冲突,实不鲜见。而调和二者,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多元、众多政治家的远见智慧和知识分子的理解支持、所处时代的形势和足够长的岁月磨合,等等,这么多必要条件,在当时的情形下,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历史苛求。
手段和目的的区别,许彦成是分得很清楚的。他不认同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洗澡”,是对这种改造方式和手段的不认同,而不是认为知识分子不需要改造。恰恰相反,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和杜丽琳的一次争论中,他说道:“你当我几岁的娃娃呀!你不用管我。别以为我不肯改造思想。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带头改造自我。知识分子不改造思想,中国就没有希望。我只是不赞成说空话。为人好,只是作风好,不算什么;发言好,才是表现好,重在表现。我不服气的就在这点。”⑥在这里,许彦成道出了他和革命政权对“洗澡”看法上的一致和分歧。他同意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思想,但不同意这种“洗澡”的手段,尤其是“语言”成为衡量“洗澡”是否有效的手段。许彦成要的是灵魂之洗,革命政权要的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意识形态编码工程师。
实际上,革命政权也需要灵魂之洗,不过是洗去知识分子过去自我的灵魂,用革命政权所规范的灵魂来重新填充它,而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之洗则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有效手段。许彦成大约远没有料到在这一层,革命政权想的还是和他“一致”。那么,真正的区别在哪?就是谁才是这个世界,包括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立法者”。革命政权已经通过斗争,成为实践领域的权威力量,这种权威力量必然需要延伸到精神思想领域。后者对前者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许彦成也许从未有过宏观层面的思考,也更未有过实践。革命政权在指挥一个如此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多各自独立的、不同的个体思想,哪怕他们在个体的道德意义上是完美的。而政治对历史社会实践的思考从不会从个体道德的意义层面出发,即使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但绝不是第一位的因素。
革命政权还无法学会如何统筹这些独异的个体思想,将它们有效纳入体系,吸收个体的有益的思想资源,而是简单地替换了事,这当然是最佳的方案。但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在实践社会理想的过程中,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开展它的思想改造工作,以期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资源,指挥着新中国的沉重转身和向着它所设计的路线前进。
可惜,个体实现良好道德行为的手段,未必能转换为政治实现良好实践的手段。这是一个政治历史永恒的困局,不单单只有那段历史才面对,不单单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
许彦成从自我完善的角度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他的答案只能限于自己。在社会宏大实践层面,他的答案过于完美,无从实践。对于革命政治而言,它没有能力、耐心和条件,将所有个体的智慧融汇为一个可以施之于全局的完美方案,政治历史的复杂,社会进步的需要纠结其中。它只能指挥所有的个体,以它所设计的方式前行,不容怀疑。它认为,新中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怀疑这条道路,将时间耗费在和众多个体思想的辩论上。不是任何历史问题,都有完美的答案,或者可以做出简单的对错之分。对于历史中的个体,要有历史的同情。在历史的难题面前,我们对革命政权希翼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进而要求的“洗澡”本身,应予历史的同情。在政治气氛浓厚的年代,对知识分子静守书斋,试图通过提升自身的人格修养,来追求真理、善良、完美、公正等美德的执着愿望,同样应予历史的同情。
注释:
①③④⑤⑥杨绛:《洗澡》,《杨绛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09~410、410~411、435、43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