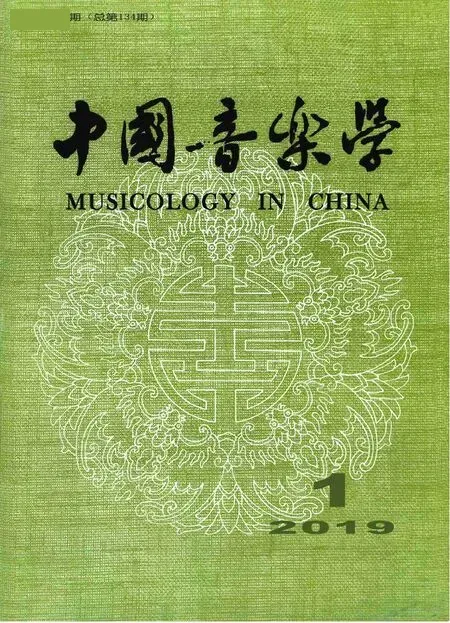手捧“中国音乐文化之火”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光
——写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首批《世界记忆名录》22周年
□邵晓洁
在当今中国,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不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对他们来说都并不陌生。不管他们对“非遗”的理解是否准确,了解是否深入,至少能从中看出,“非遗”这个词在中国的普及已相当广泛。殊不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宣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前,已于1992年为确保世界文献记忆不再受到损坏或丧失,发起了“世界的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MOW,后被称为“世界记忆工程”)工程,并于1997年宣布第一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的档案项目。收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作为首批项目被列入其中。至此,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成为首批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档案,更是全世界首个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音响档案,至今已有22年之久。
一、关于“世界的记忆”
1992年8月,萨拉热窝的两座顶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①1996年,萨拉热窝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修复工程,在被战火损毁22年之后,于2014年5月重新开馆,面对公众开放。和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在波黑战争中惨遭袭击,损毁严重,所收藏的150多万册珍贵的纸质文献毁于一旦。这个被称为“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蓄意焚书事件”使此前几个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显得尤为重要,也愈加紧迫。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遗产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我们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桥梁。它们大多保存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不同的介质和形式承载着我们的历史与记忆,展现着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文献遗产在自然因素或人为破坏的影响下,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坏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世界记忆工程”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楚地认识到人类遗产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之后发起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工程”之后,于1993年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1998年成立亚太地区委员会,并设立秘书处。2002年,国际咨询委员会修订并发布了《有关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总指导原则》)。《总指导原则》开宗明义指出,“世界的记忆”指的是记录世界人民集体记忆的文献遗产,它们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较大比例,记录了人类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是当今和未来世界共同体的历史遗产。《总指导原则》还列举了对文献遗产保存产生威胁的多种因素,分别是自然腐蚀、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明确了该项目的三个主要目标,即:一、利用最合适的技术手段促进世界文献遗产的保护;二、协助文献遗产的平等利用;三、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对文献遗产及其意义的认识。
“世界记忆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和重大成果就是建立《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亦被称为《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国际咨询委员会负责该名录申报项目的评价和入选。评估一项文献遗产能否被提名或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有几项主要的价值衡量标准,即:世界意义、起源和出处、真实可靠性、罕见性和独特性。该名录的申报和评估不仅是对文献遗产濒危程度和珍稀级别的遴选和判定,更是提醒、鼓励和强化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献遗产保护意识,促进和加强各国、各地区的文献遗产搜集、整理和保护工作。从历史文献到手稿,从照片到电影,从地图到网页,几乎一切能够用以保存人类历史记忆的载体,都可以成为文献遗产。迄今为止,已有来自世界各地近百个国家的200多项文献遗产入选该名录。截止到2017年11月甲骨文入选,中国已有11项文献遗产被列入该名录。
二、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申报首批《世界记忆名录》始末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的第二年,其文化组副组长亨利·洛珀斯(Henri Lop è s)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下简称音研所)。他参观完音研所收藏的资料后,在表示震惊的同时,遂建议时任所长乔建中就这批珍贵资料的关注和保护问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随后,音研所开始通过文化部外联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取得联系。1994年到1995年,音研所联系“世界的记忆”项目组,提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时长约7000小时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资料的转录工作提供援助,并根据当时中国的市场价格拟定了设备购置及音响转录的预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位专家回复了这一申请,并给出了75000美元的预算。
1996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挪威全委会和挪威国家图书馆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的记忆”国际会议,旨在讨论世界各国文献遗产的保护问题。此次会议的与会代表多达120人,分别来自65个国家,就“保护原始材料”“将保护纳入数据世界”“数据世界保护的立法”“优先保护计划和立项”以及“地区工作计划研讨”等多项议题展开研讨。音研所蔡良玉研究员受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委派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保护原始材料”的专题研讨中作了题为《保护中国的传统音乐遗产》的发言。①蔡良玉:《保护中国的传统音乐遗产——在第一届“世界的记忆”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7—274页。她对音研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收集的丰富音乐收藏进行了详细介绍,重点阐述了所藏中国传统音乐录音资料及其珍贵的文化价值,并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批宝贵的世界音乐文化财富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部负责人阿比德(Abdelaziz Abid)听后十分关心。同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其专家、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迪特里希·舒勒博士(Dr.Dietrich Sch ü ller)来到中国,对音研所的这批珍贵档案进行了深入考察。舒勒博士具有物理声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多重学位,是国际音响与视听档案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nd Audiovisual Archives,IASA)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对于音响档案的文化意义与价值有着独到的见解,多年来在音响档案收集、介质保护与数字化保存等技术和理念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此方面展开了较多国际间的推动与交流。在乔建中所长的陪同下,舒勒博士认真查看了全部音响的内容、存放方式、存放环境、介质类型、机器设备及其保存现状,并加以详细记录,随后与音研所领导和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研讨。最后,舒勒博士对这批历史音响档案和音研所所做的资料工作表达了由衷的赞叹,确认这批历史音响是“不可复现的,具有重大历史、学术、文化价值的,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笔珍贵遗产,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①蔡良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人民音乐》2002年第1期,第49页。,极力主张音研所向“世界记忆工程”项目负责机构提出注册申请。离开北京之前,舒勒博士还不忘强调,这些不可见的无形文化宝藏与长城、故宫那些可见的有形文化遗产具有同样的价值,人们将会逐渐意识到,必须像保护长城一样来保护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声音档案。

图1 乔建中(左)、蔡良玉(右)陪同舒勒博士参观音研所音响藏品(1996)

图2 张振涛(左)陪同舒勒博士参观音研所音响藏品(1996)
1996年12月,在舒勒博士的帮助和鼓励下,音研所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1997年12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首批被列入该名录的珍贵档案,也是全世界首批获此殊荣的音响档案。

图3 “世界的记忆”证书
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建设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作为这一学术机构的第一代学术带头人,杨荫浏、李元庆在音研所的初创阶段,将资料的搜集与普查作为首要学术任务,在音乐资料建设方面,勾画了建立一座集音响资料、乐器藏品、图书乐谱于一身的专业音乐图书馆的至美蓝图。这两位音乐理论界的学术泰斗,早在60多年前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艺术形式正在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清晰地意识到一些民间音乐甚至可能面临失传,努力倡议对民间音乐文化进行抢救性采访记录。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所提出的“抢救”一词在当时可谓是最时尚的学术语言和最前沿的学术思想。
音响文献是音乐最直接的呈现形式,对其进行系统收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音研所资料建设中最重要的学术任务之一。20世纪中叶,我国刚刚具备依靠现代科技手段获取音乐音响文献的基本录存条件。此间,杨荫浏的一系列民间音乐采访成为音研所田野工作的开端,为音研所音响档案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但为后人树立了学术风范,更为民间音乐采访提供了范例。②乔建中:《甘于寂寞无声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建所40周年献辞》,《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1期,第6页。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音研所开始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全国各地民间乐种的线索③肖梅:《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29页。。此后,资料采录和收集工作全面铺开。195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正式组建音档组。

图4 杨荫浏录制阿炳遗音的钢丝录音机、钢丝录音带(1956)
音研所研究人员一直利用一切机会采录珍贵的第一手音响资料,除1966年至1976年被迫终止外,他们的采录工作从未停止,或马不停蹄地奔赴全国各地搜集考察,或在北京本地采集各种表演和汇演,抑或邀请各地的民间艺人来北京录音,此外,还接收相关机构或个人的捐赠,转录广播电台的重要资料等。经过几十年漫长而耐心的积累,一份沉甸甸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逐渐形成。毋庸置疑,这是目前收录中国传统音乐最丰富、最完整的录音档案,不但包含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汉族音乐,还包括50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这批录音先后使用了钢丝录音机、开盘录音机、盒式录音机及数码录音机等录音设备,涉及钢丝录音带、开盘录音带、盒式录音带、数码录音带等音响介质,成为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录音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1994年,在黄翔鹏和乔建中的建议和组织下,经过音研所资料室工作人员的认真整理与编辑,中国第一部音响资料工具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录音磁带部分)出版问世,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本音乐学意义上的音响目录。该目录收录了12类音乐音响,分别是:古代歌曲、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综合类传统乐种、宗教音乐、歌舞及舞蹈音乐、民族器乐曲、合奏曲、现代创作歌曲、西洋乐器演奏的中国作品、歌剧及舞剧音乐和有关音乐的其他音响资料。从“世界的记忆”国际项目申报表中所列的文献描述和目录细节中可以看出,这本音响目录是项目申报时的重要依据。

图5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书影(1994)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具有独特的意义和珍贵的价值。从内容上看,其所收录的均为最原始的录音,几乎涉及中国音乐的各个层面,许多音乐音响的采集都是采录对象在非表演状态下完成的,是他们在生活仪式中最自然、最本真的表现,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采访对象是第一次接受采录;从采录行为上来说,这种实地考察已绝非简单意义上的采集和保存,而是有计划地从学术研究角度所进行的科学采访记录,并最终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学术史上不得不书的浓重一笔。显然,采录者所希望采集的音响资料“不是艺术音响,而是生活音响”,他们的采访行为也“不是艺术行为,而是学术行为”。①张振涛:《按下录音键——杨荫浏、李元庆与音响资料的建设》,《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1期,第17页。毫不夸张地说,这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所记录的已不仅仅是音乐形态和音乐表现形式,而是当时人们音乐生活的写照,是社会文化背景的侧影,更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
在此项目所提交的“世界的记忆”国际项目申报表“管理计划”一栏中,两家兄弟研究机构——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馆被提及。其中谈到,这两家机构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中国地方戏音像档案,如果项目入选,拟申请一并予以保护。无独有偶,2002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由恭王府迁入现址,在原资料馆的基础上,合并分散几处的戏曲、音乐、美术等研究所资料室,正式组建扩充为目前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机构的合并无形中促成和实现了资料的汇聚。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充实,有关地方戏曲音乐和曲艺音乐的相关内容,无论数量还是种类,较申报前都增加了许多。如今,这份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已难以估量。
四、国际合作探索数字化抢救与保护模式
技术与文化相互作用,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和外在的因果关系。录音技术的出现几乎颠覆了人们对人类历史与文化的认识理念和认知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对历史文化的记录手段和保存方式,同时,还促进了一些学科的发展,甚至催生了一些学科的发生。
然而,与记录文字或其他历史信息的媒介载体一样,录音载体介质及其播放设备或多或少也会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难题。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录音系统中所用设备及介质的新旧更替加速,寿命缩短,因此,如何正确地利用现代技术,采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全方位地改善历史档案物理介质的保存状况,尽可能无损提取物理介质中所保存的内容,便成为了历史档案保护的关注重点和重要课题。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记忆工程”提出了一项新动议,即保存数字化遗产,使其得以为世界人民所共享与利用。基于此,2003年,由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庆善担任课题组组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试验项目“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UNESCO Project for Digitizing Recor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正式立项并启动。
作为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化抢救工作的前期试验和基础工作,“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项目旨在“发现并解决具有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濒危音频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为规模化抢救音频档案遗产提供可行性方案”①王雨桑:《“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试验项目”成功报告》,《艺术科技》2005年第3期,第42页。。该项目的专业技术合作方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公认最早的、有百年历史的音响档案馆——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Vienna Phonogrammarchive)。项目组首先从申报的7000小时中国传统音乐录音当中,以载体类型,濒危程度,内容的珍贵性、经典性与民族多样性为筛选标准,初选出120盘开盘录音带进行了数字化转储,之后,对其中32盘共127段音乐素材进行精选,最后,将其中36段音乐制作成《中国传统音乐典藏精粹》CD样本(总时长67’),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部门。项目组专家萧梅研究员赴巴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交流与社会信息部做了汇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认为,“该项目的工作流程及其积累的经验与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濒危音响档案抢救具有实质性的示范意义”②参见萧梅《“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试验项目成果汇报》,内部资料,2004年。。

图6 舒勒博士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指导音响档案数字化抢救与保护工作(左起:萧梅、王雨桑、曹明申;2003)

图7 《中国传统音乐典藏精粹》CD(2004)
此次工作汇报及部分成果也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交流与社会信息”栏目的当日头版头条。这是国内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和资助下,与国外权威机构联合进行的关于历史音频档案抢救与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此次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第一,摸索资源特点,鉴定资源濒危程度。项目组通过摸索和鉴定,了解到这批档案所含录音介质的濒危程度已经超过了之前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时的状况,同时,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与实践无形中提升了项目组成员对录音介质的认识和鉴定能力,增加了他们的相关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第二,学习、理解并实践相关国际标准。第三,组建专业团队、形成工作模式。基于原始资料的特殊性,由民族音乐学家、音频工程师、音响档案资料管理者三合一的工作模式应运而生。此外,项目组在此次合作试验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元数据的错讹、缺失、名称不统一;音乐类型繁多导致分类困难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之后音响档案数字化抢救与保护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的数字化抢救及数据库建设
在良好的国际合作基础上,根据项目前期试验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数字化抢救与保护项目自2005年开始启动并逐步展开。此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的组建已使中国传统音乐音响资料得以整合、充实。面对更为完整、丰富的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将音响载体的物理介质保护和音响内容的数字化转储作为项目的终极目标,似乎已无法满足资源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搭建一个资源丰富、查询便捷的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数据库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项目所期望的最终成果。
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抢救保护项目全面借鉴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国际通行的操作标准(即由国际音响与视听档案协会①国际音响与视听档案协会成立于1969年,从国际音乐图书协会派生而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众多团社成员之一。协会宗旨是支持、鼓励、促进视听档案的相互交换、编档方式设计、音响档案使用、版权及其保护、保存等诸多领域的信息与专业交流。协会内根据专业不同,设有6个委员会,分别是分档编目委员会、音响目录委员会、国家档案委员会、分国与相关组织委员会、广播音响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制订的技术标准:IASA—TC03《有声遗产的维护:规范、原则与保护策略》和IASA—TC04《数字音频对象的制作与保存指南》),从设备配置与环境搭建、人员组织与机构建立、操作标准与工作流程三个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为全面掌握国内外音响档案数字化抢救与保护的现状和趋势,同时确保项目质量,项目组多次赴国内外进行考察调研②2007年,项目组再次赴奥地利,对奥地利科学院国家音响档案馆等地进行了为期9天的学习调研,此外,还先后对北京、上海、绍兴、广州等地的相关机构和个人进行了考察学习。,汲取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经验。针对不同的音响介质,项目组分别制定数字化采集工作流程和采录标准,确立音频采集规范,同时,根据载体介质的保存状况和数字化采集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还放设备,分析研究解决方案。为全面保障数据安全,项目组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制定安全策略,以数据安全为最高准则,专设数据中心,部署服务器、防火墙等,同时建立专门的数据容错和备份系统,采用在线、近线、离线相结合的存储方案。为保证元数据和专业资料信息的科学与规范,项目组组建了由音乐研究者、音响工程师、档案管理员构成的多学科互补的专业团队。项目组深知所面对的录音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在对其进行数字化转储的过程中坚持秉承保存历史信息、忠实原始音响的基本原则,不对所采录的音响做任何降噪之类的美化与修饰,以保留记忆,还原历史。

图8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媒体资源数据库截图
一个优秀的音乐音响数据库应具备哪些特质呢?无外乎从数据库资源和使用体验这两方面予以考量。从资源来说,优秀的音乐音响数据库里的资源应该丰富多样、种类全面、稀有珍贵。任何资料库的搭建都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目标、有计划、分步骤进行,大多会经历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就这一点来说,正在搭建的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数据库具有先天的优势,此不赘述。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要实现良好的操作体验,首先需要对数据库里的所有资源进行全面的分类整理,厘清逻辑关系,形成合理的结构,同时分析使用者的类型和特点,从不同使用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把握原始信息和音响信息来准确描述数据,科学全面地揭示资料的信息属性,使元数据与对象数据达到准确对应,从而清晰地呈现出查询结果,使使用者在最便捷的方式下获取最全面、最深入的结果。显然,这些衡量准则对数据库资源的规范和标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在被作为数据库资源进行衡量时显露出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和内容多种多样;二、学术界对中国民间乐种的研究日益广泛且不断深入;三、由于历史原因,所采录资料的原始著录信息不统一,部分信息不完整或者记录有误。对资料进行科学整理,是构建一个纲目有序、逻辑清晰的检索系统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录音资料的纷繁复杂给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早在1988年,音研所音响资料组的成员曾对所藏中国音乐音响资料的分类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讨论和思考。基于已使用了30多年的五大类分类法①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五大类,即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已无法适应当时的音乐研究现状,他们认为,“不存在永恒不变和面面俱到的分类方法”,并就此提出了若干思考,拟定了部分原则。②周沉执笔(音响资料组讨论):《从民族音乐研究的角度考虑中国音乐音响资料的分类——对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音响资料分类工作的体会》,载《音乐学文集——纪念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建所40周年》,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第1308—1316页。而如今,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数据库中的检索框架是在参考了已出版的各种工具书中基本定型的分类方式以及多年来在实际运用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分类方式而制订的,是一个能兼顾各种需求、真正实用、方便的数据库检索系统。③李玫:《数字技术与音乐》,载《数字化时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现——中美文化论坛文集》,贾磊磊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如上所述,音响资料的复杂和参差不齐给分类整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因而,这个数据量庞大的专业数据库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断地被打磨和完善。
结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中,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具有同等价值。视听类档案作为文献遗产的一个类型,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声、像来记录鲜活的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事项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记忆工程”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可以说是“天然同盟”。④迪特里希·舒勒:《“世界记忆”与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国艺术报》2002年12月27日,第3版。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建设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音乐家黄翔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的《小序》中把它誉为“中国音乐文化之火”。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演进,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某些音乐文化形态和音乐文化事项或正无形中发生改变,或已逐渐消亡殆尽,幸运的是,这份档案所保存的大量早期中国传统音乐能使我们及后人窥见她们原来的模样。这份珍贵音乐遗产的守护者惟有心怀敬畏之心,抱以严谨审慎的态度,才能不负先辈学者,手捧“中国音乐文化之火”,用科学的方式保护和传递这一束中华传统文化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