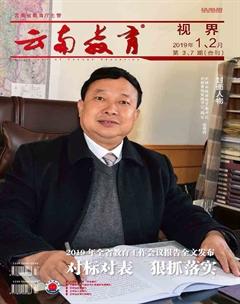最后的村小
晨光熹微,9岁的杨丽和同学结伴走在通往学校的山路上。
天气尚好时,她们需要翻过陡峭的小土山,半小时后抵达学校。遇上下雨天,她只能更早出发,绕山而行,才能平安地赶上8点的早读。
杨丽的家在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畔的山区。她家所在的江陵镇十二湾村位置偏僻。杨丽现在是吕秀清小学四年级学生。她父母在常年外打工,很少回家,爷爷卧病在床,家里仅有奶奶照看。
上学路远,杨丽从未享受过家长的接送。离家步行半个多小时的吕秀清小学,是距离杨丽家最近的学校。十二湾村距离镇上10公里,镇中心小学不提供校车,小学生也不允许住宿。如果选择去那里读书,意味着只能走读,若从家里出发,单程需要步行一个多小时,而十二湾村附近已没有其他“村小”。
像杨丽一样在吕秀清小学就读的孩子,还有46名。这所以教师名字命名的学校是为数不多的民办小规模学校,学校对孩子们免学费。吕秀清告诉记者,学校如今举步维艰,勉强维持,“如果政府不增加经费,学校顶多还能再开一年”。
教育部定义,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包括下属各教学点,是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教育的基本格局是每个行政村设立小学,下属的各自然村设教学点,推广“一村一小学”的办学目标。但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格局被打破:一是计划生育等原因导致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减少约四分之一;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三是持续10年之久的大规模“撤点并校”。
吕秀清小学在“撤点并校”的浪潮中得以幸免,是因为小学生们需要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据记者不完全了解,南充市高坪区至少有12所民办小规模学校,分散在当地的10个村子里。它们多为“一师一校”民办教学点,受乡镇中心校管理。
但如今学生减少,日常开支沉重,学校财务吃紧。多位民办老师称,高坪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在“谈判”时表示,钱只有这么多,财政预算有限,不能再增加经费,“生存不下去就走人”。
“这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吕秀清说。而当地家长则表示,村小一旦被撤并,孩子们只能舍近求远去中心校上学,这对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家庭而言,经济负担雪上加霜。
“民办教学点在全国范围内相对少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很多公办学校的待遇,它们都无法享受。是否能够得到帮助,就看當地政府的意愿了。”
2018年5月,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全国有农村小规模学校10.7万所,占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4%;在校生384.7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5.8%。这一数据,和两年前的统计相比,继续下滑。
“最穷最苦的学生”
早晨8点,村角一座两层楼的平房里,传来阵阵早读声。民办教师吕秀清满怀心事,在教室里走动巡视。上个学期近70个孩子,到这个学期开学就只剩47个了,今年没再招一年级。
生源不断流失,但仍有许多家庭坚持把孩子送来。如今在吕秀清小学就读的孩子们,家庭境况在周边村庄中属于最差的一类。
五年级学生刘静与患病的外公外婆相依为命。她父母离异之后,均外出打工,逢年过节才偶尔回家看看。
刘静家所在的搽耳镇十三村远在十多公里外。她每天清晨6点就从家出发独自上学,步行到学校需要一个多小时。如果要去镇中心校读书,她单程需要步行二十多公里。
“上学要经过火车站,走山路,走马路,还要经过一个洞子。”刘静说。她说的“洞子”是一条没有照明的隧道,昏暗潮湿,常年积水,需要几分钟才能穿行通过。每次走到这里,刘静都很心慌。“其实挺辛苦的,挺害怕,但是没办法。”
“来我们这儿上学的都是最穷最苦的学生”,吕秀清告诉记者,他们父母外出务工, 98%都是留守儿童,大多来自低保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单亲家庭。
为给家庭增收,父母们纷纷外出谋生,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南充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黎明告诉记者:“南充市是劳务输出大市,很多农村孩子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由爷爷奶奶照顾。”
2017年12月,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发布《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调研报告》,四川有农村留守儿童93万人左右,占全国留守儿童数量10.3%。其中,南充市留守儿童数量在全省高居不下。2018年1月,据高坪区人民政府统计,高坪区留守儿童高达3.6万名。
贫困让村民们少有选择。曹家沟村位于江陵镇东北部,属于川北地区典型的丘陵山区,也是江陵镇最偏远的一个村,村子293户人家,920人散居于此。没有厂矿,种植和养殖分布零散、不成规模,当地百姓致富无望。
2017年,曹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赵明在调研中初步确定,本村共55个贫困户和145名贫困人口。高坪区的情况不容乐观,多年以来为四川省级贫困县,直到2018年7月才宣布脱贫摘帽。
“村里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小孩,没办法去更远的中心校读书。根本负担不起租房、请人看护的费用。” 远在广东省东莞市打工的一位父亲显得忧心忡忡。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没得办法,不然谁不想把孩子送到中心校。”
费用差距有多大?另一位在当地打工的父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吕秀清小学读书,一个学期交220元左右的教辅费和保险费即可,总开销控制在700块左右。但去镇里读书,要租房子,请人照顾孩子。一年下来,花费近5 000元。这对整个家庭而言是一笔“巨款”。
曹家沟村委书记叶万财也说:“家里有钱的就去城里面读了,镇上读书也不交学费,但是其他费用就高多了。在那里要租房子,大人去带陪读,加起来不得了。”
之所以在镇里读书费用如此之高,是因为镇里的学校没有校车也没有住宿。高坪区会龙镇众望小学的民办老师顾忠荣告诉记者:“公办学校领导及公办学校教师怕出安全问题,怕负不起责任,所以一至六年级的学生不住校,没有民办小学校点的地方,家长只有带着孩子在集镇上租房。”
租房上学为留守家庭平添困扰。彭凯是吕秀清小学三年级学生,他的爷爷奶奶平时在家务农,支撑全家人生活。“去中心校的话,我们家要多出很大一部分的负担,路程太远,孩子还这么小。如果去照顾他,家里的农活就没人做了。”彭凯的爷爷说。
多位家长表示,如果吕秀清小学关停,在保证孩子不辍学的情况下,只能去中心校上学,家庭因此将更为贫困。
“小而弱”“小而差”
吕秀清小学位于南充市高坪区江陵镇曹家沟村,距离南充市区 40 多公里。它的前身是一所上世纪五十年代设立的公办小学,原名江陵五村小学。1991年,江陵五村小学位列被撤并名单之中。在村民的挽留下,政府将该小学“委托”给代课老师吕秀清,并将这所公办校转变为民办校,更名为吕秀清小学。
吕秀清小学是村子里唯一的学校,它承担周围3个行政村的留守儿童的上学问题,最远的孩童需要步行10多公里。学生们被分进三个复式班,即幼儿班和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一间教室里,坐着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四年级学生最大的已经13岁,最小的9岁。
“小而弱”“小而差”成为小规模学校的普遍画像,校舍简陋、师资紧缺、经费紧缺是它们的共同难题。
2018年3月,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张翼楷曾来吕秀清小学调研,萧条的景象令他难忘:“一个木头房子,一座容纳四间教室的双层教学楼,还有一间租借来的小厨房,不到10平方米的主席台上,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
吕秀清小学的教室里摆放着几排桌椅,表面可见漆面掉落。教室一角摆着一个矮脚书柜,四大名著等经典作品,均为社会捐赠。教室最前方,只有一个简单的讲台和一块黑板,城里已普及多年的多媒体设备,在这里仍是不可得的奢侈品。
尽管在外界看来,吕秀清小学教学条件远不达标,但像这样拥有独立教学楼的民办教学点,在当地寥寥无几。剩余的这些民办校中,大多租用村委会的办公场地和普通民房,没有财力自建校舍。
根据南充市政府2015年公开的数据,高坪区有小学141所,其中小学教学点高达92所。据高坪区当地一位教育工作者透露,这些村小早已被撤点并校,大多“名存实亡“。幸存的教学点之中,民办老师以一己之力承担教学任务,在当地已经司空见惯。
“最多的时候,我要教三个年级的课程,”高坪区天峰乡梁彩蓉小学校长梁彩蓉表示,每年大概招三四个孩子。为了集中统一學生的年级,只有一个孩子来报名时,她通常会婉拒,或是请孩子下一年再来报名。
“实在太辛苦了,很多时候我都不想招生了,但是我又不能走。如果让孩子们去镇上读书,很多家庭也负担不起,”梁彩蓉说。
贫困积重难返。多位民办老师表示,每年都给当地教育局写信,反映情况,希望能解决老师们工资和养老待遇,提高农民办义务校点的发展经费。但年年和教育局“谈判”后,现状得不到改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承诺,最后还是以失望告终.”高坪区佛门乡金花村小学民办老师杨成芳说。
被遗忘的代课教师
师资匮乏是小规模学校质量提升的一大瓶颈。南充市12家民办教学点中,教师年龄均为50岁以上,大多是本村或邻村人。这些民办教师作为乡村基础教育的兜底者,多年来几乎陷入被遗忘的境地。
由于教学环境条件差,自上世纪70年代起,政府就没有派驻过公办教师,教学任务一直由民办教师承担。这些教师在公立学校教书,却没有事业编制,被视为临时代课,虽长期在岗,却同工不同酬,无法享受在编教师的工资待遇,被称为代课教师,2006年全国共44.8万人,其中农村中小学有约30万人。当时各地涌现对代课教师的补偿和转正争议,上访不断,教育部曾宣布将代课教师全部清退,但对教育和教师的多年欠账却难以清偿,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在南充,“撤点并校”后当地一些村小纷纷转为民办,代课教师的身份更为尴尬。
目前,当地每年都下派部分特岗教师弥补师资的不足,但基本只能派到乡镇中心校,村小和教学点无法享受。
“条件太差了,谁愿意来我们这儿?”顾忠荣告诉记者,从自己接手民办校后,就没有领到过任何工资,五险一金等待遇从未享受过。
教师的收入哪里来?据记者了解,当地财政会对学校发放生均经费,除此之外不再给教师发放工资,老师们的收入不得不从有限的生均经费中支取。
高坪区走马乡精英小学校长姜尤林说:“养老保险是我们自己买的,国家只是给了我们农村户口买养老保险的资格,没有给我们出一分钱,农村医保就是我们自己买的,今年就交了180块。”
一边教学、一边务农成为这些民办教师的常态。“老师都靠周末种点庄稼来获得收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姜尤林说,“经费一般是6月或是12月才发放,平常是一分钱都没有,就是靠家里人补贴。我老婆在家里喂点猪,喂点鸡,把它们卖了,钱拿来补贴学校。”姜尤林目前住在几十年前建的青瓦房里,父母和妻子生病,儿子在外地上大学。
吕秀清开垦了教学楼旁边的一块菜地,利用课余时间种植蔬菜和粮食,勉力度日。他们全家“以校为家”,生活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屋内狭小,丈夫只能睡在教室后方,他的床由两张儿童桌板床拼凑而成。
“我是村子里唯一的高中生,如果我不教这个书,现在都买了房,都有存款,各方面的待遇,比现在不知道好哪儿去。”吕秀清说。
困境之源
在民办校教师们看来,他们今天的困境缘起于当地“撤点并校”的风潮。作为该政策的幸存者,当地教学点由公办转为民办,代课教师遭清退。之后,教育部门却无力安排符合标准的师资,只得安排被清退的代课教师继续授课。而政府的财政投入却不足,教师短缺、待遇不公、经费紧缺等问题日积月累。
据记者了解,12所民办校前身均为公办乡村小学,大多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有超过50年的办学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的老教师陆续退休之后,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当地行政和教育主管领导决定,用聘请代课教师的办法缓解用人之急。多位具有高中学历的村民被当地政府劝说,回到当地小学成为代课教师。
顾忠荣便是代课教师一员。1984年,19岁的他在广东打工,月薪约为1 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后来村支书说让我回来教书,并说可以转为公办教师。”顾忠荣回忆道,当时工作比较稳定,但听到娃娃没学可上,再加上可转为公办教师,再三迟疑,他选择回到村中。
令顾忠荣始料未及的是,登上三尺讲台10多年之后,一场大刀阔斧式撤点并校的风波来临。上个世纪90年代起,原有的村小教学点开始被撤销,大多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中心学校读书。2001年起,全区代课老师遭到大规模的清退,村小面临关停。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蒋峰曾在2005年对南充市农村学校进行走访。他发现,大多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比较沉重的欠债;乡镇对教育经费的截留、挤占、挪用严重;学生、教师流失越来越严重。
“以2001年南充市对中小学代课教师清理情况来看, 2002年全市小学教师共减员 274 人,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乡村小学教师,2002 年的小学毕业生流失 6 710人, 流失率达 5. 3%。”蒋峰在《均衡发展城乡义务教育的思考——基于南充市的考察》一文中写道。
孩子们上学愈发不便。村民们纷纷找到当地教育部门,希望能将村小保留。双方协商之下,这些原有的“公办校”转为“民办校”,即当地政府将学校全权“委托”给这些已被辞退的代课教师,并颁发了办学许可证。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委托办学有粗略的表述,即“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委托其承担部分义务教育任务。”但在实施情况中,多位民办校教师表示,他们与区教育局并未签订任何协议,“政府只是默认了这种办学形式。”顾忠荣说。
由于委托办学关系不明确,民办校从成立之初,就处于弱势地位。发展至今,这些民办小学也不是具有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完整设置的“完全小学”,而是归当地中心校管辖的民办教学点。
教育经费的下发随意性非常大。起初,转为民办身份的教学点依靠学费收入盈亏自负,学校没有得到过政府经费扶持。
自2001年至2007年,“两免一补”政策逐步推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免学杂费和书本费,住宿生还能得到生活补贴。根据教育部要求,从2001年开始,在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行“一费制”收费办法,即在严格核定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的基础上,一次性统一向学生收取费用,目的为了治理学校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2005年,这一政策陆续在南充市高坪区中小学推行。
“一费制”政策实施后,民办教学点的绝大部分费用均出自生均公用经费,政府没有额外的资金补助。这些教学点的教师们表示,此后的运营更为艰难。
民办校经费来源分为两个阶段。多位民办教师透露,上世纪90年代,“一费制”实施之前,民办小规模学校允许收学费,每人一学期学费230元,中心校每学期抽走180 元的管理费,剩下50元作为整个学校的运营费,如果有结余,则作为教师工资。吕秀清回忆,当时学生数量近150人,总收入可达7 500元,学校基本维持运营。
免收学费的新政落地后,民办校失去了学费这项主要的经济来源,当地政府下拨生均经费作为补偿。据杨成芳透露,2005年,生均公用经费按每年人均40元拨付;2012年至2016年,生均公用经费达到每人426元;2017年涨到人均600元。但与此同时,学生生源却在不断流失。目前,学校仅靠生均公用经费以及开设学前班的学费维持运营。
生均公用经费,指的是义务教育阶段下,政府财政对学校按人头发放的日常运营费用补贴。多名教师表示,该费用是从2005年起发放,最开始按人头拨付,一年领3 000多元。直到2010年四川省财政厅发布的文件,要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对不足100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但实际领到经费远低于这一标准。后来几经周折,直到2015年开始,他们每年才陆续领到一共6万元生均公用经费。
“一年6万块,学校的正常运转完全不够。”吕秀清介绍,这笔钱除了要交学校的电水费,网费,维修费外,还包括购买学习用品、教育设施设备费、勤杂人员劳务费、差旅费,培训费等。除去以上费用外,剩下给老师做基本生活费的所剩无几。根据规定,生均经费仅用于学校日常经费管理,但由于教师没有固定工资,只能从生均經费中结余部分领取。
“学校建房、装修、水电费,这些支出都是我们从过年工资里面扣,中心校一分钱都不给。”一位民办校老师说。
“严格地说,生均经费是不能用于支付工资的。这一点,教育局也心知肚明,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饿着肚子教书啊。”吕秀清说。
公用生均经费短缺,让学校的运转捉襟见肘,后勤设施和教师资源不足。目前农村小规模学校基本都是“小幼一体”的教学点。学校靠学前教育收取的学费来补贴日常开支。据当地民办老师反映,2005年之前,高坪区共有100多所民办村小。由于资金不足,政府扶持力度有限,这些村小陆续消失,目前仅剩12所。
2018年8月,根据南充市高坪区教育局发布《关于民办农村小学(教学点)相关问题调查核实的报告》,文件中表示安排专人逐校收集民办农村教学点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制定整改时间表,确保在暑期中全面完成整改。然而,秋季学期开学近一个月后,这些村小的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下午5点半,吕秀清站在学校村口,目送着学生放学。对于未来,她心生迷茫。“教育局的人说,办不下去就写申请,(他们)把娃娃接走,我们这些老师就不管死活了。我教了一辈子的书,却被这样对待。”而追问今后的打算,她沉默不语。(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来源:财新网 记者 丁 捷 周斯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