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部位字溯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身体部位字是产生时间较早的一批字。人类须依赖自身的力量在自然竞争中生存下来,在劳作与保护自我的活动中,必然对身体部位有深入的认识。身体结构的稳定,使得这些字所记录的语词大多一直是词汇系统中基本的核心词。因此,它们的演变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演变线索清晰。
这类字的释读难度不大,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尚存在不同意见,对它们的具体演变细节及动因的研究也不充分。我们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追溯其本形溯义,综合字际关系及其在字群中呈现出的规律,重新审视各家观点,力图对它们的形义关系作出较为完满的分析。全面梳理各阶段的典型字形,对它们形体演变及理据保留情况作一细致的考察。
二、人体部位字形义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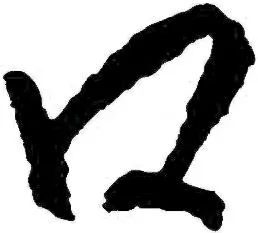


9.齿。、。中山王 壶。



























《说文》“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1]213“亦”为指事字,大象人形,两臂下分别有一点,示其所在,所表之意为“腋”。徐锴曰:“人之腋也,其处也。”[16]835段玉裁曰:“人臂两垂,臂与身之间则谓之臂亦。”[2]493卜辞中已用为表重累的虚词。睡虎地秦简作、,本象人形的“大”被分写成上下重磊的两个“人”。马王堆帛书类此。汉居延简牍作,上部写成点横,下半写为四点。东汉郭泰碑作,西狭颂(171)作,中间两点引长为竖。唐欧阳询(557-641)作,颜真卿(709-784)作,柳公权(778-865)作,右中竖带有钩势。宋赵构作,写法已与今体同。


三、结语
人体部位字中,一些字的来源相关或相同,但在写法上有一定的区别,甚至差别很大。如来源于头部的“元”“首”,来源于牙齿的“牙”“齿”,来源于手部的“手”“左”“右”,来源于足部的“足”“止”,等等。它们有的有具体与抽象之别,“首”为象形字,比较具体,“元”为指事字,比较抽象,甲骨文中“元”有始、大的用法[17],较“首”较早走上了意义引申的道路;有的为针对不同的具体对象,“牙”为臼齿,“齿”为门齿;有的是统称与对称的关系,如“手”为统称,“左”“右”为对称;有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足”为整体,“止”为其一部分。每一个文字的产生往往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生活与劳作加深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相应地就会反映在文字上。
不少人体部位字甲骨文未见,如“心”“胃”等,有些字则甲金文均未见,如“脣”“囟”“肘”等。一则可能受文体内容影响,未有涉及;二则可能因为当时人们对这些部位特别是内部器官的认识还不十分精细或根本就缺乏认知,还没有造出相应的字来。
先民造字是有严密的体系的,这给我们追溯汉字的本形溯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通过对“身”与从反身的“殷”以及“孕”的形义的综合分析,可以明确“身”的溯义在于隆起的腹部。为一个意义造出两个不同的字形来的可能性比较小,使用、识读均不方便,所以,字形上的细微差异处往往是传达字义的关键,字用上也是不同的。“孕”明显有专指的,而“身”则是在实际使用中,字义引申才出现了与“孕”相似的用法。
汉字分析须有全局观念。要在整字背景下分析符号性笔画,有的纯为饰笔,有的则可能含有一定的意图,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象形字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其组成部分均是对客观物象的描摹,有时可能为了方便识读,增加一些相关的部分,如“眉”增加了“目”,生理构造上眉目本就紧相依存,“目”只是提示更多的辨识线索罢了。会意字则具有一定的间接性,要思考构字部件意义之间的关系,有个分析、综合的过程。简言之,象形所见即所得,会意则须分析、综合。
人体部位字近取诸身,基本上是象形字或以象形部件为核心构件,因人们对自身部位的熟悉,相关的古文字不难释出。这些字在发展演变中,多受书写便捷美观的影响,形体变化颇大,理据丢失较多,但基本轮廓通过历时比较仍清晰可见,不难还原理据信息,如“人”先是上身与手臂合为一曲笔,进而为与下身及腿胫显得均衡,就成了撇捺的组合,稍加追溯,可以发现,“人”其实并非纯笔画的组合,造字的基因仍在字形里,还有如“耳”“牙”“舌”“首”“面”“足”“止”等也是稍加追溯就可以轻松找出笔画部件的古今对应关系。不少字很早就添加声符,形声化了,如“齿”的声符“止”金文已增。有些字则假借为它字,为借字所专,遂按形声的方法造出新字形来表本义,如“亦”借为虚词,后来造出“腋”表其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