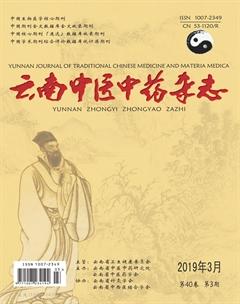艾叶挥发油成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江德裕 丁维俊
摘要:艾叶主要活性成分为挥发油,是其药效基础源于所含化学物质。随着艾叶药理作用广泛运用于临床以及气相、液相色谱质谱等提取分离技术联用的进步,使得艾叶挥发油研究得以多学科、深层次的开展。通过围绕因不同产地、不同采集时间、不同炮制方法及提取工艺的差异等因素影响艾叶挥发油主要化学成分、含量及毒性变化等做一综述,旨在为艾叶挥发油的进一步综合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及研究思路。
关键词:艾叶;挥发油;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9)03-0080-04
艾叶源于菊科植物艾 Arte-misia argyi Levl et Vant 的干燥叶,可全草入药,其性味最早见于《名医别录》,载其:“味苦,微温”,后世医家李时珍根据艾叶的功效纳总结首次提出艾叶味“辛”,现代将艾叶性味定为苦、辛,微温。中医认为“辛”能行能散,药理研究介绍辛味药所含化学成分以挥发油最多,故艾叶有温经止血、止痛、散寒逐湿、理气开郁等功效。艾叶所含化学成分复杂,主要含挥发油类,其次是黄酮类、鞣质类、三萜类、多糖类及微量元素等[1],其药理作用广泛有平喘止咳、镇痛消炎、增强免疫力、抗菌、抗病毒、止血等效用[2]。目前艾叶挥发油已检测出的成分有近100种,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产地的不同,采集时间、提取工艺等的差异对艾叶挥发油含量、成分种类乃至毒性成分含量均有较大的影响[3,4]。现将近年来艾叶挥发油及其影响因素介绍如下。
1 艾叶的挥发油成分
艾葉挥发油呈草绿色或浅黄色澄明油状液体,是艾叶主要有效成分群,被视为评价其药材质量的标准;艾叶挥发油具有抗菌、平喘、镇咳、祛痰、抗过敏、驱避蚊虫等作用,还可增强免疫功能,对抗肾上腺素和组胺引起的心肌收缩,对中枢神经系统也具有一定的镇静效果[5-9]。早期关于艾叶挥发油成分的报道仅有水芹烯、澄茄烯、侧柏醇等几种。经努尔比耶·奥布力喀斯木等[10]检测出艾叶挥发油所含成分30种,有桉树脑(22.71%)、石竹烯(13.2%)、4-松油烯醇(7.34%)、龙脑(5.28%)、樟脑(4.86%)侧柏酮(2,29%)等。杜家俊等[11]从安徽产艾叶中提取挥发油,并离出48个化学组分,所占比例最高的为蒿醇(10.26%),其次为油酸酰胺(6.51%)、环己酮(5.07%)、(Z)-13-二十二烯酰胺(4.73%)、正二十七烷(3.65%)、植醇(3.61%)、棕榈酰胺(3.38%)、2,7,7 三甲基二环[3,1,1]庚-2-烯-6-酮(2.56%)、邻-异丙基苯(2.21%)等。李利红等[12]从河南不同产地艾叶挥发油中检测到53种物质,其中含量较高的成分有:氧化石竹烯、杜仲烯、石竹烯、桉叶油素、异冰片醇、对-薄荷基-1-烯-4-醇、1αβ,2,3,4,4α,5,6,7bβ-八氢-1,1,4β,7-四甲基-1H-环丙|e|甘菊蓝及其氧化物、香叶烯、α-蛇床烯、7-异丙基-4-αβ-8αβ-二甲基-八氢 1[2H-萘酮、δ-石竹烯、Г-榄烯等。目前艾叶挥发油从最初的几个化学成分增添到近 100个化学成分。其化学成分可归结为三大类:单萜类、单萜类衍生物、倍半萜类及其衍生物。主要有:α-蒎烯、β-蒎烯、水芹烯、柠檬烯、1,8-桉叶素、蒿醇、龙脑、樟脑、石竹烯、氧化石竹烯及少量的醛、酮、酚化合物等[13]。
2 不同产地艾叶挥发油的差异
艾叶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及强,全国各地分布广泛,局部地区如湖北蕲春、河南南阳等地更是植物群落的优势物种。亚洲其他国家如蒙古、朝鲜、日本等地也均有生长,日本多为栽培种植,其模式标本采自中国华北[14]。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反映了植物对环境的响应,更是环境变化的指示物[15]。作为植物次生代谢物,艾叶挥发油组分及含量与气候因子等环境条件有很大相关性[16-18],因艾叶生长地区的水文、土壤、湿度、光照等环境气候因素的差异,文献报道中艾叶挥发油所含成分、含量及共有成分也有所不同。
不同省份艾叶挥发油成分及含量差异较大。从甘肃产艾叶挥发油分离出72个峰,其中鉴定了56个成分,占挥发油色谱峰面积的90.83%。甘肃产艾叶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桉叶素(20.45%)、蒿醇(12.12%)、樟脑(6.99%)、青蒿酮(5.85%)、左旋龙脑(4.27%)等[19]。学者研究河南驻马店产艾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共检出103个色谱峰,鉴定了69个化合物,占挥发油色谱峰总面积的96.01%,艾叶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 1,8-桉叶油素(28.59%)、龙脑(7.94%)、3,3,6-三甲基-1,5-庚二烯-4-醇(6.62%)、4-甲基-1-(1-甲乙基)-3-环己烯-1-醇(6.56%)、樟脑(6.31%)、α-松油醇(3.82%)等,其中,茉莉酮和β-紫罗酮为艾叶挥发油化学成分的首次鉴定报道[20]。从云南、四川、湖北三个产地的艾叶中提取挥发油,并比较其艾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含量,发现云南产艾叶挥发油含量约为0.18%,含有 58 种成分。四川产艾叶挥发油含量约为0.33%,含有52种成分。湖北产艾叶挥发油含量约为 0.19% 含有48种成分。云南产及湖北产艾叶挥发油含量最高的为樟脑,四川产艾叶挥发油含量最高则为α-侧柏酮[21]。王菁菁等[22]也对产自甘肃崆峒、陕西黄龙、陕西安康、湖北蕲春及河南桐柏艾叶的挥发性成分进行检测,从 5 个产地的艾叶中分别鉴定出54,52,57,47,55个成分,主要为单萜类、倍半萜类及其含氧衍生物、醛、烷烃及苯系化合物等,其中 18 种为共有成分。同样,在湖北、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 8 个艾叶材料中共鉴定出 84 种挥发性化合物,其中 17 种为共有成分,且湖北艾叶中烯类成分含量最高,而湖南和河南艾叶中酮类成分含量较高[23]。由此可知不同省份艾叶挥发油含量、化学成分、共有成分等各有差异。
同一省份,不同产地艾叶中的挥发油成分也存在差异。学者对河南方城、洛阳、叶县三个产地的艾叶挥发油成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这三个产地挥发油成分的丰富度,经对比鉴定得出 53 种化学物质,三地艾叶挥发油其成分含量成分为:氧化石竹烯(方城 27.14%、洛阳 28.91%、叶县 27.41%)、杜仲烯(方城 24.93%、洛阳 20.6%、叶县 21.16%)、石竹烯(方城 9.71%、洛阳 9.15%、叶县 6.66%)。其他成分如桉叶油素、异冰片醇、对-薄荷基-1-烯-4-醇、1αβ,2,3,4,4α,5,6,7bβ-八氢-1,1,4,7-四甲基-1H-环丙| e |柑橘蓝及其氧化物、香叶烯、-蛇床烯等也各有差异[12]。肖宇硕等[24]也对蕲艾及不同产地艾叶挥发油成分含量进行分析,经综合分析比较,明确不同产地艾叶挥发性成分有一定差异,同一产地艾叶挥发油也存在差异。
3 提取工艺对艾叶挥发油成分有影响
挥发油是艾叶的主要药效成分之一,提取质量的稳定是其药理作用以及临床疗效的保证,对于艾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具有重要意义,然提取工艺、提取时间的差异,采用不同提取方法提取同种植物的挥发油,所得挥发油化学成分的种类及其含量可能会有较大差异[25-27]。传统的提取工艺主要有水蒸汽蒸馏法、石油醚提取法、乙醚提取法等以及新技术方法如超临界CO2萃取法、半仿生提取法、微波辅助萃取工艺、活性离子水提取、超声提取法、酶提取法等。后继学者对艾叶挥发油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工艺进行优化,采用正交试验法考察提取时间(A)、料液比(B)和浸泡时间(C),发现不同提取时间、液料比、浸泡时间对艾叶挥发油得率有影响,其中提取时间对结果影响最大,挥发油得率也随着提取时间的增加而增加[28]。王小生等[29]考查CO2超临界萃取法各因素对艾叶挥发油质量的影响发现艾叶挥发油最佳提取条件为萃取压力20mPa,萃取温度30℃,分离压力8mPa,分离温 55℃,平均挥发油得率为1.443%,平均桉油精含量为0.318 mg·g-1。不同提取方法对艾叶挥发油所得成分及含量有较大的影响。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和 CO2超临界萃取法提取的艾叶挥发油化学成分存在较大差异;超临界萃取所得挥发油的化学成分较多,其中极性较小的成分含量较高;水蒸馏法所得挥发油的化学成分集中在极性较大的醇类,极性较小的挥发成分用水蒸馏法相对难以提取[30]。李静等[31]以挥发油得率和挥发油中桉油精含量为考察指标,以不同产地的艾叶(河南汤阴、安徽霍山、湖北蕲春,采集日期均为5-6月)及不同采集日期(5、6、7、8月)的湖北蕲春艾叶为对象,比较水蒸气蒸馏法和超临界CO2萃取法提取艾叶挥发油的效果,发现超临界CO2萃取法的挥发油得率明显高于水蒸气蒸馏法,但桉油精含量差异不明显。
4 不同采集时间对艾叶挥发油的影响
艾叶不同的采集期对其挥发性组分、含量及毒性成有重要影响,传统习俗认为端午前后为采集艾叶的最好时间。洪宗国等[32]对6种不同采集期(5月19日,5月26日,6月2日,6月9日,6月16日,6月23日)的艾叶挥发油化学成分及含量进行综合比较,发现采集时间的不同艾叶挥发油含量出现明显的差异。从5月19日至6月2日艾叶中挥发油含量在逐渐增加,达到最高值。端午节后含量逐渐下降。6月2日挥发油含量最高达0.953%,6月上旬的挥发油收率最高,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毒性成分最低,品质最好,是艾叶采收的最佳时期。张元等[4]选择端午节前后的1个月左右(5月8日,5月13日,5月20日,5月27日,6月3日,6月9日,6月16日)为采集的时间点,分析不同采集期艾叶挥发油含量和主要成分及毒性变化表明艾叶挥发油在不同时间节点其含量和成分有差异:挥发油含量在端午节前不断增加,节后其含量逐渐降低;随采集时间節点的推移其化学成分逐渐增多,由5月8日的69种逐渐增多为6月16日的 82种。以挥发油含量及 30 种主成分相对含量为指标,艾叶最佳的采集期为端午节前1-2周左右;以挥发油所含侧柏酮等数种毒性成分为指标,最佳的采集期则为端阳节之后 1-2 周左右。总之,不同采集期对艾叶样本所含挥发性组分、含量及毒性有重要影响。
5 其他因素
艾叶所含化学成分及含量是其药理作用的基础,因此鲜艾与陈艾挥发油成分也必然有所不同。学者研究艾叶陈化前后挥发性成分种类及含量的变化情况表明鲜艾叶在陈化过程中挥发油成分的种类及其含量确实发生较大的变化[33]。在山东药用鲜艾叶与干艾叶的挥发性成分比较中发现鲜艾叶有30种,干艾叶有46种,共有成分为18种,其中鲜艾叶特有成分为12种,干艾叶特有成分28种。说明鲜艾叶和干艾叶挥发性成分有一定差异[34]。目前对艾叶的炮制方法有醋炒,酒炒,炒焦等。醋艾叶温而不燥,可增强祛寒止痛之功;艾叶炭温经止血力强。不同方法炮制后艾叶的药理作用发生改变与其挥发油成分发生改变有关。张甜甜等[35]也对艾叶及其炮制品中挥发油成分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含量大于0.1%的成分在生品中鉴定出42个,占挥发油总量89.23%;醋炒品鉴定出42个,占挥发油总量88.10%;清炒品鉴定出44个,占挥发油总量88.46%。说明艾叶经炮制后其挥发油组分确实发生较大变化。
5 小结
艾叶是我国历史悠久、用途广泛的民俗中药材,其主要活性成分挥发油,一直被视为评价其药材质量的标准;具有祛痰、平喘、止咳、抗菌、抗病毒、抗过敏、镇痛等药理作用。不同产地、不同采集时间、不同提取工艺、不同炮制方法等因素对艾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含量变化及毒性成分含量有较大影响。地域及艾叶品种的差异对艾叶化学成分种类及含量有较大影响,艾叶种植应进一步考虑地域及区分不同品种艾叶。临床用药及药理研究也应根据不同采集期艾叶化学成分及毒理变化情况为指导。今后在全面深入研究艾叶挥发油成分及其药理效用的进程中应以其不同产地相对含量、不同采集时间点之间关系、不同提取工艺及炮制方法等作为的重要参考依据期以指导艾叶栽培、采收及临床开发应用。
参考文献:
[1]李真真.艾叶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国际药学研究杂志,2016,43(6):1059-1066.
[2]周英栋.艾叶的药理作用研究[J].湖北中医杂志,2010,32(11):75-76.
[3]戴卫波.12个不同产地艾叶挥发油的GC-MS分析[J].中药材,2015,38(12):2502-2506.
[4]张元.詹志来不同采收时间对艾叶挥发油及其挥发性主成分与毒性成分变化的影响[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18(3):410-419.
[5]李春娜,占颖,刘洋洋,等.艾蒿药理作用和开发利用研究进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12):3889.
[6]段伟丽,刘艳秋,包怡红.艾蒿精油的抑菌活性和稳定性[J].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2015,34(12):1332.
[7]吴芳芳,何炎森,卢劲梅,等.艾草驱避蚊虫研究进展[J].农学学报,2015,5(9):96.
[8]M J J Menken.Dual bioactivities of essential oil extracted from the leaves of Artemisia argyi as an Antimelanogenic versus Antioxidant Agent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by GCMS[J].Int J Mol Sci,2012,13:19.
[9]迟雪洁.艾叶不同组分发挥镇痛作用的安全范围研究[J].中国药物警戒,2012,9(6):330-332.
[10]努尔比耶·奥布力喀斯木.艾叶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和抗真菌活性的研究[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7,40(9):1195-1202.
[11]杜家俊.圣安徽产艾叶挥发油成分GC-MS分析[J].皖南医学院学报,2017,36(1):11-15.
[12]李利红,李强,邢金超,等.河南不同产地艾叶挥发油成分的GC-MS分析[J]现代牧业,2017,1(3):1-6.
[13]陈小露.艾叶化学成分研究进展[J].今日药学,2013,23(12):848-851.
[14]艾 Artemisia argyi H.Lév.& Vaniot.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据库[引用日期2014-02-22].
[15]张雅静,石辉,刘雄飞,等.植物次生代谢酚类物质含量与空气污染关系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35(4):472-476.
[16]曹藩荣,刘克斌,刘春燕,等.适度低温胁迫诱导岭头单枞香气形成的研究[J].茶叶科学,2006,26(2):136.
[17]贺志荣,项威,徐燕,等.茶树挥发性萜类物质及其糖苷化合物生物合成的研究进展[J].茶叶科学,2012,32(1):1.
[18]GouinguenéS P,T C J Turlings.The effects of abiotic factors on induced volatile emissions in corn plants[J].Plant Physiol,2002,129(3):1296.
[19]兰美兵.甘肃产艾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遗传毒性研究[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2,18(13):252-255.
[20]赵志鸿.河南驻马店产艾叶挥发油的 GC-MS 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理学版),2013,45(2):81-84.
[21]蒋潇.三个产地艾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分析[J].2015,24(17):20-22.
[22]王菁菁,郝文芳,張继文,等.艾叶挥发性成分对气候因子的响应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8(2):1-9.
[23]梁欢,卢金清,戴艺,等.HS-SPME-GC-MS 结合化学计量法对不同产地艾叶药材挥发性成分的比较分析[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4,20(18):85.
[24]肖宇硕,卢金清,孟佳敏,等.气质联用法对蕲艾及不同产地艾叶中挥发油成分分析比较[J].中国药师.2018,21(3):404-410.
[25]张小俊.艾叶顶空萃取的挥发油指纹图谱[J].中成药,2014,36(6):1244-1249.
[26]王绪颖.化学与药效学指标相结合改进痛经宝颗粒中挥发油提取工艺[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9):15-21.
[27]张小俊,赵志鸿,张壮丽,等.HS-SPME-GC-MS 测定艾叶挥发性成分方法优化[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4,20(21):66.
[28]赵志鸿.艾叶挥发油提取工艺的优化[J].中国医药导报,2014,11(35):66-68.
[29]王小生.CO2超临界萃取法提取艾叶挥发油工艺研究[J].中医学报,2017,32(9):1701-1704.
[30]石琳.不同提取方法对艾叶挥发油成分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5):21641-21643.
[31]李静,熊维政,李磊,等.种不同方法提取艾叶挥发油的效果比较[J].中国药房,2016,27(28):3982-3984.
[32]洪宗国.不同采集期艾叶挥发油含量和化学成分的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2(2):32-36.
[33]夏循礼.艾叶陈化前后挥发油成分种类及含量变化研究[J].江西中医药,2014,45(6):69-71.
[34]王丽.鲜艾叶与干艾叶挥发性成分的HS-SPME-GC-MS分析[J].山东科学,2012,25(4):27-31.
[35]张甜甜.艾叶及其炮制品挥发油成分GC-MS研究[J].中成药,2011,33(1):8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