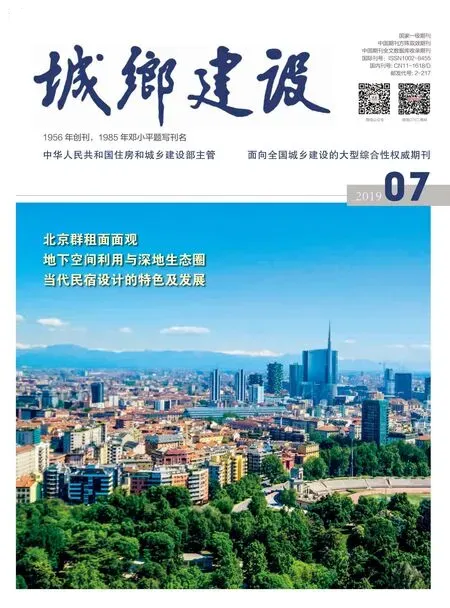控规编制模式比较研究
■ 杨慧祎
一、控规编制体系现状与评价
我国各地区控规指标构成虽略有差别,但大同小异,我国传统控规以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为基础,对城市建设提出“定性——土地使用性质”、“定量——土地开发强度”、“定位——配套服务设施落位”的要求。我国控规指标分为控制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两类。控制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公共服务设施、禁开口路段、配建车位和建筑后退红线等内容;引导性指标包括居住人口、建筑形式、体量、风格、色彩要求和其它环境要求等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控制性指标已出现了形式化的趋势,引导性指标由于缺乏强制力更是几近形同虚设。
因地制宜是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控制性指标的定量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这一基本原则。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取值的方法包括反馈法、标准法、比较法、容量法和经济法。其中比较常用的是标准法、比较法和容量法三种方法相叠加,即先由规划设计标准确定基础的取值范围,再依据上位规划的开发强度要求,通过规划编制者的经验指定该地块的各项指标,最后根据环境和基础设施容量对开发强度总和进行核准和微调。此种工作流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控规编制中的经验主义工作方法,这是由我国传统控规的编制体系直接导致的。吴良镛先生早在1998年于《关于北京市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几点意见》一文中便提出,“应在深入继续城市设计和多方案比较的基础上确定控规”。因为在总体城市设计指导下的控规层面城市设计能够贯彻体现城市不同部位的差异化特点,再据此抽象成为控规指标,控规指标的取值便也具有了因地制宜的特点。
引导性指标的设定是为了引导城市风貌而制定的,意在与城市设计衔接。但在实操过程中由于其缺乏具体操作方法和管理规则,导致引导性指标在编制过程和操作过程中均不受重视。引导性指标失职的直接结果就是城市空间品质的下降,城市建设风貌唯建筑师、开发商和领导意志是从,城市陷入建筑乱象。
二、控规编制模式
(一)“普适图则+附加图则”模式
2008年,上海市设立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并对上海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管理体系展开研究和改进工作,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上海城市发展需要的控规编制管理制度。

分级分类一级城市设计区域二级城市设计区域三级城市设计区域公共活动中心区市级中心、副中心、世博会规划区、虹桥商务区主功能区等市级专业中心、地区中心、新城中心等社区中心、新市镇中心历史风貌地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风貌区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优秀历史建筑建设控制范围等风貌区外历史建筑集中的历史街区重要滨水区与风景区黄埔江两岸地区、苏州河滨河地区、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淀山湖风景区等——重要景观河道两侧、大型公园周边地区等交通枢纽地区对外交通枢纽地区轨道交通三线及以上换乘枢纽周边地区轨道交通二线及以下站点周边地区其他重点地区 大型文化、游乐、体育、会展等设施及其周边地区



注:①“●”为必选控制指标;“○”为可选控制指标②带“*”的控制指标仅在城市涉及区域出现该种空间要素时进行控制
上海在我国传统控规编制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对落实城市设计中城市风貌控制要素的考虑,将城市规划编制地区分为一般地区、重点地区和发展预留区,并提出了“普适图则”和“附加图则”的概念。“普适图则”基本等同于我国传统控规图则,包含街坊编号、地块编号、用地面积、用地界线、用地性质、混合用地建筑量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住宅套数、配套设施、控制线、备注、建筑控制线、道路中心线控制点坐标等普适性控制要素,同时适用于城市的一般地区和重点地区;“附加图则”是针对重点地区,在普适图则的基础上,通过城市设计或专项研究编制的图则,并作为法定文件的组成部分。发展预留区可根据需要,适时增补普适图则,亦可同步编制附加图则。
上海控规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在传统控规体系中针对城市设计要求,引入“附加图则”,对城市重点地区的城市风貌实施有力的控制。上海将城市重点地区划分为“五类三级”,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重点地区的控制程度有所不同。
(二)“法定图则+设计通则”模式
“法定图则+设计通则”模式以香港和深圳的规划实践为典型。
香港的法定图则分为“分区计划大纲图”、“发展审批地区图”及“市区重建局发展计划图”。它们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和管控要求,分别制定不同类型的法定图则。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对城市建设的控制并非仅依靠法定图则,而是通过法定图则与地方设计通则相配合的方式实现。例如,香港“分区计划大纲图”的图则中仅对土地的使用性质作出了规定,“分区计划大纲图”的注释部分也仅对土地兼容性进行了说明,而其它关于城市建设的详细控制要求均在以《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为主的地方设计通则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香港的法定图则简明概要,设计通则文件中各类规定详实具体,设计通则中的规定主要通过“内部图则”和“土地契约”体现。
深圳的法定图则体系的建立主要借鉴了香港法定图则的经验,也可认为其属于“法定图则+设计通则”的模式。“法定图则的成果是按法定图则制定程序批准的‘法定文件’,包括文本和图表两部分。在编制‘法定文件’之前,应先编制‘技术文件’,作为制定‘法定文件’的基础技术支撑和解释性技术说明。其中的“图表”基本等同于香港的“法定图则”,仅明确了街坊编号、地块编号、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绿地率、土地相容性、配套设施项目名称8项内容。而与《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相对应的《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则通过“技术文件”体现。
(三)“区划”模式
区划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使用的法定规划手段,其规划层次相当于中国城市规划体系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美国的“区划”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较成熟有效的控制和指导城市土地使用和开发的法律工具。美国“区划”的法定文件包括区划图则(zoning map)和“区划”法规文本(zoning ordinance,或译为“区划条例”)两部分。“区划”图则用来表示用地分区的边界和编码,是“区划”法规的附属文件;“区划”法规文本是有裁决权的地方法律,用以控制土地的使用和开发。除此之外,“区划”手册(zoning handbook)作为由“区划”法中提取出的规定性文件,在指导城市建设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划”根据使用性质不同,将用地分为C(商业用地)、M(工业用地)、R(居住用地)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建设的容积率目标不同,将建设分为不同小类。“区划”手册对上述各种类型用地包括开发强度和城市设计的各类要素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见图3-5,表3-5)。因此,“区划”图则中所明确的土地使用类别背后便蕴含着该地块的建筑风貌控制要求。
德国是最早采用“区划”模式指导城市建设的国家。德国的法定图则德文原文称为“建造规划”。建造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引导采取的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控制方法,其控制要素不仅包括城市建筑和空间的营造方法,更强调了关于城市自然生态要素的维护(见表3-1)。与我国情况类似,德国的建造规划图则中的控制措施也由城市设计(物质形态规划设计)抽象而来,而并非依据某种普适性的规则。
三、控规编制模式的内在逻辑
(一)横向对比——“规划控制”指标
我国(北京)传统控规图则中包含7项指标内容:用地编号、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和绿地率。除去用地编号、用地面积以及用地性质外,对比我国传统控规、上海控规、深圳法定图则和美国区划手册中对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和绿地率这4项指标内容的控制方式,解析4项指标的控制意图和优化方式。
容积率。对比各地控规图则所涵盖的指标,各地控规指标相对于我国指标各有增减,但容积率似乎是恒定的选项。容积率之所以能成为核心指标,是由于容积率是所有指标中唯一决定地块开发强度的指标。其它指标如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看似可以决定开发强度的指标,实际在地块容积率一定的情况下,都是相互制约的城市设计要素指标。最简单的例子如在某一固定容积率地块城市设计中,设计师可选择采用底层高密度或高层低密度的建筑开发模式。
建筑密度与建筑覆盖率。传统控规中的“建筑密度”指标在上海、深圳和美国的图则指标中均未体现,但在上海的附加图则中作为重点地区建筑形态控制要素出现了“建筑密度”,在深圳的《深标》和美国的“区划手册”中也出现了(最高)建筑覆盖率或空地率的定量要求。
目前我国的规划实践中,建设活动少有突破控规“建筑密度”的要求。一方面,居住用地的建筑密度受居住区设计规范的限制,需达到日照间距、消防间距等硬指标。另一方面,其它类型建筑由于其使用功能决定的通达道路、集散广场等的布置,建筑密度基本上也不会过高。此外,建筑退线、使用者对项目开放空间的市场需求等因素也保障了建筑密度的要求。因此,“建筑密度”、“建筑覆盖率”等限制性指标或可以如深圳、美国的做法,归并至实施细则中,甚至直接省略,通过建筑体量的控制和各类控制建筑间距和开敞空间的法规来实现。
建筑高度与建筑体量。在上海的控规改革中保留了传统控规中“建筑高度”指标,而深圳的法定图则和美国“区划”图则均未涉及此项指标。建筑高度是一项城市设计要素指标而非控制开发强度的指标,深圳和美国在建筑高度方面的控制要求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如深圳城市规划标准中关于高度的要求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建筑的“总高度”和“裙楼高度”。“总高度”属城市层面的建筑高度,这个层面应在规划中给出高度限制范围值,其取值应依据总体城市设计和特殊地区的净空高度管制要求;对建筑“裙楼高度”的要求与“街墙”要求类似,与“天空曝光面”的要求相关,是为了保证街道的步行空间品质而设计的指标,属街道层面的建筑高度。这个层面可借鉴《深标》中“街道空间”的控制方法,对街墙的高度、连续性做出要求。
建筑高度作为建筑体量的一个空间维度,可考虑与建筑体量的平面维度结合控制。美国区划手册依据容积率划分建筑类型,对由不同容积率决定的不同尺度的建筑做了图示化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一种容积率类别便对应了一种基本的建设模式。但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城市,特别是新城,道路网密度普遍较低,街块尺度普遍较大,地块内部建筑空间组合模式多样,导致建筑尺度需由多个指标共同确定,无论是控制容积率还是控制建筑密度都无法防止体量庞大的建筑产生。因此可以考虑新增一项指标,将每个单体建筑的体积(本文姑且称该指标为“建筑体积”,建筑体积=建筑标准层面积×层数)控制在某个固定值之内,以此来控制每个建筑单体的体量。“建筑体积”的取值可根据总体城市设计对城市各风貌片区建筑体量的不同设计意图而确定。据此,“建筑体积”与“容积率”分别控制地块内建筑单体的体量和地块总体的开发量,加之建筑最大高度的限制,期望可将建筑建设控制在城市设计的意图内,并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绿地率与空地率。传统控规中的“绿地率”通常均依据规划法规规定下限取值,这种做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地块绿地率均质化,零散的小面积绿地分布于各个地块。甚至开发主体以消极的方式开发绿地以求达标,仅保证了绿地的“量”,而无法保证绿地的“质”。上海的普适图则和附加图则中均未体现“绿地率”这项指标,深圳法定图则指标中包括“绿地率”,美国“区划”手册中并没有“绿地率”的要求,但其中的“空地率”可视为与“绿地率”相关的指标。“空地率”是为了保证地块具有足够的公共空间而设定的指标,公共空间的范畴包括绿地。
绿地的控制依据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依据城市设计所确定的生态景观廊道,可以以图则标定的方式将城市设计要素抽象到控规图则。二是依据各类功能用地的规划法规中对绿地开发量的要求,可以以规划设计通则、法规等附件的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据此,上述两种控制方式可代替原本几近失灵的“绿地率”指标。
(二)纵向对比——“设计控制”方法
控规现状条件下,“附加图则”的提出和运用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以及较强的针对性。其可操作性一方面表现在它保留了原控规体系,是在原有控规的基础上做加法的改革方式。另一方面,“附加图则”将城市设计蓝图转译成为城市设计控制要素,以指标和条文的方式进行明确,并将其纳入控规,赋予其法律约束力,强化了其可实施性。其针对性一方面表现在“附加图则”仅针对城市重点地区,在控规升级的初级阶段将更为高效的把控城市风貌;另一方面,“附加图则”针对城市风貌进行专项的把控,直击城市风貌乱象的根源。
“法定图则+设计通则”模式将规划控制条件与设计控制条件分离,分别在图则和通则中体现,最终统一于“土地契约”或规划的“技术文件”,使各项控制条件得到落实。此种模式、可有效防止暗箱操作和领导意志的干预,较具有可行性。但是地方设计通则的编制通常需要一个较长周期的实践反馈和完善过程(例如《深标》通过十余年的规划实践探索才具有较强的可操性),并且在法定规划的编制体系革新的同时,也意味着规划管理体系的改革,更加繁复了规划改革的工作。所以,控规层面的规划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发展,并非一日之功。
美国的“区划”管制体系进一步简化了图则的内容,使区划图则仅作为图则标定和地块用途索引使用,具体的规划控制和设计控制内容均在区划法规文本中体现。区划管制体系“通过‘地块划分的标准化’和‘控制指标的标准化’建立起有限用地种类的标准开发模板,进而将复杂多样的建设开发按照不同的用地性质纳入各自预定的板块。”
以上各种方式均属于底线控制方式,旨在控制城市建设不出现出格的举动。各国城市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城市建设管理的缺失,均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建筑乱象。以上各种底线控制方式便是针对此种建筑乱象问题而建立的管制机制,因此也是城市规划问题导向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当底线控制方式发展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美国采用区划管制的城市风貌已得到了很好地规范,人们就会对城市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区划的严苛管制提出一些质疑。从此,“后区划”时代的城市规划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其中不乏颇具成效的城市设计导则(urban design guidelines)管控方式和已发展出多种形式的形态的条例(form-based codes)。即便如此,这些新的探索和实践仍然暴露了各自的问题和弊端,目前还难以找到一种比区划更简便明确、更公平合理、更行之有效的控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