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波动中转折
——余笑忠诗歌漫论
■夏 宏
1
余笑忠的诗,对事物之间的相触、相交十分敏感和自觉;抑或说,我逐渐聚焦于诗人倔强又耐心地在诗作中所呈现的“介入”。
他写蚯蚓:
“从泥土里被刨出的蚯蚓,它们/从未见过世面的肉身/暴露出来//以其渺小的弹性/顶撞碎石、阳光/和阳光下它自身的影子”(《告诫》,2010年);
他观盲女触摸油菜花:
“她触摸的同时有过深呼吸/她触摸之后,那些花颤抖着/重新回到枝头”(《春游》,2014年);
他感悟人们把碎啤酒瓶插砌在围墙上:
“那尖利的玻璃并非嗜血成性/被砌在围墙上,更像是/受苦刑的罪人,构成一道防线”(《围墙》,2017 年)。
在此,介入,取干预之义,意味着主动的施加和被动的受纳、反动之间的相互运动。从整体上看,余笑忠诗歌中所呈现的介入,有不平则鸣的质感,但又并非狭义的对社会生活不平则鸣式的表态。它首先体现出诗人观察事物、事态的一种方式,即其诗眼:意义发生于存在者之间此涨彼消的对抗运动和不甘于此、不止于此的运动中。
2
其诗中,无物、无人孤立,人事屡见于在紧张的对抗性关系中出场和运行,形成一种压迫感。愈是早期的,给人的紧张感、压迫感愈强。
在显性的素材上可见:人拿开水浇蚂蚁(《启蒙教育》,2001年)、农民宰耕牛(《他们这样屠杀一头耕牛》,2003年)、石头戳破赤脚(《我父亲忍着疼痛一声不吭》,2005年)、劁猪(《每一头猪都有最疼痛的一日》,2006年)、伐木(《诱人的排比句》,2011年)、毁河(《为蕲河作》,2011年)、与父亲在电话中争执(《星期天》,2014年);
在或明或暗的题旨上,他喻生活像拧床单(《拧床单》,2011年)、人的深怨如“木板上烂掉的钉子”(《春天的午后》,2011年)、名家对写作者的影响似二手烟(《二手烟受害者》,2011年)。
如果单以入世之诗来论,以上由评论者作出的罗列概述并不奇特。生之峻险,命之维艰,关系化的生存中,有存在就有损耗,此境此理人通,即便不是经教化所得的常识,也会是生活历练中的自觉。入世诗要依靠“非诗”的语境来成立,其间的社会景象丰富,也往往会勾连起世人经验性的情思与认同感,所以它直接流向波澜壮阔的政治、伦理、社会之学,当属顺理成章。对于诗歌,其中的危险性在于如果它只是事态、情态的映照折射或应激反响,甚至是“影子的影子”,听凭外来的摆布,风吹草动,就难以自撑。用不着时过境迁,这危险便会对陷入现实生活图景的诗歌发动反扑;拉长时间来看,可以见到入世诗的某些“遗址”仅留存着作为历史考据资料的价值。
余笑忠的诗不止于此。存在者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常常只是其诗的一个缘起,或者说,是其诗意运行的一种挥之不去的背景——
光阴含有敌意/一首诗,一刹那的光明(《诗》,2011年)
3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入,不止被动地落入、陷入以致“久在樊笼里”,还可以一层一层地深入,渐进式地探秘。诗人余笑忠没有停留于由对抗性生存关系而引发的感受、情绪上,他朝向了对“存在者的伤痛”的挖掘,对世道,对人性,也对物性。
诗人多着眼于受困、受挫、受损的那一方面,似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才更有入诗的意义。为何?诗歌,诗人,仅从其能够发声而言,的确具备以有余补不足的修饬功能,仿佛有损的事物在对诗、诗人发出召唤。你看他的“天问”:“难以置信,杀了那么多的鱼/为什么没有一条/发出哀鸣”(《哑口无言》,2001年)。
介入中的对抗,常让人蒙羞、蒙痛,至极处至少可能让人疯狂,“一位八旬老翁在街头跌跌撞撞/他可以在腰间胡乱缠一根麻绳”(《丘吉尔与熊十力》,2012年)。轻微一些,也会形成情思上的纠缠与郁结,“今天,我厌倦的一切/像冬天的深夜里泡在水里的床单/我不愿去碰它,又必须/独自将它拧干”(《拧床单》)。见人性,亦显人性的包袱。
随之,受损一方的隐忍不仅作为善,而且作为自我修复的力量被诗人彰显出来:乡下父亲被石头戳破赤脚血染泥草,“这么多天了,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此一声未吭”(《我父亲忍着疼痛一声不吭》);无名的受苦者,“你一言不发,紧紧/咬着嘴唇/仿佛相比之下,你的嘴唇/是甜的,可以抵消/口中全部的苦”(《长久的缄默》,2014年);以至面对残暴之力压迫时,人们会各自涌动起一种共通的情结,“蚯蚓就一直在我们的喉结里涌动/蚯蚓也和我们是同一个部分的”(《告诫》)。隐忍,若非苦痛已经多得令人麻木,那么就是承受者不再直接介入另一方,单方终止了对抗运动,避免损伤循环,留下各个自寻生路的空间。
可是钉进木板经年的那颗钉子,依然会持续地锈烂下去,不管是暴露在目光下,还是暗自。诗人把隐忍呈示出来,意蕴就有些复杂了,在赞美一种德性之外,又有点类似于拔钉子。其实,多年前诗人就开始拔了,“有几枚钉子烂在了木板里/这块木板已成朽木//要取出钉子的惟一办法/是将木板付之一炬//但我拒绝火焰粗暴的总结/我倾向于倒叙”(《喘息》,2005 年)。
对抗性关系早就在其诗中有一条向内转的路径,转入到人的自我对抗及其消解上。
4
设问与自语是一对亲戚。纳外入内,往里转,不断内推,推到水穷处,不知能否从自我的“樊笼”里转出来。自我对抗且求解,力道外现,辟出理解(再次纳入)异在的通道:
穷途末路,他给领袖写那么多信干什么呢
反过来他也可以质问:后生/你写那么多诗干什么呢/就为因特乃特你的大神?(《丘吉尔与熊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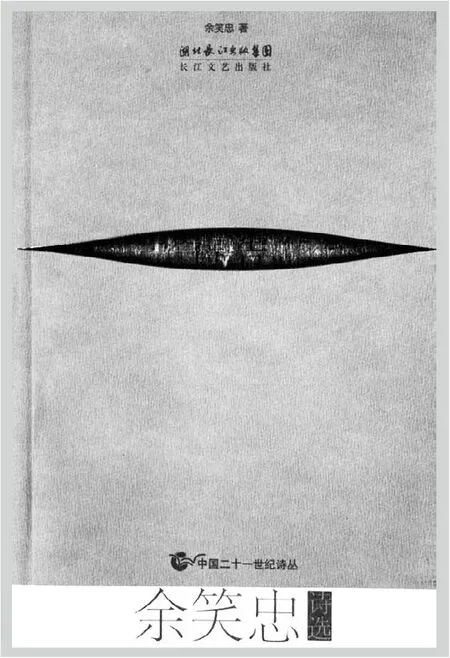
《余笑忠诗选》
观察与自省在相互选择。诗人有时很快就放下自我对抗的包袱,在一首之中就转折过来,如《春天的午后》中。有的包袱,要待多年以后在另一首诗中放下来,待到于经年累月的酿造中消化了焦躁与涩苦,且不断地开拓了“库容”。排毒,去碍,开眼,融入共在的空间:
阳台的铁栏杆上有一坨鸟粪/我没有动手将它清理,出于/对飞翔的生灵的敬意/我甚至愿意/把它看成/铁锈上的一朵花(《目击道存》,2015年)
自反性,乃个我与社会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冲突加剧的一种征候?痛苦落于生活、文化、语言中,渗透进个体的身心,免不了要考验隐忍者的意志力和打探出路的能力。在谋生之外写作的非职业诗人,写日常生活内里的得失存弃,犹如一次次地、有节奏地自我剃度。经历了自我对抗的艰难消解,才有可能从自反走向同情,对遭受损害的他者抱以贴已的悲悯,也才有可能领悟到身外有灵万物的灵光:
站起身来,眼前是竹林和杂树/一棵高大的樟树已经死了/在万木争荣的春天,它的死/倍加醒目/在一簇簇伏地而生的艾蒿旁/它的死/似乎带着庄子的苦笑/但即便它死了,也没有人把它砍倒/仿佛正是这醒目的死,这入定/这废物,获得了审视的目光(《废物论》,2017年)
5
释读余笑忠的诗歌如何处理、呈现介入运动,离不开论说其诗的灵性。它向外转,是观照并化解对抗性关系带来的沉疴的另一条路径,与向内转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可它又非诗人拿来解决问题的“器用”,它既是内生的,又是被触发的,且可能被收走,诗之为诗,人之为诗人,缺其显现不成。它有神秘的一面,想呈现它,可遇难求,却是衡量诗歌和诗人的砝码(“器用”)中最精微的一块。
不通世故之诗,易轻飘、绝路。
太世故的人写诗,可能转不出来,窍多了,反而陷于窍中。
米沃什在读了一位波兰女诗人的诗文后,悖论式地给她“盖棺”:“她不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但这正好:/一个好人不会去学习艺术的诡计。”(《读安娜·卡缅斯卡的笔记》,黄灿然译)经验之论,也许含有自省过程中的难受与通达。
余笑忠曾在点评他人的诗作时有针对性地说过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但有所思的诗,不如若有所思的诗,无名的天真状态的诗。”
出乎其外,真是难中之难,比如,灵魂出窍,非强力和谋略所能为,更非诗句语言直陈它飘出来了即是。“灵魂”这个词已被新诗滥写至失信,遑论出笼?
余笑忠在诗中对有灵的直接抒写越来越警惕、克制,他对诗歌(语言)自欺欺人之伪的一面有着自明之后的截断:“在灵魂的下层土壤里,我不知道/会生长出什么/我只知道会有自我缠绕的东西/我只知道再写下去/就有说谎的可能”(《荷花之外》,2010 年)。可是,一种在伤痛、郁结甚至悲悯之外的光亮,时常萦绕在他的诗行间,给它们照明,还可能会穿透它们。他写在大旱之春喝浑水的孩子,“小心地喝完一碗水,孩子们/小心地用手指将碗底抹干净/在他们看来,手脏点无所谓/可以往衣服上擦,但不可以/往一张白纸上擦”(《2010年春,云南的愁容》,2010年),一种与“出污泥而不染”相通的灵光,自结尾平静地浮现,回流在一首哀诗上。有时,他还呈现寻常事物相介之时的微妙,背阴的植物,“它们有修长的茎,簇拥的绿叶/但省掉了花/有时阳光洒在上面,像浇花”(《在朝西的房子里》,2015年),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连通来得很快,又戛然而止,稍纵即逝的吉光片羽,突然让残缺之物比丰实的还要完美。想象力不是被克制着,而是自然流出,甚至有点平常,像人们常用之而不觉那样,在此却会触发人的联想,连接起类似的事物与事态,比如残荷、断臂的维纳斯。
若强行分开来看,社会道德、思想逻辑中的普遍性,多为后天的营建与规约,灵性的贯通力,多为自发生成,其源难推,一旦对其纲举目张即失之于虚妄,它常体现为能够联结彼此的感应能力、良善、纯真等。余笑忠曾在一次关于他诗歌写作的对话中,受触发而言:“诗歌写作与其说需要动力不如说需要敏感,靠动力只能是支撑,而敏感则是自发的,是对事物的反应。这种反应能力一旦丧失,再强的动力恐怕也无济于事。敏感基于个人天赋和性情。”
我以为,余笑忠不仅敏锐地感应到存在者身上的灵光,且察觉到它的某种转渡。他似恐在诗中直接言明而丢失了它,转而在景、情、事、思的轮换中呈示出时隐时现的流觞曲水,常用否定句、转折语,有时甚至一否再否、一转再折,将理智与情感、审美与道德、社会与自然之域相贯连,当你指认是它、是它们时,又像不是,似幻又似真,因为它们之间的障碍不知不觉地被诗(诗人)穿透了。如这首《二月一日,晨起观雪》(2015年):
不要向沉默的人探问/何以沉默的缘由//早起的人看到清静的雪/昨夜,雪兀自下着,不声不响//盲人在盲人的世界里/我们在暗处而他们在明处//我后悔曾拉一个会唱歌的盲女合影/她的顺从,有如雪/落在艰深的大海上/我本该只向她躬身行礼
放弃对全诗的逐段细读,以单一的理性话语来作辨析会破坏诗意在多个层域自如流转的气韵。教育家孔子曾自反而叹“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数次辞官后终于安贫乐道的陶渊明“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观雪而自反的“我”领悟到“沉默诗学”的艰深与慧通,“我们在暗处而他们在明处”。诗歌的化通,离不了不可说之“慧”。据说,“不可说”是一个关于无穷语言的数量词,要不,热爱音乐和诗歌艺术的维特根斯坦为何能从语言“图像论”的设限中解放出来,走入语言“游戏论”,去化解逻辑的包袱?化解障碍,也会是某些诗人毕生呈现的悲欣交集的功课。
6
其诗,屡见禁忌(多次写洗澡、雨的冲刷、祈光)与戏谑(描摹人事之憨态、窘态)相穿梭之处,意外迭现,替空灵造居所,于训诫中别开生面。在结构上形成一张一翕的运动,打开,关上,再打开。
他近年来的诗歌中,争相夺目的冲突逐渐减少,内在的隐性的冲突耐人寻味。相应地,其诗歌的节奏从早期偏快转到后来快慢相间。在不同的诗篇中,快如“热气弥漫,流水自上而下/尘垢体肤,卑身而伏/涂抹之,揉搓之,如此反复”(《沐浴记》,2008 年),慢似“在这一口和下一口之间/可以有漫长的停顿//我在这停顿中/杯中物,也在停顿中”(《夜歌》,2011年)。在其长诗《幻肢》(2013年)中,集中呈现了这种快慢结合的律动。
气韵饱满又富有张力的诗歌,一般都具有回旋的结构和意味。有阻挡截断才有“回”,另有途径受其力、通其变才会“旋”。余笑忠的诗歌一般都不是线性地推进至结尾,每每,一首诗中后面的单元与前面的既呼应又背离,既流逸又返照,前后都在这种关联中焕发新的生机,构成内里激荡、生生不息的共同体。我将如此诗艺,视为诗人余笑忠常年敏感于、反观于乃至汇流于介入运动而得的一种回馈,被牵引到此般诗艺面前的我,又犹如那位摸花的盲女,最后,“她再也没有触摸/近在咫尺的花。又久久/不肯离去”(《春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