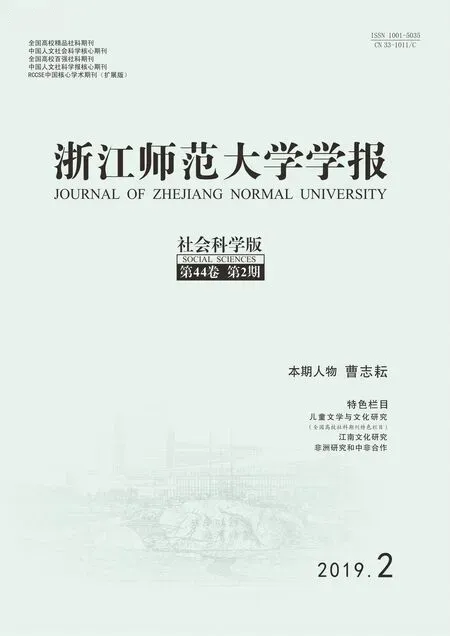论佛教典籍翻译用语的选择与创造
王云路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7)
汉译佛经,翻译者是用汉语翻译原典,采用什么样的汉语词语?是不是对当时汉语词汇的全盘照搬?笔者经过初步比较,觉得翻译者不是悉数接纳,除了翻译者本人的用词习惯之外,在词语使用上还是具有较强的自主性、选择性,乃至创造性的。其选择和创造的依据就是翻译者对汉语词语的理解程度。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词语的选用基于翻译者的理解程度
在翻译佛经中,有一种现象引人注意,就是中土早已出现、流行甚广的常用词语,汉译佛经中竟然没有出现,没有使用过,这是什么原因?比如同时代中土文献中极为普遍的连词“万一”,在中古翻译佛经中竟然没有用例。而连词“至于”就被广泛接纳。
例一:万一
在中土文献中,“万一”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连词,出现时代很早。[1]比如《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抱朴子内篇·金丹》:“世间多不信至道者,则悠悠者皆是耳。然万一时偶有好事者,而复不见此法,不值明师,无由闻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万一”作为假设连词,当萌发于秦汉,《文子·下德》:“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此例“万一”已经表示概率极小的含义,再进一步,就是表示假设的连词了。汉魏时期已经成熟,是整个中古时期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连词。①但是“万一”这种用法却没有出现在同期的翻译佛典中,其原因是什么?当时的佛典中也用“万一”,但基本上均作数词出现。我们从以下例句中可以看出翻译者对“万一”的理解:
在黄白莲华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千七百二亿万一千二百斛乃得出。(西晋法立共法炬译《大楼炭经》卷二)②
是时,即得悉见种种庄严三昧等万一千菩萨三昧增进修行。(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卷四)
可见佛经翻译者对“万一”是理解为数量值:一万一千。
为什么连词“万一”在中土文献大量使用的时候却没有在同时代的译经中出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万一”本来是词组,表示“万分之一”的数量,是比例极小的数量,转用于非数量方面,就是可能性极小的意思,因而表示假设连词,是词义的进一步虚化。而译经的翻译者汉语水平有限,对该词组虚化的过程理解还不够,所以没有接纳这个词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佛经“万一”作数字时频繁地用来表示“一万一千”(相比之下,中土文献不如佛经般频繁强调极大数目),因此挤占了表示“万分之一”这个强调极小数目应有的位置,佛经中表示数量小的“万一”也很罕见,一般要具体说成“万分之一”“万中有一”等来避免歧义,因此也就失去了进一步虚化的途径:
彼等一切诸释童子,尽力共算,不能及逮悉达太子万分之一。(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一二)
十方我作诸功德,般遮于瑟及檀那,汝魔万分无一毫。(又卷三〇)
昔有众人在江水侧坐,而观看瞻水成败伤害人民无复齐限,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堕水死者亦无有量,其中得解脱者万中有一。(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一)
佛言:我今现在谛观察之,比丘僧中终不见有,被白衣者最后末世亦复如是,信乐斯经讽诵之者,亦复少有,百万之中若一、若两。(旧题北魏吉迦夜译《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二)
佛教撰述中偶有使用“万一”,但不是连词,并非表示“可能性极小的假设”;而是名词,表示“可能性极小(或比率很低)的数量”。例如东晋法显《法显传》卷一:“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这是较早的用例。再往后看,明智旭《阿弥陀经要解》:“若无平时七日工夫,安有临终十念一念?纵令《观经》所明下品下生五逆十恶之人现世不曾修行,并是夙因成熟,故感临终得遇善友闻便信愿,如此等事万中无一,岂可不预辨资粮,乃侥幸于万一哉!”此例前有“万中无一”,足以说明对“万一”的理解还局限在数量极小的含义上。明释宗泐、释如玘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批注》序:“然承雨露之余泽,依日月之清光,庶几少裨流通之万一云尔。”以上三例“万一”是撰述的例子,而不是纯粹的译经语言,其用法也是从其数字含义引申而来,尚没有虚化为假设意味的连词。
在佛典中,作连词使用的“万一”,一是例子很少,二是时代在中古之后,三是都没有出现在译经中,而是在本土撰述或“语录”中。如:
但业行残缺愿往西方,万一不生,恐成自误,故当己行应修此业。(唐窥基《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
万一入在髑髅里,卒难得出。(南宋妙源《虚堂和尚语录》卷八)
次为州将保持,死则损多,生则益大。万一不遑恤此,潜焚幽谷,则亦匹夫之为谅耳。(南宋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五)
万一合浦珠还,岂不为山家传持之标帜乎?(又卷七)
例二:至于
译经中也不是过于抽象虚化的词语都不接纳。“至于”是一个由跨层结构产生的承接连词,是动词“至”和介词“于”组合的结果,在佛经译文中就被采纳了。
从本义上分析,汉语中“至于”首先用于表示时间和空间上的到达义。《论语·学而》:“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这是到达某地。《左传·昭公十三年》:“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这是到达某时。因为古人的时空概念是可以相通和转化的。③
如果到达的不是具体的某个地点或时间点,而是话题的开端,也就是过渡到某个人或事物,“至于”就担当起连词的功用。这个用法也是很早就出现了。《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国语·周语中》:“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则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唐杜荀鹤《乱后逢村叟》诗:“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于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此三例表示另提一事:第一例是犬马与人的并举比较,第二例是王吏与贵宾的并举论列,第三例是时间和事件的承接。所以,“至于”既是过渡到(到达)一个新的话题(人或事物),也可以看作是先后两个事物(话题)的并举,那么称作“连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再进一步抽象,连接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也是承接上文,表示引出的结果,犹言“以致于”。《后汉书·宦者传论》:“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埶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即其例。
如果因果关系出乎意料,就是“竟然”。可以看作副词。《史记·伍子胥列传》:“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如果强调达到某种程度,犹言“竟至于”“甚至于”。《北史·魏彭城王勰传》:“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亲侍医药,夙夜不离左右,至于衣不解带,乱首垢面。”④以上两例已不是简单的并举,而是隐含了作者的分析、评判和倾向性观点,而且连接的是动词。
我们再看中古译经中的例子。东汉竺大力、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下:“至于梵摩众圣,皆莫能论佛之智故,独步不惧,一无畏也。”这是提起另一个话头。西晋法炬译《法海经》:“种族虽殊,至于服习大道,同为一味,无非释子。”这是表示转折义的话头。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一六:“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剥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于髓,求众生生。”这就是简单的顺接,表示到达义。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二:“阿难!汝闻跋祇国人闺门真正洁净无秽,至于戏笑,言不及邪不?”这是顺接,表示“以至于”,有“竟然到达某种程度”的意思。
佛典中的连词例子,基本都体现了“到达”这样一个隐含义,因而使用中顺畅而自然。当然,在佛教典籍中,“至于”多表示“到……(某地或某种境界)”义之例,还是其本色用法。
对“至于”“万一”连词义的舍弃或保留,其原因主要在于翻译者对于这两个结构的理解程度,理解了虚化过程,就容易接纳和使用。另一个原因是“万一”已作为数量值使用,保存了“极少”这个含义。
二、词语的使用基于翻译者所处时代的语言流行程度
关于假借的理解,我们常常会用后起专字(或者说是“区别文”)来判定早期用字的正确与否,或者说找出本字或正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可以说颠倒了父子关系。词语使用的是不是正字,其实也是基于翻译者对词语的理解,基于当时流行并易于接受的语言事实。
例三:烧炙脯煮
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二:“适兴于世,睹诸群萌,妄想财业,爱惜无厌,因从情欲,致无数苦,于今现在贪求汲汲,后离救护,便堕地狱,饿鬼、畜生,烧炙脯煮,饥渴负重,痛不可言。”据真大成等考察,“脯煮”的“脯”是“缹”的通假字。[2]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考《说文·火部》:“,炮炙也,以微火温肉。”段注:“炮、炙异义,皆得曰也。既云炮炙,又云以微火温肉者,嫌炮炙为毛烧,故又足之,言不必毛烧也。微火温肉所谓缹也,今俗语或曰乌,或曰煨,或曰焖,皆此字之双声叠韵耳。”又“炮,毛炙肉也”,段注:“炙肉者,贯之加于火。毛炙肉,谓肉不去毛炙之也。《瓠叶》传曰:‘毛曰炮,加火曰燔。’《閟宫》传曰:‘毛炰,豚也。’《周礼·封人》:‘毛炰之豚。’郑注:‘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内则》注曰:‘炮者,以涂烧之为名也。’《礼运》注曰:‘炮,裹烧之也。’按,裹烧之,即《内则》之涂烧。郑意《诗》《礼》言‘毛炮’者,毛谓燎毛,炮谓裹烧。毛公则谓连毛烧之曰炮,为许所本。《六月》《韩奕》皆曰‘炰鳖’,笺云:‘炰,以火孰之也。’鳖无毛而亦曰炰,则毛与炮二事,郑说为长矣。炰与缹皆炮之或体也。《韩奕》之炰,徐仙民音甫九反。《大射》篇注炮鳖,或作缹,或作。是知炰、缹为古今字。《通俗文》曰:‘燥煑曰缹。’燥煑谓不过濡也。裹烧曰炮,燥煑亦曰炮。汉人燥煑多用缹字。”

但是译经中也多见“脯煮”“烳煮”。⑤如西晋竺法护译《修行地道经》卷三:“于是有二狱名烧炙、烳煮,彼时守鬼取诸罪人段段解之,持着鏊上以火熬之,反复铁铲以火炙之。”《可洪音义》卷二一《修行地道经》音义出“烳煮”条:“上音府,诸经作脯煑也,字体正作缹。”认为虽然诸经皆作“脯煑”,但“烳煮”“脯煑”的正字当作“缹煮”。
西晋竺法护译《方等般泥洹经》卷下:“于是佛复至烧炙缹煮叫唤雨黑沙烧人四大地狱中,施金色光明,遍于一切光明。”《可洪音义》卷四《方等般泥洹经》音义出“脯煮”条:“上音府,正作缹煑也。”是可洪所见本作“脯”。
《正法华经》卷二:“因从情欲,致无数苦,于今现在,贪求汲汲,后离救护,便堕地狱,饿鬼畜生,烧炙脯煮,饥渴负重,痛不可言。”《修行地道经》卷三:“已到于大苦,在烧炙烳煮,罪中殃差者,则识本行恶。”《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卷三:“其舌广长各四万里,驾犁耕舌五百亿载,各五百亿岁当吞销铜,其火焰赫,及两身上烧炙缹煮。”“缹”字日本知恩院作“烳”。以上例证均出自西晋竺法护译本,前两例没有异文。单用“脯煮”的例子也很多,如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我身寿终已,堕地狱甚久,合会及叫唤,世世见脯煮。”“脯”字宋、元、明本皆作“缹”。
再看一例。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二四:“是时,世尊即接难陀将至地狱,示彼苦痛,考掠搒笞,酸毒难计,八大地狱,汤煑罪人,一大地狱、十六隔子围绕其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烧炙缹煮,苦痛难陈。”《可洪音义》卷二一《出曜经》音义出“烳煮”条:“上音府,亦作脯,正作缹煑。”
从《可洪音义》可以看出,当时的本子多作“脯”或“烳”,可洪判定其正字当作“缹”,也就是说“脯”为假借字。这也是迄今为止学者的基本共识。
佛经中“烧炙脯煮”常常连言,成为惯用语,为什么许多版本用“脯”“烳”而不用现成的正字“缹”?恐怕主要与翻译者对词义的理解和流行程度有关。《说文·肉部》:“脯,干肉也。”就是肉干的意思,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常用词,仅以《说文》为例,就有:“修,脯也。”“膎,脯也。”“膊,薄脯,膊之屋上。”“脘,胃脯也。”⑥“朐,脯挺也。”可见“脯”是通语,流行广泛。“脯”的另一个特点是产生早。《诗·大雅·凫鹥》:“尔酒既湑,尔殽伊脯。”《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周礼·天官·外饔》:“师役,则掌其献赐脯肉之事。”“脯”用于动词煮成肉干,也早有用例。《吕氏春秋·行论》:“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高诱注:“脯,肉熟为脯。”《抱朴子·诘鲍》:“使夫桀纣之徒,得燔人辜谏者,脯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胫。”⑦因而翻译者用常见而又极为相关的“脯”字表示煨或焖的意思,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是用火烧成干肉,所以又据“脯”类推造了一个“烳”字。
表示肉干义的“脯”也可以指制作肉干的方法,这其实也是汉语体用同称现象的反映。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仍有体现,比如“叉烧”“火烧”“烧烤”“卤煮”“麻辣烫”“生煎”“小炒”等都是用制作方法表示此类食物。
“缹”字的产生较迟,应用也很有限。《说文》中并没有“缹”字(段注中才出现了“缹”字的注文,见上)。中土文献中,中古以前文献涉及很少,只在字书、辞书中涉及对此字的解释。如三国张揖《广雅》卷七:“焷,谓之缹。”《玉篇》:“缹,音缶,火熟也。”《毛诗正义》卷一八:“案《字书》:炰毛,烧肉也;缹,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煑曰缹。然则炰与缹别而此及《六月》云炰鳖者,音皆作缹。然则炰与缹,以火熟之,谓烝煑之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七《出曜论》音义:“缹煮:方妇反,《字书》少汁煮曰缹,火熟曰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四:“缹煮:方妇反,《字书》少汁煑曰无,⑧火熟曰煑。”
字书中除了人们辗转引用的《诗·大雅·韩奕》“炰鳖鲜鱼”注疏引《字书》、引服虔《通俗文》外,并无其他文献用例,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后起字。⑨中土文献中只在《齐民要术》中才多见。如《齐民要术·蒸缹法第七十七》:“缹猪肉法:净燖猪讫,更以热汤遍洗之,毛孔中即有垢出,以草痛揩,如此三遍,梳洗令净。四破,于大釜煮之。……脂尽,无复腥气,漉出,板切,于铜铛中缹之。一行肉,一行擘葱、浑豉、白盐、姜、椒。如是次第布讫,下水缹之,肉作琥珀色乃止。”所以,与“烧炙缹煮”相关的例子,早期多作“脯煮”,或据“脯”新造“烳”字,⑩是怡然理顺的,一定要用相对少见的“缹”才算“正字”,认定用“脯”或“烳”为“缹”的“通假”字,恐怕不符合语言事实,算是以今律古吧。辛岛静志先生释“脯煮”作“is dried and boiled”,就是从“脯”之干肉义引发,[3]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
三、词义的赋予基于翻译者的理解和类推
不仅仅是词语的选择和使用翻译者有权决定,就是词语含义也可以由翻译者自主决定赋予。当然,这个赋予新义的依据依然是翻译者对汉语的理解和把握程度。
例四:“逮”
汉语文献中,“逮”并无作为连词的用法。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指出“逮”字二义:一为动词“得,获得”义;一为连词“及”,“见于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经律异相》中有几处,大概都转引自《六度集经》。‘及’本动词、连词两用,而‘逮’只有动词用法。译经者不察,径用‘逮’为连词”。[4]是“译经者不察”的误用?还是译经者的创造?
徐朝红统计,“逮”字的连词用法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本缘部。王卉指出:“‘逮’做并列连词始于三国时期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终于北魏时期慧觉等翻译的《贤愚经》。”这两篇论文都提出连词“逮”是中古译经中一个特殊的并列连词。[5-6]《六度集经》卷一:“王逮臣民,相率受戒,子孝臣忠,天神荣卫,国丰民康,四境服德,靡不称善。”即其例。
下面“逮及”应当看作同义并列双音词,表示的是连词“和”义。
须我天上诸天世间人民逮及鬼神智慧得道,须我经法遍布天下,未可般泥洹。(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卷上)
“逮”作连词,毫无疑问是译经中特殊的用法,中土文献中没有出现,是怎么产生的?算不算“误用”?
笔者以为,这是翻译者基于对连词“及”的理解和对其同义词“逮”的理解而通过类推联想创造的新义。首先,因为“逮”与“及”含义相同。《说文·又部》:“及,逮也。从又从人。”徐锴曰:“及前人也。”《辵部》:“逮,及也。”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二:“吾之一国,智慧方便,无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当以相配,自恣所欲。”前秦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卷二〇:“相见日极久,梵志般涅槃,以逮如来力,明眼取灭度。”动词“逮”字用法与“及”完全相同。这是“逮”产生连词义的内在根据。
此外,“逮及”同义并列可作动词,表示达到、赶得上,中土文献常见。《后汉书·杜笃传》:“逮及亡新,时汉之衰,偷忍渊囿,篡器慢违,徒以埶便,莫能卒危。”在译经中也有使用,西晋竺法护译《诸佛要集经》卷下:“时彼会中,新学菩萨各心念言:‘弃诸阴盖不可逮及,普无等侣,行如来慧。’”又作“及逮”。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尽力从后追,不能及逮我。”旧题三国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上:“设第六天王比无量寿佛国菩萨、声闻,光颜容色不相及逮,百千万亿不可计倍。”“逮及”“及逮”是同义并列的动词。所以“逮”与“及”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考“及”本是动词,谓一只手抓住了前面的人,就是追上、赶上。追上了就是到达的意思。词义进一步虚化,作为连词,就表示“和”。《诗·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这里前后两项是并列关系。“及”作为连词,在中古译经中也广泛使用。如:
阿颰言:“我闻天帝释,与第七梵,皆下事之,所教弟子,悉得五通,轻举能飞,达视洞听,知人意志,及生所从来,死所趣向。此盖天师,何肯来谒!”(旧题三国吴支谦译《佛开解梵志阿颰经》)
这是动词“知”的宾语“人意志”与“生所从来,死所趣向”的并列。
佛即问:“王及国人民,宁安和不?谷籴平贱不?”(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卷上)
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此语,心复悲憹,闷绝躃地。(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上)
以上是简单的并列连词结构作为主语。
无忧与忍行,寂灭及善觉,安和、善友等,阿难为第七。(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一)
此例“及”与“与”对举同义,也是连词。
方膺、无量子,妙觉及上胜,导师、集军等,罗睺罗第七。(同上)
欝单越人,悉有衣服,无有裸形及半露者,亲疎平等无所适莫,齿皆齐密,不缺不疎,美妙净洁,色白如珂,鲜明可爱。(隋阇那崛多译《起世经》卷二)
以上都是并列连词。
“及”作为连词在中土文献和译经中都极为普遍,翻译者因“及”而类推,把与其含义相同的“逮”赋予了同样的连词用法。这是语言类推机制导致的结果,符合语言认知规律,是翻译者理解和类推的产物,似乎不能看作“不察”“误用”。
其次,作为动词的“逮”在译经中可以处于含义模糊、极易误解的中间状态。如东晋僧伽婆提译《中阿含经》卷一:“如是,若圣弟子亦得七善法,逮四增上心,易不难得。”这里面“逮”和“得”都是动词“获得”义,但是这一句中“逮”的位置和连词“逮”的位置相同,换句话说,处在动词“逮”与连词“逮”的中间状态。南朝宋宝云译《佛本行经》卷二:“发现先世行,逮遇前善本。”此例可以看作“逮遇”同义并列,也完全可以看作连词。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三〇:“尔时十年少者,今十罗汉是。佛说此时,其在大会,有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者,发大乘意逮不退者,信受佛语与,欢喜奉行。”这里的“逮”与前文“得”相对应,均应看作动词。这是诱发“逮”向连词过渡的外部原因,也是翻译者对此词理解模糊的一个体现。
最后,“逮”本字即“隶”,《集韵·队韵》:“隶,与也。”似也可作为能够产生连词义的一个佐证。又有“迨”。《集韵·海韵》:“迨,及也,或作隶、、逮。”“迨”有趁着、等到义。《诗·豳风·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说文·隶部》:“,及也。”引《诗》作“天之未阴雨”。段注:“‘迨’,俗字也。”
再如“亦”,是佛经中独创的连词。为什么“亦”可以作连词呢?“亦”本是“腋”的本字,指对称出现的腋下两个部位。那么用来连接同时出现的动作或状态,就是副词;如果用来连接两个名词或句子,就是连词。“亦”在中土文献中是作为副词使用的,从本质上看,就是连接动作的虚词。如果用来连接名称,大约就是连词。所以,可以看作是用法的一种类推。这里从略。
四、复音词的创造基于翻译者的理解和类推
同义并列,是中土复音词最为常见的构词方式,译经中,同样运用这种方法创造新词。
“逮”可以与同义语素并列构成双音动词。“逮得”连用例子较多,表示“获得”。如:
到安隐处,逮得己利,为人导师,演布经教,显于句义。(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二)
尔时,方便修习择法觉分,方便修习择法觉分已,逮得择法觉分满足,选择彼法,觉想思量。(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一一)
又有“逮获”。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一四:“三观为转念,逮获无上道。”
又有“逮致”,表示达到。西晋竺法护译《贤劫经》卷八:“逮致相好诸佛法,则当逮得是三昧。”西晋竺法护译《渐备一切智德经》卷四:“以修行此法,逮致斯显明。”
再如双音词“因由”。“因”“由”中土文献中常见,可作连词或介词,表示因为、由于。《孟子·梁惠王上》:“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史记·高祖本纪》:“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在佛典中“因由”并举,也可以表示缘由义,作名词。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三三:“复何因由无有念耶?”宋日称等译《父子合集经》卷二〇:“愿说其因由,除我等疑惑。”
在佛经中,“因由”也产生了连词用法,表示原因。如前秦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卷二七:“为欲求何等,因由何故来。”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四:“我身舍利安止是塔。因由是身,令我早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三:“王女牟尼,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因由昔日,灯明布施,从是以来,无数劫中,天上人间,受福自然,身体殊异,超绝余人。”“因由”均是同义并列的原因连词。
又倒作“由因”。西晋竺法护译《大哀经》卷六:“由因诸通慧,善慕经典教。”唐法照《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由因不信堕修罗,斗战相诤受苦多。”又:“由因念佛故,所以灭愚痴”。
汉语中不仅有并列式连词,也有附加式连词,翻译佛经中不仅袭用,还根据其构词方式创造了独特的并列式连词。如旧题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五:“儿闻是语,用自安隐。”失译《无明罗剎集》卷上:“噉食人血肉,用自充饱足?”“用自”是附加式连词。三国吴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卿今念我,故复来耳。”“故复”是附加式连词。
有的译经词语的构词理据似乎还难以有确解。比如:
例五:“己自”
“自”“己”义近,但也有一些语法上的区别。如《文子》卷下:“法非从天下也,非从地出也,发乎人间,反己自正,诚达其本,不乱于末;知其要,不惑于疑,有诸己不非于人,无诸己不责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废于上,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式,故禁胜于身,即令行于民。”从此例可以看出:“己”大约用作宾语(包括动宾和介宾),如“反己”“有诸己”;“自”大致用作主语,如“自正”“自为检式”。
这种情况也不尽然。在作主语而与“人”相对时,“自”和“己”有时用法相混。如《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汉书·张衡传》:“恃己知而华予兮,鶗鴂鸣而不芳。”在通常情况下,这两例的“己”写作“自”似乎完全可以。如“自以为是”“自说自话”“自力更生”等。译经中也以“自”与“人”相对应,符合汉语的行文规则。如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八:“汝岂不念:‘瞿昙沙门能说菩提,自能调伏,能调伏人;自得止息,能止息人;自度彼岸,能使人度;自得解脱,能解脱人;自得灭度,能灭度人?’”
译经中“自”和“己”单独使用也很多,基本都符合汉语“自”与“己”的语法规律:
今我用恶人之言,勅令臣下自杀其父。(东汉支娄迦谶译《阿阇世王经》卷上)
这里“自”可以看做主语“自己”,也可以理解为副词“亲自”,而后一种理解更顺畅。
不得自贵,不得自大,不得嫉妒,不得瞋恚,不得贪财利色。(旧题东汉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
想无所有,空返往空返,厄难之缘自从己起,己自贤勅病无从入。(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普门品经》)
达己净不净,何虑他人净者,己自清净亦能使彼行清净,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净行?(同上)
前两个是“自”的例子,后两个是“己”的例子,同时还出现了“己自”的例子。中土文献何时产生了双音词“自己”?
《孟子·公孙丑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赵注:“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孼,犹可违;自作孼,不可活。”这里的“自己”还是词组,谓“从自己”。其中“自”是介词,从,由;“己”表示自身。《老子》王弼注:“取天下常以无事,动常因也。及其有事,自己造也,不足以取天下。”“自己造也”犹言“由自身产生的”。可见汉魏时期“自己”还不是双音词。朱冠明引《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初辅幼主 , 政自己出。”颜师古注:“自,从也。”从颜注中也确定了我们对早期“自己”连言词组性质的判断。西汉东方朔《七谏·自悲》:“内自省而不惭兮,操愈坚而不衰。”王逸注:“言己自念,怀抱忠诚,履行清白,内不惭于身,外不愧于人,志愈坚固,不衰懈也。”此例也是“言己/自念”。可见汉魏时期“自己”还不是双音词。南朝宋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得性非外求,自己为谁纂?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仔细体会,此例的“自己”也是“由己”“从自身”的意思。也许这里既透露了“自己”本来的含义,也呈现了“自己”组合成词前的过渡状态,后来则二字视为平列关系,径直理解“自己”为“自身”,现代汉语沿用至今。魏培泉推测这类介词结构可能是反身代词“自己”的来源,因为和“自”的用法有类似之处,可能“重新分析为复合的代词”。[7]笔者赞同这个观点。
朱冠明认为:“自己”早期的例子源于东汉译经,东汉至隋的经藏和律藏中有120余例并列连用的“自己”的用例。尽管中古“自己”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佛经中,并没有为整个社会接受,但它至少在僧团、信徒等与佛教相关的人群中有了一定的口语基础,是由这个集团向整个社会扩散的。朱冠明的根据之一是“自己”有异序形式“己自”。
而笔者看法与此不同。首先是时代不吻合。朱冠明认为“‘自己’至晚在隋代已经凝固成一个双音词,尽管词汇化的程度不是很高”。[8]而汉魏时期“己自”已经大量在译经中使用了,怎么能够是尚未成词的“自己”的异序形式?其次,正因为“自己”从源头看不是一个词,与汉语的造词理据相悖,所以当时一些译经翻译者不用“自己”而新造了“己自”,以此表示“自身”。笔者试图从译经用例中找出其造词的理据。
己自计身,视诸死败,知人物皆空,空无所有,意便守止,得行欢喜。(旧题东汉安世高译《骂意经》)
太子车马衣裘身宝杂物,都尽无余,令妻婴女,己自抱男。(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二)
己自捐,肥体日耗,间关得出。(又卷六)
细寻文意,以上诸例“己自”似乎可以理解为“自己亲自”。
谓己自无欲。何谓己自无欲?(三国吴支谦译《维摩诘经》卷上)
此例“己自”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自己已经”。再如:
唯有人智者,欲止彼人,当自谨慎,己自为秽,复止他者,为人所讥,嗤其所为。(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一一)
如人己自没在深泥,复欲权宜,拔挽彼溺者,此事不然。(又卷二一)
我等今日,未离生死,己自可悲,何容贪住此恶世中?(南朝梁武帝《梁皇忏法》卷一)
这些例子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自己已经”。当然,大多义情况下“己自”就是“自身”的意思。如:
如其菩萨修如来神通,己自所建行而无所行,是乃谓菩萨。(西晋竺法护译《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三)
善乐于爱欲者,一切众生皆贪乐乐不乐苦恼,见苦则群心不愿乐,己自行杀教人杀生,己自淫泆教人淫泆,己自妄言绮语复教人妄言绮语,己自不与取复教他人窃盗他物,是故说曰善乐于爱欲也。(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二七)
是谓如来授众生决,己自觉知,余人亦见。(后秦竺佛念译《菩萨璎珞经》卷九)
大悲愍群生,常欲为拔苦,见诸受恼者,过于己自处,云何结恶呪,而作恼害事?(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一)
于一切法到彼岸,言说法句已修学,己自无疑除他疑,为我显示佛菩萨。(南朝齐那连提耶舍译《月灯三昧经》卷二)
“己自”除了“自身”“自我”这个意思之外,还隐含有“自己亲自”和“自己已经”这样两个含义,这也许是佛经翻译者舍弃“自己”而创造“己自”一词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翻译者能够创造出“己自”这个词,是否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律?我们还是从译经中寻找答案。
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二四:“如汝所言,各自爱护,然其此义亦如我说,己自护时即是护他,他自护时亦是护己;心自亲近,修习随护作证,是名自护护他。”这里“护己”“自护护他”中“自”和“己”的使用是很准确的,而“各自”“他自”“心自”与“己自”平行出现,是不是也证明了“己自”的构词方式是符合规律的?
佛言:“我不呼人,人自来请。”(三国吴支谦译《佛开解梵志阿颰经》)
佛告波旬:“且止!且止!我自知时。如来今者未取涅槃,须我诸比丘集,又能自调,勇捍无怯,到安隐处,逮得己利,为人导师,演布经教,显于句义。”(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二)
夫志行命三者相须,所作好恶,身自当之;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失译《般泥洹经》卷上)
答言:“妾之父母处与君时,日月大地及四天王悉皆证知,初婚之日,君自发言,誓不相舍,如何今日便欲独往?当知日月及以猛火,明与质俱不相舍离,君今云何而欲见舍?”(旧题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中)
径诣王所,谓王曰:“愿王自恣快乐,莫忧天下,征伐四方,臣自办之!”(前秦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卷四〇)
以上译经中,有“人自”“我自”“身自”“君自”“臣自”,加上前文引的“各自”“他自”“心自”等,是不是可以类推出“己自”?这里大部分是名词、代词与“自”组合,表示对人称自身的强调。如此看来,“己自”含义似乎要强过“自己”,一是含义丰富(包括了自我、自己亲自、自己已经等义),二是符合汉语“~自”的构词规则。汉语中还有“亲自”“躬自”“手自”等,例略。
当然,“自己”或“己自”的产生与“自”和“己”的联系很大,其间关系复杂,笔者所言也只为一孔之见,仅供批判。
小 结
佛经翻译者使用汉语时,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加上自己的理解,容易接受的就使用,觉得不易理解的也会放弃,所以具有选择性;词义或复音词的创造也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汉语的构词规律加以类推。当然,翻译者误用的情况也是并不鲜见的,这是汉译佛典行文中的另一种语言现象,值得关注。龙国富《梵汉对勘在汉译佛典语法研究中的价值》曾就汉译佛典中一些不规范的语法和用词现象作了举例和讨论,[9]可以参看,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笔者对译经涉猎不多,所言一定多有不妥,还祈方家教正。
注释:
①中土文献中“万一”的发展可参见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
②此例是否“亿万”连言亦未可知。
③如“永”本义是水流长,既表示时间上的久远,也表示空间上的遥远,“永巷”即是一例。“长”本义是头发长,既表示时间长,也表示空间长;还表示年长,居前等。“间”本义是门的缝隙,既表示空间上的间距,如“房间”,也表示时间上的维度,如时间,间隔,还可以表示抽象的“闲暇”义。
④《北史》此例《大字典》视为连词,非副词,也是可以的,因为视角不同。
⑤以下例证有数条引自真大成论文。
⑥此例“脘”《说文》有争议。一作“胃脯”,表示肉干,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句读》;一说“胃府”,取“胃的内腔”义,孙刻本、和刻本、汲古阁本《说文》均作“脘,胃府也,从肉完声,读若患,旧云脯,古卵切”。笔者以为二义均成立。《广雅·释器》“脘,脯也”,也可佐证。
⑦《大字典》《大词典》释义为“使之成为干肉”。
⑧“无”当为“缹”之讹。
⑨《诗经》中共有4例“炰”,但无作“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