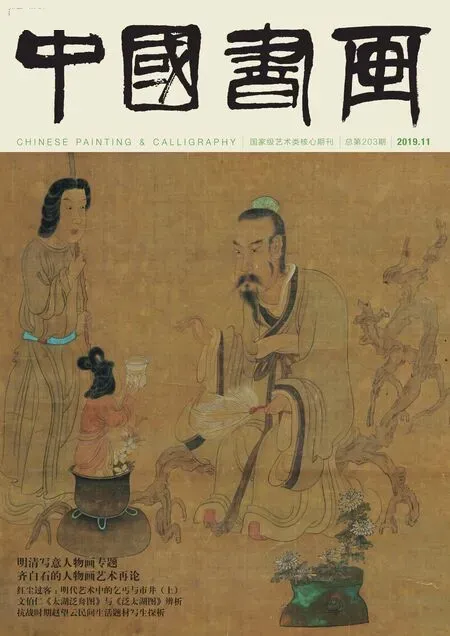月映千江
——明清时期佛教绘画面面观
◇ 陈粟裕
谈到明清时期的佛教状况,学界的普遍评价为“衰落”二字。如汤用彤先生在《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谈及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有如此评价:“隋唐之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虽有宋初自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已……然佛教究自明中叶后大衰。”〔1〕前辈学者的论述主要着眼于佛教内部的发展状况、教义与义理的研究、帝王的支持等方面,故而有此结论。
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经过唐宋之变,早已中国化、本土化的佛教在明清时期彻底融入了中国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之中:帝王、僧侣、官员、儒生乃至贩夫走卒、女红伎乐无一不在佛教的世界中寻求着归宿与安慰。佛教从殿堂从深山,走进村口巷落,走进市井繁华,走进深宅大院。八万四千法门,从上而下,不同身份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帝王寻求教法,高僧探讨义理,儒士追寻禅理,普通人家、目不识丁者忆念一句“阿弥陀佛”。
在此背景之下,汉传佛教艺术不再局限于寺院日常,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式与图像的规定,变得自由而多样,从而涌现出形态万千的佛教绘画作品。技法方面,精细谨秀的工笔画与酣畅淋漓的水墨画并存;题材方面,佛陀、菩萨、罗汉、祖师等传统佛教题材依然延续,由于净土法门的兴起以及汉地四大菩萨道场的确立,以观音为代表的四大菩萨图像盛行一时。此外由于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的流行,大量民间散圣、戏剧化的图像演绎在这一时期都能看到。用途方面,除了寺院中的供奉、民间信众的供养之外,以佛教题材绘画抒发情性乃至流入市场买卖的情况都有发生。种种现象显示了此期佛教的包容与随和,而种种表象之上,佛法“有如一月印千江,一江有月一江明”。
庙堂与市井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出现了专门的佛教画坊,以供寺院所需,著名的宁波画派即是如此,其作品华美精细,人物形态栩栩如生,为禅门所重,甚至被日本留学僧收购带回,在海外形成广泛的影响力。这样的专业画坊明清依然延续,接受寺院或者官府的委托,绘制寺院专用的佛事作品。如山西省右玉县宝宁寺藏的139幅水陆画,为明英宗所赐,用于超度阵亡将士的水陆法会之用。整套作品题材多样、人物众多,经营安排合理有序,人物面容、服饰无一不精,显示出画工高超的技法。规模如此庞大的水陆作品非一人所能,当为一个庞大的画工团队所作,而这套作品与山西地区同题材壁画如繁峙县公主寺、稷山县青龙寺在图像细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也充分说明了卷轴画与壁画之间共有的粉本渊源。
而通常由画工们完成的却具有原创性特点的作品当属高僧的肖像画。五代以后的佛寺之中,通常有祖师堂专门供奉历代的祖师;在世的高僧也会有本人的写真像,有的作为印可授予学生,有的则会在亡故后送入祖师堂进行供奉。这些写真像通常由画工进行创作,高僧的身姿一般具有固定的程式,面容部分则比较写实。明清时期,德高望重的僧侣们由于和社会名流、文人雅士互相往来,这类写真像也有名手创作的可能。如曾鲸就曾为浪觉道盛禅师、密云圆悟禅师绘制肖像。这些由名家画手创作的写真像突破了固有的程式,在力图写实高僧面容的同时热衷于表现他们的精神气质。如会稽籍画家钱复所绘的《紫柏真可像》(图1)。画面中,这位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大德,安然坐于蒲团之上,双手拢于袖中,双目微闭,若禅定状。紫柏的面容以淡墨绘成,技法上颇得波臣派的气韵。史载紫柏少年时性格刚猛,貌伟不群。画中的禅师虽步入中年,但仍可见其气概。然而对于日日进行禅思的高僧而言,“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世间万物皆是“禅机”,故而面对自己的写真像,也是参禅领悟的大好机缘。北宋以来,就有大量禅僧的自赞法语流传于世。画面上的大段文字即为紫柏面对自己的真像所发的禅语。这些看似随口而出的言语追述了自己的身平,再三阐述了自己心无外物的禅学思想。
这些高僧写真像也有不少是后世弟子、友人追思之作。如清代顾尊焘所绘的《语石早年遗照(通证禅师)》(图2)。通证禅师活动于明末清初,为上海圆津寺的第三代住持。这幅作品的构图、禅床以及红衣弟子皆是有粉本可依,唯语石清癯的面容颇具写实性。画家当为禅师的俗家弟子,在禅师故去之后作画忆念,亦是自己作为亲近之人的证明。
寺院之外,由于明清时期禅宗、净土等法门在民众间的普及,大量居士也有自己在家供奉、参禅的需求,故而佛教绘画的市场日益繁荣。与寺院中对造像的仪轨与法度存在要求不同,由于禅学的兴旺以及宋元以来写意人物画的发展,文人雅士以及附庸风雅的商贾更热衷于意味深远的禅意画。清代中期活跃于江南一带的“扬州八怪”即是将佛教、艺术、市场三者紧密结合的代表。其中,尤以金农、罗聘为代表。
金农出生在一个佛教信仰浓厚的家庭,父母皆是虔诚的佛教徒,青少年阶段,他曾经跟随父亲在寺院礼佛、居住,与禅僧们交往甚密,特别是杭州水乐洞亦谙禅师与他交往甚密。在他自己的诗文集《冬心先生集》序言中曾感叹道:“念玉溪生有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誓愿,因亦誓愿五十之年便将衣裓入林,得句呈佛,以送余生。”〔2〕虽然金农并未归隐佛门,但禅宗思想予以他一生深远的影响。面对佛教作品,金农以非常真诚的心态去创作:“余年逾七十,世间一切妄念种种不生,此身虽属秽蚀,然日治清斋,每当平旦,十指新沐,熏以妙香,执笔敬写,极尽庄严,尚不叛乎昔贤遗法也。”所以,其佛像画作有的虽夸张变形,但依然形象端庄,虽为出售、赠送之用,但毫无亵玩之意。并且其佛教题材的作品秉承了宋元以来以图悟道参禅式的艺术追求,从视觉效果到心灵体验上都颇为震撼。如其代表作品《佛像图》(图3),画面当中为红衣释迦立像,披发留须,闭目微笑,双手拢于衣袖之中。这种形象表现的是释迦牟尼结束苦修,从雪山走出,即将降魔成道前的一刻。释迦面容恬淡,嘴角隐含笑意,当是一切成竹在心。人物波迭的衣纹充满着金石感,又能上追自陈洪绶、梁楷等人的线条表现。人物背景为繁密的文字,记录了佛画的传承与自己借古创新的心意。
以擅画鬼趣而闻名的罗聘亦长于罗汉、高僧像。其佛教绘画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颇具妙趣。如清代秦咏祖评价为“人物佛像,尤奇而不诡于正,真高流逸墨,非寻常画史所能窥其涯者也”。如《高僧乞米图》(图4),袈裟衣纹以直线皴擦,如神针细衲,据榜题而知这种画法取自髡残,然用这种笔墨绘制而成的高僧像颇有石躯铁干之美,趣味高古。“乞米”源自释门弟子托钵乞食的传统,而画面中的高僧头戴风帽、满面胡须,双手托钵的形象显然借鉴了达摩祖师的模样。在禅门之中,佛钵往往是传承的信物,表面上这幅作品画的是乞米,实际上暗含了“衣钵正统”之意。与《高僧乞米图》着重于衣纹的刻画与创新不同,另一幅达摩的写意画像则笔法极简,三两根长线条勾勒出了禅定达摩的外轮廓,辅以寥寥数笔的面部刻画和佛钵、《楞伽经》这样标明身份的道具。整个画面可谓是“简之又简”,符合禅宗所追求的寂寥孤绝的美学特点。这样印记明显的作品,在书画市场上自然受到求禅好道者的喜爱与追捧。
不论是僧侣们居住的深山古寺,还是热闹喧嚣的市场,不论是工细至微的工笔道释人物,还是简单粗犷的笔墨线条,这些作品都说明了明清时期的佛教蔓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从不同角度以哲学、艺术的方式给予人们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被后人目以为“狂禅”的禅宗美学。

图3 [清]金农 佛像图轴 133cm×63cm 纸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
空与禅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慧能大师的一句偈子点破了中国禅宗绵延千年的哲学基础:“色空不二”。菩提树与明镜台是物之外相即是“色”,而万事万物的本质则是“空”。因此修行的方式从依靠外部的经典转为依靠内心的顿悟“即心即佛”。禅宗这种独特的修行方式在简化了修行路径,拓宽成佛法门,吸引了大量文士儒生的加入,但是也造成了禅宗的部分分支走上了“狂怪”之路。呵祖骂佛、焚经烧像之举甚至成为某些禅僧标榜自己的手段。明代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如高僧楚石梵琦就声称:“如来涅槃心,祖师正法眼。衲僧奇特事,知识解脱门,总是十字街头破草鞋,抛向钱塘江里著。”可见其对祖师法门的不屑一顾,对自我证悟的迷恋。此外,明代晚期由于天灾人祸,社会变动,大量中下层民众纷纷避难释门,这些缺乏长期修行和佛学熏陶的弟子们也使得原本深奥的禅法变得简单粗俗。当然这些在佛门避难或逃心的队伍中也有佼佼者,如花鸟画领域的徐渭、山水画领域的石涛、八大,以及人物画方面的陈洪绶皆在“禅意”上走出了新的道路。对“心”的肯定与标榜,对“色相”的鄙弃,使得受到这种风气影响的绘画艺术一方面呈现出重内涵、轻形式的美学面貌,另一方面,这种“不求形式”反而解放了笔墨,推动艺术形式的创新。
活动于明末清初的陈洪绶曾对入仕救国抱有很大的幻想,然而多次考试皆不中。绍兴陷落之后,陈洪绶遂遁入云门寺出家为僧。但是出家仅为权宜之计,正如他自己所言:“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一年后还俗,晚年卖画为生。虽未证得无上菩提,但禅学思想无疑对陈洪绶的画作有着深厚的影响。如其画作《无话可说》,借鉴了禅宗祖师像的传统模式:弟子向师父请法,两人一大一小做交谈状。但是画面中相貌奇古的僧侣却都闭口不言,显然这表现了禅宗“以灯传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禅法。再如《右军笼鹅图》表面上看是一幅历史人物画作,但是“右军鹅”在禅门之中有着特殊含义。如北宋时期临济宗黄龙派高僧兜率从悦语录载:“如何是祖师心印?师曰:满口道不得。曰:秖(只)这个别更有?师曰:莫将支遁鹤,唤作右军鹅。”〔3〕其后诸多禅师法语中,均将“支遁鹤”与“右军鹅”当作佛法不可言说之玄妙。因此这幅表现王羲之携童观鹅的作品很可能暗指佛法。题材之外,陈洪绶所画的释迦、观音、罗汉均在“古意”的基础上加以变形、夸张,显得意象高远。这些佛教人物形象上都能够看到贯休《十六罗汉图》的影子。贯休作为五代时著名禅僧,曾作诗言:“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4〕直指禅宗以心传心之意。而陈洪绶对贯休的学习、变化也正体现了以心传心的法门:通过笔墨、风格的学习吸纳了贯休作品的禅意,再将其丰富、夸大,凸显于世人面前,从视觉效果上给人以当头棒喝之感。
与人物形态呈现出的禅意不同的是,陈洪绶的另一幅作品《水月镜花》直接表现禅宗核心思想。水中月、镜中花,在佛教当中都是“空”的代名词。如玄奘所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载:“善观诸法皆同幻事、阳焰、梦境、水月、响声,亦如空花、镜像、光影,又等变化及寻香城,知皆无实唯现似有。”〔5〕但是陈洪绶的这幅小品却以极为精细的工笔白描绘制了水中明月、照镜鲜花两个实体。以极实写虚空,一目了然。同样的主题,“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却用写意的手法表现了一个抱膝静坐,面对水中月参悟的禅僧形象(图5)。画面下方有题记:“镜中之影,水中之月;云过山头,狮子出窟。”前两句指“空”。“云过山头”象征着禅定,而狮子则指代佛法。镜花水月为“空”的表象,而这两件作品则为镜花水月的不同的化象。实写水月与禅僧观月,表现的是正是画家对于佛法的不同领悟,是“心”的表象。
对“心”的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对自我表现的要求。清中期的画家高其佩则以手指代替毛笔,探索了新的艺术语言。其《山水人物图》的题记为:“指头点墨,每于甲肉相半处自成睛睫,洵非豪颖所能为者。然若有意为之亦莫可得是。知画自画,而我自我。离我作画,虽更舍指头与豪颖,谅亦无不可者。”可见在高其佩的眼中,手指是“我”的一部分,相比毛笔,以手指作画更能体现内心自我,故而以笔代之。从这幅作品的画面效果来看,高其佩以指作画的技法是相当成熟的,画面中一文士骑驴悠然回顾青山,显然为画家心境的写照。《指画人物》册页中亦有一幅佛教作品。佛陀以游戏坐坐于草间,画面的一角以淡墨绘出一朵莲花,佛陀见花微笑。此场景化用的是“迦叶拈花、释迦微笑”心领神会的一瞬。题记:“指头蘸墨,用吴道子笔。”而画面线条简练、随性,托名吴道子却是体现了自然、天真的禅宗美学,指尖佛亦是心中佛。
菩萨与散圣
文人儒士畅谈禅机哲理,普通民众则转向菩萨、圣人的足边,通过跪拜、忆念名号等方式祈求离苦得乐。明清时期,文殊菩萨的五台山、地藏菩萨的九华山、普贤菩萨的峨眉山、观音菩萨的普陀山这四大菩萨道场的正式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佛教彻底的本土化。汉地四大菩萨、菩萨道场的形成有着层层积累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菩萨的形象也有着不同的变化。

图4 [清]罗聘 高僧乞米图轴 110cm×42.2cm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
如对汉地观音菩萨的信仰最早源自《法华经》中的一个章节《观世音普门品》。北朝晚期始,忆念观音名号便可脱离苦海的观音灵验故事在社会上广为传颂,唐以后《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等观音类经典的翻译、流行极大地推动了普通民众对于观音菩萨的信奉。宋元明清时期观音信仰逐步世俗化、民间化,普通民众的愿望都向观音菩萨祈求,观音的愿力早已超过《普门品》中的十二大愿,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观音的形象则从犍陀罗地区魁梧英俊的男子身变成了端庄秀丽的女身。明清时期常见的观音形象有杨柳观音、白衣观音、水月观音、鱼篮观音等,姿态不一却都面含慈悲。这些观音像极大方便了女性的供奉与修行,不少女画家也选择观音像进行绘制,如明代闺阁画家方维仪就擅长白描观音像,其作品形象简练,线条优美,让人觉得可敬可亲。随着观音形象在民间的普及,成为民众对女性美的认知与标准,有的画家在画仕女人物也会参考、模仿观音的形象。如黄慎的《渔妇携筐图》,画一渔家女子手提鱼篮回头顾盼。虽服饰为世俗装扮,但是身形、动作都借鉴了鱼篮观音的形象,使得市井题材变得清新而脱俗。

图5 [清]汪士慎 镜影水月图轴 119.5cm×53.5cm 纸本墨笔 广东省博物馆藏
佛、菩萨之外,明清时期还对佛教中的一些神异人物有着特殊的喜爱。这些人物有的深于悟道,有的长于神通,佛教中将之统称为散圣,如达摩祖师、钟馗、和合二仙、布袋和尚等等。与佛、菩萨的宝相庄严相比,这些人物的形象更为活泼多样,特别是在民间画家手里更是突破了宗教的神圣感,贴近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试举两例。
禅宗寺院之中,作为初祖,达摩有着崇高的地位。平日在祖师堂中张陈其像作为纪念,“达摩忌”则专有祭祀的法事仪轨。禅寺中的达摩像一般表现为形貌端严的胡僧,凸显其祖师的身份,而在独具匠心的艺术家笔下,则侧重于表现九年面壁和一苇渡江等故事性场景,突出趣味性。如明代宋旭所作的《达摩面壁图》(图6)为山水画和人物画的结合,浅绛色的层层山石环绕,山东中的红衣达摩侧面结跏趺坐,在一片山色中格外引人注目。达摩的红色袈裟包裹全身,观壁深思,后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包袱。达摩的衣纹、外轮廓线及其简练,与精细的面部刻画构成鲜明的对比。作品通过环境的营建,突出了九年面壁的苦寒,而达摩身着的红衣,宛若代代相传的灯火。同样以对比的手法刻画达摩的还有清代傅雯所绘的《设色达摩图》(图7)。达摩身穿白衣,赤足立于画面正中,面部设色,表情及其生动、细致,瞠目张口欲说禅语的胡僧形象跃然纸上。而所穿的白衣袈裟则仅仅勾勒外轮廓线,大胆采用了留白的处理方式。而背景以淡墨略加渲染,在突出袈裟色泽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达摩步行江边,翩然欲渡的身姿。
另一位是明清时期颇受民间喜爱的神祇—钟馗。与达摩的禅宗祖师身份不同的是,钟馗原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一位神灵。其名可能来自傩仪。敦煌文书中的《除夕钟馗驱傩文》载:“铜头铁额,浑身总着豹皮。教使朱砂染赤,咸称我是钟馗,捉取浮游浪鬼。”而后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载,唐玄宗夜梦,有蓝衣人捉鬼,自称:“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6〕遂诏画工吴道子图绘其形。此后市井百姓之家便有端午节张贴钟馗的画像用以驱邪的习俗。佛门也同样继承了这一传统,将钟馗纳入佛教护法神的系统之中。如南宋时天童如净禅师有语:“天苍苍地皇皇,还知么,钟馗元是鬼。咄,赤口并消亡。且道如何,衲僧八面无门户,今古寥寥白昼长。”〔7〕便是端午节观钟馗像所发的禅语。明初松隐德然禅师端午节亦云:“目前无怪异,不用贴钟馗。”〔8〕禅师们通过画像自证禅机,民间流传着钟馗嫁妹等传说,画家们也从各个角度展现钟馗的形象。与传统的驱鬼凶神不同,明清时期的画家们笔下的钟馗有的庄重,有的诙谐,饶有兴味,也早已远离了驱邪打鬼的功能。如明代袁尚统的《钟进士像》(图8),画蓝衣钟馗,携二小鬼,一者抱着宝剑,一者捧着梅花,钟馗回首观梅。结合题记:“梅占春消息,福来当正笏。髯如铁,足践实,宝剑驱邪。古司直问:尔居何职?系何籍?唐朝进士终南客。”可知这是一幅恭贺新春的吉利画,并非表现端午的民俗。再如清代华嵒的《钟馗赏竹图》(图9),钟馗身着白衣负手持扇而立,身前为二小童,周围有竹林、太湖石为点缀。除却钟馗面容粗陋为其特征外,其余一切细节都宛若修身养性的文士,文人气息浓厚的环境与钟馗这一主人公形成强烈的反差,给人以深刻印象。金农的《醉钟馗图》与任颐的《钟进士图》都是直写钟馗形象,两者技法各具特色。金农的作品古拙大气,任颐作品突出笔意,但两人笔下的钟馗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感,人物的动作、站姿如同戏剧人物的亮相一般,是一种高度提炼并被民众广泛认可的形象。
明清时期,一个佛教故事、三位“散圣”的组合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意义。北宋陈舜俞在《庐山记》中系统讲述了这个关于东晋庐山白莲社的故事:“流泉匝寺下入虎溪,昔远师送客过此虎辄号鸣,故名焉。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合道,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盖起于此。”〔9〕表现慧远大师、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虎溪的故事、图画在北宋时依然是弘扬慧远大师创立净土宗的主题。但是到了明代,这一图像有了新的意义。从魏晋南北朝即已出现的三教合流思想,明代已经成为普遍的认知,并且是统治者推行的基本国策,明太祖朱元璋即提出儒“立纲陈纪,辅君以仁,功莫大焉”、释、道“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10〕明宪宗更是亲治《一团和气图》以表儒释道三家一体。这样的政策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积极响应,纷纷从哲学上,教理上予以回应和支持。如晚明高僧憨山德清就认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11〕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明清时期大量的《三教人物图》《三教圣人图》流行于世,如明王彬的画作,就明显在“虎溪三笑”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图10)。画面中松石点景,表示山间溪畔,画面一侧为白发道人和长须儒士,为陆修静和陶渊明,另一侧为穿红色袒右袈裟的慧远大师,三人言笑晏晏,怡然前行。画面最中间的为头戴儒巾、身穿灰色袍服的陶渊明,显然他是画面的中心。突出的重点点明了儒家为尊、道释为辅的时代主题。
以上种种或是在寺院中供奉或是在百姓家张贴的作品,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明清佛教美术的状况。在这个阶段,佛教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优秀的哲学思想、精美的图像样式滋养了人们的心灵。大乘佛教的兼容并包,以佛法诠释万物,给仕途者以梦想,给修行者以希望,给贫苦者以安慰。佛教艺术作为佛法之表象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面貌,画工、文人、职业画家的加入使得作品的数量、题材有了大幅提高,画作的内涵也趋于丰富。图解仪轨者、阐释法理者皆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日益增多。中国佛教在彻底走入民间的同时,也融入了世俗,融入了生活。诚可谓:“无处青山不道场,何须策杖礼清凉?”

图6 [明]宋旭 达摩面壁图轴121.5cm×31.5cm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款 识:万历乙巳春仲二日,善男子宋旭拜写。钤 印:宋旭之印(白) 石门山人(白)鉴藏印:夕熏楼藏(白) 祖诒审定(朱)

图7 [清]傅雯 达摩图轴 120cm×58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乾隆丁丑春,凯道人雯摹吴道子法。钤 印:傅雯(白) 傅雯字凯亭一号香嶙(朱)鉴藏印:初梨鉴藏(白)

图8 [清]袁尚统 钟进士像轴 60cm×33.5cm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款 识: 辛卯春日,袁尚统写。梅占春消息,福来当正笏。髯如铁,足践实,宝剑驱邪古司直。问尔居何职?系何籍?唐朝进士终南客。文状元题辞。雪轩姚浩书。钤 印:尚统私印(白) 袁氏叔明(白) 姚浩之印(朱) 堇行(朱) 雪轩(白)

图9 [清]华嵒 钟馗赏竹图轴 176cm×95cm 纸本设色 清乾隆二年(1737)天津博物馆藏款 识:丁巳五月五日华嵒写。钤 印:布衣生(朱) 华嵒(白) 被明月兮佩宝璐(朱)

图10 [明]王彬 三教圣人图轴 123cm×49.5cm 绢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王彬。钤 印:王彬之印(白)

[明]陈洪绶 人物图轴 129cm×53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枫溪陈洪绶写寿。

[明]文徵明 老子像轴 57cm×28cm 纸本墨笔 广东省博物馆藏款 识:老子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嘉靖己酉五月既望长洲文徵明书,时年八十。钤 印:停云(白) 文徵明印(白)鉴藏印:离庄潘氏珍藏(朱)

[明]张路(款) 桃源问津图 101cm×153cm 绢本墨笔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款 识:平山。

[明]张路 山行落帽图轴 155.8cm×98cm 绢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款 识:平山。

[明]丁云鹏(款) 白描明妃出猎图卷 28.7cm×233.6cm 纸本墨笔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南羽丁云鹏制。钤 印:丁云鹏印(朱) 墨池清兴(白)鉴藏印:初日芙蓉(白) 墨林(白) 子京(朱) 画禅(白)

[明]万邦治 醉饮图卷 24.5cm×143cm 绢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款 识:石泉。

[明]佚名 三星拱照图轴 175.8cm×89.1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钤 印:正斋(朱)

[明]徐渭 驴背吟诗图轴112.2cm×30cm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款 识:徐田水月驴背吟诗图,笪在宰鉴定。以书法作画,古人中多见之。此画虽无款识,为徐文长先生笔意靡疑。懒逸张孝思鉴。钤 印:江上外史(朱) 张则之(朱)鉴藏印:宫子行同弟玉父宝之(朱) 藉书园(朱)寔夫鉴定印(白) 徐田水月(朱)

[明] 马轼 松下问道图轴 152.8cm×72.5cm 纸本墨笔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马轼。钤 印:轼(白)

[明]吴伟 太极图轴 138.6cm×81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款 识:小仙。钤 印:小仙吴伟(朱)鉴藏印:太谷孙氏家藏(朱) 卫阳道人孙阜昌珍藏印(白)裱边题识: 吴小仙太极横披。严分宜《钤山堂书画记》中物也,笔墨苍劲,直追五季名手暨宋世梁楷。生平所见小仙之作此为第一。壬辰秋,孝同。钤 印:晴庐(朱) 惠均长寿(白) 石乐门人(白)

[明]刘俊 四仙图轴 173.3cm×119.5cm 绢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款 识:刘俊写。

[清]周璕 飞锡图轴 144.7cm×52.8cm 绢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飞锡图。嵩山周璕写。钤 印:周璕之印(白) 崑来(朱)鉴藏印:纯清阁(朱) 诸氏之(白)

[清]华嵒 二老谈道图轴 84cm×33cm 绢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款 识:南阳山中樵者嵒写。钤 印:华嵒(白) 秋岳(朱)鉴藏印:頵公审定(朱) 壬子以后所得(白)

[清]冯箕 吕洞宾像轴 113.6×63.45cm 纸本设色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浙江省博物馆藏款 识:岁在辛亥九月九日盥沐敢橅。西湖栖霞弟子冯箕。钤 印:冯箕(白) 子扬(朱)

[清]钱慧安 读经图轴 132cm×55.5cm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款 识: 读经妻问生疏字,尝酒儿斟潋滟杯。乙巳嘉平之吉,仿新罗山人华秋岳笔,清溪樵子钱慧安时年七十有三。试冰纹研并志岁月于双管楼。钤 印:吉生(朱) 双管楼(朱) 长乐寿年(白)

[清]闵贞 采菊图轴 130cm×66cm 纸本墨笔 广东省博物馆藏款 识:正斋闵贞画。钤 印:名曰贞(白) 正斋(白)鉴藏印:李维洛鉴藏印(朱) 蓝塘书屋(白)

[清]龚谷 渔翁图轴 78.4cm×36.4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时在壬寅年,作于汉皋花木深处,湘山写。钤 印:湘山(朱) 龚谷(白)

[清]任薰 云中仕女图轴 142.8cm×76cm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款 识:善丹仁兄大人雅属,阜长任薰写于吴门客次。钤 印:湘山(朱)

[清]任薰 人物故事图八条屏 240cm×60cm×8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钤 印:任薰印(白) 任薰之印(白)

[清]任颐 何以诚肖像轴 102cm×45cm 纸本设色 清光绪三年(1877)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款 识: 以诚仁兄先生五十一岁小像。光绪丁丑正月,山阴伯年任颐。先生何雅淡,矫矫其谁俦。古心映古色,老气真横秋。拥炉拨芋火,提壶营糟邱。寒意满图画,晤对为句留。噫嘻乎!那得黄山三十六峰雪,与君涤净耐寒本来面。癸未秋初,题以翁乡台先生玉照,即希法家正之。北垣弟程光斗。度岁依然百虑清,旁人争羡此幽情。暮年不减青春乐,蔗境何嫌白发生。美酒细斟成薄醉,围炉闲拨到深更,拥裘领略天伦趣,笑数千门爆竹声。俚语奉题以诚老伯大人玉照,即呈敲正。长洲小芗邵世钊待定草。天机多领悟,寄托乃遥深。境静得幽赏,岁寒盟素心。壶樽随兴到,几案却尘侵。写出萧闲态,何须园复林。辛巳秋暮,俚语奉题以诚姻叔大人玉照,即求粲正。兰客侄唐受祺。隐几悠然见性真,拥炉原不热因人。壶中日月能参破,大地长成自在春。俚句奉题以诚世叔仁大人玉照,即希郢政。世侄余文蔚莪村甫稿。钤 印:颐印(白) 任伯年(朱) 水斋诗画(朱) 受祺(白) 莪村吟句(朱)

[清]任颐 横云山民行乞图轴 147cm×42cm 纸本设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款 识: 萧山任柏年写。横云山民行乞图。同治七年之冬,胡公寿自题。谓隐者邪?奚必貌其形;谓狷者邪?奚必乞于人。遨游尘埃之外,栖息山泽之坰,瞭焉眸子而曰乞者,吾知其抑塞磊落之不平。古之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然乎?不乎?请质诸先生。先生莫对,举首青冥。辛未秋七月,蒋节赞。钤 印:任颐印(白) 公寿印信(朱) 横云山民(朱) 蒋节之印(白)

[清]任薰 秉烛图轴 204cm×121cm 纸本设色 清同治九年(1870)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款 识:同治庚午春三月,阜长任薰写于鸿城寓斋。钤 印:任薰之印(白)

[清]梁辰 人物图册 28.2cm×54cm×5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款 识: 家家扶得醉人归。壬申秋初星樵写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星樵画。为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寥莫,惟有饮者留其名。壬申八月梁辰。己巳中秋,梁辰画。触斗蛮争莫认真,丹青阿堵偶传神。群盲自擅何须怪,具眼而今有几人。壬申六月,梁辰戏作。钤 印:梁辰私印(白) 养拙居士(白) 梁辰之印(白) 星樵(朱) 养拙居士(白)梁辰私印(白) 星樵子(朱) 星樵(朱)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三 22cm×61.5cm 纸本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昔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唐文宗与学士夏日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人谓其言称尧舜,与心正笔正之言同旨。丙寅中伏,书为兰翁老长兄。汪由敦。钤 印:臣由敦(朱白相间) 师茗(朱)鉴藏印:端吾刘楷(白) 子俊珍藏(白)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二 22cm×61.5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步堂写。鉴藏印:稚珊秘玩(朱)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九 22cm×61.5cm 纸本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熊虎顾盼,鱼龙起(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八 22cm×61.5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欢乐长年。肇裔。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七 22cm×61.5cm 纸本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孟頫方雨中闷坐,忽得惠字,乃知为雨小留,同此无赖。承示画梅及观音像。一如来意题数字其上,却用奉纳,冀目入。行潦满道,不敢奉屈。临纸驰情。不宣。顷闻旆从一再过吴,何不蒙见过耶。孟頫滞留于此,未得至杭,想彼中事已定。昨承许惠碧盏,至今未拜赐,岂有所待耶?临松雪札二,竹涛毕溥。钤 印:臣溥之章(朱) 竹涛(朱) 养拙(白)鉴藏印:子俊珍藏(白) 端吾刘楷(白)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六 22cm×61.5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朱肇裔画。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五 22cm×61.5cm 纸本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兰亭帖当宋末度南时,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王顺伯、尤延之诸公其精识之尤者,于墨色纸色肥瘦秾纤之间,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兰亭谓“不独议礼如聚讼”,盖笑之也。然传刻既多,实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五字既损,肥瘦得中,石本中至宝也。芗圃先生雅属,春湖李宗翰。钤 印:李宗翰印(白)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四 22cm×61.5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得利丰余图。步堂写。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十二 22cm×61.5cm 纸本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朱肇裔字步堂,明华王府孙,与八大山人为昆季行。甲申国变后,入华山为僧,以诗画自娱。满清初入关,一般王公显贵不识汉字,皆盲人也。戏写此群盲图以讽刺之。落笔古朴,风趣盎然,迥非凡俗者所可比拟。世皆知八大山人而不知有步堂,因其画流传甚少也。步堂事迹详载《河滨全集》及《同州府志》。稚珊识。钤 印:稚珊刘钟仁章(白) 吉水人(朱)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十一 22cm×61.5cm 纸本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近思录云:若不用躬行,只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于孔子,只须一二日便说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古人只是日夜皇皇,理会这个身心。到做事业时,只随自己分量以应之。如由之果,赐之达,求之艺。只此便可从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功业则用大圣人做,随其分量,如何强得。又与长子受之书曰:早晚受业请益随众,例不得怠慢。日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劄记,以候质问,不得放过。篑山世兄属,张岳崧。钤 印:翰山(朱)鉴藏印:子俊珍藏(白)

[清]朱肇裔 群盲行乐图册之十 22cm×61.5cm 纸本设色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款 识: 七贤共市。步堂。鉴藏印:吉水刘稚山氏(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