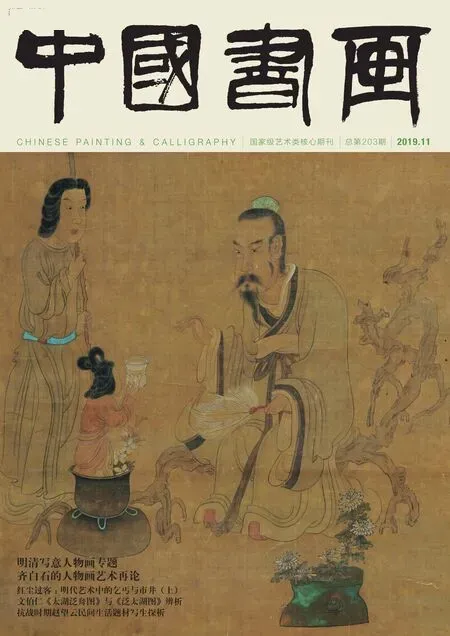抗战时期赵望云民间生活题材写生探析
◇ 于亮 赵娜
一、赵望云中国画创作题材与技巧的创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值抗战时期,民族命运岌岌可危。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民的身体、精神饱受摧残,生存大为不易,底层民间更是饿殍遍野,一片哀号。生于彼时的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思考也进入新的阶段。在当时大的文化背景下,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激烈碰撞,艺术的内涵以及功能等都在被重新思考与建构。传统思想中艺术的功能在于“成教化,助人伦”,对于当时的艺术家们依然有深远的影响,故而当时的艺术家们多认为艺术创作应该围绕社会现实展开。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当时很多艺术家吹起了“到民间去”的号角。基于此,艺术界掀起救亡思潮,音乐领域的音乐家光未然、冼星海作品《黄河大合唱》,文学上茅盾的《白杨树》、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国民精神,在反抗日本侵略等方面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些艺术作品在当时无疑将艺术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至今仍广为流传,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文化精品。在救亡思潮引导下,绘画领域内徐悲鸿、赵望云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活动尤为突出。徐悲鸿借用历史题材来表达自己的历史主张,如《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傒我后》等历史画,而赵望云则深入普通群众内部,开启“长安画派”先声。“人民”在赵望云的抗战题材作品中具有突出的高度,此与当时文艺界的抗战救亡呼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和声,也是作为“长安画派”代言人的赵望云之于中国画史的存在意义。

图1 徐悲鸿 愚公移山图卷 144cm×421cm 纸本设色 1940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艺术理想是美好的,而要将艺术创作深入普通群众的生活细节,艺术家需要更多地与现实接触,真正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基于这样的实际困难,在当时能够真正做到以身作则,深入民间底层生活的艺术家却寥寥无几。不过,在险恶的环境下,有这样一位倔强之人—赵望云,走向民间,诉说生活,凡眼见现象,无不随时绘录,深入刻画(图2)。如其所言,“时值民族生存的抗战期,广大民众应各尽所能,文人以笔当枪,为应尽之职责与本分”〔1〕。他将身经眼见的事实,结合自己的艺术理想,衍生出图像内容,再用自己的绘画技巧,将普通民众活生生的现实转化作笔下的画作,以绘画的形式向国人展示了抗战时期真实的民间样貌。由于艺术理想与娴熟的绘画技法,且缘于出身农村的原因,他熟悉农村,可以做到将民间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充满生命的温度。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国家的根本,赵望云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创作中自觉地将绘画的主体转向农民,将农民为艺术描绘对象,围绕抗战的主题展开,以独特的视角创作了众多描绘苦难的农村生活作品(图3)。赵望云的艺术观也在此期间逐渐形成,通过进行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启“农村写生”之路。自1933年开始,他通过写生的方式走进民间,直面民众,诉说人民生活状况,描绘处于战乱时期民众的劳苦生活,将民间生活情态融入绘画,天下苍生的苦难在他笔随心动的画面中活生生地展现在大众眼前。也许正因为他来自农村的人生经历,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村,能够感同身受民间疾苦,从而能将民间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赵望云勇于揭开最底层生活的面纱,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国家存亡的忧虑、对民间生活的同情,用艺术的力量向人们传递、诉说底层民众的呼声(图4)。其绘画作品由此引起强烈共鸣,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并悄然为中国画的创作注入新鲜血液。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宁晋县境的民间》《战后之罗文峪》《流亡之船》等一大批作品,将其熟知的西北民间生活传播至祖国各地,在社会各界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为中国画的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发出“长安画派”的嚆矢。

图2 赵望云《讨债人》 1934年

图3 赵望云《农村街头一座虫王庙前阶》 1934年

图4 赵望云《一个吸金丹致贫之流亡者》 1934年

图5 赵望云《柏木林的坟墓与碑志》 1934年
除了国运飘摇,政治以及时局的混乱,文化困局在当时也备受关注。当时一批有思想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文人,积极发起文化改革思潮。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新就是备受瞩目的课题,有守旧派与全盘西化派以及折中派。从康有为到陈独秀,都提出了文化革新的路径。在美术领域,王溦从学理上反思了中国画改革路径,俞剑华也曾就山水画科革新提出过全新的画论〔2〕。1926年留学归来的徐悲鸿极力推崇改变传统思维,将西方绘画融入中国画中,以素描来改造中国画造型能力的不足,将这样的思想推广到美术教育领域。“中国画改良论”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思潮,也是20世纪对中国画最务实的改变。赵望云在坚持艺术创作内容方面改进的同时,对于中国画技巧的改进也在不断探索当中。他不再拘泥于传统中国画的创作,在题材选择上以人文自然为主,在技法方面注重造型,将西方观察世界的方法用于中国画创作。一系列的实验让他的中国画呈现出全新面貌,少了些“孤冷清高”之态,多了些“烟火气息”(图5)。他自云:“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3〕
二、赵望云艺术作品传播与影响
赵望云走出舒适的象牙塔,深入民间写生,描绘当时中国民间正在经历的事,充满生活气息,这样的选择是忧国忧民思想的体现。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虽然众多艺术家都意识到艺术创作内容和艺术救国的关联性,但是能够彻底将艺术理想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却并不多。岭南画派注重战争场面以及武器的刻画和表达,俞剑华注重自然山水的客观观察,沈逸千也进行了大量战地写生与展览活动,但是能够深入普通群众,将艺术对象对准战争情况下民众生活状态的却很少。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中国画创作中,虽有徐悲鸿《巴人汲水》这样的杰作,但直到赵望云出现,中国画相关题材的人物画才在画坛形成较大影响,引起群众共鸣,更好地达到宣传全民抗战的艺术效果。20世纪30年代,赵望云多次受《大公报》的委派,漫游西北各县,通过写生反映底层农民的世间百态。1933年2月至5月,赵望云途径北平至冀南十余县的写生历程,再现十余县农民的真实生活,凭借同情民众的热忱,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生疾苦、农村破产的真相表现出来,共计创作130余幅写生作品,出版了《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图6),让读者如临其境,与民众同忧患、共患难,也因此唤醒了整个艺术界的良知。由于1933年日军对河北发动进攻,赵望云对此密切关注。1934年春,赵望云与杨汝泉一同旅行塞上,由天津出发,经唐山、遵化、张家口等地,最后至绥远,描绘了许多热血激烈的抗战场景以及战后民众生活的惨况,如《战后之罗文峪》《翠屏山》《阴雨中之八达岭》等一系列作品,共99幅作品。后均由冯玉祥题诗,杨汝泉注释,最终出版《赵望云塞上写生集》(图7)。赵望云深入陷落或未陷落的长城一带,道破祖国河山的危局以及民间生活的惨状。杨汝泉在四幅《战后之罗文峪》(图8)的说明中这样写道:
你望一望南门,虽可感到他那古老雄伟的气魄,但同时也可以想象出全城的残破。
那是太平时候,所以国家注重防守;现在呢?我们只有唏嘘而已。
沿长城北望,依然是中国所属的遵化土地,但事实上已不容我们夸耀,而只有令我们饮泪凭吊了!
这种战壕的优点:非走到跟前看不出是战壕来。这些遗物都成了令人凭吊的纪念品了。
从杨汝泉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体会战况之惨重,民众都在挣扎中活着,这样的情景耐人深思。冯玉祥也感同身受的写道:
死伤如山积,血把河水染红了。
如今外患更厉害,不抵抗者无国防;各处口子任意进,亡国滋味大家尝。不顾亡国须起来抵抗,抵抗敌人必要民众武装。
如今日本打我们,到处无有人过问,谁也不敢说伤心。
誓死收复失地,二十九军遗迹:长城要塞上,麻包作阵地。真可惜!真可惜!不抵抗的人们,把土地让给帝国主义主!自己将当亡国奴,想想你的子孙呢?
可想而知,此时国家的危难以及广大民众面对侵略的同仇敌忾。赵望云对底层生活充满“人民性”的生动刻画基于一种本真、纯粹的爱。他使艺术与民间大众生活融为一体,始终以民间生活为描绘对象,通过艺术创作让人们了解外敌对祖国的侵略场景,号召民众和侵略者浴血奋战。如盛成所说:“人为人群服务才是人,为良心所驱使而牺牲,造成一种自由自在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之中,自己是自己的主人。”〔4〕赵望云在艺术创作中也是这样去实践的。1936年,江南发生严重水灾,他看到新闻后毅然决然奔赴江南农村,心系灾区农民,在对受灾群众进行基本救助之后,又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其作品着重描绘灾难过后的景象。一系列作品后来进行展览,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出版《赵望云旅行印象画选》(图9),展览和画册的传播,让社会普遍增加了对受苦群众的关注和关心。1942年他又踏上西北之旅,历时五个月,描绘了大后方民众生活场景、西北的大好河山以及边疆地区的民族风情、羁旅之苦,诸多写生作品见于1943年出版的《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图10)。从赵望云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位艺术家以笔为枪的激情以及一种融入血液深处的“人民性”。

图6 赵望云农村写生集

图7 赵望云塞上写生集

图8 赵望云《战后之罗文峪》

图9 赵望云旅行印象画选

图10 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
结语
深怀民族精神的艺术创作必然会被民族所选择。赵望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视线从未离开过人民,作品主题和形式高度统一,立意明确,表现力强,纯粹是为人民而歌,充分体现艺术的主流价值。正是赵望云等人的努力,抗战、救亡作为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主题,汇聚了更多才情满腹的艺术家参与进来,他们以艺术的方式关心着社会,鼓舞着人民。聂耳的《前进歌》、徐悲鸿的《负伤之狮》、李桦的《怒吼吧!中国》等作品都表现了遭受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激励着人民在抗战的漫漫长夜中斗争不息。
在民族存亡的特殊时期,像赵望云这样关注社会现实、背负时代责任、怀有民族复兴精神、投笔从戎的艺术家们,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大合唱。深入农村、乡镇,贴近底层民众,注定使赵望云成为艺术史辉煌的一页。在当下画坛生态中,赵望云钟爱的题材已然成为画家们容易忽视的暗角,此足以引起画家与公众深刻的反思。真正地爱什么,才能画好什么,至今仍为中国画创作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