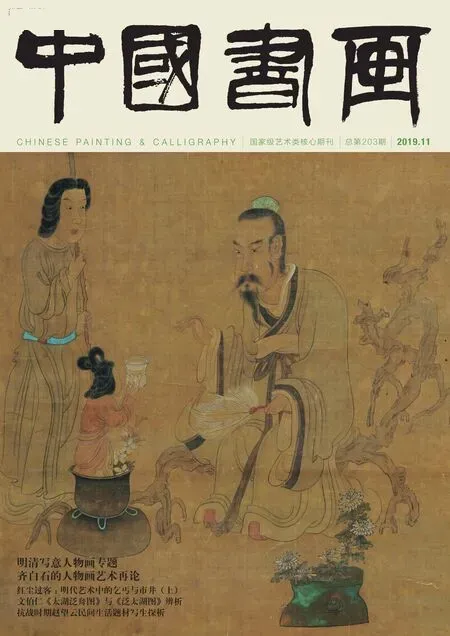红尘过客
——明代艺术中的乞丐与市井(上)
◇ 黄小峰
在过往的学术研究中,底层民众的形象得到的关注不多。本文将以明代艺术中的乞丐图像为出发点,探讨底层民众形象成为一种绘画主题的原因与意义。〔1〕
一、文人的争论
1564年至1577年,三位苏州本地的文化名流—黄姬水、张凤翼、文嘉,围绕着一件绘画作品进行了一场讨论,意见纷纭。
事情要回到1516年。初秋七月的一天,苏州画家周臣在家中闲坐,忽然间想起了平常在街市上看到的一些人。手边正好纸笔齐备,于是他突发奇想,把这些人物画出来,汇集成一套册页(图1、2)。作为一位声名卓著的“职业画家”,周臣不常仅为自己的兴趣作画,也不常在画上写上篇幅较长的题记以说明作画的前因后果。因此,这套册页中长达45个字的题记便显得耐人玩味〔2〕:
正德丙子秋七月,闲窗无事,偶记素见市道丐者往往态度,乘笔砚之便,率尔图写,虽无足观,亦可以助警励世俗云。
看得出,他在作画的时候心态轻松,不是为市场制作大幅的工整画作,而是休闲消暑时的率意小品。周臣没有给作品命名,也没有明确指出画的含义,无形中给后来者设置了一个谜团〔3〕。五六十年之后,后辈文人张凤翼(1527—1613)为画作撰写了赏观题跋,他第一次提出明确的解释:周臣画中那些流离失所的乞丐与残疾人,继承的是北宋郑侠《流民图》的政治讽喻的传统。郑侠的画隐喻的是王安石变法后的景象,而周臣的画隐喻的是正德年间宦官刘瑾、钱宁、江彬等混乱朝政造成的民生凋敝的惨景〔4〕。张凤翼为我们今天看待这幅画奠定了一个基调:画面表现的是因为社会动荡而流离失所的穷苦百姓,带有针砭时事之意〔5〕。今天,我们一般称周臣这件作品为《流民图》,便是接受张凤翼的看法,政治色彩和道德色彩在其中隐约可见。
其实,先于张凤翼看过这件作品的黄姬水(1509—1574)也在暗自揣摩画作想要表达的意思〔6〕。他在1564年的题跋中说,画中的各色人等画得入木三分,让人笑掉大牙。接着,他笔锋一转,发起感叹:可惜这位大画家已死,无法再让他去描画一下如今那些为了乞求官禄而巴结权贵、苟且钻营的人的嘴脸!黄姬水引用了一个和“乞”有关的典故,迅速地把话锋由画中乞丐的视觉形象跳转到现实世界中求官者的社会形象。这是一个文士们耳熟能详的典故。“昏夜乞哀,以求富贵者”一语,出自汉代赵歧注解的《孟子》。在《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孟子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齐国人,每天外出,回家后总是跟妻妾炫耀说与一众富贵者吃饭,饱餐酒肉。妻子将信将疑。第二天尾随丈夫以探究竟,结果发现丈夫去的是城外墓地,向那些祭祀亲人的人乞讨剩下的祭品。一座墓还不够,遍寻祭祀者以乞讨祭品。妻子为丈夫的可耻行径羞愧而泣。他回家后不知妻子已然知晓,依旧当面炫耀。孟子评论道:“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赵歧的注解是:“言今之求富贵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骄人于白日,与斯人何以异哉?”〔7〕“昏夜乞哀”成为这个故事中流传最广泛的警语。在明代,其意思已经基本固定为讽刺那些为了做官而不择手段的人。他们为谋求官禄而向当权者不知廉耻地乞讨,却在人前骄横跋扈。黄姬水未有功名,乃至收藏周臣此画的一位“卧云徵君”〔8〕,都可称隐士。由画中的乞讨者过渡到“昏夜乞哀”的乞官者,是一个合适的联想,因为他们都是以乞讨为生,一个乞饮食,一个乞官禄。
“贫士”黄姬水看到了画中的诙谐幽默,联想到了钻营官场者的讽刺漫画;“戏剧家”张凤翼看到了画中人的肢体痛苦,将画面视为精深的政治寓言;画家文嘉(1501—1583)则专注于画面的笔精墨妙,认为前两人的解读都是对画意的引申,他认为读画首先应专注于画面的风格技巧〔9〕。

图1 [明]周臣 流民图卷 31.9cm×244.5cm 纸本设色 克利夫兰美术馆藏本
这三人的题跋,特别像是关于如何观看绘画的一次学术讨论。黄姬水代表了社会学视角,张凤翼代表了政治解读,文嘉则代表了风格分析。今天的学者,更倾向于张凤翼的解读。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画中有不少乞丐和残疾人。另一个原因是周臣在题记中说此画可以“警励世俗”。这里的“警励世俗”,该如何理解?画中的乞丐、身体残缺之人等底层人物,究竟会在什么意义上有助于“警励世俗”?

图2-1 [明]周臣 流民图卷(局部) 檀香山美术馆藏本

图2-2 [明]周臣 流民图卷(局部) 檀香山美术馆藏本
二、乞丐
这件中国绘画史中奇特的画作,都画了谁?
中国学者称之为《流民图》,亦有称之为《乞食图》。画中人被视作“流民”,流民的生存方式主要是乞讨,因此也是乞丐。两种命题都可归功于张凤翼。他的题跋后来被收入了他自己的文集《处实堂集》,标题即为《跋周舜卿画乞儿》。张凤翼离周臣此画只有五六十年之远,我们离开周臣此画却已经整整五百年。按理说我们应该相信他。然而我们已经知道,早在他的时代就已经对这件作品众说纷纭。看起来我们确定能够相信的,只有周臣自己。
画家自己说,他画的是平素所见的“市道丐者”。“市道”有专门含义,本意指市中道路,后用来指代市场。譬如古人所说的“市道交”,指的就是市场中以利益为先的交往关系〔10〕。“市道丐者”指的应该是“市场中的各色人和乞丐”。因此,英文名称反而比目前的中文名更为客观,一般称之为《Beggarsand Street Characters》(直译为《乞丐与街头人物》),虽突出的依然是乞丐,但还有其他人物。诉诸画面,我们会发现周臣所画的24个人物中,的确可以划分为乞丐与市场人物两大类。
明代的乞丐是什么样子?和周臣同时代的南京人陈铎(?—1507)有一首《乞儿》散曲:“赤身露体,木瓢倒挂,草荐斜披。东家跪了西家跪,受尽禁持。宴席上残汤剩水,斋堂中素菜咸食。官府上无差役,自寻来自吃,冻饿死也便宜。”〔11〕再晚一些,冯梦龙编的话本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篇有更生动的对乞丐的描述,在“金癞子大闹莫稽”一段描述道:“开花帽子,打结衫儿。旧席片对着破毡条,短竹根配着缺糙碗。叫爹叫娘叫财主,门前只见喧哗;弄蛇弄狗弄猢狲,口内各呈伎俩。敲板唱杨花,恶声聒耳;打砖搽粉脸,丑态逼人。一班泼鬼聚成群,便是钟馗收不得。”〔12〕在《古今小说》的初刻本中,还配了描绘这一场景的插图,就画有一男一女两个乞丐。综合散曲、小说与版画,可得到一幅乞丐的标准行头:破草席或破毡子、打狗竹棍、破碗、木瓢、破帽、布条打结的破衣衫、身体大面积裸露。这样一来,就能很容易地指认出周臣画中有9个“标准乞丐”,其中3人斜背草席,3人手拿破碗,5人手持打狗棍。这些都是男性乞丐。在周臣画中,不少人腰间除了挂着篮子、罐子,还往往悬挂着一个竹筒状的物体,这也是乞丐的配置之一〔13〕。身体残疾的人丧失劳动力,也常成为乞丐。画中另有3个身体严重残疾者,居然有2个女性。1个下半身麻痹者,她双手戴有手套,以手为爬行工具。另有2个盲人,应为一老头、一老妇,靠动物导盲。用羊导盲的是一个中老年女性。这是一个十分戏剧性的形象,几乎什么惨状都在她身上出现。她不仅是盲人,还是瘤女,下巴上长着巨大无比的瘤,一条腿上还有可怕的浮肿。且以她的年纪,竟然怀抱一婴儿,似乎在哺乳。
9个标准乞丐加上3个残疾人,这12个人构成了庞大的乞丐队伍。除此之外,还有8人也可以归在乞丐名下,可称之为“技术性乞丐”。按照《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描述,乞丐中还包括以一些以杂耍、歌唱、表演而行乞的人。周臣画中有3人,一个耍猴,一个戏松鼠,一个耍蛇,正是“弄蛇弄狗弄猢狲”。还有1人打着拍板唱莲花落,他还有眼疾,正是“敲板唱杨花”。还有2人,脸上化了妆正在表演。他们应是装扮成一对夫妻,装扮为女性的那位,有尖尖的发髻,脸上涂抹了“三白”,下穿破烂红裙,手拿黄色手帕。这应是“打砖搽粉脸”中的“搽粉脸”(图3)。那什么是“打砖”呢?画中一位赤裸上身的精瘦乞丐,手中握着一块不甚规则的物体,这应该就是砖头、瓦片或石块,他将用这块硬物不停捶打自己,以自残作为乞钱的方式〔14〕。此外,画中还有一人,手拿扫帚,从裸露的上身以及打结的衣衫布条来看,也应是一位以某种特殊方式行乞的乞丐,只是暂不知扫帚的用处。

图3 [明]周臣 流民图卷(局部) 檀香山美术馆藏本

图4 [明]周臣 流民图卷(局部) 檀香山美术馆藏本

图5 帝鉴图说 18世纪彩绘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周臣的原作是册页,但在清代被分装成了一幅手卷,又在清代后期被裁割成两卷,现在分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和檀香山美术馆。不过这两个画卷并非周臣原画的全部。根据何惠鉴和周汝式的研究,至少还应有6个人物。其证据是周臣此画在清代曾经被人临仿,在俞云题跋的一件被称作《江湖三十六行》的仿本中,有6个人物是存世的画面上没有的〔15〕。这6个人也全都是乞丐,一个青年标准乞丐,一个老年的驼背乞丐,一对乞丐老夫妇,其中老妇怀中也抱一婴儿,还有扮成夫妻的两位化妆演剧者,也即“搽粉脸”。
在周臣的24个人物中,乞丐有20人。如果他画的是30个人物,那就占到26人,但余下的4人绝非乞丐。一位是打渔鼓、唱道情的道士,一位是手拿钵盂化缘的僧人,一位是背着口袋的年长女性,一位是同样背着口袋的年轻女子(图4)。这4人除了化缘僧的僧袍下缘有些破烂,显示出风尘仆仆之外,装束还颇为得体。两位妇女位于册页同一开,左右相对,衣裙整洁。年长女性头上可看到锥形的“䯼髻”,这是明代有一定地位的已婚女性的标准装束。与之最接近的䯼髻图像是山西繁峙公主寺正德十五年(1520)的水陆壁画中,可看到抱小孩的䯼髻女子,尽管远在山西,但时间只比周臣晚4年。年轻女性则梳着“云髻”。她们身后背着的包袱,老者的稍重,和脸型一样多有棱角。年少者稍轻,与脸型一样圆润。包裹意味着她们也正游走在途中。她们是什么人?
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城市中大量出现一种被称为“卖婆”的女性。陈铎有一首《卖婆》散曲:“货挑卖绣逐家缠,剪段裁花随意选,携包挟裹沿门串。脚丕丕无远近,全凭些巧语花言。为情女偷传信,与贪官过付钱,慎须防请托夤缘。”〔16〕顾名思义,“卖婆”是做买卖的女性。她们迈出家门,走街串巷做些零散买卖。她们主要针对女性客户进行推销,卖些刺绣、首饰等。由于是女性,她们往往得以进入宅门中,接触到大量闺中女性,成为深闺女子与外界接触的渠道之一,于是也从事一些特殊工作,如传递信件、情书等等〔17〕。明末松江人范濂《云间据目抄》对此有更详细的描述:“卖婆,自别郡来者,岁不上数人。近年小民之家妇女,稍可外出者,辄称‘卖婆’。或兑换金珠首饰,或贩卖包帕花线,或包揽做面篦头,或假充喜娘说合。苟可射利,靡所不为。而且俏其梳妆,洁其服饰,巧其言笑,入内勾引,百计宣淫,真风教之所不容也。”〔18〕可见“卖婆”常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松江地区,就是由别的县市所来。“婆”泛指结婚后的女性。“卖婆”们注重外表,通常都打扮得俏丽整洁。她们的标准行头是陈铎所说的“携包挟裹”,背着轻便的包袱,或是提着小匣,便于走动〔19〕。这些特征与周臣画中的形象都十分吻合。

图6 [明]石嵉 流民图卷(局部) 38.5cm×634cm 纸本设色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就是周臣眼里的“市道”:一个下层人物混迹的地方,一个热闹非凡的市场,一个形形色色的江湖。或许是因为乞丐占画面绝对多数,而且画得非常夸张生动,因此人们容易忽略“市道”。当黄姬水说画中所画是“街市丐者”的时候,他尚离周臣的本意“市道丐者”不远。而当文嘉用“饥寒乞丐”一词时,已经抹去了“市道”,描述乞丐时也带上了主观的怜悯色彩。及至张凤翼用“饥寒流离、疲癃残疾之状”描述画中人物的时候,画中主题更是被限定为极易引起恻隐之心的流民和残疾之人。作为画家,周臣并未在画面中和题记里表示出对画中人的明确态度。在这一点上,黄姬水相对而言显得更为客观。正因为相对客观,只有他从画中看到令人“绝倒”的滑稽和幽默。哪里会令观者绝倒呢?也许是画中人不同的面相,也许是他们各有千秋的牙齿,也许是头扎两个小髻的教松鼠艺人(他的嘴仔细看来竟与松鼠类似,是个豁嘴),或许还有那过于惨不忍睹的牵羊老妇脖子上巨大的瘤。
无论周臣的三位苏州后辈是否体会到画家当时的创作意图,我们都可以说,这幅集市场中各色人物于一体的作品,是一种新的绘画类型,它不但提供了新奇的图像,而且早在16世纪后期就激发了围绕着图像与其意义的热烈讨论。

图7 [清]胡葭 流民图册之一 纸本设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图8 [明]吴伟(款) 《流民图》中打架的盲艺人 大英博物馆藏

图9 《三才图会》中的市井图
三、另一种“流民”
1593年,黄河河堤大面积决口,河南、安徽、山东许多地方受灾。朝廷应对不及时,灾情持续扩大。第二年,刑科给事中杨东明(1548—1642)向万历皇帝进《饥民图》,并附以文字描述。皇帝动容,下令立即赈灾。杨东明的《饥民图》共十四幅,尚有版画图像传世,表现的是灾民的种种惨状以及为活命而做出的残忍行为,包括“人食草木”“全家缢死”“刮食人肉”“饿殍满路”“杀二岁女”“子丐母溺”“饥民逃荒”“夫奔妻追”“卖儿活命”“弃子逃生”等等〔20〕。饥民,也即流民。“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这是《明史》中对“流民”的定义。因饥荒和兵荒而离开本籍,流浪他乡,便是流民。
对于“流民图”这个词,周臣可能并不陌生,这个据说始于北宋郑侠的绘画题材在明代得到广泛的了解,以至于张凤翼在观看周臣作品的时候立即就想起来。郑侠的故事早就成为一个传奇。至于其进献给皇帝的那幅画究竟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真迹存世,对于明代人来说倒不太重要,反正人们知道,这幅画画的是饥荒中贫民的惨状。明代饥荒和天灾很多,尤其是明代后期,频繁发生。因此,在一些饥荒频发的地区,一些官吏也仿照郑侠故事,给朝廷进呈“流民图”。1540年,嘉靖皇帝为其父母在湖北修“显陵”。赶上河南、湖广旱灾,大量饥民应召修陵以谋求生活。工事结束后,近万饥民滞留当地,政府并未做出有效措施,导致“屯聚饥饿,积尸载途……其尚存者,或鬻子捐妻,或剥木掘草,或相向对泣,或矫首号天,犹可言也。及其父不顾子,夫不计妻,飘零于阴风积雪之中,匍匐于颓垣荒垅之下”。见到这种“流民死亡,凄号万状”的惨状,御史姚虞于是向朝廷进献《流民图》册:“臣不能尽述其状,谨命工为图一十有二。不避斧钺之诛,敢效郑侠之献。”〔21〕1586年,山西大饥,布政使沈子木“仿郑侠绘《流民图》奏上,得捐帑金十万为赈,命吏治粥以饲饿人,全活者甚众”〔22〕。“流民图”伴随着的是惨烈的灾荒。灾民和死亡是“流民图”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明代得到了再生。
竟也有人相信,自己见到了郑侠《流民图》的原作。长期在北京为官的鲁铎(1461—1527)是周臣的同时代人。他的文集中有一首《观郑侠流民图》长诗,透露出他曾见过一幅传为郑侠的《流民图》〔23〕:
近来偶得《流民图》,宝爱矜怜看未了。旱风吹沙天地昏,扶携塞道离乡村。身无完衣腹无食,疾羸愁苦难具论。
老人状何似?头先于步无生气,手中杖与臂相同,同行半作沟中弃。
小儿何忍看?肩挑襁负啼声干,父怜母惜留不得,持标自售双眉攒。
试看担头何所有?麻糁麦麸下□缶。
道旁采掇力无任,草根木实连尘土。
于中况复婴锁械,负瓦揭木行且卖。
形容已槁臀负疮,还应未了征输债。
千愁万恨具物色,不待有言皆暴白。……
当年此图谁所为?监门郑侠心忧时。
……
此图世远迹逾新,长使忠良肝胆热。
……
愿将此图继无逸,重模国本陈吾皇。

图10 [明]仇英(款) 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30.5cm×987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11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的局部,这个局部画有4个乞丐

图12 《上元灯彩图》中的乞丐
他描述的这幅画,与杨东民《饥民图》、姚虞《流民图》等,场景上类似,也是以成群结队的流民、瘦弱的老人和孩子、父母被迫售卖儿女等场面来引发观者的同情。想要知道明代人理解中的郑侠《流民图》是什么样,还有一种途径。在明代后期流行的图书《帝鉴图说》中,有宋神宗“轸念流民”一幅。画面上方,神宗正在观看桌上展开的一幅手卷,正是郑侠进献的《流民图》(图5)。画面下方则是《流民图》中描绘的场面,正描绘了文字中所说“有采树叶、掘草根充饥的;有衣衫破碎、沿途讨吃的;有饿死在沟渠的;有扶老携幼、流移趁食的;有恋土不去、被在官公人比较差徭、拷打枷锁的;有拆屋却房、鬻儿卖女、变价纳官的”。在清代的彩绘本中,更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神宗桌上打开的手卷里也描画了图像,正是那饿死在沟渠的人。清代官员陈士倌也仿照《帝鉴图说》制作了一套《圣帝明王善端录》,其中一开画的是宋神宗观看一幅很大的《流民图》手卷,上面画的也是十几位成群逃难的百姓。山西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有两幅描绘的是流民和乞丐,右第四十五题为“饥荒殍饿病疾缠绵自刑自缢众”,画中描绘了因饥荒而造成的惨象。在衰败荒寒、树木都已枯死的荒野,一群衣不蔽体、病痛缠身的老幼难民在逃难,后面则有自缢的女性和自刎的男子。显然,流民始终与饥荒和死亡紧密相连。右第四十六题为“依草附木树折崖摧针灸病患众”。画面主要人物是前景的流民乞丐,或残疾或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这种标准“流民图”与周臣也被后人称作“流民图”的作品差别很大。卖儿卖女、尸体遍地、吃草根树皮这些场景是“流民图”中常表现的景象,哪里能在周臣画里找到?周臣画中的僧、道、卖婆绝非流民,即便是26个乞丐,也多是一些职业性乞丐,很难笼统归为“流民”。

图13 [元]朱玉(款) 太平风会图卷(局部) 26cm×790cm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话虽如此,实际的情况却是,确实有明代文人,如张凤翼,认为周臣所画的乞丐就是郑侠《流民图》的另一种形式。我们不禁要问:明代是否真的有另一种“流民图”,它描绘的并不是饿殍遍野、卖儿鬻女的灾荒惨状,而是街市中的僧道、妇女、艺人、乞丐?
这类“流民图”确实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幅石嵉《流民图》卷,作于1588年(图6)。大英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吴伟款《流民图》长卷,是否吴伟尚存疑问,但应该是一幅明代作品。尽管叫作“流民图”,但两图的图名并非明代就有,而是晚近的鉴藏家所拟。前者得自引首处民初人柯树荣的题,后者得自溥儒题签〔24〕。他们脑中所想,还是根深蒂固的郑侠《流民图》的传统。除此之外,存世还有几件名为“乞丐图”的清代画作值得一并考察。美国私人收藏的一幅王大经1662年题跋的《百丐图》卷,以及巴黎汉学研究所收藏的清代《群丐图》,与石嵉《流民图》、吴伟《流民图》无论在画中人物还是绘画手法上都颇为相似。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还藏有一套清代胡葭的册页,也被如今的学者命名为《流民图》(图7)。这些画作可以窥豹一斑,看到同一个题材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后期的发展情况。
倘若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立即能看到其中的紧密关系。尽管对于这类所谓“流民图”中数十百个人物的具体身份还不能完全清楚,但可以看出他们都属于社会底层。他们聚在一起大致是基于两个分类方式:一是按照职业身份的不同划分为僧人、道士、卖婆、乞丐、杂耍者、算命先生、卖膏药、卖鼠药等等,即便是同可归属于广义的“乞丐”的人中又依据“专业方向”的不同,划分为滑稽表演者、耍猴者、耍蛇者、弄松鼠者、弄狗者、乐师、驱鬼辟邪者等等。二是按照外形特征划分为盲人、跛子、拐子、瘫子、矮子、瘤子等等。画家似乎并不是将这类画作用来表达政治诉求和民间疾苦。相反,人们可能会更多地去欣赏画中幽默诙谐的市井气息。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戴进款《升平村乐图》,与吴伟、石嵉的“流民图”颇为类似。只不过画卷要短一半还多,人物只有10位。极有可能这幅画被裁割过。留下来的这一段中,我们还可看到走索者、弹琵琶的盲人乐师等人物。画中老妪头上也可看到尖锥形的䯼髻,与周臣所画的年长卖婆相类。类似䯼髻在石嵉画中也可看到。和石嵉画类似,也都在肩扛索杆的男性身旁搭配年轻女性,这应是表明当时女性是走索表演的主要表演者。特殊行当的特殊行头都得到了表现,比如吴伟、石嵉“流民图”中的卖药者,都肩挑船形的石碾子。《升平村乐图》的画法与吴伟款《流民图》最为接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几幅画中,周臣的册页、石嵉的手卷,以及清代的两幅乞丐图,都只画人物,不画背景。只有吴伟款《流民图》和戴进款《升平村乐图》画出了树石相生的背景,显示出是在乡间野外或城市近郊。
我们很难理清楚这几幅画之间的具体关系,几幅画作彼此之间都有那么点近似。比如,若比较吴伟《流民图》和清代版本的《百丐图》《群丐图》,只消对比捕蛇者和盲人斗殴二段便可看得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产生的,是两幅画作的直接碰撞,还是图像模式的传播?一时难以评估。在明代中后期,表现这种底层街市人物可能已经有了一些陈规。比如,“盲人打架”“弄猢狲”“耍蛇”几乎成为这类绘画的固定配置〔25〕(图8)。与其说他们激起的是观者对饥荒、灾年、流民、政治隐喻的联想,毋宁说激起的是观者对热闹、滑稽的俗世景观的会心一笑。

图14 《太平风会图》中的乞丐
四、市井图
周臣为什么会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描绘“市道”—一个下层人物的集散地—的方法?“市道”其实就是“市井”。1609年出版的类书《三才图会》中有一幅“市井图”(图9)。画中就是一幕街市的商业景观,可以明确辨认出染坊、诊所、肉铺等店面,而街上的人最显眼的就是一位盲人算命者。除了他之外,街上还走着两位挑担子的人和一位背包裹的人。这种组合应该是表示:街边的固定店铺和街中的流动职人,构成了市场。对页对“市井”的文字说明写道:“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濯,令香洁,然后到市也。”果然,出于对“市井”的这种解释,画面在比较中央的位置画了一个小亭,亭子里有一口井。对于市场的描绘,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趣的是,在张择端描绘的大都市里,靠近卷尾的地方也画了一口井。市场中的这口井,也出现在了明代中后期传为仇英的仿本《清明上河图》中。再往后,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井更是成为一个主要景观,是一幕打架的发生地。从“市井”这个角度而言,《清明上河图》这类城市图,是否就属于一种对于“市井”的认识和写照?〔26〕
在周臣的街市人物图和仇英的繁华城市图之间,其实存在一种有趣的联系。辽宁省博物院所藏仇英款《清明上河图》的热闹街市中,在一个典衣铺前,有一个耍猴的人。他身穿一件缀满补丁的百衲衣,衣服下摆破烂不堪,已成布条飞舞(图10)。猕猴在他身前,他拿着一个篾圈,正耍猴从环中穿过〔27〕。与周臣所画的一样,这正是一个弄猢狲的乞丐。由于人物尺寸要比周臣的小很多,所以也没有画得特别细致。比如,弄猴人背着的筐、手中拿着的令箭小旗和小刀在这里没有。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破烂的衣服意味着这是一个乞丐。在画里上千个人物中,只有这个弄猢狲者身穿破烂的百衲衣,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乞丐。
有趣的是,尽管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中只有一个耍猴乞丐,但到了乾隆年间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乞丐一下增加了好几个。清院本一般认为是在仇英本和张择端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增添改编而成。画中也出现了耍猴的人,不过这回一下出现两位。一位在城门口,正牵着猴儿往内城闹市走。耍猴人这次不但衣衫整齐,耍猴工具齐备,连猴儿也身穿红色小衣。另一位在城内,同样衣帽整齐,身边还带着助手—一位肩扛长杆的青年男子,这长杆应该就是耍猴时让猴儿攀爬的。这两位耍猴人的经济地位看起来比周臣和仇英版本中的同行提高不少,已经很难用乞丐来称呼他了,而应称他们为“艺人”。实际上,包括猴戏在内的这类娱乐大众的艺人,作为一种职业工作者,本就介于乞丐与城市平民之间,可上可下。标准乞丐全部出现在闹市区,共有几种形象。第一种是身体健全的中青年乞丐,拄着棍,身穿下摆破碎的百衲衣或补丁很多的棉衣,打着绑腿,或挎着小篮,或挎着水罐,有的还背着草席。第二种是夫妻乞丐。年老的男乞丐是盲人,拄着短竹杖,他的妻子挎着篮子、搀扶着他在向人们乞讨。第三种乞丐牵着狗,应该是说明他是盲人。第四种乞丐是一家三口,老年的夫妻带着年轻的女儿。他们跪在路边,身前放着碗,在向行人乞讨(图11)。
是不是可以认为,乾隆年间院本《清明上河图》在以晚明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为参照的基础上,还有其他的图像来源?清院本中,耍猴人摆脱了乞丐的身份,成为活动在城市中的流动艺人。画中还有一位弹琵琶的盲艺人,坐在驴上,由一位年轻人牵着在大街上行走。这个弹琵琶的盲艺人形象我们并不陌生,在吴伟款《流民图》、石嵉《流民图》中,弹琵琶、拨三弦的盲艺人反复出现。只不过在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他们和耍猴人一样,成为城市中的流动艺人一分子。除此之外,《流民图》中那些算卦、卖药的人,也都在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出现并获得了更体面的职业身份。清院本中还出现了一个4人组的女子乐队,斜背着鼓,手拿拍板,边走边唱。领头的女性胸前衣服中还包着一个婴儿。这种职业化的女性,我们也可在所谓的“流民图”中看到。
“流民图”与仿本《清明上河图》之所以在人物形象上会有联系,是因为它们的主题都与市场和城市有关。明代的城市图,除了《清明上河图》之外,还有几件重要作品,分别是《南都繁会图》《皇都积胜图》《上元灯彩图》等〔28〕。从形式上来看,《南都繁会图》《皇都积胜图》和《清明上河图》更类似。首先场景辽阔,几乎是城市的一个横向切片,从整体布局来看,都跨越了郊外和乡村、繁华的内城和皇家苑囿。《上元灯彩图》则视野更集中,聚焦于热闹非凡的元宵灯市。从内容来看,《皇都积胜图》画了4个乞食乞丐、一群表演马戏的艺人和一对卖唱的艺人夫妇,丈夫似乎为盲人。《上元灯彩图》在一个酒楼门口画了2个乞丐(图12)。而《南都繁会图》中则都没有。如果说仿本《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长卷是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景观,囊括了各种建筑、各种风景、各种阶层、各种活动,而周臣、石嵉的“流民图”只是城市的一个小小局部—下层街市的景观,那么明代还有其他几件绘画恰好填补了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
五、太平风会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人朱玉款《太平风会图》长卷,高26厘米,长790厘米(图13)。将近8米的画面所描绘的全都是城市中的各色人物。从挑担、推车的市井人物开始,到挑担、驮口袋的街市人物结束,数百个人几乎全都是城市商业区的各种职业人群。可以相信目前的画面是完整的,因为从画卷开始处的挑担者乃是从右方的画外走向画里,而画卷结尾处的挑担者恰好相反,乃是从左方的画外向画卷前段走。仿佛是一整条商业街的景观,特别像是《清明上河图》中间的那条大街。画中只有人物,没有任何背景。人物虽多,但却大致按照上下各两条线路行进。倘若将之与仇英版以及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仔细比较的话,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的人物形象,同时又很难说清楚彼此之间的具体关系。简单而言,《太平风会图》中描绘了百余种不同的职业身份,许多都可以在仇英版以及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找到。
《太平风会图》虽然落有元末苏州昆山画家朱玉的款印,但应属于伪托。画面中骑马的官员戴着明式的乌纱帽即为时代的明证。尽管画前有16世纪前期苏州人吴奕的引首,画后有昆山顾潜(1471—1534)、苏州王穉登(1535—1612)、钱谷(1508—1572)的题跋,但这些证据其实不可靠。从书法上看均与这些吴中文人的真迹有差别。关键是,这三段题跋中有两段其实是从朱玉《揭钵图》卷后的题跋真迹抄录、改编而来,不但文字、书风全仿,连题跋落款也完全一样〔29〕。画的名字“太平风会”来自卷首吴奕的隶书引首。吴奕在吴中以篆书之名,并非引首题字的水平。因此可知从画面中从朱玉的款印到引首、题跋,这全套证据其实都是出于后人的作伪。
画面中的人物虽多,但希望通过人物的衣着、发饰以及物品去判断这幅画的大致时代并不容易。画中许多人戴着俗称“瓜皮帽”的小帽,这也是典型的明代百姓服饰。画中有4位女性头上可见尖锥形的䯼髻。尤其是两位骑马的女子,䯼髻高而尖耸。根据明人的记载,明代女性䯼髻到万历以后变得逐渐扁平,因此这种高耸的䯼髻,尽管在画面上有某种夸张,但可能体现出较早的作风〔30〕。存世的明代绘画中,较为接近画中䯼髻的是约绘制于永乐年间的《真武灵验图册》,其中可见到民间女性的䯼髻。而绘制于1485年前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也可看到不少的宫廷女性的高耸䯼髻。《太平风会图》的䯼髻骑马女子不是常见的景观,其中一位身穿一件背心,称作“比甲”,方领带扣。一般认为,女性穿比甲是明代中期才流行开来。尽管从服饰来断代会存在各种偶然因素,但综合各种因素,大致可以说,《太平风会图》是明代中期,约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前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它很可能会与周臣的街市人物时代相去不远,而且很可能要早于仇英,比存世的任何一本仇英款《清明上河图》都要早。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幅画便可以告诉我们,在16世纪后期仿本《清明上河图》大量出现之前,明代人对于城市和市井的图绘已经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已经有了一套独特的手法。
进一步的对比或许能提出更有趣的问题。朱玉卷在卷首第一段,画了一顶出行的轿子,轿子由两人抬,轿顶四角缠绕着红色的飘带,这应是一顶迎亲花轿。轿子前有一人骑白马,这人头戴元式笠帽,应是新郎。前面有鼓吹3排,第1排为腰鼓和拍板,第2排有2人敲鼓,第3排有2人吹笛。最前面引路的2位童子手提灯笼装的东西。轿子后面有一群骑马的女性,共4人。她们后面紧跟着1位挑担者和1位手持短棍的童子。挑夫所挑,是一个茶炉和一个大竹编盒。这个由17人组成的花轿队伍,在明仿本《清明上河图》画卷开头处也可看到。后者也都有头戴元式笠帽的骑马人,花轿也相似,也都是笛板齐鸣,鼓乐喧天。

图15 [明]张宏 杂技游戏图卷(局部)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朱玉本中还有许多的人物,在仿本《清明上河图》中以另外的面貌出现。譬如赶大车的人和赶猪群的人。十分特别的一段在画卷中间。这一段表现了各种木工,囊括大木作(做斗拱、梁架)和小木作(画彩画、打家具)。仿本《清明上河图》中也有构屋的场面。和朱玉卷类似,也有用大锯制作板材的。朱玉卷接下来有一段集中了看相、算星命(子平五星课命,算八字)、药摊。而在《清明》卷中,药室、算命也频频出现。
当脑海中同时有朱玉款《太平风会图》和仿本《清明上河图》的时候,两幅画中的许多场景都可找到相互关联。后者中出现了不少市招文字,前者也有不少。如辟邪的道士竹竿上挂着字条,上写“书符咒水驱邪除怪”。代人写文书的老儒伞盖上写着“作诗文写立轴”。甚至于脚夫推车,货物上写着“棉花二百斤”。驴背上的货物则写着“花椒”。有一些场景,前者要比后者丰富得多。比如画中有一段席地吃饭的景象。一帮人看似农人,因为有一些农具,如铲子、杈子、石碾,尤其是有一个打麦子的专用工具“连耞”〔31〕。然而一人正用弓箭瞄准这个连枷挂着的草帽,另一人则挥舞铲子。他们虽是农人,但有酒有肉,伙食相当好。有数人已经醉酒,更有人耍起酒疯。这些人应是职业化的农人,他们收完庄稼之后来到城市,寻找其他的雇佣机会。画中职业身份众多,不少女性也出来工作。醉酒农人旁边,有数位正从事纺织中“经丝”这道程序的女性。另还有两位女子在洗衣和捣衣。
这些可能都属于新兴的城市雇佣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多从乡村来到城里,为数不少。譬如,经丝场景的下面,画着一个赶牛的场景。一壮年男子背着犁在前面领路,后面一童子骑黄牛。再后面有一青年人赶着两头黄牛。他身上还背着一个工具,应是一个方耙,是耕地时犁的配套〔32〕。在背犁人腰间,还悬挂这一个奇怪的物品。这应就是“瓠种”,由瓠瓜制成,里面放种子,是用来耕地时播种用的〔33〕。显然,这是一个寻找雇主的耕地团队。
画面的丰富场景层出不穷。有许多单个或数人成组的人物,分属不同行当。有货郎卖货,货郎架与仿本《清明上河图》中非常相似。有屠户卖猪肉,有人卖浆,有人磨镜子,有人磨剪刀,有人卖丝绸,有人卖草席,有人耍一头削尖的长棍。有狗贩(有狗跟随,衣服呈类似乞丐的褴褛状),有木偶表演团队。骑马的文官穿街而过。最有趣的场面是画中打架的两对男女。看起来这是两对夫妇之间的战争。男人对男人,撸胳膊挽袖子;女人对女人,抓脸挠头,破口大骂。相比起仿本《清明上河图》中的当街打架,这里要真实且有趣许多。猴戏也在画中出现。猴儿爬上长杆,倒吊在秋千上玩杂耍。
值得注意的是画中的一些场景在仿本《清明上河图》中没有,却出现在清院本中。比如醉酒呕吐的人,比如从驴背上摔下的人。还有狗贩,他肩挑一条狗,还用一条绳子状的东西吸引狗尾随。清院本中有类似的狗贩。在仇英款的仿本《清明上河图》中,只看得到有两人抬一条狗,不知是否狗贩。在《太平风会图》卷尾,画了一人蹲下身系绑腿,相似的形象也出现的清院本中。画中还画有一人手举一件长袍,袍子的袖口和下摆似乎装饰有长毛。这可能是一件皮衣。这个人或者是裁缝,或者从事货卖旧衣的营生〔34〕。

图16 [元]王振鹏(款) 江山揽胜图卷(局部) 48.7cm×950cm 绢本墨笔 私人收藏
相比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太平风会图》中出现了更多的乞丐和盲艺人。在耍尖棍的人旁边,有一组4个乞丐:一个少年,手提瓦罐,衣衫褴褛,呈布条状。一人拿着打狗棍。还有一人有严重残疾,只能躬身行走。这4人是典型的城市乞丐(图14)。此外,狗贩的装束也比较破烂,在袖口和衣摆处有残破,但总体比前几位乞丐好。此外又有3个盲艺人一组,分别是琴、三弦、琵琶,由小童搀扶引路。另还有一小童领一抱琵琶的盲艺人。这几位不是乞丐,而属于职业卖艺人。
乞丐和艺人把周臣《流民图》、朱玉款《太平风会图》、仇英款《清明上河图》、清院本《清明上河图》连为一个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周臣所画的市井乞丐诸色人等,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也可以被视为仿本《清明上河图》出现之前,一种对城市景观的表现。
《太平风会图》这种无背景的城市景观,似乎一直到明末也有延续。同样是苏州人的张宏于1638年画了一幅《杂技游戏图》(图15),四米半的尺幅内画了119个各色市井人物,有许多和《太平风会图》《清明上河图》《流民图》相同身份的人物。其主题也是市井中的下层职业人物,如僧人、猴戏、卖药、打鼓、医人、卖鱼虾老鳖、盲人乐师、盲人算命、说书、斗羊、纸牌、磨镜、烧铜、走索等等,以及体貌特别的人,如盲人、驼背、瘫子、侏儒、秃子、癞子等等。而且同样也有打架场面。这里是两位老妇当街厮打,头面首饰掉了一地。这种女性争吵打架的场面,我们在《太平风会图》中已经见识过了。画里还有一段类似“闹学堂”场景,教书先生在打盹,调皮的学童闹翻天,有人竟胆敢给睡着的先生画鬼脸。这会让我们想起在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一个学堂景象。乞丐在画中也看得到。画中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扛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悬挂着好几只老鼠,这是卖鼠药的乞丐。画卷一开头有一组人,主体是扛着两根竹枝的一对男女,男子戴上口髯,前面有一个手拿小旗者。显然,这是一个演滑稽戏的群体,戴口髯男子的衣服上看得到好几个补丁。这两人可能是在“跳灶王”,即腊月里街市乞丐们经常从事的活动,用来沿门讨钱〔35〕。打花鼓也是一常见的市井表演。表演者是两位女性,年纪轻的女子表演花鼓,年纪稍长的怀中搂着孩子,手拿一面锣伴奏。她身上的衣服也可看到好几个补丁,虽然比卖鼠药的乞丐要好很多,但也可看成是介于乞丐和平民职业人之间的角色。职业化的女性,我们在画面里能看到不少,值得注意的是一老一少两位女性,年轻的女子搂着老者的肩头,很亲昵。年老女性背着一个包袱,手拿一个形似大棉花糖一样的东西。这个年老的女性,应该与周臣画中一样,是一个“卖婆”。
按照对城市景观描绘的不同复杂度,我们可以在所谓的《流民图》《太平风会图》《清明上河图》《杂技游戏图》之间做出更细致的层级区分:
四等:周臣所画的市井人物和乞丐,以各种类型乞丐占多数,30人中有26人,占86.7%,社会等级最高的只到云游的僧道和卖婆,堪称是最底层的市井人物,反映出最底层的城市景观。与之类似的是石嵉、吴伟的“流民图”。
三等:张宏《杂技游戏图》中,人物的身份更多样,而且阶层更高。乞丐比例减少,在119人中,可归为乞丐的有9人,只占7.6%。除了有许多城市职业人,还有一些城市居民。比如说书者身旁聚集的人群,或者是围观走绳索表演的人群。社会地位最高的是几个戴着儒士方巾的观众。画面虽然没有背景,但可以视为一条街市的景象。
二等:《太平风会图》总共470人中〔36〕,可归为乞丐的只有5人,仅占1.06%。画中市场中的职业人越来越多,几乎各种职业都有,但没有一个固定店铺。在职业人以外,城市居民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更有身份比较高的红袍文官,以及不少戴蒙元式笠帽的人,还有戴䯼髻、穿比甲的骑马女性,她们社会等级应比较高,正在穿越由各色职业人组成的市井。
一等:最高等级的是仿本《清明上河图》。它们不仅给《太平风会图》这样的闹市增加了复杂的城市环境作为背景,而且把城市景观最大限度地扩大。闹市区以固定店铺为主,而不再是零散的摊点。不仅仅是闹市区,也包括若干繁华程度小的街区,还有僻静的城市居住区、富人区、郊区、乡野。最后,更增加了帝王宫苑。乞丐在仇英本中只有1人,在清院本中有13人,但无论是哪种图本,所画人数都以千计,乞丐的比例远在千分之几了。
这不同的层级,反映出视角的不断扩大,只有把它们视为一个有关城市的视觉话语的整体,才能见出这种城市图在明代的意义。不过,乞丐、艺人和市井,并不只与大城市有关。“城市图”这个概念似乎不完全准确。无论是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还是明清的仿本,都不只是城市,也画出了乡村。在张择端的版本中,乡村的比例还比较少,从卷首驮着木炭的驴队到农田灌溉一段,更像是城市郊区。明代的仿本,开头一段的乡村景象画得更丰富。《皇都积胜图》中,乡村占的比例也不小。还有一件长卷绘画,虽然描绘了不少艺人和买卖景象,但却描绘的是乡村,这就是传为王振鹏的《江山揽胜图》卷(私人收藏),被认为描绘的是天台山、瓯江、温州一带的山区、丘陵和江景〔37〕(图16)。长卷中画了两个面江背山的乡镇集市,有店面,也有流动的商贩和街头艺人。店面有染坊、食店、酒店、旅店、杂货店等。商贩和艺人则有货郎、相面摊、药摊、卖鼠药、说书、戏剧表演、杂技走索、打把势卖艺、卖唱盲艺人等等,而且也有乞丐,既有身体残疾,只能用双手撑地移动的乞丐,也有拄着单拐的乞丐。丰富的市井景物,使得研究者形容这幅画可以与《清明上河图》相媲美。比较一下这些街市人物,看起来确实与仇英本的《清明上河图》颇有近似之处。除了固定店面和流动商贩、艺人外,还有一些特殊场景可以相互比较,比如打架的人、迎亲的队伍、建造房屋的人、二层的酒楼、拉纤的人、寺庙进香等等。在《江山揽胜图》靠近卷尾的第二段乡镇集市里,在中心位置有一个亭子,里面有一口井。这看起来也呼应了《三才图会》中“市井图”的含义〔38〕。画中的集市,即便并不是乡村,但也并非大城市,画里看不到城楼、城墙,更像是中小型的乡镇〔39〕。商贩、艺人、乞丐就在这个乡镇背景里活动。这样一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传为吴伟的《流民图》和戴进款《升平村乐图》,所配的环境似乎是乡村,而不是都会。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游走,正是这些充满流动性的乞丐、艺人、商贩的特殊性所在,因为他们就代表着市井。